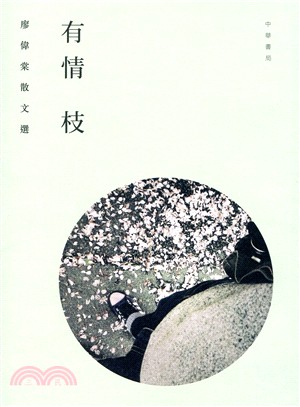商品簡介
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曾經獲得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創世紀詩刊五十周年詩歌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踪世界華文小說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度最佳藝術家(文學)等多個獎項,作品深受兩岸三地文壇和讀者歡迎。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
廖偉棠文字簡潔凝練,既富古典詩意,又具現代意象;散文內容豐富多姿,書中有懷念一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迷人風采,有對作家詩人三毛、商禽、馬驊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
廖偉棠還是一位旅行家、攝影師。本書帶領讀者雲遊四方,無論是文化名城還是邊遠小鎮,他都以極為細膩、充滿魅力的文字,使你沉浸在彼時彼地美麗的風景以及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中。
作者簡介
目次
一 初心與故夢
2 三毛,自由最初的滋味
8 十年胭脂無顏色——追念張國榮與梅豔芳
14 我們躺著,唱著,年復一年
18 父之初(九篇)
40 刻在迷宮牆上的五個斷片——獻給迷宮之王:博爾赫斯
50 婚禮
58 北京,春天的醉歌行
68 仿《野草》三題
72 致旅行者一號——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74 寄夢中的阿蘭,羅伯—格里耶
78 河兩岸,永隔一江水
84 最最現實的離別——懷商禽先生
90 幽靈的藝術
96 向絕處斟酌自己
104 詩歌的識與救贖——回憶馬驊
116 遺像
二 雲遊和霧隱
122 巴黎攝魂記
129 拉卜楞聲色斷片
140 達摩山下,寫給達摩流浪者們
149 越南的隱秘與魔幻
164 那不勒斯,一隻黑犬
172 光澤,無意慰人——追念策蘭與阿西西
179 談論東方
184 裴路迦的煙和雲
190 巴塞隆納變形記
201 鞍囊裏還有青果——從哥爾多巴到塞維拉
209 秋俳句:北陸行腳
221 春與修羅
232 通往銀與金之道
238 甕中的細江英公
241 浪蕩子的利物浦
248 雅典與伊亞
253 斧柄失,求諸野
258 江城故事
264 火車開不往辛亥
269 山河壯麗,不值一提
274 倉央嘉措的兩個節點
279 回到北平
284 在浦台島寫俳句
288 雪人讀詩時
書摘/試閱
一 初心與故夢
三毛,自由最初的滋味
誰也沒想到這是王洛賓的像;白房子是老帥哥的紀念館。房子裹沒有一個遊客,玻璃櫃子裏是他的手稿、照像和零星遺物。最後幾個櫃子屬於她,三毛和王洛賓的往來書信,一九九○年。王洛賓為她寫的《等待——寄給死者的戀歌》,一九九一年。
兩個在我少年時代非常傳奇的名字,三毛、王洛賓,一下子讓我想起了許多。初識三毛,我和很多大陸、香港的同齡人一樣,都是在八十年代末,初中的時候,同伴同學女生都在讀瓊瑤,男生都在讀金庸和古龍,這時候要顯得與眾不同,你的選擇只有三毛。在選擇不多的流行讀物中,三毛是屬於另類的。我又比其他人稍微早一點知道三毛,我在小學的時候就看過一篇連環圖,是改編自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的第一篇〈沙漠中的飯店〉,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個細節是畫中的東方長髮美女(畫家想像的三毛)藏起來一罐剪成碎塊的豬肉乾說那是中國的藥,而那個金髮人鬍子則假裝病了叫嚷著要吃肉味的藥!
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的生活,幾乎是第一次在我眼前揭開了另一個世界:幸福的概念原來可以這樣詮釋——它是包括了冒險與漂泊的。之前第一本叫我對在路上」心動的,是松本零士的《銀河鐵道999》,但星野鐵郎的歷險太高遠、也太悲情,對於一個小學生來說純屬空想;而同時閱讀的三毛卻令人想像「人間」,這個詞應該是和「自由」緊密相連的。
當時我在廣東讀初中,八十年代末的社會,與自由弔詭地若即若離,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神層面爆發遠在北方,北京和合肥是兩個重鎮;而其庸俗的物質層面爆發則近在身邊,我們在廣東可以看到香港的電視、消費很多舶來物。北方的運動第一波,一九八六的學運我們還未曾接觸就已經被消滅。但第二波,一九八九卻把我和身邊幾個小朋友都捲入。那時候我已經讀完三毛,讀到柏楊那裹去了,《醜陋的中國人》 裹那些面孔與《撒哈拉的故事》裏那個天真率性的女子實在相去甚遠,可是我們在現實中國只能找到前者的對應物,三毛也成為了一個徹底的想像,就像《銀河鐵道999》裹的美黛兒一樣,對於掙扎於鬥爭中的鐵郎也遙不可及。
生命中第一次為自由的鬥爭慘烈失敗了,我不記得從靜坐的廣場撒離回家的兩個少年心裹唱的是什麼歌。生活又靜靜回復,很快是畢業禮——雖然成人禮已經以血的方式舉行過。我們辦了一個接一個的畢業晚會,總有文藝少女,披著大披肩,唱《橄欖樹》:「我的故鄉在遠方、遠方」……我們還留在我們的故鄉,這個我們眼中亟需變革的懵懂故鄉,但我開始用筆去描寫遠方。
是她讓我如此鮮活地懂得了自由的氣息,懂得了天涯海角對於一個寫作者的意義,她讓我們想像天涯。後來我知道不只是我,遠在哈爾濱、北京或者西北、西南的她或他,少年時都如此想像,什麼時候我也能如此上路呢?什麼時候我也能把路上的幽遠與悵惘寫成文字呢?
很快我們就從三毛走到了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孃》,走到井上靖的《敦煌》,一直走到凱魯亞克的《在路上》,浪遊文學最輝煌的頂峰展現在我眼前,十多年後才反思到:也許三毛就是六十年代西方嬉皮傳統的一個東方的簡略的迴聲。回憶中最後一個場面是香港的電視新聞突然插播死亡消息:《滾滾紅塵》、醫院、絲襪……家人澄清不是白殺,但怎麼可能不是呢?少年固執地想道,這樣一個傳奇,怎麼可能以別的平庸的方式來完結?作者的生命與創作竟然可以如此密切地糾纏在一起,發生在「身邊」的,三毛是第一個完美的演示。後來是顧城,是書一果的韓波、里爾克、策蘭……那時我已經多番思考過死亡,但仍然驚訝於一個寫作者最後的抗爭、最後的自決,面對必然來襲的虛無,自殺是唯一的抗議,如果我不能選擇死亡之外的自由,那我起碼可以選擇提前擁抱它。但是,這一切始終太早,對生者太殘忍。
想起她,我仍然不忍簡單地視之為一個流行作家,她只是以自身微弱的力量為我們演示了一番有限的自由,起碼告訴了紅塵中人也可以這麼猛烈地活、猛烈地死。我不知道當年翻爛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的少年們,當中是否有百分之一的人選擇了上路,是否有萬分之一的人選擇了寫作。但《橄欖樹》依舊不時在夜深為他們重新播放一次,那女子飄揚的披肩也依然在熱風中飄揚。
那個夏天的午後,離開王洛賓紀念館,出口處有一個男人在擺賣自己的著作:王洛賓傳,他是王洛賓的兒子。我們翻了一下書,寫得平平,不好意思地衝他報以歉意的微笑,他也一笑。我們向著葡萄谷外走去,在密林中回頭,看見他站到了門外,遠遠地看著我們。我想一九九○年的時候他應該就和現在的我一般大,他是王洛賓的兒子,也許還見過來新疆找王洛賓的三毛,他選擇了留在深谷中這個白房子裏,守著一屋子的傳奇。
十年胭脂無顏色——追念張國榮與梅豔芳
他們都在演粉絲眼中的自己,一個是惆儻任性少年遊,一個是身世伶俜薄命女,但現實中張國榮是抑鬱有痛的,唯以一躍求解脫,梅豔芳是敢愛敢恨的行動主義者,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救助自己認為應該救助的,即使後者傾國之重驟眼看來是一個歌伶無法承受。她的一生都是難以承受的重,但她以枯瘦之軀挺到了最後,到最後我們才知道,她能承受那是因為她並非一個歌伶。
關錦鵬導演無疑看出了兩者,所以在十二少的父親禁止他登台的時候,如花輕柔而決絕地提醒他該上台演出了,這是梅豔芳式的堅持;所以玩世不恭醉眼惺忪的十二少,每當絕望之際會猛然抱緊了不堪一握的情人身軀,憤懣如泣血,這是張國榮式的掙扎。張國榮實際是清高出世的,所以他有資格縱情;梅豔芳實際是咬牙入世的,所以她有資格淒怨。
苦命孩子早當家(我從小就熟知梅豔芳的苦命,我的薩克斯樂手五叔,曾認識荔園賣藝時代的梅豔芳姐妹,嘗與我慨歎彼時小兒女的艱難求存;而她突然大紅之時,小報又盡傳她吸毒和賣淫的謠言),在如花與十二少的關係中,更多的是地位上身處弱者的如花支持富家子十二少對抗命運追尋理想。我想現實裏,梅豔芳之於張國榮也是這麼一個姐姐的角色。今天放映會上看到導演關錦鵬說的一個內幕:當年梅關和張分屬兩家公司,梅豔芳向關錦鵬提出要張國榮演十二少,為了跨公司借角,梅主動去張的公司提出換角建議,就是借張來演一部電影,梅也為張的公司演回一部電影。正是梅豔芳的果敢操持,才有今天《胭脂扣》雙星的完美輝映。
他們倆,之於上個世紀末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只有「傳奇」二字能夠形容。或者已經成為傳說,就像八十年代樂隊Raidas的《傳說》(林夕填詞)所唱:「重合劍釵修補破鏡,只有寄情戲曲與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變成絕世傳奇事。」一身如戲曲傳奇裏走出來的張國榮梅豔芳,在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不亞於《胭脂扣》裏那女鬼和倖存的落魄少爺與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梅豔芳是屬於小明星、白駒榮那個時代的,張國榮更早,是八旗遺少與舊上海新感覺派才子的組合。但是他們努力演出,強作百變形象、紫醉金迷,終於成為所謂黃金時代的八十年代香港的象徵,直到他們不願意演下去。
同時代現實中的譚詠麟、成龍等「豁達」者是不會自殺的,自殺的只有孤介之人,「人人都有一張小板凳,我的不帶入二十一世紀」失蹤的民謠歌手胡嗎個曾經這樣宣稱。張國榮和梅豔芳就是不願意把自己帶入二十一世紀的人,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沒有傳奇的世紀。於是在一個非常恰到好處的幕布(由SARS的陰霾組成)前面,他決定親身演繹最後的傳奇。
十年前的今天,我恰巧從北京返港,正在英國文化協會與詩人楊煉談論一個被SARS擱淺的詩歌計劃,電視正播放著香港將宣佈成為疫埠的消息,突然電話響,一個女生打來的:「張國榮跳樓死咗。不是愚人節玩笑。」——我想大多數香港人都是這樣知道這個消息的。看著《胭脂扣》的時候,我不禁想,梅豔芳那天聽到張國榮的消息是怎麼想的呢?是否心如刀割,還是淒然一笑?我想她肯定比我們更早猜到這個結局。
他們的相繼棄世,宣佈了紫醉金迷的香港的徹底告終——他們逝去,象徵著那個胭脂一樣俗豔浮華的盛世真的逝去了。二〇〇三年,舊殖民地的最後一絲暮光,在現實的赤裸追擊下化為泡影,此後才是香港人建立真正的香港認同的開始,不是通過傳奇,而是通過具體而微的現實覺悟。
看完《胭脂扣》,我竟然淚流滿面,並不是為了電影本身,就為這一對璧人的一顰一笑。雖說今天是悼念張國榮,但戲中的他卻總讓我微微一笑,他的慵懶、他的靡亂、他的意欲顛倒眾生……讓人陶醉之餘頓生憐憫,憐憫之餘又反覺釋然:這個人,是得其所歸的。而梅豔芳,「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幾乎是一開口一低首就讓人鼻酸。想起我第一次被她感動,是比《胭脂扣》還遙遠的一九八五年,十歲的我聽二十二歲的她唱中年情懷的《似水流年》,初識愁滋味,現在回想依然感歎這麼一個初涉舞台的少女怎能如許滄桑。
張國榮,我最喜歡的還是寧采臣的少年遊,一曲《倩女幽魂》是我某年的手機鈴聲。那一年我寫道:「那個永遠趕著路的書生,曾是牡丹纏蛇,現在是紅水拍土……雨水畫著花臉下台。此岸的病已經遙遠,無礙他清白。」那就是二〇〇三年,「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
二〇一三年四月
我們躺著,唱著,年復一年
「我們躺著,唱著,年復一年。」那是卡夫卡致密倫娜的信中的一句話,我曾把它引用在我的一本詩集前面作為題辭。
這平淡,也許有刻意抑制的自我感動的因素在裏面。實在是這樣啊,我們就是這樣躺著,唱著,年復一年的,然後慢慢的,我們是有點為自己感動了。但是,我們不這樣又能怎樣呢?我們唱著唱著就自然的唱了下去,並索性躺著不起來了。就像哈雷姆特王子那樣,他剛才還在高呼:「這是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倒楣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呢,現在他卻哭了,為了那躺在五潯深水底的鬼魂,為了那玩弄他扣子的父親。
這不是無奈,我們多麼自由啊,輕風常常把我們頭頂上空飄揚的白床單吹揚起來,就像海船上的旗幟,有人甚至輕輕的吹起了口哨,開那些岸上的水手的玩笑。這也不是冷靜,有人說:「太多的年輕人習慣了被忽視。」是的,這是好的,我們甚至暗地驕傲呢,但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躺著。
聽,又有人吹口哨了,並不是一首憂傷的曲子,但令人憂傷。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巨大的平原,遠方一朵朵碩大的雲低低的飄過來,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我們偶爾作夢,夢見黃昏的稻田。
對,寫不寫都無所謂了,但是寫著的時候,還是有一股莫大的快樂從心中揚起、鼓脹起來,潔白、飽滿,就像在受難日隨著小教堂鐘聲升空的氣球。我們往下一看,就看見另一些我們橫七豎八的躺在草地上,剛下過雨,水窪像鏡子,說話,閃光。
我願永遠躺在一棵白樺樹下,永遠
嘗著白樺葉子的苦味,寒冬日子的苦味。
嘗著俄羅斯的眼淚,雨雪的泥濘,
如果一個人在泥濘中死去,
那麼我們只能說:他是死於幸運。
那些跪在燒毁的教堂中
仰望雪花飄降的人們;那些在白樺樹下
拾起母親的鏡子的人們;
那些在冰水中洗蘋果的人們;
那些圍看節日輪舞,無故哭泣的人們。
我願永遠為他們祝禱,
歌聲起揚,像受難日升空的氣球。
在冬季的盡頭,小溪縱橫,靜靜流淌,
暴雨過後,一匹老馬在溪旁飲水。
歌——聲——起——揚——
啊,俄羅斯!
我願永遠躺在一棵白樺樹下,永遠
嘗著你白樺葉子的苦味,寒冬日子的苦味。
這是我一九九八年春寫的詩,寫給塔可夫斯基的詩。
我如此感傷,一代風華正茂的詩歌少年們又要嘲笑我了。但我們還是躺著吧,唱著吧。……索德格朗、阿赫瑪托娃,死在集中營裏的密倫娜,我長憶記,你們宛若希臘女像柱,白玉石上流轉著榮光。
於是又是百年、千年。拋出去的漂流瓶被海水洗得褪色了,但畢竟拋了出去;當我們貼緊我們愛人的心臓,我們聽到了沉默的賽壬——也許是靜夜裏墨水滴落,在宣紙上滲化。我們寫作,欲書花葉寄朝雲——別無它求:
白雲下,比薩的天空
在這一切美之中應當有結果。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