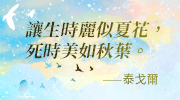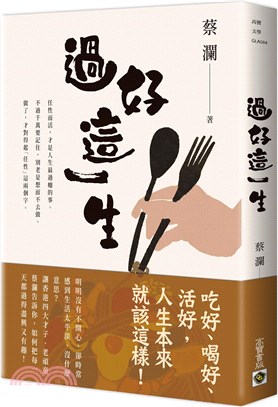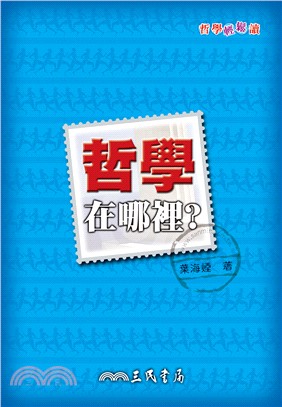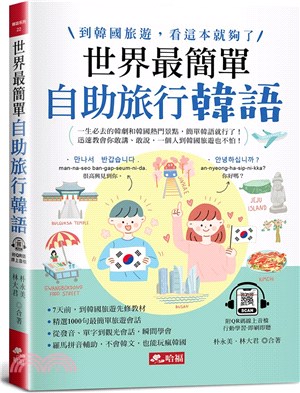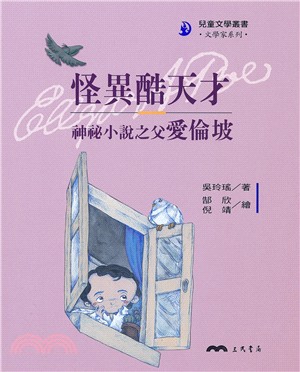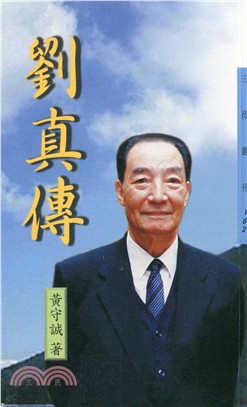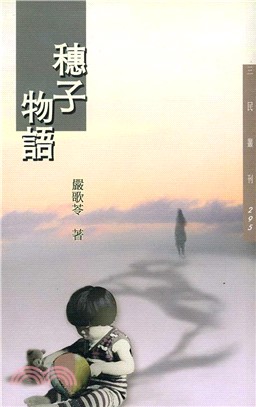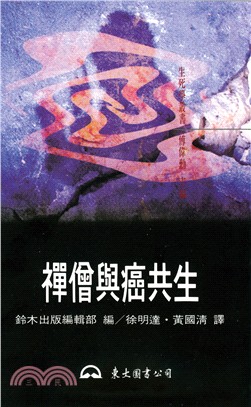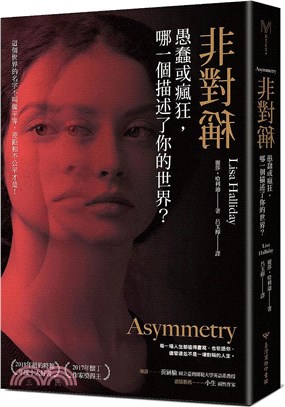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35元
商品簡介
一個軍人集團的裂變,一個少為人知的五四。
五四不僅是思想史上的標誌事件,還是政治史中的一個巨大事件場域。學生運動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洶湧的,是那個時代紛繁複雜的軍閥政治──各個軍閥和政壇派系都在搗鼓五四,而五四最終對於民國政治的走向,起著扳道工的作用。
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關係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為人忽視了,好像五四期間,這些政壇上的要角,全體失蹤了一樣。另外,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麼回事?怎麼動員的,怎麼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係,跟軍警又是怎麼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塗賬。
其實,五四對於中國政治的走向,不僅在直皖之爭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進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國最終走到今天,原因其實很多,五四絕非根本性的推動力。
作者簡介
浙江上虞人,長於北大荒。出生趕上鳴放,故曰:鳴。竇文濤評道:一出生就是右派。年幼時最大的理想是做圖書管理員,好每天有書看。及長,幻想當作家,變成文學青年。一輩子養過豬,做過獸醫,大學學的是農業機械,最後誤打誤撞,成了大學教歷史的老師,眾人眼中的學者。一生坎坷無數,碰壁無數,頭撞南牆不回頭,不是牆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長,從黑板報算起,寫過的文字無數,黑板報都擦了,小說都燒了,所謂的學術文字和隨筆評論,留下來的比較多,有些變成鉛字,好像有十幾本了,均遺憾多多。年過五十,沒有長進,再活五十年也許能好些。
其著作《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獲選南方閱讀盛典最受關注年度圖書(非文學類)、新浪中國好書榜、中國國家圖書館給高級幹部的重點推薦書目。又著有《辛亥:搖晃的中國》,寫盡大變革中的複雜國民性,解讀百年中國的激進之路。
名人/編輯推薦
易中天:張鳴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歡的──有思想,有見地,有學問,無官腔,十分好讀。
王學泰:張鳴的文章很好讀,很好看,更重要的是他很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很有見地。張鳴很多很小的文章,但揭示的問題卻很深刻。看他的書,可以使我開拓心胸,開拓眼界。
李 零:讀張鳴的文章既可以作輕鬆的享受,也可以從裡面學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識,可以說是讀史的捷徑。
丁 東:我覺得在大學裡張鳴是比較稀有的教授,民國時像他這樣的教授並不稀有,在當今大學裡,卻是太缺也太少了。
秦 暉:張鳴用材料和邏輯把很多問題講得很清楚,事實和邏輯結合起來就可以說清楚很多問題,是很有說服力的。
陳丹青:我們能不能找到真的歷史?現在有學者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在做這個事情,就是告訴你們,你們知道的這些事情在當時不是這樣的。張鳴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吳 思:看透槍桿子,瞭解鋤把子,張鳴抓住了這兩個要點,中國歷史的真相就能說個八九不離十了。我對他的理解,有時候也經常是我對我自己的理解。
徐慶全:幸運的是總有一些歷史書告訴我們一些道理,告訴我們怎樣認識社會,怎麼從歷史出發來認識現在的社會,張鳴的書也罷,吳思的書也罷,李零的書也罷,意義就在這。
解璽璋:我覺得張鳴老師很好打交道,我們很歡迎像張鳴老師這樣的學者給我們報紙和雜誌撰稿。我覺得學者應該和媒體有這樣互動的關係。
梁文道:張鳴寫史的方法像唐德剛,他的文筆是恣肆汪洋的、帶評夾敘的,非常好。
序
前言
我為什麼會研究起五四來
我為什麼會研究起五四來?這的確是個需要追問的問題。雖然說,我這個人研究歷史,或者說琢磨歷史,沒有科班出身的人那麼多界限,經常在晚清和民國之間跳來跳去,東撈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條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這種野路子出來的人,沒有家法,也就沒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對於五四,我卻一直沒有熱情,相關的史料也摸過一點,但興趣就是提不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著一個成見,認為五四跟太平天國一樣,下手的人太多,大魚早都撈沒了。
事情的轉機在二○○五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學期的課,每周一次,時間空得很,因此跟那裡的有關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紀》雜誌的編輯黎耀強先生。等我回大陸之後,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不知怎麼想起要找寫五四的稿子。然後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勸誘我寫五四。我說,你就是喜歡在大陸找人,大陸史學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幾個,怎麼會找到我的頭上?他說,別的人路數我都熟悉,能寫成什麼樣子,我現在就可以估計出來,唯獨你可以寫個跟別人筆下不一樣的五四出來。這麼一來二去,人都是喜歡被恭維的,慢慢就動了心,開始認真摸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摸了一陣之後,我發現,別看五四研究者甚眾,著述甚夥,但打周策縱、彭明起,大家關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後就是文學,說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幾位。即使寫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縱和彭明,也較少涉及這場政治運動的政治關係。好像只有臺灣的呂芳上,談到了五四跟國民黨的關係。但是,跟五四關係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為人忽視了,好像五四期間,這些政壇上的要角,全體失蹤了一樣。另外,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麼回事?怎麼動員的,怎麼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係,跟軍警又是怎麼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塗賬。
所以,我興趣來了,感覺還是有空子可鑽,有魚可撈的。
等到我下決心,真刀實槍開始鑽空子或者說撈魚的時候,發現事情遠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光資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還好,一些喜歡歷史的學生,幫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練,還是得你自己,一點點做。心情時好時壞,幹勁時小時大。就這樣,陸陸續續做了四年,直到二○○九年歲末,才初步有了眉目。
這期間,經歷了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熱,好在民間還是小熱了一回。大概有些熱心人痛感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消亡,傳統主義者要回歸傳統,制禮作樂,自由主義者要尋找歷史資源,建構中國式的憲政理論。大家回顧歷史,翻庫倒貨,把壞賬都算在了五四頭上。我正在看這方面的史料,雖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現在的文化狀況,其實賴不到多少在五四頭上。余英時先生說過,他跟陳獨秀和胡適先生是同鄉,「並且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我在離陳獨秀的出生地(懷寧)只有六七英里遠的一個小村住了八年(一九三七~一九四五)。陳獨秀我只聽說過一次,那是指責他──後來我發現這指責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我也曾在鄰縣桐城住了一年(一九四五~一九四六),桐城派文學已遭五四新文學的領袖們,特別是錢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批判,但在那裡我仍被鼓勵用古文寫散文和詩歌。直到一九四六年我回到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瀋陽這些大城市,我才開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論的影響。在戰後的幾年(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就我的記憶所及,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反偶像崇拜的反傳統主義都沒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經常困惑,在一九四九年前,五四運動或者馬克思主義總體上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有多大。」 其實,多少瞭解一點五四以後的歷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或者確切地說列寧主義,或者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其實不是通過五四,而是通過後來的革命發生的作用。但這種革命能夠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說,即使沒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樣有這樣的結果。十月革命後,共產主義革命延伸到落後國家,是一種趨勢,很多沒有發生類似五四運動的國家,一樣發生了革命。五四對於後來的革命,僅僅是說部分地催生出一點「左傾」的意向,即使這個意向,也受到另一種意向,全盤西化的平衡。最終革命鬧起來,而且成功,中間有著太多的因素,五四這根火柴跟後面的燎原大火之間,不存在對應的因果關係。不管怎麼說,中國化的列寧主義已經通過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系列群眾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從結構上改變了。最大的變化是,知書達理的精英,幾乎被掃蕩乾淨,剩餘的也斯文掃地。讓一九四九年前的余英時先生寫古文的農村環境,如果不能說完全蕩然無存,也所存無幾。中國社會,讀過「老書」(某些傳統猶存的農村,對文言文的說法)的人,已經所剩無幾,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孑孓無存。嚴格地講,儘管五四後白話文的教育開始推行,但一九四九年之前受教育的人,還都是讀過老書的。令傳統真正失落的,還是革命和後來的政治運動。
當然,儘管在有些人後來看來,五四運動儘管作為政治事件,對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種干擾,但這場政治運動,對於教育和文化的改變,其實相當的大。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儘管反對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學生喜歡,但畢竟是一場沒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戲。只是到了運動之後,這場文化運動聲音才被放大出來。政治運動過後,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學,才成了氣候。教育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造,白話文被學校接受。中國的大學,也就是在五四之後,才真正像個樣子。西式的學科分類體系,五四之後,才算真正在中國紮根。五四運動過後,當時中國的教育家蔡元培、蔣夢麟,都曾擔心獲得勝利的學生,會因此而心浮氣躁,荒廢了學業,轉而投身政治。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樣的學生是有的,而且數量不少,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家,無論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參加運動的學生還是回到了書齋,或者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軌道(曹汝霖後來的續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中國的大學,因為這些追求學問的人,沿著蔡元培開創改革的道路,越走越遠,蔡元培之後的教育家,無論梅貽琦還是蔣夢麟還是張伯苓,甚至黃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實論教育的創新和實踐,貢獻都比蔡元培的貢獻要大得多。
說也奇怪,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此前在新文化運動中追求個性自由和解放的學生,就會自動放棄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貨,將不肯服從的商人的自由剝奪,逼他們交出貨物,不服從則抓起來戴高帽子遊街。對他們來說,這樣做,並沒有心理上的障礙。因為一個是小我,一個是大我,後者事關民族大義。運動過後,一部分從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樣是為了國家和民族解放,放棄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實際上是基於新文化運動同樣的理由,全盤接受另一種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後的中國政局,西化和激進,成了主基調。即使國民黨上臺,一個不喜歡五四的半傳統主義者蔣介石當家,這個趨勢也沒有停止。襲承打倒孔家店傳統的學生,在孔府門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子見南子」,孔家人告狀告到蔣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沒有把支持演戲的曲阜師範的校長怎麼樣了。受到行政院長汪精衛支持的衛生部長,居然下令廢止中醫,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呼籲落在實處。逼得全國的中醫團結一致,鬧起來一場大的群眾運動,才算讓衛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實際上,民國時期中醫一直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況。學界的傳統主義者,陳寅恪、錢穆、馬一浮等人,靠著自身的學問,和國府中蔣介石的支持,才在國學的名目下掙得了一席之地。但就總體而言,學界的天下,依然西風獵獵,包括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化。只是,即使最激進的西化論者,也沒法在學術和教學過程中,真的把傳統?棄。
這樣的五四新傳統,在革命中和革命後的中國,其實蕩然無存。弔詭的是,革命後的大陸,年年都紀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實根本就沒有蹤影。不僅德先生、賽先生不見了,連新文化新文學也沒剩下什麼。當年新文學的健將,不是三緘其口,就是想說也說不出什麼來。而在國民黨的臺灣,五四的地位很低,沒什麼紀念,但那裡五四的新傳統卻還在。當然,五四之前的老傳統,也在。現在的人們動輒談論臺灣的雷震的遭遇,欷歔不已。但是試想一下,這個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陸,命運將會怎樣?
五四運動的發生,國人委實有點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日本的乘虛而入,後來也不至於有山東問題。當然,也正是因為一戰,中國才有了參戰之爭,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協約國一邊,最終為中國贏得了戰勝國的名義,也為自己贏得了一塊大勳章,但是,恰因為這空頭的勝利,讓國人興奮不已,結果到了巴黎開會,才發現自己原來還是原來的那塊砧板上的肉。所謂戰勝國,無非擔了空名。由熱及冷的落差,引起國人的大憤怒。自我檢討的結果,段祺瑞集團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過──當然,的確也有可罪之處。五四運動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卻給了直系一個機會,因此他們加入運動的合唱,最終導致你未唱罷我登場。北洋軍閥分裂,直皖開戰,皖系倒臺。
在民族主義的喧囂面前,運動走向勝利,為此付出代價的,不僅僅是幾位留學日本的文官。同樣是民族主義的喧囂,也導致了輿論和青年向左轉。就那麼巧,運動的溫度還沒有降下來,這邊蘇維埃俄國站穩了腳跟,想要尋求突破,打破孤立,於是接連發表兩次對華宣言,宣稱要放棄一切在華特權,而且要把沙俄時代從中國掠去的一切還給中國(掠去的實在太多了)。這樣令國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會上的屈辱,恰好形成過於鮮明的對照。連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孫中山、陳炯明甚至吳佩孚都一時難以抵擋誘惑,更何況一腔委屈的青年學生?五四過後,新文化運動並沒有停下腳步,出於群眾運動的緣故,轉向了社會改造。我們看到,無論教授還是學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層。教授做俗文化、底層文化的研究。而學生則從平民演講,走到平民夜校。進而進行社會改造的實驗,引進新村主義,辦工讀互助團,甚至給自己設計一個烏托邦的菜園子。這樣的嘗試,不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輩的引導,而且連北大校長蔡元培也給予支持。
就這樣,五四對於中國政治的走向,不僅在直皖之爭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進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國最終走到今天,原因其實很多,五四絕非根本性的推動力。也可以說,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卻沒什麼過錯,說到底,自古以來,只要國家有了這樣危難(至少當時人認為,山東丟給了日本,中國也就亡了。他們當時忘記了,山東在日本人手裡,已經有好幾年了),學生都會這樣做的。五四人的榜樣,就是北宋末年起來抗爭的太學生,這些太學生的領袖陳東,經常被五四青年在遊行的時候抬出來自況。他們的精神,古代時稱之為什麼,實在不好說,而在五四時期和現在,人們稱之為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個有魅力的東西,不僅軍閥的政爭,誰占了民族主義的制高點誰就勝利,就連後來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推行共產主義革命,民族主義也是契機和動力。儘管在歐洲,共產主義者是沒有祖國的。可是在中國,一切都不一樣了。最終,民族主義和社會改造的結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國的共產主義紅色革命。
當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遺憾。五四期間上海十幾萬工人的罷工,我明知道不是由於學生鼓動的結果。而且,我還看到許多學生勸說工人不要罷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響在滬的西方人生活的電車、電話電報以及鐵路工人的罷工,是學生特別不希望的。 雖然,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上海的幫會正在分化整合過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卻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幫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層次之分,但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在幫,雖然分屬各個不同的幫夥,但不在幫就很難立足。事實上,五四之後,中共開展工人運動,還是得借助幫會的幫助,否則工作就難以開展。我也在五四期間籌備工會的露臉名單上,看到了諸如聞蘭亭、盧達夫、劉聘卿這樣的知名幫會中人的名字。也在後來的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這些「工人團體」中發現後來露臉的何長發、王小福以及陸蘭亭、楊金榮、汪根生、李桂標這樣一些幫會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幫會裡同姓名的人。儘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麼一點。五四運動的健將之一,當時的北大學生張國燾,後來回憶說,當年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在上海,跟這些工人團體有過接觸。其中我提到的中華工業協會,他還在裡面做過短時間的總幹事。他說,這個協會號稱有過萬會員。「可是經我實地調查,所謂會員也不過是僅僅見諸名冊而已。實際上只是這個工廠有幾個人,那個工廠有幾個人,多數的會員甚至不知道是屬於哪個工廠的;也有很多會員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頭因同幫的關係介紹參加進來的。」 如果這些大名頭的工人組織,是幫會辦的,那麼,這些組織應該只是些招幌,真正組織動員工人機制是什麼?幫會在罷工中是怎樣工作的?海外漢學著作《上海罷工》中,提到國民黨統治時期,上海好些罷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後的組織者,也是杜月笙。那麼,當初五四的罷工,是不是就是此後一系列罷工的預演?
我也知道,幫會儘管屬於第三社會,但卻一直熱衷於洗白自己。不僅在經營產業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歷次涉及民族大義的場合,一向都有不錯的表現。五四之後的五卅運動,「一‧二八」抗戰,以及抗戰爆發後的淞滬抗戰,無役不從。曹汝霖自己回憶,在五四之後,他去上海,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這青幫三巨頭見了他,但卻把他帶來的警衛的四枝好槍給吞了。 可見有意刁難。在幫會請人寫的《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中,開首就是「洪門發揚民族精神歌」。 幫會這樣做,肯定有他們的強大的動機。畢竟,在中國的歷史上,唯有民國時期,幫會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憑藉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臺。只是登上政治舞臺的幫會,還是有黑社會的背景,幹點露臉的好事,尤其是爭民族大義的好事,對他們有極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麼說,幫會跟五四上海罷工的關係,我沒有弄清楚,很遺憾。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問題,希望以後的年輕學人們,會有興趣做這個題目。
寫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謂的學術專著一樣,我都是希望寫成一個散文體的東西。歷史研究不比別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價值。即使沒有這樣的追求,讓現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寫一些特別學術的文字,如果沒有人拿槍逼著,我肯定是不幹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沒有按學界的慣例,先來學術史爬梳,再寫研究思路,然後再理論預設。我就是一個事一個事地寫下來了,說完這個說那個,雖然裡面有個線索和脈絡,但外表看,就是一個一個的事。為了跟我以往的歷史文化隨筆相區別,我加了注釋,以示言有所本。其實,我的隨筆也一樣言有所本,斷沒有這個膽量胡說亂道。但是,我只是個學界的小人物,寫隨筆,隨便一點也就罷了,這本書從開始我就是按學術書來寫的,所以,非加注釋不可。說白了,就是讓注釋給我做個證明,說明我沒有亂說。我也知道,這樣寫,也許兩面不討好,學界認為我胡鬧,而一般的閱讀界又覺得過於囉嗦。但以我現在的心境,也只能這樣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只是,寫完這本小書之後,我得到了一個教訓,或者說經驗,千萬不要認為什麼領域已經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歷史更是如此。我們趕上這樣一個時代,即使是學者,大家都喜歡做前人做過的事情,在前人的題目下,添加一點東西。因此,留下的大塊空地,在哪個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魚沒有小魚還是會有的。下功夫撈,總能撈到點什麼。
後記
寫書始終是個令人遺憾的事
拖了四年,才把書寫出來,對於當時約稿的香港中大出版社的編輯,還有後來等著我出書的大陸諸位出版界的朋友,都是一種遺憾。我知道,他們原本是期待我能趕上五四九十周年的檔期的。無論在哪裡出書,趕上時機,對於書的銷售大有好處。可惜,我寫不出來。
我這個人寫東西,向有快手之稱。很多約稿,甚至約稿者說完了,回到家,我的稿子已經到了。因此,也有人批評我的東西粗。快,就難免粗,但是,如果能慢一點,我還是樂意慢的。磨得好一點,少一些不必要的瑕疵,誰不想呢?可是,我就是這個毛病,一般的情況下,寫東西犯急,答應了就得馬上寫,能在一兩個鐘頭寫出來的,磨上一兩個月,也那個樣,好不了多少。但是,寫得快,關鍵是要有心情。
我是個幹粗活出身的人,寫字這個活計,跟幹粗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幹粗活沒心情也能幹,無論割豆子還是扛麻袋,反正機械地做就是。一般情況下,任憑連長、指導員怎樣鼓動,也難以心情愉快,但任務卻都能完成。可是,寫字這活,沒心情無論如何都幹不了。別人怎樣我不知道,如果讓我硬幹,肯定一塌糊塗。就跟我下圍棋似的,高興的時候可以殺敗高手,沒心情之際逮誰輸誰。
不幸的是,這四年,我心情好的時候不多,於是,活就這麼拖下來了。拖到現在,嚴格地說,還是有些部分實際上沒做完。也就只能這樣交差了。非常感謝張彥麗和張廣生夫婦,為我提供了有關日文材料。感謝田仲勳、張楠迪揚、任智勇、胡其柱、付金柱等同學,為我尋找資料。這本小書能夠完成,沒有他們的幫助,難以想像。我的女兒張心遠,也審閱了部分書稿,幫我做了修改。同時也感謝廣西師大出版社的劉瑞琳和曹凌志,以及另一位出版圈裡的好朋友尚紅科,如果沒有他們的督催,也許這本書現在還出不來。當然,最該感謝的是現在為香港中華書局的編輯黎耀強先生,如果沒有他,我根本不會有寫這本書的念頭。
寫書始終是個令人遺憾的事,什麼時候不交稿,什麼時候覺得還需要修改。等到變成鉛字,肯定還會發現很多毛病。但是寫出來了,就交給讀者了。為喜歡自己文字的人寫東西,一向是我的心願。但願,這本小書,不會讓喜歡我的讀者失望。
是為後記。
張鳴
二○○九年歲末於京北清林苑
目次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寫在前面的話:我為什?會研究起五四來
第一幕:斑駁的武人背影
山東和青島問題
二十一條
西原借款
日元背影裡的兩件大事
皖系「帝國」
武力統一:顛峰上的噩夢
第二幕:被遺忘的角落
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迷失
外交疑雲下的學生運動
學生與軍警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悲情製造
抵貨運動的是是非非
第三幕:五四運動好玩的零碎
花界裡的愛國運動
洋人下毒的魔咒
租界裡的鎮壓事件
兩個人日記裡的五四
三個賣國賊
在親日與賣國之間
第四幕: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變
五四運動裡的軍人聲音
直皖之間:由裂痕到溝壑
中國的火藥桶湖南
吳佩孚與湖南的「驅張」運動
吳佩孚和他幕僚的兩種趨時
吳佩孚變臉:文戲與武戲
後記: 寫書始終是個令人遺憾的事
書摘/試閱
直皖之間:由裂痕到溝壑
事情要從北洋集團的分裂說起。但凡一個集團,規模大了,都會在內部形成派系。袁世凱尚在之日,人們已經在傳有直皖之分。北洋三傑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
軍閥這個概念,據陳志讓先生說,是二十世紀二○年代初,由一些學者先叫出來的。但是,很快,被稱作軍閥的人,互相開戰,也互詈對方為軍閥。 顯然,無論在那時還是現在,軍閥無疑是個貶義詞。英語裡跟軍閥近義的有兩個單詞,一是warlord,一是 militarise。前者之意為軍人割據,後者是軍事化的統治。顯然,民國前半段,也的確存在著大大小小的軍人集團,而且這一時期,軍人的確具有最大的發言權。稱之為軍閥,並不為過。當然,這一時期最大的軍人集團,就是北洋集團,或者通稱北洋軍閥。集團中人,稱自己為北洋團體。所謂的北洋軍閥,史家公認,是始創於袁世凱的一個軍人集團。事實上,這個集團也繼承了李鴻章淮系集團的部分遺產,從人員到物質都是如此。眾所周知,這個集團起家是小站練兵,也就是說,是在袁世凱主持小站練兵之後形成的。因此,這個集團的第一代骨幹,都是小站舊人。第二代,則是出身北洋系統的各級軍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輩。因此,嚴格來講,人稱北洋軍閥三大派系之一的奉系,其實不算北洋的圈內派系,充其量,跟北洋集團關係密切,與辮帥張勳一樣,都屬於北洋集團的支系。
但是,即使是北洋軍,也跟西方語境裡的據武割據、攔路搶劫的warlord,有相當大的區別。跟古代中國亂世割據的軍閥,也大不一樣。晚清一干投筆從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國內外新式軍校學生,其實相當一部分是有志愛國的青年。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們投身新軍,是為了尋出路,給自己找個更好的飯轍。但如果不考慮飯碗問題,還必須承認他們是晚清梁?超、蔡鍔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體現者,身體力行地改變傳統士大夫重文輕武的積習,因為他們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並無飯碗之憂。棄文從武,為的無非是富國強兵。不僅接近同盟會的陸軍學生吳祿貞、藍天蔚、閻錫山等人如此,跟立憲黨人走得近的蔡鍔、唐繼堯等如此,連一些北洋軍人也是如此。段祺瑞、馮國璋和吳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分(後兩人還是文秀才)投筆從戎的。我們不能說,南方參加革命的新軍士兵,當兵是為了救國,而北洋軍人就個個是頭腦冬烘的木頭人。晚清的新軍,無論北洋還是各省的,都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對於近代政治,都有著出乎尋常的熱情。在他們的某些人看來,像他們這樣的新式軍人,對於國家,負有特別的使命。 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北洋時期,當家的武夫,會如此在意共和政體的某些基本原則,尊重民眾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當然,他們也相當在意與此相關的道義和聲名。不僅對制度的尊重屬於道義名聲的一部分,而且事關民族主義的聲譽,更是他們自身合法性的組成部分。一旦某個集團在這方面被公認有虧,那麼,這個集團離下臺就不遠了。袁世凱的垮臺,不是因為討袁軍力量有多麼強大,而是他在制度堅持和民族主義兩方面都聲名大損。五四之後,我們看到,貌似強大的皖系集團,也在這個方面吃了虧。
事情要從北洋集團的分裂說起。但凡一個集團,規模大了,都會在內部形成派系。袁世凱尚在之日,人們已經在傳有直皖之分。北洋三傑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樂出頭。馮國璋和段祺瑞則不相上下,同為袁世凱的左膀右臂。馮國璋是北洋軍中的秀才,少見的文生,而且真正打過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時,袁世凱被起復,北洋軍進攻武漢三鎮,指揮官就是馮國璋,對手是革命黨中號稱知兵的黃興。開戰的結果,革命黨人敗績,三鎮丟了兩鎮。如果不是袁世凱要跟清廷和革命黨兩面討價還價,第三鎮武昌,說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馮國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統制(師長),也是馮先過關,而段則需要袁世凱通關節才過關。可是,比較起來,袁世凱卻更喜歡段祺瑞些。因為馮國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則對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馮國璋在前線賣命,段祺瑞則領一群北洋將領,一會兒擁護共和,一會兒捍衛帝制,清廷和革命黨兩邊嚇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黨人乖乖把臨時大總統寶座,送給袁世凱。在南北談判期間,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談,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黃興代表談, 可謂武人中的政治家。後來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間都嚷嚷翻了,卻還瞞著馮國璋。馮國璋上門來問,還是不說實話。但對段祺瑞,老袁卻沒法這樣蒙,也不能蒙。雖然袁世凱特別希望段祺瑞擁戴,但是段祺瑞對於帝制,明確表示反對,寧可陸軍總長不做了,也不肯順著。事實證明,段祺瑞的選擇是對的,在政治上,比馮國璋的首鼠兩端,含含糊糊要略勝一籌。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稱段合肥。馮國璋是直隸河間人,人稱馮河間。但段合肥的名頭顯然要比馮河間響,原因是中國上流社會固然對馮、段褒貶不一,但在人們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對馮國璋沒有好印象。儘管如此,馮、段之間,依然積不相能。北洋集團中,有人跟馮走得近一點,被人稱為直系。有人跟段走得近一點,被人稱為皖系。當然,不是直隸人必然屬於直系,安徽人必然屬於皖系。北洋舊耆陸建章和他的姪女婿馮玉祥都是皖人,但卻跟段祺瑞視同水火。而且,必須指出的是,早年的直系、皖系,其實跟戊戌時期的帝黨、后黨一樣,界限並不那麼清晰。齊錫生先生根據軍閥集團成員和首領的人際關係等級,對軍閥派系進行的派系分析,無疑精闢的,但應該主要適用於直皖戰爭,北洋團體分裂之後。 在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當家的那四年裡,由於段祺瑞幾乎是北洋系統所有軍校的總監(校長),所以,所有的北洋軍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學生。北洋系統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對段祺瑞都會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禮貌。直皖戰後,直系大勝,但卻不肯通緝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敗之後,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跟南方和西南軍閥相比,北洋軍閥相對比較土氣,留洋的學生較少。而相形之下,曹錕、吳佩孚的直系,這種狀況就更突出,留學生在裡面基本上沒有立足之地。而直系的一翼馮玉祥的部隊更土,連國內軍官學校的學生都很少,軍官只用自己帶出來的學兵連的人。這樣的結構,具有相當的封閉性,似乎很有利於內部的凝聚。正如美國學者安德魯‧J‧內森(Andrew James Nathan, 1943-;即黎安友)說的那樣,中國軍閥的派系都是圍繞私人關係形成效忠結構。 這對於某個規模小的集團,是合適的,比如曹錕、吳佩孚的集團,彼此按私人關係結成團體,相當牢固。但對於北洋系沒有分裂之前的狀況,就未必合適,那個時代的私人關係,往往非常複雜,北洋內部就更複雜。跟某個頭面人物走得近,不見得就會跟另外的頭面人物公開疏遠。頭面人物之間,也往往難以撕破臉皮。
正因為如此,儘管段祺瑞和馮國璋鬧矛盾,馮國璋做代總統,段祺瑞僅僅是內閣總理,但馮卻始終處於下風。馮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不滿,自己在北京手裡有一個師護衛,卻始終不敢公然表示反對,連手中沒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都不如。馮只能暗中指使親他的長江三督,時不時不痛不癢地搗一搗亂。實在受不了,想要逃出北京,在安徽被倪嗣沖截下,一槍沒敢放,硬話沒說一句,只好乖乖回來。眼睜睜看著段祺瑞另起爐灶,組織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做總統,自己規矩地下臺,回鄉養老。而長江三督之中,坐鎮武漢的湖北督軍王占元,對武力統一根本不敢反對,大軍過境,南下湖南,他乖乖地為人做後勤。
北洋集團,在那時內部自稱為北洋團體,講傳統,講禮儀,講輩分,有時也講點團結。在北洋第一代人那裡,儘管彼此面和心不和,臺上握手,臺下踢腳,但真要撕破臉皮,還真有困難。直到一九一九年底馮國璋故去,馮、段之間的關係也沒有破裂,儘管段家的黨羽,在五四運動中對馮很是猜忌和防範,總疑心運動是馮國璋搞的鬼。在喪禮上,老段卻哭得像淚人一樣,讓人看了好生感動。時人記載:
當馮氏入殮時,合肥(段祺瑞)首先趨視,撫棺慟哭,觀者莫不動容。……行禮時,痛哭失聲,涕泗橫流,幾不能仰視。其悲傷狀況,與祭人員,舉奠之及,人皆怪之。
撕破臉皮,乃至刀兵相見,是第二代的事兒。也可以說,到了北洋第二代人手上,才有真正的分裂,才有真正的直皖之爭。美籍華人學者齊錫生認為,在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的成員,還是傾向於維持這個集團的「團結一致」,以保障集團對國家的統治。督軍團的出現,以及兩次督軍團的徐州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可以說是北洋集團想要以集體的努力,維持團體團結的一種嘗試。
曹錕,人稱新直系,因為他是直隸保定人,當兵前,是保定的布販子,一個帶點傻氣的閒漢。曹錕在北洋集團中,屬於資歷稍淺的第一代人。在馮、段紛爭的時候,一向騎牆,不站在任何一邊。相對而言,跟段祺瑞走得還更近一點,段祺瑞馬廠誓師討伐復辟,曹錕是第一批響應的人。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南征,儘管人說是用了副總統做誘餌,但畢竟曹錕所部是其中最賣力的一支部隊。打下湖南之後,分贓不均,矛盾才起。即便如此,曹錕一直也沒跟段祺瑞紅臉。吳佩孚抗上,高喊和平,公然跟段祺瑞唱反調,曹錕還總做出一種不知情的樣子,裝模作樣要加以訓斥。
所謂的直皖之爭,轉機在第二代,激化也在第二代。最先壞了規矩的,是皖系的人。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剛,徐樹錚是其中之一,以別於徐世昌,人稱小徐。小徐為人,好權謀,敢作為,經常獨斷專行,計詐並出,敢為人所不敢為。在袁世凱時代,就很招人恨,連袁世凱也不喜歡他,段祺瑞做陸軍總長,選小徐做次長,老袁就不高興。但是,小徐卻深受段祺瑞的信任,無論他做了什麼,段祺瑞都給他兜著。段祺瑞的最大毛病,就是不會用人。段芝貴這樣在清末就聲名狼藉的人,曾經走奕劻父子的後門,送女伶給奕劻兒子載振,買到黑龍江巡撫,舉國臭名遠揚,但是偏能得到段祺瑞的重用。張敬堯這個飯桶將軍,貪財好貨,所帶的第七師,軍隊紀律極差,走到哪裡臭到哪裡。也是段祺瑞的寶貝,寧可得罪吳佩孚,也要把湖南督軍給他。但是,段祺瑞有一個好處,用人絕對不疑,放開手用。他用的人,捅了簍子,即使他事前並不知道,也會自己把事頂下來。敢擔責任,或者說瞎擔責任。跟段祺瑞相當熟悉的名流徐一士,說段祺瑞「蓋果於用人,己惟主其大綱,不必躬親諸政務,亦其素習然也;惟責任則自負,政治上無論成敗,從不諉過於下耳」。 在徐一士眼裡,段祺瑞有很閒逸的一面。喜歡在家裡跟清客下棋,卻不喜歡在辦公室公幹。還特意講了一個故事,說是段祺瑞做邊防督辦的時候(實際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機構),國中大事,均決定於這個衙門,連內閣都得給它做彙報,但段祺瑞卻不常去,「處中事務,向委僚屬處理」。一日雪後,段祺瑞在街頭散步,走到邊防督辦處附近,順便走進去看看,結果遭到衛兵的阻攔和呵斥。從人亮明身分,才得以進去。進去之後,諸多要員以為有什麼大事,一齊來見。結果,段祺瑞說,我只是來閒遊而已,大家該幹什麼幹什麼。 這樣的閒逸,後來讓段祺瑞吃了很大的苦頭。他發現,他不得不不斷給小徐背書。
在皖系當家的時代,小徐有兩件事做得非常失策。一是把持第二屆國會選舉,玩手段把原本的盟友文人集團的研究系玩到殘,在自家精心設計的國會選舉裡大敗,結果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知識界盟友。第二件是擅殺北洋耆老,資格跟他主公相若的陸軍上將陸建章。陸建章固然總跟段祺瑞搗亂,但畢竟是北洋老人,按北洋系的倫理,輩分必須尊重,即使鬧翻,也不能對本人及家屬動刀子,大家見面,面子上都得過得去。小徐把人騙來,一槍就給斃了,別說審判,就連請示都沒請示一下。雖說在小徐看來,陸建章可惡之極,但北洋團體的規矩和傳統,也因此而被破壞了。這兩件事,老段當初未必知情,但事情做出來了,卻只好替小徐頂著。段祺瑞的智囊之一後來接替曹汝霖做交通部長的曾毓雋,回憶徐樹錚槍斃陸建章之事時,有這樣的描寫:「徐樹錚槍斃陸建章後,他的副官長李某從天津打來長途電話,向我報告這個消息。我向段(祺瑞)報告。段聽到這個消息後,驚訝萬狀,瞪目半晌,才說出話來:『又錚(徐樹錚的字──筆者注)闖的禍太大了!現在這樣罷!你先到總統面前,探聽他的口氣如何。你就作為我還不知道。』我便到了總統府,馮見我來,不等我開口,就先問我;『你是為了又錚的事情來的嗎?』我說:『是。我來請示總統,這事怎麼辦?』馮說:『又錚在芝泉(段祺瑞──筆者注)左右,一向是為所欲為,今天這事未免太荒唐了。所好是責任內閣,你回去告訴芝泉,他怎麼辦,我就怎麼用印好了。』」 顯然,此時的馮國璋已經想開了,放手讓徐樹錚去壞規矩,得罪人,得罪人多了,皖系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後來的事情證明,段祺瑞的事,有一多半壞在徐樹錚身上。顯然,像這樣壞規矩的事,許小徐做了初一,自然就會有人做十五。做十五的人,就是吳佩孚。
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出身很苦,但很早就進學做了秀才。此人性格很誇張,但卻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沒有在家鄉走讀書科舉的路,就是因為不滿當地鄉紳請戲班子演「淫戲」,而大鬧人家壽堂,得罪了人,不得已離家出走,萬般無奈,做了「糧子」(士兵)。秀才出身的軍官,在北洋系非常少,一直也得不到重用。吳很早就碰上了段祺瑞,但段卻死活看不上他(後來,段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後來跟了曹錕,偌大年紀,還在當副官長,所謂馬弁頭,如果不是留學出身的湯薌銘看上了他,要跟曹錕「借趙雲」,吳佩孚恐怕一直都沒有機會出頭獨當一面。
在北洋軍人中,吳佩孚是個有政治理念的人,一邊是帶有理學味道的儒家倫理,一邊是模模糊糊的達爾文主義。因此,在高唱「五常八德」的同時,卻不肯附和帝制。清末和民初的國家危局,往往會刺激有志之士的民族主義神經,把情緒集中在愛國主義上。吳佩孚也不例外。民國期間,很多清末時有志報國的軍人沉淪了,把軍裝換成了馬褂,戰馬換成了八抬大轎,變成了抽大煙、討小老婆、刮地皮的軍閥,但是也有些人沒有消沉,一直想有所作為。吳佩孚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多年的壓抑只能使得他的野心更加勃勃。
出身秀才的他,在某些方面其實跟多數晚清時節的普通讀書人一樣,經歷了自身價值和命運被衝擊的動蕩。作為軍人,尤其是中國軍事現代化成果新式軍隊的軍人,又經歷了實力不如人的命運嘲弄。跟同袍不一樣,吳佩孚參加過日俄戰爭。這場曾經令中國知識界很興奮的戰爭,給他的體驗完全不同。他經歷了九死一生的考驗,也見識了現代戰爭的場面,同時也體會到中國軍隊和日本的差距。儘管他的日本同事對他不錯,但他對日本卻充滿了敵意,大概是感覺到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以及品嘗了作為軍人時中日之間的差距。
凡是有志向的人,大抵有點本事。多年的行伍經歷,使吳佩孚在練兵方面很有心得,這一點,似乎只有馮玉祥和孫傳芳可以跟他有一比。因此,他帶的兵,戰鬥力要比同時代多數軍閥要強得多。在後來的混戰中,吳佩孚因此得了常勝將軍的名聲。按他的本意,不見得樂意入湘打內戰。但恰是這個內戰使得曹錕放手讓他統率第三師,一個北洋六鎮之一的基本部隊,從此有了可以說話的本錢。一上任,就撤掉了資歷比他還老的第五旅旅長張學顏,換上自己的夾袋中人。從此,第三師成了他的部隊。而駐紮湘南,一面向北京政府要錢,一面也就地徵稅,同時享用湘桂軍方面來的錢,招兵買馬,大力度擴充實力。
另外由於跟湘軍罷戰休兵,暗中往來,吳佩孚得以交接兩個畢生的朋友,一文一武。文者張其鍠。係湘軍統帥譚延闓的進士同年,也是好朋友,民國有名的才子。因參與吳佩孚與譚延闓之間的穿針引線,兩人結為金蘭之交。此後,張其鍠便成為吳佩孚幕中文膽,吳佩孚好多膾炙人口的文告,據說都是出自他的手。吳佩孚比張其鍠要年長,但始終對張尊稱為省長(張做過省長),畢恭畢敬。而張其鍠則對吳佩孚患難相從,直到一九二七年大敗入川,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亡。武者趙恆惕。湘軍將領。當時殘餘湘軍的統帥雖為譚延闓,但譚是文人,脾氣極好,人稱「譚婆婆」,但領兵打仗是不行的,幸虧手下有員戰將,這就是趙恆惕。趙恆惕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係譚延闓最信任的將領,時為湖南第一師師長。雖說湘軍糧餉不繼,缺兵少械,但除了第三師之外,剩下的北洋軍還都懼趙將軍三分。凡交手,負多勝少。吳佩孚眼看著,張懷芝二十個營的生力軍,在趙恆惕千餘湘軍面前,一敗塗地。吳佩孚和趙恆惕惺惺相惜,從此訂交。兩人後來雖然政見各異,但交情卻一直不斷。一九二四年直奉大戰,吳佩孚大敗南歸,人人避之唯恐不遠,只有趙恆惕收留了他,讓他帶著殘軍,在岳州依舊做他的大帥。
有了本錢(實力和戰功),又有委屈(沒拿到湖南督軍)的吳佩孚,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吳佩孚的崛起,形成了北洋系分裂的第一道裂痕。但是,如果沒有後來的五四,直皖之間刀兵相見,還沒那麼快到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