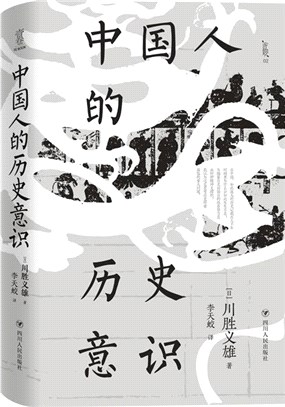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本書為史學家川勝義雄先生的遺稿集。書稿收錄了作者關於中國史研究的十余篇文章,整理為三章,分別包括中國歷史和歷史意識、道教與佛教、中世史等內容。這些文章都是作者其他專著中未收集的內容。作為中國歷史學乃至中國學的研究者,作者認為,司馬遷在中國的地位,相當於亞裡斯多德在歐洲諸學中的地位。中國的“諸學之學”並非哲學,而是以《春秋》為起點的史學。中國人的歷史意識貫穿著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本書見解*到,不僅對於中國史的學習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具有廣泛的學術史意義。
作者簡介
川勝義雄(1922-1984),1948年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1973年任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部教授,次年兼任東方部部長,多次赴法國研究和講學。日本京都學派東洋史學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國際學界久負盛名。主要著作有《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中國中世史研究》(合著)等。
李天蛟,自由譯者,留學歸國人員,已出版著作包括《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合譯)、《虐待心理學》、《清理:日本的整理藝術》等。
名人/編輯推薦
2、本書作者系知名日籍學者川勝義雄先生,所收錄的遺稿集在大陸未出版過。
目次
章
司馬遷的歷史觀
司馬遷與希羅多德
天道,是邪非邪?
中國人的歷史意識
第二章
關於馬伯樂的道教理解
附 道教眾神——如何與之進行交感
中國人的現世與超脫
——接納佛教的中國風土
道教與季節
——中國人的季節感
中國早期的異端運動
——以道教反體制運動為中心
促使中國新佛教形成的力量
——南岳慧思的相關情況
第三章
六朝貴族社會與中國中世史
六朝貴族制
中國中世史研究中的立場與方法
關於重田氏的六朝封建制論批判
後 記 島田虔次
解 說 礪波 護
書摘/試閱
天道,是邪非邪?
一
世界上沒有哪個文明積累了像中國一樣多的歷史記錄。二十世紀初,在清朝帝國崩潰期間活躍的改革者梁啟超(西元1873—1929年),在其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為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為發達。二百年前,可雲如此”。
實際上,成書於七世紀初的《隋書·經籍志》把當時所能看到的書籍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進行分類整理後,古代中國開始普遍按照上述四個部分對學術體系進行劃分,而其中“史”的部分所占比例。
這一體系的龐大程度,即使在今天的日本,看一看按照這種四部分類整理漢籍的專門圖書館,比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機構的漢籍目錄,也會一目了然。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留下了如此龐大的歷史記載,那麼,針對這一現象,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不可估量的孜孜努力呢?黑格爾曾針對中國人的這一偉大努力成果進行了簡單概括:“中國人的歷史,沒有任何判斷和道理,只是把各種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而已。”(武市健人譯《歷史哲學》上冊第265至266頁,巖波文庫)。當然,史書確實“把各種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而且這是史書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所有中國的史書,假使正如黑格爾所說,只是單純地記錄事實,這種幾千年以來編纂史書的偉大努力“沒有任何判斷和道理”,僅僅無反省地、單純通過惰性來延續,真的有可能嗎?即便存在這種可能性,至少,“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的基本“判斷”乃至觀念,是無法在這種根基之上牢固存在的。像這樣“沒有任何判斷和道理”,僅僅茫然地持續書寫龐大的歷史記錄,對於有意識的人來講大概是不可能的吧。黑格爾的上述觀點,在深入挖掘中國人基本意識的方面,不得不說正是十九世紀歐洲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成見所導致的災難性產物。
關於中國人的歷史記錄,或者說,持續書寫龐大歷史記錄的中國人的基本歷史意識,我認為日本的眾多學者持有與黑格爾觀點類似的思考方式,他們把歐洲學問當作至高無上的存在,至今仍然一脈相承。比如,作為西方古代史學家的一流學者村川堅太郎,對中國歷史學家司馬遷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根據中國“東方專制君主”制度下“個人自發性寫作”的“自由被束縛”認為,“漢朝之後的正史,在一個王朝覆滅之後,無論官方撰寫或私人撰寫,均採用了固定的形式,所謂的歷史成了王朝的歷史,所謂的修史成了編纂史料,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誰擔任這一角色都沒有太大差別,況且並不存在被稱為歷史觀的思想,因而有個性的歷史學家理所當然沒有立足之地”(世界名著5《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解說第10至12頁,中央公論社,1970年)。司馬遷暫且不提,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龐大歷史記錄的眾多歷史學家,均因受到專制君主政治權力的束縛,自發寫作的自由意志無法得以發揮,只能按照專制君主的命令,遵從司馬遷所發明的“紀傳體”歷史記錄形式,像奴隸一樣默默地“沒有任何判斷和道理,只是把各種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而已嗎?中國的眾多歷史學家,真的是一種被欺壓的奴隸一般的存在嗎?
其中突出的觀點,是自希羅多德以來傳統的歐洲觀念,即與東方專制相對的、希臘或泛西方的自由觀念。黑格爾本人曾說過:“世界史自東向西推進。也就是說,歐洲實際上是世界史的終結,因為亞洲是世界史的開端。……因而歷史一定存在東方,……自然界中外在的太陽也是東升西落。然而,名為自我意識的內在太陽則在西方出現,並且一直閃耀著光輝。……東方只有一個人(專制君主)是自由的,至今仍然如此。與之相反,希臘羅馬世界中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而在日爾曼世界中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第218頁)
這反映了把世界史當作“自由意識的進步”的黑格爾以歐洲為中心的觀點。我們沒有必要一直被這種以十九世紀歐洲為中心的思想束縛,而且,如果一直處於這種束縛之中,則始終無法理解中國文明和中國人的意識。
中國人孜孜不倦地寫下了龐大的歷史記錄,是出於怎樣的動機?如果單純出於“把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的目的,那麼中國人為什麼一直認為應該“把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司馬遷所開創的紀傳體,在其後兩千年時間裡作為史書正統的“固定的形式”被沿襲下來,又是出於什麼原因?關於這些問題,以“東方專制君主”政治權力為中心的歐洲觀點僅僅通過表面觀察所做出的說明進行了簡單劃分,而並沒有給出真正的答案。如果僅從表面進行觀察說明,而沒有深入中國自身內部找出隱藏在中國人意識根基之處的內在原因,就沒有辦法得到真正具有說服力的解答。出於上述立場,針對中國人自古以來如何看待歷史,以及他們認為歷史記載應有形式應具備怎樣的性質等問題,中國人已撰寫文章做出了提示,我將根據相關部分盡可能忠實地解說,剖析闡述內在問題。這些文章,正如本文以下所示,在體系龐大的史書中,有很多作品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史論。本書所列舉的文章不過九牛一毛,但從這些文章可以一窺中國人歷史觀的一部分,我將略做總結。
二
首先,我針對黑格爾的觀點——“中國人的歷史,沒有任何判斷和道理,只是把各種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而已”——提出一個疑問。即,中國的史書都只不過是事實的記錄,中國人是否在持續進行這種龐大史書編纂的基礎上,牢固地持有“把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就好的觀念,或者“應該這樣做”的判斷呢?
實際上,中國自古就自覺形成了“把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的判斷乃至觀念。究其根本,在中國所謂的“史”,原本就是記錄者的意思(參照正文第6頁)。把“史”解釋成歷史或者歷史記載,是後世才發生的,初則指的是記錄者、記錄官。而且,這裡的“史”——記錄者——被認為應該把“親筆”、直接、實事求是地記錄事實作為至上的義務。
《左傳》中,宣公二年晉國“史”——董狐,以及襄公二十五年齊國南史的故事為知名(參照正文第55至56頁以及第215頁),根據這些故事,不顧性命之憂與時下強權進行抗爭、絕不歪曲事實,才有資格被稱為“良史”。“史”在七至八世紀被劉知幾擴大解釋為“史書”或“歷史學家”,正如正文第214頁所強調的,他認為“史官”或歷史學家的要務必然是“彰善貶惡,不避強禦(即掌權者),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劉知幾,《史通·辨職》)。而“史之直筆”,正如宋朝文天祥所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正氣歌》)。
因此,黑格爾所說的“中國人的歷史,沒有任何判斷和道理,只是把各種事實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而已”並不成立。“原封不動地記錄事實”,如果使用中國人的表達方式“直筆”,則是“史官”、記錄者、歷史學家的至上任務,這種明確的判斷一直在中國人的身上流傳。具體來說,那是抵抗權力、賭上性命也要堅決守護的至高無上的價值,被認為是作為記錄者、著書者的知識份子的責任。這種判斷乃至觀念,正如《左傳》中所能看到的,以孔子的判斷為基礎,晚至西元前四世紀的戰國時期,便已得以確立。
這種記錄者或歷史學家的責任到底能夠切實履行多少,對於掌權者所施加的壓力到底抵抗到什麼程度,確實是個問題。但是反復確認和強調“史之直筆”的觀念與責任的事實表明,不能簡單地概括中國歷史一直處於“東方專制君主”的束縛之中。中國的歷史學家,出於其自身的獨立性,為了瞭解所發生的歷史事實,肯定留下了龐大的歷史記載。
不過,史官乃至歷史學家將“原封不動地記錄事實”作為至上任務的中國觀念,與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學家蘭克所主張的把“說明事情的本來面目”作為歷史學的目的,在語言層面其實也有相近之處。蘭克的主張,自然把價值賦予歷史事實的客觀認識之上。而在中國方面,自古以來的歷代王朝以及各諸侯國均通過制度設置了作為事實記錄者的“史官”,晚至西元前四世紀把原封不動地記錄事實的“史之直筆”自覺作為記錄者的至上責任,雖然這些史官並沒有像蘭克那樣將歷史事實的客觀認識作為歷史學目的,但終他們所留下的記錄,同樣是可信度相當之高的客觀記載。
“史之直筆”的觀念,終使“史”成了具有客觀認知的人。比如,司馬遷對諸多史官留下的記錄——初被稱為“史記”——加以利用所完成的體系完整的歷史著作《史記》,在“說明事情的本來面目”的同時,同樣也是合乎歷史學目的的一部作品。再比如,司馬遷所作的比他早一千多年的商朝王統譜,除了一兩處錯誤之外,都是極其準確的。二十世紀初以來,隨著針對出土的商朝甲骨卜辭所進行研究的推進,司馬遷所作的王統譜被證明具有驚人的準確度,這再一次有力證明了司馬遷的《史記》是“說明事情本來面目”的科學的歷史記載。
然而,在中國,這種對於歷史事實的客觀認識能夠成為結果的可能原因,雖然在於“史之直筆”——原封不動地記錄事實——的觀念及判斷,但與之相反的是,“史之直筆”的觀念把針對歷史事實的客觀認識作為至高的價值,也就是說,以純粹認知作為歷史學確立宗旨的思想,所衍生出的結果卻並非如此,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中國的“史之直筆”觀念,正如前面劉知幾所說,以“彰善貶惡”為根本動機。
但這並不是由八世紀初的劉知幾次提出的。作為典型“史之直筆”的董狐和南史,是春秋時期的史官,正如孔子將他們稱作“良史”,“史之直筆”觀念的由來正是“勸善懲惡”的《春秋》的基本批判精神。《春秋》是孔子所修訂的經典著作,同時也是中國現存古老的編年史著作,“史之大原,本乎《春秋》”(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是中國古代一貫的傳統觀念。在中國,“史之直筆”,即“原封不動地記錄事實”的觀念,是針對人間善惡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是以倫理要求為根本動機而形成的。
關於這一點,有學者曾說過:“早有組織地記載歷史的古典著作《史記》是包含史論的,是針對《春秋》以來的各個歷史事件所進行的倫理批判。在此之後一般的中國史書……直至近代……不過是針對相應歷史時期加以政治倫理考察而已。根本不存在世界史的理念或發展的思想。”(下村寅太郎《關於世界史的可能性依據》第18頁,《哲學》第18號,日本哲學會)確實,中國史書的一大特點恰恰就是強烈的倫理批判與執著的政治倫理考察。我們應該注意,中國史書,正如傳統的“史之直筆”觀念來源於倫理動機,對源自“春秋大義”的“義”進行了大量重複的追求與強調。
但是,在以此為基礎認定中國“根本不存在世界史的理念或發展的思想”之前,應該先搞清楚,中國的史書以及歷史學家為什麼如此執著於倫理,在如此執著於倫理的情況下如何寫成史書。關於為什麼的問題,反觀“說明事情本來面目”的蘭克史學,其實具有“一切時代都通向上帝”的基督教精神內核,而以倫理動機為基礎的“史”,也正是其背後中國精神的產物。問題恰恰存在於這種中國基本精神的性質之中。而我們的課題,則在於更加深刻地查明這種精神的結構。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來思考一下,中國是否“早有組織地記載歷史的古典著作《史記》……是針對《春秋》以來的各個歷史事件所進行的倫理批判”。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