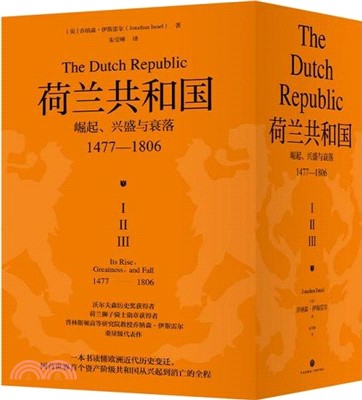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是一部全新角度的300年荷蘭共和國史,首度全方位解析荷蘭共和國從醞釀到衰落的全過程。
全書共分四大部分,分述各時代荷蘭地區的發展歷程。1477—1588年的共和國奮力擺脫勃艮第的控制,在喚醒自我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的過程中燃起一片宗教改革與大起義狂潮。1588—1647年,處於黃金時代早期的共和國不斷尋求抗爭西班牙統治的道路,在意識形態上陷入大辯論,在權力的對峙中磨合出宗教寬容政策。1647—1702年,航海貿易的大發展,讓八十年戰爭後的共和國在諸多思想的裹挾下陷入斗爭,這種斗爭既包含內部意識形態的對抗,也包含共和國與外部英、法間的競爭與廝殺。 1702—1806年,四次英荷戰爭的摧折,愛國者黨運動的席卷,即使有尼德蘭新共和國的垂死掙扎,衰落的時代也必然來臨。最終,在拿破侖政權下,共和國正式落下帷幕。
全書避免了過去以1649年為界的共和國歷史研究角度,將時間追溯到1572年之前以及延伸到取代荷蘭共和國的巴達維亞共和國時代,同時將地域從單一的北部地區拓展至南部及德意志諸國轄區。從思想史角度揭露尼德蘭南北分裂的真相,是突破傳統荷蘭史研究角度,顛覆歐洲史陳舊觀念的力作。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喬納森·伊斯雷爾,本科畢業於劍橋大學,在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在英國多所大學工作三十年,後來被任命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2016年退休。作為沃爾夫森歷史獎得主,世界知名啟蒙運動歷史學家,他與約翰·艾略特爵士和杰弗裡·帕克齊名,在學界享受盛譽。他的作品涉及從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歐洲和歐洲殖民史。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斯賓諾莎、貝勒、狄德羅和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對啟蒙運動的影響。
他的著作包括《重商主義時代的歐洲猶太人,1550-1750》(1985);《荷蘭共和國:崛起、興盛與衰落,1477-1806》 (1995);《激進啟蒙:哲學和現代性的形成,1650-1750》 (2001);《有爭議的啟蒙:哲學、現代性和人的解放1670-1752》 (2006);《思想革命:激進啟蒙和現代民主的知識起源》(2009)等。
名人/編輯推薦
1、牛津現代歐洲史系列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奠定系列質量格調
本書是牛津出版社現代歐洲史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本,在歐美學術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奠定了牛津現代歐洲史系列品牌極高的學術格調,甫一誕生,就被譽為未來多年歷史研究標桿作品。
2、作者是業內公認頂尖級學者,學術水平權威
作為眾多歷史專業獎項的獲得者,喬納森·伊斯雷爾既受到英語世界歷史業內的讚美,又受到荷蘭本土歷史學界的讚同與認可,他對歷史脈絡的把握與解析,以及對歷史事件的復現讓作品超越枯燥記錄本身,讓讀者近距離跟隨文本,體會時代激情。
3、歷史記錄廣泛全面,展現清晰的時代脈絡
作者對於時代特徵的把握嫻熟而精準,對於一手資料的搜集和分類有超凡的匯總能力,同時對歷史有其獨到見解。可為對“荷蘭共和國(尼德蘭聯省共和國)”這個國家以及這段歷史毫無概念的讀者系統性地搭建相關歷史知識構架,有助於理解其他相關荷蘭史著作。另一方面,也能與歐洲近代崛起的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互作信息補充與照應。
4、以學術角度,系統解析荷蘭共和國歷史
市面上關於荷蘭共和國的眾多作品中唯一一本以思想史角度出發,全面記錄荷蘭共和國歷史的著作。作者在本書中難能可貴而詳盡地記錄了當時社會思想的變遷歷程以及相關派別和代表人物,又從思想變化牽引出政治與經濟上的歷史事件,從而從根源上為人們解讀荷蘭共和國崛起、興盛和衰落的本源。
5、客觀、深刻的筆調;冷峻、沉著的風格
本書的寫作語言冷峻而嚴肅,有著典型的學術風格,但每個歷史事件卻都不是點到即止、一筆帶過,而是從深度參與歷史事件的人的角度,多層次、多角度地分析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讓歷史事件在敘述中行進得鮮活而穩健。配合大量的一手史料,讓每一段文字都極具說服力。
序
前 言
在這樣一個大部頭著作的開端,用簡短的文字說明本書採用的研究方法並解釋其框架似乎是合宜的。
我的研究目的是將荷蘭大起義與黃金時代置於更寬廣的背景中,也就是整個近代早期之中。在耕耘這部作品時,我越發確信,只有將荷蘭大起義和黃金時代置於寬廣的背景中,才能領會它們的意義。這意味著,我們一方面要重返勃艮第時期,另一方面要推進到拿破侖時代。1579—1795 年間,荷蘭共和國的官方名稱是“聯省共和國”,1579年建立的烏得勒支(Utrecht)同盟則是其奠基性聯盟。同盟常被視為與過往的決裂,然而如果在14—15世紀的背景下考察,它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意義。
要完成像本書這樣的任務,研究者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論述尼德蘭北部與南部之間的關係——前者的大致所在地後來發展成現代的荷蘭王國,後者則發展成現代的比利時和盧森堡。回到我剛開始寫作的1982年,那時我跟所有同事一樣確信,大起義之前低地國家南北之間的分隔沒什麼重大意義,當時只存在哈布斯堡治下的尼德蘭。其下轄的17個省之間盡管存在巨大差異,但或多或少地統一於布魯塞爾的哈布斯堡宮廷的統治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在南部,北部在許多方面只是南部的附庸,這似乎顯而易見。
從這個角度看,這場1572年大起義導致的,因1579—1585年間的一系列事件被鞏固的南北分裂,似乎是人為的、非自然的,且並不能在此前的歷史中找到根據。歷史學家彼得·蓋爾(Pieter Geyl)第一個清楚地意識到,大起義之前並不存在與南部相分離的“獨特的北部意識”或荷蘭民族意識這類東西。在這一點上他無疑是對的。他得出的進一步結論似乎也是正確的,即起義是個意外事件,它沒有歷史根據,並且毀滅了一個更大的統一體誕生。我認為可以公正地說,一個龐大的尼德蘭共同體在16世紀70年代被人為地摧毀,這樣的信念隨後發展成了穩固的共識。然而,隨著研究的推進,我開始相信蓋爾的修正派觀點只有第一點是正確的:1572年之前的確不存在“荷蘭”或特定的北尼德蘭身份認同,也沒有明確的南尼德蘭意識。事實上,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8世紀末之前,這些東西並未在任何意義上存在。盡管如此,在1572年大起義之前很久,政治、經濟和地理的因素就已經讓北部和南部成了各自獨立的實體。尼德蘭的南北二元性事實上已經存在了數個世紀。放在中世紀晚期和16世紀早期的背景下看,1572年事件和南北的最終分裂只是對此的確認,並且也是這種二元性的邏輯結果。
在聯省共和國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人們的忠誠和身份認同都是以各省、各城鎮,有時候甚至是以當地村莊為基礎的,而非與共和國整體相聯繫。從這一方面來說,逐漸形成的松散的聯邦結構與民眾的性情、態度十分相適。特別的是,占主導地位的荷蘭省與其他省份之間的緊張關係時常是政治事件的中心問題,各省一直竭力保護自己的地方利益,避免被荷蘭省統治。這種緊張關係在大起義之前存在了數個世紀,然而在我看來,正是這種緊張讓斯海爾德河口和馬斯河以北的政治體系得以形成。
然而,如果說南北兩地在1572年之前就已是政治和經濟上基本獨立的地區,且此後也依然如此,那麼它們倒也確實發展出了統一的文化。這體現在宗教、思想和藝術方面,很大程度上也體現在語言和文學方面——對說荷蘭語的南部省份佛蘭德(Flanders)、布拉班特(Brabant)和林堡(Limberg)來說就是這樣。在這一方面,大起義確實造成了前所未有且決定性的分裂。北部實行加爾文主義的宗教改革時,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運動在南部取得勝利,大起義由此分裂了曾經一致的文化,以兩種相互衝突、敵對的文化取而代之。就這點而言,我們可以說大起義擴大並加深了早已存在於政治和經濟生活之中的二元對立。
我的研究主題是荷蘭共和國,但我並不希望在時間範圍和地理範圍上過於局限。我認為,要理解共和國,充分領會它在藝術、科學和精神生活方面,以及商業、航海、社會福利和技術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重要意義,我們既需要把故事的起源追溯至1572年之前很久,也需要了解取代了荷蘭共和國的巴達維亞共和國(1795—1806年),還需要研究比單純的北尼德蘭更廣泛的體系。在主要關注北部的同時,我將嘗試闡述南北之間的關係,比較雙方的異同,於是即便南部受到的關注較少,它也仍是這幅畫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也主張,在18世紀以前,尼德蘭和德意志之間不存在固定不變的邊界;尼德蘭和相鄰的德意志諸國轄區重疊,邊境地區紛爭不斷,最重要的是,二者在宗教和文化上相互影響,這一切都是本書故事中不可或缺、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它們卻常常被人忽略。因此,我不僅頻繁提及東弗裡斯蘭(East Friesland)、本特海姆(Bentheim)、林根(Lingen)、明斯特蘭(Münsterland)、蓋爾登(Geldern)、馬克(Mark)和於利希—克萊沃(Jülich-Cleves),而且力圖在一定程度上將
這些地區納入本書的整體視野。
最後,也許應該說明一下,在討論18世紀的最後幾章時,我有意盡量言簡意賅。讓故事在1780年戛然而止當然不合適——這個時間點正是E. H. 科斯曼(E. H. Kossmann)《低地國家(1780—1940)》(The Low Countries,1780-1940)一書的起始。如果我這樣做,就相當於無論故事如何完結,都把讀者棄在半路上。但是,像我處理本書其他部分的內容那樣詳細討論共和國的最後那些年,似乎既無必要又不可取,因此在本書最後兩章,我唯一的目標就是為主體部分展開的主題提供簡明扼要的結尾。
目次
第 1 章 導論 1
第一部分創建共和國, 1477—1588 年
第 2 章 邁入近代 9
第 3 章 1470—1520 年: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的緣起 47
第 4 章 1516—1559 年:領土合並 64
第 5 章 1519—1565 年:荷蘭宗教改革早期 87
第 6 章 大起義前的社會 125
第 7 章 1549—1566 年:哈布斯堡政權的崩潰 154
第 8 章 1567—1572 年:阿爾瓦公爵的鎮壓 184
第 9 章 大起義的開始 201
第 10 章 大起義與新國家的誕生 213
第二部分 黃金時代早期,1588—1647 年
第 11 章 1588—1590 年:共和國的鞏固 275
第 12 章 1590—1609 年:成為大國 284
第 13 章 共和國的體制 326
第 14 章 荷蘭世界貿易霸主地位的肇始 363
第 15 章 大起義之後的社會 388
第 16 章 新教化、天主教化與認信運動 429
第 17 章 身份認同的分化:《十二年停戰協定》 476
第 18 章 1607—1616 年:荷蘭政治體內部的危機 502
第 19 章 1616—1618 年:奧爾登巴內費爾特政權的傾覆 517
第 20 章 1618—1621 年:反抗辯派的加爾文宗革命 537
第 21 章 1621—1628 年:身陷重圍的共和國 571
第 22 章 1629—1647 年:迎來勝利的共和國 605
第 23 章 1590—1648 年:藝術與建築 654
第 24 章 1572—1650 年:智識生活 678
第三部分 黃金時代晚期,1647—1702 年
第 25 章 1647—1650 年:威廉二世執政期 713
第 26 章 社會 731
第 27 章 1647—1702 年:宗教 765
第 28 章 自由與寬容 813
第 29 章 17 世紀 50 年代:巔峰時期的共和國Ⅰ 839
第 30 章 1659—1672 年:巔峰時期的共和國Ⅱ 884
第 31 章 1672 年:災難之年 952
第 32 章 1672—1702 年:威廉三世執政期 965
第 33 章 1645—1702 年:藝術與建築 1031
第 34 章 1650—1700 年:智識生活 1062
第 35 章 殖民帝國 1117
第四部分衰落的時代,1702—1806
第 36 章 1702—1747 年:攝政官治下的共和國 1149
第 37 章 社會 1195
第 38 章 教會 1220
第 39 章 啟蒙運動 1244
第 40 章 1747—1751 年:第二次奧倫治革命 1280
第 41 章 蹣跚的共和國與“南部”的新活力 1293
第 42 章 1780—1787 年:愛國者黨革命 1316
第 43 章 共和國的落幕 1333
第 44 章 尾聲 1344
注 釋 1354
參考文獻 1479
譯後記 1537
書摘/試閱
第1章
導論
所謂的“荷蘭共和國的新世界”給17、18世紀歐洲內外的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無論他們是直接與這個“新世界”接觸,還是通過它的航海、貿易或書籍等印刷品間接與之相連。“新世界”持續地吸引著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學者、商人、神職人員、士兵、水手和藝術鑒賞家,至今仍在近代西方文明史上擁有重要意義。近代早期的觀察者尤其被這裡各個領域的創造力和數不勝數的新奇事物震撼。他們來到荷蘭,因這裡的景象驚奇——海運和商業規模驚人,金融行業和工業技術成熟,城市風景優美、秩序井然、乾淨整潔,宗教和思想實現了相當程度的寬容,孤兒院和醫院運行極佳,教會權力受到節制,軍隊從屬於市政權威,藝術、哲學和科學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當然,外國人在驚奇的同時,也常常表現出批判、不滿、鄙視,有時甚至是赤裸裸的敵意。對於外來者而言,共和國治下的荷蘭社會有許多特徵是畸形和可惡的。荷蘭當局準許多元教會並存,人們則有討論宗教和思想問題的自由,而17世紀末以前,這些事讓許多人驚駭。還有一些人不讚同給予婦女、仆人和猶太人等特定群體自由,這些群體在歐洲其他國家一直被限制在卑賤、拘束的生活狀態中,在其他歐洲人看來,荷蘭給這些群體的自由是過度的。外國貴族傾向於嘲笑荷蘭生活和政治中中產階級的做派,取笑他們不符合恰當的社會等級。17世紀,客渡駁船很少出現在歐洲其他地方,許多乘坐荷蘭客渡駁船旅行的外國紳士不安地發現,最普通的荷蘭百姓都能隨意地與他們交談,毫不考慮他們的等級,仿佛他們只是隨便哪個普通人。1694年,一個德意志人寫道:荷蘭省女仆的舉止和穿著都與她們的女主人十分相似,以至於很難判斷誰是主人,誰是仆人。 共和國的官方名稱是“聯省(the united provinces)”,歐洲人普遍認為這裡是神學、知識界和社會混亂的溫床,它顛覆了男性與女性、基督徒與異教徒、主人與仆人、貴族與非貴族、士兵與平民此前慣常且恰當的關係,倔強地拒絕給予貴族、士兵乃至丈夫應得的榮譽和地位。同時,對於大多數外國人而言,共和國的政治機構更應該被鄙視而不是讚賞。
因此,外國人想要效仿的事實上從來就不是荷蘭共和國“新世界”的全部現實。各個領域都有很多新奇事物,一般而言,他們對采納其中某種新方法更感興趣。那些渴望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人,學習並借鑒荷蘭的商業和金融手段。從16世紀90年代到1740年前後,在這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共和國在世界航海和貿易領域整體上居於首位,也是能想象到的各種貨物的中央倉庫。這個中央倉庫不僅儲存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商品,也匯聚了相關的商品信息、儲存和加工商品的技術、對商品進行分類和檢驗的方法,以及宣傳和商業洽談的方式。17世紀,即便是荷蘭商業繁榮的頭號勁敵,如路易十四的大臣柯爾柏(Colbert)和英國外交官喬治·唐寧(George Downing,唐寧街的名稱由此而來)爵士,都刻苦地仿效荷蘭模式,努力引進荷蘭技術。與荷蘭在世界貿易中的首要地位密不可分的是,共和國在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也是歐洲的技術領頭人,許多外國人關注這裡的技術發明,從造船方面的新工藝到改良的水閘、港口起重機、伐木機、織布機、風車、時鐘和路燈。這裡的外國人甚至包括在1697—1698年和1716—1717年兩次到訪荷蘭省的沙皇彼得大帝。關心農業技術創新的外國人相對較少,但是關注這一領域的人會在荷蘭的排水系統、園藝、飼料作物和土壤補給方式等方面發現大量技術革新,它們可以應用到其他地方,並帶來利潤。18世紀英格蘭農業革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借鑒聯省的技術和創新後實現的。另一些人則震驚於荷蘭市民生活的秩序井然、高效的福利體系、監獄和刑罰實踐以及低得驚人的犯罪率,這些都是荷蘭社會的顯著特徵。軍人則對聯省進行的軍事革命懷著強烈的興趣,尤其是在1648年之前的歲月裡。荷蘭軍事革命自16世紀90年代開始,由執政莫裡斯(Maurits)和弗雷德裡克·亨德裡克(Frederik Hendrik)推行,其特點是不僅火炮、戰略戰術、防御工事、圍城手段和軍事運輸方面有所革新,軍事紀律和秩序也大大提升。從16世紀80年代到17世紀中葉,尼德蘭的北部和南部都是新教歐洲和天主教歐洲的“重要軍事學校”;1672年到1713年,低地國家因位於路易十四與歐洲反法聯盟大決斗的戰略中心,又一次成了歐洲的主要軍事實踐場所。最後,還有一群傾心於學術和藝術的人,因聯省豐富的圖書館資源、科學收藏和出版商以及最重要的思想和宗教自由而絡繹不絕地前往荷蘭。這些人中有些是近代早期最偉大的哲學家,如笛卡兒(Descartes)、洛克(Locke)和培爾(Bayle)。笛卡兒斷言,世上再沒有別的國家,“可以讓你享受這種完全的自由”。
17和18世紀,外國人認為相比當時歐洲的其他社會,共和國賦予了它的公民、外國居民更多的自由,黃金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也確實特別強調自由。在荷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作家馮德爾(Vondel)創作的眾多戲劇中,唯一一部關於荷蘭特有主題的作品《巴達維亞兄弟》(Batavische Gebroeders,1663年),便是根據古代巴達維亞人——17世紀的荷蘭人將他們視為自己的祖先——從羅馬人那裡爭取自由的斗爭改編的。前文那位評論荷蘭女仆的德意志作家聲稱:“這裡的居民熱愛他們的自由勝過任何東西”。荷蘭共和國這種著名的自由基於良心自由。不過,正如英格蘭大使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爵士在1672年前後所寫,它延伸到了更廣闊的領域,創造了一種“普遍的自由與安適,它不僅僅局限於良心自由這一點,還擴展到其他能使生活方便、安寧的方方面面,大家各行其是,只關心自己的事情,毫不關心他人的事情”。義大利新教作家格雷戈裡奧·萊蒂(Gregorio Leti)曾在義大利、日內瓦和英格蘭生活。1683年,他定居阿姆斯特丹。在這裡的見聞令他歡欣鼓舞。他在荷蘭省感受到的真正的自由與義大利的腐敗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他看來,腐化墮落、體制性的專制和對個體尊重的缺失是威尼斯和熱那亞共和國的特徵。
沉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年)及其宣傳者將自由作為他們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核心正義原則。威廉在1568年發布宣言,解釋他為何拿起武器反抗尼德蘭的合法統治者:一方面,他提到西班牙國王侵害了各省的自由與特權,在十分有限的意義上使用了“自由”一詞;另一方面,他也採用了現代意義上的抽象說法,宣稱自己是自由的捍衛者。他強調,人民“過去享有自由”,現在卻被西班牙國王打入了“不可容忍的奴隸狀態”。大起義之後,相互敵對的各意識形態團體在定義各自的立場時,仍將自由作為核心要素。下述例子頗具代表性:1667年,共和國治下的荷蘭省三級會議頒布了它最著名的法案之一,即所謂的《永久法令》(Perpetual Edict,又譯作《排除法案》),廢除了荷蘭省執政一職,他們為此辯護的理由是,這對保護和推進自由而言是必要的。羅梅因·德霍赫(Romeyn de Hooghe)是17世紀末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也是奧倫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Ⅲ of Orange)積極的宣傳家。1706年,他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著作來描繪聯省,將它稱為“世界上已知的國家中”,生活“最自由、最安全的一個”。
不過在黃金時代,許多活躍在共和國裡最富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天才卻感到失望,他們發現這裡著名的自由覆蓋的範圍事實上並不夠廣。笛卡兒起初滿懷熱情,而到17世紀40年代,他開始憂慮自由的局限。斯賓諾莎(Spinoza)一直焦慮不安。作為17世紀荷蘭主要的共和派作家之一,埃裡克斯·瓦爾滕(Ericus Walten)崇敬自由,痛恨專制,最終卻因為瀆神的罪名而受到調查,死在海牙的監獄中。德霍赫也不得不從阿姆斯特丹搬到哈勒姆,以避免因傳播色情圖畫而遭受審訊。除此之外,格勞秀斯(Grotius)、埃皮斯科皮厄斯(Episcopius)和其他許多名人也有抱怨的理由。不過,在所有這些人看來,這種相對的自由仍舊是共和國提供的生活便利和有利條件之一——就算不是其中最寶貴的。
在那個時代,共和國真的特別有助於思想、想象力和才華的發展,它提供了許多學術書籍、科學研究收藏、藝術家的素材和神學家的不同觀點,其豐富程度是歐洲其他地方難以匹敵的。近代早期,歐洲眾多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化人物都誕生在北尼德蘭,或將這裡視為第二故鄉,他們包括伊拉斯謨(Erasmus)、利普修斯(Lipsius)、斯卡利杰爾(Scaliger)、格勞秀斯、倫勃朗(Rembrandt)、馮德爾、笛卡兒、惠更斯(Huygens)、弗美爾(Vermeer)、斯賓諾莎和培爾等。在大師們令人震驚地集中在這片如此狹小的土地上的同時,荷蘭在商業、航海、金融以及農業和技術方面處於首要地位,這不是巧合,它們有所關聯。此外,如果聯省沒有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維持著歐洲軍事大國的地位,沒能在更長的時間裡維持著世界主要海上強國的身份,上述成就一個也不能實現,更不能持久。即便在共和國的鼎盛時期,荷蘭的人口也不過200萬,但正是這個比其主要對手小得多的社會取得了上述所有成就。
一個地區眾多領域的創造力和成就同時飛速提升,歷史上這樣的時刻無疑是罕見的。當這種情況真的出現時,如古典時代的雅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人們常常驚奇地發現,這種持續的創造力常常限於相當狹小的地理空間內。同時,正是因為這種時刻的稀少和創造力的強勁,這種黃金時代難以用一般的歷史標準來評價。展現荷蘭黃金時代的全貌是困難的。不可避免,許多問題仍然無法涉及。因此,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另一種做法更具吸引力,即專注於荷蘭輝煌成就的這個或那個側面,如農業或航海,然後將其與歐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相關領域的發展進行比較。歷史學家確實常常這樣做,但考察這一極其豐富的圖景的全貌的做法則較少有人選擇。這種方法確實更費勁,然而完成這樣的壯舉是多麼有價值!對於每個曾了解過荷蘭共和國特定側面的人而言,通過不懈努力去領會它的全貌有助於加深和豐富他們對特定問題以及整體的認識。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