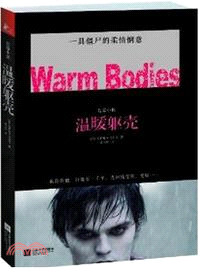商品簡介
這是R從未體驗過的經歷。他不再滿足於墳墓裡的生活,他想再次呼吸,他想重生。茱莉希望幫助他。然而,他們必須經過一番艱難的鬥爭才能改變那個灰暗而腐朽的世界……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艾薩克.馬裡昂(Isaac Marion) 譯者:白小洋
艾薩克.馬裡昂(Isaac Marion),出生於美國華盛頓西北部,一直生活在西雅圖及其附近地區。他曾有過各種奇異的工作經歷,諸如為臨終病人運送靈床或是監督一些父母看望被收養兒童。《溫暖軀殼》是他的處女作,寫成之後,驚豔文壇。
目次
編者序 在唯美裡遇見驚奇
缺失
我已經死了,但死亡並不是一件壞事。我已經沒有名字,我的名字可能是以“R”開頭;其他的我就不記得了。畢竟,我們僵屍的生命一無所有,沒有思想,沒有感情,沒有過去,沒有未來。直到那天我看到了她……
獲取
在這陰森的床上,躺在她的身邊,我可以清晰地記得從相遇到此時的點點滴滴。儘管我把過去成千上萬個時刻像高速公路的垃圾一樣丟掉了,但牙關緊閉的我確信:我會永遠記住這一刻。
新生
我穿過黑暗的進入通道,向另一頭的亮光跑去,不知道這是生存之道還是通往天堂之路。我是在來還是在去?不管怎樣,現在回頭太晚了。隱蔽在暗紅的夜空下,我踏入了活人的世界……
書摘/試閱
我已經死了。但死亡並不是一件壞事,對此我已能泰然處之。我很抱歉不能做個常規的自我介紹。我已經沒有名字了,我們幾乎都沒有名字。就像丟車鑰匙一樣,我們也丟掉了我們的名字;就像忘記周年紀念一樣不再記得。我的名字可能是以“R”開頭的,但其他的我就不記得了。有意思的是,我活著時總是忘記別人的名字。我的朋友M說,對僵屍來說,任何事情都是有趣的,但他們卻不能笑,因為他們的嘴唇都已經腐化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我們長得說不上好看,但我的情況要好點。我的軀體還處在腐爛的早期,我只是皮膚蒼白,身上有難聞的氣味,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人們看到我,會誤以為我是活人,只是需要休假而已。我穿著黑色休閒褲、灰襯衫,打著紅領帶。從這一身得體的穿著來判斷,我生前可能是個商人、銀行家、經紀人或者臨時工。M有時會取笑我。他指著我的領帶,想笑,但只是從肚子裡發出沉悶的聲響。M穿著一件乞丐裝和一件淺白色T恤。那件T恤已經很髒了,他當初應該選一件深色的。
我們喜歡拿我們的衣服開玩笑,並且猜測我們之前究竟是誰,這些衣服是我們僅有的線索。有些人的著裝很隨意,不像我穿的這麼明顯。他們穿著短褲、毛衣、便褲。所以我們也只是隨便猜猜。
你或許曾經是個服務員,或許是個學生。但你能聽到客人召喚的鈴聲或校園裡的鈴聲嗎?
永遠不會。
據我所知,沒有僵屍還清晰地記得什麼。我們的記憶只是對一個遠去的世界的模糊、片段的印象。這些微弱的印象如同幻肢一樣揮之不去。但我們還能認出文明的標誌——建築、汽車——但這些於我們沒有任何意義。我們沒有過去,只是此刻身居於此。時光在流逝,我們各行其是,從不產生什麼疑問。但就像我剛剛說的,這種情況感覺不錯。我們看上去沒有意識,但其實不然。這就像齒輪,雖然鏽跡斑斑,但仍在強勁地運轉,只不過輪齒被一片片磨掉,其外部運動不明顯了而已。我們呻吟、號叫、聳肩、搖頭,有時也蹦出幾個字。這與以前也沒什麼不同。
但令我感到悲傷的是,我們的確忘記了我們的名字。於我而言,最為可悲。我懷念我的名字,也為其他人難過,因為我愛他們,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我們幾百個僵屍居住在某個大城市外一個廢棄的機場裡。我們並不需要保暖或遮風避雨,只是喜歡住在牆壁和屋頂下的感覺;要不然我們此刻可能就正遊蕩在一片塵土飛揚的空地上,這將是一件異常恐怖的事情——我們四周空無一物,沒有可以觸摸的實體的東西,只有我們和廣漠無垠的天空。我想這就是徹底死去的狀態吧——絕對的、無際的空虛。
我想我們在這兒已經很長時間了。我身上的肉還算健全。但有些老者都已經形似骷髏,只是身上還粘著幾片乾癟的肌肉。但不管怎樣,肌肉還能伸縮,一直處在運動狀態。我從沒見過我們當中有人老死,也許我們是不死的。對於我們,未來如同過去一樣是一片茫然。我似乎對現狀也不必操心,因為時間並不緊迫倉促。死亡讓我變得從容。
M找到我時我正在乘電動扶梯。它們自動運行,我每天乘坐數次,都成了習慣。機場雖然已經荒廢了,但有時電力會突然運轉,可能是地下室裡的應急電機發出的。燈忽明忽暗,熒屏忽明忽滅,機器突然啟動。我很珍惜這樣的時刻——當事物獲得生命的時刻。我站在攀升的臺階上,就像幽靈在升往天堂。這是兒時甜蜜的夢想,現在只不過是一陣乏味的空笑而已。
在上上下下大約三十幾次後,我升到頂部,M在等我。他身高近兩米,幾百斤的肌肉和脂肪搭在骨架上。鬍鬚,禿頭,傷痕累累已經腐爛的臉——我走上樓梯頂時,他可怕的面容映入我的視野。他就是在天堂之門迎接我的天使嗎?他腐爛的嘴裡淌著黑色的口水。
他遠遠地指向一個模糊的地方咕噥說:“城市。”
我點點頭,隨他去了。
我們是要去尋找食物。當我們朝著城區慢慢挪動時,我們已經召集了一個獵尋隊。即使沒人感到饑餓,這樣的行動總是很輕易就能招募到成員。我們很少出現思想一致的時候,但當這一思想形成時,我們都遵循它;否則我們只能無所事事,一天到晚呻吟號叫。多少年來,我們也確實處在這種狀態。光陰就這樣逝去,我們身上的肉已經漸漸萎縮,而我們仍在這裡,等著它腐爛消失。我總是想知道我究竟有多大歲數。
我們獵尋食物的城市離我們很近,這倒給我們提供了便利。我們第二天午時左右到達目的地,接著便開始搜尋食物。饑餓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新奇的感覺。我們不是感到肚子餓——我們中有的甚至沒有肚子。但是一種空洞凹陷的感覺遍佈全身,就好像細胞在收縮。去年冬天有許多生還者加入了僵屍的行列,我們的獵物變得稀缺,因此我也得以目睹我的同伴們徹底死去。從僵屍到死屍只是一個平淡的過程。他們只是速度變緩,然後就停下了。過了一會兒我才意識到他們已經徹底死去了。起初,這使我感到不安。但是對此過多的關注反而違反我們的禮節。我號叫了幾聲,轉移了注意力。
我想世界大概已經終結了。當我們漫遊穿過城市時,發現城市像我們一樣破敗不堪:建築都已經倒塌;生銹的汽車橫七豎八,堵塞了街道;大多數玻璃都已經粉碎。風從空蕩蕩的高層建築吹過,發出淒涼的嗚咽聲——淒慘如行將就木的動物的呻吟。我不知道是什麼造成了這一切。是疾病?戰爭?社會滅亡?或者僅僅是因為我們?僵屍已經取代的活人嗎?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當世界末日到來時,你是什麼,都沒任何差別了。
我們來到一座荒廢的公寓樓前,便開始嗅尋活人的氣味。我們所要聞的不是汗水或皮膚的麝香味,而是沸騰的生命能量——就像閃電和薰衣草的離子氣味。但我們無法用鼻子聞到。這種氣味像芥末醬一樣滲入我們的身體內部,觸動大腦附近的某個部位。我們在樓裡集合,然後就向樓裡大舉進攻了。
我們找到了獵物。他們蜷縮在一個小工作室裡,窗戶都已經用木板封住。他們穿得比我們還差:身上只裹著幾片肮髒的破布,臉已經很久沒刮了。我們當中,只有M在他的肉身還存在時留著金色小短胡,其他的臉都很乾淨。我們不必再為刮鬍子、理髮、剪指甲而費心,這是死亡帶來的又一特權——我們不必再和生理機能作鬥爭。我們狂野的身體終於被馴服了。
我們吞食著活人,儘管動作緩慢笨拙,但內心卻很堅定。塵土飛揚的空氣中彌漫著槍聲,彌漫著火藥味;鮮血四溢,黑色的血液灑在牆上。我們只顧忘我地吃,即使丟失一隻胳膊、一條腿,甚至身體的大半截,我們也都漠視不顧——這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形象問題。但是我們中有的腦部中彈後就倒下了。顯然,在我們蒼白乾枯的軀幹裡還存在著一些重要的東西,沒有了這些東西,我們就只是死屍。我左右兩邊的同伴重重地摔在地上,甩出陣陣濕氣。但我們數量很多,佔據壓倒性優勢。我們撲在活人身上,盡情地吞食。
進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啃掉一個男人的手臂,但是我討厭這樣做。我討厭聽到他慘叫,因為我不喜歡痛苦,也不喜歡傷害別人。但現實世界迫使我們不得不如此。當然,如果我不把他吃完,如果我留下他的大腦,他還會站起來,跟我回機場。這可能會讓我感覺好些。我會把他介紹給大家,或許我們還會站在一起號叫一會兒。雖然說不上是“朋友”,但是這樣我們會更近一點兒。但前提是我得限制我自己,我留下充足的……
但我沒有也不能那樣做。一如往常,我徑直取精華部分——它能使我的大腦如同顯像管一樣豁然明朗。我吃掉了大腦,大約30秒之後,就有了記憶。遊行、香水、音樂等生活的記憶在我腦中閃現,然後消失。我站起身,我們踉踉蹌蹌地走出了城。雖然身體仍然灰白陰冷,但感覺好點兒了。確切地講,我們說不上感覺“好”,也不是“高興”,當然更不是“有活力”,只是感覺不那麼死氣沉沉了。這就是我們的最佳狀態。
我們漸漸遠離了城市。我拖在隊伍的後面,步伐比別人更沉重。在一個裝滿雨水的水壺旁,我停下擦洗臉和身上凝結的血跡。M退了回來,將一隻手搭在我肩膀上。他知道我討厭這些活動,他也知道我比大多數同伴要敏感一些。有時他會逗我,將我亂蓬蓬的頭髮盤成辮子,然後說:“女孩,變成……女孩。”但是當我心情沮喪時,他也會嚴肅起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只是看著我。他面部表情單調,但此刻我知道他要說什麼。我點點頭,我們又繼續前行。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必須要殺人。我不知道咬破一個人的喉嚨有什麼成就感。我竊取他的東西以填補我的空白。他消失了,我殘留了下來。肯定是上天某個瘋子立法者制定了這一簡單、無聊、隨意的規則。但為了維持自己的存在,我們必須遵循這一規則。我嚴格執行了它的規定。整個過程中我一直在吃,中間停了停,然後又接著吃。
這一切都是如何開始的呢?我們怎麼變成了現在這樣?是某種奇異的病毒所致?還是伽馬射線,古老的詛咒?抑或是一些更荒謬的東西?我們沒有討論過。我們生來如此,無需抱怨,也沒有疑問,只是做自己的事情。
我的內心與外部世界存在著很深的隔閡,我的感情無法將之穿越。當我發出呐喊時,外部世界聽到的是低沉的號叫。
在出站口,一雙雙饑餓的眼睛,或者說眼洞更為確切,在等候我們。我們將戰利品扔在地上——兩個完整的人、幾條肥碩的大腿、一具殘缺不全的肢體——全部還有餘溫。這些是我們的殘羹剩飯。我的同伴們撲上去,像動物一樣在地板上開始了美筵。肉體細胞中殘留的生命能量可以維持僵屍不死,但不親自獵食的僵屍永遠得不到滿足。這就像出海的人由於吃不到水果和蔬菜,會因為缺乏營養而變得委靡、虛弱,總是感到饑餓。饑餓是一隻孤獨的野獸,它不情願地接受殘肉和留有餘溫的血。但它真正渴望的是親密感——那最終時刻在我們眼神之間流動的冷漠的關聯感,就像那黑暗消極的愛。
我向M揮揮手,然後離開了群體。我雖已習慣了僵屍發出的無處不在的惡臭,但今天這味道出奇得臭。對於我們來說,我們可以呼吸也可以不呼吸,但我需要一些空氣。
我慢慢走出去,來到走廊裡,踏上了行李輸送帶。窗外的景象在我眼前劃過。外面空空蕩蕩,跑道上長滿了雜草和灌木叢,綠意一片。龐大的白色飛機一動不動停滯在水泥地上,就像一條條擱淺的鯨魚。啊,白鯨,終於被征服了。
我靜靜地站在輸送帶上,看著外部世界在我眼前劃過,思想幾乎一片空白。這在我活著時可能永遠無法做到。我記得曾經的努力和往日的雄心壯志,我記得曾經我總是目標明確。而現在,我只是站在輸送帶上,任它帶我向前。我到了終點,轉身又返回去。剛才的世界消失了。死去真的很容易。
我這樣重複了幾個小時後,突然發現在輸送帶對面站著一個異性。她耷拉的頭搖來搖去,但不像我們,她走路不搖晃,也不號叫——我喜歡她這一點。當我們走近時,我緊緊地盯著她的眼睛看。曾有一瞬間,我們並排站立,相距僅幾尺;接著擦身而過,各自走向大廳的一頭;然後轉身看看對方,又回到了輸送帶旁。當我們再次相互走過時,我朝她笑了笑,她也向我笑了笑。第三次我們彼此經過時,機場停電了。我們停下來,整好站在一條直線上。我呼哧呼哧說了一聲“你好”,她聳聳肩,算是回應。
我喜歡她!我伸出手摸了摸她的頭髮。她也處在腐爛的早期,膚色蒼白,兩眼深陷,但骨頭和器官並沒有暴露出來。如同其他僵屍一樣,她的虹膜是奇異的淺灰白色。她穿著一件黑裙子和合身的白色上衣。我猜她生前可能是個接待員。
她胸前別著一個銀色的名牌。
她有名字。
我使勁盯著名牌看,向前傾,臉離她的胸只有幾寸遠,但這於事無補。名牌上的字母在我的眼裡旋轉倒置,無法穩定下來。像往常一樣,我看不懂這些字母,對我來說,它們只是一行沒有意義的文字。
這裡又出現了一個M所謂的經典諷刺:名牌和報紙上寫著我們的問題的答案,它們就在我們的周圍,但我們卻不會閱讀。
我指著名牌,看著她的眼睛問:“你的……名字?”
她只是茫然地看著我。
我指著自己,發出了我名字的殘餘部分:“Rrr。”然後我再次指向她。
她垂下眼睛看著地面,搖了搖頭。她也不記得了。她甚至不記得一個音節,還不如我和M。她徹底沒有身份。但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我牽住她的手離開了輸送帶,我們的胳膊伸在護欄外面。
我們相愛了,要不然能是什麼情況呢。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