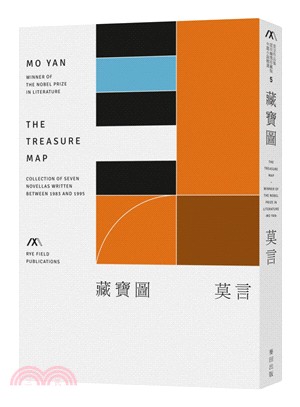商品簡介
●201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繼《透明的紅蘿蔔》之後,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說集。
●特別收錄:莫言親筆手寫毛筆總序、 莫言鮮為人知的珍貴照片
「莫言將夢幻寫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社會合而為一。」──諾貝爾獎委員會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本書精選莫言七篇中篇小說:〈模式與原型〉、〈我們的七叔〉、〈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師傅愈來愈幽默〉、〈野騾子〉、〈藏寶圖〉。
藏寶圖裡有什麼?藏寶圖裡藏有各種稀奇古怪的人生百態。
一根能看出人的動物原形的通靈虎鬚;一個活得像條狗的男人;有著奇異靈魂的駝子;將公共汽車改造成男男女女幽會野合場所的老翁;被丈夫背叛也要帶著兒子活得像個男人的女人……。故事中的男男女女,他們的韌性與掙扎、欲望與無奈,在莫言筆下躍然生動。
莫言的創作大膽奔放,言人不敢言,寫人不敢寫。他以幽默荒誕的手法,展現他對土地、人性、現實的關懷。這部中篇小說集,可以看到莫言成熟的寫作風格,以及創作歷程中階段性的轉變。
作者簡介
莫言 Mo Yan
本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一九五五年二月生。
少時在鄉中小學讀書,十歲時輟學務農,後應徵入伍。
曾就讀於解放軍藝術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
一九九七年脫離軍界到地方報社工作。
一九八○年代開始寫作,至今已累積上百部作品。
著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食草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勞》、《蛙》;中篇小說集《紅耳朵》、《冰雪美人》、《透明的紅蘿蔔》、《藏寶圖》;短篇小說集《蒼蠅.門牙》、《初戀.神嫖》、《老槍.寶刀》、《美女.倒立》,散文及其他《會唱歌的牆》、《小說在寫我》、《說吧!莫言》、《我們的荊軻》、《盛典:諾貝爾文學獎之旅》等。
莫言是當代最被國際注目的大陸作家,作品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並受邀到世界各地演講。於2004年獲頒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獲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09年被推選為德國巴伐利亞藝術科學院通訊院士,2010年被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LA)推選為會員。
所獲重要獎項包括:
2012諾貝爾文學獎
2011茅盾文學獎、韓國萬海大獎
2008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紐曼華語文學獎、香港浸會大學‧華語長篇小說紅樓夢獎
2006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
2005義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
2004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
2001法國Laure Bataillin外國文學獎、聯合報十大好書獎等。
目次
台灣版序
模式與原型
我們的七叔
牛
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
師傅愈來愈幽默
野騾子
藏寶圖
書摘/試閱
模式與原型
一
急煞車使狗的額頭撞在了冰涼的帆布車篷上。車裡的警察弓著腰站起來。一個警察拔開了囚車的插銷,車門便自動地往外開了。
警察們笨手笨腳地跳下去,站在車門的兩邊。其中一位紅臉膛、大耳朵的小個子警察對著車裡喊:「狗,下來!」
突然湧進來的光明和涼氣刺激得狗眼流出了淚水。他看到車下那幾位警察臉都閃爍著寒冷、扎人的光芒,宛若河道裡的冰塊。他的腦子昏昏沉沉,思緒像天上的流雲一樣飄遊,無法定位。車上那位還沒跳下去的警察,從背後推了狗一把,大聲說:「下去,讓你下去,聽到了沒有?」
狗咧咧嘴,迷迷糊糊地問:「這是哪兒?」
「這是東北鄉,你的老家!」車上的警察不耐煩地說著,又推了他一把。
狗用戴著銬子的雙手抓著那位警察的胳膊,哀求道:「政府,好政府,你們斃了我吧,我不願意看到鄉里的人……」
車下的警察抓著他的腳往下一拖,車上的警察就勢把他往下一推,於是他就沉重地跌在了被嚴寒凍得裂了縫的堅硬土地上。
由於手不方便,狗的臉先於身體觸到了地面。他感到鼻子一陣痠痛,牙齒和雙唇嘗到了泥土的味道。幾隻手叉著他的胳膊將他提起來時,他感到有兩股溫熱的液體從鼻子裡流出來。一低頭,他看到有一些大顆粒的血珠子劈劈啪啪落在地上。血珠落地,破成一些更小的血珠兒在地上滾動一陣,然後才湮到地裡去。他感到整個臉都不屬於自己,只有那兩道熱辣辣的流血的感覺存在著。有一些血珠兒流進口腔,讓他的舌尖嘗到了血液的腥味。
一位英俊的警察從褲兜裡掏出了一塊揉搓得皺皺巴巴的粉紅色手紙,遞給那位紅臉大耳的小個警察,說:「給他堵堵。」
小個警察看一眼同伴,極不情願地接過紙,剝開,嘟囔著,把紙在狗的鼻孔下輕描淡寫地按了按,然後扔掉。看著那塊沾在地上的紙,小個警察說:「他媽的,來例假也不挑個時候。」
狗對警察們的斥罵已經習以為常。一個放火燒死親娘的人還有什麼尊嚴好講呢?幾個月的教育,已經使他相信自己連條狗都不如。
--你的名字叫狗?
--是。
--你連條狗都不如。
--是。
英俊警察看看地上的髒紙又看看狗繼續流血的鼻孔,訓斥那位小個警察:「笨得你!我讓你把他的鼻孔堵住!」
小個警察斜著眼睛瞅一下英俊警察,罵罵咧咧地低語著,把地上那塊沾血的紙撿起來,撕成兩半,搓成兩個團兒,走到狗面前,罵道:「低下你的狗頭!」狗順從地低下頭。小個警察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腳,罵:「仰起你的狗臉!」狗順從地仰起臉。他感到小個警察惡狠狠地把那兩團沾著沙土的紙捅到自己的鼻孔裡,冰涼的疼痛飛一般地擴散到他的雙耳裡去。他忍不住地哀嚎起來。
「還他媽的嚎!」小個警察又踢了他一腳。
英俊警察嚴厲地盯了小個警察一眼,說:「你注意點。」
小個警察啐著唾沫,走到一根枯樹枝般戳在地裡的水管子旁,煩惱地擰龍頭。擰了半天也沒有水流出來。小個警察踹了水管子一腳,罵道:「聾子耳朵--擺設!」水管子晃動著。水管子周圍結了一層青白色的厚冰。水管子烏黑,顯示出煙燻火燎過的痕跡。小個警察在那片冰上滑了個趔趄,險些跌倒。然後他向一道圍牆走去,圍牆的背陰處,有一些陰森森的積雪。小個警察抓起雪搓手,一邊搓一邊罵。搓一陣,走回來,在一棵粗糙的楊樹幹上擦手。狗看到小個警察的雙手凍得通紅。
狗還看到小個警察的兩扇大耳朵也凍得通紅,他緊接著感到那兩扇大耳朵冰涼、僵硬,有一些格外鮮紅的地方是凍瘡,尚未潰爛。狗看到小個警察響亮地擤出一些清鼻涕抹到楊樹上。楊樹上還抹過許多人的鼻涕。狗已經辨認出了這是東北鄉政府的大院子,那棵楊樹曾經拴過狗的驢車也拴過狗自己。狗看到今天是一個乾冷的天氣,時辰是上午,太陽在東南方向兩竿子高處掛著,陽光應該算明媚但不溫暖。狗看到英俊警察和他的三個同伴都不停地踏著步,搓著手,往手上哈氣。一團團的白氣從他們的嘴裡、鼻孔裡呼呼地噴出來。狗看到小個警察的手上也冒熱氣兒。狗看到這幾位縣裡來的警察都穿得很單薄,肚子裡也沒有什麼油水。狗不曉得他們為什麼要冒著嚴寒把自己拉回到東北鄉。狗感到這些警察也挺不容易,他心裡有些愧疚。奇怪的是狗儘管衣不遮體,但並不感到十分寒冷,面對著那些為抵禦嚴寒不停地蹦跳的警察,狗感到他們像一些扮鬼相的猴子。狗只是感到身體麻木,一行一動都不方便,四肢不聽指揮,否則也不會像個死人一樣實趴趴地跌在地上。狗感到手腕上的銬子已經把太陽的熱傳達到自己手腕上。狗在銬子狹窄的平面上能夠很費勁地看到自己狹長的臉,這張臉連狗自己都厭惡。狗看到牆上的磚頭有紅色的也有黑色的,牆根上有白雪也有灰色的煤渣子。狗看到路邊的草上沾著一層毛茸茸的霜花。狗嗅到了一股朝氣蓬勃的生活氣息。這氣息與其說他是用鼻孔嗅到的,還不如說他用眼睛看到、用耳朵聽到、用腦子回憶到更為準確,因為他的鼻孔裡堵著紙,他感到鼻子已經凍凝了。
囚車冒著黑煙在空地上拐了一個彎,然後熄了火,開車的警察跳下車,打火抽菸。那打火機不好用,啪嚓嚓打了幾十下也不著火。一個警察說:「老趙,扔了吧,幾十下打不著,還要它幹麼。」
司機警察說:「沒油了。」說完就走到囚車旁,擰開油箱蓋,沾一些汽油,滴在打火機筒裡的棉絮上。
狗感到自己已在鄉政府大院裡站了許久,而鄉政府大院像一個冷冷清清的廢磚窯,人都到哪裡去了呢?臉皮永遠被酒精燒灼得通紅的鄉委書記哪裡去了?肥胖得像小熊一樣的鄉長哪裡去了?還有那比男人還像男人的女副鄉長哪裡去了呢?狗運動著稀粥一樣的腦漿費力地思想著。他不明白警察們來這兒幹什麼。狗抬頭看到一群麻雀在蕭條的樹枝上跳動著,他是先聽到了雀叫才抬頭。他的眼睛裡有淚水,涼涼的。他知道自己是沙眼,一見風、一著涼就淌淚。狗看到鄉政府的房屋上有很多並列著的、一模一樣的門窗,門窗上的油漆都因為風吹日曬褪了顏色,狗記得它們原來都是碧綠的。突然間有很多鐵皮煙囪從磚牆上伸出來,洶湧地冒出了焦黃的煙霧。那些煙濃厚極了,像海綿一樣。狗看著那些盤旋扭動的煙霧,感到自己深陷在淤泥的深潭裡,愈掙扎陷得愈深,那些焦黃的濃煙團團旋轉著包圍了他。是那火紅色的大公雞撕肝裂膽般地啼叫聲,把他從沉綿的夢魘狀態中驚醒,他張大嘴巴吸了幾口氣,然後,不顧警察的咋呼,用手背把鼻孔裡的紙團揉出來,兩股凜冽的冷氣宛若鋼錐沖進去,直透天靈,儘管痛苦銳利,但腦子頓時清楚了許多,那些纏繞得讓人呼吸困難的煙團,也裂開了縫隙,於是他看到了兩隻站在雜色磚頭砌成的牆上、面對著金色的太陽、抻頸奓羽啼鳴的公雞。公雞斑斕的羽毛光澤華麗,在陽光中閃爍,雞冠和顫抖的尾羽,宛如抖動的紅色與藍色混雜的火苗兒,親切地喚起了他沉痛的記憶。
公雞佇立牆頭,機械地轉動著腦袋。幾隻羽毛灰褐色的母雞先是在牆根下的垃圾裡漫不經心啄著什麼,後來都停止了啄食,像接到了命令的士兵一樣,咯咯叫著,朝公雞佇立的牆頭飛去。這些格外肥胖的母雞的飛行簡直像一場滑稽表演,牠們都有飛的強烈意識,但都缺乏飛行的能力。在距離公雞半米高處,就像一團團草坯,沉重地跌落下來,隨著牠們的身體飄飄落下的,是牠們振動翅膀時脫落的骯髒羽毛。
狗看雞,入了迷,使他短暫地忘掉了困厄的處境,恍惚如坐在生產隊的場院裡等待著生產隊長派活兒。那時候生產隊飼養棚裡的牛馬正被兩個專職飼養員依次拉出來。飼養員一正一副。正飼養員是上三代都是雇農的老貧農孫六。孫六,六十歲左右年齡,禿頭,嘴裡只剩下一顆孤獨的長牙。副飼養員是一位刑滿釋放分子,姓沈,四十歲左右年齡。瘦小的個頭,顯得有幾分文質彬彬。瘦得肋骨凸凸的牛馬晃晃蕩蕩地走出飼養棚,到一只安放在水井邊的大缸飲水,一股好聞的、熱烘烘的牛屎味道撲進狗的鼻子。牛呼呼地喝著水,拉著屎,撒著尿,屎和尿冒著縷縷短促的乳白色熱氣,井裡冒出一團氤氳的熱氣,井台上結著冰砣子……隊長說:狗!
狗從沉思遐想中回到這個嚴酷的上午,鄉政府那一排房屋上的鐵皮煙囪裡的焦黃煙霧都變成了藍色的淡煙。一扇門開了,一位身穿警服、光著頭的鄉村警察弓著腰小跑過來。狗一眼就認出了這個四十多歲的邋遢男人是鄉派出所的吳所長,外號「吳尿壺」。他曾親手把一副生了鏽的舊手銬套在狗手腕上。因為鑰匙失靈,開銬時動用了小鋼鋸。狗看到吳所長齜著被菸茶染黃的牙齒,很歉疚地笑著,顛顛地小步跑著,在距那位縣裡來的英俊警察幾步遠的時候,就伸出了他那隻沾滿煤灰的大手,用沙啞的喉嚨喊:
「啊呀呀,宋隊長,這麼早就來了……」
那位英俊的宋隊長及時地將雙手插進褲兜裡,用冷漠的神情對著灰禿禿的鄉村警察的滿臉熱情,冷冷地說:
「吳所長,難道你們沒接到電話?」
「接到了,接到了,」吳所長把那隻大手羞答答地縮回來,摸著衣角,說:「這麼冷的天,俺尋思著領導同志們就不來了呢……」
「怎麼會不來?!」宋隊長威嚴地說,「說定了的事情怎麼會不來呢?你們書記呢?鄉長呢?」
吳所長摸摸光頭,咳嗽一陣,說:「年關到了,書記和鄉長上縣去了……關鍵是集上還沒有幾個人,同志們先進屋暖和暖和……」
「真他娘的不像話!」小個子警察罵起來。
吳所長看看狗,眼一瞪,對準狗的頭,搧了一巴掌,罵道:
「都是你這狗日的!攪得雞狗不得安寧!」
吳所長又搧了狗一巴掌,就前去拉開門,讓縣裡的警察進屋。狗對這個搧自己腦袋的鄉警並無惡感,他看到鄉警褪色的警服上,有一塊巴掌大的油污,很鮮明地在背上,形狀像一隻烏龜。
警察們進了屋,吳所長說:
「狗日的,你在外邊涼快著吧!」
宋隊長說:
「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讓他進來。」
吳所長說:
「狗日的,那就進來吧,還不快謝謝宋隊長!」
狗的目光穿過冰涼的淚水,看著屋裡模糊的景物,想按照吳所長的教導向宋隊長道謝,但他張不開嘴。他用手背沾了沾眼裡的水,畏畏縮縮地靠在牆角,盡量緊靠牆壁,少占空間,因為小小的房間裡,已經滿是警察了。
狗知道這間屋子是吳所長的辦公室兼宿舍。狗看到一張破舊的鐵床占據了房間的六分之一,床上的被子髒極了。吳所長手忙腳亂地把被子捲起來,露出了一張墊在褥子下的黑狗皮。
吳所長說:「請坐請坐。」
兩個警察一齊坐在那張床上,床又搖晃又咯吱。吳所長從那張破桌子上拎起警帽,扣在頭髮花白的腦袋上。桌子上顯出了一個清晰的帽印,其餘的桌面上落著一層厚厚的灰塵。吳所長彎著腰捅爐子,又捏著煤鏟子往爐子裡填煤。一股嗆鼻子的黑煙從爐底返出來,警察們咳嗽起來。英俊警察說:「老吳,你想把我們嗆死嗎?」吳所長說:「怎麼敢怎麼敢呢?窮鄉破所,沒有好煤燒,哪能跟縣局裡比?去年冬天我去局裡開會,看到院子裡堆著小山一樣的﹃大同塊﹄,小斧頭劈開,茬面明晃晃的,像瀝青一樣,填到爐子裡,嗚嗚地響,火旺生風,屋子裡熱得光著脊梁都不覺冷。都是警察,您在城裡享的是什麼福?您說是不是宋隊長?」
宋隊長不理吳所長的嘮叨,擼起袖子看看錶,說:「這東北鄉人,怪不得窮,都快九點了,還不出來趕集。」
吳所長說:「宋隊長,您可是說差了,東北鄉人勤快得很。」
宋隊長說:「九點,準時遊街,老吳,讓你準備的鑼鼓家什呢?」
吳所長說:「不用準備,文化站就有,隨用隨拿。」說著,他撿起一顆訓練用的木柄手榴彈敲著牆壁,大喊:「小高!小高!」
隔壁門響,一個縮著脖子、留著大分頭的小伙子推門進來,說:「吳老尿,麼事?」
吳所長說:「我日你大爺,你個屁臨時工也敢叫我吳老尿?去找找文化站的喬美麗,讓她把鑼鼓家什拿出來,待會兒遊街用。」
「遊街?遊誰?」小高一歪頭看到了縮在牆角的狗,說,「哎喲,是狗呀,我還以為早把你斃了呢!」
狗憤怒地看著留著大分頭、一臉粉刺疙瘩的小伙子,舉起雙手砸過去,小伙子一歪頭,狗的銬子砸在他的脖子上,痛得他齜著牙叫喚。
吳所長說:「活該,再讓你貧嘴薄舌!」
那挨了打的小高罵道:「吳老尿,吳老尿,啤酒瓶裡撒泡尿,迷糊糊喝一口,咦,變質啤酒不起泡!」
縣裡來的警察們哈哈大笑起來。小個警察戳戳老吳的腰,問:「哎夥計,是真的嗎?」
吳所長滿臉通紅,說:「沒有這回事,這幫小兔崽子吃飽了閒著沒事就瞎編排我,咱老吳再迷糊也不能把尿當啤酒喝,您說是不是?」
英俊警察又擼起袖子看了看錶,說:「九點了,不等了,早遊完早回去。」
吳所長說:「哎呀,急什麼嗎?等會兒等會兒,等日頭再上上。」
英俊警察說:「老吳,你別囉唆,快去找鑼鼓家什。」 吳所長扔掉爐鉤子,拉門時看看狗的臉,歎一口氣,說:「狗呀狗,我教育了你多少次,要你孝敬你娘,你倒好,一把火把老東西給燒死了!害得我寒冬臘月裡也不得安寧。」
狗此刻正被屋子裡的溫暖折磨著,就像一棵凍透了的白菜突然移到爐邊烤著,外表糜爛成泥,裡邊還是一坨冰,那滋味難以描述。他只看到吳所長開合著嘴巴,迸出一些奇形怪狀的聲音,宛若燃燒後的紙燼,在房間裡輕飄飄地飛舞著。
門在吳所長身後在狗的面前被響亮地關上了。狗被這堅硬的聲音撞擊一下。但隨即門又半開了,伸進來了吳所長戴著骯髒的警帽的腦袋和半截身體。他用醉醺醺的眼神盯著狗,沒頭沒腦地說: 「也許你還有冤枉?」 狗忽然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煩惱,對著吳所長那張邊緣模糊的臉啐了一口,以前所未有的野蠻態度罵了一句: 「操你娘!」 吳所長懵懂了,眨巴著眼皮想了半天,忽然蘇醒過來似的,長出了一口氣,說: 「你這狗崽子。」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