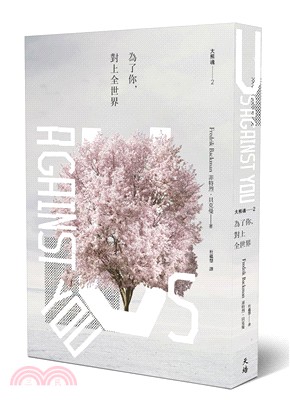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42元
商品簡介
被他擊碎的是我,但憤怒的是你們
比身為受害者更不幸的,是你們在我手中成為受害者
我無法修復你們的傷,無論我多麼想
這是有關愛的故事,有些人被愛、有些人相愛、有些人不愛了,有些人只是彼此的「錯誤」。有時候好人會做出可怕的事,因為他們相信如此能保護所愛之人。有時候恨一個人是如此輕而易舉。
當一個男孩,冰球隊的耀眼新星,強暴了一個女孩。大家就此失去方向。相信謊言很簡單,真相太困難。但是在謊言裡,每個人逐漸分崩離析。夫妻不再緊握彼此的手、有良知的人因愧疚而不斷傷害自己、失去信念的人迷失在酒精裡、年輕人會在黑暗的森林裡互鬥至死、有祕密的人招架不住沉默的壓力,暴力就這樣在這裡蔓延。
然而,這是他們的小鎮。兩支冰球隊之間的敵對狀態演變成一場金錢、權力,以及生死存亡、彼此糾纏的瘋狂掙扎。還有所有圍繞著冰場跳動的心,那些依然懷抱夢想,努力拚搏的人們,如何彼此扶持。有些人會陷入愛河,其他人則被擊垮;會有非常成功的日子,也有一塌糊塗的時候。然而,這個小鎮會重新透出生氣,但是星星之火也同時悄悄燃起。我們將會聽見一聲震天巨響。因為,他們賭上一切,對上全世界。
本書特色
★ 百萬暢銷作家菲特烈.貝克曼最新長篇小說,又深感人心的溫暖之作。
★ 菲特烈.貝克曼《明天別再來敲門》、《清單Hold不住的人生》、《阿嬤要我跟你說抱歉》三部作品英文版銷售超過千萬冊。
★ 《明天別再來敲門》改編電影二○一七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決選入圍。
★ 本書出版即上美國《紐約時報》排行榜小說前五名。
★ 本書即將改編同名影集,眾所期盼。
★ 喬喬‧莫伊絲(電影《我就要你好好的》原著作者)、張亦絢(作家)、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教務主任)感動推薦
作者簡介
菲特烈.貝克曼是瑞典超人氣部落客和專欄作家。他的處女作《明天別再來敲門》曾獲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暢銷書榜首,在全球銷售超過百萬本,並被改編成獲獎無數的電影。貝克曼另外兩本小說《阿嬤要我跟你說抱歉》以及《清單Hold不住的人生》也都一舉躍上瑞典出版界排行榜榜首,並且長據美國《紐約時報》排行榜小說前十名,更是全美年度暢銷書第二名。他善於運用幽默、溫馨的筆調敘述動人心弦的故事,即使故事中有殘酷現實,他仍能發掘出激勵人心的力量,且一點都不落俗套。
譯者簡介 杜蘊慧
喜愛親近自然、接觸不同語言及文化、立志一輩子保持好奇心。由於無法安安分分只做一種工作,現於美國南加州從事品牌行銷、中英法文翻譯、植物插畫、語言及繪畫教學、產品設計工作。閒暇時在國家公園擔任原生植物復育義工。
名人/編輯推薦
媒體讚譽:
貝克曼重回為冰球痴狂的瑞典小鎮,重續《終將碎裂的我們-大熊魂1》裡小鎮居民的熱情、暴力、堅毅、以及人性。貝克曼這本出色的小說結合了斯堪地那維亞傳說和希臘悲劇的特色,黑暗和挫折伴隨溫柔及生氣,毫不保留為小鎮氛圍注入活力。──《出版人週刊》
這部貝克曼的作品具有豐沛的讀書會討論主題潛力;他探討了暴力、政治手腕、社區、女性主義、性別差異、犯罪、運動在社會中的角色,以及令我們每個人感到坐立不安的隱憂。──《圖書館期刊》
貝克曼筆下個性迥異的主角們彼此糾纏串聯,終於引發一場無法避免的大爆炸,固然令大熊鎮更哀傷,或許卻也更睿智。貝克曼描寫的這座小鎮,尤其能與置身種族歧視、恐同、以及憎恨女性等問題的社區居民產生共鳴。──《書頁評論》
貝克曼藉本書傳達對世俗的諷刺和希望,而他的寫作技巧使此兩者令人難以抗拒。──《柯克斯評論 》
在菲特烈貝克曼的作品中,我們看見絕妙的文字和洞悉事件真義的卓越眼光──對與錯、恐懼與勇氣、愛與憎恨、友誼和忠誠的重要性與極限,不一而足。貝克曼是現今世上最棒、最有趣的小說家。和全世界的優秀小說家站在一起,他的身影媲美巨人──而這位巨人的分量仍在與日俱增之中。──《華盛頓時報》
貝克曼創造了情感細膩的國度,遠比書中的瑞典小鎮還龐大……一本能令讀者深陷其中的小說。──《芝加哥論壇報》
本書以敏銳的角度探索復原與重生。──《美國周刊》
假如亞力山德麥考史密斯和梅芙.賓奇的小說有愛的結晶,必會是瑞典作家菲特烈.貝克曼的作品。貝克曼以幽默的態度接納人類的惡習與失敗,他與眾不同的風格中還結合了對筆下人物既寬廣又富同情心的視角。他的小說吸引了廣大的書迷,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本小說帶我們目擊了社區的傷口復原、家庭重整、主角們成長的過程。──《華盛頓郵報》
無庸置疑,貝克曼所有的小說都以令人屏息的優雅手法描繪出人性的真實面。──《柯克斯評論 》
目次
2 三種人
3 像個男人
4 女人永遠是禍水
5 人人都有上百種面貌
6 如果沒仗可打,他們也會自己開戰
7 從吃午餐開始
8 當關係破裂的時候
9 今晚他需要找個打架的對象
10 你該怎麼對孩子解釋?
11 最後一次成為贏家的機會
12 我準備在此燃燒
13 於是他們給了他一支軍隊
14 陌生人
15 維達.瑞紐斯
16 大熊鎮對上全世界
17 嗜血而來,縱火而去
18 女人
19 一樣的藍色馬球衫
20 鞋子裡的刮鬍膏
21 他躺在地上
22 隊長
23 「為了唯一要緊的事付出所有」
24 她體內的大熊才剛甦醒
25 母親的歌
26 這裡會變成誰的小鎮?
27 憎恨和混亂
28 「該死的玻璃!」
29 她在那裡殺了他
30 他們這種人不該有好下場
31 黑暗
32 然後他拿起獵槍走進森林裡
33 醒不過來
34 對警用馬匹施暴
35 只要你是頂尖的
36「難道變態就不散步嗎?」
37 我們的能耐
38 比賽
39 暴力
40 永遠公平,也永遠不公平
41 如果你們抬頭挺胸
42 他們氣勢如虹
43 我們無處不在
44 狂飆突進
45 櫻花樹
46 我們會說是場意外
47 我們永不會忘記的愛情故事
48「喔,老天!喔,老天!我的寶貝!」
49 每個人都有一支球棍。兩座球門。兩支隊伍。
書摘/試閱
1 總歸是某人的錯
這個故事是事件的後續發展,時間是當年的夏天到隔年冬天。講的是大熊鎮和鄰居海德鎮,以及兩支冰球隊之間的敵對狀態如何演變成一場金錢、權力,以及生死存亡彼此糾纏的瘋狂掙扎。它也講冰場還有所有圍繞著冰場跳動的心;講人和運動,以及兩者之間如何彼此扶持。它講的是我們這些懷抱夢想,努力拚搏的人們。我們有些人會陷入愛河,其他人則被擊垮;我們有非常成功的日子,也有一塌糊塗的時候。這個小鎮會重新透出生氣,但是星星之火也同時悄悄燃起。我們將會聽見一聲震天巨響。
有些女孩將令我們驕傲;有些男孩將令我們功成名就。身穿不同顏色服裝的年輕人們會在黑暗的森林裡互鬥至死。一輛車將會在夜裡飆行。我們會說那是一場意外車禍,但是意外總是需要機會才能發生,而我們會知道這場意外原本是有辦法避免的。總歸是某人的錯。
我們愛的人會死。我們會將自己的孩子們埋在最美的樹底下。
2 三種人
砰──砰──砰──砰──砰。
大熊鎮的最高點是鎮裡最後一棟建築物往南去的小丘。從大熊丘上的豪宅區,你可以一眼望見底下靠近鎮中心的工廠、冰館、成排住家樓房、以及大熊漥的出租公寓區。兩個女孩站在大熊丘上,俯瞰她們的小鎮。她們是瑪亞和安娜,很快就要滿十六歲了,很難斷定她們是因為無視於彼此的差異,或是因為她們毫無差異所以才成為閨密。她們其中一個愛樂器;另一個愛槍。她們厭惡對方的音樂品味,使得這個話題和寵物一起成為她們延續了十年的兩個主要鬥嘴內容。去年冬天兩人一起在歷史課上被趕出教室,因為瑪亞偷偷說:「安娜,妳知道誰喜歡狗嗎?希特勒!」而安娜不甘示弱:「那妳知道誰喜歡貓嗎?約瑟夫.門格勒!」(譯註:納粹集中營醫生,利用四十萬名囚犯進行人體實驗並致死)
她們永遠在鬥嘴,但是無條件地愛對方。從她們小時候起,有些日子裡她們覺得是兩個人合力對抗全世界。今年早春時瑪亞遭遇到那件事之後,這種感覺更強烈了。
現在是六月初。這裡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是被封存在冬天裡,但是在這個時節,會有幾個星期是令人欣喜的夏天。包圍她們的森林像是吸飽了陽光而酣醉,湖邊的樹木快樂地擺動著,但是女孩們的眼神充滿警戒。通常對她們來說,一年的這個時候正充滿無盡的冒險;她們會在大自然裡耗上一整天,天黑之後才穿著勾破的衣服,滿臉髒兮兮地回到家,眼裡滿是童年。如今這一切已不復在。
她們已經是大人了。對某些女孩來說,這並非出於她們的選擇,而是不得不被迫接受的事實。
砰。砰。砰──砰──砰。
一位母親站在屋外。她正在將孩子的物品裝進車裡。孩子長大的過程中,你曾做過多少次類似的事?你必須從地上撿起多少玩具、得在孩子該上床的時候費勁搜索多少布娃娃、曾在孩子念幼稚園時丟掉多少隻落單的手套?有多少次,你納悶如果老天要人類繼續繁衍,那為什麼不讓人類演化出另一雙手,方便伸進亂七八糟的沙發底下和冰箱裡層?我們又花了多少時間在玄關枯等孩子們?他們害我們長了多少白頭髮?為了他們的一輩子,我們抵上了自己的多少輩子?當稱職的父母究竟需要付出些什麼?說來不多,所有一切就夠了。你只需要付出一切。
砰。砰。
站在小丘上的安娜轉頭問她的死黨:「妳還記不記得我們小的時候?妳老是喜歡假裝我們有小孩?」
瑪亞點點頭,眼睛一刻也沒離開腳下的小鎮。
「妳還想要小孩嗎?」安娜又問。
瑪亞的雙脣極微小地動了動,回答:「不知道,妳呢?」
安娜輕輕聳肩,半慍怒半哀傷地說:「也許等我變老以後吧。」
「多老?」
「不知。三十歲吧,也許。」
瑪亞靜默良久,又問:「妳要男生還是女生?」
安娜的回答聽起來像是她已經思索了一輩子:「男生。」
「為什麼?」
「因為雖然這個世界有時候對他們很糟糕,但是對我們卻是一直都很糟糕。」
砰。
做母親的關上後車廂,用力忍住眼淚。因為她知道假如自己放任第一顆眼淚落下,就會永遠停不下來。無論做父母的到了什麼年紀,我們永遠不想在兒女面前落淚。我們情願為兒女做任何事;做兒女的並不懂得這個心態,因為他們不了解任何以「無條件」為前提的付出,究竟能龐大到什麼地步。父母的愛令人無法承受,既輕率又不負責任。睡在床上的孩子們這麼小,坐在床邊的我們心裡早已碎成片片。這是充滿缺憾與內疚的一輩子,我們到處貼滿快樂的全家福照片,卻將幸福畫面之間令人心傷的空隙隱藏起來。那些黑暗房間裡無聲的眼淚。我們清醒地倒在床上,怕極所有有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幸,所有他們會陷他們於受害者角色的不利處境。
做母親的走到車子另一邊打開門。她跟其他母親並沒什麼不同:她有付出愛,也會害怕,會崩潰,深感羞恥,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她曾在兒子三歲時坐在他的床邊,看著他的睡臉並害怕所有有可能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一如所有其他父母的擔憂。但是她從未料想到自己必須害怕的是,這一次他成了加害者。
砰。
清晨到來,整座小鎮還在沉睡。大熊鎮的主要幹道還是空的,但是站在丘上的兩個女孩始終盯著這條路。她們耐心地等著。
瑪亞已經不再夢見那段強暴過程了。凱文那隻摀住她的嘴的手,他壓在她身上的體重令她的夢窒抑無比,他那四壁擺滿冰球獎盃的房間,她的上衣鈕釦彈跳著滾過的房間地板。她現在只會夢見大熊丘上的慢跑跑道,從這裡就看得見。那天凱文獨自在那裡慢跑,她拿著獵槍從黑暗中現身。當獵槍指著他的頭時,他嚇得全身發抖,哭哭啼啼地哀求她饒命。在她的夢裡,她殺了他,夜夜如是。
砰砰。
一位母親能逗孩子格格笑多少次?孩子又能令母親大笑多少次?當我們第一次被孩子們刻意地逗笑得前俯後仰時,我們才意識到原來他們也有幽默感。他們會開玩笑,學到如何左右我們的感覺。如果他們愛我們,便會很快地在左右我們的感覺之後學到如何對我們撒謊,不讓我們心裡七上八下,假裝他們很快樂。他們以飛快的速度摸清楚我們的喜好。我們也許以為自己了解他們,但是他們心裡有另一本記錄成長過程的相簿,並且以跳級方式成長。
那位母親又有多少次站在屋外,不斷檢查時間,不耐地呼叫兒子的名字?今天她不需要如此了。因為當她花了幾個小時替他收拾行李時,他始終靜靜地坐在副駕駛座上。他那副曾經健壯的體格如今顯得消瘦,這幾個星期以來她總是無法勸他進食。他的眼睛空洞地望穿擋風玻璃。
一位母親能夠原諒兒子到什麼程度?她有可能在事前知道答案嗎?沒有哪一個做父母的能想像那個小小的兒子在長大之後竟然會犯罪。她不知道如今他晚上都做什麼惡夢,但是他每每被嚇得從夢境裡尖叫著醒來。那天早上,她在跑道旁找到他,冷冰冰的身體動也不動,因為恐懼而全身僵硬。他尿了褲子,絕望的眼淚在臉頰上凝結成冰。
他強暴了一位女孩,但是沒人能證明。將來會有人說他僥倖躲過,他們一家人都逃過刑責。是沒錯。但是對他的母親來說,她永遠不會如此覺得。
砰。砰。砰。砰。
剎車燈亮起片刻;做母親的向後照鏡裡看了最後一眼,那座曾經是他們家的房子,信箱上的姓「厄道爾」已經被逐字撕掉。凱文的父親獨自將行李塞進另一部車裡。那天,他和凱文的母親一同站在跑道旁,看到兒子的毛衣被眼淚浸濕,褲子飽是尿液。他們的人生在那天之前早就已經被狠狠擊裂,但是那是她頭一次看到紛飛的碎片。當她半扛半拉地在雪地上將兒子拖回家時,做父親的拒絕助她一臂之力。那已經是兩個月前的事了。從那一天起,凱文從未離開家半步,他的父母之間也幾乎從不交談。人生教她一件事,那就是男人比女人更喜歡用斬釘截鐵的方式定義自己,而她的丈夫和兒子總是以兩個字自我定義:贏家。她記得做父親的不斷強力灌輸兒子一個信念:「世界上只有三種人:贏家、輸家、還有旁觀者。」
如今呢?如果他們不再是贏家,又成了什麼?做母親的放開剎車,關掉收音機,開上路之後轉過街角。她的兒子坐在她身邊。做父親的坐進另一部車,獨自駛往另一個方向。離婚文件已經寄出去了,同時還有給學校的信.說明父親已經搬往另一個城市,母親和兒子則去了別的國家。信的最末尾有母親的電話,已備學校有任何疑問,但是沒人會打電話給她。這個鎮將會盡全力忘記厄道爾一家曾經是它的一分子。
車子裡經過四個小時的靜默,他們已經離大熊鎮夠遠,再也看不到森林的影子。凱文悄聲問母親:「你認為一個人有可能變得完全不一樣嗎?」
她搖頭,用力咬著下唇,使勁地眨眼直到眼前的路變得一片模糊:「不會。但是他有可能變成更好的人。」他伸出顫抖的手,她握住那隻手,彷彿他還是當年那個三歲小男孩,在懸崖邊搖搖欲墜。她輕輕說:「我沒辦法原諒你,凱文。可是我永遠不會放棄你。」
砰──砰──砰──砰──砰。
那就是這座小鎮的聲響,到處都聽得見。如果你住在這裡,也許就能了解我在說什麼。
砰砰砰。
小丘頂上站著兩個女孩,看著車子駛出視線。她們馬上就要十六歲了。她們一個抱著吉他,另一個抱著獵槍。
3 像個男人
關於別人,我們所知最慘的事就是我們得靠他們;他們的一舉一動牽動著我們的人生。這裡指的不光是我們選擇來往的「別人」、或是我們喜歡的「別人」,還包括其他所有的「別人」:那些笨蛋們。你們這些排隊時總是排在我們前面的人、根本不懂得開車的人、喜歡低級電視節目在餐廳裡大聲喧嘩、冬天時你的小孩還在托兒所裡傳染腸病毒給我小孩害他大吐特吐的人。你們這些停車技術奇爛無比還搶走我的工作連投票都投錯黨的人。分分秒秒,你們都在影響我的人生。
親愛的老天爺,我真的恨死來這一招。
在熊皮酒吧裡,一夥默默無語的老頭們排排坐著。有人說他們大概七十幾歲,但是這個數字十分啟人疑竇。老頭總共是五位,卻有八個不同的意見。大家封他們是「五叔公」,大熊鎮的每一場冰上曲棍球賽裡,他們總是站在計分板旁邊大吹法螺,爭執不休。球賽結束之後,又再前往熊皮酒吧繼續大吹法螺,爭執不休。五叔公們偶爾捉弄彼此,使受害者以為老年痴呆症悄悄爬上身了:有時候他們幾杯黃湯下肚,趁著夜色換掉別人的門牌號碼、藏起大門鑰匙。有一回,其中四個人從車道上拖走第五個人的車子,再換上一模一樣的租賃車,害得他第二天早上無法發動車子時,嚇得以為自己終究逃不過該進老人院的命運。五叔公去看球賽時喜歡用大富翁遊戲裡的假鈔買票,而有一年的幾乎整個球季裡,他們假裝身處一九八○年的冬季奧運。每一回當他們瞥見大熊鎮冰球俱樂部的運動總監彼得.安德森時,就衝著他講德文,還叫他「漢斯.韓姆夫」(譯註:一九八○年冬季奧運會的西德冰球隊教練)。總監的怒火與時俱進地緩緩燃起,令五叔公比獲得延長賽勝利還開心。鎮上的居民常說,五叔公很有可能全都已經老到番癲了,但是誰有那個鬼辦法證明?
熊皮酒吧的老闆娘拉夢娜在吧檯上一字排開五只杯子。眼前只有一種威士忌,卻有好幾種不同的哀戚。五叔公這一輩子一路跟著大熊鎮冰球俱樂部爬上巔峰,而今又直落到冰球聯盟的最底部。今天是他們人生最悲慘的一天。
蜜拉.安德森正在前往辦公室的路上,手機響起。她最近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而心煩氣躁。手機從她的手裡滑落到駕駛座下面,蜜拉用極為精準的人體解剖部位名詞咒罵數次,她的丈夫總是說她這些詞彙足以令一夥喝醉的水手們大為羞愧。蜜拉終於摸到手機之後,電話另一端的女人花了好幾秒才從那一串咒罵裡回過神。
「喂?」蜜拉爆吼。
「那個,對不起,我這裡是超達貨運。您的電子郵件裡說要報價……」女人小心翼翼地說。
「妳是……哪一家公司?超達貨運?沒有啊,妳一定是打錯號碼了。」蜜拉說。
「您確定嗎?我這裡有一份文件說──」女人繼續講,然而蜜拉的手機再次滑落,嘴裡自由爆射出與手機外型類似的人體生殖部位詞彙,當她終於又撿回手機時,女人已經知趣地掛斷了電話。
蜜拉並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她真正在等的是丈夫彼得的來電。今天,彼得要跟當地議會開會決定冰球俱樂部的未來。她對會議結果的焦慮感,就像有條大橡皮筋綁住她的胃,越纏越緊。她把手機丟到副駕駛座上,手機螢幕的背景照片是她的女兒瑪亞和兒子李歐。螢幕短暫亮起之後,隨即轉為黑暗。
蜜拉繼續開車往辦公室前進,假如她停下車來在網路上搜尋「超達貨運」,她會發現那是搬家公司。如果其他不怎麼在乎當地冰球隊的城鎮,冒安德森一家的名要求搬家公司報價,也許看似是個無傷大雅的玩笑,然而大熊鎮不是那種城鎮。在森林深處的死寂之中,不需要大吼大叫就能造成震耳的威脅。
當然,蜜拉很快就會想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是個聰明的女人,也住在這裡夠久了。大熊鎮有許多特質:大片景色炫目的美麗森林,是這個政客們只著眼在大城市發展的國家裡,最後的野生寶地。這裡還有友善、謙虛、努力工作、熱愛大自然和運動的人們;無論客隊是誰,永遠塞滿看台座位的球迷們;將臉孔塗成綠色去看球賽的退休老人們;有責任感的獵人們、技術高超的釣魚人;和森林一樣堅毅,和冰雪一樣不妥協的鎮民們;對任何需要幫助的人慷慨伸出援手的鄰居們。在這裡生活不容易,但是他們會笑笑說:「人生本來就應該不容易。」這些都是大熊鎮的特質。但是……話說,這個鎮也有其他的特質。
幾年前,一位老冰球裁判和媒體談到職業生涯裡最糟糕的幾段回憶。位居第二、三、四位的回憶,都是大城裡氣憤的球迷們對判決結果不滿意時,朝球場冰面上丟菸草罐、硬幣、高爾夫球的軼事。第一名得主則發生在一座位於森林深處的小冰球館裡,當時裁判在比賽最後一刻判決客隊獲得以眾擊寡的集中攻勢權。客隊得分了,大熊隊落敗,裁判抬眼瞧了一下向來保留給「熊迷」們的站立席。如果在往日,那片站立席總會塞滿穿著黑夾克,令人震耳欲聾地高唱或是以駭人之勢大叫的男人們。然而就在那一刻,他們並未大聲吼叫。「熊迷」們只是站在原地,一片靜默。
蜜拉的丈夫.大熊鎮冰球俱樂部的總監彼得.安德森,是第一個意識到危險的人。他快速衝進記分員的包廂,就在代表比賽結束的鈴聲響起時,瞬間關掉冰館所有的燈。警衛在一片黑暗中將裁判們帶領出冰館,駛離該處。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假使當時不這麼做,會有怎樣的下場。
這也是為什麼在這裡,柔性威脅絕對管用。給搬家公司打一通電話就夠了,蜜拉很快就會明白背後的意義。
議會裡的會還沒結束,但是大熊鎮上早已有幾個人知道會議結果是什麼。
議會樓外有兩幅旗幟長年飄揚著:國旗和議會的會旗,本地政客們從會議室裡就能看見這兩幅旗幟。再過幾天就是仲夏日,凱文和家人已經離開本鎮三個星期。當他們離開時,也改變了本鎮的命運:並不是即將到來的命運,而是已經發生的命運。但是並非每個人都已經意識到這件事。
議員之一緊張地咳了幾聲,勇氣十足地試著扣上西裝的釦子。他試了好久,彷彿好幾頓聖誕節自助餐都吃完了,雖然理論上這個比喻不可能成立。然後他說:「我很抱歉,彼得,但是議會決定我們最好把資源用在一支球隊上,而不是兩支。我們想用在……海德鎮的球隊。這樣對每個人都有利,當然其中也包括你,只要你同意就行。你要了解現在的……情勢。」
彼得.安德森坐在會議桌的另一頭。被背叛的醒悟將他連滾帶爬地打入黑暗之中,當他勉強開口說話時,聲音幾乎細不可聞:「可是我們──我們只需要一點點幫助,幾個月就夠了,等我們找到足夠的贊助人。議會只需要當我們向銀行貸款的保人而已。」
他閉上了嘴,當下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愧。很顯然地,議員們已經跟銀行經理談過了──他們都是鄰居,還一起打高爾夫球和獵駝鹿。這個決定是在彼得走進會議室之前早就做下的。當議員們叫他來開會時,他們謹慎地強調這是「非官方的會議」。
這場會議不會有會議紀錄。會議室裡的椅子分外窄小,手握大權的男人們必須坐在兩張椅子上。
彼得的手機震動了一下。他打開手機,是一封電子郵件告知他大熊鎮冰上曲棍球俱樂部的領隊已經辭職的消息。他肯定曉得這場會議裡會發生什麼事,而且八成已經答應了海德鎮給他的工作。彼得被扔下來獨自面對這場迎面痛擊。
桌子另一頭的政客們不自在地扭動身體。彼得看得出來他們腦中的想法:「別丟你自己的臉了。不要再辯解,也不要求我們。像男人一樣面對現實吧!」
大熊鎮坐落在一座大湖旁,湖的一邊有細長的湖岸。每年的這個時節,湖岸是屬於鎮上青少年的,此時天氣無比和暖,幾乎能讓你忘記大熊鎮的冬天有九個月長。在海灘球和賀爾蒙充斥的湖岸上,坐著一位戴了太陽眼鏡的十二歲男孩。他的名字叫李歐.安德森。去年的湖岸上沒什麼人知道他的名字,然而現在大家不但知道他,還不時地偷眼瞧他是否隨時要大爆發。幾個月之前,李歐的姊姊瑪亞被凱文強暴了,但是警方無法找到任何證據,因此凱文無罪開釋。鎮上的居民分成兩派,大部分站在凱文那一邊。公憤逐漸累積,這一批人開始想辦法逼走李歐一家人。他們將寫了「婊子」的石頭砸向他姊姊房間的窗戶;在學校裡霸凌她;人們在冰館裡開了一場會,企圖開除她和李歐的爸爸,也就是大熊鎮冰上俱樂部的運動總監。
一名證人挺身而出,他和瑪亞同齡,事發當時也在那棟屋子裡。但是他的仗義直言並未造成任何影響,警方仍然袖手旁觀,小鎮依舊保持緘默,大人們沒做任何能夠幫助瑪亞的事。直到有一天晚上,就在鎮民大會不久之後,發生了一件事。沒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在那晚之後凱文突然足不出戶,接著開始有傳言說他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三個星期前的一個早上,他和家人忽然不知去向。
李歐原本以為如此一來一切都會變好。然而,情勢卻變得更糟。他才十二歲,但是已經在這年的暑假中學到:與其選擇複雜的真相,人們終究寧願相信簡單的謊言,因為謊言有萬古不變的優勢:真相永遠得符合實際發生的事件,但是謊言只要易於使人信服就行了。
當俱樂部的會員們在春天的會議上,以些微之差通過讓彼得.安德森繼續留任的提議之後,凱文的父親便立刻安排凱文從大熊鎮轉往海德鎮的冰球俱樂部。他還說服了教練、幾乎所有的贊助商、以及幾乎所有少年組的球員們和他一起轉隊。凱文一家人突然在三個星期前搬走後,情況瞬間大逆轉,但是說來奇怪──在那之後,現狀並沒任何改變。
那麼,李歐又期待什麼?期待每個人突然之間領悟到凱文犯了罪,而向他和家人道歉?期待贊助商和球員們回到大熊鎮,低頭認錯?他們會才怪!在這個鎮上,沒有人會低頭認錯,只因為人們往往因為不承認自己犯錯,而造成人生中最大的錯誤。凡是犯的錯越大、造成的傷害越深,萬一我們讓步之後,所犧牲的自尊也越高。所以沒人願意認錯。
突然之間,大熊鎮所有有錢有勢的人不約而同選擇另一個戰術:他們停止承認自己曾跟厄道爾一家走得很近。人們開始耳語,一剛開始聲音很低,接著漸漸地有了自信:「那個孩子確實是有點不對勁。」或是「誰都看得出來,他爸給他太多壓力了」。後來,奇怪地演變為:「那一整家人喔,向來就不……你知道嘛……不像我們這些人。那個爸爸也不是這裡的人,是別的地方來的外人。」
凱文轉到海德鎮冰球俱樂部的事件,剛開始被描繪成「他是惡意指控的受害者」和「無辜被扣帽子趕盡殺絕」,而現在卻有另一個版本:贊助商和其他球員們也轉往海德鎮,不是為了追隨凱文,而是因為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他已經從海德俱樂部會員名單上除名了,但是大熊鎮的會員名單卻還有他的名字。這些理論使每個人都能夠遠離加害者和受害人,如此一來之前和凱文稱兄道弟的人可以叫他「變態」,又同時叫瑪亞「婊子」。謊言很簡單;真相太困難了。
大熊鎮的冰球俱樂部開始被許多人謔稱「凱文俱樂部」,海德鎮自然而然地出現反向自我認同。球員家長們寫信給當地議員們,闡述「責任」和「不安全感」。當人們覺得受到威脅時,就會開始營造能滿足自己的說詞。一件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慢慢累積:有一晚,某個人在大熊鎮外的路標上寫下「強暴犯!」。又過幾天,一群來自大熊鎮和海德鎮的八歲孩子們,因為嚴重鬥毆而從夏令營中被趕回家,鬥毆起因是海德鎮的孩子們對大熊鎮孩子們叫嚷「大熊鎮的強暴犯!」。
李歐坐在湖岸上,十五公尺外坐著凱文從前的好友們,幾個又高又壯的十八歲男孩。他們現在改戴海德鎮冰球隊的紅色帽子了。當初他們在網路上寫瑪亞「活該」、凱文是無辜的,因為「哪個人他媽的就算雞巴沾屎,會想要碰一下那個賤貨」? 說得倒像瑪亞開口要他們哪個人用那種東西碰她似的。而今這些男孩們堅稱凱文從來不跟他們一掛,而且他們會不斷重複同樣的謊言,確保凱文只跟大熊鎮俱樂部沾上邊,因為無論故事如何被扭曲,這些男孩只想充英雄。贏家永遠是他們。
李歐比那些男孩小六歲,不僅矮多了,也弱多了,但是他有幾個朋友仍然說他應該「有點什麼行動」;那幾個渾蛋至少有一個得「受點教訓」;李歐必須「像個男人」。在你十二歲時,男子氣概是件複雜的事。不過在其他年齡也同樣複雜。
接著,開始有噪音響起。幾個人低頭看著身下的海灘巾,全湖岸上的手機此起彼落地響了起來。從一兩支開始,然後是全部,直到手機鈴聲全混在一起,彷彿一支交響樂團裡所有的樂器同時演奏。
新聞快報來了。
大熊鎮冰球俱樂部正式煙消雲散。
「不過只是個運動俱樂部而已,還有比那更重要的事。」要是你認為運動不過就是跟數字扯上邊的事情,那麼說這種話就很容易了。但是運動從來不僅止於此,你可以自問一道最簡單的問題:孩子在打冰上曲棍球時有什麼感覺?這個問題不難回答。你曾經陷入愛河過嗎?就是那種感覺。
十六歲的少年沿著大熊鎮外的路跑步,他叫阿麥。樹林裡的車庫中,渾身髒兮兮的十八歲大男孩正幫他的父親拿工具和疊輪胎,他叫波波。在一座院子裡,四歲半的小女孩從露台上將冰球碟射向磚牆,她叫艾莉西亞。
阿麥希望有一天,他的冰球能打得好到將他和母親帶離這個地方。
對他來說,運動就是未來。波波只希望他還能盡情歡樂一個球季,什麼責任都不用負,因為他知道在那之後,他人生的每一天只會複製父親的人生。對波波來說,運動是能開心玩耍的最後機會。
至於對那個在露台上努力射出球碟,四歲半的女孩艾莉西亞來說呢?你曾經陷入愛河過嗎?那就是運動在她心中的感覺。
手機響起,整座小鎮完全靜止。再沒什麼比八卦傳得還快了。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