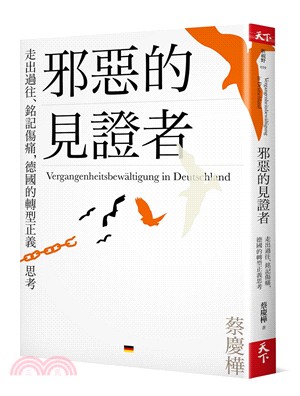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 系列名:新視野
- ISBN13:9789863985129
- 替代書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n Deutschland
- 出版社:天下雜誌
- 作者:蔡慶樺
- 裝訂/頁數:平裝/224頁
- 規格:21cm*14.8cm*1.6cm (高/寬/厚)
- 重量:254克
- 版次:1
- 出版日:2020/02/24
- 適性閱讀分級:629
商品簡介
每一個國家,都有繞不過的傷口。見證了過往殘酷的許多名字,就這麼被時間抹去。
當舉世都盛讚德國人能正確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這本書對於同樣身處歷史、族群議題中等待和解的台灣,
或許能打開一扇希望之窗,以及值得借鏡的典範。
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由書籍、展覽、影劇、少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等多重面向,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他在一個個血淚斑斑的泛黃故事中,帶領讀者看見回憶、述說、反抗、面對的勇氣,以及德國社會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前行。不僅是面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對人性、對道德的深刻探問。
一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從重創中站起來,不只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生,
更必須在精神及文化上學會哀悼,癒合不可能癒合之創傷。
本書以在德文中特有的一詞概念貫穿:「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發生的、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如何面對、克服傷痛,才得以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勇敢撕開和諧的偽裝,才能從根源療癒,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
為無名者做傳,我們一起做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
從另一岸到這一岸,我們都站在轉型正義的起點上。
※※強力推薦※※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簡介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一】善良,是一種選擇
德國文化觀察家&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人性兩難的場景
德軍士兵威廉奉命,準備燒毀戰區的一棟平房。他以為房子裡早就已經人去樓空了,然而當他提著汽油進去時,卻撞見一對年老的俄羅斯夫婦在餐桌前用餐。老夫婦與他四目相望,接著老先生緩緩地提起茶壺,倒了一杯茶想請這位闖入他家的陌生士兵喝。然而到了最後,德軍士兵還是只能遵照命令,燒毀老夫婦的家。
蔡慶樺的《邪惡的見證者》中,到處都是這種人性兩難的場景。剛開始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心想大概就是在探討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但是看完後才發現這本書討論的不僅僅只是歷史的問題,它還討論到同婚、藥物氾濫、兩代之間的歷史記憶等至今還在德國廣為人討論的議題。像上面描述的這幕景象,就是來自於德國第二公共電視台(ZDF)為紀念50週年台慶,於2013年推出的影集《我們的母輩父輩們》(Unsere Mutter, unsere Vater)。這部影集立刻獲得廣大的迴響,知名週刊《明鏡》甚至宣稱這部影集代表「德國反思歷史的制高點」。許多德國人終於從冷硬生僻的歷史課本外,開始了解自己父母、祖父母那輩經歷的那個集體瘋狂年代,甚至到最後開始問起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是我遇到這種事情呢?我會怎麼做?
「我會怎麼做?」
我認為,這一句話透露出德國歷史工作的真正核心。我在漢堡大學讀書時曾經有一門課很有趣,在十幾堂課堂裡,每堂學生都要探討一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是其他什麼社會科學的理論,而全部圍繞著的就只有一個問題:「納粹大屠殺為什麼會發生?」
因此,整個學期下來我們討論了傅柯的《規訓與懲罰》、討論了阿多諾關於啟蒙運動的種種評判及其他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討論了米爾格倫實驗裡人們對於分散責任的毫無防備、也討論了路西法效應。在整個讓人頭昏腦脹的學期以後,我得出自己的結論是:當當人們受命去執行一些道德上不允許做的任務時,他們會陷入一種叫做認知失調的心理狀態中。為了擺脫這樣心理上的不舒適感,他們就會開始改變自己的心態。其中一種選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意指放棄思考。當上級的規定與指令下來時,即不加思索地加以服從,把一切都交給規定與領袖說了算。一九六一年,前納粹黨衛軍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首次提出了這樣的概念,她認為艾希曼只不過是個官員,而且意識形態在他的行為中並非扮演主角。她堅持將艾希曼描述為禽獸、是惡魔的化身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會讓歷史研究者忽視,暴政專制的政權如何能輕易引誘平民百姓參予罪行。不加思考的執行命令的確是一種惡。但是後世的德國年輕人要接受的,可能是更令人傷感的一項事實,那就是他們的父母非但不是被迫,甚至本人就可能是這種體制的狂熱支持者。
蔡慶樺的文章中,就提到這樣的一個故事。在《陌生的父母: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的日記與信件中記錄的時代歷史》這本書中,編輯者克勞斯在父母過世後,便在閣樓裡找到了父母及叔叔留下的日記本以及信件。
克勞斯的父親一輩子擔任新教牧師,而母親協助父親,兩人一直被鄰里視為服事上帝的善人,知識與品格都是社區模範。在他和妹妹的記憶中,母親曾送給她《安妮的日記》,對她敘述在二戰時候猶太人曾經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而父親也曾悼念抵抗納粹的神學家及白玫瑰運動。因此他從小便相信,那麼善良的父母親,在那十二年間一定是站在正確的一方,一定是獨裁政權的受害者,而不是幫兇。但在翻閱信件以後,赫然發現他的上一代是如何成為狂熱的希特勒支持者,甚至到最後當他們被蓋世太保盯上、要他出賣同志提供教會內抵抗者的名單時,他也照做了。當克勞斯兄妹看到這些信件時,自然完全無法接受現實。他甚至一度想逃離那個父母的家,而也不知道該拿這些信件怎麼辦。
慘劇,其實比我們想像得更近
書裡的許多故事都在考驗我們的人性。當你沒看過這些故事、看過前人的掙扎時,你其實根本不會知道你也許比自己所以為的更容易受騙、也更軟弱。故事的主角克勞斯兄妹與其他許許多多的德國人大可以將過去掩蓋,然後在每個夜晚爬上床、心安理得地進入夢鄉。但是,當意識逐漸模糊的時候,卻開始有一些微微的思緒在暗處滾動,起初只像是水中泛起一點小小的氣泡,但是卻越來越多、最後竟然像是滾水般的沸騰起來。他知道人們會開始忘記這一切,他知道那些審判、那些歷史,會隨著時間淡出人們的視野,像一隻越來越遙遠的蒼蠅,就像以前的他一樣。但慘劇其實比想像中離我們更近,只要我們忘記,它就會再重演。最後他選擇將所有的文件出版成書。他認為必須記錄時代歷史真相,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而原因很簡單:「使未來不再有相同的錯誤被犯下。」
這就是德國人即使要爬過那段污穢不堪的過去、也要尋找真相的最終原因。這是德國人的選擇。他們選擇告訴大家:這些暴政的支持者並非惡魔。反而恰恰是因為他是個「人」、擁有人性的弱點,而當相似的時代再次來臨時,我們也會做出相似的事情。而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讓別人相信,會有一個超越時代價值觀的正義存在,萬一當那個極端的時代再臨時,它也許能幫助人們克服自己的軟弱,並選擇拒絕成為暴政的幫兇。
善良,是一種選擇;這句話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要經過選擇以後,人們才能走向善良。作者蔡慶樺希望我來推薦這本書,但我卻說:不需要。事實上只要你一翻開這本書,你就根本停不下來了。唯一的問題是:你準備好了嗎?
你有把握從現在到看完整本書,你的每個選擇都是善良的嗎?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這幾年靠追逐蔡慶樺博士的「德意志思考」專欄,慢慢蓄積自己國際素養的能量,今日專欄結集《邪惡的見證者》,不啻是思辨能量的一次爆發。 如同蔡慶樺書中所言,哲學家海德格指出「德文」這個字的原意是「翻譯」,但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之意。
在這個當代人在經歷世俗、啟蒙,卻也失去傳統價值的「無父當代」,我們亟需蔡慶樺替我們翻譯那些已經被遺忘、應該被見證、卻被遺忘了的名姓。這些曾經愛過、恨過、疼痛過的名姓是波,是浪,是擺渡人蔡慶樺為我們展開這一場德意志歷史之旅的航道。
邀請朋友打開《邪惡的見證者》,讓我們從「無能哀悼」的一岸,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是的,如果一年只讀一本書,我推薦這本《邪惡的見證者》。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04:00AM
凌晨四點,因為時差,我清醒。很想好好地睡,但女兒說她肚子餓,我說,我們再試試看睡一下好不好?她試了,但沒有辦法。後來開始唱起歌來: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因為是即興創作,我是世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聽到這首歌的人,儘管我閉著眼睛假裝睡覺。
終於,我意識到無法讓她繼續睡,或者說,我意識到她讓我無法繼睡,我只好起來,幫她烤吐司,結果,她玩著玩著,就忘了要吃我烤好的吐司。吐司涼了,我的心沒有。因為我昨晚讀的《邪惡的見證者》,讓我意識到,我正在見證一段幸福。
你知道些什麼?你記得些什麼?很多人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幹嘛提起。是呀,幹嘛提起呢?
事實上,那些殘酷的故事,都不是什麼你可以輕易說是怪物做出來的事,而是一個一個跟你我一樣,原本平凡也沒什麼兇惡基因的普通人,在歷史的那當下,做出了選擇,儘管在當時候,他們或許不覺得有其他選擇,更不清楚歷史就是這樣形成。如果我們不去觀看,我們都有可能再犯下一樣的錯誤,傷害其他的人。
我的母親因為車禍腦傷因此有記憶力喪失的問題,她能記得的時間只有五到十分鐘。她還願意跟我說話時,會問我當兵沒,我會回答她,那已經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她會緊跟著追問,那你有在工作噢?那要存錢,存老婆本。當我回答她我已經結婚快十年了,她會勃然大怒,責怪我怎麼結婚沒找她去?這時,我得趕快找出結婚照,給她看。這時她會露出靦腆的表情,說抱歉她忘記了,下一句,就會笑著說,「不過,恭喜你耶,竟然有人願意嫁給你。」
我總愛說,別人家的我不確定,我家的結婚照是有用處的,它讓我的母親每天都有機會,為我開心。
有時,望著我的母親,我會想,如果我們不知道真相,也不記得真相,那我們和失憶症又有什麼兩樣?你什麼重要的事都不記得,憑什麼你可以有記性呢?那對我母親來說,會不會不太公平?
你知道些什麼,決定你對未來的判斷。你記得些什麼,更決定你對於價值的取捨,甚至,也決定你這個人在這世上的價值,和世界該如何取捨你。
法蘭克福機場
去過歐洲的人,大概很有機會到法蘭克福機場,因為是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不管要到歐洲哪個國家,你有很大的機會在這裡轉機,這裡甚至是許多人踏上歐洲土地的第一站。只是,拉著行李箱快步奔向美麗歐洲的我們,不太有機會知道,這個繁忙的國際機場,竟然也有屬於他的一段納粹歷史。
一九四四年,一千七百位匈牙利猶太女子被迫來到這裡,為了強化納粹空軍戰力,拖著孱弱身軀,扛著比自己還重,高達五十公斤的砂石,一步一步蓋出法蘭克福的第一條飛機跑道。年紀最大四十七歲,最小十三歲,許多人在過程裡被守衛活活打死,或者在殘酷不人道的折磨中沒有尊嚴地死去,一千七百人最後只有三百三十人存活。而在一九七○年一位倖存者,回到這裡,當她向市政廳詢問集中營遺址和紀念碑時,市政廳的人員感到十分疑惑,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法蘭克福這裡並沒有納粹集中營,他們認為這位倖存者記錯了,他們感到十分不解。
這整個集中營的歷史,被完全抹去。
直到後來經過數十年,當地的學生們意外在某份集中營資料裡,發現自己家鄉的名字,而出身當地的他們不曾聽說家鄉父老提及,感到十分好奇,開始研究爬梳,拼湊出這段確實存在的歷史,他們甚至回頭找上當初承包這個機場工程的營建公司,呼籲能夠針對受難者發表道歉聲明並賠償。這在多年後因為成為地方的重大活動後終於發生,他們邀請十九位匈牙利的倖存者回來,並一一念出那一千七百個名字。
我的眼淚在這裡泛滿,我女兒問我怎麼了。我說,眼睛痠。
有眼的就該看
我很感激蔡慶樺讓我知道這個故事,那沒有讓我比較好過,但或許可以讓我有機會變比較好一點,甚至,讓我有機會幫我的孩子多知道一點,多記得一點。那會讓她好一點。我看著年幼的她,希望她不需要經歷像那些姊姊們的悲慘故事,而那並沒有人可以向我保證。唯一可以做到的人,是我自己。
當我知道這件事,記得這件事,在乎這件事,並且試著告訴別人這件事,我們才能有機會避免這件事再度發生。見證這些見證的我們,當然是見證者。邪惡害怕我們看著它,直視它,因為隱蔽躲藏是它滋長最好的養份。
它吃的不是別的,正是其他人的「別過頭去」,一如愛因斯坦當初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中,因為猶太人身份被迫離去,其他院士的「別過頭去」,並不比納粹來得不邪惡。
你當然是個見證者,除非你閉上眼睛。而那,讓你和沒有選擇而失明的人有什麼兩樣?不,你糟糕許多,因為你有選擇,你做了選擇。比這些恐怖的事,更恐怖的是,不看。同樣的事情,現在也在我們的網路上看得到,你不看,你不管,讓它一個集中營一個集中營的蓋,而最後,也許你不再只是從外面看,你可能得從那裡面看外面,並且看不到外面。
不過,也有個稍稍好的消息,就是當我們看著它、傳講它、警戒它,它就不那麼有機會再度發生。當我們願意去見證邪惡,邪惡自然會膽怯的,它會的。
你該見證,你當見證。那讓你勝過邪惡。那讓我們勝過邪惡。
這書,有眼的就該看。
序
【自序】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蔡慶樺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志這個國家,二來我希望從德國式的思想模式,為沒那麼熟悉德國的台灣社會引入一些不同觀點、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一些思考台灣問題的資源。
出乎意外地,即使「文長慎入」,這個專欄受到相當多讀者支持。不少人寄來正面的回應,表示驚訝在網路上有這樣談論人文議題的長文,高興能夠讀到對於德國的深入思辨;有些人的意見非常精彩,甚至能與我的文章發展出深度對話;有些人對某些議題感興趣,希望我多談談某個領域;還有各式各樣跟德國有關的問題,例如德國旅遊問題、留學問題、情感問題、工作問題......。當然,也有對我某些文章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我也感謝許多批評與指正。這些迴響,都是「德意志思考」專欄不斷成長的能量。我不一定有時間回應,但是我都讀了。感謝中文世界每一位花時間細讀、分享、評論的人。
《獨立評論》並沒有要求我以什麼頻率或內容供稿。因為自身工作的關係,我的寫作時間不多,又需要時間消化大量德文文獻,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寫作規劃,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又因為我是個閱讀興趣廣泛的人,我的「想到什麼」,還真的想到很多什麼。於是哲學、政治、歷史、媒體、人權甚至情感,都是我書寫的材料。其實,要觀察這個多元複雜的國家,專欄內容不也必然具備多變的樣貌?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與納粹歷史或轉型正義有關。我並沒有特意這麼安
排。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還不是那麼熱門的詞彙,當時我也不是針對轉型正義而寫,卻在巧合下處理了許多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其實也不是巧合。要看清德國這個國家的過去,又怎麼能繞開這一點?《獨立評論》提議,蒐集這些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出版一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幾年下來,竟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
我告訴主編,我想寫的是那些在歷史中應該被記得、卻被遺忘了的名字。而這些名字,都見證了某種邪惡或者殘酷,都經歷了在時代中的無力。有些人獲得了平反,有些人卻就這麼被忘記。這本書,希望能夠讓世人見證應該被見證的,記得已經被遺忘的。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ü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目次
推薦序一:直視傷口才能真正治癒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 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 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 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化」
誰才應該感到遺憾?
一個被放逐的學者
拒絕成為歷史共犯
4. 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
跨越世紀的小人物
被全世界最冷峻的牆隔開
一夕封閉的邊界
與自己的國家奮戰
留下倖存者的聲音
5. 「讓我們的男人回來!」
怒吼的女人
守護我們珍惜的一切
這是反抗,也是革命
6. 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恨納粹,但無法恨德國人
當個人被「非人」化
是桂冠,還是災難?
7. 希特勒的迷幻時代
毒品與藥物的黃金時期
你的身體屬於誰?
亢奮的戰場
跑呀!跑呀!跑呀!
藥癮心態與全民毒品
8. 這一代人的母輩父輩們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在克服過往之外,是時候克服悲傷了
加害者是否也可能是受害者?
美國人眼中的可疑觀點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9. 撕下那張粉紅標籤:德國同志運動的漫漫長路
當同性戀被視為有罪
「老媽說沒問題啦!」
柏林議員的震撼彈
10. 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
「淨化」是什麼意思?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11. 暴政有其界限:檢察官鲍爾的雷默爾審判
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不法國家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格格不入者
12:陌生的父母們
魔鬼的交易
原罪?
13:無能哀悼: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無父的社會
無能哀悼
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書摘/試閱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麽?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那麼勇敢面對奧斯威辛。那不只是無法啟齒的尷尬話題,也是無法表達、無法想像的事。德國最重要的政論談話節目《君特.姚赫談話秀》(Günther Jauch)於一月二十五日時邀請了兩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參與一九六三年起訴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檢察官維斯(Gerhard Wiese)上節目,談論那無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問維斯,為什麼一般的德國人這麼不談集中營問題?維斯說,一般的德國人認為,清理納粹的工作已經被盟軍完成,他們只想盡快回去過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訴的集中營工作人員,在戰前也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正常」德國人。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建立在對那些「絕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國社會平常不願意碰觸。姚赫指出,戰後的四○、五○年代,大部分的德國人不願探究奧斯威辛,認為大部分德國人民與集中營無關;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
在那之後,人們以為罪責問題早已經被司法回答,所謂的「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經與七十年後的今日無關;然而,當姚赫的節目上,這兩位倖存者緩緩敘述奧斯威辛裡發生的事情時,整個共和國的觀眾還是為之震動。
▎兩位見證者的故事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ä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