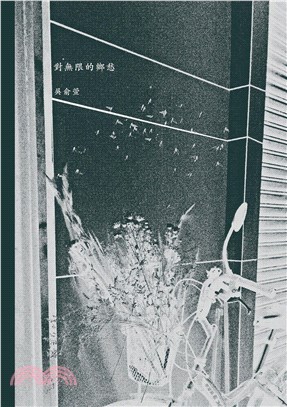商品簡介
女巫詩人吳俞萱的閱讀札記,每一篇都是愛的追獵。
面對所愛,就是面對無限。
無法停止去細究愛人的深處,每一寸波動。
顧城、沙林傑、席勒、河瀨直美、貝克特、
小津安二郎、卡夫卡、孟若、安部公房、荷索、
五十嵐大介、莒哈絲、柯札克、大衛林區、荷塔慕勒……
給她生命的,她喚他們為愛人。
她是吳俞萱,從第一本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到最新的閱讀札記《對無限的鄉愁》,她無法停止去細究愛人的深處──那些繁複而神祕的心靈邏輯、語言難以駕馭的詩意狀態、深刻而幽微的美學形式,吳俞萱欲望一刀鑿開它們,住進裡邊。
《對無限的鄉愁》是以一種刺點分析的書寫方式來回應那些刺痛吳俞萱的愛人。追憶它們、為了深入它們而啟動的對話狀態,是她對無限的鄉愁。
◆ 俞萱談中國詩人顧城
我在阿翁的課堂上讀到〈麥田〉,無法抵禦龐大的顫動從詩的某處以整個群落的力量撞擊而來。當下我非常哀傷,像是,終於醒來。於是每日讀顧城的自選集《海籃》和《顧城詩全編》,一字一字讀出聲來,一首一首錄音。起床刷牙的時候聽,穿越大霧上學的時候聽,散步去飯館的時候聽,洗澡的時候聽,入睡前也讓顧城為我掩上世界。沒有別的方法了。我要無時無刻跟顧城在一起。
◆ 俞萱談電影《席勒:死神與少女》
席勒與女人做愛的方式不是進入她們的肉體,而是進入她們的情感所強烈叫喚出來的他的創作想像。用最單薄的鉛筆細線來盛裝最濃稠賁張的情慾筆觸,他對她們身體的回應,是以紙上那些激越纏縛的線條與色相,將她們流動的情慾,永遠凝固留存下來。
◆ 俞萱談法國作家莒哈絲
《如歌的行板》、《廣島之戀》、《勞兒之劫》的小說開頭,那些勞兒般的女子突然墜落,等她們從愛情的劫難中醒來,發覺自己根本沒有墜入洞裡,那洞不顧她們的強烈渴慕而逐漸消隱,她們的一生便圍繞著這份虛空而展開。每天回到咖啡館、回到街道、回到草叢,憑藉揣測和記憶,重新孵育一個洞,把自己塞進裡面,吸吮自己的苦難。
◆ 俞萱談美國作家沙林傑
純真的目光,能單刀直入去看一切事物,赤裸裸地站在真實面前,無畏相信地獄就是無能去愛。沙林傑從不干擾他的小說人物走向自身的命運,他寫生命難以抵賴的順從和變形。純真無法突圍,僅是記起自己是誰、記起活著的感覺,承受這樣的危險。
◆ 俞萱談中國詩人余秀華
她的直和她的倔,幾乎是過度用力擺正自己而形成的另一種歪斜和飄忽。直白現身的,不過是懺情露骨的語調,那轟然翕動而不可視見之物,才真正裹藏了她的明澈洞察。詩中那些留白、那些停頓和斷裂之處,以及一句接著一句層疊翻轉的虛實明暗,不動聲色地把簡淨的詞語變濁,在含渾中剝開了幽深的層次。
◆ 俞萱談日本漫畫家五十嵐大介
他起造的一部部漫畫,或說一部部神話,就是扯掉那蒙蔽人類的語言,試圖回到渾然共振的自然連結和應答之中。那一瞬間,人的形體消散,融進更大的世界。海龜瞳孔的顏色、海岸邊樹葉的形狀、風吹拂肌膚的觸感……,一切都在跟我們對話,就連握在我們手中的故事,也潛藏了世界的碎片。
◆ 俞萱談台灣詩人廖人
耽美的抒情早已無法擔負他想表達的事物,因為美不能對抗陳腐的一切,美本身也是陳腐的一部分。廖人透過一種挑釁的醜惡美學,建立一個全新的感知模式去解構共識秩序,他的言說位置就是一個堅守道德的作戰位置。
◆ 俞萱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荷塔.慕勒
當她放下手中的書稿,我走向她。她問:「妳來自中國?」我說:「不是,我來自台灣。」她關切地追問:「妳所身處的地域,是否也有極權的陰影?」原來,她含血挖鑿的傷口不僅是個體的險境,也是集體的命運。苦難存在的一日,她的精神流亡便無法終結,無法不繼續寫下那些幾乎不存在任何可能性的存在境況。以此突圍,抵抗死亡的秩序。
作者簡介
台東人。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肄業,前往日本參與大野一雄舞踏工作坊。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沒有名字的世界》;攝影詩文集《逃生》、《忘形──聖塔菲駐村碎筆》、《死亡在消逝》;文集《居無》、《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對無限的鄉愁》。曾獲選東華大學「楊牧文學研究中心」青年駐校作家、原住民文創聚落駐村藝術家、美國聖塔菲藝術學院(Santa Fe Art Institute)駐村作家。目前與四歲兒子在花蓮玉里用阿美族的語言來學習阿美族的吟唱、祭儀、種植、捕獵,在愛之中而不為愛命名。
序
沒有葉片燃毀
沒有枝梗斷裂
日子像玻璃一樣清透
然而,必須有更多
──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
目次
目錄 我們看不見最初的日子──顧城
當我向你關上我自己──艾莉絲.羅爾瓦雀《蜂蜜之夏》
雙生的火焰──烏帕塔舞團《穆勒咖啡館》
幻影敗露──七等生
距離──里爾克、羅丹
不要停止凝視裂隙──戴伶智《似乎憂愁卻又美好》
醜惡墜落於無──小津安二郎
廝守和永別──湯姆.卡倫《Pink Wall》
愛情誕生於一則隱喻──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挖洞──莒哈絲
因為我從不糾纏你,所以牢牢掌握著你──吉田修一《再見溪谷》及其改編電影
欲望的獻祭──Baboo《海納穆勒.四重奏》
這是我的人生,而它終於回返──大衛.芬奇《控制》及其原著小說
他人即地獄──沙特《無路可出》
審判──安部公房《沙丘之女》
穿透鏡子的凝視──迪特.伯納《席勒:死神與少女》
著魔的神──廖人《13》
漆黑的命──畢飛宇《推拿》及其改編電影
無可遏止的笑──陶德.菲利普斯《小丑》、太宰治
死生之際,恆常有光──河瀨直美
失去什麼,才能身而為人?──岩井俊二
風的過境──余秀華
瞬間傾注了一輩子的愛情──高村光太郎《智惠子抄》
匿跡──艾莉絲.孟若
急流在林木中──楊牧
野詩的詩意──馬來班頓《以前巴冷刀.現在廢鐵爛》
我正好在這裡──愛麗絲.米蘭尼《辛波絲卡.拼貼人生》
飛在空中的那種東西──沙林傑
拯救景框之外的真實──荷索《戈巴契夫,幸會》
溢出──保羅.康涅提《夢游者》
草地上有積雪,昨天已經開始融化──湯姆.福特《夜行動物》及其原著小說
這世界太光,我們承受不起──藍尼.亞伯漢森《不存在的房間》及其原著小說
循著獸蹄,探勘地球──艾倫.柏林納
向著隱匿的地平線──派屈克.莫迪亞諾
沉默的團塊,還在搏動──萊特里亞《戰爭》
九命鳥──荷塔.慕勒
世界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之內──雅努什.柯札克
往回走,為了看見未來──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衍動的碎片──大衛.林區
摒棄所有願望──貝克特、鄭志忠《貝克特與我》
撕開現實──五十嵐大介《海獸之子》
旺盛的死絕──卡夫卡
凝視乾癟,直到有了春天的意願──鄭琬融《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
我們走向了我──紀洛姆.尼克婁《愛重逢以後》
書摘/試閱
〈漆黑的命〉
輕輕閉上眼。眼睫毛疊在一起,很輕很輕地顫動。一片稀薄卻又雄渾的黑暗,輕輕落了下來。黑暗之中,沒有維度,無邊無際。黑暗一點一點吃掉我們的眼睛。吃掉遠近。吃掉美醜。吃掉外面的世界。吃掉外面的自己。我們的身體慢慢成了一只巨大的眼睛。觸碰是看,聽聞是看,想像是看。
存在,變得具體。一點動靜,都落心上。畢飛宇的小說和婁燁改編的電影《推拿》,要我們看一群盲人怎麼看、怎麼推移微渺的心願、怎麼拿起沉重的命運。無邊無際的生命,到底關於距離。只有距離,能夠丈量生命的無邊無際。人們都說,盲人是迷信的,多多少少有點迷信。他們相信命。命是看不見的,盲人也看不見,所以,盲人離命運的距離就格外地近。
電影裡的命運,環環扣動一個人和另一些人。情慾的因果,明朗而封閉,全數都在一間盲人按摩院孕生和鑿落。小說要談的命運不是這樣的。那是無法追究,無法和解的。每一個章節細數一個盲人的身世,段落那麼絕對地斷裂,身世卻又如此蕪雜完整。此時此地他們交會,而總有更龐大更漆黑的東西無法交付給眼前這些人這些事。
電影拍了命運的連,小說寫了命運的斷。一如推拿,兩者都不能使勁。起始和終局的選擇,婁燁相信了命運的突圍,畢飛宇攤露了人與自己、人與世界的厚殼,無法突圍。因為人與人的距離太過遼遠,連觸及都那樣困難。在漆黑裡相擁,她問,我們是幾個人?他說,一個人,我們是一個人。而這終究,只是丈量了心願稀薄而命運雄渾。
〈摒棄所有願望〉
我很喜歡鄭志忠的戲,每回都有那麼一刻,衝破意識的層次。《貝克特與我》就像劇中重複喊出的那一聲「啊」,就像禪師訓練弟子集中心思在那沒有涵義的「無」的聲音。重複去唸,唸到整個身心被它浸透,任何思想無法闖入。並非人在唸「無」,而是「無」在重複自己。
貝克特的劇本,癱瘓詛咒和拯救。他寫的人總以等待永恆的姿態等到幻滅,再也無能行動、無法懷藏欲求,疲憊地發覺有限無法抓住無限。《貝克特與我》改編貝克特的劇本《戲Play》,戲名「貝克特與我」暗示了兩個主體的相互對話,而非單純的搬演和再現。原作描寫一個男人、妻子和情人置身於三個甕中,僅僅露出頭來,沒完沒了地述說他們的愛戀糾葛。
貝克特給出的舞台指示明確:「舞台前方中央有三個相同的、灰色的甕,高約一公尺。彼此相接觸。每一個甕口有一個人頭,脖子卡在甕口。……他們始終面向前方,不轉向。臉孔皆失落在歲月的衝擊中,似乎成為甕的一部分。」而鄭志忠捨棄了甕,捨棄了貝克特刻意削去身體動作、削去戲劇性的演出設定,即使仍舊憑藉破碎的言說來啟動無法完整勾畫的人際關聯,但他改以三個行李箱圍成一個向內的聚合空間,突顯一男兩女精神向外散逸的三角陣列。
鄭志忠為何如此詮釋貝克特?他抓住了什麼東西,以此回應貝克特?戲的開頭,三人紛紛脫掉外衣,剩下素淨的黑色和淡粉色的內衣褲,他們頻頻繞圈而他們口中發出的單音「啊」不斷扯壞他們的圓。總是這樣,他們試圖對話,而他們的言語背離他們的意願,就連偶然重疊的那一聲「啊」也有著不同的聲調。漸漸地,他們的同時言說形成一種非指涉性的環境聲響,流動而隨時遭遇「啊」而中斷且即時回流的關係鋪陳,繞出一個音場,暗示我們:各人的獨白是單向的匯流,無限趨近而終將無法聚合,而言說的間歇,那眾聲的「啊」以斷裂的形式連繫了三人的當下,徹底取消言說的內容。
就在那個片刻,他們所無能描述的整個存在凝聚於此。貝克特原作設定的「受困的身體」在《貝克特與我》變成了「行動的身體自行揭露行動的無意義」,那仍是一種受困的狀態,因機械化的動作和述說模式而逐步打造出行動的甕身。外在的囚困成了一種自囚,就像劇中男女說的:「未來一定會來,這樣是沒有未來的。」、「如果有一天我說了實話,是不是就沒有光了?」鄭志忠抓住的貝克特劇作核心或許是一種繁複的背反:身體的動以及動的無效性、相接的對話因為突兀的邏輯而斷裂懸宕,流動也是凝滯,咆嘯亦為失語。
直到繞圈的三人並排一列,重複先前的對話,抬起的雙臂放了下來,變為屈膝抬腿,直到最後一句獨白止於「我們在一起不久之後」意外懸停,三人抬起的腳,懸在半空──鄭志忠朝向貝克特的黑洞塌陷,回應《啞劇》最後那人靜立不動,注視自己空無一物的雙手;《終局》的終局,那人的雙臂垂到椅子的扶手,保持不動,場面持續片刻;《等待果陀》最後,一人問:怎麼,我們走不走?另一人說:好,走吧。然而,緊接這兩句對話的舞台指示,寫了「他們不動。」;《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結尾,那人雙唇蠕動:「也許我最好的年歲已經過去了。那時還有個幸福快樂的機會。但是我不要它們再回來。現在我心中已無熱情之火。不,我不要它們回來。」舞台指示寫著「克拉普一動也不動地瞪著前方。錄音帶繼續在沉默無聲中旋轉。」
朝向未來,於是不動?或是不動,才能走進未來?我認識的貝克特,就是鄭志忠抓住的──摒棄所有願望,真切看透實情,僅僅待在當下,摒棄過去,摒棄未來。
〈野詩的詩意〉
班頓是馬來群島的民間詩歌,任一首詩,誰都可以隨手挖掉幾個字,再補上幾個字。甚至,僅僅留住一個搖晃心地的詞,其餘重寫。不過,重寫也得遵循嚴格的限制:四行為主,隔行最後一個字押尾韻。提筆的人得遷就押韻再回頭斟酌選字,意外地破除了「我」的有限而受寫作條件的誘導和啟發而翻出新的意識。
在馬尼尼為翻譯的班頓詩選《以前巴冷刀.現在廢鐵爛》中,她的版畫如虎添翼。刻刀的線條轉折無法圓滑,留下許多犄角與古怪的收筆,就像口語的班頓野詩處處展露力的勢頭和頓挫,充滿野性的況味。每一首詩仰賴尾端兩句的情思反撲前頭兩句的具體物象,令白描的景物內裡萌生躍動的心。例如「燕子飛呀跌了下來,╱掉到海裡鯊魚吞了。」描寫燕鳥的落難,「跌」和「吞」似是喪失自由與可能性,後兩句「誰說我不喜歡呢?╱若花兒想被裹緊!」一現身,立刻顯露這落難、這喪失自由與可能性即是「我」自由做出的終極選擇:就像花兒被裹緊、燕子被鯊魚吞,「我」也想臣服於另一人的懷擁和吞噬,甘願失去自我來融進對方。
取消主體性是他們展現主體性的方式,就像「一千隻鴿子成群飛,╱一隻停在院子中央。╱要死在你指甲末梢,╱才能以你掌心為墓。」或「花瓣放在碗裡,╱花朵在箱子裡。╱沒和君見面前,╱死一樣的活著。」這種結構的詩也大量出現在這本馬來班頓詩選之中。起頭兩句表述一個客觀事態,末端兩句所示的觀點和情感意向,回頭賦予物象和事實一主觀的意涵,連續四行詩句於是形成一座靈動的寺廟,而法力無邊的神明呼之欲出――
呼之欲出而確然不破的迂迴邏輯,就是這些野詩的詩意所在。每一詩作並置毫不相關的畫面,語言本身和敘事的懸缺斷裂形成雙重的抽象性,斷句一如電影的鏡頭剪接,鋪排一種飽含意義的序列關係。一塊斷片指向每一塊斷片,局部用以隱喻全部,句法結構串起了每一塊斷片,直到結尾的寓意竄出,瞬間打亮了整個文本,將所有隱伏的曖昧、難以明說的純情、強烈窒息的愛慾和執念,全部照亮,一如照亮漆黑內裡纏結的臟腑,我們才恍悟了神明的造形。生命的深度,早已浮現於凡常的視象之中。
〈穿透鏡子的凝視〉
分不清楚,他在凝視什麼?
當女人順著情慾的流動撲向他,將自己毫無保留地攤露開來,無數次他說「別動」,命令她們停下,停在情慾為她們的身體自然形塑的奇異姿態裡。隨即他拿起畫筆,將日常的纏綿,隔絕在畫紙之外。彷彿還有比情慾更撩動他的東西,令他能冷酷地打斷現實的親密,熱切地在紙上描畫那些女人的眼神和形體。
若凝視是他的追逐,他在追逐什麼?
《席勒:死神與少女》電影最初的畫面,閃現著火焰焚燒的紙鈔、女人哀戚的臉、男人揮舞的手……。烈焰的殘餘,不若漆黑的人影墜逝。而他靜靜凝視一切。或許,不是凝視,他在吸納所有驚嚇,吸納所有瘋狂,吸納帝國時代的整個崩毀。就像我們跟隨攝影機的流動,穿越曲折的空間、穿越曲折的光影,最後停在一個女人的速寫臉孔上。那是他不顧自己瀕死的衰頹,向時間掙來的最後一眼。
他在凝視那些猙獰的險境,追逐那些不復重來的信任交託。
導演選擇他的瀕死時刻作為凝視他的起點,向前逆溯同時往後鋪展他的一生怎麼向著死亡挺進。而電影的構圖、場面調度、剪接和敘事邏輯,無一不在摹擬他的創作狀態和繪畫風格。像是兩個女人闖進舞台,以她們自身的追獵戲碼,破壞並取代一齣優雅的靜止展演──那勢不可擋的暴烈和穿刺,如同他和他的作品在那個時代的駭麗現身。
要人屏息的,還有那些運用鏡子和他的畫作來進行的轉場橫渡,因為鏡子和繪畫藝術同樣具有映像和再現的意涵,瞬間就讓虛實交融,令現實和記憶指向未來。而那些人世的情愛關係,再怎麼許下誓約,都沒有跟他一生遷徙作畫的那只鏡子還要忠實牢靠。
畢竟,他不是凝視她們,而是凝視鏡子,成為她們與他自己的觀眾。就像1910年的作品〈畫著鏡前裸體模特兒的自畫像〉、1913年的〈愛侶〉、1915年創作的〈情人〉、〈做愛〉、〈死神與少女〉和〈坐著的一對情人〉……,他在看和被看、畫和被畫的雙重位置上,陷入一種從欲望到映像,又從映像到欲望的無盡循環。他要畫眼前的女人,也要畫鏡子反射出來的他們結為一體。
於是,穿透她們,穿透鏡子他在凝視的,是那扭曲的身形終究無法遮掩的直白情感。於是,他與她們做愛的方式不是進入她們的肉體,而是進入她們的情感所強烈叫喚出來的他的創作想像。用最單薄的鉛筆細線來盛裝最濃稠賁張的情慾筆觸,他對她們身體的回應,是以紙上那些激越纏縛的線條與色相,將她們流動的情慾,永遠凝固留存下來。
〈往回走,為了看見未來〉
爆炸了。他們從夢中驚醒,不知道要逃。走到陽台,看見遠方的紫紅色大火。他們轉身,叫醒孩子。一起回到深黑的天空下,守著奇異的光芒。從沒想過,死亡看起來如此美麗。他們告訴孩子:「看看吧,你會記得它,直到生命的盡頭」。消防隊員趕去滅火,幾個小時以後,全身水腫。沒有別的醫法,只能灌下大量的牛奶。逃也來不及了。他們不知道自己活不過十四天。下葬的時候,腳腫得無法穿上任何尺碼的鞋子。這座城市的表面將被鏟起、動物將被射殺,全部埋進一個洞穴。倖存的人也將被連根拔起,走到半途倒下、入睡不再醒來、生下畸形的嬰孩。一個接一個死掉,不會有人在乎,因為不會有人想跟死亡靠得那麼近。
可是,她走近了,走向末日的劫餘。1986年,車諾比核災發生,各國記者爭先報導蘇聯共產體制的弊端、核能反應爐的設計缺陷、核電廠操作員的執行不當、高放射性物質的危害程度……,白俄羅斯記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選擇走近救災士兵、遷居難民、前共黨官員,紀錄他們面對絕境的禱告和懺悔:離家之前,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房屋上;離家之後,夢見自己回家整理床鋪;看見懷孕的狗而嫉妒;相信開槍的是人,提供子彈的卻是上帝。亞歷塞維奇用了十年整理這些口述歷史,在1997年完成《車諾比的悲鳴》,得到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授獎的瑞典學院認為亞歷塞維奇探索蘇聯及後蘇聯時期民眾的情感和靈魂歷史,超越了新聞報導的格式,開創獨特的文學類型──多重人聲拼貼──為當代的苦難和勇氣樹立了紀念碑。對亞歷塞維奇而言,結合「訪談紀實」的寫作形式,原本就是俄羅斯的文學傳統:「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將不同的聲音組成一個整體,這是掌握時代的一種嘗試。」1985年她的第一部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訪問那些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婦女,同年出版《我還是想你,媽媽》呈現蘇聯反抗德國納粹入侵的戰爭底下倖存孩童的純真自述:「我們家正好孵出一窩小雞,我怕牠們被弄死」、「房子,別著火!房子,別著火!」、「我深夜打開窗子,把紙條交給風」、「一把鹽,這是我們家留下來的全部」。
1991年出版的《鋅皮娃娃兵》聚焦於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的十年戰爭,採訪參戰的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書名源自那些守在家鄉的母親,遠遠望著一列列鋅皮棺材,深怕自己的孩子躺在裡頭。這部作品問世,遭到軍方和共產黨抨擊,1992年,亞歷塞維奇受到政治法庭審判,因國際人權組織的抗議而中止。此後,她的新聞報導被打壓、私人電話被竊聽,不得不在2000年離開自己的國家,流亡法國巴黎、瑞典哥德堡和德國柏林等地。2013年的新作《二手時代》採訪俄羅斯居民在蘇聯解體後的生活轉變,各篇藉由「過去……現在……」的敘事結構,凸顯人們活在「用過」的語言、文化和意識形態之中,沒有創新的生活目標和生命想像。
戰爭連綿、帝國垮臺、社會主義崩潰,無論蘇聯還是俄羅斯時代,都是鮮血橫流、屍骨遍地。亞歷塞維奇說,那是劊子手和受害者之間的永恆對話:「每個人都有這些故事,每個家庭都能述說痛苦。我常感到困惑,我們是誰?為什麼我們所歷經的苦難,無法轉變成自由?這對我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被奴役的意識,總是佔了上風?為什麼我們寧可為了物質利益,放棄自由?或是像過往的歷史那樣,因為心生恐懼而犧牲了自由?……我擔心的是,這條恐怖的路,我們要走多久?一個人還能承受多少創傷?」即使,「在我們的時代,很難當一個誠實的人,但是,沒有必要屈服於極權仰賴的妥協。……我出身蘇聯的傳統,身為作家,我必須為人民說話。」
亞歷塞維奇說:「我一直在尋找一種體裁,它將最適合我的世界觀,傳達我的耳朵如何傾聽丶眼睛如何看待生命。」透過「人類的聲音自己說話」,每個人的口頭言語紀錄國家歷史,同時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這種創作體裁,她稱之為「文獻文學」:「今天,當人和世界都變得如此多面和多樣,藝術中的文獻檔案也變得愈來愈令人感興趣,而藝術本身則常常變得無能。文獻檔案使我們更貼近現實,因為它捕捉並保存原原本本的東西。……根據這些材料寫了五本書之後,我宣佈,藝術不能理解很多關於人的事情。」亞歷塞維奇選擇面對未知,尊重任何情感的涵義,保護它們內部的變化,並且不將她個人的情感和評斷置入一個敘事體系,「文獻文學」的透明客觀,就像蘇珊.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所說:「人們面對暴行,期待的是見證的重量,而非藝術的玷污──藝術在此等同於虛偽或矯飾」。
然而,句子若是思想存在的條件,作家開展句子的方式塑造了作家自身,那麼,亞歷塞維奇未曾寫下任何一個句子,僅僅複寫他人的獨白和沉默,她的創造性如何體現?其實,她的作品並非單純的文獻檔案,她紀錄而來的「每五個訪問,擷取其中一個。而任何一個採訪對象至少錄製四捲錄音帶,整理出一百到一百五十頁的訪談內容,最後只用大約十頁。」她的創造性體現於材料取捨的眼光和敘事結構的掌握,若以《車諾比的悲鳴》為例,亞歷塞維奇展示了外在的暴力停息、內在的暴力繼起的那一瞬間,受難者的記憶不斷帶著他們重返記憶的幽影──那些來不及看清、來不及理解就在心上鑿入驚愕和恐懼的印象:女人躲到樹叢,用磚塊敲自己的頭;眼見持槍的勤務工抓起初生的嬰兒,一把扔出窗外;帶馬去殺掉的時候,牠們哭了起來……
這些苦難的記述構成了我們閱讀的一種震撼:我們落入每一篇敘述者「我」的言詞之中,我們不再是單獨的自己,我們是與故事相關的每一個人,承擔他們的情感流向。但是,撕心裂肺如此真實強烈而事件全貌逐漸模糊渙散,此刻我們才懂得亞歷塞維奇說自己不是一個冷靜的事件紀錄者,她的心永遠停留現場。她渴望再現的並非事實真相,而是受難者如何在身心動盪之中把握情感的真相:捨命抓住的是什麼?孩子、逝去的愛人、公寓的門、沒有歌詞的歌、不復存在的祖國……。荒謬暴力的極權統治一再否定個體的生命意義,而亞歷塞維奇的訪問清晰逼現了他們生命斷裂之際乍然浮現的存在歸屬,也就是一無所有、退無可退的生命察覺了自己的存在底限,在無家可歸的時候找到了「家」──那已然失落、終將失落的精神依歸。
受難者的獨白慢慢托出他們的精神依歸,來回補綴和探問:「我不應該講……但我還是要告訴你」、「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亞歷塞維奇在書中保留了他們急切叮囑的重複語句、刺痛椎心的空白停頓、無以為繼的悵然懸止……,他們的言說和沉默、自我表述和自我諦聽的交相鼓動,構成了一個個情感漩渦。他們投入一個漩渦,面臨崩潰邊緣又將自己推落下一個漩渦,反覆襲捲自身的生存狀態。我們無法在字裡行間讀到亞歷塞維奇的提問與回應,那使他們的獨白更顯無助和瘋狂,一如孤獨的殘響,無法不墮入虛無。她的敘事佈局和篇章擺放次序,隱然呈現她對情感張力的精準堆疊和節制收束。
而且,她的「多重人聲拼貼」除了反應戰爭和威權的暴力,還反思了新聞報導和歷史論述的生產過程。她說:「歷史只對事實感興趣,而把感受排除在真實之外」,她感興趣的,「不是事件,不是戰爭,不是車諾比,不是自殺,而是人類在我們自己的時代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她收集千種聲音和命運的創作行動,源於一個自我去碰觸另一個自我的過程所引發的情感波動。無意反映客觀事件,而是匯聚個體的意見和行動來揭露歷史建構的特定角度。相對於展示有限的歷史事件,亞歷塞維奇嘗試展現歷史的另一個維度:同一事件為不同個體開啟的無限存在歷程。
過去不曾消失,甚至還沒過去。她寫下的苦難、掙扎和冀望,這些不是遠方的歷史,而是我們共有的現實。亞歷塞維奇說:「整個世界處於危險之中。恐懼成了我們生活裡的一大部分,甚至比愛更大。我們都需要勇氣來繼續生活,希望我們都擁有足夠的勇氣。」她承擔的,並非創作者的責任,而是作為一個人的責任。責任(responsibility)意味了回應(response)的能力(ability):承擔我們的存在、回應我們的存在,不放棄對抗那把從未放下的刀斧。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