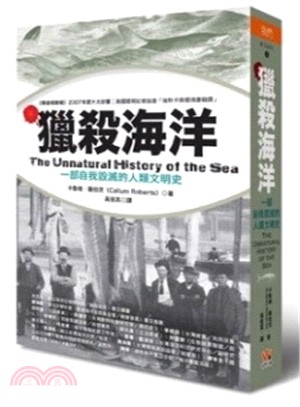商品簡介
在石油開採之前,西方主要的燃料竟是鯨脂!
我們現在吃的魚,為什麼是祖先們不吃的餌料魚?
人類將走向吃浮游生物的未來?
本書根據早期的探險家、海盜、商人、漁民和遊人所留的手記與航海記錄等第一手資料,重建過去充滿鯨魚、海獅,海獺、海龜與巨大魚類的海洋面貌。而十五世紀的航海員所描述的豐富海洋生命,更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但海洋中豐富的生命並不是在一夜之間消失,而是長久以來不受約束的海洋商業行為所導致的。原本豐富多元的海洋物種被人類快速消耗、滅絕。著名的例子如:一七四一年探險家在白令海峽發現為數眾多的斯特勒海牛,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就被人類獵捕致滅絕。雖然現代漁業已經到了毫不留情的程度,但海洋生物資源密集開採並非現代化或是工業化才開始,而是早在十一世紀歐洲就已展開。
本書透過探討悠久的商業漁業史,見證海洋的轉變。海洋的未來並不一定會是空蕩蕩的,相反的,只要透夠過一些約束來管理海洋資源,便能恢復過往充滿生命力的海洋。而佛羅里達與紐西蘭海洋保留區的設立,已將動植物的數量恢復到一個世紀以來前所未見的水準,這樣的成果證明,歷史不一定要一再重演,我們能將海洋恢復到比我們所見還更豐富的盛況。
國際好評】
「編寫引人入勝,細節豐富精彩,令人難以把書放下。」-《費城詢問報》
「重要且充滿熱情,卡魯姆.羅伯茨發出了起而行的有力呼喚」-《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本書用第一手資料描述壯觀豐富的海洋生物,以及人類與奇妙海洋生物相遇的生動場景。書的大部分讀起來像是威爾斯(H. G. Wells)的科幻小說。」-《多倫多環球郵報》
「本書將讓你再度感恩因開發而失去的海洋資源、提高對海洋現況的危機意識與採取行動的急迫感以及對作者提出的解決之道抱存希望……請閱讀並思考書中的訊息,不然就要落伍了。」─詹姆斯.埃斯蒂斯,《生物科學期刊》
【國內推薦】
《漁:一部自我毀滅的文明史》這本著作,描述了人類數百年來如何荼毒、糟蹋老天賜予人類的海洋漁產資源。作者卡魯姆.羅伯茨(Callum Roberts),蒐集了早期許多探險家、海盜、商人、漁民和遊人的海洋遊歷經驗及漁撈等各種文字記錄。這些紀錄普遍提及過去魚類資源無比豐茂的情況,若拿來對比如今漁源枯竭的蕭條慘境,簡直如天壤之別。這些昔時記錄,如一筆筆血淋淋的見證,見證了人類如何短視近利的、如何殘暴的、如何幾近傾家蕩產的糟蹋了原本不虞匱乏的大海資源。……台灣漁業發達,無論沿海、近海或遠洋,我們同樣已經走過全盛時期,並已走到得面對魚源枯竭窘境的地步。這本著作,提供我們拉開視野,拉開觀看時間,以史書的縱深,讓我們從書中瞭解,目前魚類資源狀況我們的確已經走到必要正視漁業問題的關鍵時刻。──廖鴻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創會會長)
讀《漁》這本書,感覺像看荷馬的史詩,道盡海洋生命的興衰;感覺像看莎翁的戲劇,悲傷層層捲來,結局尚未現,遺憾已無盡;感覺像看自己心愛的親人,躺在急救檯上,全身遭千刀萬剮,輾轉呻吟,危在旦夕,但救命之道,卻還遙不可及。……「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漁》一書,或許是海洋自然史中第一次讓人能看到全貌的「古」吧!
──方力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創館館長)
目錄:
第一部分 資源豐富時代的探險家與掠奪者
第一章 無害之終
第二章 密集捕撈之始
第三章 新疆土-紐芬蘭
第四章 魚比水多
第五章 掠奪加勒比海
第六章 商業冒險時期
第七章 捕鯨:第一個全球工業
第八章 前往海豹的末日世界
第九章 歐洲大漁業時代
第十章 第一次拖網捕撈革命
第十一章 工業化漁業的開端
第二部分 現代的工業化捕魚
第十二章 取之不盡的海洋
第十三章 捕鯨傳奇
第十四章 清空歐洲海洋
第十五章 國王鱈的衰亡
第十六章 河口的緩慢死亡:切薩皮克灣
第十七章 珊瑚礁的崩壞
第十八章 變動的基線
第十九章 幽靈棲地
第二十章 漁獵公海
第二十一章 褻瀆最後的偉大荒野
第三部分 海洋的過去與未來
第二十二章 無處可藏
第二十三章 炭烤水母或是旗魚排?
第二十四章 漁業管理新方向
第二十五章 回復豐富海洋
第二十六章 魚的未來
【專文推薦】--廖鴻基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海洋文學作家)
傾蕩
海洋遼闊深邃,一個人即使盡一輩子認真努力地航行,也航不遍大海的每個角落;長久以來,人類對外太空的探索遠超過對內太空(深海)的瞭解。如此敻遼空間裡蘊藏的自然資源,好幾個世紀來,一直被許多人認定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而海洋自然資源中,漁產又屬於可再生資源。確實如此,若取之有道,人類確實擁有永遠也抓不完的漁獲。
問題恐怕就出在是否「取之有道」。
《漁:一部自我毀滅的海洋與文明史》這本著作,收集了人類數百年來如何荼毒、糟蹋老天賜予人類的海洋漁產資源。作者卡魯姆.羅伯茨(Callum Roberts),蒐集了早期許多探險家、海盜、商人、漁民和遊人的海洋遊歷經驗及漁撈等各種文字記錄。這些記錄普遍提及過去魚類資源無比豐茂的情況,若拿來對比如今漁源枯竭的蕭條慘境,簡直如天壤之別。這些昔時記錄,如一筆筆血淋淋的見證,見證了人類如何短視近利地、如何殘暴地、如何幾近傾家蕩產地糟蹋了原本不虞匱乏的大海資源。
那是多麼讓人懷念的年代:用魚叉純手工方式在海邊短短時間就能叉到漁獲,魚多到隨便抓一堆上來,吃不完就堆著任其腐敗當作農作物肥料,那年代,魚多到可挑可選。
如今,我們已失去了九成屬於海洋食物鏈高層且有生態指標意義的鯊魚,意思明白,我們大海的食物鏈金字塔已到了崩毀邊緣。我們的漁撈方式不再是憑藉漁夫經驗,和一輩子打魚累積的傳統漁撈技術,如今是依賴先進的船體,以及先進的各種漁具和儀器,進行掠奪式的強勢捕撈。如今,我們的漁具隨便也能下探到數百公尺,甚至一、二千公尺深,許多深海魚種尚未被海洋生態學界充分認知前就已完全消失。如今我們採捕、食用的漁產,有許多是上個世代用來誘魚的餌料,我們往下挖掘已經在動搖我們的海洋根本。
這本書廣泛地將地球上主要漁場、主要漁撈、主要漁產,包括沿海、近海、遠洋,也將水表漁撈、底棲漁撈、大洋漁撈,分別一一例舉,呈現從過去到現在的漁撈狀況、漁撈方式的差別。本書所寫下的,幾乎就是人類行為造成漁類資源從極盛到枯竭的一部急速衰竭的海洋傾蕩史。
衰敗的原因十分明顯:過漁(過度漁撈)及開發、污染擴及於海洋。
工業革命使得漁船航行能力大增,材料革命使漁具輕巧耐用,管理革命讓漁業得以最少人力發揮最大漁撈效率,電子革命將閉著眼的探索式漁撈,轉變為睜著眼的巧取豪奪。
當採捕量大於魚類資源的繁衍量,無所節制地追逐漁獲量,也就是所謂「取之無道」,這樣的漁業,已注定走向蕭條、走向孤寂。
台灣漁業發達,無論沿海、近海或遠洋,我們同樣已經走過全盛時期,並已走到得面對漁源枯竭窘境的地步。這本著作使我們拉開視野,拉開觀看時間,以史書的縱深,讓我們從書中了解目前魚類資源狀況,我們的確已經走到必要正視漁業問題的關鍵時刻。
不能再隨機發展,必要積極管理。不是細微末節的探討,而是大刀闊斧重點改革。劃定有效執行的海域生態(魚類資源)保護區,至少達到國際標準(覆蓋我們海域面積達二О%)。有效執行漁撈管理:漁撈量、漁撈季節、漁撈方法、漁具限制、魚體尺寸等等限制及管理。禁止捕撈食物鏈低層的餌料魚類,例如魩仔魚等,因為牠們是吸引魚類靠近我們沿海的最大誘因。
本書呈現了深刻的全球海洋問題、魚類資源問題、漁撈問題,也提醒我們可以採取的補救措施。說起來簡單,但若缺乏積極作為,將很快走到盡頭。台灣漁業若要繼續走下去,必要「取之有道」,必要尊重及珍視老天賜予海島的魚類資源,並進行積極管理,我們的漁業才有繼續走下去的機會。
【專文導讀】--方力行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理事長、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創館館長)
讀《漁》這本書,感覺像看荷馬的史詩,道盡海洋生命的興衰;感覺像看莎翁的戲劇,悲傷層層捲來,結局尚未現,遺憾已無盡;感覺像看自己心愛的親人,躺在急救檯上,全身遭千刀萬剮,輾轉呻吟,危在旦夕,但救命之道,卻還遙不可及。
不過,其實這是一本說理的書,作者透過了深入的文獻收集和詮釋,將一些千年以前早已被人們忘記了的漁業記述史料,一一找出,細細編排,娓娓道來,重現了一再發生,卻一再被遺忘的海洋生物歷史傷痕。我忍不住想,現今社會中轟轟烈烈、有關海洋保護的各項作為,會不會像早在一二八九年法國就頒布的禁漁令,以及其後的各次漁業保護法令與運動一樣,重複被提出,又重複被遺忘。看似江山代有才人出,其實不過是一部人類思潮和發展的辯證史,最終仍留海洋獨憔悴?希望羅伯茨這一本完整的海洋自然歷史呈現,終可讓能人志士看出其中無法落實的問題,將海洋保育畢其功於一役。「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漁》一書,或許是海洋自然史中第一次讓人能看到全貌的「古」吧!
全書是從斯特勒大海牛消失的故事開始,這也是所有海洋生物學者感到最迷人、也迷樣的生物,就像陸地上紐西蘭的度度鳥、澳洲的袋狼、馬達加斯加的象鳥,在大多數現代學者出生前,牠們就已消失了。大海牛的縮小版就是現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儒艮的模樣,只是其體長可以大到驚人的七到九公尺,海牛也被認為是「美人魚」傳說產生的原因,在風急浪高的海洋中,據傳浮在浪頭的大海牛會用前鰭將小寶寶摟在胸前哺乳,以防被海浪打散,遠遠看去,就像抱著孩子的「美人」一樣。如此淒美的動物,居然在一七四一年被發現後不到三十年間,就遭人類獵殺滅絕了,真是令人不勝唏噓!但事實更為殘酷,遠在十六世紀之前,原本廣泛分布的大海牛,就因為人類的捕獵和棲地消失,而退聚到了白令島這最後的一個據點了,不幸再碰上一群不習前人歷史的傲慢人類,自大地以為這是他們的偉大發現,自以為是地給予致命的一擊,終於導致大海牛種族的永遠絕滅。
看完這個三百年前發生的例子,有沒有覺得跟現在身邊發生的環保案例似曾相識?改變的是不同受害的物種,不變的是人性中有我無他,永遠覺得歷史需從自己手中開始的傲慢。
讀完海龜消失的過程後,也令我大吃一驚,以往加勒比海的海龜可以多到從三千萬到六億隻,在以前也是島民或美洲沿海印第安人利用的食物,上萬年來,相安無事,可是一加入西方國家的商業行為,從一艘帆船要裝上七十五隻陸龜和一百七十隻海龜來作為新鮮食物開始,到買賣龜肉、龜脂及龜湯罐頭……,居然將曾經上億的龜族都捕殺得瀕臨絕種,前後兩個世代相較,可知生物不是不可以利用,而且可以永續利用,只是在利用時,要如何駕馭那顆貪婪的心而已。
海洋從滿海的鯨魚,到現在都已瀕臨絕種,也是個非常類似的過程,書中的一句話「鯨魚油是石油發現之前,西方最重要的油脂及能量來源」令人瞠目結舌,歐美如此巨大的人類文明群社,都要靠著殺戮可憐的鯨魚來維持,還要加上海豹、海獅、海象等眾多海洋哺乳類的陪葬,難怪海中生物都幾乎被吃乾抹盡了。好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的保育(或贖罪)意識逐漸抬頭,推廣保育概念不遺餘力,也忙著要求其他的國家共同建立保育法規和制度,以確保世界資源的綿延不絕。不過,既然全球鯨魚、海豚、海龜、海獺、海狗,甚至企鵝、海象的大量屠殺與瀕臨絕滅,都不是東方民族的罪過(跟據書中所言,日本除外),那我們是不是不需要如此戮力推動國際上明星生物的保育,而應該將國內有限的資源和能量,更多些投入到本土物種的照顧上?西方發展出來的野生動物友善與保護觀念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只是在進入在地行動之後,可能不宜一路盲從,而是需要更深度的瞭解、思考與判斷,才能做到又對、又好、又真正有利地區生物及生態的事。
不過,若講到海洋中的魚,台灣就不可能置身事外了,從一九六○年代起,台灣的遠洋漁業船隊就縱橫四海,從捕鮪魚、魷魚、鯖魚、鰹魚、鯊魚……,大型拖網、圍網、流刺網、延繩釣,各種漁業無一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漁獲量也都是數一數二,這為當年窮困的台灣,帶來了無限的海外資源和巨額的外匯。不過,時過境遷,海洋早已枯竭,人心卻依舊近利,缺乏保育及資源管理意識的台灣大型漁業公司,一如書中所言的西歐國家掠奪非洲漁源般,挾著優勢的捕魚科技設備,以合作或購買入漁權的方式,進入未經開發的友邦海域,頂著別人的帽子,搜刮世界上僅存的海洋資源。我親眼看過他們的探魚科技設備:海洋溫度衛星照片、GPS、海水溫鹽儀、海流剖面儀、電子海底地形圖、彩色聲納魚探……,應有盡有,在如此遼闊大洋上洄游的魚群,本應有非常大的躲藏空間,居然毫無逃避的機會,甚至有些不肖廠商會超額捕撈,以走私魚的形式,販售不合法的魚蝦獲利。所賺到的錢又都存在海外,成為個人或家族的資產。記得新聞報導過,二○一一年綠色和平組織「彩虹勇士號」訪台的時候,就曾趁著月黑風高,跑到台灣一家國際上認為惡名昭彰的漁業公司運搬船上去懸掛抗議標語,只是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對國際事務漠不關心的態度,在國內沒有掀起一絲漣漪。
因此,在我們看這本書時,也千萬不要覺得現今的海洋資源枯竭,只有西方是罪魁禍首,記得在一九五○年以後,海洋經由科技的突飛猛進而慘遭竭澤而漁的年代中,台灣也奮勇向前,而且因為整體資源保育和社會公益觀念的不足,至今未嘗稍歇。或許這本書可喚起國人,除了自己先實踐海洋保護外,也應要求政府對台灣以外的全球漁業,從限制不肖廠商開始,盡一份力。
在通篇敘述海洋生物殺戮史之後,羅伯茨在全書結尾時提出了幾項具體的解決方向,不過,因為他本身是許多國家的海洋保護區顧問,所以將足夠而嚴格執法的「海洋保護區」設置,視為最重要而且是最終的解決之道。自己作為一個以台灣或熱帶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海洋生物學家,我覺得在海洋保育知識的傳播上,可能還需要更周延和積極的做法,羅伯茨忽略了現今全球暖化已是一個海洋學者無法不正視的問題,對大洋性的魚類和深海生物或許還有退路,但對熱帶珊瑚礁生態系中無法移動的關鍵種——珊瑚而言,變暖變酸的海水勢必造成重大的傷害,就算牠們身處在保護區中,也難逃滅亡的命運,因此在約十年前,少數具前瞻性的科學家,已經由保種、選種、人工培育、易地保育……等各種實驗,來建立熱帶海洋生態系的保護技術與方案,讓社會知道,海洋永續豐盈的環境在經過人類各種各樣的摧殘改變之後,消極的保護固然必要,積極的作為更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本書描述的海洋史中也指出,許多物種的滅絕固然是由於人類的貪婪捕獵,卻更是由於生態系中顯現出來環環相扣的複雜性,進而反映出人們單向思考的愚昧,譬如因為海獺生活在沿岸容易被人類獵捕而減少,直接導致牠們捕食的海膽數量增加,又造成海藻的減少,當然也形成了吃海藻的大海牛族群因為變少,而更容易被發現牠的人們一下子就消滅了。譬如人類捕殺大型鯨魚,以大型鯨類為食的虎鯨就只得改吃海獺,連帶造成海獺的族群無法恢復。至於將大型掠食性魚類或草食性魚類捕走,造成無脊椎動物增加,海藻生長,珊瑚消失,或外來種興盛的例子,大家就更耳熟能詳了。這些連鎖性的反應,直接告訴人類,若任意破壞了自然,我們將永遠不知道傷害會在哪兒發生?擴散到何處?又會何時停止?在自然史中,一千年前就已出現的教訓,人們好像並無法記取,而每一次略有新的科技進展時,又忙著再大張旗鼓重演壓榨自然生命的歷史。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或許真正在傷害海洋的,不是沒有想法,不是沒有宣導,不是沒有法律,而是缺乏知識、缺乏倫理、缺乏自制的人性吧!
這也或許是讀這本書副標「一部自我毀滅的海洋與文明史」的真意,作者文字上講的是海洋生物的興衰、保護自然的理念,以及如何脫困的方法,但是人們如果不能藉由外在生命的變動甚至滅絕,來觀照我們的內心,地球上再多的資源,也不夠智人這個失控的物種揮霍。
【內文節錄】
第四章 魚比水多
早期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首次航行深入到新世界廣大的河口和河流尋找腹地時,他們對於會發現什麼,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那時候,歐洲的河川漫布著人類的排泄物、堵塞著沉積物,而河川的上游水道充斥著接連不斷的水壩和河堰。中世紀早期,歐洲的主要河流都還是沁涼清澈的,但到了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的時候,閃亮的魚群為了產卵而奮力逆流而上的畫面,早已被人們遺忘。歐洲人重新在新世界的河流與河口,發現了他們家鄉已失去了的東西。
早期新世界旅行者所評論過的地方包括一六○七年在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地區建立的詹姆斯城(Jamestown),它也是北美現今仍留存最早的英國殖民聚落。美國東部廣闊的切薩皮克河口地區,範圍超過十六萬五千平方公里,包括現在的維吉尼亞州、馬里蘭州、紐約州、賓州、德拉瓦州和華盛頓特區。河流穿過三百公里的內陸區域,和有著錯綜複雜的島嶼及水道,河口地區還包含了一萬八千五百公里的海岸線。
有著旺盛企圖心的二十七歲船長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和他的同伴們,在切薩皮克灣南邊支流之一的詹姆斯河邊,建立起詹姆斯城殖民地。沿著這條河向內陸航行時,他們被周遭富饒又清新美麗的環境迷住了,史密斯寫道:「這條河是由許多美好的小溪匯集而成的,而這些小溪又是由無數的流水和令人愉快的泉水組成。每一條涓涓細流,都對這條河有很大的貢獻,就像是人體中的血管一樣。」 1
在這些殖民者到達後不久,殖民地的議會寫信給他們在英國的支持者:
我們定居在距河口八十英里(約一百二十八公里)處,這裡很寬廣,水很甘甜,還可向內繼續航行一段。而且,這裡奔流的水道充滿了比我們所求還要多的魚,連最幸運的人也沒見過那麼多的鱘魚和其他鮮美的魚。這裡的土壤非常富饒,長著橡樹、梣木、核桃樹、楊柳、松樹、肉桂、西洋杉和其他樹木,還有一樣不知名的樹木,會產生跟乳香一樣美好的樹脂。2
對新來到的殖民者而言,看到切薩皮克灣,就像是看到了伊甸園a。這樣的第一印象,後來也藉由探索滋養切薩皮克灣的河流後被證實了。史密斯和一小隊人在一六○八年探索了穿過現今華盛頓特區的波多馬克河(Potomac River),史密斯寫道︰
波多馬克河……寬度約為六到七英里(大約十公里),河上可航行的距離有一百四十英里(約二百二十四公里),河水是由與之接壤的山丘上所流下的甜美河流和泉水匯聚而成的,原住民在這些山丘栽種,所生產的果實種類跟數量之多,不亞於水中超乎尋常豐盛的魚。3
讓史密斯和他的同伴們著迷的,不僅僅是詹姆斯河和波多馬克河。切薩皮克灣最大的支流薩斯奎哈納河(Susquehanna River),從海灣的北部將豐沛的河水帶入,激發了史密斯的靈感,他寫道︰「天地之間沒有比這裡更寬敞,更適宜人居的地方了」。4
這些在新世界的河流就像中世紀早期歐洲的河流一樣,非常乾淨。河水流經濃密的森林谷地,與可以保護土壤不受侵蝕的洪氾平原,這些河川的清澈度一定讓這些十七世紀的歐洲人目眩神迷,因為他們早已習慣充滿垃圾、污水不斷飛濺到倫敦大橋和堤壩的泰晤士河。這也難怪他們的旅行日誌上,充滿了對晶瑩剔透的河流和甜美泉水的詠嘆。中世紀早期的歐洲人認為,新世界的河流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這些河裡似乎都有快要滿溢出來的魚。史密斯的同伴沃爾特.拉塞爾(Walter Russell)和阿納斯.拖德契爾(Anas Todkill)在一六○八年進入切薩皮克灣的支流勘察時記錄下:
我們發現水獺、河狸、貂、山貓和林貂,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水中,都有很多的魚,牠們都將頭抬出水面,好像是想被網抓走一樣。而我們的船行駛在牠們中間,我們試圖用煎鍋來撈魚,不過,我們發現這不是一個抓魚的好工具。在切薩皮克灣的這些魚,比我們曾經到過的任何地方的魚都要更好、數量或種類都更多,但牠們並不是用煎鍋就可以抓到的。5
他們後來由波多馬克河航行進入海灣,退潮之際,在一處滿是牡蠣的礁岩邊停靠。
我們盯著藏匿在水草和沙子中的魚,我們的船長用他的劍來刺魚並當作一種運動,我們全部的人也跟著用這方法抓魚,不到一小時,我們用劍抓的魚就夠我們全部人吃了b。
稍早,在一六○二年同樣航行在新英格蘭海岸的加百利.亞契,也是詹姆斯城的殖民者之一。他在一六○七年寫回英國的信中,描述了河流和河口中豐富的生命:
主要河流中盛產又大又好的鱘魚,每條小溪溪口都有非常好的深水魚,靠海的海灣中也有許多魚、牡蠣礁岩,還有很多大螃蟹,比我們那裡的都還要好吃,而且一隻就夠四個人吃了6。
史密斯在一六○八年也描述了切薩皮克灣的豐盛:
這些魚中,我們熟悉的有鱘魚、鯨魚(grampus)、鼠海豚、海豹,及尾巴非常危險的魟魚,還有烏魚、白鮭、鱒魚、鰨魚、鰈魚、鯡魚、江鱈、條紋鱸魚、鰻魚、八目鰻、鯰魚、蚌和貽貝等等。7
很明顯地,史密斯和其他十七世紀的寫作者提到的動物,都是如今在灣區很少看到的。領航鯨或殺人鯨(grampus c)8和其他更大的鯨魚,在當時都是切薩皮克灣的常客。舉例來說,一尾五十四尺(十六‧六公尺)長的鯨魚於一七四六年在詹姆斯河被逼至絕境後被宰殺。早期新世界的一項污染防治辦法,是在一六九八年由殖民地時期維吉尼亞下議院議員向總督提出的訴願:「請公告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原因,在維吉尼亞州的切薩皮克灣裡攻擊或殺害鯨魚。」並進一步說明,因為腐爛的遺骸所造成的污染會毒死魚,並且把河水變得「又臭又有害健康。」9這裡的鼠海豚也很多,一位瑞士的旅行者弗朗西斯.路易.米歇爾(Francis Louis Michel)在一七○一年造訪切薩皮克灣,他是這麼提到鼠海豚的:「牠們跳躍的聲勢如此巨大,特別是在天氣轉變時,牠們會製造出很大的噪音,讓那些在小船或獨木舟上的人深恐自己會掉落水中10。」十八世紀初期,探索卡羅萊納的約翰.勞森所寫的報導指出,鼠海豚「不論在海中或河中,只要是鹹水的地方,經常都能發現。我們甚至在北卡羅萊納海灣中的淡水湖裡發現鼠海豚」d。11
鑽紋龜(Diamondback terrapins)也在切薩皮克灣和其他的海灣與河流中大量繁殖,人們視牠們為珍貴的食物。如果約翰.懷特(John White)的畫作可以相信的話,雙髻鯊(hammerhead sharks)也出沒在切薩皮克灣。懷特是沃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伙伴,他是北美第一個英國殖民地羅諾克(Roanoke)的總督,他有很多時間和機會研究海灣和其中的生物,也留下了很多描繪美麗動植物和美洲原住民的畫作。在他所描繪的動物中,鱷魚也是切薩皮克灣中的生物,北卡羅萊納的河口就是牠們分布的北界。12勞森跟懷特一樣,是一位對於美洲原住民的生活和習俗很敏銳的觀察家:
這屋子熱得像火爐,印第安人在這裡睡覺,整夜都會流汗。那裡的地板從來沒有鋪好過,也從來都不打掃,所以他們身上始終有些泥土……但在他們的小屋中我從來沒有感到任何不好或令人討厭的氣味,如果我們也像他們那樣生活在我們的房子裡,我們應該會被我們自己的髒污毒死。這證實了這些印第安人真的是世界上最甜美的人。13
在殖民時期,鱘魚是切薩皮克灣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動物。那時候,他們所測量到的鱘魚至少有十八英尺(五‧五公尺)長,重達八百公斤。歐洲的鱘魚在第一個千年結束之時就沒有再見到過了,而新世界給了十七世紀的歐洲殖民者一個機會,品嚐這種很早以前就被法律規定只能獻給英國和法國君主享用的魚。他們喜歡這樣的機會。在孵育季節,難以計算的鱘魚從海洋洄游到河口,早期在詹姆斯城的殖民者就是靠牠們度過了殖民之初食物還很稀少的時期。鱘魚也迅速成為重要商品,一桶一桶醃製的鱘魚和魚子醬是早期新世界出口的商品之一。早在一六一二年,詹姆斯城的總督湯瑪士.戴爾(Thomas Dale)就宣布抓到的所有鱘魚和魚子都是屬於他的,第一次違反規定的人要被割去耳朵,第二次要被關在船上一年!14一個半世紀後,英國訪客安德魯.伯納比(Andrew Burnaby)的著名評論主題就是在波多馬克河抓鱘魚:
鱘魚和鰣魚的數量多得驚人,在一天之內,兩英里(約三.二公里)的範圍中,一些在小筏裡的紳士就可以用魚鉤抓到六百尾鱘魚,他們把釣鉤垂到河底,然後,當感覺到有魚在磨擦或有魚上鉤時就拉起釣鉤;至於鰣魚,拉起圍網一次,就能抓到超過五千尾的鰣魚e。15
(圖說)十九世紀末,美國華盛頓州哥倫比亞河上一天的鱘魚捕撈成果。鱘魚漁業在西部沿海的發展較東部沿海晚,而像這樣的景象,在十七到十九世紀間的切薩皮克灣和其他東部河口是很常見的。(來源:當代明信片)
鱘魚不僅在切薩皮克灣很豐富,在整個北美東部的河流,一直向北到達聖勞倫斯和五大湖區都有很多,這裡是另一個中世紀早期歐洲河川的寫照。本拿比(Burnaby)及許多的人都明確描述,從海洋洄游回來產卵的物種有多麼地豐富,讓這些見到如此盛況的人相信魚的數量還可能更多。這些魚中,主要的有鰣魚和灰西鯡(alewife),牠們都屬於鯡魚家族。春天的時候,這些數量多到無法估計的魚從海中傾入河流。一七二八年,在威廉.伯德二世(William Byrd II)所寫的《維吉尼亞自然史》中,他描述鯡魚(灰西鯡):
當牠們產卵時,所有的河流和水域都被牠們塞滿了,只有親眼見到這驚人景象的人才會相信,那裡的鯡魚跟水一樣多。簡而言之,這真是不可思議!那裡能發現的數量,真的多到無法形容,也無法理解,你一定要親自去看一下f。16
殖民者用網子、漁堰和陷阱很容易就可以抓到鰣魚和灰西鯡。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住在弗農山莊(Mount Vernon estate)時,在波多馬克河中抓了很多,拉起一次圍網就可以抓到數千尾。一七七四年,單單在華盛頓的強森渡輪(Johnson’s Ferry)就抓到了九千八百六十二尾鰣魚和一百五十九萬一千五百尾灰西鯡,17而這僅是整個波多馬克河中的一小部分。一八三二年的時候,這條河上一共有一百五十八個漁場,將近八千名漁民和四百五十艘船在這裡捕魚,估計他們一共抓了兩千兩百五十萬尾鰣魚和七億五千萬尾灰西鯡。18這還不包括其他流往切薩皮克灣的河流,它們也同樣維繫每年捕撈量驚人的漁業。
一七九○年,喬治.華盛頓在選擇美國國會地點時,他的動機不僅僅只為了找個離家近的地方。後來他提到,他看到了「地面上有清澈的泉水可供飲用,有湍急的溪流可以提供麵粉磨坊所需的動力……而且,河流上游終年都有很多魚。」19
維吉尼亞有的不只是乾淨的河流和豐富的魚,所有河口和河流都提供了魚類產卵的路徑。在新英格蘭殖民地,像是條紋鱸魚(striped bass)和鮭魚也加入了鱘魚的洄游。一位熱愛條紋鱸魚的人士寫道:
鱸魚是在這個國度中最好的魚之一,雖然人們很快就厭倦了其他魚類,但他們從來沒有厭倦過鱸魚;這是一種肉質細緻、緊實、又肥又美好的魚,魚頭骨中有又甜又好吃的骨髓,口感很好,也增進食慾。在牠們數量很多的時候,我們只吃魚頭,然後把魚的身體部分用鹽巴醃起來,作為冬天的糧食。牠們的數量比長身鱈或是鱈魚都還要多,這些魚大約三到四英尺長(約九十到一百二十公分),有些比較大,有些比較小,在一波潮汐大約三小時的時間中,一個人就可以抓到十幾、二十尾。20
十七世紀中葉,新英格蘭是英國最成功的海外殖民實驗地,威廉.伍德,也就是剛剛提到的那位條紋鱸魚愛好者,在殖民地生活了四年,並在一六三四年為可能會成為殖民者的人及「心靈旅行的讀者」寫了一本名為《新英格蘭的前景:一個真實、生動且實驗性的描述》(New England’s Prospect: A True, Lively, and Experimental Description)的書,他帶領讀者在波士頓地區現今相當著名的地方,一站一站地導覽,像是女巫城(Salem)、查爾斯城(Charlestown)、布魯克林(Brookline),和波士頓本身,並列出了各地的優點。在伍德書中一頁又一頁地描述著的豐饒世界,是由有著無數種魚貝類的河川所組成的。但與今日的情況對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21
伍德留下的記錄,讓我們了解這些河流和其中的魚,特別是洄游魚類,對早期殖民者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例如,他描述波士頓旁的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
距離沃特鎮(Watertown)和牛頓鎮(Newton)一.五英里(約二.四公里)的地方,是一座流水清澈的瀑布,水流經查爾斯河後流向海洋。沃特鎮民在這瀑布下游建了一座漁堰來抓魚,用這個方法,他們抓到了很多鰣魚和灰西鯡,在兩波潮汐之間的時間,他們就抓到了十萬尾,這對這個殖民地來說是不小的貢獻。載重較小的船才可以上行到這兩個城鎮,因為岸邊有牡蠣岩礁會阻礙較大的船前進。22
麻薩諸塞州河流中豐富的鮭魚,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這種魚早已變得稀少罕見,而且大部分都是保留給貴族享用。緬因州和加拿大東部的鮭魚數量之豐,必定和歐洲在中世紀早期的一些河川一樣。喬治.卡特賴特上尉在日記中反覆提到十八世紀拉布拉多的鮭魚和新世界殖民者對鮭魚屠殺的規模:
一七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再高一點的地方,有一座非常美麗的大瀑布,垂直落下大約十四英尺高(約四.三公尺)。瀑布下方有一個深潭,深潭中滿滿都是鮭魚,若丟一顆球下去不會不擊中一些魚的。岸邊遍布成千上萬被白熊殺死的鮭魚,其中很多還相當新鮮。大量的鮭魚仍持續跳躍到空中。整個境內都充滿熊的蹤跡……。
一七七九年七月十八日星期天,魚仍然極多,一間新的九十英尺(約二十七.五公尺)乘二十英尺(約六.一公尺)的捕鮭屋建好了……一開始只下了十張網,幾天後,魚實在太多了,大家感激地再次拉起四張網;昨天,當他們拉起一些網後,就沒有鹽和木桶來醃更多的魚了,他們一天殺三十五蒂厄斯(tierces)g的魚,或是七百五十尾魚,如果有更多的網子,他們可以再殺更多。這一天殺了六百五十五尾魚。天氣晴朗美好。23
新世界豐盛的河流和河口,為一代代的殖民者提供了穩定的食物來源,幫助他們度過了嚴冬、乾旱,以及間歇發生的農作物歉收。灰西鯡和鰣魚會溯流至上游產卵,對距海兩百五十公里的維吉尼亞藍領山區(Blue Ridge Mountains)而言,這些洄游魚類為內陸的殖民者帶來海洋的豐盛。這些魚通常都被大量捕捉,常常被堆置到腐敗,特別是當用來保存的鹽缺乏的時候。較有事業心的殖民者則把多的魚拿來作為肥料。24
魚多到殖民者可以選擇他們想吃什麼魚。早期的新英格蘭人顯然很少想到大比目魚(halibut),根據威廉.伍德的記載:
(楷體字)
大比目魚跟鰈魚(plaice)或大圓鮃(turbot)有點相似,有些有兩碼長(約一百八十三公分),一碼寬(約九十一公分)和一英尺厚(約三十公分)。因為有很多其他更好的魚,牠們除了頭和鰭拿來燉或烤都很好吃之外,其他部分較不受歡迎,在白鱸魚(while bass)的季節,這些大比目魚很少被抓來吃。至於棘背鰩(Thornback)和鰩魚(skates)則用來餵狗,因為在很多地方都賣不了錢。25
一名十八世紀早期的訪客這樣形容新世界的豐饒:「我坐在河水的源頭處垂釣,而等待魚上鉤所花的時間,與我將魚從釣鉤上取下的時間一樣多的。」26然而,這種情況並不會持續下去,因為,折磨中世紀歐洲的問題,也不可避免地在新世界重演。隨著殖民地的擴增、食物和磨坊動力的需求增加,以及為了種植作物和取得木材,土地上的植被遭到濫伐。原本清澈的河水開始混濁,河流也因為泥沙而淤積,磨坊水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每條水道中。漁堰橫跨了河流中每一個合適的彎道和瀑布,然後,一群又一群溯流的魚就被擋住了。
流入切薩皮克灣以北的德拉瓦灣的聖瓊斯河(St. Jones River)的故事,很典型地將十九世紀初期河川附近居民所經歷的問題呈現出來。問題不只是魚的數量減少,還有如何取得魚的問題。聖瓊斯河的感潮帶h,從海灣上溯到德拉瓦的首府多佛(Dover),蜿蜒了三十二公里。十九世紀早期,河流的邊界被農場環繞,德拉瓦高等法院暴躁的理查.庫伯(Richard Cooper)法官的農場就是這樣。一八一六年時,庫伯因為在水中建造了一座漁堰,把水中洄游的鰣魚跟灰西鯡都攔截下來,激怒了上游的鄰居們,因為漁堰阻斷了魚溯流產卵的通道。庫伯拒絕讓鄰居過來捕撈這些魚,這些人就到他家前面遊行,要求他把漁堰拆除。庫伯法官有備而來,他在漁堰上架設一座迴轉砲對著他們。由於沒有獲得滿意的回應,六十三個人向立法機關提出請願,希望可以將漁堰移除,因為漁堰造成「貧困階層的人缺乏肉類可食用」。27德拉瓦州早在一七三六年起,就禁止漁堰設置在公有土地上,但是,庫伯的農場是私有地。儘管庫伯有很多政治關係,但法院還是站在他的鄰居們這邊。一八一七年,法院宣布所有在聖瓊斯河中的漁堰都是違法的,要求立即清除。這應該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可是,當時的日子並不好過,國家正慢慢地從一八一二年的第二次獨立戰爭中恢復,而一連串又濕又冷的夏天導致作物產量降低。一八一九年,超過一百人向立法機關請願,這回是請求讓漁堰合法化,而許多簽署這份請願書的人,跟之前提出禁止漁堰的竟是同一批人!請願人士指出,聖瓊斯河已經變得非常泥濘,漁民抓不到魚,因為無法看到魚,他們聲稱漁堰是唯一能抓到魚的方法。立法機關同意讓漁堰再次合法興建,但是有附加條件,規定漁堰必須符合特定尺寸,以及保持應有的間距,而且,漁堰必需一年撤下一次,好讓水流沖刷走河底的泥沙。
定期移除漁堰是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淤積問題。漁堰不論是在漲退潮時都會有泥沙淤積,但是,這條法律不足以解決這個規模越來越大的問題。一八一六年,聖瓊斯河水域中,大約三分之二的森林都遭到濫伐,裸露的土壤很容易受侵蝕,特別是在有暴風雨的時候。漁堰大大加速了聖瓊斯河的改變,從原本可航行的水道,變成由淺沙丘組成的迷宮,沼澤、灌木遍布,扼殺了土地,不再適宜耕種。到了一八二四年,貫穿多佛鎮約十公里的河道已無法航行,突然間,問題從原本的漁業權變成迫切需要維持河流的暢通以利航行。一八三○年,漁堰捕魚這種方法被放棄了,不僅是由於泥沙淤積,也因為能捕到的魚越來越少了。
聖瓊斯河的故事在各處不斷重演。十九世紀末,一位來自維吉尼亞州的老前輩被問到對捕魚最早的回憶,他大約可回溯到一八○○年,雖然他回憶起他年輕時有更多的魚,但他說當他年輕的時候,聽更年長的人說過魚還要比他們有過的多更多:「土地上的植被遭濫伐所造成的河流淤積,應該是魚群被摧毀的原因。」28正如中世紀的歐洲,從海裡洄游到河流中的魚想尋找的清涼、乾淨且湍急的河水,已經被流速緩慢、泥濘的河道或池塘、湖泊取代。
魚群在一條接著一條的河中減少。魚很少的狀況在沿岸間蔓延開來,隨著魚群減少,用來阻斷洄游魚類溯游產卵通道的網子卻不斷增長,有些長達四到五英里(約七公里)的網子橫跨河的兩岸,而它們只會加速魚群減少。管理單位太慢注意到這樣的問題,而且處理的方法只是不斷地通過立法,讓網具尺寸和漁場的使用有越來越嚴格的限制。舉例來說,德拉瓦州於一八二九年立法通過對設置在德拉瓦河中的刺網和圍網依長度課徵重稅,以使網的尺寸減小。29往北邊一點,康乃狄克州的聯合大會在一七一九年通過一項法令,讓鎮議會有權力禁止設置橫跨河流、阻礙流水的障礙物,以保護漁業。30一七三五年時,通過第二項法令,規定所有的磨坊主人都要在水壩旁邊設置給魚通行的通道,並且在灰西鯡產卵的季節要將水壩打開。但是,由於漁獲量減少及工業化增加的壓力下,立法者的努力總是落後,提供魚類族群恢復的時間,總是比魚類因為棲地惡化所需要調整恢復的時間短。也許比魚類產卵通道減少還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魚類受到殖民活動的衝擊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到了十九世紀初期,許多通道坍塌,其他的也岌岌可危。美國東部工業化經濟更加快了魚群損失。十九世紀中葉,羅倫佐.沙賓(Lorenzo Sabine)在為美國財政部(U.S. Treasury Department)調查北美漁業狀況後,很明確地指出漁業資源減少的原因,以他討論到加拿大紐布朗斯維克省(New Brunswick)的鮭魚為例:
效忠者和早期的殖民者發現幾乎每一條河流都有鮭魚。然而,現在有些河中的鮭魚不會出現在一些河裡了,在大多數河裡則是越來越稀少,然而,鮭魚是聖約翰(St. John)重要的出口商品……在聖克洛依河(St. Croix,紐布朗斯維克省和緬因州的邊界河)鮭魚瀑布(Salmon Falls)的捕獲量,在三十年前,每年有三個月的時間,每天有平均兩百尾的捕獲量……但是,數量減少非常多,有人說一八五○年整年下來,在這條河裡抓鮭魚的人,總共只抓到了兩百尾而已。有人指出,豎立在河中、橫跨兩岸的水壩是造成漁業改變的原因,而事實也證明了這樣的說法……在兩三條比較小、沒有阻礙物、水較不混濁的溪流中,還是有人在抓鮭魚,並成功獲利i。31
魚群數量減少,漁民於是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海洋物種,以維持生計和貿易。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牡蠣,當旅行者一抵達新世界,就已經注意到了牡蠣,或許引起他們注意的原因是,在河口的牡蠣礁岩非常廣大,對他們的航行造成困難。約翰.勞森就提到,在十八世紀初,美洲原住民在其獨木舟上增加了一小個龍骨,「以保護他們的船不會被在溪流和海灣中無數的牡蠣礁岩損壞。」32一七○一年,來自瑞士的旅行者米歇爾對於切薩皮克灣中的牡蠣族群數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牡蠣的數量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整個岸邊都是牡蠣,所以船必需避開牠們。」33他和其他人也都很滿意這些牡蠣的品質:「牠們比在英格蘭的那些還大,實際上有四倍大。我通常把牡蠣切一半,這樣我才能把牠們放到我的嘴巴裡。」34勞森也喜歡他們:「不論大小的牡蠣,幾乎在所有鹹水的溪流中都可以找得到,品質很好,而且滋味美妙!」他說道:「尤其是醃製的大牡蠣最為美味。」而他描述其他的貝類則是由於不同的原因:
沙海螂(steamer或long-neck clams)是一種我們常發現的貝類,其價 值在於可以增加男性的性能力,並讓無法生育的婦女多產;但我認為她們 並不需要這些海鮮,因為卡羅萊納的婦女不需要牠們的幫助就夠多產了。35
十九世紀末期,牡蠣捕撈全面展開。一般觀察者看了一九六○年代歐洲和北美近代河川整治工作前的河口後,會以為是污染問題摧毀了被喻為烏托邦的中世紀歐洲和早期美洲的河流。但是棲地的改變和減少,加上過度捕撈,早在更嚴重的污染影響之前就已發生了。我很快就會說到,事實上,過度捕撈,特別是對牡蠣的過度捕撈,增加了日後污染的嚴重程度。北美洲豐盛美好如伊甸園般、充滿各種魚貝類的河流,在歐洲人殖民後,無法倖存,很快就步上了舊世界河川的後塵。
第二十一章 褻瀆最後的偉大荒野
一九六七年,我學會捕魚,這對當時才五歲的我來說,那是個天堂般的夏天,我花了很多時間,趴在距離我家不遠的蘇格蘭高地上一處池塘邊草地上,凝視著淺淺的水,然後,我就成為水中生物的一份子,在泥巴和水草間追逐著牠們稍縱即逝的生命。我跟蹤拖著卵石狀和棒狀身體匍匐前進的石蛾(caddis)幼蟲,穿過覆滿腐葉土的洞穴和峽谷,我看著有角的幼蟲拖著身體爬上蘆葦,及蜻蜓脫離在水中的幼蟲期,但是,最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刺魚(sticklebacks),牠們是我的獵物。雄刺魚有著鮮豔的紅色肚子,吸引著雌刺魚,及跟我一樣的小男孩。一整天下來的成果,就是果醬瓶中憤怒面孔的數量。
在離我的池塘很遙遠的世界中,披頭四的知名度達到巔峰,而冷戰也籠罩著世界。蘇聯的捕魚船隊全面地在公海上尋找可以開發的新漁源。當美國人成功抵達月球之時,蘇聯探索地球上最後的荒野,成為在超過一千公尺深、有著無盡黑夜水域中捕魚的先鋒。其努力標示了第三次和最後一次的拖網革命。第一次革命,在本書前面有討論過,是由十四世紀所發明的拖網所揭開的;而第二次革命則是十九世紀後期的蒸汽動力拖網漁船。
蘇聯的第一艘深海拖網漁船,用更大的絞盤與增加纜繩的長度和強度,簡單地改良那些已經使用在大陸棚上的拖網。一九六○年代中期,蘇聯、波蘭和東德的漁業調查船,有系統地探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從大陸的兩側,用回聲探深儀和拖網橫掃整片海洋。在接近冰點的大西洋深處、淺水區拖網鞭長莫及的區域中,他們發現了大量可供開發的物種,像是格陵蘭大比目魚和圓吻突吻鱈(roundnose grenadier)。拖網拖過這些未曾開發過的魚場,每小時就可撈捕十五到三十公噸的魚,讓二十世紀初期的漁民們嘗到了祖先們在十九世紀淺水海域中捕魚時所獲得的成功滋味。格陵蘭大比目魚看起來比在大陸棚捕捉到的大比目魚顏色更深、且更瘦一些,而牠們馬上就有了一個現成的市場。至於圓吻突吻鱈,有著鈍形的頭、凸出的大眼,及鞭狀的細尾,比較不為大眾所熟悉,但在味道上,牠毫不遜色,漁業科學家描述牠的肉質「可口、細緻,比鱈魚更嫩。」1這種魚又大,肉質又緊實。蘇聯共產主義下的消費者,即使排在無止盡的隊伍中,也是耐心等待,並無怨言。
受到初期成功的鼓舞,很快就有了拖網漁船隊開始在公海上作業,提供漁獲給巨大的海上水產加工船來處理。一開始,他們在泥濘的大陸坡,也就是大陸棚向下陡降到大洋深處海溝的泥濘斜坡區域進行捕撈作業,但是,粗糙的地表會造成拖網破裂,早期參與調查的俄羅斯漁業科學家派什尼克(Pechenik)和特洛伊安諾斯基(Troyanovskii),描述了他們在北大西洋邊緣所遭遇到的各種不同海床:「在大陸棚邊緣和大陸坡上半部,大約八百到一千公尺深的地方,到處都是礫石、卵石,或是大石頭。幾乎到處都有海綿,有些地方則有珊瑚。」2而且,「這些由大石頭、珊瑚和海綿結合成複雜的海底構造,讓漁具很難在冰島南方的大陸坡上運作,拖網被纏住、撕裂的狀況,在這裡經常發生……在(拉布拉多大陸坡)的某些區段,約八百到八百五十公尺深的地方,珊瑚對拖網造成很大的阻礙。」3
得做些什麼事,來處理這樣的問題。沒過多久,網具進行改良,用沉重的鋼和橡膠製成的滾輪和鏈條,取代了在淺水區拖網上較小的滾筒和拖底鏈。於是,拖網現在可以「跳躍」穿過崎嶇的區域,通過岩石、珊瑚或是海綿等障礙物,這些海底障礙物都在拖網行經的路徑上被刮倒。這樣的漁具被稱為「滾輪式底拖網」(rockhopper gears),可在海底山的兩側和尖端區域進行捕撈,也因此開發了更具經濟價值的漁場。
深海的生產力甚至比公海還低,大多數生活在海溝動物,幾乎完全依賴來自淺水區的食物。像是在陽光可及處有水中植物所產生的有機物質,以及動物屍體和植物上飄落的一點點食物。從陽光可照射到的水層,這些有機物像雪花般下沉到黑暗之中,有些動物則會更積極地尋找食物,在夜晚從深層水域上升到淺層水域覓食。雖然養份貧乏的公海海域生產力很小,食物來源非常有限,但它們仍提供了海洋食物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將食物從海表層帶到深海中殷殷期盼的掠食者口中。
泥濘的海底平原就跟大陸一樣廣大,覆蓋大部分的海底區域,但當地形單調的海底平原兩側向中央推擠出了海底山,將它的頂峰推上到交疊的水層時,製造出了像是個口袋一樣的高生產區域。海流在海底山周圍循環,與來自表層的海水混合後,形成巨大的迴旋,將海床上的養分帶到表層。海底山因為將養分帶到海表面,形成了像是綠洲一樣的高生產力區域,吸引著野生動物。對於鮪魚之類的物種,這是些地方是牠們遷徙穿越大洋時的航點和補給站。來自日本的長鰭鮪,會在夏威夷的海底山停留幾天,在溫暖的表面海水和冷涼的海底山坡水域中來回下潛,在旅途繼續之前先進行覓食。信天翁飛行數千英里,追捕在海底山坡上迴旋水流中的魚類和魷魚,然後將獵物帶回到遙遠的小島棲息地,餵食等待中的幼雛。
流經過海底山的海流帶來食物,就像是不停止的輸送帶,將廣袤海洋中的產物,分送給生活在這周圍的動物們,使得海底山區域能夠維持數量很多的魚。舉例來說,一九六○年代末期,蘇聯的漁民發現數量龐大的李氏擬五棘鯛(pelagic armourhead)群聚在夏威夷的海底山周圍。4李氏擬五棘鯛看起來像是熱帶的笛鯛,背部高高聳起,胖胖的,有著深色專注的雙眼,其銀灰色的身體,像是幽靈般與灰藍色的深海融合為一,拖網漁船可以很輕鬆地將一群群擠在一起的李氏擬五棘鯛舀起。蘇聯人發現了這樣一個金礦,然後,漁業爆發式地發展,蘇聯和日本的漁船每年就撈捕了數萬噸的魚來換取現金,但這個魚礦在崩壞之前,僅僅持續了十年。在一九七六和一九七七年之間,漁獲量從三萬公噸下跌到僅剩三千五百公噸,之後就再也沒有恢復過。但漁民卻不為所動,因為估計至少有八萬座以上的海底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中,這使得他們能夠保持樂觀。
大多數在泥濘大陸坡上活動的魚並不適合人類食用,因為在水流很弱的深海中,牠們不大需要強而有力的肌肉,而且牠們所能獲得的食物非常貧乏,無法維持高活動力的生活,牠們水水軟軟的肉很不好吃,由於油脂含量很低,也不常用來製成動物飼料。相較之下,漁民對海底山很有興趣,且海底山魚類也較受人歡迎。因為此區有著強勁水流,生活在此的魚類,肌肉特別發達,加上此區的食物豐富營養,滋養了海底山魚類。
下一個魚礦是在紐西蘭海域。蘇聯的船隻在查漢姆海嶺(Chatham Rise)八百到一千公尺深處捕撈時,巧遇具有商業價值的鮮橘色魚群。這種從背部到腹部都很寬的魚,有著強健、像是披了盔甲的頭,像貓頭鷹般專注的眼睛,和向下彎曲的嘴,雖然牠們只有七十公分長,但是很粗壯,而且肌肉發達。5紐西蘭人很快就加入了蘇聯的船隊追捕這種魚,離開沿海區域,去探索他們國家周圍的海底峽谷和山脈。
要銷售這種長相奇特的魚,首先就是幫牠換個名字,「大西洋胸棘鯛」(Hoplostethus atlanticus)是科學家所取的學名,屬於燧鯛科(slimehead)。但是,不論燧鯛魚片包裝如何精美,用這個名字很難讓消費者把牠放到推車上,不過,若改名為「橘棘鯛」(orange roughy),對消費者就很有吸引力了。牠們緊實如瓷器般的肉質,在貨架上看起來很不錯,更好的是,牠能承受幾次的退冰跟冷凍而不會腐壞,這讓牠成為像是鱈魚這類淺水魚很理想的替代品。橘棘鯛的味道並有沒什麼特別之處,然而,經處理後,裹著麵包粉的魚片、魚餅和炸魚條的銷售量很好。
查漢姆海嶺是一座水下山脈,綿延在紐西蘭南島以東,範圍跟南島的面積一樣大,最高峰在海面下五百公尺左右,是在深海底拖網可及的之處,漁民迅速準備好深海捕魚的器具,於是,漁獲量猛然大增,在一九八○年代中期達到每年五萬公噸。在紐西蘭的成功,誘使澳洲漁民也開始在塔斯馬尼亞(Tasmania)試試他們的運氣。艾倫.巴奈特(Alan Barnett)是第一個在那裡抓到橘棘鯛的漁民之一,一九八九年,他在塔斯馬尼亞東邊的大陸棚邊緣,一座名為聖海倫山(St. Helen’s Hill)的海底山挖到了漁礦。聖海倫山是一個圓錐形的死火山,從深超過一公里的海床上方六百公尺處,如同許多具有商業價值的深海物種一樣,橘棘鯛也在海底山周圍聚集產卵。聖海倫山是魚群交配混戰的區域,漁船可以利用聲納發現密集的魚群,然後下拖網將牠們撈起,如果下網的位置對了,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捕撈到五十、六十公噸的魚。一位漁民說,初期在這裡抓魚非常容易,只要在水中拖一個布袋a(chaff bag),就可以抓到魚。6在頭一年,聖海倫山區域的橘棘鯛漁獲量驚人地達到了一萬七千公噸,被捕撈上岸的魚數量驚人,擠滿了所有的冷凍設施,滿載的卡車甚至得將漁獲載到垃圾掩埋場丟棄。
捕撈得實在太多又太快了。在早期,漁業管理者對於橘棘鯛不了解,而且也沒有管理深海漁業的經驗。紐西蘭的漁業管理者認為應該要有所節制,於是依據他們對體型大約相當的淺海魚生物學之了解,來設定捕撈配額。他們假設,深海魚類和淺海魚類,除了居住的深度不同之外,其他各方面都一樣,但是事實證明,生活在深海是非常不同的。橘棘鯛是一種奇怪的魚類,當魚從一個個的海底山區域被撈起後,漁獲量很快就垂直下跌。原來,這種魚被捕獲時已經非常老了。雖然海底山是生產力的熱點,但這只是相對其他深海部分而言。在黑暗且寒冷的區域中,生命步調非常緩慢。科學家們一開始用魚鱗上的環狀構造錯估了橘棘鯛的年齡,對淺海魚來說,由於一年中生長速率的改變,使得牠們身上的鱗片會有特殊的年輪,但在橘棘鯛的魚鱗上形成輪,需要更長的時間。根據封存在魚的耳石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測量結果,提供了正確的魚齡估算,結果顯示,橘棘鯛可以活到至少一百五十歲!那些在魚販攤位上出售的魚,對人類來說,其年齡相當於老年人!此外,這種魚直到二十二至四十歲,才會達到生殖成熟。
這樣長壽且晚熟的組合,使得牠們跟其他魚類一樣,難以逃離過漁的命運。此類物種的數量成長率都很低,對於需要可長期持續的漁業來說,必須遵守的原則是:魚類被捕撈的速度,不能高於牠們可以自行補充的速度。由於橘棘鯛成長速度緩慢,牠們的可永續捕撈量,大約是每年其族群數量的百分之一到二。牠們會在海底山周圍聚集的特性,導致容易被發現和捕撈,而增加了過漁的風險。再加上牠們多在產卵場遭捕撈,更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淺海中的物種在聚集產卵期間特別脆弱,例如溫帶海洋的鯡魚和熱帶的石斑魚,在其產卵期通常都會季節性或區域性地限制捕撈,諷刺的是,深海漁業中,漁民捕撈因產卵而聚集的魚類,以確保有足夠的漁獲與收益。
深海漁業捕撈的速度遠高過可永續的量,族群的崩潰勢不可免。在十年之內,澳洲和紐西蘭的漁業即陷入困境,漁獲量急轉直下。漁業管理者努力遏止漁獲量下滑,於是將配額量訂得更為嚴苛。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澳洲的棘鯛熱潮就結束了,每年的漁獲量下降到了大約幾百公噸。紐西蘭的漁業比較穩定,但也只是因為其深水漁場較為廣大,漁獲量在一九九○年代下降後,維持在每年約一萬五千噸,但這種穩定並不是通過管理控制,而是經由一連串新漁場的過漁,當所有的新漁場都一一被發現及捕撈殆盡後,紐西蘭橘棘鯛漁業將踏上和澳洲一樣的末路。
原本不受這些問題干擾的深海,於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間,深海漁業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由於淺海漁業魚群數量的下滑,以及越來越多的規定限制,使得特別像是歐洲的漁民,從大陸棚轉向深海捕撈。對於胸懷壯志的年輕船長來說,沒有配額限制的深海,不只可以謀生,甚至是可以發財的地方;而對於投資的銀行家而言,深海提供了具吸引力的回報,而且比傳統漁業所冒的風險更小。帶著新式巨型拖網的漁船船隊於是啟航了,每艘都價值數百萬美元並配備有高度先進的定位儀器,用來找魚和抓魚。
在北大西洋,這些超級拖網漁船再度無情地於先前俄羅斯與東歐船隊打開的傷痕上運作。在一九六○年代充滿商業希望的圓吻突吻鱈,在大西洋被剷除一空,許多漁業科學家擔心這個物種的數量已經低於能夠恢復的邊緣。在大西洋的橘棘鯛數量,比澳洲和紐西蘭海域的還少,而其漁獲量在五年內爆增又爆跌。三十年後的現在,深海漁業的目標物種來了又去,就好像早期一連串淺海魚類遭過度捕撈的過程,正被以快轉模式重複放映,不同的是,即使我們已停止捕撈,但深海魚類卻較難以復原。因為牠們成長緩慢,繁殖較難成功,加上拖網持續不斷損壞其棲地,都削減了牠們能夠自數量枯竭而恢復的能力。
關於拖網漁業造成魚類及其棲地破壞性影響的投訴,在二十世紀初期陷入了沉默。也許,在整個世界的淺海大陸棚上隆隆前進的拖網,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而漁民認為,對於這種不可抗拒的未來,沒有甚麼好爭辯的。但他們之所以停止抗議,或許是因為有證據顯示,損害也是隨著時間而減少。第一艘拖網漁船進入無人捕撈過的漁場,摧毀了那些歷經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形成的海底生態。在最初幾年,底拖網的拖動,將原本滿是珊瑚、海綿、海扇和海葵的海床,變成了由泥巴、卵石、海星和蠕蟲組成的海底。雖然後來的拖網繼續捕捉了許多體型過小的魚,然而,最糟糕的破壞已經出現,最脆弱的魚類早就被清除一空,無法再捕撈到眾多的數量。在二十世紀後期,深海漁業這種破壞原始區域的漁撈方式,重新點燃了使用底拖網捕魚的爭議。
(圖說)豐富的動物相,包含珊瑚、海扇、海綿和無脊椎動物,覆滿了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中阿黛勒島(Adale Island)的水下山坡。這一幕是透過潛水器窗口拍下來的,呈現出從未受到底拖網襲擊的區域。(阿爾貝托.林德納(Alberto Lindner)∕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
最有利可圖的深海漁業目標,是在具有重要生物意義的區域,包括海底山、 峽谷和山脊。大多數深海棲息地都被泥巴覆蓋,但在這些地方,強勁的海流足以把沉積物帶走。海流帶來的食物,提供群聚的魚類食用,並維持有著豐富濾食性動物的動物相,它包含了珊瑚、海綿、海扇、水螅和無數其他脆弱的物種。蘇聯漁業科學家記錄下這些動物,僅因為牠們在一九六○年代對於捕魚構成障礙。7但近年來,因為有了潛艇燈的燈光束,照亮了海底山坡的面貌,才顯露出這個地方是一座有著無脊椎動物、華麗而豐美的花園。一九九○年代中期,美國的潛水艇經過了阿拉斯加海底山的兩側,科學家們遇到了有著不可抗拒的美麗的珊瑚林。亮橘色的水螅掛在赭黃色的海綿上,像是精緻的葉片隨著巨浪起伏;礁岩上,柳珊瑚的紅色扇葉向上伸展,像迷宮般有刺的水螅體隨著微風般的水流,讓浮游生物在其中漂動;黑櫻桃色的陽燧足緊抓住一個亮粉橘色的珊瑚分枝,在一瞬間就彎起牠錯縱複雜的腕;體型細長的螃蟹,躡手躡腳地跨過成堆疊起、有著堅硬外殼的薰衣草色海鞘。在這片林地中間,受到聚光燈驚嚇的魚,先是停住不動,然後就輕搖閃亮的魚尾,向下潛入黑暗之中。
面對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景象,很難想像在十八世紀時,人們會認為深海中沒有生命存在。當時,睿智的人們認為,沒有生物能夠承受深海中足以壓碎身體的壓力、永遠的黑暗,和海溝中如北極般的冰冷。在《歐洲海域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European Seas)一書中,博物學家愛德華.福布斯(Edward Forbes)用網和耙網來探測深海的深度,他探測到了兩千英尺(六百一十五公尺)。福布斯是不列顛群島中的曼島(Isle of Man)人,他在一八五○年代總結了當時所知的:
我們所在區域的深海中,最終也最深的地方,有著深海珊瑚,在歐洲大洋中的這些植形動物,因為有石化的特徵,而被如此命名。在這麼深的地方,奇特生物的數量很少,但足以呈現這個區域的特色……當我們下潛到更深處,那裡的生物越來越多變,也越來越少,表示已經逐漸靠進海底深淵,在那裡,生命要不是不存在,要不就是僅有微乎其微的生命火花,證明生命的存在。它的極限還未知,在這片廣袤的深海區域中,還有最美好的地方等待著深海探險去發現。8
福布斯沒能更進一步參與深海探勘,一八五四年,三十九歲的他,就要獲得愛丁堡大學的教授職位時就過世了。如果他還活著,一定會參加第一次的深海大探勘——「挑戰者號」(Challenger)的探險。皇家海軍艦艇「挑戰者號」於一八七二年從英國的普次茅斯港(Portsmouth)啟航,在海上超過三年。這艘船環繞整個地球,並煞費苦心地放下鋼製的顎,在空中抓緊再放開,達數百次之多,在其所到之處,甚至是最深的海底,都帶回了有生命存在的證據。
深海生物終於獲得確認,從那時候開始,許多國家加入了深海探索。經由這些探險活動,記錄深海中的生命,與評論這深不可測的海洋。深海很快就被證明是提供這個星球生物最大空間之處,也就是生物圈的百分之九十五都在深海,無奈的是,大部分時候,當這些動物被帶到表面時都已經瀕臨死亡,並且往往因為快速減壓,使得牠們的外型被扭曲得很可怕,因而沒有人見過牠們生活在深海中的自然面貌,直到了美國探險家威廉.畢比(William Beebe)和他的同伴歐提斯.巴頓(Otis Barton)決定親自去探訪深海生命。一九三○年代初期,他們開發出能夠帶著他們潛入深海的「探海球」(bathysphere),這個球體是由一.五英吋(四公分)厚的鋼所製成的,雖然不太舒適,但足夠裝得下兩個男人,這個球體是由鋼纜懸掛在船的底部,他們在裡面蜷屈著身體,透過兩個三英吋(約八公分)石英玻璃的小舷窗來觀察海溝。一九三四年,在百慕達外海,探海球成功地下探到大西洋的半英里(八百公尺)深,畢比記錄了他們潛入深海的經驗:
隨著深度越來越深,只有微光,我們會說這仍然還有點亮,在我看來,這就像是一道快要熄滅的恐怖火焰。我發現,我們都期待著光線被吹滅、進入絕對黑暗的一刻。但是,只有在自己把眼睛閉上再張開的時候,才意識到從深藍色轉變到更深藍色的過程緩慢得可怕,在地表有著滿月的夜晚,我總是能想像黃色的陽光,和盛開鮮紅色的無形花朵,但在這裡,當搜尋用的光線關上,黃色、橘色和紅色都不可想像,整個空間充滿著藍色,沒有任何思緒可以想到其他顏色。9
更向下深潛,他們遇到充滿生命的水層——凝膠狀半透明的樽海鞘(salps),牠是一種像是海鞘(sea squirts)的動物,彷彿緞帶般掛在海中;飛奔過的蝦子;被強光燈嚇呆的魚;好奇的魷魚,和無數微小的橈足類和浮游生物。當關了燈,他們發現,像是星座般的魚類和浮游生物點亮了黑暗,牠們在虛無中,用無聲的藍色、紫紅色、粉紅色、純白色的脈衝光彼此溝通,畢比繼續說道:
有時候,未知生物所發出的光線是如此明亮,我的視線因此昏花了好幾秒,在一般情況下,有豐富的光線,讓人無可避免地想到在清朗、沒有月亮的夜空星星,牠們不斷移動,讓人搞不清牠前進的方向,因而無法集中視線,但在經過一連串的努力之後,我開始可以明確跟隨這些互相有關聯的光線,在很多情況下,最後可以看出來魚類的輪廓。10
畢比和巴頓開啟了由人類操控載具探索深海的時代。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探險家和科學家們拜訪了海底山和峽谷,在海洋深處乘著墨西哥灣暖流,並於一九六○年碰觸到最深的海底——位於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Pacific Mariana Islands)附近馬里亞納海溝的「挑戰者深淵」(Challenger Deep)。這道有著一萬○九百二十公尺深的海溝,在輕易裝下珠穆朗瑪峰之後,仍有很多的空間。而即使在最底層的世界仍有生命。領航員賈克.皮卡德(Jacques Piccard)和唐.華許(Don Walsh)於一九六○年的航行中,在海溝的底部休息時,他們看到了一隻魚、一隻蝦和海參爬行的痕跡,這才終止了人們認為在最深的海底不可能有生命存在的想法。
一九七○年代,深海科學家已開發出了更便宜的方法來到海底。藉由建造可以栓在母船上的遙控潛水器(ROV)下潛,然後由在母船上的工作小組操控。當時,生物學家已取樣的地方,只是深海海底的萬分之一,仍然有許多地方待探索。人們開玩笑地說,我們對月球陰暗面已有的了解比深海還多。遙控系統大大提高了勘探的速率,再加上與載人潛水器結合,令人興奮的發現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一九七七年,海洋科學家們搭乘「艾文號」(Alvin)在加拉巴哥群島附近、兩千到三千公尺深的海底巡航時,發現了深海熱泉(hydrothermal vents),這些熱泉噴出黑色、富含硫磺的水,溫度高達攝氏三百度左右,如果是在陸地上,這樣的水早已經滾了,但因為深海高壓的關係,使得這些水不致於沸騰。對生物來說,沐浴在炎熱、富含礦物質的水中,是非常豐足的,像是血紅色的管蟲、巨大的白蛤、紅色的蝦、蒼白的龍蝦、排列緊密的棕色貽貝,和其他許多生活在這裡的生物,讓深海生物學整個改觀。早先,這些生物如何在這裡倖存下來是一個謎,直到哈佛大學的生物學家發現牠們與一種細菌共生,這種細菌可在沒有光線的狀態下將硫化物轉變為能量及食物。現在,已知的深海熱泉遍布海洋各處。
一直到了過去十年左右,我們才意識到在北大西洋深海的冷水區域中有大量的珊瑚礁聚落,愛德華.福布斯在十九世紀中期就很清楚知道有深水珊瑚,但他並不知道牠們會成礁。早期的拖網漁船船長都知道在深海中哪裡有大片的珊瑚生長,因為珊瑚會扯壞他們的漁網。一九二○年代,法國科學家茹班(M. L. Joubin)發表了一篇《深海珊瑚——拖網漁船的麻煩》(Deep Sea Corals: A Nuisance to Trawlers),標註了分布在歐洲大陸棚邊緣的珊瑚,好讓漁民得以避開高風險的區域。
在過去幾年中,法國漁船船主大幅增加船隻的噸位和馬力,這讓他們能夠操縱拖網抵達以前從沒到過的深海區域。
在冰冷黑暗的海水中,大約是從水深兩百公尺處開始,他們遇到了分枝狀的珊瑚,這些珊瑚是由極其堅硬的石灰石所組成的,牠們有著白色且尖銳的邊緣,其堅硬度和瓷器一樣。網子會因此被撕裂,並掛在珊瑚上頭,牠們所做最微不足道的壞事,就是牠們充滿著斷裂的枝幹,讓拖網無法在此處作業。有一天,「丁鱥號」(Tanche)的拖網,僅拖一次網,就撈起了五到六噸的斷裂枝幹。11
一直要到了一九八○年代,北海石油企業用遙控潛水器擦過海床,來繪製海底地圖,以便安排管線路徑時,這些壯麗的珊瑚礁才終於被展現出來。有些綿延數十公里的珊瑚礁聚落,是珊瑚在滿布砂礫的海底山脊上,以每年幾公厘的速度,花了幾千年所建造的,這些珊瑚礁是千餘種物種的棲地,也是許多具重要商業價值的魚類和其他人類不太熟悉的生物的家。
在這寒冷、仙境般的美麗珊瑚中,挪威科學家發現令人不安的事實,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人早一步發現這裡。遙控潛水器沿著珊瑚礁的邊緣航行,發現活珊瑚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碎石和沙粒。有些地方,幾公尺巨大的珊瑚礁塊被拖起來,翻到旁邊的活珊瑚上,在海扇和海綿中間的空隙中,有像大鐮刀割出的深溝橫跨海底。沒多久後,他們看到了頂端纏著撕裂拖網的珊瑚礁,以及沉重鋼製拖網門拖行通過珊瑚礁後切出的溝槽,發現罪魁禍首就是拖網捕撈。他們計算的結果是,三○%到五○%的挪威深海珊瑚礁已嚴重受到二十世紀後期的拖網漁業嚴重損傷或毀壞。如同在茹班的文章中所呈現的,在現在這波深海底拖漁業之前,淺海的珊瑚礁很可能已經遭受同樣的命運。挪威漁民曾在海底的「粗糙表面」上用雙拖網捕撈,首先投下一條鎖鏈懸掛在兩艘船中間來移除障礙物,然後再返回,將魚從殘骸之中撈起。
現在的商業拖網漁船可以在水下兩千公尺作業,這深度是威廉.畢比早期下潛深度的兩倍,每到一處,科學家都會發現拖網具破壞性影響的證據。幾十年來,深海拖網漁船在公海上漫遊,摧毀了無數的重要生物棲地,如果是在陸地上,那些地方早就被劃為國家公園。在那些深海生物甚至還沒有科學描述之前,我們就已經失去牠們。現今的海洋學家想必了解埃及古物學家的挫折,當他們發現新墓穴石時,卻發現墓穴早就被洗劫一空了。當科學家們的潛水器降落在新標示出的海底山上,打開燈光後,能看到的只有過去生命的殘存碎片。緬因大學的科學家萊斯.瓦特林(Les Watling)談起他在二○○五年時,拜訪西北大西洋的海底山的經歷:
我們到崛起角海底山(Corner Rise seamounts)研究深海珊瑚和海扇,即使牠們距離任何你所能到達的北大西洋上的陸地都一樣遠,俄羅斯自一九七○到一九九○年間,在這裡捕了大約二十年的魚。我們依美國著名陽遂足分類學家的名字,把第一座稱為萊曼海底山(Lyman Seamount)(那時我們不知道俄國人叫它做亞庫塔特(Yakutat))。在完全現代化製圖之後,我們挑了好幾個潛水點,並準備好遙控潛水器。當遙控潛水器下降到超過一千公尺深的時候,我們無不充滿極大期待,在潛水器向下沉的兩小時中,控制室裡的每個人都在問:我們將會降落在什麼樣的海底、我們會發現多少種和多少數量的珊瑚、這在科學上代表了什麼意義等等的問題,雖然在萊曼海底山,我們並沒有預期會有什麼樣的景象映入眼簾,但最後我們還是既驚訝又困惑,感到驚訝的是,因為那裡看起來像是海底山的上層已經被毀壞、壓碎和崩解,顯示出的是,它覆蓋著到處都是被深深割劃過的表層;而讓我們感到困惑是,因為我們沒有想到漁具會造成如此浩劫。我們要求遙控潛水器的駕駛員這樣開、那樣開,而每種視角都呈現出相同的殘破景觀。很多可能造成這樣重度破壞的原因都被提出來,它有受損嗎?難道這是在自然過程中造成的?但是,我們知道有人在這裡捕魚,因此問題變成:究竟是什麼樣的漁具,或是漁具的哪個部分,能夠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似乎是俄羅斯漁具沉重的拖網門反覆地在這海中央的山峰上拖行,而它所造成的結果是,現在這裡幾乎沒有任何生命存在。表面除了碎石,什麼都沒有,看起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珊瑚聚落都不可能在這裡恢復了。12
(內文)
同樣破壞性的力量也已經造訪過其他地方。北美東部外海地區有著奇特美麗的玻璃海綿(glass sponges)區域,在被拖網拖過後,已經被人們遺忘了。南方海洋中的海底山曾有著住滿無脊椎動物的繁茂森林,但在幾十年間,因用拖網捕撈橘棘鯛,目前此處已被清除一空,僅剩下光禿禿的岩石。一個關於早期珊瑚礁被澳洲捕撈橘棘鯛的船隻混獲的研究,發現每二.二五公噸的橘棘鯛被拖上海面,就有一噸的珊瑚礁也一起被撈起。13我們只能推測還有多少珊瑚礁被毀壞後仍留在海底。但是,當澳洲科學家比較被拖網拖過,以及沒被拖過的海底山,可看出極為強烈的反差。尚未被拖網拖過的海底山表面覆蓋著地毯般的珊瑚和其他無脊椎動物,而被拖網拖過的海底山,則是一片令人震驚的不毛之地,縱橫交錯著拖網反覆拖行的傷痕,暴露在裸露岩石的荒涼景象中。
即使可能有機會恢復,但深海拖網所造成的傷害,也將持續數個世代。許多巨大珊瑚花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才形成目前的規模。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peace)在紐西蘭利用《資訊自由法》迫使漁業觀察員將他們在深海拖網船上所拍到的照片公開,在其中一張照片裡,有個比人還高、超過數百公斤重的巨大珊瑚礁,從網上取下後,被起重機吊起丟回海中。
深海漁業雖是捕撈,但更像是採礦,而被撈走的深海魚類,就像是煤或石油,是無法再生的資源。從事深海漁業的巨大船隻,一天光是運作就需要數千美金,他們用無法永續的速度捕撈,就只是為了平衡收支。沒有任何一種工業規模的深海漁業可同時兼顧商業利益與永續,如果用可永續的速率來捕魚,他們就會破產。但是,深海漁業瘋狂的地方並不只是開採目標魚群,無數沒有商業價值的物種也變成了魚鉤和魚網下的犧牲品,就向目標物種一樣,牠們非常容易受到過度捕撈的影響,因為牠們生長緩慢,例如有著駝峰和閃亮眼睛的庫克笠鱗鯊(prickly sharks);有著奇怪獨角的劍吻鯊(goblin sharks);可以吞下比自己還大的獵物的寬咽魚(gulper eels);像足球一樣大的巨型單細胞;沒有外殼的有孔蟲(xenophyophores);沒有下巴、滴著黏液無頜的盲鰻(hagfishes);用鰭站立的三腳魚(tripod fish)。許多物種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這個星球上,牠們的生命即將結束,卻連個訃文或是墓誌銘都沒有。
從一九七○年代以來,世界上的海底山因為漁業追求快速利潤而被無情地開採,蘇聯船隊在其他國家還沒有注意到他們在那邊活動前,就把大多數大西洋區域的海底山一掃而空,深海拖網漁船船長就像是十八世紀在未被發現的區域中獵捕海豹的船長一樣,必須是第一個發現資源的人,因為這些資源的發現者,同時也是毀滅者。不久之前,深海似乎比月亮還遙遠,更鮮為人知,仍然是地球上最後的邊疆,讓人類擴張和占用,但是,在海底深淵,我們仍繼續長期建立的模式,將大型動物獵捕殆盡,同時也破壞牠們的棲地。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拖網漁船破壞原始的海洋荒野,撕毀看不見的森林,將無人知曉的黃石公園剷平。根據一八八三年英國皇家調查委員會中,蘇格蘭鄧巴(Dunbar)的羅伯.史密斯(Robert Smyth)提出的證詞:「如果社會大眾知道更多(拖網)所造成的破壞,也知道它仍繼續使用的話,民眾會譴責這種邪惡的捕魚方式。」14他的話至今仍然跟當時一樣真實。
作者簡介
海洋保育生物學家,現職為英格蘭約克大學環境系教授,也是位多產的作家及學者,擔任美國、英國、加勒比海島國國立海洋保留區顧問。
譯者:吳佳其
德國波昂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班生,研究方向為海洋自然資源管理。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