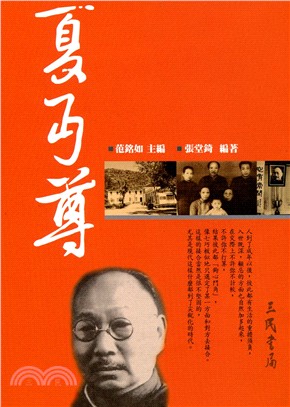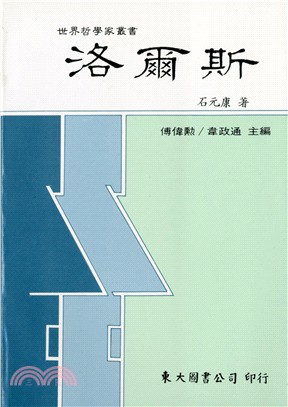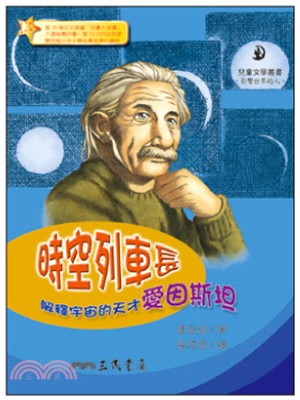商品簡介
《看日出——吳冠中老師66封信中的世界》除了66封吳冠中原信,還配上了多幅他信中提到的畫作,并加上了鄒德儂對吳冠中創作思想、創作過程的講解,從中既可以了解到吳冠中迎著一切艱險去創造的喜怒哀樂,也能夠領略到吳冠中藝術的國際視野、現代精神和博大精深。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畫面中間略偏左,滿鋪兩顆棗樹,樹干、枝椏曲曲折折,紅棗、綠葉麻麻點點。題字從左向右,自右往下,再由下而左,圍著棗樹幾乎布滿一圈,形成襯托棗樹的一個灰面,好一幅彩點、墨線與灰面的小小交響詩。畫上寫的是:
“三月,所有的樹木都已抽芽發葉,只棗樹光禿著烏黑僵硬的干枝,死一般的沉寂,全不羨慕春色。
小院角落,平野荒漠,深山空谷,只要能伸下一腳,便足立命安家。
雖然瘦,頂風不低頭。曲曲折折,遍體枝節,針刺密,并非就是荊’棘,秋來掛滿果實。
棗實甜蜜,紅不似血,紅得沉著樸實,是獨特的紅色,棗紅色。”
這是吳冠中老師所獨有的,與他的繪畫同樣具形式感的深邃文字,非詩,非詞,也不像雜文,卻有著與詩詞及雜文一樣的韻律和靈魂。這,是他在“文革”漫漫黑夜里的自嘆,是他文字版的“自畫像”,更是吳冠中藝術在困苦的環境中,頑強拼搏并終將崛起的預言式寫照。今天,我們都在享用著吳冠中藝術紅得沉著樸實的甜蜜棗實。
1975年5月27日,吳冠中老師到青島四方機車車輛廠的第二天,我和俞壽賓、張效孟三個業余畫友開始了與吳師的一段親密接觸。在日夜相隨的一個月嶗山和市區寫生中,詳讀了他藝術創作過程的細枝末節,聆聽了他藝術人生的苦戀求索,領受了他作為教師的偉大人格魅力。這段經歷成為我人生的轉折點,特別是此後到1987年末的12年間,吳師給我等回的66封信,不但飽含他對我,一個建筑藝徒關愛、教育和扶持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它們注解了吳冠中藝術迎著一切險阻去創造,賦予中國藝術以國際視野和現代精神的藝術進程。我慶幸,當年自作主張違背“信勿保留”的師命,小心珍藏了這些文獻。
1980年代初,吳冠中藝術已堅定地跨越過“油畫民族化”路標,開始了充滿艱險的“中年變法”歷程,他以“油彩墨彩轉輪來”所激發的全新創造力,成功地畫出了一批融中西藝術于一爐且具強烈現代性的全新中國繪畫作品,并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他那以《望盡天涯路》為代表的傳奇藝術生涯,以《風箏不斷線》為代表的藝術理論,以及包含在1987年出版的《吳冠中文集》中的藝術思想,當然還有同時期舉辦的那些畫展和出版的種種畫冊,都是吳冠中藝術沖破黎明前黑暗時刻的光芒。而在這66封個人信件里,吳冠中表達思想更為自由、直白。他對後生的滿腔熱忱,他對自己坦白而真誠的剖析,他針對社會藝術愚昧所作的精準而犀利的批判,以及他那雋永而優美的文字……無不鮮明地道出他壓在心底的藝術訴求,生動地反映出他在新征程中的喜怒哀樂。每當翻動這些書信原件,那紙張、那字跡,真實而生動地訴說著那年月、那事情,字字讓人怦然心動,信中字句的文學品性,散發著陣陣醇香……我愿與更多朋友分享閱讀中的百味,共睹吳冠中藝術的凌晨及日出時光。
這些信寫在35年前,事情的確離我們很遠了,但內中的道理卻離我們很近,它對當今藝術社會和藝術人生的警示作用,依然鮮明。
進入新的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市場業已形成,社會對藝術之寬容度,已經和現代藝術的故鄉相差無幾,可以說,進入了一個什么都可以成為藝術品,誰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的自由境界。然而,就在這創作環境最開放、學術研究最自由的時日,我們的藝術創造力,包括建筑藝術的創造力在內,似乎并無相應幅度的提升,甚至有些下降。許多藝術家或建筑師,在藝術難關面前,繞開藝術門類的本體,企圖走一條易操作或模仿之路,辜負了這個寬松時代賦予的創造環境。
吳冠中藝術艱辛而獨特的進程,清楚地驗證了作為藝術家的必備性格——要創造,現代性的創造,中國文人的創造。這個進程也指出,創造沒有近路,甚至沒有路。吳冠中當年面前也沒有路,他像魯迅在《兩地書》里所說的那樣,顧不了那么多的危險,“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跨進去,在荊叢里姑且走走”。吳冠中藝術在“只能伸下一只腳”的地方起步,勇往直前,“頂風不低頭”。也許,真正的大師,文學的、藝術的、科學的,都需要歷練苦難,生活的,思想的,當然更有專業的。吳先生在這些信中表達出的那些創造中的痛苦、快樂甚至“狂妄”,值得今天的從藝者認真體味、踐行。
我和俞壽賓、張效孟是對吳冠中藝術生活片段的近距離觀察者,盡管視野不寬,時間不長,但所見真切,感觸良深。當時,我們不過是三個普通的業余繪畫青年,如今,也只是再普通不過熱愛美術的“70後”老漢。我們沒有畫出令人矚目的“名作”,也沒有做出動人心魄的“大事”,然而,我們為自己的職業生涯能融入吳冠中藝術及其思想而驕傲。他的思想不但指導了我們工作中與美術有關的領域,同時在藝術視野、思想方法乃至做人處事方面,吳冠中藝術及思想對我們的影響也是關鍵性的、持久性的。“嶗山聞道”之後,我確立了探求現代藝術和現代建筑的人生目標;返回天津大學建筑系任教以後,努力讀書、譯書,西方現代藝術的,西方現代建筑的,以至後來偶然落腳于中國現代建筑的研究,都與吳冠中藝術思想和吳冠中老師的直接扶持有關。
師恩如泉,我輩無以報答。
面對這些信件,我想起第一次見吳先生時,看到他帶來的幾幅畫,其中兩幅至今不忘。一幅是油彩《野菊花》,那野菊,繁盛、強壯,表現出在山巖雜草中沖破一切困難向陽怒放的生命力。野,勝過家,家菊已聽人管束,往往故作姿態。而野菊,按照自己的意志生長壯大,盡管生存條件困難,仍然長得茁壯而且快樂。另一幅小型水墨是《黃山日出》,那是我見到吳師的第一幅“中國畫”,群松向左右甩開臂膀,層云上下交錯漂浮,云頂閃出半個紅日,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吳師的畫中出現太陽。這兩幅作品,一幅油彩,一幅墨彩;野菊在地,紅日在天。它們似乎是一個明白的預兆,吳冠中藝術必然在橫跨油彩和水墨兩塊田園的輪作中,在祖國的原野上,冉冉升起一輪藝術紅太陽。鄒德儂,于天津大學“有無書齋”
2010.12.11
目次
一 嶗山聞道
二 師恩如泉
三 同學同耕
附錄
附錄1 在繪畫實踐中學習“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體會·吳冠中
附錄2 有感于本書的譯出·吳冠中
附錄3 我的美術緣·俞壽賓
附錄4 為現代性而戰斗:吳冠中藝術的第一品格·鄒德儂
圖版資料
參考文獻
後記
書摘/試閱
5月31日,吳師、壽賓、效孟、朱君、李君和我一行6人,擠在廠里派的一輛吉普車內,出發了。幾天來,他始終有疑慮,嶗山是否有東西可畫?我也擔心,會不會因期望過高而虛此一行。
在顛簸的路上,吳先生不斷望著吉普車窗外的景色,在轉過一個山坳時,他突然喊道:“我聞見老虎味兒啦!”我們應聲驚訝地望出去,原來眼前山坡的梯田上,麥子熟了,一道道金色麥秸與一道道褐色田埂,黃、褐相間排列,確實有些“虎皮”的味道。我不由得想起前幾天他曾說,藝術家必須有一雙能發現“美”的眼睛,心中不禁為他精彩的比喻而感慨。
吉普車駛近劈石口,水箱里的水開了鍋,大家就下車休息。吳先生對著山景贊嘆道:“好哇!有氣派!山已完全滿意,就看海了。”車開到返嶺村,我們在選定的駐軍營房落了腳。在安排好吃住後,吳先生滿意地說:“這次畫它一個月,也沒有問題啦!”
午飯後,聽駐軍的連指導員說,“此處至北九水如果徒步翻山,大約只需2小時”,這話立即扯動了我們想與大山親密接觸的神經。當時正是中午時分,大家算來,如果返廠的車把我們帶到北九水,我們再用2個小時徒步翻山,返回營房吃晚飯應該很有把握。我們只顧為進山而興奮了,也沒有理會指導員還說過,“這段山路很難走,山中有狼,前些年還發現過特務在山里發信號彈”。大家迫不及待,登上返廠的吉普車揚長而去。後來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嶗山歷險差點喪命的故事,就此開始了。
我們在這段渺無人煙的大山中迷路,輾轉了8個多小時的經歷,確有許多事情威脅到我們的性命。例如,在沿陡峭的山溝,踏著滾圓、帶青苔的石頭爬行時,一失足就會滾入溝底;在沒膝的草叢中攀爬時,我們的確聽到了蛇在草中游的唰唰聲;如果那天大家真的夜宿山間,遭遇狼群也是很平常的事兒。
但大家艱難攀登的一路,始終有爽朗的說笑聲,伴隨著不斷的大口喘息。我們擔心年近60的吳先生累壞了,吳先生說:“不累,我現在的感覺,像我20歲的時候一樣。”夜幕漸漸降下,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在仍然找不到出路的恐懼中,大家還是相互鼓勁兒,加快腳步,而且還半真半假地相繼呼喊著:“快呀,逃命要緊!”就是在這樣的險峻氛圍里,吳師一邊喘著粗氣,一邊講他和同學泛舟在塞納河上寫生,不料翻船落水,幾乎葬身魚腹的歷險傳奇。他笑著加了一句“當年大難不死,今天也不會有事兒”,給大家壯膽。
第二件有趣的事兒,發生在我們脫險後,借宿旅店擁擠的房間里。我們6人勉強在這間小屋里躺下之後,某君無意中把登山後的汗臭腳丫,伸向了吳先生的鼻尖。我提醒他把腳收回,吳先生說:“不用,不用!我的鼻子聞不見臭味。”我想,吳先生也太能遷就人了,連這事兒還能忍耐。誰知道,他竟然真的沒有嗅覺,并隨之講出,他當年錯把“雪花膏”當成同學自制的白色油彩,獨自在房間內作畫,揮灑得芳香滿屋,而自己卻渾然不覺的一個段子。熄燈前的這個“余興”節目,笑得我們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大隊書記在家里做飯招待我們,炕上、炕前坐滿一屋,炕桌上竟然出現了久違的紅加吉魚。我們膠東人認為,海魚以加吉魚最美,各色加吉以紅色最佳。我們和大隊書記素不相識,以後也很難再度相逢,我們老少6個“落難人”中,連一個當過小組長的芝麻官兒也找不出來,而大隊書記昨晚先讓民兵隊長安排我們住宿,今晨又“高規格”款待我們,還安排我們搭拖拉機趕回駐地,也許就是因為當中有這位北京來的“教圖畫的先生”吧。這樣真誠、樸實、重教、好客的膠東山區民風,今天恐怕難找了。
部隊的營房十分簡陋,我和吳先生同住一問,屋里空空的,只有一張光板兒單人床、一只昏暗的電燈泡和一堆柴草;其余的人住另一間,屋內只有一大堆柴草。沒有被子,從駐軍連部借了幾件軍用棉大衣,我們把帶來的自制油畫板鋪在地上,再加上大衣,連鋪帶蓋就都有了。我們與戰士一起搭伙食,雖沒有特殊照顧,但不限量,部隊的飯菜吃得香甜。大家白天出去畫畫,晚上聚在吳師身旁,斜靠在柴草堆上,聽他講學藝之路,講“美”術之道,罵江青之罪……寂靜山溝里的那些夜晚,我們聽得如醉如癡,飽嘗喜怒哀樂,那才是真正的互動教學。
在“文革”似乎永遠也不會結束的漫漫長夜,在這個獨特的課堂上,我也開始認識作為教師的吳冠中,作為藝術家的吳冠中,作為多難中國知識分子的吳冠中,并且開始注意觀察正在登上快車道的吳冠中藝術。
在中國的藝術界、建筑界,已經把“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結合”,當作褒揚藝術成就的萬能“光榮花”,在我當學生的時候,就熟知贈給藝術家或建筑師及其作品的這個亮麗標志。其實,“東方”與“西方”這類概念過于寬泛,比如,經常說的“東方”,有東亞,還包括印度,甚至地處非洲的埃及也算。所以,用這一概念來談論藝術,很難讓人們得到具體而鮮活的認識。因而簡單地用“東方”和“西方”之間的結合來形容吳冠中藝術的特征,雖然正確,但不清晰。
回想我在接觸吳冠中及其藝術作品的第一個月里,就有許多感性的因素,提示我思考他這個人和他的藝術之中存在著許多個“之間”問題,比如“國畫”和“油畫”之間,中國藝術和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藝術之間,文學和繪畫之間,藝術實踐和藝術理論之間等,而這一切又總是關聯到傳統與現代之間。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這些“之間”里的尋覓、取合、釀造等勞作,日益凸顯出與吳冠中藝術創新的直接因果。
至30余年後的今天,僅吳先生自己寫的相關文字,就足以讓人們清楚而正確地了解吳冠中藝術背後的這一復雜而系統的支持體系。當年我親耳聽到和親眼看到的那些提示性的感性因素,讓我領受著無盡的興味,終身不忘。
吳先生早期棄工學畫,在學畫中又從國畫系轉油畫系的過程,先兆式地預示了他中年之後游走于水墨與油彩之間的那條路。
吳先生說,他很喜歡他的老師潘天壽。先生。在生活中潘先生是位極和善、極隨和的長者,但他的畫作卻很不隨和而極具個性,你根本想象不出,那些作品會是出自這樣一位老先生之手。他還說,如果有潘天壽和齊白石的畫,讓他只能選一張,他會選潘天壽的作品,因為其作品有國際眼光。我也十分喜歡潘天壽的畫,畢業後還特意到北京美術館參觀過潘天壽畫展,寫過體會筆記。潘先生的作品構圖險峻,形式強烈,有時帶有一些抽象元素。所謂國際眼光,我想,可能就是在國畫的范疇內發現和處理抽象元素的眼光吧,從而體現出一些現代藝術的精神,潘先生能當選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有道理。
吳先生留學法國,注定了他要走一條使中國藝術和以法國藝術為代表的“西方”藝術體系結合起來的路。他說,留法的學生帶回來的東西很不相同,一種是古典主義的“寫實”,一種是現代藝術的新觀念,如變形或抽象等等。這些到了中國,也就有了兩類“中西之間結合”,一類是中國畫結合西畫的“寫實”,拓展中國畫的表現力,如徐悲鴻;一類是中國畫結合現代藝術的變形、抽象等全新藝術觀念,如林風眠。徐悲鴻的寫實,與延安的革命藝術,同來自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匯合,形成由官方所支持并排斥其他藝術方向,特別是強力排斥西方現代藝術種種方向的主流藝術。而官方所倡導的“油畫民族化”,是執行這條路線的主體思想。P14-19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