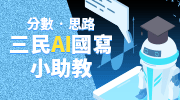燃燒的原野(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胡安‧魯爾福作品
ISBN13:9787544722209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作者:(墨西哥)胡安‧魯爾福
出版日:2020/03/01
裝訂/頁數:精裝/201頁
規格:20.8cm*14.6cm (高/寬)
版次:1
人民幣定價:28 元
定價
:NT$ 168 元優惠價
:
87 折 146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燃燒的原野》是胡安·魯爾福的短篇小說集,這些作品展現了墨西哥的鄉村世界,描寫了1910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後的現實生活,深刻地暴露了其革命的不徹底性。對這本故事集,評論界相當重視,從敘述學、人類學、社會政治等角度切入,把這十幾個故事顛來倒去地解剖把玩。在文學史上,《燃燒的原野》被當成是墨西哥現代文學的開創性作品之一。
作者簡介
作者:(墨)魯爾福
名人/編輯推薦
胡安·魯爾福,墨西哥小說家,被譽為“拉丁美洲新小說的先驅”,一生只留下篇幅極其有限的作品,卻被歷代文豪奉若至寶。出生于墨西哥農村,在孤兒院長大。貧苦的童年并未遮掩他求知的欲望和創作的才華。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便是由自己創辦的刊物《面包》刊發的。
《燃燒的原野》是胡安·魯爾福的短篇小說集,書中收錄的這些作品展現了墨西哥的鄉村世界,描寫了1910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後的現實生活。
《燃燒的原野》是胡安·魯爾福的短篇小說集,書中收錄的這些作品展現了墨西哥的鄉村世界,描寫了1910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後的現實生活。
序
在真正認識胡安·魯爾福(1918—1986)之前,我總記著:墨西哥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佩德羅·巴拉莫,代表作《胡安·魯爾福》。導致我犯下這個錯誤的部分原因在于,除了《佩德羅·巴拉莫》,魯爾福好像沒寫過別的什么東西。無疑,中篇小說《佩德羅·巴拉莫》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被認為是西班牙語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中最優秀的小說之一。在《佩德羅·巴拉莫》之前,魯爾福還出過一部短篇小說集,就是這本《燃燒的原野》;在《佩德羅·巴拉莫》之後,魯爾福基本上就不再發表作品了。
《佩德羅·巴拉莫》的盛譽并不能削弱《燃燒的原野》的魅力。事實上,對這本故事集,評論界也相當重視,從敘述學、人類學、社會政治等角度切入,把這十幾個故事顛來倒去地解剖把玩。在文學史上,它被當成是墨西哥現代文學的開創性作品之一。因為在《燃燒的原野》之前,墨西哥小說基本上還是紀實性的現實主義,全景式記錄現實。到了魯爾福那里,農村生活的主題雖然依舊,但表現手法卻悄然改變了。
米蘭·昆德拉在分析卡夫卡時曾指出,卡夫卡之後,小說開始朝詩的方向改造自己。對于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來說,情節不再是最誘人的部位了。現代人要想看一個精彩故事,與其捧書本,不如去看場電影,或是打開電視看法制節目。小說家努力要做的,是通過故事展現生活的種種可能,探索人的生存困境。主題的意義凸顯,情節的背景黯淡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的確越來越接近詩歌。雖說如此,魯爾福的故事并不缺乏情節性,改編成電影劇本完全是可能的。我想強調的是,論他在這些短篇小說中的藝術造詣,氛圍營造比情節演進更為重要。
這本短篇小說集展現的是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鄉土世界,講的是農民的故事。如果把“詩”和“農村”聯系起來,人們最先想到的也許是田園牧歌,好浪漫,好純真,好環保……但魯爾福筆下的哈利斯科農村,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們能感覺到的,是殘酷、絕望、孤獨、冷漠……而這些東西是以詩意的筆調表述出來的(為免去自夸之嫌,我得加一句:至少小說的西班牙原文是這樣的)。
有評論認為:“這些作品主要描寫1910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後的現實生活,深刻地暴露了其革命的不徹底性。”這話沒錯。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曾指出,比“墨西哥革命”這一提法更確切的提法,是“墨西哥大造反”。通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了解到,參加“革命”的墨西哥農民不是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擁有一套思想理論,“革命”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和他們家人的生活狀況。該書被介紹到中國來時,也曾被譯為《烈火平原》,看上去挺像是一部革命小說。不過,我不認為批判革命是魯爾福的寫作目的。真要那么做的話,他該寫的不是小說,而是《哈利斯科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還有評論認為:“魯爾福關愛貧苦農民。”這話也對。若要研究20世紀墨西哥的三農問題,這些作品可以做很好的材料。但我覺得不能據此認為,關愛農民是魯爾福的寫作目的,真要那么做的話,他就該寫一輩子的鄉土小說。在我看來,魯爾福是想寫一些超越前人的、至少是和前人不一樣的小說。他想在形式上做一些探索。事實證明,他成功了。對比一下《佩德羅·巴拉莫》,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在《佩德羅·巴拉莫》中得到成功運用的現代派技巧,已經在《燃燒的原野》里初露鋒芒。
胡安·魯爾福用不讓我們犯困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墨西哥鄉村世界。說實在的,通過對這本集子的閱讀和翻譯,我覺得我對農民了解得更多了。我的一位墨西哥同事告訴過我,在他看來,墨西哥農民和中國農民是很相像的。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都是階級兄弟,定能互相理解。我隱隱地覺得,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農民,都是相似的。
比如,對土地的依賴。在城市人的眼里,土地只是意味著多少錢一平米或是一個月多少錢的空間。在農民的眼里,土地絕不僅僅意味著財產。土地就是生命。離開了土地,人就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了。在第一個故事《我們分到了地》里,農民們為了土地去鬧革命,革命結束後政府允諾搞土改,給他們分地,當他們哼哧哼哧地跑去看地時,卻發現上當了……農民對土地的訴求,城里人大概是很難深刻理解的。墨西哥農民的土地問題從沒有得到根本上的解決。20世紀末,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奪去土地的恰帕斯州印第安農民重新打起了“薩帕塔”游擊隊的旗號,發起了新的革命。
農民幾乎總是窮苦人。窮苦人的命運幾乎總是殘酷的。在《都是因為我們窮》這個故事里,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殘酷的邏輯:發洪水了,窮人家的牛給水卷走了;牛沒了,窮人家的女兒就嫁不出去了;嫁不出去,就要淪落為風塵女子了。一場自然災害就這樣可以改變一個窮丫頭的命運。在另一個故事里,一個男人受渾身爛瘡的折磨好多年後,要求家人把自己帶到遠方去見聖母贖罪。經過艱難的朝聖之旅後,他懷著被治愈的希望死在路途的終點,而他妻子和他弟弟在帶他去朝聖的途中偷歡,卻又在他死後良心難安,原罪與救贖的主題,在這三個窮苦人之間奇妙地交織在一起。
在農村,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傳統和積習。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中,兩兄弟得知他們的妹妹讓村子里的一個人給糟蹋了,于是,他們不得不去找到那人把他給殺掉。雖然他們不想這么干,但按照風俗,這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就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著去殺人了。家族間的仇殺、復仇,是拉美文學中常見的題材。在魯爾福的短篇小說里,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題材。為什么墨西哥人喜歡復仇?它有沒有社會文化心理上的根源?作家并沒有義務去解釋這些問題。魯爾福所做的,只是把它表現出來,表現得或平白或復雜,表現得或驚心動魄或充滿悲涼。
魯爾福的創作與他的幼年經歷不無關系。在他六歲的時候,其父在一場農民暴動中被人殺害。四年之後,他的母親也去世了,他就被送進一家孤兒院。他的求學經歷也是一路坎坷。在他預備去瓜達拉哈拉大學報到時,學校里正在鬧罷課,他只好轉去墨西哥城。在家鄉修得的學分不足以讓他進入國立自治大學,他便只好在文哲系旁聽藝術史課程。他做過攝影師和銷售代理人,周游全國各地,因此搜集了不少創作素材。魯爾福是從30年代末開始寫作的,先是在《美洲》和《面包》這兩家雜志上發表短篇小說,50年代初,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墨西哥作家中心的資助,才得以在1953年將已發表的七個短篇湊上另外八個故事結集出版,書名為《燃燒的原野》(1970年再版時又加了兩篇,始為今版十七篇)。1955年,他出版了《佩德羅·巴拉莫》,名聲大噪。之後他就沉寂了。關于他沉寂的原因,我所了解到的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出于正直的品性,在意識到自己創作力枯竭後,就主動退出文壇,不愿再給印刷機增添負擔;一說他一不小心寫出《佩德羅·巴拉莫》後,就生活在這部偉大作品的陰影里,不得不靠酗酒來麻痹自己。博爾赫斯曾略帶調侃地揣測說:“埃米莉·狄金生認為出書并不是一個作家命運的基本部分。胡安·魯爾福似乎認同狄金生的這個觀點。”
魯爾福所寫的,用他的同胞、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話來說,是墨西哥最土的東西。筆者所譯的版本是2003年西班牙行星出版社的修訂版。編輯在出版說明中承認,雖然已經參照西班牙語言學院的最新正字法標準對文本作了修正,但還是盡可能地保留了魯爾福文字的特色。因此,破譯一些哈利斯科方言中的特有詞匯,著實讓我費了點勁。魯爾福在創作的時候,是不會像昆德拉那樣老想著我這部作品是會被翻譯成另一種文字的吧?無論如何,最土的東西被詩意地表現出來,成為了可以為全世界讀者接受和欣賞的東西,這是胡安·魯爾福創造的奇跡。
2010年5月于南京
《佩德羅·巴拉莫》的盛譽并不能削弱《燃燒的原野》的魅力。事實上,對這本故事集,評論界也相當重視,從敘述學、人類學、社會政治等角度切入,把這十幾個故事顛來倒去地解剖把玩。在文學史上,它被當成是墨西哥現代文學的開創性作品之一。因為在《燃燒的原野》之前,墨西哥小說基本上還是紀實性的現實主義,全景式記錄現實。到了魯爾福那里,農村生活的主題雖然依舊,但表現手法卻悄然改變了。
米蘭·昆德拉在分析卡夫卡時曾指出,卡夫卡之後,小說開始朝詩的方向改造自己。對于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來說,情節不再是最誘人的部位了。現代人要想看一個精彩故事,與其捧書本,不如去看場電影,或是打開電視看法制節目。小說家努力要做的,是通過故事展現生活的種種可能,探索人的生存困境。主題的意義凸顯,情節的背景黯淡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的確越來越接近詩歌。雖說如此,魯爾福的故事并不缺乏情節性,改編成電影劇本完全是可能的。我想強調的是,論他在這些短篇小說中的藝術造詣,氛圍營造比情節演進更為重要。
這本短篇小說集展現的是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鄉土世界,講的是農民的故事。如果把“詩”和“農村”聯系起來,人們最先想到的也許是田園牧歌,好浪漫,好純真,好環保……但魯爾福筆下的哈利斯科農村,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們能感覺到的,是殘酷、絕望、孤獨、冷漠……而這些東西是以詩意的筆調表述出來的(為免去自夸之嫌,我得加一句:至少小說的西班牙原文是這樣的)。
有評論認為:“這些作品主要描寫1910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後的現實生活,深刻地暴露了其革命的不徹底性。”這話沒錯。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曾指出,比“墨西哥革命”這一提法更確切的提法,是“墨西哥大造反”。通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了解到,參加“革命”的墨西哥農民不是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擁有一套思想理論,“革命”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和他們家人的生活狀況。該書被介紹到中國來時,也曾被譯為《烈火平原》,看上去挺像是一部革命小說。不過,我不認為批判革命是魯爾福的寫作目的。真要那么做的話,他該寫的不是小說,而是《哈利斯科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還有評論認為:“魯爾福關愛貧苦農民。”這話也對。若要研究20世紀墨西哥的三農問題,這些作品可以做很好的材料。但我覺得不能據此認為,關愛農民是魯爾福的寫作目的,真要那么做的話,他就該寫一輩子的鄉土小說。在我看來,魯爾福是想寫一些超越前人的、至少是和前人不一樣的小說。他想在形式上做一些探索。事實證明,他成功了。對比一下《佩德羅·巴拉莫》,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在《佩德羅·巴拉莫》中得到成功運用的現代派技巧,已經在《燃燒的原野》里初露鋒芒。
胡安·魯爾福用不讓我們犯困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墨西哥鄉村世界。說實在的,通過對這本集子的閱讀和翻譯,我覺得我對農民了解得更多了。我的一位墨西哥同事告訴過我,在他看來,墨西哥農民和中國農民是很相像的。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都是階級兄弟,定能互相理解。我隱隱地覺得,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農民,都是相似的。
比如,對土地的依賴。在城市人的眼里,土地只是意味著多少錢一平米或是一個月多少錢的空間。在農民的眼里,土地絕不僅僅意味著財產。土地就是生命。離開了土地,人就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了。在第一個故事《我們分到了地》里,農民們為了土地去鬧革命,革命結束後政府允諾搞土改,給他們分地,當他們哼哧哼哧地跑去看地時,卻發現上當了……農民對土地的訴求,城里人大概是很難深刻理解的。墨西哥農民的土地問題從沒有得到根本上的解決。20世紀末,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奪去土地的恰帕斯州印第安農民重新打起了“薩帕塔”游擊隊的旗號,發起了新的革命。
農民幾乎總是窮苦人。窮苦人的命運幾乎總是殘酷的。在《都是因為我們窮》這個故事里,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殘酷的邏輯:發洪水了,窮人家的牛給水卷走了;牛沒了,窮人家的女兒就嫁不出去了;嫁不出去,就要淪落為風塵女子了。一場自然災害就這樣可以改變一個窮丫頭的命運。在另一個故事里,一個男人受渾身爛瘡的折磨好多年後,要求家人把自己帶到遠方去見聖母贖罪。經過艱難的朝聖之旅後,他懷著被治愈的希望死在路途的終點,而他妻子和他弟弟在帶他去朝聖的途中偷歡,卻又在他死後良心難安,原罪與救贖的主題,在這三個窮苦人之間奇妙地交織在一起。
在農村,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傳統和積習。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中,兩兄弟得知他們的妹妹讓村子里的一個人給糟蹋了,于是,他們不得不去找到那人把他給殺掉。雖然他們不想這么干,但按照風俗,這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就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推動著去殺人了。家族間的仇殺、復仇,是拉美文學中常見的題材。在魯爾福的短篇小說里,我們也能找到類似的題材。為什么墨西哥人喜歡復仇?它有沒有社會文化心理上的根源?作家并沒有義務去解釋這些問題。魯爾福所做的,只是把它表現出來,表現得或平白或復雜,表現得或驚心動魄或充滿悲涼。
魯爾福的創作與他的幼年經歷不無關系。在他六歲的時候,其父在一場農民暴動中被人殺害。四年之後,他的母親也去世了,他就被送進一家孤兒院。他的求學經歷也是一路坎坷。在他預備去瓜達拉哈拉大學報到時,學校里正在鬧罷課,他只好轉去墨西哥城。在家鄉修得的學分不足以讓他進入國立自治大學,他便只好在文哲系旁聽藝術史課程。他做過攝影師和銷售代理人,周游全國各地,因此搜集了不少創作素材。魯爾福是從30年代末開始寫作的,先是在《美洲》和《面包》這兩家雜志上發表短篇小說,50年代初,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墨西哥作家中心的資助,才得以在1953年將已發表的七個短篇湊上另外八個故事結集出版,書名為《燃燒的原野》(1970年再版時又加了兩篇,始為今版十七篇)。1955年,他出版了《佩德羅·巴拉莫》,名聲大噪。之後他就沉寂了。關于他沉寂的原因,我所了解到的有兩種說法。一說他出于正直的品性,在意識到自己創作力枯竭後,就主動退出文壇,不愿再給印刷機增添負擔;一說他一不小心寫出《佩德羅·巴拉莫》後,就生活在這部偉大作品的陰影里,不得不靠酗酒來麻痹自己。博爾赫斯曾略帶調侃地揣測說:“埃米莉·狄金生認為出書并不是一個作家命運的基本部分。胡安·魯爾福似乎認同狄金生的這個觀點。”
魯爾福所寫的,用他的同胞、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話來說,是墨西哥最土的東西。筆者所譯的版本是2003年西班牙行星出版社的修訂版。編輯在出版說明中承認,雖然已經參照西班牙語言學院的最新正字法標準對文本作了修正,但還是盡可能地保留了魯爾福文字的特色。因此,破譯一些哈利斯科方言中的特有詞匯,著實讓我費了點勁。魯爾福在創作的時候,是不會像昆德拉那樣老想著我這部作品是會被翻譯成另一種文字的吧?無論如何,最土的東西被詩意地表現出來,成為了可以為全世界讀者接受和欣賞的東西,這是胡安·魯爾福創造的奇跡。
2010年5月于南京
目次
清晨
那個夜晚,他掉隊了
我們分到了地
科馬德雷斯坡
都是因為我們窮
那個人
塔爾葩
馬卡里奧
燃燒的原野
求他們別殺我
盧維納
北渡口
你還記得吧
你聽不到狗叫
地震的那天
瑪蒂爾德·阿爾坎赫爾的遺產
安納克萊托·莫羅內斯
那個夜晚,他掉隊了
我們分到了地
科馬德雷斯坡
都是因為我們窮
那個人
塔爾葩
馬卡里奧
燃燒的原野
求他們別殺我
盧維納
北渡口
你還記得吧
你聽不到狗叫
地震的那天
瑪蒂爾德·阿爾坎赫爾的遺產
安納克萊托·莫羅內斯
書摘/試閱
聖加夫列爾從濃霧中冒了出來,為晨露潤濕。夜里,云霧要尋找人的熱氣,就在村子上頭過了一宿。現在,太陽快要出來了,這濃霧便慢慢地爬起身,卷起它的床單來,在屋頂上留下一道道白花花的紋路。一團灰色的水汽,隱約可見,從濕漉漉的地面和樹叢間升起,給云朵吸引過去,卻在一瞬問遁影無蹤。接著出現的就是一縷縷黑糊糊的炊煙,聞起來是橡木燃燒的味道,將黑灰漫灑在整個天空。
遠方的群山仍隱沒在陰影里。
一只燕子飛過街道,接著響起了第一聲晨鐘。
一家家的燈火熄滅了。一團土灰色的煙霧將整個村子籠罩起來。村子在晨曦里又酣睡了一會兒。
老埃斯特萬騎在一頭奶牛的背上,趕著牛群,行進在通往希基爾潘的兩旁長著無花果樹的道路上。他跳上牛背,為的是躲開直往臉上撲的蚱蜢。他拿帽子驅趕著飛蚊,時不時用他那掉光了牙的嘴巴盡力吹響口哨,讓那些牛兒不要落在後頭。牛兒們一路嚼著草,讓青草上的露珠沾濕了身子。天漸漸地亮起來。他聽到在聖加夫列爾響起的晨鐘聲,就趕忙從牛背上下來,跪在地上,伸開雙臂畫著十字。
一只貓頭鷹在樹問發出怪叫,他趕忙重新跳上牛背,脫下襯衣,讓風兒吹走他的驚懼,然後繼續行路。
“一,二,十……”牛群通過村口的攔畜坑時,他數著牛的數目。他抓住其中一頭牛的耳朵讓它停下腳步,扯著它的鼻子對它說:“禿頭啊,現在你要和你的小犢子分開啦。你想哭就哭吧,這可是能見著你的小牛犢的最後一天啦。”母牛望望他,眼神平靜,又甩動尾巴拍拍他,然後向前走去。
現在敲響的是最後一聲晨鐘。
這些燕子不知是從希基爾潘還是從聖加夫列爾飛來的;只見它們來來去去,在空中盤旋著,不時掠過地上的泥水坑,將胸口潤濕;一些燕子嘴里叼著東西,用尾羽粘點爛泥然後就離開大路遠去了,消失在灰暗的天際。
云朵已經飄到群山之間,遠遠望去,倒像是那些青山的裙子上綴著的灰色補丁。
老埃斯特萬向天空中疾速飄過的五彩云條抬眼望去:有紅色的、橙色的、黃色的。群星正在慢慢地變成白色。最後的幾點星光熄滅了,太陽整個地噴了出來,在草尖上灑下一顆顆水晶股的露珠。
“我的肚臍眼一直露在外面,陣陣發寒。我也記不得為啥會那樣。我到了畜欄門口,沒人給我開門。我拿起塊石頭敲門,把石頭都砸裂了,還是沒有人出來。那會兒我只當是我的老爺堂胡斯托還在睡大覺呢。我跟那些奶牛啥也沒說,啥也沒解釋,我就自個兒走開了,不讓它們瞧見,免得它們跑來跟著我。我摸到籬笆矮點兒的地方,翻到另一邊,落在一群小牛犢里頭了。我正在把畜欄門閂抽出來的時候,看見堂胡斯托老爺從閣樓那邊下來,把熟睡的瑪嘉麗塔姑娘抱在他懷里,一路穿過畜欄,沒有發現我。我蜷著身子貼著墻,躲得好好的,他肯定沒見著我。至少當時我是那么想的。”
老埃斯特萬一邊讓奶牛一頭一頭地進了欄,一邊擠著奶。最後是那頭要和小牛犢分開的母牛,一直在不停地哞哞叫,老埃斯特萬心生憐憫,也讓它進去了。“最後一次啦,”他對母牛說,“看看它,舔舔它吧。再看看吧,好比它快要死啦。你就要生了,還跟這個長不大的東西親熱。”他又對牛犢說:“再嘗幾口吧,這些奶頭現在不是你的啦;你準會發現,這奶好鮮,鮮得像是喂新生兒吃的。”可他看到它同時吸著四個奶頭時,便踢了它幾腳。“你這牛犢子,看我砸爛你的嘴。”P1-3
遠方的群山仍隱沒在陰影里。
一只燕子飛過街道,接著響起了第一聲晨鐘。
一家家的燈火熄滅了。一團土灰色的煙霧將整個村子籠罩起來。村子在晨曦里又酣睡了一會兒。
老埃斯特萬騎在一頭奶牛的背上,趕著牛群,行進在通往希基爾潘的兩旁長著無花果樹的道路上。他跳上牛背,為的是躲開直往臉上撲的蚱蜢。他拿帽子驅趕著飛蚊,時不時用他那掉光了牙的嘴巴盡力吹響口哨,讓那些牛兒不要落在後頭。牛兒們一路嚼著草,讓青草上的露珠沾濕了身子。天漸漸地亮起來。他聽到在聖加夫列爾響起的晨鐘聲,就趕忙從牛背上下來,跪在地上,伸開雙臂畫著十字。
一只貓頭鷹在樹問發出怪叫,他趕忙重新跳上牛背,脫下襯衣,讓風兒吹走他的驚懼,然後繼續行路。
“一,二,十……”牛群通過村口的攔畜坑時,他數著牛的數目。他抓住其中一頭牛的耳朵讓它停下腳步,扯著它的鼻子對它說:“禿頭啊,現在你要和你的小犢子分開啦。你想哭就哭吧,這可是能見著你的小牛犢的最後一天啦。”母牛望望他,眼神平靜,又甩動尾巴拍拍他,然後向前走去。
現在敲響的是最後一聲晨鐘。
這些燕子不知是從希基爾潘還是從聖加夫列爾飛來的;只見它們來來去去,在空中盤旋著,不時掠過地上的泥水坑,將胸口潤濕;一些燕子嘴里叼著東西,用尾羽粘點爛泥然後就離開大路遠去了,消失在灰暗的天際。
云朵已經飄到群山之間,遠遠望去,倒像是那些青山的裙子上綴著的灰色補丁。
老埃斯特萬向天空中疾速飄過的五彩云條抬眼望去:有紅色的、橙色的、黃色的。群星正在慢慢地變成白色。最後的幾點星光熄滅了,太陽整個地噴了出來,在草尖上灑下一顆顆水晶股的露珠。
“我的肚臍眼一直露在外面,陣陣發寒。我也記不得為啥會那樣。我到了畜欄門口,沒人給我開門。我拿起塊石頭敲門,把石頭都砸裂了,還是沒有人出來。那會兒我只當是我的老爺堂胡斯托還在睡大覺呢。我跟那些奶牛啥也沒說,啥也沒解釋,我就自個兒走開了,不讓它們瞧見,免得它們跑來跟著我。我摸到籬笆矮點兒的地方,翻到另一邊,落在一群小牛犢里頭了。我正在把畜欄門閂抽出來的時候,看見堂胡斯托老爺從閣樓那邊下來,把熟睡的瑪嘉麗塔姑娘抱在他懷里,一路穿過畜欄,沒有發現我。我蜷著身子貼著墻,躲得好好的,他肯定沒見著我。至少當時我是那么想的。”
老埃斯特萬一邊讓奶牛一頭一頭地進了欄,一邊擠著奶。最後是那頭要和小牛犢分開的母牛,一直在不停地哞哞叫,老埃斯特萬心生憐憫,也讓它進去了。“最後一次啦,”他對母牛說,“看看它,舔舔它吧。再看看吧,好比它快要死啦。你就要生了,還跟這個長不大的東西親熱。”他又對牛犢說:“再嘗幾口吧,這些奶頭現在不是你的啦;你準會發現,這奶好鮮,鮮得像是喂新生兒吃的。”可他看到它同時吸著四個奶頭時,便踢了它幾腳。“你這牛犢子,看我砸爛你的嘴。”P1-3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