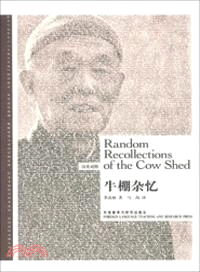牛棚雜憶(漢英對照)(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13527347
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作者:季羨林
出版日:2013/02/04
裝訂/頁數:平裝/391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商品簡介
《牛棚雜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本回憶錄,作者希望總結教訓,喚醒更多人對歷史的反思,讓更多知情者出來說話,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作者簡介
季羨林(1911—2009),語言學家,翻譯家,作家。字希逋、齊奘,山東臨清人。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4年畢業,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1946年回國后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先后榮膺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中國南亞學會、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中國語言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亞非學會等多個學會的會長。一生致力于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在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上頗多建樹,成為我國當代學貫中西、聲望卓著的大師。
名人/編輯推薦
《牛棚雜憶(漢英對照)》作者希望總結教訓,喚醒更多人對歷史的反思,讓更多知情者出來說話,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序
《牛棚雜憶》寫于1992年,為什么時隔六年,到了現在1998年才拿出來出版。這有點違反了寫書的常規。讀者會懷疑,其中必有個說法。
讀者的懷疑是對的,其中確有一個說法,而這個說法并不神秘,它僅僅出于個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點私心而已。我本來已經被“革命”小將——其實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極泰來,人間正道,浩劫一過,我不但翻身起來,而且飛黃騰達,“官”運亨通,頗讓一些痛打過我,折磨過我的小將們膽戰心驚。如果我真想報復的話,我會有一千種手段,得心應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進行報復的。
可是我并沒有這樣做,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打擊,報復,穿小鞋,耍大棒。難道我是一個了不起的寬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嗎?否,否,決不是的。我有愛,有恨,會妒忌,想報復,我的寬容心腸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動報復之念,我立即想到,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種氣氛中,每個人,不管他是哪一個山頭,哪一個派別,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異化為非人。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然后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我這里所謂“非人”,決不是指畜生,只稱他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我焉敢苛求于別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這些想法,我才沒有進行報復。
但是,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這還不是一切,還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們都知道,當年打派仗的時候,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企業,甚至某一些部隊,都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現在看起來兩派都搞打、砸、搶,甚至殺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誰也不比誰強。現在再來討論或者辯論誰是誰非,實在毫無意義。可是在當時,有一種叫做“派性”的東西,摸不著,看不見,既無根據,又無理由,卻是陰狠、毒辣,一點理性也沒有。誰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樣,一個原來是親愛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屬兩派,則夫婦離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鬩于墻”,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讀書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書中還從未發現過這種心理狀況,實在很值得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認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嚴重。但是,我自己認為,我的派性來之不易,是拼著性命換來的。運動一開始,作為一系之主,我是沒有資格同“革命群眾”一起參加鬧革命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呼聲響徹神州大地,與我卻無任何正面的關系,最初我是處在“革命”和“造反”的對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厭惡政治,同國民黨沒有任何沾連。大罪名加不到我頭上來。被打成“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應有之義,不可避免的。這兩陣狂風一過,我又恢復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跡于革命群眾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犟勁,我敢于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么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犟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犟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熱的“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哆用長矛刺殺校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o“老佛爺”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幾乎把自己一條老命賠上。詳情書中都有敘述,我在這里就不再噦嗦了。
不加入一派則已,一旦加入,則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纏得緊緊的,說話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過,天日重明;但是,人們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濃或淡的痕跡,稍不留意,就會顯露出來。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對立面,批斗過我,誣蔑過我,審訊過我,踢打過我。他們中的許多人好像有點愧悔之意。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里面藏著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后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后打擊報復。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號入座,易如反掌。懷著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么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
那么,你為什么干脆不寫這樣一部書呢?這話問得對,問得正中要害。
實際上,我最初確實沒有寫這樣一部書的打算。否則,十年浩劫正式結束于1976年,我的書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寫,中間隔了這樣許多年,所為何來?這16年是我反思、觀察、困惑、期待的期間。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條蠢驢,對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殘暴、混亂、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蒙羞忍恥、把我們國家的經濟推向絕境、空前、絕后——這是我的希望——,至今還沒人能給一個全面合理的解釋的悲劇,有不少人早就認識了它的實質,我卻是在“四人幫”垮臺以后腦筋才開了竅。我實在感到羞恥。
我的腦筋一旦開了竅,我就感到當事人處理這一場災難的方式有問題。粗一點比細一點好,此話未必毫無道理。但是,我認為,我們粗過了頭。我在上面已經說到,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應該在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中受到足夠的教訓,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轍。這樣的機會恐個白以后再難碰到了。何況在那些打砸搶分子中,確有一些禽獸不如的壞人。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顏色。有的偽裝成正人君子,有的變為某將軍、某領導的東床快婿,在這一張大傘下躲避了起來。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縱橫捭闔的伎倆,暫時韜晦,窺探時機,有朝一日風雷動,他們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點子多,深通厚黑之學,擅長拍馬之術。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在的癌細胞,遲早必將擴張的。我們當時放過了這些人,實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懷疑,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總起來看,是安定團結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會上道德水平有問題,許多地方的政府中風氣不正,有不少人素質不高,若仔細追蹤其根源,恐個白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關,同上面提到的這些人有關。
上面是我反思和觀察的結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著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了出來。一些元帥、許多老將軍,出生入死,戎馬半生,可以說是為人民立了功。一些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絕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大都是勤奮工作,赤誠護黨。所有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潑了一身污水,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國古來有“飛烏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說法。但干這種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們卻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里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里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干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么可卟自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們大概認為我在說謊,我在談海上蓬萊三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皮膚,只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此外,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對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而說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么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這一類人現在已經四五十歲了,有的官據要津。即使別人不找他們算賬,他們自己如果還有點良心,有點理智的話,在燈紅酒綠之余,清夜捫心自問,你能夠睡得安穩嗎?如果這一類人——據估算,人數是不老少的——也寫點什么東西的話,拿來與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寫的東西對照一讀,對我們人民的教育意義,特別是我們后世子孫的教育意義,會是極大極大的。我并不要求他們檢討和懺悔,這些都不是本質的東西,我只期待他們秉筆直書。這樣做,他們可以說是為我們民族立了大功,只會得到褒揚,不會受到譴責,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就這樣,我懷著對兩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東方太陽出來了,然而我的期待卻落了空。
可是,時間已經到了1992年。許多當年被迫害的人已經如深秋的樹葉,漸趨凋零;因為這一批人年紀老的多,宇宙間生生死死的規律是無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說:“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壽幾何兩個期待中,其中一個我無能為力,而對另一個,也就是對被迫害者的那一個,我卻是大有可為的。我自己就是一個被害者嘛。我為什么競傻到守株待兔專期待別人行動而自己卻不肯動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還是讓我自己來吧。這就是<牛棚雜憶>的產生經過。我寫文章從來不說謊話,我現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希望對讀者會有點幫助。但是,我雖然自己已經實現了一個期待,對別人的那兩個期待,我還并沒有放棄。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寫了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夠實現。
1998年3月9日
讀者的懷疑是對的,其中確有一個說法,而這個說法并不神秘,它僅僅出于個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點私心而已。我本來已經被“革命”小將——其實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極泰來,人間正道,浩劫一過,我不但翻身起來,而且飛黃騰達,“官”運亨通,頗讓一些痛打過我,折磨過我的小將們膽戰心驚。如果我真想報復的話,我會有一千種手段,得心應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進行報復的。
可是我并沒有這樣做,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打擊,報復,穿小鞋,耍大棒。難道我是一個了不起的寬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嗎?否,否,決不是的。我有愛,有恨,會妒忌,想報復,我的寬容心腸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動報復之念,我立即想到,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種氣氛中,每個人,不管他是哪一個山頭,哪一個派別,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異化為非人。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然后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我這里所謂“非人”,決不是指畜生,只稱他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我焉敢苛求于別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這些想法,我才沒有進行報復。
但是,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這還不是一切,還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們都知道,當年打派仗的時候,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企業,甚至某一些部隊,都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現在看起來兩派都搞打、砸、搶,甚至殺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誰也不比誰強。現在再來討論或者辯論誰是誰非,實在毫無意義。可是在當時,有一種叫做“派性”的東西,摸不著,看不見,既無根據,又無理由,卻是陰狠、毒辣,一點理性也沒有。誰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樣,一個原來是親愛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屬兩派,則夫婦離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鬩于墻”,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讀書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書中還從未發現過這種心理狀況,實在很值得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認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嚴重。但是,我自己認為,我的派性來之不易,是拼著性命換來的。運動一開始,作為一系之主,我是沒有資格同“革命群眾”一起參加鬧革命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呼聲響徹神州大地,與我卻無任何正面的關系,最初我是處在“革命”和“造反”的對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厭惡政治,同國民黨沒有任何沾連。大罪名加不到我頭上來。被打成“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應有之義,不可避免的。這兩陣狂風一過,我又恢復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跡于革命群眾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犟勁,我敢于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么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犟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犟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熱的“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哆用長矛刺殺校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o“老佛爺”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幾乎把自己一條老命賠上。詳情書中都有敘述,我在這里就不再噦嗦了。
不加入一派則已,一旦加入,則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纏得緊緊的,說話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過,天日重明;但是,人們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濃或淡的痕跡,稍不留意,就會顯露出來。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對立面,批斗過我,誣蔑過我,審訊過我,踢打過我。他們中的許多人好像有點愧悔之意。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里面藏著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后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后打擊報復。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號入座,易如反掌。懷著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么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
那么,你為什么干脆不寫這樣一部書呢?這話問得對,問得正中要害。
實際上,我最初確實沒有寫這樣一部書的打算。否則,十年浩劫正式結束于1976年,我的書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寫,中間隔了這樣許多年,所為何來?這16年是我反思、觀察、困惑、期待的期間。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條蠢驢,對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殘暴、混亂、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蒙羞忍恥、把我們國家的經濟推向絕境、空前、絕后——這是我的希望——,至今還沒人能給一個全面合理的解釋的悲劇,有不少人早就認識了它的實質,我卻是在“四人幫”垮臺以后腦筋才開了竅。我實在感到羞恥。
我的腦筋一旦開了竅,我就感到當事人處理這一場災難的方式有問題。粗一點比細一點好,此話未必毫無道理。但是,我認為,我們粗過了頭。我在上面已經說到,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應該在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中受到足夠的教訓,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轍。這樣的機會恐個白以后再難碰到了。何況在那些打砸搶分子中,確有一些禽獸不如的壞人。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顏色。有的偽裝成正人君子,有的變為某將軍、某領導的東床快婿,在這一張大傘下躲避了起來。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縱橫捭闔的伎倆,暫時韜晦,窺探時機,有朝一日風雷動,他們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點子多,深通厚黑之學,擅長拍馬之術。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在的癌細胞,遲早必將擴張的。我們當時放過了這些人,實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懷疑,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總起來看,是安定團結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會上道德水平有問題,許多地方的政府中風氣不正,有不少人素質不高,若仔細追蹤其根源,恐個白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關,同上面提到的這些人有關。
上面是我反思和觀察的結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著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了出來。一些元帥、許多老將軍,出生入死,戎馬半生,可以說是為人民立了功。一些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絕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大都是勤奮工作,赤誠護黨。所有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潑了一身污水,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國古來有“飛烏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說法。但干這種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們卻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里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里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干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么可卟自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們大概認為我在說謊,我在談海上蓬萊三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皮膚,只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此外,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對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而說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么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這一類人現在已經四五十歲了,有的官據要津。即使別人不找他們算賬,他們自己如果還有點良心,有點理智的話,在燈紅酒綠之余,清夜捫心自問,你能夠睡得安穩嗎?如果這一類人——據估算,人數是不老少的——也寫點什么東西的話,拿來與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寫的東西對照一讀,對我們人民的教育意義,特別是我們后世子孫的教育意義,會是極大極大的。我并不要求他們檢討和懺悔,這些都不是本質的東西,我只期待他們秉筆直書。這樣做,他們可以說是為我們民族立了大功,只會得到褒揚,不會受到譴責,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就這樣,我懷著對兩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東方太陽出來了,然而我的期待卻落了空。
可是,時間已經到了1992年。許多當年被迫害的人已經如深秋的樹葉,漸趨凋零;因為這一批人年紀老的多,宇宙間生生死死的規律是無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說:“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壽幾何兩個期待中,其中一個我無能為力,而對另一個,也就是對被迫害者的那一個,我卻是大有可為的。我自己就是一個被害者嘛。我為什么競傻到守株待兔專期待別人行動而自己卻不肯動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還是讓我自己來吧。這就是<牛棚雜憶>的產生經過。我寫文章從來不說謊話,我現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希望對讀者會有點幫助。但是,我雖然自己已經實現了一個期待,對別人的那兩個期待,我還并沒有放棄。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寫了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夠實現。
1998年3月9日
目次
三版自序
再版自序
抄書代序
壹我最尊敬體貼她們
貳我的擇偶條件
叁我的母親
肆我的教師
伍叫我老頭子的弟婦
陸請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婦
柒使我心疼頭痛的弟婦
捌我的奶娘
玖我的同班
拾我的同學
拾壹我的朋友的太太
拾貳我的學生
拾叁我的房東
拾肆我的鄰居
拾伍張嫂
拾陸我的朋友的母親
后記
再版自序
抄書代序
壹我最尊敬體貼她們
貳我的擇偶條件
叁我的母親
肆我的教師
伍叫我老頭子的弟婦
陸請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婦
柒使我心疼頭痛的弟婦
捌我的奶娘
玖我的同班
拾我的同學
拾壹我的朋友的太太
拾貳我的學生
拾叁我的房東
拾肆我的鄰居
拾伍張嫂
拾陸我的朋友的母親
后記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