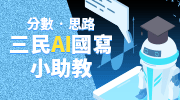草原文學:中篇小說卷(下)(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06370820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優秀蒙古文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工程組委會 編著
出版日:2013/10/01
裝訂:平裝
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中篇小說卷·下》收入《巖 嘯》《蒙古貞阿爸》《森林的嘆息》《中年萬歲》《老人與戈壁》五個中篇。這些小說秉承現實主義精神,敘述豐茂淳樸,多元地表現了蒙古族濃郁而獨特的風貌情調,且頗具當代性。尤其是《巖嘯》和《森林的嘆息》兩篇,前者不只是人虎之間的一段傳奇故事,亦寄托了作者對人性和社會關系的復雜性的深刻反思,就此而言更像一個寓言;后者對現實的批判鋒芒畢露且入木三分,表現出了極大思想和道德的勇氣;而作為二者共同背景的,則是一個民族在生命本體意義上與自然的血脈相通、不可分割。《老人與戈壁》在結構上突破了線性敘述和平面展開的窠臼,更多引入了蒙太奇式的跳躍和刻畫手法,以突出局部的質感和感染力,體現了(民族)傳統敘述向現代性敞開的新的可能。
名人/編輯推薦
優秀蒙古文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工程組委會編著的《中篇小說卷(下)》收入《巖嘯》《蒙兀兒斤大伯》《森林的嘆息》《中年萬歲》《老人與戈壁》五個中篇。本書所收五個中篇小說,展現了濃郁而獨特的蒙古族風貌情調,涉及馬、狗、摔跤、狩獵等草原民族生活中的核心元素。描摹一個民族在生命本體意義上與自然的血脈相通,昭示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我之間最直捷的交流路徑。
序
致讀者
《草原文學重點作品創作工程》和《優秀蒙古文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開始和讀者見面了。這是值得加以慶賀的事情。因為,這一工程不僅是對文學創作的內蒙古擔當,更是對文學內容建設的草原奉獻!
在那遠古荒蠻的曾經年代里,不知如何稱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國北方的大地山林間穿梭奔跑,維持著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們繁衍起來并開始有專屬各自的族稱,然后被人類發展的普遍規律所驅使著,一個接一個地走出山林過起了遷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變成了這些民族人群書寫盛衰成敗的出發地。揮舞著戰刀和馬鞭,匈奴人第一個出發了,緊接著鮮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踏著前人的足跡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如今,回首望去,他們奔騰而去的背影猶如一隊隊雁陣,穿過歷史的天空漸漸遠去……
雁陣飛去,為的是回到溫暖舒適的過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續地奔騰前去,為的卻是要與人類歷史的發展潮流融匯對接。
這是一個壯觀的遷徙,時間從已知的公元前直到當今年代。雖然形式不同,內容也有所變化,但這種遷徙依然不停地進行著。歲月的塵埃一層又一層,遷徙的腳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經歷過滄桑的草原充滿了關于他們的記憶。在草原的這個記憶中,有他們從蠻荒走向開化的跋涉經歷;有他們從部落成長為民族的自豪情懷;有他們建立政權、制定制度、踐行管理的豐富經歷;有他們敬畏自然、順應規律,按照草原大地顯示給他們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們按著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態創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聲歌唱、飲酒狂歡,豁達樂觀而不失細膩典雅的風俗習慣;有他們擔當使命,不畏犧牲,奮力完成中國版圖的大統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間的無障礙對接的鏗鏘足跡;更有他們隨著歷史的發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內容的一次次轉型與中原民族相識、相知,共同推進民族融合、一體認知,攜手同步的歷史體驗;還有他們帶著千古草原的生存經驗,與古老祖國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運,共同創造中華文化燦爛篇章的不朽奉獻……
承載著這些厚重而鮮活的記憶,草原唱著歌,跳著舞,夏天開著花,冬天飄著雪,一年又一年地走進了人類歷史的二十一世紀。
隨著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節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異的時候,我們在它從容的腳步下發現了如土厚重的這些記憶。于是,我們如開采珍貴的礦藏,輕輕掀去它上面的碎石雜草,拿起心靈的放大鏡、顯微鏡以及各種分析儀,研究它積累千年的內容和意義。
經過細心的研究,我們終于發現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還有它留給往時歲月的悲壯憂傷的英雄主義遺風!這樣,當世人以文化為各自形象,與世界握手相見時,內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號——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內容,而文學就是為這一需求提供產品的心靈勞作。因有赤橙黃綠青藍紫,世界才會光彩奪目。文學也是應該這樣。所以,我們大力倡導內蒙古的作家們創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內涵、草原文化特點、草原文化氣派”的優秀作品,以饗天下讀者,并將其作為自治區重大的文學工程加以推動。如今,這一工程開始結果了,并將陸續結出新的果實落向讀者大眾之手。
在此,真誠地祝福這項工程的作品帶著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風的清爽和鳥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遠!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烏蘭
《草原文學重點作品創作工程》和《優秀蒙古文文學作品翻譯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開始和讀者見面了。這是值得加以慶賀的事情。因為,這一工程不僅是對文學創作的內蒙古擔當,更是對文學內容建設的草原奉獻!
在那遠古荒蠻的曾經年代里,不知如何稱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國北方的大地山林間穿梭奔跑,維持著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們繁衍起來并開始有專屬各自的族稱,然后被人類發展的普遍規律所驅使著,一個接一個地走出山林過起了遷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變成了這些民族人群書寫盛衰成敗的出發地。揮舞著戰刀和馬鞭,匈奴人第一個出發了,緊接著鮮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踏著前人的足跡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如今,回首望去,他們奔騰而去的背影猶如一隊隊雁陣,穿過歷史的天空漸漸遠去……
雁陣飛去,為的是回到溫暖舒適的過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續地奔騰前去,為的卻是要與人類歷史的發展潮流融匯對接。
這是一個壯觀的遷徙,時間從已知的公元前直到當今年代。雖然形式不同,內容也有所變化,但這種遷徙依然不停地進行著。歲月的塵埃一層又一層,遷徙的腳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經歷過滄桑的草原充滿了關于他們的記憶。在草原的這個記憶中,有他們從蠻荒走向開化的跋涉經歷;有他們從部落成長為民族的自豪情懷;有他們建立政權、制定制度、踐行管理的豐富經歷;有他們敬畏自然、順應規律,按照草原大地顯示給他們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們按著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態創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聲歌唱、飲酒狂歡,豁達樂觀而不失細膩典雅的風俗習慣;有他們擔當使命,不畏犧牲,奮力完成中國版圖的大統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間的無障礙對接的鏗鏘足跡;更有他們隨著歷史的發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內容的一次次轉型與中原民族相識、相知,共同推進民族融合、一體認知,攜手同步的歷史體驗;還有他們帶著千古草原的生存經驗,與古老祖國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運,共同創造中華文化燦爛篇章的不朽奉獻……
承載著這些厚重而鮮活的記憶,草原唱著歌,跳著舞,夏天開著花,冬天飄著雪,一年又一年地走進了人類歷史的二十一世紀。
隨著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節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異的時候,我們在它從容的腳步下發現了如土厚重的這些記憶。于是,我們如開采珍貴的礦藏,輕輕掀去它上面的碎石雜草,拿起心靈的放大鏡、顯微鏡以及各種分析儀,研究它積累千年的內容和意義。
經過細心的研究,我們終于發現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還有它留給往時歲月的悲壯憂傷的英雄主義遺風!這樣,當世人以文化為各自形象,與世界握手相見時,內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號——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內容,而文學就是為這一需求提供產品的心靈勞作。因有赤橙黃綠青藍紫,世界才會光彩奪目。文學也是應該這樣。所以,我們大力倡導內蒙古的作家們創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內涵、草原文化特點、草原文化氣派”的優秀作品,以饗天下讀者,并將其作為自治區重大的文學工程加以推動。如今,這一工程開始結果了,并將陸續結出新的果實落向讀者大眾之手。
在此,真誠地祝福這項工程的作品帶著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風的清爽和鳥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遠!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烏蘭
目次
巖 嘯 【001】
嘎·希儒嘉措 著 白·呼和牧奇 譯
蒙兀兒斤大伯 【095】
巴·格日勒圖 著 席·照日格圖 譯
森林的嘆息 【169】
巴布 著 照日格圖 譯
老人與戈壁 【229】
阿尤爾扎納 著 照日格圖 譯
中年萬歲 【285】
賽音巴雅爾(已故)著 照日格圖 譯
嘎·希儒嘉措 著 白·呼和牧奇 譯
蒙兀兒斤大伯 【095】
巴·格日勒圖 著 席·照日格圖 譯
森林的嘆息 【169】
巴布 著 照日格圖 譯
老人與戈壁 【229】
阿尤爾扎納 著 照日格圖 譯
中年萬歲 【285】
賽音巴雅爾(已故)著 照日格圖 譯
書摘/試閱
巖 嘯
一
孟夏正午的驕陽當空炙烤,夏營地油綠的草場上牛羊攢堆停歇。
“爸爸,這個小木匣子放哪兒?”南斯樂瑪在收拾房屋之前指著用包袱包裹的黑色小木匣子問海姆楚格。幫助父親從牛車上卸下六個哈那①的蒙古包搭建起來,往里面搬運家什,前后忙活很是疲憊,但她臉上卻洋溢著喜悅之色。從做姑娘時起就早已習慣了遷徙搬家之事,已沒有什么新鮮感可言。但是,做了媳婦后的第一次夏營盤搬遷,讓她感到格外的心曠神怡。用手掌擦拭滲于額頭的汗水,向后籠絡梳理耷拉在臉上的秀發,朝父親矜持地微笑時,麗眸里閃耀著可人的靈光,顯示著鄉下草原不多見的美貌少婦的風韻。
端坐在蒙古包中央打點火撐子②的海姆楚格聽到兒媳的話后欠了欠身,看著她不停地里外忙活,投去疼愛的恩慈目光,他說:
“喏,孩子啊,把那遞給我,爸爸收拾吧。”他小心翼翼地接過南斯樂瑪遞給他的粗布包裹的小木匣子,轉身朝向了西北方向的哈那腳。
海姆楚格是個何時都不會發怒煩躁、不說生硬嗆人話語的人,他心善仁慈、溫和謹慎、寬容厚道。現已年過六旬沒齒皓首,作為他一生經歷生活的坎坷蹉跎的印證,滿臉刻下縱橫交錯的褶皺。同時,他暗自總感到身體有些不適的征兆,曾經膀大腰圓的身體日漸消瘦,近來更是眼窩凹陷,面部憔悴,只有鼻梁顯得愈加凸出了。在偏遠的鄉下,年邁的人總是把這種突如其來的不適狀態歸結于年齡,幾乎沒有人懷疑其為疾病,很少有人去問醫就診。但是,海姆楚格自己卻清楚地知道這個每況愈下的狀況的緣由。那是二十年前,他守護著絕氣的妻子,自己卻失神摔倒后,心里落下殘疾,幾經治療也沒有除根,殘留成了病魔。老漢清醒地感悟到這個背后有來頭的東西肯定會糾纏住他的生命不放。他也沒讓兒子和兒媳知道這件事。因為他向來就是個心氣堅強的人,所以,咬著牙抵御著病魔的逼迫和折磨。疼痛像潮水一樣涌來的時候,讓他死去活來,退去的時候卻如同抽絲一樣釋然。這個東西給了老漢二十年的暗示,不定哪天就把兒子遺孤于世,這讓他擔驚受怕到現在。但是,僥幸沒有發生什么意外。現在老漢更沒有什么可怕的了。兒子如今長大成人,老朽身軀成為多余也是自然之理。然而,只有一件東西讓他留戀糾結著現在的生活。那就是那個從未撒手、悉心看護到如今的小木匣子。為此他感到非常遺憾和揪心。
“爸爸,我去泉眼打水回來熬茶。您的臉色很不好看,先躺一會兒吧。剩下的活兒等他回來再說吧。”媳婦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一樣說著,她在包里的主座上鋪開生牛皮,攤開納線毛氈①,提著水桶出去了。
“心地善良的好女兒啊。可憐的孩子,阿尤樂貴是個給你幫前忙后的那種人嗎……”老漢隨其身后自言自語著長嘆了一口氣。他沒有按照媳婦的囑咐躺下歇息,起來在哈那腳的西北角挖了個小坑,用防潮塑料布包裹好那個小木匣子放在里面,上面擱上了木板子。接著,他把搬進來的四方木頭柜子置放在上面,將容納圣人雕塑的佛龕擺放在柜子的正中央,點起了線香和長明燈,清理整肅了衣帽后跪下,合掌祈禱道:
“列祖列宗,宇宙上蒼,山神地祇,請求保佑。請賜給我們頭上沒有災禍侵襲,腳下沒有苦難遭遇的國泰民安的盛世吧!”這是海姆楚格每次搬遷搭營后,必須首先虔誠地完成的一項既定的禮儀。然而,他信奉膜拜的不是喇嘛神佛,而是山神地祇、列祖列宗。原先他家有過幾幅祖先的畫像,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給燒毀了。后來,他托鄰居一個上大學的名叫巴雅爾的小伙子請來這尊成吉思汗的塑像供奉起來。他非常虔誠地敬奉這尊祖先的塑像。可是在老漢外出的空當,兒子胡亂鼓搗著不慎掉在地上,摔出了裂紋。為此,海姆楚格狠狠揍了一頓從未動過一個指頭的兒子。然而,他總覺得這件事不是兒子的過錯,而是自己在祖先面前造下了罪孽,經常痛苦自責。為了擺脫這種心靈的痛苦,他點香掌燈的次數也頻繁了起來。
海姆楚格如是祈禱完,似乎感到自己的虔誠得到了一時的通達,松了一口氣。他也為自己剛才藏匿的那個小木匣子不曾被賊寇偷盜而攜帶到了現在放寬了心。過去只是存放在冬營盤,從不帶著游走原野草場。所以,那時候也不用擔心丟失和損壞。可是,現在一切與以往大不相同了。讓老漢心懷忐忑、產生疑慮的事情也越來越多了。
這是發生在可愛的夜鶯歡唱山林、碧綠的草原葳蕤揚波的時候,夏營地的人家沿著達爾給延丘梁陸陸續續搬遷而來的事情。
海姆楚格一家按照一貫的老規矩依偎在額很寶拉格——阿給蘇圖的山麓斜坡,與其他人家保持著一定距離,選擇一處臺地搭建蒙古包,建立起了營盤。老漢每年先于別人來到這里夏營的原因,不僅在于能夠盡情品嘗額很寶拉格清澈純凈的泉水,自由享受臺地的清風爽氣,而且還因為這里接近山林,便于砍柴取薪,還可以隨便放養畜群。跨著達爾給延丘梁星羅棋布地落座開來的夏營地的人家,裝點著延綿起伏的溝谷地帶,整個夏天看起來讓人心曠神怡、浮想聯翩。滿目眺望濫觴自阿給蘇圖山澗,瀲滟流淌的姚樂圖河兩岸翠綠的草叢上悠然游走的色彩斑斕的畜群和凹地那如同萬千馬隊任韁馳騁一樣氣勢磅礴的氤氳,可算是至高的人間幸福了。自古以來,人們把阿給蘇圖富庶的山巒拉開背部屏障,豪爾格①巖石疊嶂的峰嶺對峙西南邊,由其中間姚樂圖河汩汩流淌,自寶日嘎蘇泰臂彎北岸至前面山坡涌起的這塊騎馬全速奔馳數里都不會有障礙的廣袤大地,叫做達爾給延西熱②。
從阿給蘇圖渾圓山頭縱情眺望夏營地人家,眼前潔白的蒙古包星羅棋布地展開,牛羊悠然游走,恰似綠松寶石臺面上擺放了銀碗,撒滿五色珍珠瑪瑙一樣讓人賞心悅目,給人以生活富綽的吉祥感覺。不知何人,曾在何時,在這個臺地上縱馬馳騁,可能突發奇想地起了這么個好聽的名字吧。在達爾給延西熱南面對之而立的雄嵬高大的豪爾格罕山是個擁有無數神話故事的四方形的蒼茫大山。據說,豪爾格罕山里有一百零八個洞穴。因為,那里什么東西都可以存儲,所以,上輩的人們將其命名為“豪爾格”也必有其由啊。將辛勤勞作獲得的珍貴果實儲存在“柜櫥”里,再將盛滿器皿的食品從“柜櫥”里取出,擺放在“桌子”上,這是何等形象的富庶生活的表現啊。蒙古地方的大好山水是其民眾分秒不可背離的生活之必然條件啊。
海姆楚格的家族是孛兒只斤①氏,所以,被稱作為金枝玉葉,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代又一代。據說,在成吉思汗時期,他們的祖先有個叫額兒吉格泰②的大將軍征戰回回國,將其收于麾下,乘勝進兵,金戈鐵馬席卷亞美尼亞、沙俄荒原大漠,建立了豐功偉績。海姆楚格將其引以為豪,并要求子嗣們也以此作為榮耀。為此,他時常魂牽夢繞于祖先浴血奮戰的北方曠野,同時也為顯示自己是大家門第,搬遷夏營地時總要占據水源地頭。然而,這些已是過去的話題了。可是現在不一樣了,過去的那份自豪和炫耀的成分越來越在減少,憂愁和痛楚的成分越來越在增多。海姆楚格已經沒有了過去的那種魂牽夢繞的虛幻的自豪感了。他現在已經不得不承認冷酷無情的現實環境,但心中又有割舍不掉的東西。他醒悟到了這些后,生成了一種自欺欺人的暫時的解脫——逃避這冷酷無情的現實的想法,占據了他大片心理空間。
要說為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海姆楚格的冬營盤正好坐落在這片營地的南部邊緣。近年來他受夠了居住南部邊緣的禍害。甭說絡繹不絕的、來歷不明的人們不分晝夜地紛至沓來,就連去年準備蓋房子用的檁子在他們搬到夏營盤的空當都不知了去向。正在他打聽消息的時候,竊賊又破窗而入,盜走了他打算賣給供銷社的山羊絨,而且還像狗一樣在炕上拉了一堆屎。這可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丟了東西還不算,被糟蹋了家,玷污了名聲,老漢一氣之下告到了旗里。但是,誰也沒管這事。就在這時候仿佛是賊在說“你再告一回”一樣,在大熱的秋天,在野外把他家的一頭肥牛宰殺后帶走了。海姆楚格憤懣至極,詛咒了一陣世態的荒亂,知道也不會管什么用,就開始神經質地疑神疑鬼了起來。
慶幸藏匿在柜子下面坑道里的那個小木匣子沒有遭劫,他合掌誦念阿彌陀佛了。只要這個木匣子在手,丟失了什么東西他都不屑一顧了。其實,對一個已經黃土掩埋了半截的人來說,大可不必這樣為生活愁苦煩惱了。就是一個人看管著冬營盤清閑地生活也沒人說他不可。說來說去,還是這個小木匣子讓他牽腸掛肚,讓他不得安心地閉上眼睛而折磨他到現在。在這個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的亂世,與其說怕獨自一人留在冬營盤丟掉老命,還不如說擔心丟失這個小木匣子更為貼切。所以,一方面給兒子和兒媳打個幫手,另一方面為了保護那個小木匣子,他來到了夏營盤。
在剛來夏營盤的前一些日子里,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樣平靜安和。但不知道為什么,海姆楚格心中總有一種不祥預兆的恐懼感。山野顯得寂寥空蒙,就連水流舒緩的姚樂圖河的嘩嘩的流淌聲,也似乎在乘著陣風傾訴著什么,仿佛預示著兇多吉少的事情到了時候就會降臨,給人一種坐臥不安的危機感。的確,那件事來得比他潛意識中的預感還要快了許多。
那事發生在搬到夏營盤半個月后的一個晚上。孟夏的驕陽由阿給蘇圖山頭沉下,灑遍山川原野的橙黃色夕照漸漸被靛灰色的夜幕覆蓋,天空綴滿閃爍的星辰,萬籟沉浸在了安詳的夜韻中。海姆楚格的二十多頭牛散臥在蒙古包的前后反芻著,百十來只羊舒坦地歇息在營盤上。任何聲響都會穿透神秘的寧靜安和的夜色,如是覆蓋了草原大地。時而從散布在達爾給延西熱上的夏營地的人家那里傳來狗吠聲。浩特其和會拉嘎兩條犬聽聞著遠處的動靜淡淡地吠叫著,突然它們像看到了什么似的急促地吠叫著哀鳴起來。其他人家的狗也聞訊此起彼伏地連聲吠叫起來。這急促的狗吠聲給干完一天的活計剛剛開始吃晚飯的海姆楚格家帶來了異常的緊張氣氛。
“這是怎么了,孩子?疥子(狼的隱諱語)不會這么早就來吧?”海姆楚格側耳傾聽,用充滿憂慮的目光看著兒子阿尤樂貴說。
“這幫臭痞子吃飽撐的亂嚎叫呢。”阿尤樂貴漫不經心地說著一心撲在飯菜上,顯得很不愉快。他似乎在盤算著與什么人的交易得失一樣總是耷拉著個臉,不露一絲笑容。而且說的話也總是生硬而讓人厭惡。外面的人看了還會覺得他對妻子,或者是對父親態度蠻狠殘暴呢。這家的那兩個人已經習慣了他的性情,自然也就不會多想什么了。
“疥子來了狗也能對付得了吧。爸爸你就放心吃飯吧。把碗遞給我。”兒媳心領神會地說。有了身孕,體態日漸顯眼的兒媳的智慧如同她的人一樣美麗清澈。不知是由于心軟,還是誠實懦弱,什么事情都看著丈夫的臉色行動的這個心地善良的女人,在兩代男人中間撮合著說的話,對海姆楚格沒有產生多大的慰藉。他們家的這兩條名犬可是個非常厲害的敢抓人的狗。它們有著曾經多次抓捕過潛伏進入營盤的野狼的歷史。海姆楚格一輩子最喜歡好馬和好狗。他仗著好馬和好狗,被鄰里間稱為“高手海姆楚格”。他還常說:“好馬、好狗比起賴人強多啦。”但奇怪的是兒子一點兒也沒有隨他,對他養的狗就像有仇似的總是惡狠狠地虐待打罵,讓人費解。海姆楚格理解狗的意圖比理解兒子的心思還要勝過一籌。
狗們的吠叫聲越來越密集而急促,老漢及時地意識到了那吠聲里雖說顯示著保護家園、迎戰強敵的堅強意志,但是其中不免流露著驚恐畏懼的跡象。他看了看兒子和兒媳,把手中的碗推向火撐子邊,右手托在鋪設在右側的生牛皮上,左手拄著膝蓋“嗨”的一聲站起來,取下掛在哈那頭上的心墜布魯①掖在腰間推門走了出去。
“爸爸,飯還沒吃……要不我出去看看……”兒媳幾乎要拽住他的袍裾似的急忙提醒道。
“你是有孕在身的人,黑燈瞎火的干什么,孩子啊。回屋去。”說罷,海姆楚格在夜幕下朦朦朧朧地走遠了。
站在父親身后聆聽了少許動靜后,南斯樂瑪折回屋里,用厭惡的目光瞥了一下阿尤樂貴,嗔怪說:
“你也有點兒太甚了。睜眼看著就讓老人跑腿,怎么不出去看看呢。”
“人老了疑心就重了,這話不假啊。狼什么時候在這黑夜里襲擊過營盤呢?剛剛放羊回來也不能消停地吃口飯茶。”他怒不可遏地將空碗重重地推給了妻子。
“念及爸爸的那顆苦心,你也該出去看看啊,又不是讓你去守夜。”
“守夜的人去守夜是應該的吧。我跟了一天羊屁股還不夠嗎?你不要在那兒瞎咧咧,小心扯爛你的嘴唇。對了,把那酒瓶子遞給我,身上有點兒發冷。”阿尤樂貴白了一眼妻子,命令似的說道。妻子臉上顯現出鄙夷的神色,但再沒有心思和他拌嘴,盛滿飯遞過去后,像既害怕拉響炸彈的導火線,而更畏懼頂過來的槍口一樣,怯懦地慢慢拉開碗櫥,用顫巍巍的手握住了她冒著讓人渾身打顫的冷雨買回來的那瓶酒。就在這時,傳來圍繞著營盤的遠處吠叫的家犬們突然開始哀鳴,出現了牛羊驚恐地走動的動靜。
南斯樂瑪走出屋外,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濃厚的雨云布滿天空,遠處傳來悶悶的雷鳴聲。趁著遠處閃電的光亮一看,牛羊已經不在營盤,聽到父親在北邊溝壑入口處追趕畜群的吆喝聲。不斷的閃電時時勾勒出殷紅的天涯的輪廓,除此之外遠近什么東西都看不見。世間萬物失去原本的存在形式,如同融化在了黑黢黢的夜里。如果沒有接連的閃電,真是難辨哪方是天,哪方是地。在沉悶的令人窒息的氛圍中,所有的東西仿佛都停止了活動,偶爾的閃電顯現著灌木草叢像逼將而來的披頭散發、張牙舞爪的魑魅魍魎。走著,覺知哪里有點兒動靜,將手電打過去,也只有穿透黑暗的一道白光。她覺到好像有手持兇器的眾多強盜向她的家園包抄過來,這時,朝西南豪爾格罕山方向狂吠亂叫的牧戶的家犬們像被心墜布魯猛擊了頭部一樣慘叫了一聲沒有了動靜。趁著閃電光亮,她看見自家的兩條狗浩特其和會拉嘎夾著尾巴,豎著鬃毛由她身邊拼命向東逃跑。南斯樂瑪第一次看見狗被嚇得這般消聲隱息地逃遁,想到肯定有可怕的東西逼近自家的營盤,她的毛發都不由自主地奓起來。跑進屋里催促丈夫快點出來,但沒被理睬。她抄起掛在哈那頭上的父親的獵槍,朝北邊溝壑入口處踉蹌著跑去。
聽到達爾給延西熱上夏營地人家的狗的狂吠亂叫走出來的男人們零零星星地喊叫著,但是,看到從豪爾格罕山上下來,蹚過姚樂圖河,朝營盤逼近的如同并列的兩把手電隱隱約約的綠光,誰也沒有弄清楚是什么,就膽怯地躲進了各自的蒙古包。家犬都閉嘴夾尾逃之夭夭,更不用說人了,就連草木也垂頭折腰,盡皆沉浸在了恐怖氛圍之中。
“俗話說盲犬吠月,結果怎么了?”阿尤樂貴悠閑地待在屋里心寬肚敞地譏笑著大口大口地喝著酒。也不知道是酒精中毒的影響,還是對什么東西都懷有過度的貪欲,目中燃燒著貪婪的欲火,由于嬌生慣養形成的肆無忌憚的脾性使其噘著鄙視他人的嘴,時常低著頭好像尋覓掉落在地上的東西一樣的行走姿勢養成了脖頸前傾的習慣。然而,這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其實是個長相標致的人。他趁著無人阻攔不停地暴飲著烈酒。這時,蒙古包的圍墻發出了噼啪的響聲。
“這些壞蛋總是禍害圍氈。”阿尤樂貴罵罵咧咧,但無意出去驅趕羔羊。繼續背靠著哈那舉著酒瓶子。突然,有個什么東西重重地戳了一下他的后背。
“嗨,這幫該死的孽種。深更半夜往哈那眼里伸嘴的淘氣的山羊崽子。無聊的討厭鬼,看我豁開你們的嘴唇。”他怒斥著抽出了別在腰帶上的刀子,轉身一看,原來不是山羊羔子的嘴,而是一個撩起圍氈從哈那眼里伸進來的木碗大小的黃色蹄子張揚著的利爪。冷不防看到的情形,使阿尤樂貴眼睛都差點兒蹦出來了。他嚇得撂下了酒瓶子和刀子,慘叫一聲,起身躍向門口,不料被火撐子絆倒摔了個馬趴。
海姆楚格和兒媳收攏了驚炸的畜群,空放了幾槍,大聲呼喊著,在午夜時分勉強把走散的畜群趕回到營盤。打手電確認,僥幸沒有丟失一只羊羔。但是,想到那個突然襲來驚炸畜群,讓獵狗心驚膽戰的可怕的東西,公媳二人心驚肉跳、毛發悚然。不知獵狗逃往哪里,沒有一點兒音訊。周圍越是趨于平靜,越是感到有個長有猙獰眼睛的怪物在窺視他們。
說來也奇怪。好像是為了給那個可怕的東西作掩護助威,布滿天空的烏云滴雨未下瞬間退卻了,雷聲也不響了。空蒙的天空閃爍著星辰,山川原野似乎進入夢鄉,世界恢復寧靜,仿佛剛才什么都沒有發生。達爾給延西熱上的人家里好像沒有剩下有生命的東西一樣寂靜,喧鬧了一陣的獵狗消聲閉嘴再也沒有吠叫。不會放過任何覬覦營盤和畜群而來的人和狼的兇猛的獵狗,也不知道被什么東西卷走了。看夠了人世間無數奇異現象的年逾六旬的海姆楚格感到詫異和不解,同時,恐懼和憤恨油然而生。海姆楚格清楚地知道,狗是個警覺而富有智慧的動物,就算捕獲了偷襲畜群的狼,它們也不會因征服了敵人而安心酣睡的。因為他的兩條愛犬浩特其和會拉嘎總是探聽著遠近的動靜徹夜吠叫個不停,所以,他能從犬吠聲中判斷周圍的一切,因而,在守夜中也從未有過任何的閃失。但是現在別說狗了,就連蟈蟈都嚇得銷聲匿跡,死一般的寂靜籠罩了整個世界,給人一種極其不祥的預兆。
海姆楚格和兒媳眺望著遠處天邊的星斗,悄悄地聆聽了一會兒響動,回到了屋里。滿屋彌漫著嗆人的酒味,只見阿尤樂貴撞在門上不省人事地俯臥在地上。額頭碰開裂綻,鮮血流淌在臉上。他倆像被彈簧射出去一樣叫喚著奔向阿尤樂貴。扶起他的上半身,呼喚他的名字,用力晃動也不見他蘇醒。于是,拿來一碗涼水潑向他的臉,去掐人中,阿尤樂貴這才“啊”地慘叫了一聲,像瘋了一樣指了一下西北面的柜子,目光停滯了片刻,又指向了東北面的哈那。突然,他又瞪著驚恐萬狀的眼睛瘆人地喊叫著,朝門的方向蹬腿伸手匍匐而去。
海姆楚格的心一下子懸在了嗓子眼兒上。點著燈跑到西北角移開柜櫥查看,幸好那個小木匣子安然無恙。老漢靜了靜心,緩緩地深呼吸著,心絞痛病差點兒又犯了。他按摩著胸脯坐了一會兒感到舒坦了一些,朝阿尤樂貴指的東北角的哈那的穿孔處瞟了一眼,腦海里瞬即掠過了鬼的念頭。但是也沒有看到特別稀奇的東西。細細觀察也只有幾根粗硬的黃色的毛發掛在哈那的皮筋綴子上。老漢捏起那毛發打量了一下沒有說話。聞到酒味,他很不愉快地想,肯定是兒子喝醉了酒弄出這荒唐事的,便出去到他守夜的篷子車上歇息了。
海姆楚格圍繞臥在營盤上的畜群的外圍巡視了一周,站在原地探聽動靜,但寂靜主宰了一切,就像躲避一種食肉動物,懼怕發出些許的聲響,簌簌顫抖著藏臥在灌木叢中的鵪鶉一樣,所有的生靈蜷縮在了各自的位置。老漢沒有弄清楚究竟來了什么。要是強盜,狼豺來了肯定會掠走牲畜和物件,狗也不會那么恐懼。是不是把狗給抓走了?他獨自想著試著呼喚兩條狗的名字。看到兩條狗隱隱約約從東邊的溝壑處跑過來,他愛撫著搖尾垂耳的狗的額頭說:
“怎么了?來過什么東西?你倆看見了嗎?快告訴我。”他等了一會兒也沒有回聲,才知道自己向不會說話的動物問了話,長噓了一口氣。能有什么呢,一切不是都挺好嘛。就是在雷雨中獵狗們虛張聲勢地吠叫,畜群驚炸了唄……他如是想著心里豁朗了一些,鉆進篷子車里躺下了。但是,那個讓他產生奇怪念頭的可怕的預兆盤踞在他的心里,讓他久久不能入睡。
從篷子車的縫隙里可以看到天空放晴,星斗近在咫尺地閃爍。海姆楚格越想今天晚上的事越對兒子泄氣。又開始喝酒了。在這如同迎戰襲來擄掠家人幸福的敵人一樣恐慌危急的時刻,還能若無其事地坐著喝酒,真是太夠嗆了。一個年富力強的青年男人,就不要說我這個動了土的老頭子了,就連懷孕挺著大肚子的女人都不如啊。看到了什么嚇成了那個樣子呢?天生是個 貨啊。他這樣想著,既生氣又傷心。
海姆楚格只有這么一個傳宗接代、接繼薪火的兒子。在兒子的前后也沒有生過其他孩子。他對兒子傾注了所有的慈愛。也不知道是因為沒有得到母愛孤苦伶仃成長的緣故,還是因為擔心缺少了父親的關愛會變得冷酷怪異,除了那次兒子不慎摔裂了圣主的雕塑以外,海姆楚格不用說打了,就連呵斥都很少。俗話說,老到臨頭孩子是心病,他萬萬沒想到兒子會變成這樣一個德行。因為兒子上學進了城以后,看著就和往常不一樣了。與其說學到了文化知識,還不如說沾染了詭異的脾性。海姆楚格暗自想,學到文化知識的人的性格是不是會變得詭異呢。但是,那個時候兒子還不喝酒。與左鄰右舍的同齡人都不怎么說長道短的兒子突然開始說:
“什么最有用?只有朋友有用。朋友多的人走到哪里都不會被冷落。弄不到手的東西也會自然到來。”這是他娶了媳婦以后的事。自那以后,他就時常領來一些不知來歷的或是不堪入目的人一起喝酒。
海姆楚格這一輩子兄弟姐妹很多,但從不喝酒。起初他想,人靠相識,畜靠草坡,沒有過多地阻止兒子與雜七雜八的人來往,可當他覺察到的時候,事情已經變了正樣。兒子去農村里的次數多了起來,來家里的人也絡繹不絕了。起初搗騰來的是瓜果,接著是酒水,作為這些的回饋,開始弄走的是畜肉,后來竟弄起了山羊絨。不久,兒子開始經常對妻子發脾氣,牲口也任意撒開不管了。老漢預感到,即將把腦袋泡入酒瓶子里的兒子,不定哪一天就會把牲畜抓出去禍害光了。他為了讓兒子阿尤樂貴脫離那個罪孽的迷魂湯,絞盡了腦汁,想盡了辦法。起初他采取了柔和的方法,但已經無濟于事了。到了后來,他進行嚴厲的訓斥,兒子嗆著他發威,差點向他動手。將他與領來的那些人一起轟出家門,一走就好幾天不回來了。為此,相互之間積下了深重的怨恨。
欲來者來之,欲去者去之。常言說,父母只能生養孩子的身,無法生養他們的心。二十多歲,七尺男兒,該怎么辦,該怎么走,自己應該清楚。不日就要入土的、不及老綿羊歲數的我何苦傷神費心呢!老漢想著,一段時間里他不管不顧了。但是,積怨終究沒有代替了父親的慈愛。是不是過分的嬌生慣養讓他學壞了呢?老漢寬容著兒子,從自己身上找著原因,在今年搬遷夏營地的時候,又一次萌生了新的希望。他想,來到夏營地,遠離來往的眾人,兒子會靜下心來,安穩一時。這就是他今年夏天先于別人提前搬來,居住在部落邊緣的原因。剛來夏營地的日子里,果真他們家里沒有什么人過往,可能是由于沒有朋友,阿尤樂貴也不喝酒了。對家里人也顯得性情平淡靜默,這些原來都是為了討得一口酒水,而他的內心卻在煩悶。海姆楚格不遺余力地猜出了他的心思,但是,暗自卻相信總有一天兒子會改邪歸正的。可是,誰又會料到堅持來、堅持去,一喝酒竟是這樣的糟糕相……
海姆楚格回想著這些輾轉反側,徹夜不能成寐,他不時地長嘆一口氣。
那天夜里格外地漆黑,而且還異常地寂靜。除了阿尤樂貴夢魘著喊叫了幾聲外,沒給達爾給延西熱夏營地上的人家帶來任何的災荒,平安度過了。
…………
一
孟夏正午的驕陽當空炙烤,夏營地油綠的草場上牛羊攢堆停歇。
“爸爸,這個小木匣子放哪兒?”南斯樂瑪在收拾房屋之前指著用包袱包裹的黑色小木匣子問海姆楚格。幫助父親從牛車上卸下六個哈那①的蒙古包搭建起來,往里面搬運家什,前后忙活很是疲憊,但她臉上卻洋溢著喜悅之色。從做姑娘時起就早已習慣了遷徙搬家之事,已沒有什么新鮮感可言。但是,做了媳婦后的第一次夏營盤搬遷,讓她感到格外的心曠神怡。用手掌擦拭滲于額頭的汗水,向后籠絡梳理耷拉在臉上的秀發,朝父親矜持地微笑時,麗眸里閃耀著可人的靈光,顯示著鄉下草原不多見的美貌少婦的風韻。
端坐在蒙古包中央打點火撐子②的海姆楚格聽到兒媳的話后欠了欠身,看著她不停地里外忙活,投去疼愛的恩慈目光,他說:
“喏,孩子啊,把那遞給我,爸爸收拾吧。”他小心翼翼地接過南斯樂瑪遞給他的粗布包裹的小木匣子,轉身朝向了西北方向的哈那腳。
海姆楚格是個何時都不會發怒煩躁、不說生硬嗆人話語的人,他心善仁慈、溫和謹慎、寬容厚道。現已年過六旬沒齒皓首,作為他一生經歷生活的坎坷蹉跎的印證,滿臉刻下縱橫交錯的褶皺。同時,他暗自總感到身體有些不適的征兆,曾經膀大腰圓的身體日漸消瘦,近來更是眼窩凹陷,面部憔悴,只有鼻梁顯得愈加凸出了。在偏遠的鄉下,年邁的人總是把這種突如其來的不適狀態歸結于年齡,幾乎沒有人懷疑其為疾病,很少有人去問醫就診。但是,海姆楚格自己卻清楚地知道這個每況愈下的狀況的緣由。那是二十年前,他守護著絕氣的妻子,自己卻失神摔倒后,心里落下殘疾,幾經治療也沒有除根,殘留成了病魔。老漢清醒地感悟到這個背后有來頭的東西肯定會糾纏住他的生命不放。他也沒讓兒子和兒媳知道這件事。因為他向來就是個心氣堅強的人,所以,咬著牙抵御著病魔的逼迫和折磨。疼痛像潮水一樣涌來的時候,讓他死去活來,退去的時候卻如同抽絲一樣釋然。這個東西給了老漢二十年的暗示,不定哪天就把兒子遺孤于世,這讓他擔驚受怕到現在。但是,僥幸沒有發生什么意外。現在老漢更沒有什么可怕的了。兒子如今長大成人,老朽身軀成為多余也是自然之理。然而,只有一件東西讓他留戀糾結著現在的生活。那就是那個從未撒手、悉心看護到如今的小木匣子。為此他感到非常遺憾和揪心。
“爸爸,我去泉眼打水回來熬茶。您的臉色很不好看,先躺一會兒吧。剩下的活兒等他回來再說吧。”媳婦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一樣說著,她在包里的主座上鋪開生牛皮,攤開納線毛氈①,提著水桶出去了。
“心地善良的好女兒啊。可憐的孩子,阿尤樂貴是個給你幫前忙后的那種人嗎……”老漢隨其身后自言自語著長嘆了一口氣。他沒有按照媳婦的囑咐躺下歇息,起來在哈那腳的西北角挖了個小坑,用防潮塑料布包裹好那個小木匣子放在里面,上面擱上了木板子。接著,他把搬進來的四方木頭柜子置放在上面,將容納圣人雕塑的佛龕擺放在柜子的正中央,點起了線香和長明燈,清理整肅了衣帽后跪下,合掌祈禱道:
“列祖列宗,宇宙上蒼,山神地祇,請求保佑。請賜給我們頭上沒有災禍侵襲,腳下沒有苦難遭遇的國泰民安的盛世吧!”這是海姆楚格每次搬遷搭營后,必須首先虔誠地完成的一項既定的禮儀。然而,他信奉膜拜的不是喇嘛神佛,而是山神地祇、列祖列宗。原先他家有過幾幅祖先的畫像,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給燒毀了。后來,他托鄰居一個上大學的名叫巴雅爾的小伙子請來這尊成吉思汗的塑像供奉起來。他非常虔誠地敬奉這尊祖先的塑像。可是在老漢外出的空當,兒子胡亂鼓搗著不慎掉在地上,摔出了裂紋。為此,海姆楚格狠狠揍了一頓從未動過一個指頭的兒子。然而,他總覺得這件事不是兒子的過錯,而是自己在祖先面前造下了罪孽,經常痛苦自責。為了擺脫這種心靈的痛苦,他點香掌燈的次數也頻繁了起來。
海姆楚格如是祈禱完,似乎感到自己的虔誠得到了一時的通達,松了一口氣。他也為自己剛才藏匿的那個小木匣子不曾被賊寇偷盜而攜帶到了現在放寬了心。過去只是存放在冬營盤,從不帶著游走原野草場。所以,那時候也不用擔心丟失和損壞。可是,現在一切與以往大不相同了。讓老漢心懷忐忑、產生疑慮的事情也越來越多了。
這是發生在可愛的夜鶯歡唱山林、碧綠的草原葳蕤揚波的時候,夏營地的人家沿著達爾給延丘梁陸陸續續搬遷而來的事情。
海姆楚格一家按照一貫的老規矩依偎在額很寶拉格——阿給蘇圖的山麓斜坡,與其他人家保持著一定距離,選擇一處臺地搭建蒙古包,建立起了營盤。老漢每年先于別人來到這里夏營的原因,不僅在于能夠盡情品嘗額很寶拉格清澈純凈的泉水,自由享受臺地的清風爽氣,而且還因為這里接近山林,便于砍柴取薪,還可以隨便放養畜群。跨著達爾給延丘梁星羅棋布地落座開來的夏營地的人家,裝點著延綿起伏的溝谷地帶,整個夏天看起來讓人心曠神怡、浮想聯翩。滿目眺望濫觴自阿給蘇圖山澗,瀲滟流淌的姚樂圖河兩岸翠綠的草叢上悠然游走的色彩斑斕的畜群和凹地那如同萬千馬隊任韁馳騁一樣氣勢磅礴的氤氳,可算是至高的人間幸福了。自古以來,人們把阿給蘇圖富庶的山巒拉開背部屏障,豪爾格①巖石疊嶂的峰嶺對峙西南邊,由其中間姚樂圖河汩汩流淌,自寶日嘎蘇泰臂彎北岸至前面山坡涌起的這塊騎馬全速奔馳數里都不會有障礙的廣袤大地,叫做達爾給延西熱②。
從阿給蘇圖渾圓山頭縱情眺望夏營地人家,眼前潔白的蒙古包星羅棋布地展開,牛羊悠然游走,恰似綠松寶石臺面上擺放了銀碗,撒滿五色珍珠瑪瑙一樣讓人賞心悅目,給人以生活富綽的吉祥感覺。不知何人,曾在何時,在這個臺地上縱馬馳騁,可能突發奇想地起了這么個好聽的名字吧。在達爾給延西熱南面對之而立的雄嵬高大的豪爾格罕山是個擁有無數神話故事的四方形的蒼茫大山。據說,豪爾格罕山里有一百零八個洞穴。因為,那里什么東西都可以存儲,所以,上輩的人們將其命名為“豪爾格”也必有其由啊。將辛勤勞作獲得的珍貴果實儲存在“柜櫥”里,再將盛滿器皿的食品從“柜櫥”里取出,擺放在“桌子”上,這是何等形象的富庶生活的表現啊。蒙古地方的大好山水是其民眾分秒不可背離的生活之必然條件啊。
海姆楚格的家族是孛兒只斤①氏,所以,被稱作為金枝玉葉,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代又一代。據說,在成吉思汗時期,他們的祖先有個叫額兒吉格泰②的大將軍征戰回回國,將其收于麾下,乘勝進兵,金戈鐵馬席卷亞美尼亞、沙俄荒原大漠,建立了豐功偉績。海姆楚格將其引以為豪,并要求子嗣們也以此作為榮耀。為此,他時常魂牽夢繞于祖先浴血奮戰的北方曠野,同時也為顯示自己是大家門第,搬遷夏營地時總要占據水源地頭。然而,這些已是過去的話題了。可是現在不一樣了,過去的那份自豪和炫耀的成分越來越在減少,憂愁和痛楚的成分越來越在增多。海姆楚格已經沒有了過去的那種魂牽夢繞的虛幻的自豪感了。他現在已經不得不承認冷酷無情的現實環境,但心中又有割舍不掉的東西。他醒悟到了這些后,生成了一種自欺欺人的暫時的解脫——逃避這冷酷無情的現實的想法,占據了他大片心理空間。
要說為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海姆楚格的冬營盤正好坐落在這片營地的南部邊緣。近年來他受夠了居住南部邊緣的禍害。甭說絡繹不絕的、來歷不明的人們不分晝夜地紛至沓來,就連去年準備蓋房子用的檁子在他們搬到夏營盤的空當都不知了去向。正在他打聽消息的時候,竊賊又破窗而入,盜走了他打算賣給供銷社的山羊絨,而且還像狗一樣在炕上拉了一堆屎。這可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丟了東西還不算,被糟蹋了家,玷污了名聲,老漢一氣之下告到了旗里。但是,誰也沒管這事。就在這時候仿佛是賊在說“你再告一回”一樣,在大熱的秋天,在野外把他家的一頭肥牛宰殺后帶走了。海姆楚格憤懣至極,詛咒了一陣世態的荒亂,知道也不會管什么用,就開始神經質地疑神疑鬼了起來。
慶幸藏匿在柜子下面坑道里的那個小木匣子沒有遭劫,他合掌誦念阿彌陀佛了。只要這個木匣子在手,丟失了什么東西他都不屑一顧了。其實,對一個已經黃土掩埋了半截的人來說,大可不必這樣為生活愁苦煩惱了。就是一個人看管著冬營盤清閑地生活也沒人說他不可。說來說去,還是這個小木匣子讓他牽腸掛肚,讓他不得安心地閉上眼睛而折磨他到現在。在這個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的亂世,與其說怕獨自一人留在冬營盤丟掉老命,還不如說擔心丟失這個小木匣子更為貼切。所以,一方面給兒子和兒媳打個幫手,另一方面為了保護那個小木匣子,他來到了夏營盤。
在剛來夏營盤的前一些日子里,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樣平靜安和。但不知道為什么,海姆楚格心中總有一種不祥預兆的恐懼感。山野顯得寂寥空蒙,就連水流舒緩的姚樂圖河的嘩嘩的流淌聲,也似乎在乘著陣風傾訴著什么,仿佛預示著兇多吉少的事情到了時候就會降臨,給人一種坐臥不安的危機感。的確,那件事來得比他潛意識中的預感還要快了許多。
那事發生在搬到夏營盤半個月后的一個晚上。孟夏的驕陽由阿給蘇圖山頭沉下,灑遍山川原野的橙黃色夕照漸漸被靛灰色的夜幕覆蓋,天空綴滿閃爍的星辰,萬籟沉浸在了安詳的夜韻中。海姆楚格的二十多頭牛散臥在蒙古包的前后反芻著,百十來只羊舒坦地歇息在營盤上。任何聲響都會穿透神秘的寧靜安和的夜色,如是覆蓋了草原大地。時而從散布在達爾給延西熱上的夏營地的人家那里傳來狗吠聲。浩特其和會拉嘎兩條犬聽聞著遠處的動靜淡淡地吠叫著,突然它們像看到了什么似的急促地吠叫著哀鳴起來。其他人家的狗也聞訊此起彼伏地連聲吠叫起來。這急促的狗吠聲給干完一天的活計剛剛開始吃晚飯的海姆楚格家帶來了異常的緊張氣氛。
“這是怎么了,孩子?疥子(狼的隱諱語)不會這么早就來吧?”海姆楚格側耳傾聽,用充滿憂慮的目光看著兒子阿尤樂貴說。
“這幫臭痞子吃飽撐的亂嚎叫呢。”阿尤樂貴漫不經心地說著一心撲在飯菜上,顯得很不愉快。他似乎在盤算著與什么人的交易得失一樣總是耷拉著個臉,不露一絲笑容。而且說的話也總是生硬而讓人厭惡。外面的人看了還會覺得他對妻子,或者是對父親態度蠻狠殘暴呢。這家的那兩個人已經習慣了他的性情,自然也就不會多想什么了。
“疥子來了狗也能對付得了吧。爸爸你就放心吃飯吧。把碗遞給我。”兒媳心領神會地說。有了身孕,體態日漸顯眼的兒媳的智慧如同她的人一樣美麗清澈。不知是由于心軟,還是誠實懦弱,什么事情都看著丈夫的臉色行動的這個心地善良的女人,在兩代男人中間撮合著說的話,對海姆楚格沒有產生多大的慰藉。他們家的這兩條名犬可是個非常厲害的敢抓人的狗。它們有著曾經多次抓捕過潛伏進入營盤的野狼的歷史。海姆楚格一輩子最喜歡好馬和好狗。他仗著好馬和好狗,被鄰里間稱為“高手海姆楚格”。他還常說:“好馬、好狗比起賴人強多啦。”但奇怪的是兒子一點兒也沒有隨他,對他養的狗就像有仇似的總是惡狠狠地虐待打罵,讓人費解。海姆楚格理解狗的意圖比理解兒子的心思還要勝過一籌。
狗們的吠叫聲越來越密集而急促,老漢及時地意識到了那吠聲里雖說顯示著保護家園、迎戰強敵的堅強意志,但是其中不免流露著驚恐畏懼的跡象。他看了看兒子和兒媳,把手中的碗推向火撐子邊,右手托在鋪設在右側的生牛皮上,左手拄著膝蓋“嗨”的一聲站起來,取下掛在哈那頭上的心墜布魯①掖在腰間推門走了出去。
“爸爸,飯還沒吃……要不我出去看看……”兒媳幾乎要拽住他的袍裾似的急忙提醒道。
“你是有孕在身的人,黑燈瞎火的干什么,孩子啊。回屋去。”說罷,海姆楚格在夜幕下朦朦朧朧地走遠了。
站在父親身后聆聽了少許動靜后,南斯樂瑪折回屋里,用厭惡的目光瞥了一下阿尤樂貴,嗔怪說:
“你也有點兒太甚了。睜眼看著就讓老人跑腿,怎么不出去看看呢。”
“人老了疑心就重了,這話不假啊。狼什么時候在這黑夜里襲擊過營盤呢?剛剛放羊回來也不能消停地吃口飯茶。”他怒不可遏地將空碗重重地推給了妻子。
“念及爸爸的那顆苦心,你也該出去看看啊,又不是讓你去守夜。”
“守夜的人去守夜是應該的吧。我跟了一天羊屁股還不夠嗎?你不要在那兒瞎咧咧,小心扯爛你的嘴唇。對了,把那酒瓶子遞給我,身上有點兒發冷。”阿尤樂貴白了一眼妻子,命令似的說道。妻子臉上顯現出鄙夷的神色,但再沒有心思和他拌嘴,盛滿飯遞過去后,像既害怕拉響炸彈的導火線,而更畏懼頂過來的槍口一樣,怯懦地慢慢拉開碗櫥,用顫巍巍的手握住了她冒著讓人渾身打顫的冷雨買回來的那瓶酒。就在這時,傳來圍繞著營盤的遠處吠叫的家犬們突然開始哀鳴,出現了牛羊驚恐地走動的動靜。
南斯樂瑪走出屋外,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濃厚的雨云布滿天空,遠處傳來悶悶的雷鳴聲。趁著遠處閃電的光亮一看,牛羊已經不在營盤,聽到父親在北邊溝壑入口處追趕畜群的吆喝聲。不斷的閃電時時勾勒出殷紅的天涯的輪廓,除此之外遠近什么東西都看不見。世間萬物失去原本的存在形式,如同融化在了黑黢黢的夜里。如果沒有接連的閃電,真是難辨哪方是天,哪方是地。在沉悶的令人窒息的氛圍中,所有的東西仿佛都停止了活動,偶爾的閃電顯現著灌木草叢像逼將而來的披頭散發、張牙舞爪的魑魅魍魎。走著,覺知哪里有點兒動靜,將手電打過去,也只有穿透黑暗的一道白光。她覺到好像有手持兇器的眾多強盜向她的家園包抄過來,這時,朝西南豪爾格罕山方向狂吠亂叫的牧戶的家犬們像被心墜布魯猛擊了頭部一樣慘叫了一聲沒有了動靜。趁著閃電光亮,她看見自家的兩條狗浩特其和會拉嘎夾著尾巴,豎著鬃毛由她身邊拼命向東逃跑。南斯樂瑪第一次看見狗被嚇得這般消聲隱息地逃遁,想到肯定有可怕的東西逼近自家的營盤,她的毛發都不由自主地奓起來。跑進屋里催促丈夫快點出來,但沒被理睬。她抄起掛在哈那頭上的父親的獵槍,朝北邊溝壑入口處踉蹌著跑去。
聽到達爾給延西熱上夏營地人家的狗的狂吠亂叫走出來的男人們零零星星地喊叫著,但是,看到從豪爾格罕山上下來,蹚過姚樂圖河,朝營盤逼近的如同并列的兩把手電隱隱約約的綠光,誰也沒有弄清楚是什么,就膽怯地躲進了各自的蒙古包。家犬都閉嘴夾尾逃之夭夭,更不用說人了,就連草木也垂頭折腰,盡皆沉浸在了恐怖氛圍之中。
“俗話說盲犬吠月,結果怎么了?”阿尤樂貴悠閑地待在屋里心寬肚敞地譏笑著大口大口地喝著酒。也不知道是酒精中毒的影響,還是對什么東西都懷有過度的貪欲,目中燃燒著貪婪的欲火,由于嬌生慣養形成的肆無忌憚的脾性使其噘著鄙視他人的嘴,時常低著頭好像尋覓掉落在地上的東西一樣的行走姿勢養成了脖頸前傾的習慣。然而,這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其實是個長相標致的人。他趁著無人阻攔不停地暴飲著烈酒。這時,蒙古包的圍墻發出了噼啪的響聲。
“這些壞蛋總是禍害圍氈。”阿尤樂貴罵罵咧咧,但無意出去驅趕羔羊。繼續背靠著哈那舉著酒瓶子。突然,有個什么東西重重地戳了一下他的后背。
“嗨,這幫該死的孽種。深更半夜往哈那眼里伸嘴的淘氣的山羊崽子。無聊的討厭鬼,看我豁開你們的嘴唇。”他怒斥著抽出了別在腰帶上的刀子,轉身一看,原來不是山羊羔子的嘴,而是一個撩起圍氈從哈那眼里伸進來的木碗大小的黃色蹄子張揚著的利爪。冷不防看到的情形,使阿尤樂貴眼睛都差點兒蹦出來了。他嚇得撂下了酒瓶子和刀子,慘叫一聲,起身躍向門口,不料被火撐子絆倒摔了個馬趴。
海姆楚格和兒媳收攏了驚炸的畜群,空放了幾槍,大聲呼喊著,在午夜時分勉強把走散的畜群趕回到營盤。打手電確認,僥幸沒有丟失一只羊羔。但是,想到那個突然襲來驚炸畜群,讓獵狗心驚膽戰的可怕的東西,公媳二人心驚肉跳、毛發悚然。不知獵狗逃往哪里,沒有一點兒音訊。周圍越是趨于平靜,越是感到有個長有猙獰眼睛的怪物在窺視他們。
說來也奇怪。好像是為了給那個可怕的東西作掩護助威,布滿天空的烏云滴雨未下瞬間退卻了,雷聲也不響了。空蒙的天空閃爍著星辰,山川原野似乎進入夢鄉,世界恢復寧靜,仿佛剛才什么都沒有發生。達爾給延西熱上的人家里好像沒有剩下有生命的東西一樣寂靜,喧鬧了一陣的獵狗消聲閉嘴再也沒有吠叫。不會放過任何覬覦營盤和畜群而來的人和狼的兇猛的獵狗,也不知道被什么東西卷走了。看夠了人世間無數奇異現象的年逾六旬的海姆楚格感到詫異和不解,同時,恐懼和憤恨油然而生。海姆楚格清楚地知道,狗是個警覺而富有智慧的動物,就算捕獲了偷襲畜群的狼,它們也不會因征服了敵人而安心酣睡的。因為他的兩條愛犬浩特其和會拉嘎總是探聽著遠近的動靜徹夜吠叫個不停,所以,他能從犬吠聲中判斷周圍的一切,因而,在守夜中也從未有過任何的閃失。但是現在別說狗了,就連蟈蟈都嚇得銷聲匿跡,死一般的寂靜籠罩了整個世界,給人一種極其不祥的預兆。
海姆楚格和兒媳眺望著遠處天邊的星斗,悄悄地聆聽了一會兒響動,回到了屋里。滿屋彌漫著嗆人的酒味,只見阿尤樂貴撞在門上不省人事地俯臥在地上。額頭碰開裂綻,鮮血流淌在臉上。他倆像被彈簧射出去一樣叫喚著奔向阿尤樂貴。扶起他的上半身,呼喚他的名字,用力晃動也不見他蘇醒。于是,拿來一碗涼水潑向他的臉,去掐人中,阿尤樂貴這才“啊”地慘叫了一聲,像瘋了一樣指了一下西北面的柜子,目光停滯了片刻,又指向了東北面的哈那。突然,他又瞪著驚恐萬狀的眼睛瘆人地喊叫著,朝門的方向蹬腿伸手匍匐而去。
海姆楚格的心一下子懸在了嗓子眼兒上。點著燈跑到西北角移開柜櫥查看,幸好那個小木匣子安然無恙。老漢靜了靜心,緩緩地深呼吸著,心絞痛病差點兒又犯了。他按摩著胸脯坐了一會兒感到舒坦了一些,朝阿尤樂貴指的東北角的哈那的穿孔處瞟了一眼,腦海里瞬即掠過了鬼的念頭。但是也沒有看到特別稀奇的東西。細細觀察也只有幾根粗硬的黃色的毛發掛在哈那的皮筋綴子上。老漢捏起那毛發打量了一下沒有說話。聞到酒味,他很不愉快地想,肯定是兒子喝醉了酒弄出這荒唐事的,便出去到他守夜的篷子車上歇息了。
海姆楚格圍繞臥在營盤上的畜群的外圍巡視了一周,站在原地探聽動靜,但寂靜主宰了一切,就像躲避一種食肉動物,懼怕發出些許的聲響,簌簌顫抖著藏臥在灌木叢中的鵪鶉一樣,所有的生靈蜷縮在了各自的位置。老漢沒有弄清楚究竟來了什么。要是強盜,狼豺來了肯定會掠走牲畜和物件,狗也不會那么恐懼。是不是把狗給抓走了?他獨自想著試著呼喚兩條狗的名字。看到兩條狗隱隱約約從東邊的溝壑處跑過來,他愛撫著搖尾垂耳的狗的額頭說:
“怎么了?來過什么東西?你倆看見了嗎?快告訴我。”他等了一會兒也沒有回聲,才知道自己向不會說話的動物問了話,長噓了一口氣。能有什么呢,一切不是都挺好嘛。就是在雷雨中獵狗們虛張聲勢地吠叫,畜群驚炸了唄……他如是想著心里豁朗了一些,鉆進篷子車里躺下了。但是,那個讓他產生奇怪念頭的可怕的預兆盤踞在他的心里,讓他久久不能入睡。
從篷子車的縫隙里可以看到天空放晴,星斗近在咫尺地閃爍。海姆楚格越想今天晚上的事越對兒子泄氣。又開始喝酒了。在這如同迎戰襲來擄掠家人幸福的敵人一樣恐慌危急的時刻,還能若無其事地坐著喝酒,真是太夠嗆了。一個年富力強的青年男人,就不要說我這個動了土的老頭子了,就連懷孕挺著大肚子的女人都不如啊。看到了什么嚇成了那個樣子呢?天生是個 貨啊。他這樣想著,既生氣又傷心。
海姆楚格只有這么一個傳宗接代、接繼薪火的兒子。在兒子的前后也沒有生過其他孩子。他對兒子傾注了所有的慈愛。也不知道是因為沒有得到母愛孤苦伶仃成長的緣故,還是因為擔心缺少了父親的關愛會變得冷酷怪異,除了那次兒子不慎摔裂了圣主的雕塑以外,海姆楚格不用說打了,就連呵斥都很少。俗話說,老到臨頭孩子是心病,他萬萬沒想到兒子會變成這樣一個德行。因為兒子上學進了城以后,看著就和往常不一樣了。與其說學到了文化知識,還不如說沾染了詭異的脾性。海姆楚格暗自想,學到文化知識的人的性格是不是會變得詭異呢。但是,那個時候兒子還不喝酒。與左鄰右舍的同齡人都不怎么說長道短的兒子突然開始說:
“什么最有用?只有朋友有用。朋友多的人走到哪里都不會被冷落。弄不到手的東西也會自然到來。”這是他娶了媳婦以后的事。自那以后,他就時常領來一些不知來歷的或是不堪入目的人一起喝酒。
海姆楚格這一輩子兄弟姐妹很多,但從不喝酒。起初他想,人靠相識,畜靠草坡,沒有過多地阻止兒子與雜七雜八的人來往,可當他覺察到的時候,事情已經變了正樣。兒子去農村里的次數多了起來,來家里的人也絡繹不絕了。起初搗騰來的是瓜果,接著是酒水,作為這些的回饋,開始弄走的是畜肉,后來竟弄起了山羊絨。不久,兒子開始經常對妻子發脾氣,牲口也任意撒開不管了。老漢預感到,即將把腦袋泡入酒瓶子里的兒子,不定哪一天就會把牲畜抓出去禍害光了。他為了讓兒子阿尤樂貴脫離那個罪孽的迷魂湯,絞盡了腦汁,想盡了辦法。起初他采取了柔和的方法,但已經無濟于事了。到了后來,他進行嚴厲的訓斥,兒子嗆著他發威,差點向他動手。將他與領來的那些人一起轟出家門,一走就好幾天不回來了。為此,相互之間積下了深重的怨恨。
欲來者來之,欲去者去之。常言說,父母只能生養孩子的身,無法生養他們的心。二十多歲,七尺男兒,該怎么辦,該怎么走,自己應該清楚。不日就要入土的、不及老綿羊歲數的我何苦傷神費心呢!老漢想著,一段時間里他不管不顧了。但是,積怨終究沒有代替了父親的慈愛。是不是過分的嬌生慣養讓他學壞了呢?老漢寬容著兒子,從自己身上找著原因,在今年搬遷夏營地的時候,又一次萌生了新的希望。他想,來到夏營地,遠離來往的眾人,兒子會靜下心來,安穩一時。這就是他今年夏天先于別人提前搬來,居住在部落邊緣的原因。剛來夏營地的日子里,果真他們家里沒有什么人過往,可能是由于沒有朋友,阿尤樂貴也不喝酒了。對家里人也顯得性情平淡靜默,這些原來都是為了討得一口酒水,而他的內心卻在煩悶。海姆楚格不遺余力地猜出了他的心思,但是,暗自卻相信總有一天兒子會改邪歸正的。可是,誰又會料到堅持來、堅持去,一喝酒竟是這樣的糟糕相……
海姆楚格回想著這些輾轉反側,徹夜不能成寐,他不時地長嘆一口氣。
那天夜里格外地漆黑,而且還異常地寂靜。除了阿尤樂貴夢魘著喊叫了幾聲外,沒給達爾給延西熱夏營地上的人家帶來任何的災荒,平安度過了。
…………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優惠價:87
183
海外經銷商無庫存,到貨日平均30天至4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