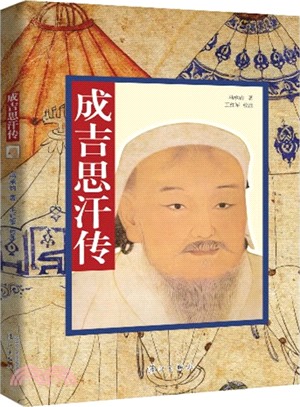成吉思汗傳(簡體書)
商品資訊
人民幣定價:22 元
定價
:NT$ 132 元優惠價
:87 折 115 元
絕版無法訂購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是我國近代著名史學家和傑出翻譯家馮承鈞所著,該書先扼要介紹了成吉思汗的身世,既而梳理了其崛起和對諸部落整合的情況,最後較詳細地記述了成吉思汗西征與去世的經過。作者既深受近代學術思想的薰陶和科學方法的訓練,又通曉拉丁、梵、蒙、藏等諸種文字,對史實考訂比較審慎,故本書脈絡分明,持論也比較平實,是成吉思汗傳記諸多版本中不可多得的一種。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乾坤大挪移”是《倚天屠龍記》中描繪的一種最厲害的武功,而在胡文輝眼中,馮承鈞先生堪稱中外交通史領域的“張無忌”,他修練出“乾坤大挪移”般的功夫,使他在中外交通史領域的翻譯和著述所向披靡,成果卓著,這本《成吉思汗傳》就是其代表作之一。除了享受到獨特的閱讀快感之外還想獲得一些比較可靠的歷史知識的讀者,可以閱讀此書。
序
《成吉思汗傳》是史學家馮承鈞的一部部頭不大卻很有名的著作。該書和馮氏的翻譯密切相關,所以此處先以較多筆墨談談馮氏在翻譯領域的成就及其取得這些成就的條件,再概述馮氏撰述此書的緣起、本書的內容和版本,借以理解此書在馮氏著述中尤其在與同類書籍相較時所展現出的風格。
馮承鈞(一八八七一一九四六),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漢口)人。曾赴比利時、法國留學,歸國后適逢辛亥革命發生,被任命為湖北都督府秘書。一九一三年任眾議院秘書,后轉為教育部僉事,凡十五年,其間歷兼北京大學講師及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一九二九年任立法編纂委員。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九年被聘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編輯。后被聘為臨時大學第二分班史學系教授,專任中亞交通、西北史地、蒙元史等課程。一九四六年病逝。
與其年壽相比,馮氏在史地翻譯領域的成就可謂厚重。
馮氏去世后,王靜如撰有《馮承鈞先生事略》一文,內云馮氏“譯著等身”,其“譯述名著之多,實達近三十年來之最高峰”,“一生譯著不下百數十種,約五百萬言,其中關于法學書籍,多未刊印;而中國文史之譯作,其行世者,即約三四十本”。堪稱馮氏知交的向達在《悼馮承鈞先生》中也提及,馮氏“翻譯以及自著的專書和論文甚多”,雖然“昆明方圖能夠看到的不過一二十種”。另一位和馮氏“并無奉手之雅”,但對馮氏“素具仰止之忱”并將其列為自己“所佩服的前輩之一”的朱杰勤,出于仰慕和哀悼,給馮氏的譯著列了個自認為“未敢認為完備”的清單,其中載馮氏譯著共四十二種。以傳世諸書驗上述諸人的記載,便知所言不虛。即以今日眼光視之,其譯著數量亦屬可觀。
王靜如還談到,馮氏“譯文流暢,用詞正確,治史學者莫不欽服”,“每有新意,皆極精確,尤以論疏勒為西方所從出,實發前人所未發,允為最近得意之作也”。朱杰勤于馮氏去世兩星期后記下了自己的感觸,認為“馮先生是第一流的翻譯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違原本。間遇罕見之名詞,又為之厘定漢名,斟酌至善”,還將馮氏與嚴復和林紓放在一起月旦一番,認為就翻譯技術而論,馮氏要居于嚴、林之上。他說:“但就翻譯成績而論,馮先生是近代第一流翻譯家。清末翻譯界中嚴復(幾道)與林紓(琴南)并稱,但因時代關系,他們的翻譯技術尚未達到完美地步,持較馮先生,則他們好像椎輪,而馮先生好像大輅了。”以后人的眼光來看,這種評價或有溢美成分,但能獲得識與不識者如此交口稱贊,則其譯著的質量和水準之高應不難想見。
關于譯介的重要性,馮氏曾有這樣一段論述:“吾人研究本國史,姑就書本一方面言,常感史部紀事編年之書,未能完全滿足學者之需要。有無數問題之解說,不得不于史部以外書中求之。檢尋古今書目,屢見非史部之書,而可供參考之用者不少,《釋藏》其一種也。吾人之社會,自漢以降,受佛教之薰染,已有千數百年。佛教之與中國,關系極為密切,舉凡社會諸大元素,如政治、文學、信仰、制度,莫不受其影響。是以今之歐洲人、日本人之治中國學者,常取材于我《釋藏》之中。余前讀諸學者之史地撰述,常因其中梵文名詞,感有滯礙。讀書時間,泰半消耗于尋求此項義解或漢譯古翻之中。茍能解其一義,識其一名,或別紙錄之,或標注于《翻譯名義集》各條之上。積之既久,略得其解。”
或正因切身體會到譯事之重要,故馮承鈞能埋頭苦干達數十年,即“病中握管維艱”,不得不“命兒子先恕筆受”,亦不中輟,以期用他國的歷史補本國之不足。后來,向達在悼念馮氏的文章中充滿感情地寫到:“近二三十年來孜孜不倦以個人的力量將法國近代漢學大家的精深的研究,有系統地轉法為漢,介紹給我們的學術界,使我們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特別是陳寅恪先生所謂的近緣學,如西域南海諸國古代的歷史和地學,能有一種新的認識新的啟發者,這只有馮承鈞先生!”“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有“純學者”③之譽的嚴耕望對馮氏的評價更高,他說:“馮承鈞先生畢生從事西文中譯的工作,把早期西方漢學家的幾十部重要論著翻譯成中文,讓一般不能通解原文的人都能閱讀運用,真是功德無量!我常常向同學們說,馮先生的學問當然比陳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對中國史學界的貢獻,決不在陳先生之下。”
近人胡文輝在其所著的《現代學林點將錄》一書中給百年來的學林英雄排座次,認為馮氏在學問上“盜寶西天”,堪比古希臘神話中盜火給人類的普羅米修斯,“論近人引進西學之功,在思想層面,嚴復自不作第二人想;在學術層面,則無出馮承鈞其右者”,故將馮氏喻為《水滸傳》中“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馮氏能于中外交通史領域獲得如許成就,并非偶然。
馮氏“年十七(光緒二十九年)得游學歐洲。十九考入比利時列日國立大學法學預科,翌年轉入法國巴黎大學法科,凡四年畢業。復入法蘭西學院,后于宣統三年歸國”,留歐約九年之久。由于筆者沒看到有關馮氏留學生涯的原始材料,這里只能結合馮氏和他人的敘述予以揣測:留歐期間,馮氏對翻譯和研究工作必備的科學方法和語言文字均下過苦功。
馮氏對國人因缺乏科學方法而未能充分利用我國的巨量史籍甚為痛惜,曾云:“吾國之史籍釋藏,為今日學界無比之鴻寶。顧其過去之效用,僅供文人尋求掌故及信奉誦習之需而已。鮮有用科學方法從事整理者。”又云:“乃今日歐洲日本學界以科學方法治佛學者紛紛,而國人應之寥寥,洵可恥也。”所幸的是,馮氏自己本為研究法律之人,“曾受嚴格之社會科學訓練”,這種訓練恰恰是其他研究者所缺乏的。
不獨如此,他很早就努力掌握進行譯介和研究所需的語言文字。馮氏本人曾謂:“比年以來,予從事于我國史部外國史料之鳩集,舉凡載籍之舊文,西儒之新撰,視力之所能,皆網羅之,翻譯之,有時旁涉及于素所未習之語言之學,梵天之書。”在談到修改《元史》時,馮氏認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一是“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語言”;二是“明了漢字古讀,尤應知元人讀法”;三是“名從主人”。朱杰勤認為,馮氏“據《元秘史》、《親征錄》、《元史》及多桑、巴兒脫德、伯希和撰諸書,寫成《成吉思汗傳》,其名稱考訂確有特出之處”。據向達講,“他在法國學問興趣旁及于語言文字以及西域南海有關的歷史地理,因此搜羅的各種語言的字典文法之類的書籍甚多”,應該說,正是早期的這種努力,使他逐步習得了多種語言,能超越馮氏者,或陳寅恪一人而已。
在《占婆史·譯序》中,馮氏寫到:“昔之四裔,浸染中國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今之境地相接,而隔塞最甚者,亦莫逾越南。昔日交廣并稱,其地原為中國南服。不幸誤于交州牧守之貪利侵刻,始而自立,終為法國所據,致使書同文行同倫之華化民族淪人異國,良可慨矣。”在《鄭和下西洋考》序言中,馮氏也寫到:“西方史書言新地之發現者,莫不盛稱甘馬(Vasco da Gama)、哥倫布(Columbus)等的豐功偉業。就是我們中國人編的世界史,也是如此說法。好像在講座中很少有人提起在這些大航海家幾十年前的中國航海家鄭和。這真是數典而忘祖了。”因此,馮氏之致力于譯著事業,亦可視為胸中積郁的民族情緒的一種發抒。
當然,馮氏能取得如此成就,也和他對各種史籍的熟諳密不可分。關于這一點,只需看其譯著的種類便可明白,此處不再贅言。
馮氏在翻譯方面成績卓著,其著述亦復不少,諸如《景教碑考》、《西域地名》、《歷代求法翻經錄》、《元代白話碑》、《王玄策事輯》、《成吉思汗傳》、《中國南洋交通史》,以及《瀛涯勝覽校注》、《星槎勝覽校注》、《海錄注》、《諸蕃志校注》等。
《成吉思汗傳》初版于一九三四年,初名《成吉思汗事輯》。馮氏在該書緒言中談到其撰述的緣起:一是以往“修《元史》者對于成吉思汗之事跡遺漏甚多”;二是新修改篡者雖史事增多,也參照西書對年代進行了改訂,但仍有重大缺陷,就是“支離則較舊史更甚”,尤其是對大量漢語外的地名、人名缺乏考訂,“其穿鑿附會,竟使任何聲韻皆可相通”,致使“歧互更較舊史為難讀”,誤人甚深。有鑒于此,馮氏乃據中國史籍《元秘史》、《親征錄》、《元史》,以及西方多桑(C.dOhsson)所著的《多桑蒙古史》、巴兒脫德(Barthold)所著的《蒙古侵略時代之突厥斯單》(第二版英譯本)、伯希和(Pelliot)考訂諸文等,詳加考訂,撰成此書。
全書除緒言外共有十一章,首先扼要介紹了成吉思汗的身世,既而梳理了成吉思汗崛起對諸部落整合的情況,最后記述了成吉思汗西征與去世的經過。全書對史實、地名、人名的考訂比較精審,脈絡亦甚分明,持論比較平實,是成吉思汗傳記諸種版本中不可多得的一種。 該書的版本情況大致如下。一九三四年四月,本書作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史地小叢書”之一首次出版,為繁體豎排;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第二版;一九四五年一月,內遷到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在渝出版第三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作為“新中學文庫”之一種出版第四版。二〇〇九年,中國三峽出版社將此書收入“四為書系”,以簡體橫排出版,書中配有插圖多幅。同年,東方出版社也出版了該書的簡體橫排版(和張振珮所著的《成吉思汗評傳》合刊)。
一九六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將此書列入“史地叢書”出版(平裝),是謂“臺一版”;一九六六年出版“臺二版”。一九六九年,該館再次出版此書,一九八一年此書被收入該館的“人人文庫”出版。
此次出版,以一九四七年繁體豎排版為底本,參考他本和相關史籍,加以點校,以簡體字橫排出版。點校時遵循以下原則:
一、全書采用現代通用標點符號;
二、對于人名、地名譯音,以及人名、地名改為簡體字易引起誤解者,均仍其舊,存其原貌;對于錯字、別字,于腳注中注明,以便參照;
三、人名、地名不一致者,均予以統一;
四、對底本中漫漶不清者,以及他本中脫漏之處,皆參考有關資料予以補充、校正。
五、對書中的人名、地名、(包括山脈、河流、湖泊、海)、朝代名、部族名等,下加橫線,以便閱讀。
由于水平有限,舛誤在所難免,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王紅軍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馮承鈞(一八八七一一九四六),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漢口)人。曾赴比利時、法國留學,歸國后適逢辛亥革命發生,被任命為湖北都督府秘書。一九一三年任眾議院秘書,后轉為教育部僉事,凡十五年,其間歷兼北京大學講師及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一九二九年任立法編纂委員。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九年被聘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編輯。后被聘為臨時大學第二分班史學系教授,專任中亞交通、西北史地、蒙元史等課程。一九四六年病逝。
與其年壽相比,馮氏在史地翻譯領域的成就可謂厚重。
馮氏去世后,王靜如撰有《馮承鈞先生事略》一文,內云馮氏“譯著等身”,其“譯述名著之多,實達近三十年來之最高峰”,“一生譯著不下百數十種,約五百萬言,其中關于法學書籍,多未刊印;而中國文史之譯作,其行世者,即約三四十本”。堪稱馮氏知交的向達在《悼馮承鈞先生》中也提及,馮氏“翻譯以及自著的專書和論文甚多”,雖然“昆明方圖能夠看到的不過一二十種”。另一位和馮氏“并無奉手之雅”,但對馮氏“素具仰止之忱”并將其列為自己“所佩服的前輩之一”的朱杰勤,出于仰慕和哀悼,給馮氏的譯著列了個自認為“未敢認為完備”的清單,其中載馮氏譯著共四十二種。以傳世諸書驗上述諸人的記載,便知所言不虛。即以今日眼光視之,其譯著數量亦屬可觀。
王靜如還談到,馮氏“譯文流暢,用詞正確,治史學者莫不欽服”,“每有新意,皆極精確,尤以論疏勒為西方所從出,實發前人所未發,允為最近得意之作也”。朱杰勤于馮氏去世兩星期后記下了自己的感觸,認為“馮先生是第一流的翻譯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違原本。間遇罕見之名詞,又為之厘定漢名,斟酌至善”,還將馮氏與嚴復和林紓放在一起月旦一番,認為就翻譯技術而論,馮氏要居于嚴、林之上。他說:“但就翻譯成績而論,馮先生是近代第一流翻譯家。清末翻譯界中嚴復(幾道)與林紓(琴南)并稱,但因時代關系,他們的翻譯技術尚未達到完美地步,持較馮先生,則他們好像椎輪,而馮先生好像大輅了。”以后人的眼光來看,這種評價或有溢美成分,但能獲得識與不識者如此交口稱贊,則其譯著的質量和水準之高應不難想見。
關于譯介的重要性,馮氏曾有這樣一段論述:“吾人研究本國史,姑就書本一方面言,常感史部紀事編年之書,未能完全滿足學者之需要。有無數問題之解說,不得不于史部以外書中求之。檢尋古今書目,屢見非史部之書,而可供參考之用者不少,《釋藏》其一種也。吾人之社會,自漢以降,受佛教之薰染,已有千數百年。佛教之與中國,關系極為密切,舉凡社會諸大元素,如政治、文學、信仰、制度,莫不受其影響。是以今之歐洲人、日本人之治中國學者,常取材于我《釋藏》之中。余前讀諸學者之史地撰述,常因其中梵文名詞,感有滯礙。讀書時間,泰半消耗于尋求此項義解或漢譯古翻之中。茍能解其一義,識其一名,或別紙錄之,或標注于《翻譯名義集》各條之上。積之既久,略得其解。”
或正因切身體會到譯事之重要,故馮承鈞能埋頭苦干達數十年,即“病中握管維艱”,不得不“命兒子先恕筆受”,亦不中輟,以期用他國的歷史補本國之不足。后來,向達在悼念馮氏的文章中充滿感情地寫到:“近二三十年來孜孜不倦以個人的力量將法國近代漢學大家的精深的研究,有系統地轉法為漢,介紹給我們的學術界,使我們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特別是陳寅恪先生所謂的近緣學,如西域南海諸國古代的歷史和地學,能有一種新的認識新的啟發者,這只有馮承鈞先生!”“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有“純學者”③之譽的嚴耕望對馮氏的評價更高,他說:“馮承鈞先生畢生從事西文中譯的工作,把早期西方漢學家的幾十部重要論著翻譯成中文,讓一般不能通解原文的人都能閱讀運用,真是功德無量!我常常向同學們說,馮先生的學問當然比陳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對中國史學界的貢獻,決不在陳先生之下。”
近人胡文輝在其所著的《現代學林點將錄》一書中給百年來的學林英雄排座次,認為馮氏在學問上“盜寶西天”,堪比古希臘神話中盜火給人類的普羅米修斯,“論近人引進西學之功,在思想層面,嚴復自不作第二人想;在學術層面,則無出馮承鈞其右者”,故將馮氏喻為《水滸傳》中“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馮氏能于中外交通史領域獲得如許成就,并非偶然。
馮氏“年十七(光緒二十九年)得游學歐洲。十九考入比利時列日國立大學法學預科,翌年轉入法國巴黎大學法科,凡四年畢業。復入法蘭西學院,后于宣統三年歸國”,留歐約九年之久。由于筆者沒看到有關馮氏留學生涯的原始材料,這里只能結合馮氏和他人的敘述予以揣測:留歐期間,馮氏對翻譯和研究工作必備的科學方法和語言文字均下過苦功。
馮氏對國人因缺乏科學方法而未能充分利用我國的巨量史籍甚為痛惜,曾云:“吾國之史籍釋藏,為今日學界無比之鴻寶。顧其過去之效用,僅供文人尋求掌故及信奉誦習之需而已。鮮有用科學方法從事整理者。”又云:“乃今日歐洲日本學界以科學方法治佛學者紛紛,而國人應之寥寥,洵可恥也。”所幸的是,馮氏自己本為研究法律之人,“曾受嚴格之社會科學訓練”,這種訓練恰恰是其他研究者所缺乏的。
不獨如此,他很早就努力掌握進行譯介和研究所需的語言文字。馮氏本人曾謂:“比年以來,予從事于我國史部外國史料之鳩集,舉凡載籍之舊文,西儒之新撰,視力之所能,皆網羅之,翻譯之,有時旁涉及于素所未習之語言之學,梵天之書。”在談到修改《元史》時,馮氏認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一是“了解北方西方若干語言”;二是“明了漢字古讀,尤應知元人讀法”;三是“名從主人”。朱杰勤認為,馮氏“據《元秘史》、《親征錄》、《元史》及多桑、巴兒脫德、伯希和撰諸書,寫成《成吉思汗傳》,其名稱考訂確有特出之處”。據向達講,“他在法國學問興趣旁及于語言文字以及西域南海有關的歷史地理,因此搜羅的各種語言的字典文法之類的書籍甚多”,應該說,正是早期的這種努力,使他逐步習得了多種語言,能超越馮氏者,或陳寅恪一人而已。
在《占婆史·譯序》中,馮氏寫到:“昔之四裔,浸染中國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今之境地相接,而隔塞最甚者,亦莫逾越南。昔日交廣并稱,其地原為中國南服。不幸誤于交州牧守之貪利侵刻,始而自立,終為法國所據,致使書同文行同倫之華化民族淪人異國,良可慨矣。”在《鄭和下西洋考》序言中,馮氏也寫到:“西方史書言新地之發現者,莫不盛稱甘馬(Vasco da Gama)、哥倫布(Columbus)等的豐功偉業。就是我們中國人編的世界史,也是如此說法。好像在講座中很少有人提起在這些大航海家幾十年前的中國航海家鄭和。這真是數典而忘祖了。”因此,馮氏之致力于譯著事業,亦可視為胸中積郁的民族情緒的一種發抒。
當然,馮氏能取得如此成就,也和他對各種史籍的熟諳密不可分。關于這一點,只需看其譯著的種類便可明白,此處不再贅言。
馮氏在翻譯方面成績卓著,其著述亦復不少,諸如《景教碑考》、《西域地名》、《歷代求法翻經錄》、《元代白話碑》、《王玄策事輯》、《成吉思汗傳》、《中國南洋交通史》,以及《瀛涯勝覽校注》、《星槎勝覽校注》、《海錄注》、《諸蕃志校注》等。
《成吉思汗傳》初版于一九三四年,初名《成吉思汗事輯》。馮氏在該書緒言中談到其撰述的緣起:一是以往“修《元史》者對于成吉思汗之事跡遺漏甚多”;二是新修改篡者雖史事增多,也參照西書對年代進行了改訂,但仍有重大缺陷,就是“支離則較舊史更甚”,尤其是對大量漢語外的地名、人名缺乏考訂,“其穿鑿附會,竟使任何聲韻皆可相通”,致使“歧互更較舊史為難讀”,誤人甚深。有鑒于此,馮氏乃據中國史籍《元秘史》、《親征錄》、《元史》,以及西方多桑(C.dOhsson)所著的《多桑蒙古史》、巴兒脫德(Barthold)所著的《蒙古侵略時代之突厥斯單》(第二版英譯本)、伯希和(Pelliot)考訂諸文等,詳加考訂,撰成此書。
全書除緒言外共有十一章,首先扼要介紹了成吉思汗的身世,既而梳理了成吉思汗崛起對諸部落整合的情況,最后記述了成吉思汗西征與去世的經過。全書對史實、地名、人名的考訂比較精審,脈絡亦甚分明,持論比較平實,是成吉思汗傳記諸種版本中不可多得的一種。 該書的版本情況大致如下。一九三四年四月,本書作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史地小叢書”之一首次出版,為繁體豎排;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第二版;一九四五年一月,內遷到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在渝出版第三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作為“新中學文庫”之一種出版第四版。二〇〇九年,中國三峽出版社將此書收入“四為書系”,以簡體橫排出版,書中配有插圖多幅。同年,東方出版社也出版了該書的簡體橫排版(和張振珮所著的《成吉思汗評傳》合刊)。
一九六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將此書列入“史地叢書”出版(平裝),是謂“臺一版”;一九六六年出版“臺二版”。一九六九年,該館再次出版此書,一九八一年此書被收入該館的“人人文庫”出版。
此次出版,以一九四七年繁體豎排版為底本,參考他本和相關史籍,加以點校,以簡體字橫排出版。點校時遵循以下原則:
一、全書采用現代通用標點符號;
二、對于人名、地名譯音,以及人名、地名改為簡體字易引起誤解者,均仍其舊,存其原貌;對于錯字、別字,于腳注中注明,以便參照;
三、人名、地名不一致者,均予以統一;
四、對底本中漫漶不清者,以及他本中脫漏之處,皆參考有關資料予以補充、校正。
五、對書中的人名、地名、(包括山脈、河流、湖泊、海)、朝代名、部族名等,下加橫線,以便閱讀。
由于水平有限,舛誤在所難免,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王紅軍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目次
書摘/試閱
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之傳說
蒙古人在十三世紀以前,好像不知有文字,所以以前的事跡全憑傳說,我們只能以傳說目之,不可認其為史實。這種傳說既憑口述,種類必多,可惜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有兩說:一說是《元秘史》所傳之說,蒙古源流之傳說也可附于此類;一說是剌失德丁書之傳說,《圣武親征錄》的傳說與剌失德丁書大致相同;可惜譯人將原文的卷首刪了,僅始于也速該,使我們不能將原書所傳之成吉思汗的先世取來對照剌失德丁書;《元史》世系表的傳說同此說大同小異,也可附于這一類;我們以后省稱前說為甲說,后說為乙說。
據乙說,成吉思汗誕生之兩千年前,蒙古民族被其他民族所破滅,僅遺男女各二人,逃避一地,四面皆山,山名額兒格涅昆;這個名稱我以為應改作),因為波斯文字不著韻母,難免沒有錯誤。我想就是現在的額爾古納河附近之一山崖,因為qun的本義猶言崖也。這部分的傳說,除開年代可疑外,似乎有點近類真相。《舊唐書》曾說有蒙兀室韋,《南齊書》中著錄有些鮮卑名稱,似出蒙古語,可以證明當時的蒙古居地在黑龍江上流同呼倫淖爾一帶,后來漸漸西徙,雖西徙,仍與弘吉剌、斡勒忽訥兀惕、亦乞剌思等部繼續通婚姻,而這些部落皆在也兒古納(額兒古納)水附近也。
乙說又云,避難的后人因地狹人眾,乃謀出山。先是其人常在其中采取鐵礦,至是乃積木以焚礦穴,鐵礦既镕,因辟一道,遂出山外,遷居到斡難、怯綠連、禿剌等水沿岸。這種捶鐵的傳說,同樹癭生子的傳說,北方民族多有之。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優惠價:87
115
絕版無法訂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