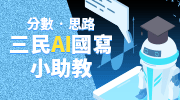美國陪審團制度(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11857705
出版社:中國法律圖書公司(法律出版社)
作者:(美)藍道夫‧約拿凱特
譯者:屈文生;宋瑞峰;陸佳
出版日:2013/12/01
裝訂/頁數:平裝/457頁
規格:20.8cm*14.6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屈文生
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出版專著《從詞典出發:法律術語譯名統一與規範化的翻譯史研究》、《普通法令狀制度研究》及譯著《歐陸法律史概覽:事件,淵源,人物及運動》、《中世紀的法律與政治》、《盎格魯-美利堅法律史》、《世界上偉大的法學家》等6部。曾在《歷史研究》、《中國翻譯》、《比較法研究》、《學術研究》等雜誌發表論文50餘篇。主持並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法律術語譯名統一與規範化研究》等。2010年被評為上海市曙光學者。
宋瑞峰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學士,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法律經濟學碩士。
陸佳
華東政法大學英語學士,北京大學法律碩士。
名人/編輯推薦
——哈利·威靈頓(已故),“耶魯當代法叢書”總編輯,耶魯大學斯特林教席榮譽教授,耶魯大學法學院、紐約大學法學院前院長
目次
目錄
凡例001
序001
致謝001
前言001
第一章概述00
第二章制約權力的濫用0
第三章挖掘事實0
第四章陪審團和社會價值觀0
第五章遵從決定0
第六章陪審團的規模及其表現
第七章一致同意與僵局陪審團
第八章鄰近地區
第九章最多元化的美國民主團體
第十章有因回避
第十一章無因回避
第十二章對陪審團進行“科學的”遴選
第十三章對抗制
第十四章證據的展示
第十五章指示
第十六章陪審團裁決與證據的核心作用
第十七章 陪審團對複雜案件的審判
第十八章陪審團否決
第十九章裁決的終局性
第二十章改革
索引
罪名及刑法、侵權法上術語譯法
譯後記
書摘/試閱
序vii
我那時很緊張,極度緊張。我作為紐約市的一名公設辯護人(public defender)僅僅執業了兩個月,可我卻即將經歷自己參與的首場陪審團審判。雖然我在紐約市法律援助協會(New York City Legal Aid Society)的這份工作使我在出庭自由發揮之前得到了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但我從未見過一場真正的審判。
兩名被告人所受的正式指控是“扒竊罪(jostling)”,這是紐約州法律規定的一項罪名,懲罰的是無謂地將手置於他人的口袋或錢包附近或裡面的人,旨在懲罰扒手。但是,起訴書(complaint)裡提到的卻遠非兩人的扒竊行為。那份文書指控兩人在波威裡街波威裡街(Bowery),又譯包厘街,是紐約市的一條街道,有許多廉價旅館和流浪者。——譯者注將一個人打得不省人事,並從其口袋中拿走了錢財。
除了提出指控的那段話外,我對該案幾乎一無所知。紐約州的法律甚至沒有規定我必須被告知檢方證人是誰,更不用說獲知他們將說些什麼了。我所能做的僅僅是按照我被教導的方式來行事。
在法官進入法庭之前,我試探性地喊出了起訴書中列出的被害人的名字,希望他能跟我談一談。viii沒有人答應。我提高聲音喊了一遍,還是沒有人答應。然後我喊“墨菲警官”(Officer Murphy),就是實施了逮捕的那名警官。有個胸前衣袋上晃著枚金徽章的男人示意我到外面去。
他對我說的頭幾句話怒氣十足。“我拼命工作才做到了警探。我是墨菲警探,不是警官。”在紐約市警察局的警銜序列中,警官(officer)為最低一級,警探(detective)比之高一級。——譯者注他幾乎是啐出最後一個詞的。隨後他告訴我,他當時一直在調查一起搶劫案的詳情,就在那時他看見我的當事人在扒竊一個醉漢。我問警探被害人在哪裡,他承認雖然自己多次去過被害人提供的住址——一家廉價旅館,但卻無法找到那名波威裡街的住戶。
我走進法院內部去和我的當事人談一談,他們待在羈押室(holding cell)裡。那兩個人都比一般的被逮捕者要年長許多,他們沒有交保釋金。他們的“前科檔案(rap sheets)”顯示了長長的逮捕記錄,而且雖然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我看過了數千份這樣的犯罪記錄,但兩名當事人中有一人的檔案中的一個條目是我今後再沒見到過的。20年前,他在印第安那州的韋恩堡因為流浪罪(vagrancy)被捕。雖然在那個時期這些記錄上很少會記載逮捕後的處理結果,但那條記錄上卻有。上面簡練地記著:“被送上前往芝加哥的公共汽車”。
兩名被告人中的一人走到羈押室的前部,透過柵欄對我說話,緊張地堅稱自己對於被控罪行一無所知,但希望進行辯訴交易(plea bargain)。可是地區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曾說過,要進行任何交易,必須要兩名被告人都認罪。另一名當事人平靜地坐在羈押室裡最遠的那個角落,讀著一本《聖經》。他在那兒語氣堅決地說:“我不認罪。如果這是犯罪,被害人在哪兒?”我對他解釋說,指控不會因為缺少被害人而被撤銷,而他僅僅重複道:“如果這是犯罪,被害人在哪兒?咱們上法庭去。”於是我們就上了法庭。
我之前可能設想過,會有某種威嚴或莊重的氣氛籠罩著陪審團審判,然而,《佩瑞·梅森》和《辯護人》裡的法庭跟這一個可不一樣。《辯護人》(The Defenders)是美國的一部法律題材電視劇。《佩瑞·梅森》(Perry Mason)是系列偵探小說名,後改編為電視劇及電影。——譯者注曼哈頓的輕罪陪審團審判(misdemeanor jury trials)是在狹小、密閉、幽深的房間裡進行的,陰暗的燈泡嗡嗡作響。那種氣味是電視永遠也沒法展現出來的。一部分氣味來自於一代又一代出庭前沒洗澡的軀體;另一部分則來自偶爾噴灑的地板消毒劑。氣味中還有其他成分,不過即使是在年復一年地走進這樣的房間之後,我也不敢說能猜出所有的成分。
那場審判的陪審團遴選(jury selection)過程我已記不太清了,同樣想不起來的還有檢察官和我自己的開場陳詞。那位警探作證講述了被告人是如何打了另一個人並拿走他的錢財的。在我的交叉詢問(cross-examination)中ix,我暗示員警所處的觀察點使其無法看見他聲稱看見的全部情況,不過我主要還是反復強調這個事實:假想的被害人並未對此案表示出興趣,而且無法被找到。警探是唯一的證人。
我的總結陳詞一定讓我的一名當事人很高興,因為它基本上是“如果這是犯罪,被害人在哪裡?”的各種變體。檢察官回應稱,法庭上很少會見到比這更一目了然的案情了。隨後法官告訴了陪審團他們作裁決時需要適用的法律,陪審團便開始商議(deliberate)。從審判開始算起到商議啟動最多過去了兩個小時。
大約45分鐘後,陪審團作出了裁決。書記員此處作者原文為“clerk”。在美國法中,“clerk”有多種含義。其中一種是標記法庭上負責整理文書、進行記錄等工作的職員(類似于我國法律中的“書記員”),另一種是表示由法學院學生或畢業生擔任的、輔助法官或律師進行法律研究、文書起草等工作的人員,常譯作“法官助理”。二者職能或有交叉。此處譯為“書記員”。——譯者注告訴我的當事人起立並面向陪審團。我的心在怦怦地跳著,我問自己:“我也要起立嗎?”沒有人告訴過我應該怎樣做。正當我擔心是不是要使自己陷入難堪的時候,陪審團主席(foreman)宣佈了第一個裁決。我沒聽見。不過當陪審團被問到第二名被告人如何時,我聽得很清楚,“無罪。”
我松了口氣。幾天以後,實施了逮捕的那名警探在法庭的一條走廊裡看見了我。他伸出了手。“律師先生,”他說,“我輸得心服口服。”這就是那場陪審團審判的內容嗎?它是員警和我之間的一場以陪審團作為裁判的較量嗎?
陪審團制度開始顯得比我所意識到的更為複雜和神秘。一方面,我覺得我的當事人的所作所為可能確實如那名員警所說,儘管我懷疑員警並未看見他聲稱自己見到的所有情況。另一方面,檢方無法證明搶劫罪成立,我認為檢方是在濫用關於扒竊罪的法律來指控被告人。根據制定法的表述,他們是有罪的,但是那個無罪裁決卻並不顯得不公正,或許它還可能是正確的。
幾周後我又到了法庭上。另一位律師和我為一位英格蘭裔和一位愛爾蘭裔移民辯護,他們被控企圖傷害(assault)另一位愛爾蘭裔移民。辯方主張那只是酒吧外的一場小衝突,但被害人給自己拍了裸體照片,表明自己遭到了一頓結結實實的痛毆。兩名被告人都供稱是被害人而非他們自己先動手的。陪審團對由另一位元律師代理的那名被告人作出了無罪裁決,但卻宣佈他們無法就我的當事人達成裁決。這看起來有些荒唐。證據顯示,要麼兩個人都有罪,要麼兩人都無罪。但是,另一位被告人之前從未被逮捕過,而我的當事人之前曾犯過企圖傷害罪。陪審團被告知,他們不得利用這一先前事件來做出我的當事人有暴力傾向、故而犯有所控罪行的判斷。法官倒是指示他們說,他們應當評估這一先前罪行是如何影響該被告人供稱自己沒有先動手時的可信度的。我並不十分肯定該項指示的含義,我也懷疑陪審員們是否能理解。x即便如此,當我克服了未能獲勝的失望之後,我意識到陪審團拒絕裁定我的當事人無罪的決定似乎並不是不公正的。
我沒有產生那種認為若沒有陪審團,這些審判會通過某些方式變得更加完善的看法。替代選項是什麼?僅有的選項是,要麼不進行審判,要麼進行法官審判(bench trial),即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由一名法官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不進行審判這個選項意味著進行辯訴交易。極少數法律糾紛是由某種形式的審判解決的。審判其實並不被視為文明的爭端裁決方式。相反,它們是種威脅。如果一方當事人不接受對方提出的解決條款,“咱們法庭上見”這種回答是個不好的兆頭。要做一名出色的出庭律師(trial attorney),往往倒並不意味著要在那些偶爾到了法庭上的案件裡表現出色,而是要在許許多多並不上法庭的案件中有效地進行談判。討價還價的最終籌碼總是審判。當然,如果一名律師不願出庭應訴或者不能很好地應訴,那麼進行審判這個威脅就沒有什麼威力了。不過,我很快就認識到,審判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確保大多數案件都會以調解或者辯訴交易告終。
我早期參與的一場法官審判使我認識到,這套制度往往會使那些真正希望進行陪審團審判的人洩氣。紐約人棄置傢俱的方式通常是把它們擺在大街上。路過的人可以在清潔車把這些棄置物清理掉之前查看它們並拿走自己想要的東西。我的當事人——姑且稱之為施瓦茨(Schwartz)——拿了一些棄置的桌椅。另一個人則說他自己早已主張了對它們的所有權,並說施瓦茨違犯了先占(first possession)這條街頭規則。吼叫和斥責升級成為一場爭吵。由於施瓦茨拒不讓步,另外那個人攔下了一輛警車,最終施瓦茨被控企圖傷害罪(assault)、盜竊罪(theft)和擾亂治安(disorderly conduct)。
施瓦茨堅稱自己沒有錯。當他獲知可以承認自己行為不檢(這並非刑事罪名)從而被判有條件釋放(conditional discharge)——實際上就是根本不判刑——時,他斷然拒絕了,並堅持要進行陪審團審判。可是,陪審團審判不是那麼容易安排的。曼哈頓只有兩個法庭可用於輕罪的陪審團審判,不過用於處理重罪的預審階段工作(preliminary matters)以及進行輕罪的辯訴交易的法庭則要多得多。只有在雙方顯然都真正做好了訴訟準備的情況下,才能將一起案件呈交至陪審團審判的法庭裡。這通常意味著雙方的證人都必須到庭。但是,如果他們都到庭了,該案件僅僅會被標記為可以開審。如果陪審團審判的法庭已經被其他審判佔用(通常都是如此),那麼該案件就會被推延至另一個日期,那時這一程式必須重新開始。
xi這一制度往往挫傷了其他被告人進行陪審團審判的意願。例如,一名被控盜竊汽車的年輕男子曾堅持進行陪審團審判。在我看來,他的辯護頗有說服力,有很大機會被裁定無罪。在3個月內,他5次嘗試確定自己的審判的日期,5次都失敗了。每一次嘗試時,為了去法院,他都得請假不去上班。他的執著使他損失了一周的薪水,而且他擔心再請假便會使他失去工作。當檢察官最後告訴我們,如果他認罪,他會被處以150美元的罰金,那名早已損失了比這多的薪水的年輕人終於讓步並認罪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偷車,他沒偷的可能性是頗高的。不過我明白為什麼就算他無罪,他也承認自己有罪。
施瓦茨則不同。為了安排他上法庭的日期,他得無窮無盡地來法院,但他還有三名證人——一位退休的男士、一位家庭主婦以及一位年輕的證券經紀人。每個人都目擊了那場爭執,而且都確認了施瓦茨的說辭。每個人都來過法院兩次,在一個法庭裡等了大半天,最後僅僅被告知當天不會進行審判了。當同一結果看起來就要在第三天發生時,證券經紀人告訴我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會再來了。當我看見那名母親點頭表示同樣的看法時(每次她來法院她都得請個保姆),我告訴我的當事人,我覺得我們有必要當天進行審判。這只有在被告人同意不進行陪審團審判而進行法官審判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我以為,如果他同意這麼做,案件會發送至羅根(Logan)法官處審理。我曾經參與過他主持的數場聽證會和一場法官審判,他看起來挺公正的。然而,羅根法官的案件負荷已經太多,他堅稱我的案件要被發送到其他人處。最後它被發送至沃爾夫(Wolfe)法官處。
許多律師,包括我的主管律師,都告訴我我犯了多大的一個錯誤。沃爾夫是出了名的脾氣暴躁和記仇。據說沃爾夫從未見過一個無罪的被告人,而且別人告訴我要檢查我的當事人的鞋子。故事是這樣的:一天晚上,沃爾夫看完歌劇回到家時,發現自己公寓的門半掩著。他看見客廳一片狼藉,這時又聽見自己的臥室裡傳來聲響。他在那裡看到窗戶大開,盜賊從消防梯逃走了。這位元法官所能看到有關那個盜賊的全部情況就是一隻穿著運動板鞋的腳。從那以後,這位法官就對每一名被告人都很嚴苛,尤其是對那些穿運動板鞋的人。
當我們往審判庭走去時,看到施瓦茨穿著一雙邋遢的便鞋,我算放了心。他的證人作證情況良好。我覺得很有把握,但當我進行總結陳詞時,法官似乎都沒在聽我說話。檢察官陳詞話音剛落,法官就嚴厲地宣佈:“第240條第20款罪名成立(guilty of two-forty-twenty)。”施瓦茨大聲叫嚷,xii法警沖過去制止他。在他繼續喊叫的時候,我拽住他,試圖向他解釋。法官只判定他擾亂治安罪名成立,法官判定他的盜竊和企圖傷害罪名不成立,不過他沒有明白地宣佈這一點。我的當事人還以為自己被判定所有罪名成立。
當我終於設法使施瓦茨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時,他嘟囔了一句:“陪審團永遠不會這麼做。”隨後,法官對被告人處以罰金,儘管如果他認罪的話他只會被判有條件釋放。也許在陪審團審判的情況下結果也會一樣,但這個結果對於被告人來說顯得不合理。施瓦茨的憤怒都指向了作出了判決的那一個人。
這個故事強調了每一名出庭律師都應當認識到的教訓。陪審團審判的替代選項是法官審判,而法官們並不是沒有感情的神。他們也是人,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地擺脫自己生活經歷的限制,他們披上法袍時都有意無意地承載著這些經歷。
後來,我繼續代理了一些被控以更嚴重罪名的當事人,也成為了其他出庭律師的主管律師。這些經歷教會了我一個被大多數刑事辯護律師所認識到的生活現實:陪審團大多數情況下會作出有罪裁決。這個事實可能會使我不再對陪審團制度抱有希望,但我還是一再為陪審員履職的嚴肅程度感到驚訝。人們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被挑選出來,受命擔任陪審員。多數人都不喜歡這個活兒,他們為了到庭必須作出犧牲。他們被要求做出關於一些他們不認識的人的決定,並評估一些他們永遠也不希望遇到的情境和遭遇。若這些普通公民一點兒也不關心他們被要求做的事,這是很好理解的。但他們其實會關心。不管我是否同意他們的決定,我都觀察到,陪審員們幾乎總是為做出正確的決定而苦苦思索。
這個事實由於少數例外而顯得尤為突出。最使我鬱悶的那個例外發生在一起搶劫案的審判中。一名女子走在布魯克林區
布魯克林區(Brooklyn),紐約市的一個區。——譯者注一個遍地瓦礫、樓房破敗的貧民區。兩個年輕男人從她身後沖上來,奪去了她的錢包,並把她推倒在地。她看見兩人逃進了一幢廢棄的樓房。她的喊叫聲使人報了警。她供稱自己一直盯著襲擊者的藏身之處,直到警方在那裡逮捕了被告人,接著她立即指認該被告人為罪犯之一。
我認為,交叉詢問證明了她幾乎無法觀察搶包者。他們是從後面沖上來的,xiii一人在她的一邊。她沒有回頭看,而且他們是在她前方跑掉的。我試圖展示,她頂多有可能是瞥見了兩人中一人的側面,而且儘管她堅稱自己持續地盯著兩人的藏身所,故他們不可能在不被自己發覺的情況下逃脫,但她無法解釋為什麼警方在該建築裡只發現了搶包者中的一人。
被告人是一名少年,他供稱警方逮捕自己的時候,他只不過是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幢建築裡玩耍。他發誓自己對搶劫案一無所知。受害人的錢包未能找到。
隨後我出示了自己認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被告人被發現時所處的建築並非搶劫者藏匿之處。受害人堅定地指認了一個地點。警方同樣堅定地說他們是在另一個地點找到被告人的。我出示了官方記錄,證明被告人被發現時所處建築距受害人所指的地點有相當的距離,兩座建築間並無連接結構。
我的主張是,受害人顯然是糊塗了,而且當她在警方拘留所裡看見戴著手銬的被告人時將他指認為罪犯之一,其實是很自然的,但這一指認是錯誤的,或者至少在其正確性上存有合理疑問。然而,陪審團不到一小時就作出了有罪裁決。陪審員離開的時候,我嘗試和他們中的一些人交談,以瞭解自己是怎麼失敗的。只有一個人停了下來。他對我說,我非常出色地履行了這樣一個明顯有罪者的代理工作。然後他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笑著說:“我們對你讓那座建築移動位置的辦法尤其感到敬佩。”他看上去像是期待著我會因為這個笑話笑起來。我沒有笑,他便大步走開了。我當然非常惱怒,因為我輸了,但我之所以惱怒,還因為他顯然沒有嚴肅認真地對待論據或事實。這種行為是我極少在陪審團中碰到的。
相反,我倒是發現絕大多數陪審員都盡職盡責。例如,一位陪審員在作出一項有罪裁決後的第二天到我的辦公室找到了我。警方說當一名警官敲公寓門的時候,另一名警官站在後面,並看到被告人把毒品丟到窗外。不過當時除了被告人外的其他人都在公寓裡,而指認了那名出現在五樓窗戶處的被告人的警官是從一個斜角看到被告人丟毒品的。該公寓並非被告人所有,我辯稱他們認錯了人。至少部分陪審員同意這一點,他們宣佈達成懸案陪審團。然而,法官請他們離場進行進一步商議。隨後陪審員們請求法官闡明“佔有”(possession)的含義。xiv法官告訴他們,法律所定義的佔有不局限於當場的、實體的控制。它還包括“推定佔有”(constructive possession),即任何人在存在毒品的場合都被推定佔有這些毒品。我提出反對,辯稱關於推定佔有的法律規則要求以認識到某物體存在並明顯控制它為要件。我被推定佔有我辦公室書架上的書,即使我並未實體佔有它們;但我的訪客則不佔有它們。然而,法官並未讓步,15分鐘後陪審團便宣佈了一項有罪裁決。
0
第二天,那名作出了有罪裁決的陪審員提出了抗議。“法官重新定義佔有之後,我就別無選擇了。我不認為您的當事人扔出了毒品,但法官所說的話使我別無選擇。昨晚我沒法入睡,一直想著那個孩子。”
因為陪審員幾乎總是努力作出正確的裁決,所以在我不認同裁決結果的那些案件中,我不會問:“你們這幫人出了什麼問題?”我倒是會問:“哪些資訊是我沒能出示的?”“哪些問題是我沒想過要問的?”“哪些論據是因為我的疏忽而沒能提出的?”在一些案件中,我意識到其結果並不是由我或者陪審團的失誤導致的,而是由陪審團所獲知的法律所決定的。
這一結論並不意味著我就不關心誰擔任陪審員。我和其他出庭律師一樣,對此非常關心。在每一起案件中,誰會成為一名好的陪審員,誰會成為一名不好的陪審員,我有著自己的看法,而且我會根據這些看法來行使無因回避請求(peremptory challenges)。我們工作時對於獲召擔任陪審員的人所知極少,也沒有陪審團遴選顧問(jury consultants)來告訴我們誰會成為一個理想的陪審員。我們會瞭解到一個人的年齡、種族、性別以及他與執法機關和犯罪受害者的關係。我們會試圖從職業、教育程度和居所周邊環境等資訊中推斷出其經濟狀況。我們可能會從一個人的姓名中猜測其種族。我們會嘗試著從衣著、說話方式以及隨身帶的報紙等“線索”中作出推斷。我們會分析回答問題時的猶豫以及眼神接觸。但通常所有這些資訊都只足以讓我們將候選陪審員分成模式化的類別。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所生活的法律行當中是允許律師任意進行模式化分類的。種族和性別通常是主要的分類標準。例如,在一場審判中,已選出了11位陪審員,檢察官和我都尚未用完無因回避請求權。每當一名黑人被提名擔任最後一位元陪審員時,檢察官都會行使無因回避請求;而每當一名白人被提名時,我都會做同樣的事。這種情況持續到我們中的一方用盡了分配到的無因回避請求權。或許我們一直相信著直接詢問、xv間接詢問和總結陳詞的力量,以及法官所說的話的重要性,但我們也極為相信陪審員身份的重要性。
在那段較早的時期,我和其他人之所以重視陪審團遴選(jury selection),不僅僅是因為我們都認為陪審團的組成可能會影響到其決定,還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決定可能極其重要。每一次當我看見圍欄後面那個幾分鐘前剛被陪審團裁定有罪者的臉時,我都會記起上述事實。而且我會永遠記得那個在被陪審團裁定有罪後跳上十層樓處的窗臺的那個人。他失去了平衡,墜落致死。
到20世紀80年代我不再常規地代理案件時,我對陪審團制度已有了許多看法,這些看法並不總是一致的。具備更優證據的那一方通常會在陪審團審判中勝訴,但陪審團的組成可能至關重要也仍是一個事實。陪審員們主要受常識和邏輯的影響,但有時一場煽情的發言倒是最佳策略。那些不夠聰明或教育程度不高、無法理解複雜問題的陪審員可以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帶入這項任務中,這使得他們具備的知識通常比任何法官所具備的都要更有價值。一般來說,要想做出正確的決定,陪審團比法官更值得信任,但也不能在每一起案件中都信任陪審團。
從那時起,我積累了更多的關於陪審團的認識,它們改變了我的看法,也體現在了這本書裡。我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的案件進行了探討。我展示了陪審團制度的發展史,同時探討了其他國家是如何解決法律糾紛的。我考察了探究陪審團決策過程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書中還納入了從陪審員、法律評論者和小說、電影及報紙社論等大眾文化的視角對陪審團制度的看法。
經歷和研究引導我得出了關於陪審團制度的幾個核心結論,得出這些結論的理由我會在本書中進行闡述。第一個結論看起來無甚新意:陪審團制度十分重要。它不僅對於要由陪審團來決定其糾紛的訴訟者來說重要,而且對於要受這些決定影響的更大範圍的社會來說也很重要。陪審團之所以重要,還因為他們在美國的政府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個結論或許會令人吃驚:當前的美國陪審團制度運轉甚佳。陪審團在做決定時要比許多人設想的更為理性。我認識到人們,包括執業生涯早期的自己,總是過高地估計了諸如陪審團的組成、律師的表現等因素對審判結果的影響。事實是,向陪審團出示的證據是決定裁決結果的首要因素,這是陪審團制度運轉甚佳最核心的原因。
xvi第三個結論是,儘管陪審團制度運轉甚佳,但它還有改進的空間。既然陪審團的裁決是根據出示的證據所作出的,產生更好的陪審團裁決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改善陪審團所獲取並需要考慮的資訊——即改善向陪審團出示的證據。
我希望本書能使人們更好地理解陪審團制度、該制度的運轉方式、它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它在美國法律與社會中的根本性地位以及它的優缺點。這些認識可能會製造出一個還要更好的陪審團制度。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