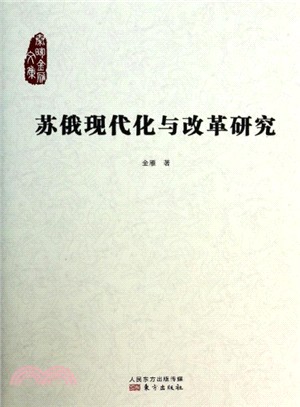商品簡介
傳統、改革與革命,俄羅斯走過的路的確是令人浩嘆的。在現代化進程中,俄國人也曾有過通過公正的“分家”擺脫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權利、個性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的沖動,尤其當反對派運動以自由主義一社會民主主義為主流、而當局又由開明改革派主導的時候,這種沖動曾經有過通向成功的良好機遇。但俄國人未能把握這一機遇。隨著“要否分家”之爭被“如何分家”之爭所取代,不公正的將分家”方案擊敗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場家長霸占家產驅逐子弟”的改革贏來了一時的繁榮,卻種下了不祥的種子,當反對派運動主流轉為民粹主義,而當局則扮演“貪婪的家長”角色時,建立公民社會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為滿足的自由派丟棄了公正的旗幟,也就埋下了為“貪婪的家長”殉葬的伏筆。
于是當危機爆發時,“重建大家庭”便成洶涌大潮,此時再談如何“分家”已不合時宜,回歸公社世界勢成必然,剩下的問題只是誰來當新的“公社之父”?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出奇制勝的一幕,但對俄國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70多年后俄國人又重作努力,試圖跳出歷史的怪圈。然而,別人會不會又跳人這個怪圈呢?
作者簡介
目次
《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再版序
自序
“富農問題”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蘇聯“富農”為“資產階級”說質疑
農村階級分析方法的源流與“富農”成分劃定標準
集體化前“富農”的經濟地位與階級屬性
農村“分化”的性質與允許“富農經濟”發展的政策
20年代蘇聯關于“農村分化”問題的統計學研究
農村分化統計研究的發展階段及特點
“動態研究”學派與“預算研究”學派
涅姆欽諾夫的統計學成就
蘇聯1927-1928年度的糧食危機
“供”的太少還是“求”的太多
糧食危機與“富農”問題
糧食危機與商品荒
糧食危機與價格政策
蘇聯集體化前夕富農經濟“自行消滅”問題
1928-1929年問對富農的政策
富農經濟的“自行消滅”
富農標準的下降與“富農”隊伍的擴大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典型實踐:蘇聯集體化時期的“消滅富農”運動
從“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到“貢稅論”
“消滅富農”與全盤集體化
“消滅富農”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
蘇俄歷史觀之重構
俄羅斯傳統文化與蘇聯現代化進程的沖突
俄羅斯的村社文化傳統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進程的沖突
“西學東漸”與村社制度的復興
在文化沖突中重構蘇聯史
19世紀俄國的“離土不離鄉”:身份性農民的非農化浪潮
“公社世界”的危機與身份壁壘
農民等級中的“邊緣人”
身份制的廢除與“離土不離鄉”的消失
從奇吉林到魯多爾瓦伊:公社傳統與俄國近代史的“怪圈”
奇吉林事件:向束縛者企求保護的農民
魯多爾瓦伊事件:更強大的“保護”與更嚴酷的束縛
魯多爾瓦伊之后:極端的“保護”與極端的束縛
民粹主義:俄國與世界,昨天與今天
民粹主義的幽靈在世界徘徊
歷史上的“革命民粹主義”與“警察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雙向異化
轉型危機中的精英與大眾
斯托雷平改革與村社復興運動
“分家”:瓦解“公社世界”
改革的原則與特點
改革的成果與影響
改革走向反動
“路標”改變以后:世紀初沙俄改革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悲劇
沖破公社世界,呼喚市場與憲政
1905年風波:自由主義反對派與政府開明派的雙輸之局
“反動時期”的“徹底改革”與自由主義的大尷尬
“路標”改變之后:俄國社會運動的“缺席”者
“保守化”的精英與“激進化”的大眾
“雪崩”、“人民專制”與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末日
傳統、改革與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再認識
傳統俄羅斯:三位一體的“公社世界”
政治專制下的經濟改革:“斯托雷平奇跡”的甜頭與苦果
“公社世界”的復興:“反傳統”還是“超傳統”
1917年革命還是“十月革命”
政治風云與蘇聯地名學
俄國地名政治性更改的傳統
第一次地名更改風潮
第二次地名更改風潮
第三次地名更改風潮
第四次地名更改風潮
城頭變幻大王旗:政治氣候的晴雨表
書摘/試閱
“富農問題”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按照通常說法,蘇聯的意識形態要求在農村中消除兩極分化,解決貧富矛盾。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盤集體化就是在這種思路引導下發生的“過火”、“冒進”之舉,是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左”傾錯誤。但已有學者指出,消滅剝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并非這場運動的真正思想動因。據查,在“大轉變”前的一年里斯大林13次提到集體農莊的好處,其中只有一次原則性地講到集體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制度,其余講的都是集體農莊能夠大量提供廉價“商品糧”,而這是國家不可能從小農那里弄到的。實際上,“集體化—消滅富農”運動正是在1927—1928年糧食收購危機、國家從小農那里采用“非常措施”強購廉價糧而遭到消極抵制之后才發動的,它的“原始積累”性質顯然比一般的烏托邦狂要實在得多。
全盤集體化就是要把農民編制起來提供“原始積累”。顯然,它與農村中是否發生了貧富差異并沒有什么關系。更與農村中是否有“資產階級”毫不相干。哪怕當時的小農是“一拔齊”地全無差別,只要國家需要“原始積累”,他們就必須被編制成集體農莊,而為了壓制他們的反抗,并為集體農莊本身提供積累,“消滅富農”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富農”作為一種經濟類型已經“自行消滅”以后還會有如此規模的“消滅富農運動”。
蘇俄歷史觀之重構
“在堅持俄國的公社制度方面,極左與極右離奇地結合起來”。最“革命”的民粹派與最反動的“警察”都在大力鼓吹集體主義、米爾精神、公社制和“共耕制”,極力抵制“個人主義”與自由財產,都力圖維護俄羅斯“國粹”而反對“西方瘟疫”,并且為實現這一切又都寄希望于農民,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歷史的怪圈。
社會主義國家目前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反思運動,從批評領袖個人及個別政策的錯誤,到對理論、制度模式的反省。而對于中蘇等國來說(與因蘇軍占領而“輸入”社會主義的東歐諸國不同),追溯舊模式的社會—文化根源,對舊模式中反映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進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稱為反思的第三階段,也是更為深刻的階段。這一階段在我國已全面展開,在蘇聯自1987年起也已為少數思想敏銳者所提出。但背著“發達的超級強國”包袱、國內民族問題又十分尖銳的蘇聯,進行這種反思顯然比已在民族危機中掙扎了100多年的中國更困難。西方學者對此雖然注意較早,但出于反社會主義偏見,往往簡單地把“斯大林現象”與歷史上的沙皇專制作類比,因而也難以科學地看待這一問題。
我國與蘇聯革命前同是不發達國家,有某些類似的文化傳統,又長期實行蘇式體制,因此這個問題對我國目前的改革與反思運動也有重大意義。作為外國人研究俄羅斯傳統有困難的一面,但也有“旁觀者清”的優勢,不受俄國民族情緒和西方反社會主義偏見的影響,科學地認識蘇聯歷史的傳統文化之根,應該是可能的。
轉型危機中的精英與大眾
1906年俄國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歷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會規則,它是以權貴利益本位為出發點,貴族、地主、富農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貧弱階層承擔改革的代價。這種不公正競爭的力量與反競爭的“公正”要求不斷積累,最終使沙俄與改革均被葬送,俄國歷史遂轉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改革期間把“路標”轉向“保守主義”的自由知識分子,則成為這一轉向的犧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國的反對派運動逐漸由自由主義運動變成了民粹主義運動,由知識分子運動變成了工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與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了與貪官污吏類似的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極度下降,引導與影響公眾的能力也大為削弱,以至于運動一起便無人能加以約束,出現不“嘩眾”便不能“取寵”的態勢,“激進比賽”也就勢不可免。
“革命”意識形態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與社會上革命(動蕩)因素的增加與躁動形成了強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公,還削弱了社會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強者”哲學與“官方個人主義”打碎了傳統道德秩序,也沖毀了公社精神、教會集體主義所烘托起來的沙皇作為共同體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眾對“皇權”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們不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規范的耐力資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義失落的同時,“亂世心態”卻在滋長,形成了某種一哄而起,趁亂發泄的心理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進主義”的宣傳造成秩序的解體,而是秩序的解體造成了一種嘩眾取寵的“激進比賽”,而這種比賽的終點線便是“公社世界”復興加上“人民專制”的確立。
……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