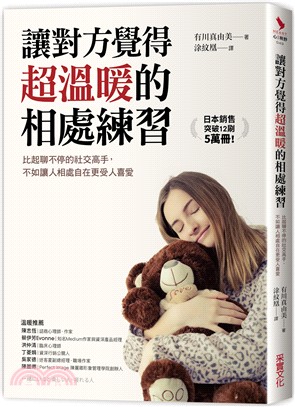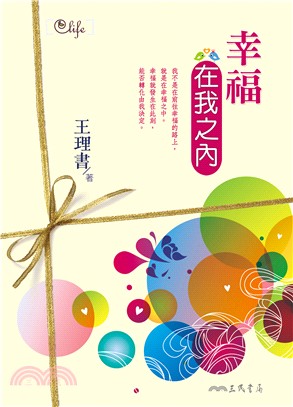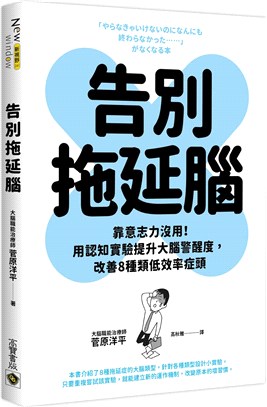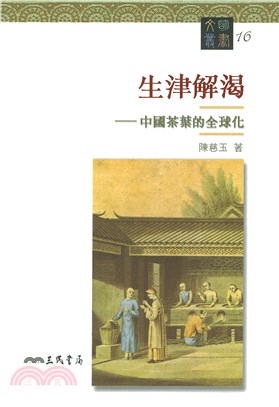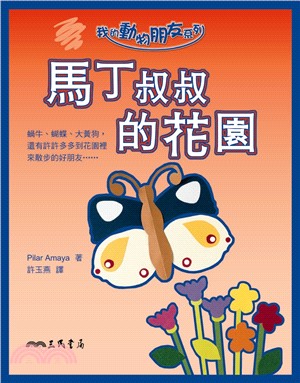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讀愛因斯坦全集,追蹤一代科學偉人的思想和生平,領略科學和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深遠影響,《愛因斯坦全集》是國際科學史界有史以來最有雄心的一項大工程,它不僅填補科學史上的一些空白,而且澄清一些廣為流傳的訛誤,其學術價值和文化積累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愛因斯坦全集》是目前研究愛因斯坦最權威,最全面的資料。
目次
文檔列表
插圖列表
介紹性資料
第10卷簡介
本系列的編輯方法
致謝
翻譯注釋
檔案來原始程式碼符號;
縮寫符號
文獻
補充書信1909-1920
書信,1920年5-12月
文獻清單的字母索引
記事表(日程表)
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引證索引
勘誤
書摘/試閱
第10卷導言
本卷,收錄了465份信件,共分為兩部分。
該卷上半部分收錄了211封信件。這些信件是對已發表在第5,8,9卷,寫於1909.5-1920.4月的信件的補充。其中:124封信,大部分出自愛因斯坦之手,這些來自遺贈的家庭信件,全部保存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愛因斯坦檔案庫裡,由Margot Einstein(1899-1986年)保管。她確保了這些信件在她去世後的20年裡一直沒有公之於眾; 66份信件來自於蘇黎世中央圖書館的手稿收藏室,由Gina Zangger(1911-2005年)收藏;還有21份信件從其他收藏處獲得。
該卷下半部分收錄了254份信件的全文,這些信件是從1920年5月到12月期間共614份現有的信件中選取的。編輯選取的這些信件,力求對理解愛因斯坦的工作和生活均具代表性和重要性。不作全文刊登,而只有摘要的信件,在本卷的末尾按時間順序有詳細清單。
1909年到1920年的信件刊登在本卷的第一部分,這些信件為讀者研究愛因斯坦的個人生活與學習,以及瞭解他與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素材。本卷不包括愛因斯坦與Mileva Maric之間的在1903年結婚之前的早期的信件,它們都收錄到了已出版的第1卷之中。之後所能獲得的家庭書信都刊登在本卷裡,包括:愛因斯坦親自寫給Mileva Einstein-Maric的信,還包括寫給他在蘇黎世的兩個兒子Hans Albert 和 Eduard,以及少量的寫給他在柏林的堂妹Elsa Einstein的信。 Elsa Einstein 在1919年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
本卷還首次刊登了Hans Albert 和 Eduard Einstein寫給愛因斯坦的書信;也是自第1卷來,第一次刊登Mileva Einstein-Maric寫給愛因斯坦的書信。由愛因斯坦在1916年4到1919年10月撰寫的書信,主要是以明信片的形式寫給Elsa Einstein的。這期間,他們的信件很少保存下來,最大的可能,是因為早在1912年4月,愛因斯坦就承諾要“永遠銷毀” Elsa Einstein的信(見卷五,文檔389)。其次,大量的信件是愛因斯坦寫給Heinrich Zangger的。
愛因斯坦在蘇黎世和柏林家庭成員的補充函件,以及與Zangger之間的信件,都已經在以前的卷裡出版。總之,這種材料讓讀者可以更豐富和更全面地瞭解到愛因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得不面臨的個人生活和許多困難,以及它所帶來的後果:疾病,營養不良,經濟憂慮,分居,離婚,以及再婚等。
此外,補充書面信件還包括愛因斯坦在1909年和1910年間寫給數學家Vladimir Varicak的9份信件,他是一位與愛因斯坦在相對論長度收縮認識論上有過公開爭論的人(愛因斯坦1911f [第3卷,文檔22])。 Varicak對用相對論來解釋Lobachevsky’幾何感興趣。愛因斯坦的信件主要致力於解決如何為一個作非均勻旋轉運動的剛體做相對論定義的問題。
本卷第二部分刊登的家庭信件中,主要描述了在1920年的最後8個月裡,愛因斯坦的一些個人生活的新資料,例如他與他的兒子在德國南部的第一次休假,以及他嘗試將他在蘇黎世的家搬到這裡等。還有少量的Elsa Einstein的信件,讓我們可以看到,在Elsa Einstein自己的眼裡,她與愛因斯坦的關係。
本卷的第二部分還為讀者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有助於理解在此期間愛因斯坦所集中思考的若干科學問題,包括他與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德國與荷蘭)的物理學家,一定程度上還包括美國的物理學家之間的聯繫,以及他在德國以及在荷蘭、丹麥、挪威旅行時所作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講稿。這些材料為我們清楚地揭示了愛因斯坦在新獲名人地位、隨之進入社會公共舞臺後面臨的許多新挑戰,主要是面對一系列日益增多的針對相對論的刻薄攻擊。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愛因斯坦對他新職業的反應,以及他的家人、親密友人和同行在很大範圍內成為公眾人物時的應對。同時,這些材料還展現了當時德國(及其他國家)科學與科學界的發展圖景。
1920年10月,愛因斯坦終於成為了Lyeden大學的特邀教授,這直接導致了著名的《乙太和相對論》就職演講的誕生。載于本卷的一些書信也見證了愛因斯坦在荷蘭的逗留和與熱情好客的荷蘭同事的友情。但是,從信件中可以看出,只有 Paul Ehrenfest才是這段時間裡愛因斯坦最重要和親密的私人朋友和科學夥伴。
I
在1914年春天,愛因斯坦從蘇黎世經由Lyeden(Leyden)前往柏林,擔任普魯士科學院常任院士的新職務。到了這一年夏天,愛因斯坦和他的妻子,Mileva Einstein-Maric分開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一天,Mileva帶著他們的兩個兒子,Hans Albert 和Eduard,回到了瑞士。愛因斯坦則繼續留在柏林近20年。在1915至1920年間,他共前往瑞士5次。1915年夏天看望他的兒子,1916年春天以及1917年夏天,他再次前往蘇黎世試圖與Mileva離婚。1919年初,他再次前往蘇黎世,在那裡,他完成了與Mileva的離婚,並作為嘉賓在蘇黎世大學裡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相對論的演講。1919年6月,在柏林,愛因斯坦娶他的堂表妹Elsa Einstein為妻。此後不久,他又一次前往蘇黎世看望了自己的兒子以及身患絕症的母親,並再次在蘇黎世演講。
本卷刊登的信件中,有149份是愛因斯坦自己寫的,時間大多在1916年到1919年之間,其中67封是寫給Elsa Einstein的,55 封是寫給Heinrich Zangger的,其餘27封是寫給其他家庭成員、朋友和同事的。愛因斯坦在1917-1919年離開柏林期間,寫給Elsa的信件和明信片分為兩個系列。1917年愛因斯坦與好朋友Zangger的來往信件很多,當時Mileva Einstein-Maric正生病就醫,住在蘇黎世的Zangger是愛因斯坦與家人間的連絡人。對兒子的照料以及伴隨的經濟生活安排是愛因斯坦在這些信件裡主要關心的問題。
在1915-1919年間的信件共61封。29封由Hans Albert和 Eduard Einstein所寫,往往是共同寫的,有時還伴隨著Mileva的信,都是在他們父母分居後的5年裡寫的。有12 封是Mileva在他們婚姻的最後一年,1918年發出的。以前卷裡刊登過愛因斯坦在此期間寫給Mileva的32封信和寫給孩子們的34封信件。本卷的這些信件是進一步的補充。
補充的家庭信件中,還涉及到了參與家庭事務的其他人員:包括愛因斯坦的妹妹Maja Winteler-Einstein,以及她的丈夫Paul Winteler,以及愛因斯坦的老朋友米Michele Besso和他的妻子Anna Besso-Winteler,Paul Winteler的姐姐等等。Zangger,Winteler和Besso對家庭都提供了許多幫助,並在愛因斯坦和Mileva 分居的5年裡以及隨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呼籲他們維持關係,並關注孩子們的照料問題。
愛因斯坦和Elsa L?wenthal, née Einstein,既是堂妹又是表妹,他們從1912年開始親密交往。Elsa是愛因斯坦下決心接受柏林職位的重要因素。[1] 但到1916年他們仍然分居兩處——愛因斯坦住在單身公寓,Elsa與兩個女兒Ilse 和Margot以及父母Rudolf 和 Fanny Einstein都住在柏林西南區。現存的與在柏林家族之間的通信幾乎全由愛因斯坦寫給他們。這個時期從Elsa Einstein發出的信件可謂少之又少。愛因斯坦離開柏林期間的旅途中,通常都以明信片的形式,像旅遊日記似地,寫給Elsa和她的女兒們,日期從1916年春到1920年秋——只是在1918年沒有信件現存。
這裡刊登的第一批寫給Elsa Einstein的明信片,是1916年4月他去瑞士探望自1915年9月起就未見到的兩個兒子期間以及與漢斯徒步旅行時所寫。那次見面,與愛因斯坦分居近兩年的Mileva Einstein-Maric否認她曾經同意離婚(卷8,文檔 210a)。* 第二組明信片始於1916年秋天,愛因斯坦旅居Lyeden期間住在他的朋友Ehrenfest家時,在信中愛因斯坦寫到他對當地的文化氣氛以及相對論在荷蘭廣為接受的深刻印象(卷8,文檔 261b and 262b)。
*卷8,文檔 210a, 收錄在當前卷。在引言中(包括在正卷中)採用這一縮寫形式以區別於本卷條目與以前出版的卷中條目。
大兒子Hans Albert Einstein的來信最早見於1915年——他快到11周歲生日之時,直到1920年。他的話題很多,談到他的弟弟拼錯了單詞,轉述Eduard希望父親能與他們住在一起,還提到自己在1915年彈奏海頓與莫札特的奏鳴曲以及在1920年能彈奏更複雜的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的作品(卷8,文檔69a and 69b, 以及卷9,文檔 288a)。Hans Albert也與父親交流自己在手工藝方面的興趣,曾寄給他一幅木雕航船的草圖(卷8,文檔278a),甚至火車與飛機模型。這些信件多少反映了愛因斯坦大兒子對複雜的家庭事務的看法,小小年紀就要承擔壓力與責任的認識,以及對愛因斯坦本人直接與Mileva對話處理有關假期安排和經濟問題的期待(卷8,文檔 91a)。在Mileva幾近精神崩潰、停留在蘇黎世一處療養院的1916年春天,一連數月,兩個兒子由女管家照料。1917年4月份,她的健康狀況再度惡化,這時13 歲的Hans Albert Einstein不得不獨自照顧自己。此時他們經濟艱難,因為愛因斯坦寄往瑞士的撫養費由於很多原因常常不能按時到達。到4月底,Mileva與Eduard都住進了醫院——Mileva是慢性脊柱神經壓痛,Eduard是肺炎,Hans Albert甚至也在醫院陪住了一小段時間。隨後,由Zangger的家庭照顧(卷8,文檔 330a)。
在已出版的第5和第8卷裡刊登的愛因斯坦與Heinrich Zangger的書信中,愛因斯坦主要談到了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表達了個人的情感和感想,也經常強調他們之間的友誼對自己的重要性。[2] 身為瑞士聯邦科技學院(ETH)法醫學教授的Zangger,在1911年10月愛因斯坦被授予ETH理論物理研究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3] 就科學方面的問題,他們之間定期通信。[4] 愛因斯坦與他討論1911年的Solvay會議,講述自己的工作進展,[5] 並評論當前研究以及他的同事的能力。愛因斯坦經常向Zangger徵求建議,並對Zangge常年累月地照顧家人極為感謝。當愛因斯坦移居到柏林,與Einstein-Maric分居後,Zangger越來越多地成為了他聯繫家人的重要人物。[6] 愛因斯坦經常向他諮詢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7] 提到了分居後的困難,以及答覆Zangger請愛因斯坦考慮重回蘇黎世的提議等。[8]
在本卷中,與Zangger的補充信件也表達了類似的主題,但重心是個人事務及家庭危機問題,包括愛因斯坦對Einstein-Maric、孩子、以及分居的看法(卷8, 文檔41a, 96a, 159a, 和 161a),以及對再婚的考慮(卷8, 文檔196a)。愛因斯坦也談到了他對柏林一些明顯疏遠的學術同行的感受(卷 8, 文檔45a)、跨國旅居的艱難(卷 8, 文檔118a, 232a, 和 352a),以及當時廣泛的饑荒、經濟困難、食物配給等等(卷 8, 文檔 237a, 247a, 和 291a)。
科學話題依舊是兩人相互通信的重要部分:愛因斯坦講述自己的工作進展(例如, 卷 8, 文檔 41a, 144a, 和 370d),而Zangger邀請愛因斯坦參加自己組織的概率論研討會(卷 8, 文檔 533a)。有幾封信,愛因斯坦與Zangger交流了他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破壞性的驚愕(例如見卷 8, 文檔 34a, 159a, 和 261a)。還有信件涉及對朋友Friedrich Adler的支持,對他因為刺殺奧匈總理伯爵 Karl Stürgkh之事在維也納將被判處死刑表示抗議(卷 8, 文檔 326a和330b)。1917年8月,愛因斯坦富有卓見性地提出了建立一個戰後國際和平組織的建議(卷 8,文檔372a)。
大約20封由愛因斯坦所寫的信中,都是設法解決在蘇黎世的家中不斷重複出現的家庭危機問題(例如,卷 8, 文檔 276a, 332a和471a)。這些信件大都談及家人的健康問題,包括Einstein-Maric (卷 8, 文檔 242a, 250a 和269a), 愛因斯坦本人(卷 8, 文檔287b, 299a 和326a), 以及他們的兒子 Eduard (卷 8, 文檔352a, 361e 和 367b), 或者他們三人(卷 8, 文檔308a 和 391a)。這是1917年年初,愛因斯坦不僅在柏林的演講多了一倍,還得計畫再次訪問蘇黎世,真是最困難的時期。 與Hans Albert一起,他計畫看望已經轉到Arosa H?chwal療養院的Eduard(卷 8, 文檔344)。在1917年6月Hans Albert寫給父親的信中,他詳述了自己學習拉丁文時遇到的困難,並自稱是“Sauerkrautlateiner”(酸菜拉丁學者;蹩腳拉丁學者);他還寫道,他讀了父親最近出版的關於相對論理論的流行著作,並希望再次見面時父親能把書中晦澀難懂的第二部分解釋給他聽(卷 8, 文檔 346a)。
愛因斯坦在1917年6月底前往瑞士和德國南部的旅途中,兩個月期間共給Elsa Einstein寫了28封明信片和一封信。在Heilbronn看望自己母親時,寫到他胃病復發後一直保持節律飲食;並不止一次地邀請Elsa在他回到柏林之前到德國南部共度假期,得到一些平日作為女兒和母親無法享受的“自由” (卷 8, 文檔 370e)。[9]與Hans Albert一起呆在妹妹(Maja)、妹夫家時,愛因斯坦還在信中寫到了對於妹妹一家 “難以言傳地舒適”的生活的嚮往,並再度表達了離開柏林、與Elsa一起追求平靜生活的念頭(卷 8, 文檔 361a)。在與Marcel Grossmann見面一年後,他還給Elsa寫到離開柏林到蘇黎世大學工作的打算。這些信件顯然讓Elsa感到不安,因為不久以後愛因斯坦又說他只是考慮那樣一種可能性,而當下他們還是應該留在柏林(卷 9, 文檔72e, 74d, 77a和79a)。即便如此,1920年,經歷過那年夏天人們對相對論的攻擊以及他向同行重申還會繼續留在柏林後,愛因斯坦仍向Elsa表達了他想離開柏林的想法——一個讓他“頭痛”的城市(文檔149)。
在1917年寫給Elsa的信中,愛因斯坦描述了自從1916年4月就未見到兒子Hans Albert,說他是個“理想的孩子”,儘管有時“相當調皮搗蛋”,“明顯受了(他)媽媽的影響”。在Arosa看望他的總在生病的小兒子時,寫道,看到他“光彩”面容時的喜悅,說他膚色“就像個農夫的孩子般健康”。在愛因斯坦看來,兩個兒子的母親不在他們身邊顯然是有益的;儘管他們經常生病,愛因斯坦還是喜歡陪在孩子們身邊, 並認為Eduard的身體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在信件中,愛因斯坦還再次向Elsa保證說,“我們的女孩兒” Ilse和 Margot對他來說也是一樣地珍貴(卷 8, 文檔361b,361c,361d和361f)。
在戰爭期間,愛因斯坦自己的健康問題,以及一定程度的糧食短缺,在Zangger和Winteler家庭的幫助下,都得到了緩減。 Winteler家庭送食物包給愛因斯坦(卷 8, 文檔291a,297a,357a,661a和661b) 。他與他的妹妹Maja Winteler-Einstein 的信件,往往圍繞德國和瑞士日常生活的惡化 (卷 8, 文檔 475b 和 561b, 卷 9, 文檔 128a),流感疫情(卷 8, 文檔 561a),瑞士總罷工(卷 8, 文檔 659a 和659b),各種金融問題,如他們在Schweizerische Auer-Aktien-Gesellschaft的聯合投資(卷 9, 文檔 96a, 206b 和239a),以及他們的身患絕症的母親Pauline(卷 9, 文檔96a,128a和206a)等等展開。
到了1918年1月,由於用於Eduard的醫療費用,愛因斯坦在蘇黎世的家人經濟困難加重。Hans Albert在信中請求愛因斯坦預支下季度的撫養費,因為瑞士-德國間的匯率正在朝不利的方向日益變化。幾周以後,Hans Albert又寫信給愛因斯坦,對自1917年12月到1918年4月臥病在床的父親表示關切,同時又憤慨地指出父親所說的Eduard是“被慣壞了”的話毫無道理。他說愛因斯坦對家庭困難缺少基本瞭解,他對全力幫助他們的Heinrich Zangger很理解,甚至要比對親生父親的理解還要多(卷 8, 文檔 435a和442a)。
1918年2月,在本卷Mileva Einstein-Maric的一封信裡,她對愛因斯坦重提離婚的企圖表示反對。一個月後,她似乎接受了愛因斯坦的提議,附加條件是必須保證愛因斯坦死後她擁有寡婦補助金,並且愛因斯坦要直接和她聯繫、郵寄撫養費,不能通過中間人。由於她脆弱的身體狀況,以及在醫院和療養院的長期治療——這是1916 年夏到1917年秋最糟的事,導致對孩子們的安排和照顧不周。而且在1918年的頭幾個月,當Mileva的身體狀況有所改善後,她明確表示不同意愛因斯坦將Hans Albert從她身邊帶走的提議(卷 8, 文檔 461a, 475a, 482a 和482b)。
1918年夏天,愛因斯坦取消了回蘇黎世與孩子們同去阿爾卑斯山旅行的計畫。在1918年6月系列信件的第一篇,近8歲的Eduard表達了自己對愛因斯坦取消假期計畫的失望,同時還有Hans Albert的一封信。在隨後的通信中,Eduard對父親講述了他最近的讀書、愛好、玩伴等情況,以及因為健康不佳無法參與學校活動的遺憾(卷 8, 文檔 557c 和659c, 卷 9, 文檔 183a)。當時在四個月內,Eduard兩次遭受西班牙流感的侵襲(卷 8, 文檔 557a, 588a 和646a)。Hans Albert在他的信裡也表達了對愛因斯坦不能前來的失望之情;一個月後又解釋說他自己無法前往德國看望父親,因為 (在蘇黎世)他要照料家庭的日常生活而無法脫身(卷 8, 文檔 557b 和 588b)。
1918年6月底前,愛因斯坦與Elsa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前往波羅的海海邊度假。期間,愛因斯坦與瑞士的學術界討論了他前往蘇黎世任職的事。儘管愛因斯坦拒絕了瑞士方面的就職提議,他還是接受了每年兩次共5到6周時間的講學訪問邀請。當年夏天,愛因斯坦與Mileva的離婚行政判決也在蘇黎世做出。兩人於6月最終簽署了離婚協定。8月底,愛因斯坦向Mileva的律師,也是他們共同的朋友Emil Zürcher Jr.寫了一封正式信函,表明兩人的關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18 年12月,愛因斯坦離開柏林前往蘇黎世離婚法庭;在1919年初,他遊歷瑞士並做了第一次系列訪問講座,最終在2月14日辦完了離婚手續。
愛因斯坦與Elsa Einstein在1919年6月2日結婚。四周以後,同時也是在日蝕觀測證明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幾天之後,愛因斯坦離開柏林開始為期7周的旅程。他前往瑞士探望病重的母親,陪伴兩個兒子一段時間,並在蘇黎世做了關於相對論的講座。在寄給Elsa的23封明信片中,愛因斯坦詳述了他每週往返于蘇黎世與母親所在療養院之間的行程,以及他“想到母親受到折磨”時的憂痛。不過在Hans Albert身邊他感到“無法形容地快樂”,他們一起製作飛機模型。而Elsa則對愛因斯坦暫居蘇黎世的住所感到不快,稱那是“一個母獅窩”,雖然當時Mileva不在家裡(卷 9, 文檔 70b 和86a)。
在1919年8月中旬重返柏林後,愛因斯坦陸續接到英國天文學家觀測日蝕的結果。9月,他得知探測隊成功地拍攝到了日蝕圖像,並通過Hendrik A. Loren瞭解到Arthur S. Eddington也獲得了支援性的資料。在愛因斯坦對日蝕觀測結果發表了簡短的評論之後,於10月18日啟程去荷蘭旅行兩周,期間住在好友Paul和Tatiana Ehrenfest的家裡。10月23日,他在給Elsa的信中說,Eddington(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已向Lyeden物理學家報告,廣義相對論得到了證實。但這一喜悅資訊由於他母親的病危受到壓抑。他安慰Elsa,期待病危的母親很快到柏林(卷9,文檔 148b 和151a)。
1919年10月,愛因斯坦通知在蘇黎世的家人說,他們將不得不搬到德國南部居住,因為他認為要支援他們住在瑞士的費用已難以為續(第9卷,文檔135)。Mileva拒絕了這一要求, 解釋說她的不穩定健康狀況在德國可能缺乏合適的照料,她還辯解說,Hans Albert不應該中斷學業,並說改善經濟狀況的唯一辦法只能是讓Hans Albert儘快成長自立(卷9,文檔 148a 和183c)。1920年初,愛因斯坦在蘇黎世的家人再度分開,住所也被租了出去:Eduard由於肺病復發去往一家療養院;Mileva回到自己有病的父母身邊;Hans Albert則再次與Zangger一家待在一起(卷9, 240a)。
1920年7月,當Mileva和兩個兒子又回到蘇黎世住所後,愛因斯坦提議秋天由他帶著孩子們去德國南部度假(文檔 70)。10月初,在南部歡樂的暫住時光中,愛因斯坦似乎對兩個兒子有著矛盾的看法:他寫信給Elsa說兒子們都“成長得極好”,同時又說很難把他們看作是他的“血脈傳承”;他們有著“碩大厚實的手”,而且儘管“似乎充滿了智慧”,但他們又似乎有“難以描述的低智”之處(文檔179)。愛因斯坦重申了讓Mileva和兩個孩子移居德國的想法。作為回應,Hans Albert懇請他的父親能放棄這個想法,讓他不受中斷地完成學業(文檔 212),儘管愛因斯坦繼續堅持說Hans Albert來達姆施塔特可以就讀很好的工藝學校(文檔 232)。事實上,1920年,愛因斯坦的經濟狀況有了顯著改善,不止薪水大增,而且有關相對論的出版物收入也豐厚起來(見記事表)。
Ⅱ
在愛因斯坦的信件中, 1920年夏天在德國的反對相對論的公共活動構成了一個重要的話題,詳見本卷第二部分涉及的相應內容。1920年八月,一個系列講座宣稱愛因斯坦是一個騙子和鼓吹者。幾周後,在巴德瑙海姆(Bad Nauheim)的德意志法制論自然研究者(Gesellschaft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rzte)的第一次戰後會議上,他和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Philipp Lenard為相對論的問題而鬧僵。[10]公眾一致稱讚愛因斯坦為“一個具有自由主義國際觀點的猶太人”(第7卷,文檔45),正如他自我評價一樣,這令反對他的人感到不滿。
8月6號,右翼政論家Paul Weyland在國家主義者日報上的一篇具有煽動性的文章中,指責愛因斯坦使用了剽竊和鼓吹手段,這項指責最早是由Ernst Gehrcke提出的,他是柏林物理工業標準的光譜學家。[11]在尖銳且不加掩飾的反猶太偏見中,Weyland聲稱愛因斯坦擁有其“特別出版社,特別追隨者”,它們不停地向公眾發佈一些支持愛因斯坦的言論。對於一個同時代的讀者來說,肯定能理解其中的反猶太主義的暗示。在之前的幾個月裡,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柏林人日報報導了1919年太陽日食的結果,並且有一篇誇張的散文稱讚“最高的真理,超越了伽利略和牛頓,超越了康得”,被“來自太空深處的神諭”揭開。由猶太出版商Rudolf Mosse發行的這份報紙在反猶太主義者圈內被稱作“猶太報紙”;該篇文章的作者,新聞工作者Alexander Moszkowski,是一本猶太幽默書的作者,也是愛因斯坦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愛因斯坦自己寫了一篇關於日食的短文發表在高水準的自然科學雜誌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上(Einstein 1919d [第7卷,文檔23]),雜誌的主編Arnold Berliner也是一個猶太人。在1919年12月,柏林人報在其頭版刊登了一張愛因斯坦的特寫照片,標題寫著:“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新巨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的理論開創了我們理解自然的一次新革命,他的深刻見解同哥白尼、開普勒、牛頓一樣重要”。這個雜誌屬於烏爾斯坦出版社,它的所有者同樣是猶太人。Weyland煽動性地說:假如現在日爾曼科學團結起來,一起反對他,“並且清算總帳”,那麼愛因斯坦只能去指責自己。
1920年八月中旬,右翼報紙上刊登了一項通告,公佈了二十個反對相對論的講座。講座設在柏林交響樂團主演奏會大廳(可以容納超過1600人)。8月24日,Weyland和Gehrcke是最先的發言者。Weyland在他對相對論的批判中,引用愛因斯坦的出版物來證明他的主張。特別地,他將目標放在關於日食的新聞報導上,“從這個總部裡(愛因斯坦的人),流行的觀點被喚醒”——試圖同哥白尼、開普勒、牛頓進行比較。愛因斯坦自己應該被指責:從他到“和他的圈子有密切聯繫的出版物”中,只需要一句話就可以令這種“榮耀和尊敬的浪潮”結束。根據Weyland的觀點,相對論純粹是一種奇想和虛構。在講座中,Gehrcke也認為相對論除了“一堆催眠的東西”什麼也沒有(Gehrcke 1920b)。
愛因斯坦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他在8月27日通過在柏林人日報發表的文章回應這一爭論。不僅僅只針對Weyland,還有其他支持Weyland觀點的人,例如Gehrcke和Lenard。愛因斯坦通過他尖銳的措辭指責他們(Einstein 1920f [第7卷,文檔45];亦可參見本卷文檔148)。愛因斯坦甚至還準備離開柏林和德國,主要是因為他相信在科學界,Weyland得到了廣泛的支援,他也將這一觀點在媒體上公開了。
隨著事態的發展,愛因斯坦收到了很多來信的支持。各行各業的人士都來信表達了他們對於反愛因斯坦活動的憤怒:例如Toni Schrodt,她稱自己為“只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女孩”(文檔121),還有Elsa伯爵夫人(文檔122);猶太人(文檔117,136)和神父(文檔124);學生和教授(文檔111,112,123)。Ina Dickmann曾聽過反對相對論的講座,他懇請愛因斯坦不要離開德國,尤其是當德國處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之中(文檔113)。
一些知名的同事,例如Fritz Haber和Max Planck都請求愛因斯坦留在柏林(文檔119和133)。普魯斯教育部長,社會民主人士Konrad Haenisch寫了一封支持信,並在每日出版物上刊登(文檔135)。一部分傑出文藝界人物發來了電報,包括戲劇導演Max Reinhardt和作家Stefan Sweig,他們在三個星期後發出了他們的個人信件。女權論者和新祖國聯盟(League of the New Fatherland)的成員Minna Cauer也表達了她的支持(文檔117,151和152)。
愛因斯坦的好友Paul Ehrenfest向他保證,如果決定離開德國,在荷蘭可以給他安排全職工作,但是他也表示他認為愛因斯坦在柏林人報上的諷刺性回擊是具有誤導性的(文檔114和127)。
德國物理學會(DPG)會長,物理學家Arnold Sommerfeld兩次寫信給愛因斯坦(文檔131和147)。他請求愛因斯坦不要“逃離旗幟”,並表示德國給愛因斯坦的待遇要比他在戰爭中其它地方給他的待遇好。Sommerfeld嘗試在愛因斯坦和Lenard之間進行調解,他這樣做也是擔心DPG的柏林會員和首都以外會員間的激烈爭論,特別是Johannes Stark,Wilhelm Wien,和Lenard。兩個陣線的科學家想要在即將到來的會議上展開辯論,並且可能要討論DPG的重組。Johannes Stark,Wilhelm Wien,和Lenard代表政治范 圍的權利並且拒絕魏瑪共和國的憲法民主,而愛因斯坦覺得在一個新共和國裡“他的政治願望可以變成現實”。[12]
愛因斯坦收到的信件也表明了隨著他榮譽的提高,他在猶太人群中所處的新地位。一個來信者特別提到了納粹的徽章,它出現在講座大廳,並且是反猶太的;另一個來信者拿他和Baruch Spinoza、Moses Mendelssohn進行比較;如果愛因斯坦想去巴勒斯坦,一個藝術家以他的名譽承諾,他可以在計畫中的希伯來大學中得到職位;東加沙猶太複國組織告訴他,他們因為他是猶太人而感到驕傲(文檔115,118,136和178)。
愛因斯坦想離開德國的第一個傳言在媒體上出現後十天,人們才得得知愛因斯坦對這一傳言的明確回復。海尼斯是首先收到回信的人之一:愛因斯坦已經決定離開柏林(文檔137)。致Ehrenfest的信中表達了他對自己那篇文章的遺憾,但是強調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面對一而再、再而三的無端指責,他有必要向大眾表明自己的立場。另一方面,愛因斯坦也相信“反相對論團隊將會很快瓦解”,並且開玩笑地說,他不會“如Sommerfeld所說的那樣遠離旗幟”(文檔139)。Weyland的宣導在科學、社會領域沒有得到太廣泛的支持,隨後只有一篇反對相對論的文章發表。
在“我對於反相對論團體的回應”(Einstein 1920f [第7卷,文檔45])中,愛因斯坦向他的對手們提出了挑戰,在一個月後的GDN?會議上進行一場辯論。在反相對論運動開始前,愛因斯坦已經打算同數學家Robert Fricke和Arthur Schoenflies就相對論在會議上展開廣泛的討論,以替代計畫中的講座(文檔48和50)。但是現在,很多人,包括日爾曼出版物的編輯,希望出現一個轟動性的“愛因斯坦爭論”。但最終根據不完整的記載(參見第7卷,文檔46),愛因斯坦和Lenard之間簡短的十五分鐘“鬥爭”,或是“鬥雞”(文檔163),被報紙描述成交換意見的激烈爭論,其間人們堪稱“冷靜的典範”。不過氣氛還是非常緊張,並且辯論大大影響了Elsa Einstein,她後來得了病(文檔154和166)。
這些事件後,一些愛因斯坦的朋友和同事開始擔心更深入地宣傳愛因斯坦和他的工作可能產生的結果。1920年十月Alexander Moszkowski打算出版一本書,內容主要是來自與愛因斯坦對話。Max和Hedwig Born強烈地要求愛因斯坦停止它的出版。他們認為這本書可能引起新的反對愛因斯坦的消極運動,因為 Weyland曾指責愛因斯坦一直在自吹自擂,而這本書似乎印證了這一點。通過讀Moszkowski的其它文章,Hedwig Born(即Max Born的妻子)擔心這本自傳可能會成為“同猶太人的粗魯對話”,特別是擔心這樣的作品可能為那些指責愛因斯坦自行出版的人提供藉口。相比他的妻子,Max Born給出的警告更為嚴厲:如果這本書出版了,愛因斯坦的“猶太朋友將不會得到反猶太團夥想得到的東西”。顯然受Born觀點的影響,身處荷蘭的愛因斯坦寫信給Elsa說,自傳的出版將是“悲慘的”。在他看來,這件事比今年夏天的反相對論宣傳和講座要“嚴峻得多”(文檔166,174,175,180,182-185以及187)。最後,這本書出版時在它的介紹中有一個免責聲明,愛因斯坦對其中的內容不負任何責任(Moszkowski 1921)。
但愛因斯坦重新建立了他對反猶太主義和猶太社區在德國地位的看法,並稱不管是猶太人中的同化主義還是激進主義,它們都無助於消除某些德國公眾的反猶太情緒(參見第7卷,文檔34、35和37)。1920年9月,抗議反猶太主義聯盟(Association for Combating Anti-Semitism)邀請愛因斯坦加入領導團,他讓他的繼女和秘書Ilse做出了回復,因為他不相信“我們猶太人能夠直接同反猶太主義戰鬥”,所以他們應該避免將他選入管理層(文檔150)。1920年12月柏林的官方猶太社團要求愛因斯坦交付長期拖欠的會稅,他告知他們,他從來沒有正式加入猶太社團:雖然他認為自己是猶太人,但他已經遠離了“傳統的宗教形式”。然而,他已經準備好每年都向猶太慈善事業捐贈(文檔238)。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愛因斯坦得到了超過以前作為科學家的名流地位:當廣義相對論和它的大量出版物在1919年晚些時候初次被大眾接受後,愛因斯坦面對的攻擊則是針對他的科學工作,他的猶太人身份以及他的左派政治觀點。二月份“文學大廳的喧鬧(Uproar in the Lecture Hall)”(參見第7卷,文檔33),八月份柏林交響樂大廳事件, 1920年10月在Bad Nauheim的相對論爭論以及“Moszkowski事件(Moszkowski affair)”將他置於公共和個人的論戰中並消耗了他大量精力。雖然他的瑞士的同事多次嘗試說服他回到蘇黎世(文檔192),雖然Ehrenfest建議他在Leyden謀得一個全職,在那裡愛因斯坦可以充分享受自己的時光,但他還是留在了柏林。在一些記者眼中,Sommerfeld呼籲一種愛國主義意識(參見日程表1920年8月28日,P. Havel),愛因斯坦感覺有責任避免這種尷尬並且意識到這可能使他和柏林的同事間造成疏遠,而這些同事給予了他很大的支援(文檔211,239和245)。當愛因斯坦本人對海外新聞報告輕描淡寫時,日爾曼官方卻認為它們有其它含義(參見文檔239)。德國駐倫敦大使,Friedrich Sthamer表示,英國媒體用非常不友好的言辭猛烈攻擊愛因斯坦,特別是“愛因斯坦教授是把德國文化元素放在第一位的,隨著愛因斯坦的名字被廣泛關注。我們不應該使這樣一個人離開德國,有了他我們可以做真正的文化宣傳”。[13]
交響樂團的事件捲入了其它政治漩渦之中。在1920年3月中旬的反對派卡帕政變(Kapp Putsch)和激進右派的暴動之後,和平主義者和其他一些被描繪成“叛國者”的人認為德國正在變成暴力的目標。[14] 5月份,愛因斯坦簽署了一份建議書,提交給德國科學院,支持共和國憲法,並且6月份他又一次表達了他的國際方向和主張(參見文檔3和56)。1920年6月6日,新憲法下的第一次選舉中,魏瑪聯合政府被擊敗,對社會民主黨和德意志民主黨是一個大的損失,政治派別更加分化。[15] 1920年夏天,柏林的和平主義學者受到威脅和恐嚇。Hellmut von Gerlach因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而取消了演講並考慮離開德國。Emil J. Gumbel被打倒並且被判為兇殺犯,而愛因斯坦早期曾支持過的Georg Nicolai也面臨著來自右翼的暗殺的危險。[16] 正如本卷中所反映的,此時民族主義者和反動傾向遍佈學術生活的每個地方,例如在羅斯托克大學(University of Rostock)(文檔12)和圖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文檔38)。
愛因斯坦的新名聲使許多組織尋求他的支援。在1920年7月,他參加了宣導和平和社會公正的組織,並和國際學生交流(文檔73,74,86,87和141)。10月和11月,他為支持Jozsef Kelen出席了一個審訊,後者是一個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失敗後受審的匈牙利工程師(文檔186,194,200和202)。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