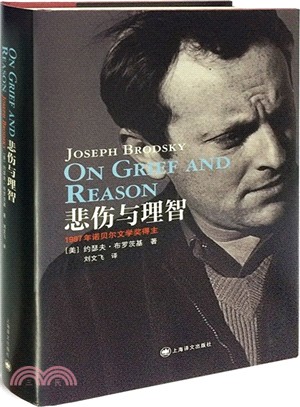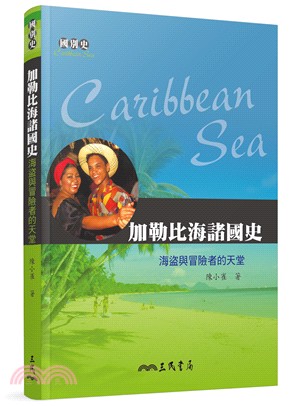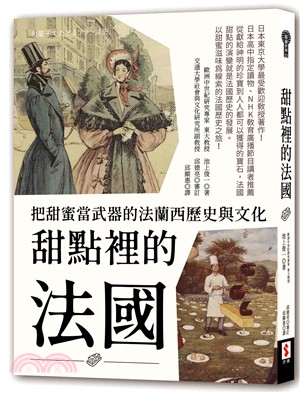悲傷與理智(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新浪2015年度十大好書第四名
2015年新浪中國好書榜5月榜榜首
華西都市報《當代書評》2015年度“十大好書”榜第三名
深圳讀書月2015年度十大好書
新京報2015年度好書·4-5月榜榜首
新京報2015年度好書·年中榜·文學(2種)
首屆書店文學獎年度書單
2015年鳳凰網年度圖書
南方都市報2015年度圖書
北京晨報2015年度圖書
豆瓣讀書2015年外國文學類年度圖書
中華讀書報2015年度百家圖書之文學(20種)
中華讀書報2015年6月月度好書榜(20種)
★約瑟夫布羅茨基是以美國公民身份獲取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但他在大多數場合卻一直被冠以“俄語詩人”之稱謂;他在一九七二年自蘇聯流亡西方後始終堅持用俄語寫詩,並被視為二十世紀後半期*重要的俄語詩人,甚至是“**俄語詩人”(洛謝夫語),可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文學界,布羅茨基傳播*廣、更受推崇的卻是他的英語散文,他甚至被稱作“*偉大的英語散文家之一”(《泰晤士報》)。
★布羅茨基散文集《小於一》2014年幾乎橫掃國內所有年度好書榜單,讓人真正見識到“小眾圖書”的“大眾潛力”。《悲傷與理智》是他生前出版的*後一部散文集,為其散文創作的集大成者,更是贏得了世界範圍的讚譽。這卷文集可以說是通向布羅茨基的詩歌觀和美學觀,乃至他的倫理觀和世界觀的一把鑰匙。
★譯者劉文飛先生是將布羅茨基介紹給中國讀者的先驅,1998年,由他執筆翻譯的《文明的孩子》一度曾是中國知識分子重要的精神食糧,其中就有四篇名作選自這部文集。時光荏苒,十餘載後中國讀者終於得以一睹《悲傷與理智》的全貌。
《悲傷與理智》共收入散文二十一篇,大致分為回憶錄、旅行記、演說講稿、公開信和悼文等幾種體裁。這些散文形式多樣,長短不一,但它們訴諸的卻是一個共同的主題,即“詩和詩人”。這卷文集可以說是通向布羅茨基的詩歌觀和美學觀,乃至他的倫理觀和世界觀的一把鑰匙。文集中*後一篇作品《悼斯蒂芬·斯彭德》完成後不到半年,布羅茨基自己也離開了人世,《悲傷與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羅茨基生前出版的*後一部散文集,是布羅茨基散文寫作、乃至其整個創作的“天鵝之歌”。在這部題材豐富、視界浩淼的散文集中,約瑟夫布羅茨基開篇便用深沉內省的目光審視了自己在蘇俄的早年經歷以及隨後去往美國的流亡生涯。接著,作者用驚人的博學探討了詩歌的張弛變幻、歷史的本質、流亡詩人的雙重困境等一系列頗具廣度與深度的話題,思維的觸手延攬古今,上及古羅馬賢帝馬可奧勒留,下至現當代詩人托馬斯哈代與羅伯特弗羅斯特,將對存在本質的哲學探討與對詩歌美學的熾烈情愫糅合鍛造為繼《小於一》之後的又一部世所罕見的奇作。
上海譯文出版社此次翻譯出版的《悲傷與理智》是這部佳作的shou個國內中文譯本,在翻譯文學界具有填補空白的重大意義以及不可替代的文學與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他的散文具有大師的力量與精準,時而卻又發散出先知般的道德光輝。”——《華盛頓郵報》
“英語文壇*偉大的散文家之一......一部世人為之慶賀的傑作。”
——《泰晤士報》
序
譯序
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1940--1996)是以美國公民身份獲取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但他在大多數場合卻一直被冠以“俄語詩人”(Russian poet)之稱謂;他在一九七二年自蘇聯流亡西方後始終堅持用俄語寫詩,並被視為二十世紀後半期最重要的俄語詩人,甚至是“第一俄語詩人”(洛謝夫語),可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文學界,布羅茨基傳播最廣、更受推崇的卻是他的英語散文,他甚至被稱作“偉大的英語散文家之一”(on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 great essayists,見企鵝社英文版《悲傷與理智》封底)。作為高傲的“彼得堡詩歌傳統”的繼承人,布羅茨基向來有些瞧不起散文,似乎是一位詩歌至上主義者,可散文卻顯然給他帶來了更大聲譽,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世界範圍內三位最重要的布羅茨基研究者列夫洛謝夫(Lev Loseff)、托馬斯溫茨洛瓦(Tomas Venclova)和瓦連金娜帕魯希娜(Valentina Palukhina)都曾言及散文創作對於布羅茨基而言的重要意義。洛謝夫指出:“布羅茨基在美國、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整個西方的作家聲望,因為他的散文創作而得到了鞏固。”帕魯希娜說:“布羅茨基在俄國的聲譽主要仰仗其詩歌成就,而在西方,他的散文卻在塑造其詩人身份的過程中發揮著主要作用。”溫茨洛瓦則稱,布羅茨基的英語散文“被公認為範文”。作為“英文範文”的布羅茨基散文如今已獲得廣泛的閱讀,而布羅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散文集《悲傷與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 1995),作為其散文創作的集大成者,更是贏得了世界範圍的讚譽。通過對這部散文集的解讀,我們或許可以獲得一個關於布羅茨基散文的內容和形式、風格和特色的較為全面的認識,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布羅茨基創作中詩歌和散文這兩大體裁間的關係,進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布羅茨基的散文創作,乃至他的整個創作。
一
約瑟夫布羅茨基一九四零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父親是海軍博物館的攝影師,母親是一位會計。天性敏感的他由於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而主動疏離周圍現實,並在八年級時主動退學,從此走向“人間”,做過包括工廠銑工、天平間整容師、澡堂鍋爐工、燈塔守護人、地質勘探隊員等在內的多種工作。他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寫詩,並接近阿赫馬托娃。他大量閱讀俄語詩歌,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兩三年內“通讀了”俄國大詩人的所有作品,與此同時他自學英語和波蘭語,開始翻譯外國詩歌。由於在地下文學雜誌上發表詩作以及與外國人來往,布羅茨基受到克格勃的監視。一九六三年,布羅茨基完成《獻給約翰鄧恩的大哀歌》(Большая элегия Джону Донну),並多次在公開場合朗誦此詩,此詩傳到西方後引起關注,為布羅茨基奠定了詩名。一九六四年,布羅茨基因“不勞而獲罪”被起訴,判處五年刑期,被流放至蘇聯北疆的諾連斯卡亞村。後經阿赫馬托娃、楚科夫斯基、帕烏斯托夫斯基、薩特等文化名人的斡旋,他在一年半後獲釋。在當時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這所謂的“布羅茨基案件”(Дело Бродского)使布羅茨基舉世聞名,他的一部詩集在他本人並不知曉的情況下於一九六五年在美國出版,之後,他的英文詩集《獻給約翰鄧恩的大哀歌及其他詩作》(Elegy to John Donne and Other Poems, 1967)和俄文詩集《曠野中的停留》(Остановка в пустыне, 1970)又相繼在英國和美國面世,與此同時,他在蘇聯國內的處境卻更加艱難,無法發表任何作品。一九七二年,布羅茨基被蘇聯當局變相驅逐出境,他在維也納受到奧登等人關照,之後移居美國,先後在美國多所大學執教,並於一九七七年加入美國國籍。定居美國後,布羅茨基在流亡前後所寫的詩作相繼面世,他陸續推出多部俄、英文版詩集,如《詩選》(Selected Poems, 1973)、《在英國》(В Англии, 1977)、《美好時代的終結》(Конец прекрасной эпохи, 1977)、《話語的部分》(Часть речи, 1977; Part of Speech, 1980)、《羅馬哀歌》(Римские элегии, 1982)、《獻給奧古斯都的新章》(Новые стансы к Августе, 1983)、《烏拉尼亞》(Урания, 1987;To Urania, 1992)和《等等》(So Forth, 1996)等。一九八七年,布羅茨基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該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之後,布羅茨基成為享譽全球的大詩人,其詩被譯成世界各主要語言。一九九一年,他當選美國“桂冠詩人”(Laureate Poet)。蘇聯解體前後,他的作品開始在俄國發表,至今已有數十種各類單行本詩文集或多卷集面世,其中又以聖彼得堡普希金基金會推出的七卷本《布羅茨基文集》(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т. I-VII, 2001-2003)和作為“詩人新叢書”之一種由普希金之家出版社和維塔諾瓦出版社聯合推出的兩卷本《布羅茨基詩集》(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в 2 т., 2011)最為權威。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布羅茨基因心髒病發作在紐約去世,其遺體先厝紐約,後遷葬於威尼斯的聖米歇爾墓地。1996)等。一九八七年,布羅茨基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該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之後,布羅茨基成為享譽全球的大詩人,其詩被譯成世界各主要語言。一九九一年,他當選美國“桂冠詩人”(Laureate Poet)。蘇聯解體前後,他的作品開始在俄國發表,至今已有數十種各類單行本詩文集或多卷集面世,其中又以聖彼得堡普希金基金會推出的七卷本《布羅茨基文集》(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т. I-VII, 2001-2003)和作為“詩人新叢書”之一種由普希金之家出版社和維塔諾瓦出版社聯合推出的兩卷本《布羅茨基詩集》(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в 2 т., 2011)最為權威。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布羅茨基因心髒病發作在紐約去世,其遺體先厝紐約,後遷葬於威尼斯的聖米歇爾墓地。1996)等。一九八七年,布羅茨基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該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之後,布羅茨基成為享譽全球的大詩人,其詩被譯成世界各主要語言。一九九一年,他當選美國“桂冠詩人”(Laureate Poet)。蘇聯解體前後,他的作品開始在俄國發表,至今已有數十種各類單行本詩文集或多卷集面世,其中又以聖彼得堡普希金基金會推出的七卷本《布羅茨基文集》(Сочинения Иосифа Бродского, т. I-VII, 2001-2003)和作為“詩人新叢書”之一種由普希金之家出版社和維塔諾瓦出版社聯合推出的兩卷本《布羅茨基詩集》(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в 2 т., 2011)最為權威。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布羅茨基因心髒病發作在紐約去世,其遺體先厝紐約,後遷葬於威尼斯的聖米歇爾墓地。
像大多數詩人一樣,布羅茨基在文學的體裁等級劃分上總是抬舉詩歌的,他斷言詩歌是語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布羅茨基曾應邀為一部茨維塔耶娃的散文集作序,在這篇題為《詩人與散文》(Поэт и проза;A Poet and Prose)的序言中,他精心地論述了詩歌較之於散文的若干優越之處:詩歌有著更為悠久的歷史;詩人因其較少功利的創作態度而可能更接近文學的本質;詩人能寫散文,而散文作家卻未必能寫詩,詩人較少向散文作家學習,而散文作家卻必須向詩人學習,學習駕馭語言的功力和對文學的忠誠;偉大如納博科夫那樣的散文家,往往都一直保持著對詩歌的深深感激,因為他們在詩歌那裡獲得了“簡潔與和諧”。在其他場合,布羅茨基還說過,詩歌是對語言的“俗套”和人類生活中的“同義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於文化的積累和延續,更有助於個性的塑造和發展。
同樣,像大多數詩人一樣,布羅茨基也不能不寫散文。在談及詩人茨維塔耶娃突然寫起散文的原因時,除茨維塔耶娃當時為生活所迫必須寫作容易發表的散文以掙些稿費這一“原因”外,布羅茨基還給出了另外幾個動因:一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need),一個識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寫一首詩,但一個詩人卻不可能一生不寫任何散文性的文字,如交往文字、日常生活中的應用文等等;二是主觀的“衝動”,“詩人會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突然想用散文寫點什麼”;三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對象”和某些題材,如情節性很強的事件、三個人物以上的故事、對歷史的反思和對往事的追憶等等,就更宜於用散文來進行描寫和敘述。所有這些,大約也都是布羅茨基本人將大量精力投入散文創作的動機。除此之外,流亡西方之後,在一個全新的文學和文化環境中,他想更直接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想讓更多的人聽到他的聲音;以不是母語的另一種文字進行創作,寫散文或許要比寫詩容易一些。布羅茨基在《悼斯蒂芬斯彭德》(In Memory of Stephen Spender)一文中的一句話似乎道破了“天機”:“無論如何,我的確感覺我與他們(指英語詩人麥克尼斯、奧登和斯彭德。——引者按)之間的同遠大於異。我唯一無法跨越的鴻溝就是年齡。至於智慧方面的差異,我在最好的狀態下也會說服自己,說自己正在逐漸接近他們的水準。還有一道鴻溝即語言,我一直在竭盡所能地試圖跨越它,儘管這需要散文寫作。”作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美國桂冠詩人,他經常應邀赴世界各地演講,作為美國多所大學的知名文學教授,他也得完成教學工作,這些“應景的”演說和“職業的”講稿在他的散文創作中也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但布羅茨基寫作散文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們猜想還是他熱衷語言試驗的內在驅動力,他將英語當成一個巨大的語言實驗室,終日沈湎其中,樂此不疲。
布羅茨基散文作品的數量與他的詩作大體相當,在前面提及的俄文版七卷本《布羅茨基文集》中,前四卷為詩集,後三卷為散文集,共收入各類散文六十餘篇,由此不難看出,詩歌和散文在布羅茨基的創作中幾乎各佔半壁江山。布羅茨基生前出版的散文集有三部,均以英文首版,即《小於一》(Less Than One, 1986)、《水印》(Watermark, 1992)和《悲傷與理智》。《水印》一書僅百餘頁,實為一篇描寫威尼斯的長篇散文;另兩本書則均為近五百頁的大部頭散文集。說到布羅茨基散文在其創作中所佔比例,帕魯希娜推測,布羅茨基“各種散文作品的總數要超出他的詩歌”。洛謝夫也說:“《布羅茨基文集》第二版收有六十篇散文,但還有大約同樣數量的英文文章、演講、札記、序言和致報刊編輯部的書信沒有收進來。”(洛謝夫《布羅茨基傳》中文版第294頁)布羅茨基生前公開發表的各類散文,總數約合中文百萬字,由此推算,布羅茨基散文作品的總數約合中文兩百萬字。
據統計,在收入俄文版《布羅茨基文集》中的六十篇各類散文中,用俄語寫成的只有十七篇,也就是說,布羅茨基的散文主要為“英文散文”。值得注意的是,布羅茨基的各類散文大都發表在《紐約圖書評論》、《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和《紐約客》等英美主流文化媒體上,甚至刊於《時尚》(Vogue)這樣的流行雜誌,這便使他的散文迅速贏得了廣泛的受眾。他的散文多次入選”全美年度最佳散文“(The Best American Essays),如《一件收藏》(Collector's Item)曾入選“一九九三年全美最佳散文”,《向馬可奧勒留致敬》(Homage to Marcus Aurelius)曾入選“一九九五年全美最佳散文”。一九八六年,他的十八篇散文以《小於一》為題結集出版,在出版當年即獲“全美圖書評論獎”(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作為《小於一》姐妹篇的《悲傷與理智》出版後,也曾長時間位列暢銷書排行榜。需要指出的是,出版布羅茨基這兩部散文集的出版社就是紐約大名鼎鼎的法拉爾、斯特勞斯和吉羅克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Giroux,簡稱FSG),這家出版社以“盛產”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而著稱,在自一九二零年至二零一零年的九十年間,在該社出版作品的作家中共有二十三位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中就包括索爾仁尼琴(1970年獲獎)、米沃什(1980年獲獎)、索因卡(1986年獲獎)、沃爾科特(1992年獲獎)、希尼(1995年獲獎)和略薩(2010年獲獎)等人。順便提一句,《悲傷與理智》扉頁上的題詞“心懷感激地獻給羅杰威斯特勞斯”,就是獻給該社兩位創辦者之一的羅杰威廉姆斯小斯特勞斯(Roger Williams Straus, Jr.)的。
散文集《悲傷與理智》最後一頁上標明了《掉斯蒂芬斯彭德》一文的完稿時間,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而在這個日期之後不到半年,布羅茨基也離開了人世,《悲傷與理智》因此也就成了布羅茨基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散文集,是布羅茨基散文寫作、乃至其整個創作的“天鵝之歌”。
二
《悲傷與理智》共收入散文二十一篇,它們大致有這麼幾種類型,即回憶錄和旅行記,演說和講稿,公開信和悼文等。具體說來,其中的《戰利品》(Spoils of War)和《一件收藏》是具有自傳色彩的回憶錄,《一個和其他地方一樣好的地方》(A Place as Good as Any)、《旅行之後,或曰獻給脊椎》(After a Journey, or Homage to Vertebrae)和《向馬可奧勒留致敬》近乎旅行隨筆,《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或曰浮起的橡實》(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or Acorns Aweigh)、《表情獨特的臉龐》(Uncommon Visage)、《受獎演說》(Acceptance Speech)、《第二自我》(Alter Ego)、《怎樣閱讀一本書》(How to read a Book)、《頌揚苦悶》(In Praise of Boredom)、《克利俄剪影》(Profile of Clio)、《體育場演講》(Speech at the Stadium)、《一個不溫和的建議》(An Immodest Proposal)和《貓的“喵嗚”》(A Cat's Meow)均為布羅茨基在研討會、受獎儀式、書展、畢業典禮等場合發表的演講,《致總統書》(Letter to a President)和《致賀拉斯書》(Letter to Horace)為書信體散文,《悲傷與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和《求愛於無生命者》(Wooing the Inanimate)是在大學課堂上關於弗羅斯特和哈代詩歌的詳細解讀,《九十年之後》(Ninety Yeasr Later)則是對里爾克《俄耳甫斯。歐律狄刻。赫爾墨斯》(Orpheus. Eurydice. Hermes)一詩的深度分析,最後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是為詩友所做的悼文。文集中的文章大致以發表時間為序排列,其中最早的一篇發表於一九八六年,最後一篇寫於一九九五年,時間跨度近十年,這也是布羅茨基寫作生涯的最後十年。
這些散文形式多樣,長短不一,但它們訴諸的卻是一個共同的主題,即“詩和詩人”。布羅茨基在他的諾貝爾獎演說中稱:“我這一行當的人很少認為自己具有成體系的思維;在最壞的情況下,他才自認為有一個體系。”(《表情獨特的臉龐》)也就是說,作為一位詩人,他是排斥所謂的理論體系或成體系的理論的。但是,在通讀《悲傷與理智》並略加歸納之後,我們仍能獲得一個關於布羅茨基詩歌觀和美學觀、乃至他的倫理觀和世界觀的整體印象。
首先,在藝術與現實的關係問題上,布羅茨基斷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像力的分量就等於、並時而大於現實”(《戰利品》)。他認為,不是藝術在模仿現實,而是現實在模仿藝術,因為藝術自身便構成一種更真實、更理想、更完美的現實。“另一方面,藝術並不模仿生活,卻能影響生活。”(《悲傷與理智》)“因為文學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釋各種人類命運、各種體驗之含義的手冊。”(《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他在他作為美國桂冠詩人而作的一次演講中聲稱:“詩歌不是一種娛樂方式,就某種意義而言甚至不是一種藝術形式,而是我們的人類學和遺傳學目的,是我們的語言學和進化論燈塔。”(《一個不溫和的建議》)閱讀詩歌,也就是接受文學的熏陶和感化作用,這能使人遠離俗套走向創造,遠離同一走向個性,遠離惡走向善,因此,詩就是人類保存個性的最佳手段,“是社會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險形式;它是一種針對狗咬狗原則的解毒劑;它提供一種最好的論據,可以用來質疑恐嚇民眾的各種說詞,這僅僅是因為,人的豐富多樣就是文學的全部內容,也是它的存在意義”(《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與一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一個讀過狄更斯的人就更難因為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而向自己的同類開槍”(《表情獨特的臉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羅茨基在本書中不止一次地引用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題,即“美將拯救世界”(beauty will save the world),也不止一次地重申了他自己的一個著名命題,即“美學為倫理學之母”(aesthetics is the mother of ethics)。布羅茨基在接受諾貝爾獎時所做的演說《表情獨特的臉龐》是其美學立場的集中表述,演說中的這段話又集中地體現了他的關於藝術及其實質和功能的看法:
就人類學的意義而言,我再重複一遍,人首先是一種美學的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的生物。因此,藝術,其中包括文學,並非人類發展的副產品,而恰恰相反,人類才是藝術的副產品。如果說有什麼東西使我們有別於動物王國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語言,也就是文學,其中包括詩歌,詩歌作為語言的最高形式,說句唐突一點的話,它就是我們整個物種的目標。
一位研究者指出:“約瑟夫布羅茨基創作中的重要組成即散文體文學批評。儘管布羅茨基本人視詩歌為人類的最高成就(也大大高於散文),可他的文學批評,就像他在歸納茨維塔耶娃的散文時所說的那樣,卻是他關於語言本質的思考之繼續發展。”(列翁語,見俄文版《約瑟夫布羅茨基:創作、個性和命運》一書第237頁)關於語言,首先是關於詩歌語言之本質、關於詩人與語言之關係的理解,的確構成了布羅茨基詩歌“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他將詩歌視為語言的最高存在形式,由此而來,他便將詩人置於一個崇高的位置。他曾稱曼德施塔姆為“文明的孩子”(child of civilization),並多次復述曼德施塔姆關於詩歌就是“對世界文化的眷戀”(тоска по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е)的名言,因為語言就是文明的載體,是人類創造中唯一不朽的東西,圖書館比國家更強大,帝國不是依靠軍隊而是依靠語言來維繫的,而詩歌作為語言之最緊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組合形式,無疑是傳遞文明的最佳工具,而詩人的使命就是用語言訴諸記憶,進而戰勝時間和死亡、空間和遺忘,為人類文明的積澱和留存作出貢獻。但另一方面,布羅茨基又繼承詩歌史上傳統的靈感說,誇大詩人在寫作過程中的被動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們:詩人是語言的工具。“是語言在使用人類,而不是相反。語言自非人類真理和從屬性的王國流入人類世界,最終發出這種無生命物質的聲音,而詩歌只是其不時發出的潺潺水聲之記錄。”(《關愛無生命者》)“實際上,繆斯即嫁了人的'語言'”,“換句話說,繆斯就是語言的聲音;一位詩人實際傾聽的東西,那真的向他口授出下一行詩句的東西,就是語言。”(《第二自我》)布羅茨基的諾貝爾獎演說是以這樣一段話作為結束的:
寫詩的人寫詩,首先是因為,詩的寫作是意識、思維和對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個人若有一次體驗到這種加速,他就不再會拒絕重複這種體驗,他就會落入對這一過程的依賴,就像落進對麻醉劑或烈酒的依賴一樣。一個處於對語言的這種依賴狀態的人,我認為,就可以稱之為詩人。
最後,從布羅茨基在《悲傷與理智》一書中對於具體的詩人和詩作的解讀和評價中,也不難感覺出他對某一類型的詩人及其詩作的心儀和推崇。站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講壇上,布羅茨基心懷感激地提到了他認為比他更有資格站在那裡的五位詩人,即曼德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弗羅斯特、阿赫馬托娃和奧登。在文集《小於一》中,成為他專文論述對象的詩人依次是阿赫馬托娃(《哀泣的繆斯》〈The Keening Muse〉)、卡瓦菲斯(《鐘擺之歌》〈Pendulum's Song〉)、蒙塔萊(《在但丁的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Dante〉)、曼德施塔姆(《文明的孩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沃爾科特(《潮汐的聲音》〈The Sound of the Tide〉)、茨維塔耶娃(《詩人與散文》〈A Poet a....
目次
目錄
譯序/劉文飛
戰利品
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或曰浮起的橡實
一個和其他地方一樣好的地方
表情獨特的臉龐
受獎演說
旅行之後,或曰獻給脊椎
第二自我
怎樣閱讀一本書
頌揚苦悶
克利俄剪影
體育場演講
一件收藏
一個不溫和的建議
致總統書
悲傷與理智
向馬可奧勒留致敬
貓的“喵嗚”
求愛於無生命者
九十年之後
致賀拉斯書
悼斯蒂芬斯彭德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