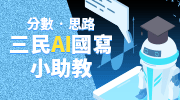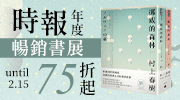世界名著典藏(名家全譯本):老人與海(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世界名著典藏
ISBN13:9787511724670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作者:(美)歐內斯特‧海明威
譯者:張熾恆
出版日:2024/10/25
裝訂/頁數:平裝/146頁
規格:20.8cm*14.6cm (高/寬)
版次:1
商品簡介
《世界名著典藏:老人與海》塑造了人類文學史上一個平民英雄的形象。古巴老漁夫圣地亞哥出海八十四天都一無所獲,但他卻并未絕望,最終釣上了一條大魚。他和大魚在海上搏斗了三天,才將魚殺死,并將其綁在小船的一側。歸程中大魚一再遭到鯊魚的襲擊,回港時就只剩下了脊骨和尾巴。它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學中的突出地位,這篇小說相繼獲得了1953年美國普利策獎和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
《世界名著典藏:老人與海》這本書,不僅可以讓你認識到一位在生活的重壓下依然保持優雅風度的老人,一個在精神上不可戰勝的硬漢子,更能讓你感受到深刻的人生體驗和莊嚴的生命經歷,以及一個人完美而崇高的人格和永不言棄的精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海明威(1899—1961),美國作家和記者,被認為是20世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海明威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他被譽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并且是“新聞體”小說的創始人。1954年,他因《老人與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譯者簡介:
張熾恒,詩人,有詩集《蘇醒與寧靜》出版。著名翻譯家,有經典文學譯著多種(近50個版本)在大陸和臺灣出版,涵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和童話,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布萊克詩集》《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全集》《泰戈爾詩選》《老人與海》和菲茲杰拉德小說選。
書摘/試閱
他是个独自驾一只小帆船1在湾流2上捕鱼的老人。到今天为止,老头儿已经接连下海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捕到。前四十天里,有个男孩陪着他。可四十天一无所获之后,孩子的爹妈对他说:这一阵子老头儿肯定是兜底交上霉运了。那是坏运气里面最厉害的一种。遵父母之命,孩子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礼拜他们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看见老头儿每天回来时小帆船里空荡荡的,男孩心里面难受。他总是下去帮老头儿拿东西,或者是钓索卷儿,或者是钩鱼竿3、鱼叉和卷裹在桅杆上的帆。那面帆用面粉口袋片打了补丁,卷起来时仿佛一面象征永远失败的旗。
老头儿身形单薄瘦削,脖梗子上皱纹很深。从他的腮帮子上一溜顺着颊边往下,长着些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出来的良性皮肤瘤。他那双手则因为同大鱼较量,被钓索勒出了深深的伤痕。不过没有一道伤疤是新的。它们已年深日久,如同无鱼的荒漠中岁月侵蚀所形成的地貌。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显得老迈,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同海水一样蓝,带着愉快的、毫不沮丧的神采。“桑地亚哥,”小帆船被拖到了岸边,他们往上爬时,男孩说道,“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出海啦。我们家已经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头儿教会了孩子捕鱼,男孩很爱他。
“不,”老头儿说,“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待着吧。”
“可是你记得吗,你曾经八十七天没逮到一条鱼,接下来三个礼拜我们却天天捕到大鱼。”
“我记得,”老头儿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动摇了才离开我的。”
“是爹爹赶我离开你的。我是个孩子,得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头儿说,“这很正常。”
“他不怎么有信心。”
“是,”老头儿说,“可我们有,是不?”
“是的,”男孩说,“先去露台饭店,我给你买杯啤酒,然后再把东西拿回家,好吗?”
“我就不客气了,”老头儿说,“打鱼人酒不分家嘛。”
他们走进露台饭店,坐了下来。不少渔夫拿老头儿打趣,他并不生气。还有些渔夫,那些上了年纪的,眼睛看着他,心里为他难受。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斯斯文文地聊湾流,聊他们把钓索漂下去有多深,聊持续不变的好天气和最近经历的事情。当天有收获的渔夫都已经返回,各自将马林鱼剖开,满满地平摊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端各有两个人扛着,摇摇晃晃地抬到收购站去,在那儿等冰柜货车将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而捕到鲨鱼的人已将所获送进小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场,那儿的人把鲨鱼吊在滑车上,取出肝,割下鱼鳍,剥去皮,肉切成一片一片,准备腌制。
刮东风的日子里,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场会飘过来一股子味儿。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气味,因为风转而向北刮去,且又渐渐平息了。露台饭店外阳光明媚,令人怡悦。
“桑地亚哥。”男孩儿说。
“唉。”老头儿应道。他正握着酒杯,回想多年前的事。
“我去给你弄点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吗?”
“不用了。你去玩棒球吧。我仍然有力气划船,罗杰里奥会帮我撒网的。”
“我想去。我不能和你一起捕鱼,就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你已经给我买了一杯啤酒,”老头儿说,“你是个男子汉啦。”
“你第一回带我上船,我多大?”
“五岁。那天我拖上船的鱼太生猛了,它几乎把船折腾成碎片,害你差点丢了小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啪嗒啪嗒地拍打,横座板也被拍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我被你扔到船头,待在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旁边,感觉到整个船在颤抖。你用棍子揍它的声音就像砍倒一棵树,甜丝丝的血腥味儿罩住了我全身。”
“你是真记得,还是因为我跟你说过才知道的?”
“从我们第一次一起下海起,每一件事我都记得。”
老头儿用他那双久经太阳灼晒的眼睛看着他,目光里深信不疑,充满了爱。
“假如你是我自个儿的小子,我会带你出海去赌赌运气的,”他说,“但你是你爹你妈的,而且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好吗?我还知道去哪儿弄四条鱼饵。”
“我自己有,今天剩下的。我给它们抹了盐,放在盒子里。”
“还是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头儿说。希望和信心从未在他心中消失过,此刻更是焕然一新,如同乍起的微风。
“两条吧。”男孩儿说。
“就两条,”老头儿同意了,“不是偷来的吧?”
“就算去偷我也愿意,”男孩儿说,“但那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头儿说。他心地单纯,不会去琢磨自己怎么就到了如此谦卑的程度。但他知道自己到了谦卑的程度,而且知道这并不丢人,不会给真正的自尊心造成任何伤害。
“看这湾流,明儿会是个好天。”他说。
“明天你去哪儿?”男孩儿问。
“去远海,风向转了再顺风回来。天亮前我就出港。”
“我想法子叫船主人也跑远些,”男孩儿说,“那样你如果钓到真正的大鱼,我们就可以过去帮你了。”
“他不肯跑太远的。”
“是的,”男孩儿说,“可我能看到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一只追鱼群的鸟儿,那我就可以叫他跟着鲯鳅往外跑了。”
“他的眼睛已经那么不好使?”
“差不多成瞎子了。”
“奇怪,”老头儿说,“他又从来不曾捕过海龟。那才是伤眼睛的活儿呢。”
“可是你去莫斯基托斯海岸捕海龟好多年,眼睛还是好好的。”
“我是个怪老头儿。”
“可你如今还有足够的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还行吧。我还有不少窍门可以用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男孩儿说,“然后我要拿手撒网去捉沙丁鱼。”
他们从小船上拿起渔具。老头儿将桅杆扛在肩上,男孩儿抱起木箱,里面装有一卷一卷编得很结实的钓索,又拿了钩鱼竿和带柄的鱼叉。装鱼饵的盒子放在小帆船的船尾板下面,盒子旁边那根棍子是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的。没人会偷老头儿的东西,但还是把船帆和粗钓索拿回家的好,因为让它们沾露水是有害处的。再说,老头儿虽然拿得准当地人绝不会对他下手,他还是认为,没必要把一根钩鱼竿和一柄鱼叉留在船上,诱惑别人。
他们顺着道儿一同走到老头儿的棚屋跟前,进了敞开的门。老头儿将裹着船帆的桅杆靠放在墙上,男孩儿把箱子和其他渔具放在它旁边。桅杆差不多跟这座单间的棚屋一样长。屋子是用大椰子树坚韧的苞壳造起来的,那玩意儿叫作“海鸟粪”。屋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泥地上一处用木炭做饭的地方。墙壁是拿纤维很结实的“海鸟粪”苞壳片压平了,交叠着镶砌成的。墙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帧《科布雷圣母像》。这些画儿是他妻子
的遗物。从前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妻子的着色照片,但被他取下来了,因为他看在眼里,心里面就凄凉得受不了。如今它放在墙角的搁板上,用一件干净衬衫罩着。
“你有啥吃的吗?”男孩儿问。
“一盆子鱼拌黄米饭。你也吃一点吧?”
“不了。我回家去吃。我帮你生火好吗?”
“不用啦。待会儿我自己生。吃冷饭也不要紧的。”
“那我把手撒网拿走啦?”
“好的。”
手撒网并不存在。手撒网是什么时候卖掉的,男孩儿记得很清楚。但他们照常每天将这套子虚乌有的把戏演一遍。一盆子鱼拌黄米饭同样是虚构的,这个男孩儿也心知肚明。
“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老头儿说,“你想看见我逮一条去掉下水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回来吗?”
“我拿手撒网去捞沙丁鱼。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我想读一读棒球赛的消息。”
男孩儿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属子虚乌有。但老头儿从床底下把它拿了出来。
“是佩德里科在饭店里给我的。”他解释道。
“我捞好沙丁鱼就回来。我会把我们俩的鱼放一起冰镇着,明天早上再分。等我回来,你给我说说棒球赛的消息。”
“扬基队不可能输的。”
“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要对扬基队有信心,我的孩子。想一想大将迪马吉奥吧。”
“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也担心底特律老虎队。”
“慎着点,不然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色萨克斯队你也要担心啦。”
“你下点功夫,等我回来讲给我听。”
“你觉得我们该不该买张尾号八十五的彩票?明儿可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买,”男孩儿说,“可你的了不起的纪录是八十七,就买八十七好么?”
“不会两次都八十七的。你估摸着你能弄到一张尾号八十五的吗?”
“我去预订一张。”
“一张。那就是两块五哟。这笔钱我们向谁去借呢?”
“这不难办。两块五我随时都借得到的。”
“估摸着我也能借到。但我是尽量不借债的。开了借债的头,讨饭日子在后头。”
“穿暖和点,老爹,”男孩儿说,“现在可是九月份了。”
“正是来大鱼鱼汛的月份,”老头儿说,“换了五月份,全是好渔人。”
“我这就去捞沙丁鱼。”男孩儿说。
男孩儿回来的时候,老头儿在椅子里睡着了。太阳下了山。男孩儿从床上拿来旧军毯铺在椅子背上,盖住老头儿的肩膀。真是很奇怪的两个肩膀,老头儿尽管老了,却依然强健。老头儿的脖子同样很壮实,此时他的脑袋向前耷拉着,脖梗上的皱褶就不怎么明显。他的衬衫补过许多回,弄得就跟那面船帆似的。那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一块一块深浅不一。老头儿的脑袋很苍老了,眼睛闭上时,脸上便了无生气。报纸摊放在他膝头,被他的一只胳膊压住,在晚风中才没被吹走。他赤着脚。
男孩儿撇下他离开了。回来的时候,老头儿依然睡着。
“醒醒,老爹。”男孩儿说,将手放在老头儿一只膝盖上。
老头儿睁开了眼睛,有一会儿,他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似的。然后他露出了笑容。
“你弄到什么了?”他问。
“晚饭,”男孩儿说,“我们该吃晚饭了。”
“我还不是很饿。”
“快吃吧。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呀。”
“我曾经这样干过。”老头儿边说边起身,拿起报纸折好。然后他开始叠毯子。
“把毯子裹在身上吧,”男孩儿说,“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你饿着肚子去打鱼。”
“那你得长命百岁,好好保重自己,”老头儿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米饭,煎香蕉,还有点儿炖菜。”
饭菜装在双层金属盒里,是男孩儿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两副刀叉和汤匙各用一张餐巾纸包着,装在他口袋里。
“这是谁给的?”
“店主马丁。”
“我得跟他说声谢谢。”
“我已经说过了,”男孩儿说,“你不必再去啦。”
“我要把一条大鱼的肚子肉送给他,”老头儿说,“他这样帮我们不止一回了吧?”
“没错。”
“那除了鱼肚子肉以外,我还要另外送他一点儿东西。他对我们非常体贴的。”
“他送了两瓶啤酒。”
“我最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可这是瓶装的阿图埃伊牌啤酒,喝完我把瓶子送回去。”
“劳烦你了,”老头儿说,“我们开吃吧?”
“我早问过你啦,一直在等着呢,”男孩儿轻声款语地说,“我想等你准备好了,再打开饭盒。”
“现在我准备好了,”老头儿说,“刚才去洗手耽误了点时间。”
男孩儿心里面说:你去哪儿洗的呢?村子里的供水处在前面路边,跟这儿隔两条街呢。男孩儿心想:我该给他捎点水来的,外带一块肥皂,一条像样的毛巾。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呢?我得再给他弄一件衬衫,准备一件过冬的外套,搞一双什么鞋子,还要加一条毯子。
“炖菜味道好极了。”老头儿说。
“给我说说棒球赛吧。”男孩儿请求道。
“我说过的,美国联赛就数扬基队了。”老头儿快活地说。
“今天他们输了。”男孩儿告诉他说。
“这算不上什么。大将迪马吉奥重振雄风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队员呢。”
“那是自然。可他是关键人物。要说别的组,在布鲁克林队和费城队中间,我本该选布鲁克林队的。可转念一想,我又想到了迪克·西斯勒,想起他在老公园击打出的那几个了不起的好球。”
“那几球可真是没得比。我从没见过谁击打出那么远的球。”
“你还记得他常来露台饭店的那些日子吗?我曾经想带他出海捕鱼,可我太腼腆了,没敢开口。我叫你去请他,你也不敢。”
“我知道。真是错过了大好机会哟。兴许本来他有可能跟我们去的,那样我们就一辈子有得咂摸了。”
“我想带大将迪马吉奥出海捕鱼,”老头儿说,“听说他爹也是个渔夫。兴许他曾经跟我们一样是穷人,能理解我们的心意。”
“大将西斯勒他爹可绝不是穷人,他在我这个年纪,我说的是老西斯勒,就已经在大联赛上打球了。”
“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站在开往非洲的一条横帆船的桅杆前面。我看见过黄昏时沙滩上的狮子。”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的。”
“我们聊非洲呢还是聊棒球赛?”
“还是聊棒球赛吧,”男孩儿说,“给我说说大将约翰·J.麦克格劳。”他把J念成了“乔塔”。
“早年有段时间他也常来露台饭店。但他一杯酒下去,人就变得粗野,说话很难听,不好相处。他的心思用在赛马上不比用在棒球上少。至少他是整天把赛马名册揣在口袋里的,他经常在电话里提到赛马的名字。”
“他是个大经理,”男孩儿说,“我爹认为他是最大的。”
“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头儿说,“假如杜罗歇接连好几年都来这儿,你爹也会认为他是最大的经理。”
“那说真格儿的,谁是最大的经理呢,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觉得他们分不出高低。”
“最好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Que Va,”男孩儿说,“好渔夫有很多,很棒的也有那么几个,可最好的只有你一个。”
“谢谢你。你说得我很开心。希望别来一条太大的鱼,把我们俩给否了。”
“没那样的鱼,只要你的力气还像你说的那么大。”
“我的力气兴许已经没我想的那么大了,”老头儿说,“但我知道许多窍门,而且我有决心。”
“现在你该上床睡觉了,睡足了明天早晨才有精神。我把东西送回露台饭店去。”
“那就晚安吧。明天早晨我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男孩儿说。
“我的闹钟是岁数,”老头儿说,“老人为什么醒那么早?为了过上更长的一天吗?”
“我不知道,”男孩儿说,“我只知道小孩子睡懒觉,睡得沉。”
“我不会忘的,”老头儿说,“我会及时叫醒你。”
“我不喜欢船主人来叫醒我。就好像我不如他似的。”
“我知道。”
“好梦,老爹。”
男孩儿走了。刚才他们吃饭时,桌上也没个灯,这时老头儿摸黑脱掉裤子,上了床。他把裤子卷起来,将那张报纸塞在中间,做成个枕头。他将毯子裹在身上,在铺着另外一些旧报纸的钢丝弹簧床上睡了下来。
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他梦见了自己还是个男孩儿时见到的非洲,绵长的金色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还有高高的海岬和巨大的褐色山峦。如今,每天夜里他都回到那一带海岸,在梦里听见海浪的轰鸣,看见当地一只小船从浪涛间驰骋而来。他睡着时能嗅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还有清晨陆地上吹来的风所挟带的非洲的气息。
通常他嗅到陆地上吹来的风就会醒来,穿上衣服,去把男孩儿唤醒。不过今夜陆地风的气息来得特别早,他在梦里知道时间还早,就继续把梦做下去。他见到岛屿的白色峰峦从大海上升起,接着又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泊锚处。
他的梦里不再有暴风雨,不再有女人,不再有大事件,不再有大鱼,不再有打斗和角力,也不再有他的老婆。如今他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像小猫一样在薄暮中嬉戏,他爱它们像爱那个男孩儿。他从来不曾梦见过男孩儿。他就那样醒了,透过敞开的门望着月亮,将裤子摊开来,穿上。他走到棚屋外面撒了一泡尿,然后就顺着道儿走去叫醒男孩儿。在凌晨的寒气中他直打哆嗦。不过他知道,打打哆嗦会暖和起来,而且没多久他就要划着船儿出海了。
男孩儿家的门没上锁,他轻轻地推开门,赤着脚悄悄走了进去。男孩儿熟睡在前屋里一张帆布床上。月亮正在淡出天幕,借着透进屋子的月光,老头儿能清楚地看见他。老头儿轻轻拿起男孩儿一只脚,握在手里,男孩儿被弄醒后转过脸来望着他。老头儿点点头,男孩儿从床边椅子上拿起裤子,坐在床沿上,将裤子穿上。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