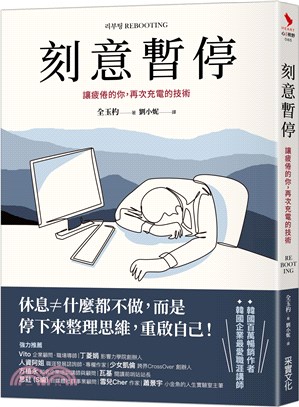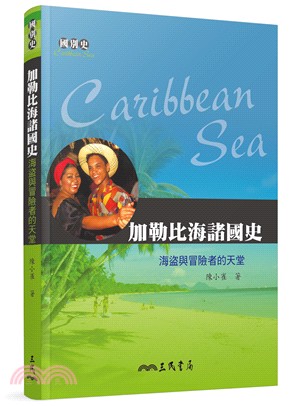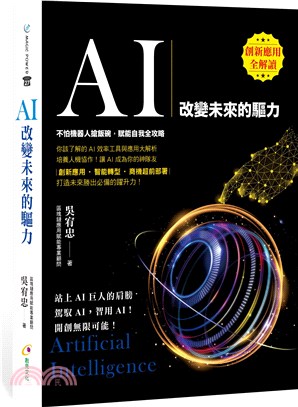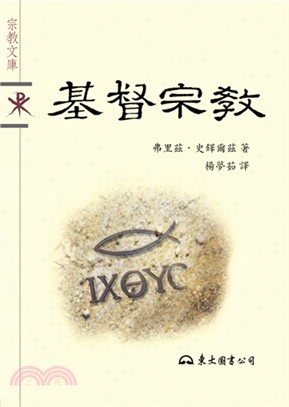商品簡介
《戀人與鐵》收錄了楊典39篇短篇小說,整體而言除了延續《惡魔師》《鵝籠記》的部分氣息外,本書的寫作傾向主要來自對生命流逝或愛的焦慮,以及探究什麼才是文學“推動”的問題。
“戀人”通常指的是人性中的羅生門、棱鏡或移動的變壓器,這個概念是私人的、隱秘的,同時也是反抗的,是屬於大歷史的名詞。萬事皆有理可循,唯愛情(戀人及對戀人的幻想)可以毫無道理——無端的愛,先驗的愛,隱秘的愛,變態、畸戀、惡趣、絕望與毀滅的愛,乃至不分男女、不分動植物與時空異化的愛。在智力遊戲與純敘事化小說甚囂塵上的時代,“愛”是個已腐爛的字。
《戀人與鐵》恰恰是為了能降解這種失敗與誤解。
作者簡介
楊典(1972—),作家、古琴家、畫家,代表作有小說集《惡魔師》《鵝籠記》《懶慢抄》《鬼斧集》;隨筆集《隨身卷子》《孤絕花》《琴殉》《肉體的文學史》;詩集《女史》《麻醉抄》等。
名人/編輯推薦
戀人就是可以將幾十年濃縮到一個下午的人。而人間那些夫妻,不過是將一個下午稀釋成了幾十年的人。
萬事皆有理可循,唯愛情可以毫無道理。——楊典
序
序
鹽與蜂的文學
萬家禁足期間,寂寞京城又下了雪。自凌晨至午後,鱗甲紛紛,江山盡瘦。已忘了這是今冬第幾場雪了。寒氣逼人下,潛心寫作以御寒,自然又饞起酒來。可旋即便想起陸務觀之句“中年畏病杯行淺,晚歲修真食禁多。謝客杜門殊省事,一盂香飯養天和”之類,倒句句都是過來人的話,只得寫字佯醉而已。窗前靜觀鵝毛時,為聊補遺憾,便學乾坤一腐儒之窮酸,小賦半闋曰:“佚詩難覓追病國,饞酒不得賽相思。鵲剪寒林分疏密,雪掩群魅未舞時。”寫舊詩,真算是沒有用之事。恰若莊南華山木與鳴雁,普魯斯特躲在家裡敘述他那些隱秘的、本無人會關心的少女與韶光。文學或詩大概本來就是“沒有用的”。就像這窗外要風景何用?房子夠住就行了。愛情何用?能繁殖就行了。美食何用?能吃飽就行了。尊嚴何用?能活著就行了。可那種看上去沒什麼實際之用,而又從生命本身中靜水流深,或劇烈迸發出來的東西,或許又是人所必需之物。
傳說1187年,埃及蘇丹薩拉丁在攻占十字軍占據的耶路撒冷後,兩邊軍隊都死人無數,城市也千瘡百孔,斷壁殘垣,只剩下一堆石頭。人問薩拉丁,犧牲這麼大,你要這麼一座破城空城到底有什麼用,有何價值?薩拉丁攤開雙手笑道:“一文不值。”然後忽然又交叉雙手道:“無價之寶。”耶路撒冷,便是文學。
據說,只有六十二歲的海明威曾拿著自己的一摞小說對人道:“什麼文學,這就是一堆字而已,一堆字,對於真生活來說毫無意義。”然後放聲大笑,走回屋裡,用腳丫扳動了塞在嘴裡的獵槍。鯊魚與海沒有消滅老人,巴黎的流動盛宴、兩次飛機墜落、拳擊、斗牛、乞力馬扎羅雪山上的豹子或戰場上的武器與喪鐘,毫無功績的前克格勃間諜身份等,也沒有消滅這位故作強者的愛達荷州第五縱隊“老兵油子”,他每天太陽照常升起,喝酒釣魚。但終的才思枯竭、負傷引起性功能問題(有爭議)、父親的影響與晚年的疾病、電療、抑鬱症與記憶力衰退等,卻提前要了他的命。他曾說過:“死在幸福之前光榮。”海明威生前早已聞名天下,榮譽、金錢與地位全都享有,可文學雖然對現實生活沒意義,那沒有文學的現實生活,卻更沒意義。幻想與健康,便是文學。
對太宰治而言,無數次地重復殉情於絕望,便是文學。
對川端康成而言,打開煤氣閥後仍然沉默無語,不留一個字而去,便是文學。
對薩德而言,在監獄與大革命的封閉中,秘密地去虛構那些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其實根本無用的色情行為,便是文學。
對自幼與兄長一起抄遍中外群書的周知堂而言,“我一生著作不足掛齒,唯晚年所譯之希臘對話錄勉強可讀”,這著作等身卻又無牽掛之精神,便是文學。
宋人蔡絳《西清詩話》曾載杜少陵之言:“作詩用事,要如釋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鹽有用,水更有用,而那無用的,卻不能單獨拿出來的咸味,便是文學。
《景德傳燈錄》曾載神贊禪師,一日見其師於燈下讀經,忽然有一只蜂急觸窗紙,滿室求飛,乃云:“世界如此廣闊,不肯出,鉆他故紙,驢年去得。”又偈云:“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大癡。百年鉆故紙,何日出頭時?”此蜂、此驢、此鉆,便是文學。
文學並不一定是已出版之書,更非文學之盛名。即便成王敗寇論合理,也不能完全抵消心性之所求。文學對於愛文學者而言,只是某種與身俱存亡的本能,拿出來說,或一錢不值,放在心裡則又瞬息萬變。故見近日有人在談什麼“當代文學無革命”,還順便把我也劃到“文學革命”或“文學不革命”的任何範疇裡,這都是錯誤的。我跟整體性寫作傾向、代際劃分、流派、風格或批評家們所設定的各種山頭都毫無關係。我的寫作純屬家教失誤與個人行為:大多固執、渺小、獨立地寫了很多傲慢與荒唐的字,基本上又全是些偏見、惡趣與怪癖。我寫的書都是些閑書,沒什麼用,故我是可以被大眾忽略的,唯願不會被大時間遺忘,就算萬幸了。
不知不覺,又到今年新書付梓時刻。祖佛共殺,唯留天地敬畏;縱浪大化,仍須小心翼翼。文學上的道理也差不多吧,即凡事不做便都簡單,一句話就可以否定之。真做起來才知道前人之辛苦偉大處。人都有局限。即便不高山仰止,也會對創造者的某種困境、局限與不得已心領神會。
當代漢語寫作,類型化的東西太多。現在比我更年輕的一代,對那種智力遊戲式的,靠機巧構思、科學幻想或錯覺陷阱等編織的長短篇小說,皆駕輕就熟。譬如用量子力學來杜撰複雜的推理故事,用星際穿越來反觀人類的渺小等。此類小說出現時也會引人入勝,因漢語此類作品過去不多。但不知為何,我總是覺得,這種對純粹智力與技術的偏好終也不會太長久。當然,此類小說我也寫,不過本質卻有所不同。我相信,好的小說,除了智力與技術等之外,重要的還是作者骨子裡必須要有一種元初的本能,一種不可抑止的叛逆勁頭,一種從心中迸發出來的內在激情,才能真正抵達。生命狀態不僅是文學護身符,我也視此為一切偉大文學之“推動”。若沒這個東西,恐怕再聰明狡猾的寫作,終仍會淪為機械的公式與麻木的敘述,化為某個時代語言形式的過眼煙云吧。
慚愧,我也並非想在此作什麼“文學批評”。竊以為很多對當代漢語寫作作批評者,也習慣性地喜歡指點江山。此歷代通病,毋庸贅言。群體爭鳴的意義再大,也會小於一部真正的好作品出現。四十年來,乃至一百多年來,此類泛泛之批評亦太多。而文學本是必須“小中見大”的私人心中的秘密宇宙觀。我是那種相信用一本好書(包括閑書或未完成之書),就足可代表一個時代,乃至一種文化模式的人。文學本不需要搞成鋪天蓋地的社會思潮與普遍觀點(當然,若實在有此嗜好,也有其自由,但並不是重要)。譬如,一本始終沒有作者真相的《金瓶梅》,也可以代表明人寫宋人,乃至寫整個中國人之歷史景觀了。再譬如,若只能選一位二十世紀的西方作家,那卡夫卡便幾乎可以代表整個二十世紀之作家。因他的作品(其日記書信也是小說)就是他這個人,而被他寫到的那些小說人物倒是次要的。這並不是說,同代就沒有別的偉大作家。二十世紀的好作家多如牛毛。但於文學性本身,則不需要拉大旗作虎皮式地全都羅列出來,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否則加繆或馬爾克斯也很好,索爾仁尼琴或科塔薩爾也可以,馮內古特、卡爾維諾或川端康成的掌小說當然無可挑剔,喬伊斯、赫胥黎、喬治·奧威爾、塞林格、舍伍德·安德森、貝克特、魯爾福、納博科夫、拉什迪、卡達萊、帕維奇、庫切、聚斯金德或波拉尼奧等等也都嘆為觀止,那就沒完沒了了。各國文學都是群峰,而越全面,就越有明顯的缺陷,越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如從博爾赫斯到埃科的很多作品,在我看來也只能算是“第二經驗”之寫作。只有完全從個體衝決網羅而出之文學,因內心感受達到沸點而突然發明之文學,以及文學對個體生命之“無用性”,才接近我所認定的高度。那是根本惡的高度,懷疑一切的高度,平常心的高度,同時也是透徹愛、性、夢與死的高度。這就像戀人的痛苦作為現象很普遍,作為概念也人人都懂,但唯有每個人自己那些不可替代的,即純粹屬於私人戀愛經驗裡的痛苦,才是真實的。
文學必須是個人的,所以才會各有所好。簡而言之:“文學就是我,我就是文學。”唯有個人才是包容的,集體則往往會是一致排外的。寫作,無論顛覆傳統與否,創新、解構或將某種觀念推到極致與否,具有現代性或批判性與否,便一定要作用於社會與世界嗎?就不能是冷僻的、私人的,甚至關於一顆被封閉之內心的反映嗎?文學可以包括社會學,但不一定或根本就不是任何社會學。它們可能會同時存在,但互相之間又毫無關係。很多作家,生前何曾引起過什麼社會思潮或集體效應?他們茍活於他們的時代表象下,本都是些毫無用處、潦倒、污名化,甚至是卑賤如塵土的邊緣人。他們的寫作完全是出自私人的嗜好,就像被語言霸占了血汗的賭徒。的確,寫作就像宗教,或一場不切實際的奇異愛情,是一種成熟到已經不思悔改的賭博。輸贏全無所謂了,只剩上癮,且很難戒掉。文學家癮發時無救,還會代入各種新發明的理由,他會破罐破摔,終變成一個敗家子。
好的文學正是從這悲慘的失敗、無奈的被忽略裡才得來的。
這本小說集名為“戀人與鐵”,乃因其中部分篇章,皆是以一位虛構(或以某個真人作鏡像)的少女或戀人為符號而寫。《說文》云:“孌,慕也。”即除了愛戀,還有景仰與羨慕之本義。戀,也許是某種難以言說的標準,即便是想象的標準。繁體的“孌”,從。在《說文》中,“”之本義為亂、治以及不絕等。故“戀”字足可以表達一種類似治亂交疊,起伏綿延的心情。《玉篇》云:“,理也。”可見混亂的內部也是有規律可循的。現代漢語的“戀人”一詞其實來自日語。特意用了這個詞,也是為了避免與諸如情人、愛人等在現代漢語中因諸多歷史語境之多義性而產生的誤讀。因日本文學也尤其重視女性的意義。“戀人”作為一個隱喻,一個獨立的修辭,過去也散見在我的很多作品中,無論詩還是小說。這並非僅僅是因我們八十年代都曾受到過羅蘭·巴爾特《戀人絮語》、克爾凱郭爾《誘惑者日記》或谷崎潤一郎《癡人之愛》等書的影響,更非因對張、胡、二周或喻血輪、姚靈犀等那一代作家的情感觀有什麼新的理解;也非如夏濟安先生在日記中說的那樣:“我對自然不大有興趣,我認為除女人以外,沒有美(Kierkegaard也有此感)。我要離脫了人世後,才會欣賞自然。我喜歡一個人住在荒山古廟裡,這不是為了自然之美,而是對人生的反抗。在此世界上,只有女人是美的。”(見夏志清《雞窗集·亡兄濟安雜憶》)寫作或有起因,但任何具象又都不是我寫作的目的。因這戀人也不僅僅指女人(亦非任何性別),而是觀念。我的“戀人”也可以是反抗人生或世界的。
寫這本書純是從我本身的觀念出發而作的一種嘗試。
記得早年次讀中國偉大的那本堪稱“戀人百科全書”即《石頭記》時,我也完全不懂為何這樣一本無聊、絮叨、脂粉氣,靠摔盆砸碗、喝茶寫詩、婆婆媽媽和唉聲嘆氣的書,會被稱為“中國古代小說成就”。三十歲以前都讀不下去。四十歲以後才漸漸明白,所謂成就,並非紅學或索隱派的論證史多麼綿長,也不是脂本與其他諸版本等的差異,而大概是指中國人在這裡,次有了“大旨談情”的勇氣。當年如果沒有《石頭記》,中國也照樣是中國。事實上就算有了這本書,中國也還是中國,中國人也還是那副黑色的樣子,永遠也不會變。但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言:“一個人在讀過《紅樓夢》之後,他的人和世界就會變得有點不一樣了。”我覺得這話是有道理的。因之前數千年的經史子集裡,都沒有正式談過愛的問題、戀人的問題。雖也有西廂牡丹桃花白蛇,老衲機鋒,列女悲苦,但還只是“臨去秋波那一轉”,托志於幽魂而已。甚至有了《金瓶梅》那樣偉大的“具有現代性的小說景觀”,大膽地寫了性與死,也仍缺了點什麼。是作為“戀人”的小說人物賈寶玉的出場告訴了我們,原來中國並不只是一個充滿經學文字與訓詁的準野蠻部落。原來我們不是只會帝王將相、打打殺殺、經學科舉、仙山俠隱。原來我們也有愛,且可以是無端端的愛,先驗的愛,隱秘的愛,變態、畸戀、惡趣、絕望與毀滅的愛,乃至不分男女,不分動植物與時空異化的愛。且中國人的愛、慕、戀、情、義等,也是一個連續性的,不一定會因情感關係結束便消失的情感邏輯關係。原來我們的文明與性欲並不只是為了一個只會傳宗接代、繁殖仕途匹夫的酋長國;原來我們的生命中有權表達對這個荒謬世界的理解,有權相信夢、敬畏美,為青澀幼稚的愛情說話,懷念大於整個人生的青春,維護弱小者或戀人的尊嚴與自由,反對既定的秩序與假設的倫理社會體系,並有權選擇對“無”的崇拜。原來“情不情”也可以是天經地義的。原來女性偉大。原來我們也是人。
前幾年,我也是因此才寫了《鵝籠記》裡的那篇《沁芳閘》。
“戀人”通常是人性中的羅生門、棱鏡或移動的變壓器。正如愛從沒有定義,甚至大部分時候是反的、偏的甚至惡的,故“戀人”這個概念在我的敘事中是私人的、隱秘的,同時也可以是反抗的,屬於大歷史的名詞。人本是缺陷與遺憾的產物。只有在戀愛中的人,哪怕是虐戀或失戀,才能明確感受到這種與生俱來的缺陷與遺憾,並有效地反抗它的壓迫。事實上歷代有一大部分暴亂、政變、屠殺乃至革命的秘密,都不過是為了愛情,或消解愛情的失敗。甚至很多哲學的出現,初也是哲學家為了給本人失敗的愛情“復仇”,便尋求用理性戰勝感性的寧靜。因萬事皆有理可循,唯愛情(戀人及對戀人的幻想)可以毫無道理。戀人是一枚不可理喻的反邏輯晶體。這也是性欲、革命與宗教都解決不了的。文學也是勉為其難,充其量只能算一種用來緩衝痛苦的替代品。
當然,寫小說本就是一件自討苦吃的事。
譬如,事實上歷來就有相當一部分讀者(甚至作家)都只看得懂,或只願意去看得懂寫寫“現實”的作品。稍微超前或抽象一點,能量大一點,語言升級一點,就會被看作是製造“閱讀障礙”或“不說人話”了。事實上寫作的重要性,從來就不是看寫作者能否熟練地表達現實或抽象、具體或荒誕、對愛與恨怎麼看、通俗社會問題與晦澀歷史觀念如何運用到故事裡、東西方語言傳統功底是否扎實、形式結構是否足夠先鋒,以及作品是否進入了現代性等這些細枝末節的事。文學主要就是看寫作者自己是否有平地而起,凌空創造一種思維方式的勇氣。文學可以獨立存在,所謂“千載已還不必有知己”。中國的大多數問題,都出在是否能創造、能理解與能包容不同的思維方式上。而中國文學的阻力,恐怕也並非來自“大眾不讀書”,而恰恰是一般讀者及自以為讀過點兒書,其實早已被某種傳統閱讀習慣洗腦的各類人裡。對文學廣度與深度的認知全憑天賦。比作家的天賦更重要的,是讀者的天賦。這個問題不是讀書多少能決定的。好在我是那種敢於冒犯讀者的寫作者。說到底,幾十年來,有沒有讀者都無所謂,何況還有一些。甚至對我的書全都是負面評論也沒關係。負面也是一種對創造性發生的興觀群怨。文學若形不成某種悖論,也沒意思。
再譬如,這個世界還需要長篇小說嗎?不是我給大家潑冷水,長篇我也在寫,也會出,但我真心覺得這世界大概已不需要長篇小說了。尤其是十萬字以上的長篇。很可能以後連中短篇小說都不需要。超短的筆記體,因與信息化同步,估計還能堅持一陣,看運氣吧。埃科當年說得有理:即便對那些歷史上的名著,以後的人也可能想要看故事梗概,或看縮寫本就行了,不需要再看完整的作品。寫得越厚,越是無用功,尤其漢語小說。對未來而言,傳統意義上的長篇小說編織得再複雜,形式再奇異,實驗性文本再先鋒或再具顛覆性,本質也已無真正的創造性。越長往往就越顯得土氣老套,就像被注水稀釋後的酒。長篇小說除非重新發明,否則長篇小說可以休矣。
好在《戀人與鐵》仍是短篇集,且在短篇集裡也只算是一本小書,很多篇幅很短。其中重要的篇章,大多來自今年上半年的寫作,另有二三篇修訂自過去從未出版過的舊稿。筆記體志怪“切夢刀”,則算是對《懶慢抄》的某種補充。整體而言,除了延續《惡魔師》《鵝籠記》的部分氣息外,本書的寫作傾向,主要還是來自對生命流逝或愛的焦慮,以及探究前文所說的,究竟什麼才是文學“推動”的問題。我們這一代,從小也都受過某種“仇恨教育”,並在暴力、冷漠與麻木中成長。習慣了叢林的殘酷與謀生的卑鄙之後,那陌生難學的東西,莫過於愛。中國人一般都不願意承認,愛的艱難遠勝於一切哲學或科學。即便承認,在文學裡,也都喜歡運用現實主義的形式,譬如寫寫具體的婚姻、外遇、禁忌或濫情等。但愛(戀人哲學)卻不一定是具體的。因愛會以其極度的快樂而抵達一種不快樂,就像教徒以宗教般的壓抑抵達一種痛苦的狂喜。而且,這秘密的喜悅再波瀾壯闊,也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裡清楚,不足為外人道。西詩所謂“苦難沒有認清,愛也沒有學成”。在現代生活中,“愛”字同時也代表著俗氣與淺薄的表達。在智力遊戲與純敘事化小說甚囂塵上的時代,“愛”是個已腐爛的字。只是每個人又都會不斷遭遇愛或被愛的襲擊,並常常慘遭失敗。中國歷代大多數現實的苦難、犯罪、沉冤、衝突與無奈,追根溯源也是來源於愛的失敗及對愛的誤解。只是因漢語傳統從來就沒有這個表達習慣,故只好用別的那些話語系統來詮釋而已。寫“戀人”也是為了能降解這種失敗與誤解。不過,無論我是假借眉間尺前傳、且介亭、契丹軍師、少年玄奘、棋手、拉迪蓋、籠中豹、博物館還是獅子樓,無論我寫的是古代志怪還是現實記憶,這廣義上的“戀人”之喻,都不該被任何概念所坐實。擬向即乖,這也是常識。人生在世,即便無寫作、無解釋,乃至沒有一句話可說,也會有一種巨大之激情,如水中鹽、窗內蜂,令每一位飲者自知,並從背後狠狠地推動著我們去感知存在與虛無的悖論,試圖從蒙昧的窗紙中鉆出去,哪怕是以頭撞墻。不是嗎?觀念先行時,詞語亦毀滅,是不是被稱作“文學”,又有什麼關係呢?
2021年1月—6月
目次
序 鹽與蜂的文學 ·001·
戀人與鐵 ·001·
且介亭之花 ·003·
洗墻
——“且介亭之花”續編 ·008·
寒暄
——或“嶄新的野蠻”(陰陽本) ·023·
草窗雨霽 ·029·
叛軍時代的繡花針 ·048·
點心 ·069·
一 ·071·
筋斗云
——或“群魔的玩笑” ·073·
隱形 ·079·
一窩猩紅的蛇 ·085·
停止簡史 ·090·
聖兵解
——或“燒尾宴”中的《龍龕手鏡》 ·096·
就義 ·117·
棍棒夢 ·120·
藩王的刺青 ·123·
單馱記 ·129·
坐臘 ·133·
巨匠(Demiurge) ·136·
中國斗笠 ·141·
敵人絮語
——十二世紀一位黑契丹軍師的幻術、兵法、畸戀與哲學手稿 ·145·
獅子樓客話
——作為詭辯、色相與哲學困境下的“微狂人日記” ·163·
新籠中豹 ·181·
壁虎 ·187·
一點不斜去 ·189·
吾友拉迪蓋 ·191·
衝刺 ·195·
焊槍 ·200·
誰是博物館中的血腥少女? ·203·
肉嶲 ·210·
麻袋
——或“一個現實問題” ·213·
指南車上的崔豹 ·221·
倒影與狗 ·225·
快 ·229·
發小 ·230·
金叉 ·231·
瀾 ·245·
獅吼九千赫 ·269·
切夢刀筆記(七十則) ·274·
一、髓焰之肉 ·274·
二、占婆圖書館 ·275·
三、哥德巴赫的飛翔姿勢 ·275·
四、叱咤女首艷本 ·276·
五、獨輪車之帆 ·276·
六、土耳其定向儀(突厥羅盤) ·277·
七、掌心雷 ·277·
八、切夢刀 ·278·
九、黑火 ·278·
十、青蚨與趙鵲 ·278·
十一、天廁之疑 ·279·
十二、機械女轱轆頭 ·280·
十三、人肉炮彈與占星術 ·280·
十四、悲喬葉哭 ·281·
十五、煮宮 ·281·
十六、過庭鰍 ·282·
十七、毛發的數量 ·282·
十八、羅眄的事 ·282·
十九、筷子豬 ·283·
二十、人 ·283·
二十一、左臂 ·284·
二十二、肺魚之象徵 ·285·
二十三、鬼敲鐘與郭子儀 ·285·
二十四、晉磚中的阿Q正史 ·286·
二十五、有物混成 ·287·
二十六、紙樓祭 ·288·
二十七、仙人彈琴 ·288·
二十八、Steam-punk話本人物造型 ·289·
二十九、羅襪 ·289·
三十、雨的朝代 ·289·
三十一、吞象奴 ·290·
三十二、阿拉伯移動光軌儀 ·290·
三十三、藏畫與納肝 ·290·
三十四、明月 ·293·
三十五、窄門、矮扉與懸關 ·293·
三十六、內經:宏大敘事小說 ·294·
三十七、名古屋泳骨 ·294·
三十八、衡功 ·294·
三十九、鴿叔 ·295·
四十、沒蹤跡處莫藏身 ·295·
四十一、鏡卜 ·297·
四十二、選擇派教義 ·297·
四十三、赤翼黑鰭 ·297·
四十四、魯迅號導彈 ·298·
四十五、蛋糕的日子 ·298·
四十六、六維與機器 ·300·
四十七、螃蟹 ·301·
四十八、海豹 ·301·
四十九、霍屯督陰唇 ·301·
五十、癭 ·302·
五十一、元儒 ·303·
五十二、黑能量 ·303·
五十三、云階 ·304·
五十四、乳房緩刑 ·304·
五十五、禿頂 ·304·
五十六、火柴占 ·305·
五十七、蛇入後庭 ·305·
五十八、啞兔 ·305·
五十九、提頭行者 ·305·
六十、巨型河童 ·306·
六十一、火地島“女食” ·306·
六十二、撒尿廟(或江紹原愛經九種) ·306·
六十三、講話 ·309·
六十四、王曠懷 ·309·
六十五、肩神 ·309·
六十六、肉胎 ·310·
六十七、霧大人 ·310·
六十八、獨目小僧與食睛 ·311·
六十九、海糧記 ·312·
七十、陽明土 ·313·
書摘/試閱
戀人與鐵
我昔日的戀人生下了一塊鐵,巴掌大小,楚國為之震驚。①此事她也沒告訴我。鐵就放在她宮殿的門檻上。每一個進出之人,都能看見,且必須從鐵上邁過去。鐵沒有父親。鐵是有形狀的。我因無法私下與她談論這一痛苦的形狀,故只能公開變成快樂的話癆,或偶爾靠踐踏山林,否定金屬取樂。往事肥遁後,我與戀人已很久沒說話了。戀人的沉默是正的,我的寂靜則是反的。這沉默與寂靜,就如把一雙用臟的手套從裡到外翻過來,形狀不變,左右互換,也還能戴。現在的人,都厭倦了喧囂。我記得前朝之猛士唐俟曾言:“我還期待著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那擺在門檻上的意外的鐵,便算是新東西嗎?喧囂與寂靜是一樣的嗎?這只有手套裡的手清楚。
戀人太年輕了,必須蠻橫無理。她與鐵緊密相連。她青春的惡與美,常泥沙俱下,對我的抽打狠如壯麗的鞭刑,其實根本沒法寫。如今勉強能寫,乃因我自己早已沒有了青春。雖說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也算一種安慰,但較之我對她與鐵的敬畏而言,仍是太難過、太抑鬱,並隔著一層痛失寂寞後的大時間中的傷心。
寫作只是為了聊勝於無鐵,為了免於崩潰。
亡國弒君之前,我常聽聞,戀人無事時,便會拿著那沉重的鐵,四處向人展示它有偉大的銹、迷人的尖。她可以白天把鐵吞進肚子裡,午夜再吐出來。她可以當街用鐵投擲她厭惡的人,非死即傷。只是她從不對我展示。獨處時,她還會伸出少女的粉舌,嘗一嘗那鐵。鐵是甜的。一塊殘酷的硬糖。鐵的出現,即便楚王也不理解。楚王從不知有我,正如我從不認為這人間有任何的王。戀人的沉默也是實心的無,高密度的無,因她從不解釋為何自己會產下這門瘋狂的玄學。作為她過去的一位秘密知己,我對鐵的邏輯,當然有自己的看法,只是無法對戀人說。楚國就是個罐頭,裡面四分之三是肉餡,只有四分之一是空氣,且是三十年前的空氣。不對她說,尚有文學。若說了,不僅文學會消失,恐怕連戀人都看不見了。盡管玄鐵後來會被玉璽、夢、冶金技術、鐵屋建築與武器等所霸占,足以傾倒天下,但我依然愛著這戀人的異化。出於對她與鐵的尊重,我寧願在這漆黑的罐頭裡像秒針一樣瘋狂旋轉,令時間不增不減,始終都像初次見到她時那樣。
那天,我戴著一副骯臟的手套,正在製造火,撰寫一本傳世韜略。可她忽然來了。剛看到她眼時,我便不禁暗自低頭流淚。我可以為她去做一切荒謬的事、殘忍的事甚至卑鄙的事。我根本不能理解我自己,故從頭至尾與她說話時,都是冷冰冰的。
2021年4月
且介亭之花
她已很久沒想起過那個留連鬢絡腮胡須的中國人了。他現在胡子都該白了吧?對她的少女時代而言,那是一段充滿歧視的偏見,是多年來被密封的壯烈遺憾。
十幾年前,就坐在那間舉世聞名卻荒草萋萋的破亭子裡,他便對她說過:“我現在覺得什麼都沒意思了,都麻木了。糧食、城市與豬也都是死的。”
她仰起頭又問:“怎麼會,愛情呢?”
“當然也是。”
“我倒不這麼覺得。”
“你年輕。你是圈外人。”
“那我們以後怎麼辦?”
“你可以回家,可以繼續寫詩。”
“你呢?”
“我事太多,你就別費心了。”
“這算是你的決定了?”
“談不上什麼決定,我們從來也沒真正在一起過。”
“可我剛才還挽著你的胳膊,在路上散步呢。”
“你多慮了,據我所知,這條街也是早就死了的。就算還有幾個活人,恐怕也沒有誰會注意我們的胳膊吧?”
中國人說著,低頭看了看少女的手。她的手便握成了拳,像一頭沮喪小鹿,離開了他胳膊修長的懸崖,朝衣袖的山洞中縮了回去。然後他又抬起頭看了看這破敗亭子的卯榫穹頂,以及掛在歪斜木柱上的斑駁對聯。可對聯寫的什麼,恐怕他一輩子也想不起來。
他只記得,且介亭漆黑瘦小,就立在馬路邊,像一個因多年站街而佝僂的蒼老娼妓。取這樣的亭名,大約也是因中國人都很熟悉吧。他們約到這裡見面,本是想避嫌。按照目前整座城市的瘋狂與危險,無論是兄妹、戀人或夫妻,都是不能見面的,也不必見面。他知道過去不過是一個時間圈套,是瘋子手中的黃金,很難面對。一面對就成了此刻,過去就被熔斷了,化了。唯有故意“不見面”和“近距離地回避”,可以勉強抵達這無限含蓄的深度。未來是膚淺的,只配拿來虛度;只有過去值得探索,而且深不見底,總是與此刻並行。況且戀人見面,都需要極其強大的、殘忍的克制力。見面還會毀了沒見面時的一切。搞不好見面之時,便是這整條街乃至城市被炸掉之時。好在且介亭是一座被忽略的廢墟,除了附近腌臜的野貓與渾身污泥的流浪狗,誰也不會進來打擾這不得已的見面。
“你送我的那幾本書怎麼辦?”她又問。
“可以轉送給李元,或者你的什麼同窗好友。”
“李元,你不是恨他嗎?”
“哪有的事。”
“我記得你這麼說過。”
“太準確的表達方式總會引起一些誤讀。友誼也是一種
誤讀。”
“那我們的那些信呢?”
“都燒掉吧。”
“燒?我舍不得。”
“又不是你的詩,有什麼舍不得?”
“就是舍不得。不想。”
“你是想得太多了。身外之物。”
“但這次真的不想。”
“難道你還要把那些信隨身攜帶嗎?”
“也可以寄存在李元那裡呀。”
“那更麻煩。誰知道那家伙會做出什麼來。”
“你還是不信他。”
“他倒不足掛齒。信會毀了你。”
“還有一個辦法。”
“什麼?”
“我可以把信寄回我老家去。”
“路上寄丟怎麼辦?現在發生什麼都有可能。”
“真丟失了,不也正是你想要的結果嗎?”
中國人聽到這裡,倒也不知怎麼回答了。他伸手看了看手表。
黃昏,一只翅膀被彈弓打殘了的燕子,這時正好落在且介亭的匾額上撲騰。它好像把巢築在了匾額的後面,隱約能聽見群燕嘰嘰喳喳之聲。
那些年,作為一位傲慢的、固執的少女,她始終在中國黑暗的地方為戀人寫詩。她那尖尖的、小小的腦袋,不知道為何總是會模仿性地寫出一些冷酷的大意象,如:“我尖銳的親吻是粉色的裝甲艦,闖入中國戀人腐爛的前額。”可惜,當年那位連鬢胡須尚黑的中國男子,暮氣太重,從來都不讀她的詩。她甚至都不能確定,他們到底算不算戀人。在且介亭幽會,他們後的對話是那麼平淡、無聊。他甚至還帶著些微的不耐煩。為了掩飾這中國式的尷尬,她只好從兜裡拿出一粒棕色發亮的硬糖,剝開印著中世紀藍色云紋圖案的糖紙,放到嘴裡慢慢吮著。吃糖也是他們過去常在一起時的嗜好。他從不抽煙,此刻則時不時地拿出手帕來輕輕擤一下鼻涕,或擦一擦鬢角的細汗。少女知道,中國人根本沒有感冒,不過就是想為這無言的戀人時光增加一些根本不值得懷念的動作。
直到後,當馬路盡頭已出現黑壓壓的人群與武器,他們才打起精神來。他握了握少女的手,示意她離開。情急之下他們有沒有擁抱,對此兩個人完全不記得了。
“那些人是衝你來的嗎?”她著急地問。
“應該是。”他並不著急,似乎早已等得夠了。
“那你快走吧。”
“我們朝相反方向走,分頭離開。”
“再也見不到了嗎?”
“不好說。”
“如果活著,你還會回家嗎?”
“也不好說。你別去找我。”
“以後……我是說以後,我怎樣做才能記得起你的臉?”
“也可以不記得。”
“怎麼會?”
“不記得是好事。對我的記憶越多,你越危險。”
“以後什麼都沒了,總得有記憶吧?”
“記憶壞。你別自討苦吃。”
“就算我記不得你,你也會記得我。”
“真是小孩子話。我一生孤苦,不需要記得任何人。”
“或許我對你不一樣。”
“不一樣?”
“我是對你全部記憶的否定。”
“你說什麼?”
中國人剛有些詫異,可話音未落,寫詩的少女便如一頭潔白的幼獸般,伸出爪子忽然捧起他的臉,將口中的硬糖用柔軟的舌頭強行送到了他的嘴裡,像是要以此堵住他想繼續說的那句話。然後她便轉身,衝著人群疾馳而去。她穿過肉墻的人群,並消失在肉墻裡。中國人感到嘴唇有點發疼,像是被這幼獸猛地撲上來時的虎牙撞出了血。那粒泯滅在少女芳唾中的硬糖,此刻早被她舔得化了一半,棱角也變成了滋潤的橢圓,唯滾燙、潮濕而甜絲絲的唾液能讓他對她後那一滴兇猛的眼淚記憶猶新,如飲燒酒。
含著剩下的糖,中國人側目看著街角人群。肉墻中有一個穿長衫的、皮膚白皙的靦腆後生,手裡拿著一把他從未見過的手槍,還背著一根帶紫檀魚線轱轆與錫墜的釣魚竿。後生朝中國人喊道:“嘿,我看你就別跑了。都這把年紀了,何必再折騰呢?”說著,便遠遠地朝他猛地拋來了一個黑乎乎的東西。
或許是且介亭前的落日太炫目,少女的糖還在嘴裡,也令他走神,故他完全看不清那空中飛來的是一枚子彈,還是魚竿上的錫墜。
2021年2月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