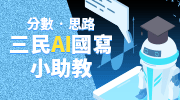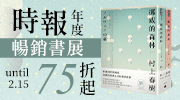商品簡介
於是我說:
在博識的原野上時間掠過
枝杈啄食燃著綠色光芒的和平
而大地在如紗的薄霧下呼吸
而大地伸展。喀啦作響
它黏連的肩膀。它的血管裡
有火焰噼啪。
它的沉眠像八月的番石榴樹般蛻皮
在渴望光明的處女島群上
而大地跪在它活水的
長發裡
在它眼底等待著
繁星。
——埃梅·塞澤爾《純血者》
作者簡介
埃梅·塞澤爾
(Aimé Césaire,1913-2008)
法國詩人、劇作家和政治家,黑人精神運動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出生於法國海外省馬提尼克島,十八歲時靠獎學金就讀巴黎的高中。巴黎成為塞澤爾黑人意識覺醒和反思黑人境況的平臺。塞澤爾一生反對種族歧視、殖民統治與文化同化政策,高聲歌頌獨特的黑非洲文明,詩集代表作有《還鄉筆記》《神奇的武器》等。塞澤爾於2008年4月17日在法蘭西堡去世,4月20日法國為他舉行國葬,2011年移葬聖賢祠。
譯者簡介
施雪瑩,博士,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準聘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法語國家(地區)文學研究、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譯有《還鄉之謎》《三孔橋》《天空之藍》《物質的迷醉》等作品。
名人/編輯推薦
塞澤爾一生反對種族歧視、殖民統治與文化同化政策,高聲歌頌獨特的黑非洲文明,詩集代表作首次出版中譯本。
目次
神奇的武器 _ 1
槍決通告 _ 3
純血者 _ 5
絕勿同情 _ 22
太陽長蛇 _ 24
句子 _ 25
致拂曉的詩 _ 26
往見 _ 28
神話 _ 30
海難 _ 31
幸存 _ 32
彼岸 _ 34
神奇的武器 _ 35
預言 _ 39
夜之達姆達姆鼓 _ 41
懷鄉 _ 42
自動水晶 _ 43
黎明之征 _ 44
殘骸 _ 47
授職儀式 _ 49
原始森林 _ 51
天使報喜 _ 54
達姆達姆鼓(一) _ 56
達姆達姆鼓(二) _ 57
偉大的正午 _ 58
巴圖克 _ 71
海與洪水之牢 _ 81
女人與刀 _ 84
而狗沉默(悲劇) _ 87
後記:神話 _ 205
死囚之歌(譯後記) _ 207
書摘/試閱
死囚之歌
(譯後記節選)
埃梅· 塞澤爾是訴說不可言說之人。
但不是通過還原人的本質,剝離他的社會屬性,直面個體的存在——這確實是一種途徑。塞澤爾所做的並非如此,他像一頭滿心憤怒的野獸,在存在、詞語的網裡撕咬,要從這細密的網裡扯開裂口,獲得呼吸的權利。所以他是入世而非超脫的,他的筆下沒有遺世獨立的豁然,所以他是暴烈而非典雅的,他的筆下沒有凝固時間的永恒。
我們不應批判死囚的歌聲不夠優雅——毋寧說,正是在瀕死的狀態裡,他的作品無可比擬地貼近生命本身,幾乎等同於生命本身的嘶吼。他讓我們看到了對不可言說的另一種抵抗,它無法脫離生存的迫切,因為它在生存的每一刻都感受著威脅;它無法超越社會的結構,因為它正被自身所處的社會遮蔽、覆蓋。它是在社會、文化、政治的多重維度裡對一個亟待誕生的無名自我的追尋。
《神奇的武器》是一部獨特的作品:這是一個法國前殖民地馬提尼克島作家面對近四百年奴隸貿易與殖民壓迫所進行的創作,它表現出無可否認的介入性;但這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一個說法語的非裔詩人、劇作家在先鋒文學、非洲傳統與美洲經驗交匯下的文學實踐,它因而體現出獨特的詩學追求。哪怕從體裁上看,《神奇的武器》也難以歸類。它的主體是詩,卻又包含一部劇作《而狗沉默》。後者雖被塞澤爾本人稱作“悲劇”,卻更像用詩歌語言寫成的對話,
沒有明確的事件,只有高度象徵的人物與近乎囈語的獨白。
該如何理解這樣一部作品?所能寫下的似乎永遠只是走進這個世界的一條通路。入口還有很多——對所有偉大的作品而言莫不如是。
“身體—世界”與非人的“我”
“靈魂拒絕構想一個沒有軀體的靈魂。”這是巴西現代主義之父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在《食人主義宣言》裡說的話。他似乎與同樣身處美洲境遇的塞澤爾產生了共鳴。塞澤爾通過文本尋找的絕不是一個脫離軀體的自我——實際上,回顧加勒比海地區法語文學,自我往往首先通過軀體而非靈魂(如果我們確實要將兩者分開的話)表現出來。法屬圭亞那詩人達馬斯在禁錮自我的文化束縛面前本能地“反嘔”( hoquet)。這種被異質“食糧”填滿的消化不良在以塞澤爾、達馬斯與桑戈爾為代表的“黑人精神”(Négritude)運動作家作品裡隨處可見。它是自我對外部強加的文化與身份的一種生理性反胃,被壓抑的情感與衝動仿佛一陣呃逆,隨時準備將所有外來填鴨式的內容傾吐而出。
美洲作家與知識分子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中沒有忘記身體。莎士比亞的劇作《暴風雨》,盡管設定在地中海的無名荒島,卻在不斷被改寫與引用的過程中成為新大陸殖民史的寓言。遭遇海難、以魔法統治荒島的米蘭公爵普洛斯帕羅(Prospero)固然是殖民“主人”的經典形象,可誰能代表新大陸的居民?在美洲作家——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區及拉丁美洲作家對自我身份的不懈探尋中,“愛麗兒—卡列班”( Ariel-Caliban)構成了鮮明對照。丑陋野蠻的奴隸卡列班是無形溫順的精靈愛麗兒的反面。但正是這個未開化的、身體的、被奴役的卡列班,成為包括塞澤爾在內法語、西班牙語作家共同體認的物件。古巴詩人、作家羅貝托·費爾南德斯·雷塔馬爾在 1971年發表的文章《卡列班》中說,1969 年,三位不同語種的加勒比海地區作家不約而同又滿懷自豪地將“卡列班”視為“我們的象徵”;一些學者甚至將二十世紀末加勒比海地區作家的這股傾向命名為“卡列班流派”。正如雷塔馬爾所說,卡列班( Caliban)由莎士比亞對“食人”(cannibal)一詞異序排列而來,本就是對根深蒂固的“食人土著”形象的影射。它被視為野蠻、落後的象徵,不僅因為“同類相食”是未開化的可怖行徑,也因為進食行為是人類需求中最基礎的一種,是與精神追求相對的原始部分。呼喚卡列班,既是對被構建形象的刻意挪用,也是對被貶低的身體的關注。
具體到《神奇的武器》中,自我首先是一種具身經驗——它的思想、情感與身體感覺、肉體記憶密不可分。於是我們看到詩人筆下這番奇異的景象:
我遭啃噬的腦袋被我的身體吞下。
我的眼睛直直落入
這不再被看而觀望四周的物體中。(《純血者》)
主動的、食人的身體吞下了詩人“笨拙地搖晃”的大腦,代表意識的“觀看”行為自此由身體完成——它代替頭腦成為知覺的主體,它的體驗也構成自我的源頭。但塞澤爾作品中的軀體還有它的獨特之處。它不是封閉的整體,而是碎片化的。字裡行間只有手腳、肩膀、膝蓋,張開的眼睛、鼻子、耳朵,被剖開的大腦、跳動的脈搏與奔流的血液。這些器官與機能仿佛各自有了獨立的生命,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動作。也正因如此,塞澤爾創造的軀體是開放的:它不僅存在於空間之中,更有甚者,四肢百骸、身體發膚竟都與萬物融為一體,消融在世界,又將世界納入其中。“我”的眼睛變作果瓤(《絕勿同情》),“我”的聲帶變作花瓣(《黎明之征》),“我”的身體是卵石吃掉魚群、鴿子和睡眠(《太陽長蛇》)。可這世界並不比“我”的身軀更廣大,因為遊蛇、垛堞不過是“我”的血管、鮮血(《巴圖克》),“日子”與“河灣”都在“我”發咸的胸膛(《往見》),而原始森林與稀樹草原的呼喚都從“我”阿留申的雙眼中噴涌而出
(《原始森林》) ……
最終,詩人在《純血者》中高喊:“我是火,我是海。 / 世界分崩離析。而我便是世界”。萬物借“我”長出肢體,而“我”也分享世界的感官。“大地在如紗的薄霧下呼吸”,舒展它黏連的肩膀與血管(《純血者》);生活長出血肉,其中流過毒蛇酸液的激情(《絕勿同情》);“手指豐腴的河流”在“石間長發”裡尋找一千面月亮的旋鏡(《夜之達姆達姆鼓》)。這是獨特的物我關係:它不以精神、情感為主要媒介,而通過身體感官,由共同的冷熱、顫動、饑餓、疼痛溝通個體與世界。它既不全然主動、也不全然被動,不是內在感受向外部事物的純粹投射,也不是主觀視角對客觀世界的完全扭曲,而是內外、主客關係的模糊與重構。在《神奇的武器》裡,我們看不到一個完整而獨立的自我,面對一個完整而獨立的世界,一切都在無盡的動蕩中彼此滲透、彼此融合。或許對此最恰當的表述,便是“被附身”(en transe)、“被捕捉”(être saisi)的狀態,這是塞澤爾在非洲及加勒比地區文化傳統以及德國人類學家列奧·弗羅貝尼烏斯的論
述基礎上的概括,指主動放棄對自我的掌控,並由此順應世界,以致超越自我、革新世界的過程。
身體的經驗與世界的經驗一體兩面,構成了塞澤爾作品中“身體—世界”的運行機制。這個機制塑造出一個非人的“我”——既低於人又高於人。一方面,塞澤爾似乎在刻意強調它原始、本能的一面——這具“身體—世界”為生的欲望所驅使,只知用“野獸的臂膀”擊打(《神話》),發出“撕咬”和“哀鳴”(《預言》)。甚至連它的樣貌都表現出某種動物特徵,臉不再是臉,而是野獸的鼻吻( gueule)。這當然是對種族主義不乏幽默的反諷。詩人說起他“下頜凸出的笑聲”,提起他“三百年來殘缺的靈長類嘴臉”,就像他在《還鄉筆記》中高聲贊揚他“帕胡因人駭然躍起的丑陋”,都揭露了對黑人的歧視性描述。但與此同時,這種動物性也包含了一種肉體記憶,無論掙扎、擊打、呼號,都是面臨生存絕境的求生本能。塞澤爾的詩歌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暴力與死亡,海難與滿是沉船的海洋、火山爆發與地震侵襲、鞭打受刑與血淋淋的傷口……我們不難看出這些意象的歷史隱喻,它們背後有黑奴貿易擁擠貨倉裡黑人的經歷,有包括馬提尼克島在內的安的列斯群島居民的經歷,有到達新世界的勞力在種植園裡被當做奴隸的經歷。當詩人寫到凝滯的大海中“我們嘶啞的喘息交織”,當他寫到海難中那些“拍打新鮮空氣”的“頭顱”、“拍打太陽”的手掌與“拍打土地”的“聲音的赤腳”,他通過身體經驗喚起的是奴隸船艙內被當作貨物的祖先所感受到的痛苦與窒息。由此,身體的經驗超越個體,成為集體記憶的載體。甚至,在此意義上,它成為對歷史記述的補全,不僅因為在法屬安的列斯群島的歷史檔案裡,非裔黑奴的第一人稱見證相較英語是缺乏的——甚至可以說幾乎是空白,更因為這種極端創傷的體驗,恰恰是歷史無法充分傳遞的,它需要以某種方式被補全。身體的途徑,便是塞澤爾所找到的途徑。
但另一方面,塞澤爾又賦予了這個“身體—世界”超人的力量。因為在與世界合一的過程中,身體也融合了世界的能量。“我”“過短的臂膀借火焰伸長”(《彼岸》);當“大地割下太陽的頭皮”,我便也如森林一般有了“燃木冒煙的眼睛”(《偉大的正午》)。自我的革新和世界的革新同時完成,或者說自我的革新正是通過世界的毀滅和重構而完成。塞澤爾的作品無時無刻不在呼喚著一場即將開始又尚未到來的末日,好讓新的生命與世界從腐朽之軀裡蛻殼、重生。在一次又一次暴力與死亡之後,身體與世界同時迎來新生。“嫡長的土地”在牽牛花的子宮裡默默等待;“我們”也不斷走向“源泉之夜漿液濃稠的腹膜”。正如塞澤爾在《預言》一詩的末尾寫道:
濃煙驟起化作野馬衝向臺前用它脆弱的孔雀尾羽在熔巖邊緣逡巡片刻隨即撕裂衣衫一瞬敞開胸膛而我看著它化成不列顛群島化作小島化作碎石一點點融化在空氣清明的海中
其中沉浸著預示未來的
我的嘴臉
我的反抗
我的名。
如果說這一切在詩作中還稍顯晦澀,那《而狗沉默》就好像是注解,無比清晰地將這些主題的社會維度展現在讀者面前。也難怪塞澤爾會說戲劇是接觸大眾、“喚醒大眾意識的最佳途徑” 。劇作的主人公,一位起義失敗、身陷囹圄的奴隸,面對戀人與母親的溫情、獄卒的恐嚇,毅然走向死亡。這個並不複雜的故事卻濃縮了作家的所有關切: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的劫掠、黑人奴隸在新世界的反抗與退敗、殖民政策與文化同化的威脅、理性主義主導的現代社會與傳統文明的碰撞……但塞澤爾在創作這部劇作時,依然使用了詩歌的語言。是語言的統一而非體裁的統一,為《神奇的武器》這部構成奇特的作品提供了依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