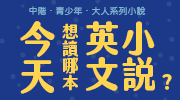彼女的日復一日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收錄年度散文〈彼女日誌〉
追思孤寂的年少時期裡,帶來光與暗的
白金玫瑰一般的情感
張亦絢、楊莉敏專文導讀
言叔夏、李時雍、孫梓評、許俐葳、許閔淳、盧慧心
低迴推薦
「彼女」一詞在日文裡具有雙關的意涵,既是「女朋友」,也是作為代名詞的「她」,一個永遠的女性第三人稱。林薇晨向來善於捕捉生活細瑣、智識靈光,少寫貼身的私人情事,然而在新作《彼女的日復一日》裡,她回溯十年之前的一段隱祕戀愛,以及同一時期的一趟英國倫敦之旅,字裡行間盡是難以告人的絢美與陰翳。
本書收錄二十餘篇副刊專欄文章,以及引發無數迴響的長篇散文〈彼女日誌〉,篇篇各自獨立又相互勾連,展現林薇晨一貫清麗而天然的寫作技藝。在倫敦的假期,她走走停停,嘗試生蠔,採買鮮花,踏訪名勝,觀賞冬天的街景與路樹,心中始終掛念著遠在台北的他。而在台北的公寓裡外,她與他過著微甜微澀的日復一日,在不斷循環的相聚與分離中練習擱置難題,並且安頓自己的情感。戀愛著的兩人各有偏執、軟弱、稚拙及真誠,短暫相伴之後,從此成為她生命裡無法輕易忘卻的傷,發熱且發痛。
在這本散文集裡,林薇晨動用不同的敘述人稱,從「我」化為「她」,又從「她」成為「我」,隨著主觀與旁觀視角的切換,作者也不斷向內叩問,提出琢磨長久的疑惑與思索。這是一本關於遠行與戀愛的踟躕之書,而所謂的戀愛,其實也是一趟一去不復返的旅程。
作者簡介
林薇晨
1992年出生於台北,政治大學新聞學士、傳播碩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新詩獎,作品入選《九歌112年散文選》、《九歌111年散文選》等數本選集,著有散文集《青檸色時代》、《金魚夜夢》。
Instagram:rabbited92
名人/編輯推薦
散文的「彼時彼地」常是「此時此刻」的一種發明。但《彼女的日復一日》藉由某種攤展的技術,似乎消弭了這種「此」與「彼」的分野:那些遠方的街道,散漫的散步,彷彿沒有終點的旅行⋯⋯,如同貓步跨越了日子與日子的邊界。跨得過去的,跨不過去的,隱密的生活,皆如同立體的娃娃屋般,被攤展成平面。誰是「彼女」?誰又被留在「此時此地」?這個少女學式的命題,或許也被隱密地埋藏在其中。——言叔夏(作家)
我們知道,寫下的字,都像一個替代物,彼女代替我,以小小的她者,旅行的倫敦代替有間老公寓窩藏的台北,昨夜擲出的信,交換另一個早晨。薇晨記寫所揭開一段二十二歲隱密的戀愛像一種覆蓋。多年後我們會知道寫下的愛,愛是唯一無以替代的所指。——李時雍(作家)
旅行時感官警戒而易於觸動,因為時空是借來的,為那偶然的新鮮而詫奇,又恍惚夢幻,所見一切,除了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如果耽溺一些,還可以穿上漂亮的假裝,偏偏是這樣剔透的一顆心,想望「最普通」的幸福,終究沒有得到應允。跟隨彼女的旅程,看她如何把甜蜜寫得準確而不渙散,把痛苦藏得節制而不倉促,私密坦白,青春熾熱,卻毫不干擾如何再現記憶中每一張日常的構圖。我早該知道,旅行那麼近似愛情。戀人或許是借來的,但願書寫永遠屬於自己。——孫梓評(作家)
一種理智的耽溺,一種親密的恥感。這樣極其貴重的文字,被林薇晨寫了出來,而且寫得實在太美。閱讀這本散文集的感受很特別,彷彿注視著新娘頭紗下的面孔,看見了隱沒於蕾絲的肌膚,而「新娘」這個關鍵詞放在這裡,又是多麼不合時宜。薇晨的文字隱隱觸碰著這些不合時宜,那樣的痛與快是酸甜微苦的草莓汁,縱然有尖刺,也在書寫裡被可愛地收攏了,這是我極為佩服她的一點。我們所能知曉的,大概僅是彼女日記裡的百分之幾——婚外情的敘事,追根究柢,就是隱瞞的記憶,也是遮掩的技藝。因此,這是一種站在裡側的文學,由待過那個位置的人,在颱風過後,來向我們報一場戀愛的信。——許俐葳(作家)
《彼女的日復一日》並置兩種充滿時差的遠行,呈現愛裡關係的樣貌。在迴環的生活裡,「距離」成為一切敘事的關鍵詞,「遠」與「近」恰如花瓣之兩面,互依互存,不斷翻旋。曩昔的情感已是製成標本的蝴蝶,失去伴隨翅翼振動的所有後續效應,卻以紋路的絢美、鋼針的透亮,揭示了「看似」之下的真實,然而真亦是幻,永恆也許不過浮漚。透過宛如手術的寫作,薇晨優雅地持刀取心,細細端詳包裹於日常格律裡的瘋狂與疼痛,那心跳是她的、他的,也是你的、我的。——許閔淳(作家)
戀與愛都需要一個對象來投注感情,宛如追隨一個發光體,然而感光之後,留下的心之風景仍取決於個人的質地。無論戀人的輪廓在何處留白,陰刻或陽刻,補上的都是映射的自我。戀與愛也是動詞,戀愛的動詞卻是談,從「我」到「她」又回到「我」,戀愛確實是談出來的,但無論與誰對話,都沒有與自己對話重要。薇晨的散文就像她的私人放映室,有些快門按得很慢,教人思索,十年也不長。——盧慧心(作家)
目次
集序 時差
推薦序 現在她什麼都能唱 張亦絢
推薦序 花開花明的地方 楊莉敏
牡蠣之旅
花與情人節
康橋輕舟
道地與否
船裡博物館
百貨童年往事
午後女王公園
晚間劇場
冬天的樹
摩天輪迴
如果倫敦不快樂
還魂記
跨年
家具們
泳池約會
酪梨之愛
婚紗雜誌
失語症
霰
芙
飛機雲
溫度計
三人的情人節
菸
畢業生
寶麗萊
瓦斯表
春藍
彼女日誌
後記 十年前後
書摘/試閱
跨年
老公寓裡有小沙發,小茶几,小鍋小爐,小冰箱,一切都是縮小的尺寸,組成了一個袖珍天地。整間屋子有點舊了,依山傍水的環境十分潮溼,天花板一角罹患壁癌,油漆鱗鱗剝落。浴室洗臉台的鏡子因為霧氣蒸了又乾,蒸了又乾,印著星星點點的水漬。鏡子上殘留一張淡紅的囍字剪紙,他租下屋子後,一直也不去撕。這裡應當曾是誰的新家,有誰曾在這裡雙宿雙棲,可是不是現在了。也許是因為這種不合時宜的新婚氣息,浴室裡忽然流露了低低的惆悵,像是水龍頭的旋鈕沒拴緊,笛答笛答,水滴濺上浴缸裡冰涼的磁磚。
到了他的美髮日,她去浴室的櫥櫃取來染髮膏,戴上塑膠手套,把兩劑染髮膏擠在小茶几上的碟子裡。先擰一條雪白的膏,再擰一條米白的膏,又以梳子尖尖的尾巴將它們拌勻。調著調著,兩條白膏融合成一團,漸漸變成灰色,接著深灰,接著是更深的灰,越來越深,終於成為純然的烏黑。她跪在小沙發上,他坐在沙發下的地毯上,等待她替他染。她每隔一陣子執行這項任務,仍舊不甚熟練,小心翼翼拿梳子的細齒蘸滿了黑膏,一篦一篦塗抹於他的白髮,額上的,腦後的,頸上的,耳後的,儘管十分注意,還是不免弄污了些許肌膚。脖子左側有一塊黑漆漆的,不趕緊擦拭就要有好幾天洗不掉了,因為黑會滲進身體的深處。
以前沒有她的時候,他本來也要自己替自己染的。有了她,只是增添一名笨拙的助手,並不能算是實惠。可是兩人都是喜歡乾淨的人,定期掃蕩白髮,大約也有一種同心協力的意味。歲末是最適合清理居家的時節,以黑消滅白,這黑也成了代表潔癖的黑。她總覺得自己正在進行一件粉刷的工作,心裡充滿了除舊布新的快樂。
於是白色的昨天變成黑色的今天。黑色的今天又要變成白色的明天。黑白黑白。黑白黑白。日復一日,她的手指在他的黑髮與白髮之間穿梭,如同安撫一匹駿逸的斑馬。不知不覺,她也過上了黑白交錯的日子,與他見面的時候是黑,與他分別的時候是白。染黑的頭髮是不宜告人的隱私,只能有自己與自己人知道。小茶几上的收音機裡,宋冬野在那裡憂傷地唱道:「斑馬,斑馬,你還記得我嗎?」他最喜歡的一首歌。在歌聲裡,他去浴室把染髮的梳子和碟子沖了沖,回來坐在小沙發裡,伸手在電暖爐邊烤烤。玻璃窗外,陰翳的冬天持續著,一天比一天更寒冷。
她寫作,寫下文章與文章。她與他的關係是許多詞語疊合而成的日常生活,主詞,動詞,受詞,串連出或長或短的句子。有時她當他的主詞,有時她當他的受詞,然而單是「當」這個動詞,其中便已經有一種主動的氛圍。她是自願的,她想。
白髮長得真快,她得不時替他檢查檢查,確認是否需要補染的手續。撥撥探探之際,偶爾也會發現髮漩中央藏匿著一簇新爆出的白髮,如同跨年夜裡施放的銀煙火。花開富貴。心想事成。歲歲平安。她對著只有她看得到的白髮暗自許願,拿著蘸妥染髮膏的梳子,輕輕替他熄了那些燃燒的白髮。
跨年這天剛好在週間,他不必回家。她和他到醫學大學附近一塊停車場的草坪上與眾人一起等待煙火當空的剎那。兩人抱膝坐在黑暗中聊天,聊起他念大學時她還在讀小學,他一臉苦笑羞慚,要她不要再說下去,否則本來已經白髮參差,越說越真的老了。其實他看起來並不老,只是似乎總是顯得累。
午夜一分一秒迫近,摩天的高樓上忽忽開始顯示倒數的數字了。草坪上趺坐仰面的人們齊聲咒罵道:「前面的人可以坐下嗎?聽不聽得懂人話呀?」語帶嬉笑,簡直分不清是出於憤怒還是出於遊戲而嚷的了。站著的人們不為所動,繼續遮擋視線,該讀秒時雙方還是和和氣氣讀秒了。煙火是早生的華髮,絲絲鬚鬚的斑斕,很快就又隱沒在黑夜裡。那是黑夜太過濃稠,染髮膏一般凝滯,強勢,將煙火給染得不見蹤影。黑是潔癖的黑。現在她終於明白為何不拘哪一國,人類總是習慣以煙火揭開新年的序幕,或許關鍵就在於那最後的乾淨吧。大掃除後的歸零。無名天地之始。兩人互道新年快樂,在這第一個共度的一月一日。
跨年跨年。她與他之間橫亙了數年,她怎樣也趕不到他那裡,於是索性安心告訴自己,都是白髮長得太快,而她永遠來不及長大。
泳池約會
他賃居在一個高齡化的社區裡,社區中央的大公園裡有一座游泳池,全年開放,於是他春夏秋冬都去游泳,後來也邀著她同行。在前往游泳池的路上,兩人總會遇到許多老人,及其輪椅、柺杖、助步器,都是他復健診所裡常年的患者。每經過一位老人,他就低聲對她介紹剛才那位得了某某病症,做著某某治療,可是一路誰也不曾認出他來,自顧自蹣跚走了過去,好像他脫下白袍就換了張臉孔一般。兩人遂有一種隱去真身的樂趣了。
午後的游泳池裡也都是老人,然而是這社區裡較為健康的那一群。他與她各自進了更衣間,約在踏腳池前見面,一起下水。游泳池的水並不冰涼,波浪陣陣,微溫微皺,緩緩摩挲著她的肌膚。救生員端坐在紅漆高腳椅上,瞇著觀音的眼睛垂望一方湛藍浮世,也有望不透徹的祕密。
游泳真是一項獨立的運動,誰都幫助不了誰,誰都只能自己悶頭前進,並且折返。獨立的同義詞經常是:孤獨。她不擅長自由式換氣,總是游到半途就要起身呼吸,再接著游下去。游了幾趟,她上岸休息一會兒,他依舊在快速泳道裡一趟一趟地來回。他是一個善於來回的人。每個星期他搭上列車,定時在南北之間奔波,北部有重要的情人,南部有重要的家人。他將北部與南部的擔子負在肩上,漸漸立成了一座不偏不倚的天秤。她想,日復一日過著這種生活,他也會感到疲倦嗎?是她讓他疲倦嗎?如果他終於倦怠了是否就會捨棄她呢?她又想,也許在他而言根本就沒有這些問題。他是該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一切苦思惡想都是多餘,徒勞,都是腳跟的水花應當踢踢掉。理性?理性是什麼?理性就是妥善分配自己的情感,如同穿著一件布料穠纖合度的泳衣,須裸之處裸,須裹之處裹,很有羞恥的意思了。
她最喜歡游泳之後,坐在他那老公寓的小浴缸裡,他替她洗頭髮。修長的十指在她的頭皮上按摩著,搓揉著,溫柔而富於力道。當蓮蓬頭的水柱嘩嘩澆灌下來,她總是想起一句最無意義的諧音雙關:「懸瀑沖洗shampoo。」偶爾她也想起〈九龍公園游泳池〉這首歌:「我原是世間其中的粒子,如何沖擊我都可以。」她教他唱,他的粵語發音讓兩人笑得不得了。
某天他的頸後冒出了一莓一莓的紅疹,也不知道是不是對於游泳池裡的氯過敏。兩人於是暫停游泳的行程了。她跟他借了證件,打電話幫他在她住處附近一間頗有名氣的皮膚科診所掛了號,陪他去看病。從前還只是筆友時,她曾經在信件裡和他聊過這位皮膚科醫生,關於她的專家派頭太大,在網路上引起諸般非議與酸諷,然而處方是靈驗的。他在回信裡寫道:「看來名醫架子雖大,還得有真才實學才撐得起來呢。」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並非名醫,也沒有喬張作致的資格。如此乾淨的自謙。她後來終於知道,他是謙虛得近於虛無,幾乎沒有了自己的成分。
在小診間裡,那高傲的皮膚科醫生完全是貴婦面貌,梳一個圓髻,穿一件墨綠絲絨洋裝,曳地的長裙綴滿珠珠滴滴的水鑽。身上不曾披白袍。他對貴婦醫生娓娓描述自己的症狀,那醫生只約略瞧了一眼紅腫的患部,隨即解說自己開什麼藥,藥怎麼搽,指尖拿一枝鋼筆在病歷表上迤邐一串草體英文,那翩翩手勢華美至極,如同紙間的蝶式。他諦聽醫囑,連聲應好,一點也不像是個每日診治患者的權威人士。這般唯唯諾諾的模樣,她還是第一次見到,不禁淺淺地笑了。
她忽然發現這是她第一次聽到他和別人說話,這才知道他也有這樣一種乖巧的語氣。她與他向來就是兩人獨處,雙雙待在只有彼此的關係裡,即使置身最喧譁的餐廳也還是與世隔絕,在公眾的眼皮底下半藏匿。他人看見他們,但是並未真正看懂他們。有目擊者的確認,有旁觀者的欣賞,這段關係遂暫時顯得合理了。她與他在哪裡都像在游泳池,周圍人潮團團包羅,彼此在眾目睽睽中扮演登對的情侶,可是誰都與他們不相干,甚至她與他亦不相干。游泳池是最孤獨的場所。
那些約會的下午,在每個無人相識的地方,她當當洛琳・白考兒,他當當亨弗萊・鮑嘉,一起過足了心照不宣的戲癮。然後他游向彼岸的家,留她在原地蒐集水花,一朵一朵,捉在掌上又旋即消散。
春藍
暮春的藍天向來予人一種緊急之感,因為隨時都要風雲變色,青紫電光打將下來,彈指間霹靂四伏。每日看見這樣烈火煅燒過的,似乎堅不可摧的藍天,她總覺得自己應當出門晃晃,可是做什麼都不對,做什麼都不配這好天氣,時間就在苦思惡想之際蹉跎掉了。
她最害怕正午十二點,一旦過了這陰陽交界,秒針就要走得越發匆匆,彷彿時間也在趕著避雨,再不找個騎樓或屋簷跑回去,躲進去,渾身便會淋得千山萬水。獨自待在家裡,靠在窗邊旁觀大雨下得暴力的午後,那雨的衝動與倏忽即止的仁慈簡直要教人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生出一種病態的依戀。為愛狂亂。她正在為愛狂亂。她沒有辦法踏出家門,可是也不能一直自己一人,她需要別人幫忙看住她那即將發瘋的靈魂。
終於和他談完的那天,她搭上離開的公車,在車子後側的座位哭得不能自已。隔鄰的一個女士發現了,也沒多問什麼,只是遞給她一條手帕,輕輕笑道:「你不要傷心,人生本來就是這樣變化無常的。我跟你說,難過的時候你可以禱告,禱告的效果很好哦。」於是她接過手帕,整張臉埋在那裡面沉默地嚎啕,哆嗦,就著陌生人偶然供應的良善。這是第幾次了?她又捨棄他了,把那些不可以的不能夠的統統留在原地,兀自內疚地前進了。
春天的末尾,她經常到住處附近的一條長街上泡咖啡店,一天嘗試一間小店,還沒全部輪過一遍春天就要結束了——拉花比春花更為耐久。她喜歡各種蛋糕軟香溫玉的表情,頂端櫻桃是紅腫的瘤,夾層草莓是暗地裡的炎,巧克力醬是滴滴的膿,它們裹上鮮奶油像穿著一襲清潔無菌的病袍,乖乖躺在盤子裡,仍舊使人感到樂觀,健康,等待刀與叉的手術。咖啡店裡坐滿各路各派的外科醫生,彼此低語談笑也如同正在討論最適合的療程。那時她常常浮躁而焦慮,覺得自己就像一塊蛋糕,需要誰來立刻替她切除身心的痛楚,可是呼天搶地未免太過羞恥了。苦難若有等差,則求救亦有階級之分。她遂只能望著窗外的藍天發怔,反正咖啡店裡永遠要有一個看似無聊慵懶的人。無聲的煩憂,是為氣氛。
有時候她想起尚未化作往事的惱事,精神賁張,紅血球與白血球在管線裡迅速穿梭,彷彿有一團上體育課的小學生在她體內紅白大對抗,各組嚌嚌嘈嘈競相把無數小球拋進高懸的竹簍,登時滿天珠玉,亂亂飛得不得了。儘管如此,她相信自己仍舊顯得寧靜肅穆。破壞咖啡店的寧靜肅穆是不道德的。
她愛極愛極這條長街,每棟樓房不出七層,高高低低錯落,一棟帶著一間咖啡店,她可以逐日拜訪宛若投醫,回訪則是回診。連續四棟五層的公寓挨著就是一首五絕,連續數棟四層的公寓挨著就是一首詩經,五層七層五層,遂成了曖昧的日本俳句,公寓小窗倒映出的花影、磚瓦罅隙間綠茸茸的蘚苔、陽台欄杆上停駐的貓與雀、居民開門之前收束抖擻的洋傘,便是不言而喻的季語。她想起羅蘭・巴特初識俳句後的驚嘆:「俳句說:『就是這個,就是如此,就是這樣。』這麼說更清楚:『這!』」參差的樓房凹凹凸凸畫出了整條長街的天際線,一折一折像韻律失調的心電圖。徘徊路邊,挑選宜於入座的咖啡店時,她的目光在這裡向上爬一格,在那裡向下爬一格,轉瞬起伏,視域上緣不斷感測到一股盎然的藍意,那藍天是藍得美不勝收。這裡缺乏都市的巴別塔,女媧補天的靈龜足,山稜,水平,教堂的筆尖鐘樓,歌劇院的圓貝穹頂,建築學上的一切屏蔽與突刺均謙卑退位,有的只是窯爐天候,以及將要滂沱的威基伍德式的藍天。
暮春的晴朗像一隻寶藍陶瓷茶壺,藍得鮮潔,藍得易碎。時間過去,陰雲疊聚如同髒污的指紋,眾人交互斟酌把玩,終於不小心摔傷了茶壺,令那瓷器落地炸出貫耳的響雷。砰訇一聲,整個完美的蔚藍忽然就八花九裂的,濺散的熱茶淋得世界又香又痛又迷糊。
那些蒸悶踟躕的白晝暈成一段長假,假期的最後一天應當也有離情別緒。咖啡店裡,醫生們總在那裡診治蛋糕,她總在窗邊支頤沉思,偶爾揪出每張木桌抽屜裡都有的一本素描冊子草草書寫平假名俳句,五七五,五七五,並且提醒自己直到天空轟然綻開蜿蜒電光像茶壺上的第一簇裂痕之前,必須嚴格守住格律和眼淚。
跨年
老公寓裡有小沙發,小茶几,小鍋小爐,小冰箱,一切都是縮小的尺寸,組成了一個袖珍天地。整間屋子有點舊了,依山傍水的環境十分潮溼,天花板一角罹患壁癌,油漆鱗鱗剝落。浴室洗臉台的鏡子因為霧氣蒸了又乾,蒸了又乾,印著星星點點的水漬。鏡子上殘留一張淡紅的囍字剪紙,他租下屋子後,一直也不去撕。這裡應當曾是誰的新家,有誰曾在這裡雙宿雙棲,可是不是現在了。也許是因為這種不合時宜的新婚氣息,浴室裡忽然流露了低低的惆悵,像是水龍頭的旋鈕沒拴緊,笛答笛答,水滴濺上浴缸裡冰涼的磁磚。
到了他的美髮日,她去浴室的櫥櫃取來染髮膏,戴上塑膠手套,把兩劑染髮膏擠在小茶几上的碟子裡。先擰一條雪白的膏,再擰一條米白的膏,又以梳子尖尖的尾巴將它們拌勻。調著調著,兩條白膏融合成一團,漸漸變成灰色,接著深灰,接著是更深的灰,越來越深,終於成為純然的烏黑。她跪在小沙發上,他坐在沙發下的地毯上,等待她替他染。她每隔一陣子執行這項任務,仍舊不甚熟練,小心翼翼拿梳子的細齒蘸滿了黑膏,一篦一篦塗抹於他的白髮,額上的,腦後的,頸上的,耳後的,儘管十分注意,還是不免弄污了些許肌膚。脖子左側有一塊黑漆漆的,不趕緊擦拭就要有好幾天洗不掉了,因為黑會滲進身體的深處。
以前沒有她的時候,他本來也要自己替自己染的。有了她,只是增添一名笨拙的助手,並不能算是實惠。可是兩人都是喜歡乾淨的人,定期掃蕩白髮,大約也有一種同心協力的意味。歲末是最適合清理居家的時節,以黑消滅白,這黑也成了代表潔癖的黑。她總覺得自己正在進行一件粉刷的工作,心裡充滿了除舊布新的快樂。
於是白色的昨天變成黑色的今天。黑色的今天又要變成白色的明天。黑白黑白。黑白黑白。日復一日,她的手指在他的黑髮與白髮之間穿梭,如同安撫一匹駿逸的斑馬。不知不覺,她也過上了黑白交錯的日子,與他見面的時候是黑,與他分別的時候是白。染黑的頭髮是不宜告人的隱私,只能有自己與自己人知道。小茶几上的收音機裡,宋冬野在那裡憂傷地唱道:「斑馬,斑馬,你還記得我嗎?」他最喜歡的一首歌。在歌聲裡,他去浴室把染髮的梳子和碟子沖了沖,回來坐在小沙發裡,伸手在電暖爐邊烤烤。玻璃窗外,陰翳的冬天持續著,一天比一天更寒冷。
她寫作,寫下文章與文章。她與他的關係是許多詞語疊合而成的日常生活,主詞,動詞,受詞,串連出或長或短的句子。有時她當他的主詞,有時她當他的受詞,然而單是「當」這個動詞,其中便已經有一種主動的氛圍。她是自願的,她想。
白髮長得真快,她得不時替他檢查檢查,確認是否需要補染的手續。撥撥探探之際,偶爾也會發現髮漩中央藏匿著一簇新爆出的白髮,如同跨年夜裡施放的銀煙火。花開富貴。心想事成。歲歲平安。她對著只有她看得到的白髮暗自許願,拿著蘸妥染髮膏的梳子,輕輕替他熄了那些燃燒的白髮。
跨年這天剛好在週間,他不必回家。她和他到醫學大學附近一塊停車場的草坪上與眾人一起等待煙火當空的剎那。兩人抱膝坐在黑暗中聊天,聊起他念大學時她還在讀小學,他一臉苦笑羞慚,要她不要再說下去,否則本來已經白髮參差,越說越真的老了。其實他看起來並不老,只是似乎總是顯得累。
午夜一分一秒迫近,摩天的高樓上忽忽開始顯示倒數的數字了。草坪上趺坐仰面的人們齊聲咒罵道:「前面的人可以坐下嗎?聽不聽得懂人話呀?」語帶嬉笑,簡直分不清是出於憤怒還是出於遊戲而嚷的了。站著的人們不為所動,繼續遮擋視線,該讀秒時雙方還是和和氣氣讀秒了。煙火是早生的華髮,絲絲鬚鬚的斑斕,很快就又隱沒在黑夜裡。那是黑夜太過濃稠,染髮膏一般凝滯,強勢,將煙火給染得不見蹤影。黑是潔癖的黑。現在她終於明白為何不拘哪一國,人類總是習慣以煙火揭開新年的序幕,或許關鍵就在於那最後的乾淨吧。大掃除後的歸零。無名天地之始。兩人互道新年快樂,在這第一個共度的一月一日。
跨年跨年。她與他之間橫亙了數年,她怎樣也趕不到他那裡,於是索性安心告訴自己,都是白髮長得太快,而她永遠來不及長大。
泳池約會
他賃居在一個高齡化的社區裡,社區中央的大公園裡有一座游泳池,全年開放,於是他春夏秋冬都去游泳,後來也邀著她同行。在前往游泳池的路上,兩人總會遇到許多老人,及其輪椅、柺杖、助步器,都是他復健診所裡常年的患者。每經過一位老人,他就低聲對她介紹剛才那位得了某某病症,做著某某治療,可是一路誰也不曾認出他來,自顧自蹣跚走了過去,好像他脫下白袍就換了張臉孔一般。兩人遂有一種隱去真身的樂趣了。
午後的游泳池裡也都是老人,然而是這社區裡較為健康的那一群。他與她各自進了更衣間,約在踏腳池前見面,一起下水。游泳池的水並不冰涼,波浪陣陣,微溫微皺,緩緩摩挲著她的肌膚。救生員端坐在紅漆高腳椅上,瞇著觀音的眼睛垂望一方湛藍浮世,也有望不透徹的祕密。
游泳真是一項獨立的運動,誰都幫助不了誰,誰都只能自己悶頭前進,並且折返。獨立的同義詞經常是:孤獨。她不擅長自由式換氣,總是游到半途就要起身呼吸,再接著游下去。游了幾趟,她上岸休息一會兒,他依舊在快速泳道裡一趟一趟地來回。他是一個善於來回的人。每個星期他搭上列車,定時在南北之間奔波,北部有重要的情人,南部有重要的家人。他將北部與南部的擔子負在肩上,漸漸立成了一座不偏不倚的天秤。她想,日復一日過著這種生活,他也會感到疲倦嗎?是她讓他疲倦嗎?如果他終於倦怠了是否就會捨棄她呢?她又想,也許在他而言根本就沒有這些問題。他是該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一切苦思惡想都是多餘,徒勞,都是腳跟的水花應當踢踢掉。理性?理性是什麼?理性就是妥善分配自己的情感,如同穿著一件布料穠纖合度的泳衣,須裸之處裸,須裹之處裹,很有羞恥的意思了。
她最喜歡游泳之後,坐在他那老公寓的小浴缸裡,他替她洗頭髮。修長的十指在她的頭皮上按摩著,搓揉著,溫柔而富於力道。當蓮蓬頭的水柱嘩嘩澆灌下來,她總是想起一句最無意義的諧音雙關:「懸瀑沖洗shampoo。」偶爾她也想起〈九龍公園游泳池〉這首歌:「我原是世間其中的粒子,如何沖擊我都可以。」她教他唱,他的粵語發音讓兩人笑得不得了。
某天他的頸後冒出了一莓一莓的紅疹,也不知道是不是對於游泳池裡的氯過敏。兩人於是暫停游泳的行程了。她跟他借了證件,打電話幫他在她住處附近一間頗有名氣的皮膚科診所掛了號,陪他去看病。從前還只是筆友時,她曾經在信件裡和他聊過這位皮膚科醫生,關於她的專家派頭太大,在網路上引起諸般非議與酸諷,然而處方是靈驗的。他在回信裡寫道:「看來名醫架子雖大,還得有真才實學才撐得起來呢。」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並非名醫,也沒有喬張作致的資格。如此乾淨的自謙。她後來終於知道,他是謙虛得近於虛無,幾乎沒有了自己的成分。
在小診間裡,那高傲的皮膚科醫生完全是貴婦面貌,梳一個圓髻,穿一件墨綠絲絨洋裝,曳地的長裙綴滿珠珠滴滴的水鑽。身上不曾披白袍。他對貴婦醫生娓娓描述自己的症狀,那醫生只約略瞧了一眼紅腫的患部,隨即解說自己開什麼藥,藥怎麼搽,指尖拿一枝鋼筆在病歷表上迤邐一串草體英文,那翩翩手勢華美至極,如同紙間的蝶式。他諦聽醫囑,連聲應好,一點也不像是個每日診治患者的權威人士。這般唯唯諾諾的模樣,她還是第一次見到,不禁淺淺地笑了。
她忽然發現這是她第一次聽到他和別人說話,這才知道他也有這樣一種乖巧的語氣。她與他向來就是兩人獨處,雙雙待在只有彼此的關係裡,即使置身最喧譁的餐廳也還是與世隔絕,在公眾的眼皮底下半藏匿。他人看見他們,但是並未真正看懂他們。有目擊者的確認,有旁觀者的欣賞,這段關係遂暫時顯得合理了。她與他在哪裡都像在游泳池,周圍人潮團團包羅,彼此在眾目睽睽中扮演登對的情侶,可是誰都與他們不相干,甚至她與他亦不相干。游泳池是最孤獨的場所。
那些約會的下午,在每個無人相識的地方,她當當洛琳・白考兒,他當當亨弗萊・鮑嘉,一起過足了心照不宣的戲癮。然後他游向彼岸的家,留她在原地蒐集水花,一朵一朵,捉在掌上又旋即消散。
春藍
暮春的藍天向來予人一種緊急之感,因為隨時都要風雲變色,青紫電光打將下來,彈指間霹靂四伏。每日看見這樣烈火煅燒過的,似乎堅不可摧的藍天,她總覺得自己應當出門晃晃,可是做什麼都不對,做什麼都不配這好天氣,時間就在苦思惡想之際蹉跎掉了。
她最害怕正午十二點,一旦過了這陰陽交界,秒針就要走得越發匆匆,彷彿時間也在趕著避雨,再不找個騎樓或屋簷跑回去,躲進去,渾身便會淋得千山萬水。獨自待在家裡,靠在窗邊旁觀大雨下得暴力的午後,那雨的衝動與倏忽即止的仁慈簡直要教人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生出一種病態的依戀。為愛狂亂。她正在為愛狂亂。她沒有辦法踏出家門,可是也不能一直自己一人,她需要別人幫忙看住她那即將發瘋的靈魂。
終於和他談完的那天,她搭上離開的公車,在車子後側的座位哭得不能自已。隔鄰的一個女士發現了,也沒多問什麼,只是遞給她一條手帕,輕輕笑道:「你不要傷心,人生本來就是這樣變化無常的。我跟你說,難過的時候你可以禱告,禱告的效果很好哦。」於是她接過手帕,整張臉埋在那裡面沉默地嚎啕,哆嗦,就著陌生人偶然供應的良善。這是第幾次了?她又捨棄他了,把那些不可以的不能夠的統統留在原地,兀自內疚地前進了。
春天的末尾,她經常到住處附近的一條長街上泡咖啡店,一天嘗試一間小店,還沒全部輪過一遍春天就要結束了——拉花比春花更為耐久。她喜歡各種蛋糕軟香溫玉的表情,頂端櫻桃是紅腫的瘤,夾層草莓是暗地裡的炎,巧克力醬是滴滴的膿,它們裹上鮮奶油像穿著一襲清潔無菌的病袍,乖乖躺在盤子裡,仍舊使人感到樂觀,健康,等待刀與叉的手術。咖啡店裡坐滿各路各派的外科醫生,彼此低語談笑也如同正在討論最適合的療程。那時她常常浮躁而焦慮,覺得自己就像一塊蛋糕,需要誰來立刻替她切除身心的痛楚,可是呼天搶地未免太過羞恥了。苦難若有等差,則求救亦有階級之分。她遂只能望著窗外的藍天發怔,反正咖啡店裡永遠要有一個看似無聊慵懶的人。無聲的煩憂,是為氣氛。
有時候她想起尚未化作往事的惱事,精神賁張,紅血球與白血球在管線裡迅速穿梭,彷彿有一團上體育課的小學生在她體內紅白大對抗,各組嚌嚌嘈嘈競相把無數小球拋進高懸的竹簍,登時滿天珠玉,亂亂飛得不得了。儘管如此,她相信自己仍舊顯得寧靜肅穆。破壞咖啡店的寧靜肅穆是不道德的。
她愛極愛極這條長街,每棟樓房不出七層,高高低低錯落,一棟帶著一間咖啡店,她可以逐日拜訪宛若投醫,回訪則是回診。連續四棟五層的公寓挨著就是一首五絕,連續數棟四層的公寓挨著就是一首詩經,五層七層五層,遂成了曖昧的日本俳句,公寓小窗倒映出的花影、磚瓦罅隙間綠茸茸的蘚苔、陽台欄杆上停駐的貓與雀、居民開門之前收束抖擻的洋傘,便是不言而喻的季語。她想起羅蘭・巴特初識俳句後的驚嘆:「俳句說:『就是這個,就是如此,就是這樣。』這麼說更清楚:『這!』」參差的樓房凹凹凸凸畫出了整條長街的天際線,一折一折像韻律失調的心電圖。徘徊路邊,挑選宜於入座的咖啡店時,她的目光在這裡向上爬一格,在那裡向下爬一格,轉瞬起伏,視域上緣不斷感測到一股盎然的藍意,那藍天是藍得美不勝收。這裡缺乏都市的巴別塔,女媧補天的靈龜足,山稜,水平,教堂的筆尖鐘樓,歌劇院的圓貝穹頂,建築學上的一切屏蔽與突刺均謙卑退位,有的只是窯爐天候,以及將要滂沱的威基伍德式的藍天。
暮春的晴朗像一隻寶藍陶瓷茶壺,藍得鮮潔,藍得易碎。時間過去,陰雲疊聚如同髒污的指紋,眾人交互斟酌把玩,終於不小心摔傷了茶壺,令那瓷器落地炸出貫耳的響雷。砰訇一聲,整個完美的蔚藍忽然就八花九裂的,濺散的熱茶淋得世界又香又痛又迷糊。
那些蒸悶踟躕的白晝暈成一段長假,假期的最後一天應當也有離情別緒。咖啡店裡,醫生們總在那裡診治蛋糕,她總在窗邊支頤沉思,偶爾揪出每張木桌抽屜裡都有的一本素描冊子草草書寫平假名俳句,五七五,五七五,並且提醒自己直到天空轟然綻開蜿蜒電光像茶壺上的第一簇裂痕之前,必須嚴格守住格律和眼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