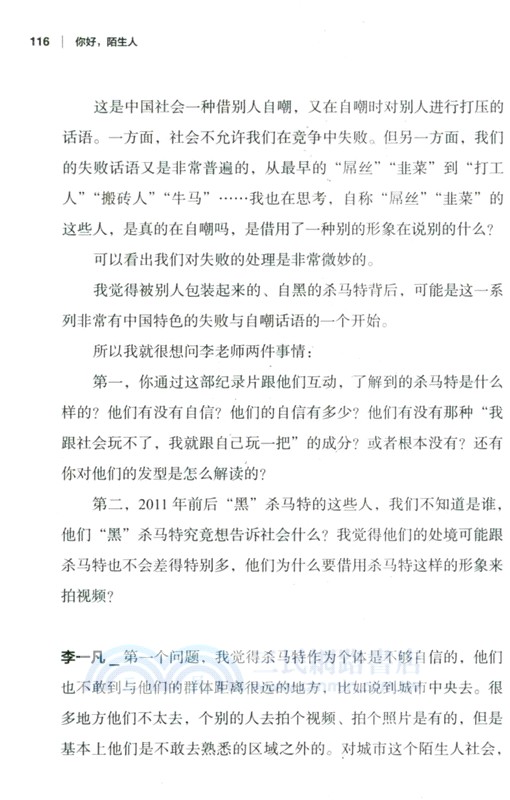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1.當今極富聲譽的人類學家項飆“附近的消失”話題續作。作為當今中國社會學界的重要學者,項飆的新作深入探討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關係的變化,尤其是“陌生人”現象及其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書中不僅分析了陌生人現象的普遍化,還提出了“陌生化”和“透明化”等創新性概念與“安生式思考”的方法,為理解現代社會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2.首次完整闡釋“陌生人及陌生化”概念的多層次內涵,提出一種安生式思考的方法與實踐。書中探討的陌生人與陌生化問題與現代社會的實際情況緊密相連,如城市化形成的陌生人社會、技術發展帶來的社交疏離、社會信任的缺失等,能夠引發讀者的共鳴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還能疏解大眾情緒,增強社會信任,對社會的修復與治理具有積極意義。3. 跨學科對話的研究方式為“看見陌生人”的實踐提供了場景和縱深。本書創新性地結合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多個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對陌生人這一話題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這種對話非常具有創新性,打破了學科的界限,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範式。不僅能夠吸引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專業的學者和學生,還吸引對社會現象和人際關係感興趣的大眾讀者。4.本書分享了豐富的實踐案例,具有很強的啟發性和借鑒價值。本書不停留於關注或批判的層面,更是給出應對陌生化洪流帶來的疏離與孤獨的實踐方法。項飆提出從看見身邊的陌生人開始,構建一種安生式思考的方法與實踐,即基於具體現實、注重生活經驗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不僅關注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還關注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感受和體驗,可以幫助我們在陌生化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和行動點,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會關係。在陌生化的洪流中看見他人,看見自己,在看見的過程中察覺意義。《你好,陌生人》是人類學家項飆領銜的一部剖析現代社會人與人關係的作品。本書以三聯人文城市發起和策劃的系列對話為緣起,以“你好,陌生人”為話題切入點,通過項飆與多位跨領域學者的深度對話,探討了現代人們如何在日益陌生化的社會中重新發現他人,重建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連接。在現代社會生活的快節奏與高度透明化的背景下,我們逐漸陷入“陌生化”的困境,對身邊的人與事逐漸變得無感。本書反思
作者簡介
項飆,1972年生於浙江溫州,20世紀90年代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完成本科、碩士學習,1998年受邀免試進入英國牛津大學讀社會人類學博士,2003年獲博士學位後留校,2015年成為牛津大學教授,現為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著有《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Global “Body Shopping”(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獲2008年度美國人類學協會安東尼‧利茲獎,中文版《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合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學出版社,2013年),與《單讀》主編吳琦合著訪談式作品《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發表論文多篇,曾獲2012年威廉‧L. 霍蘭德獎(William L. Holland Prize)、英國科學院中期職業發展獎等。
劉小東,藝術家,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代表作《你的朋友》《三峽好人》
何襪皮,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類學博士,罪案研究者,公眾號“沒藥花園”主理人
李一凡,藝術家、紀錄片導演,代表作《殺馬特我愛你》《淹沒》
劉悅來,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上海社區花園發起人
沈志軍,南京市紅山森林動物園園長,動物園創新設計實踐者
賈冬婷,三聯人文城市、三聯中讀執行總編輯
段志鵬,設計研究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訪問學者
著有《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Global “Body Shopping”(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獲2008年度美國人類學協會安東尼‧利茲獎,中文版《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合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學出版社,2013年),與《單讀》主編吳琦合著訪談式作品《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發表論文多篇,曾獲2012年威廉‧L. 霍蘭德獎(William L. Holland Prize)、英國科學院中期職業發展獎等。
劉小東,藝術家,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代表作《你的朋友》《三峽好人》
何襪皮,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類學博士,罪案研究者,公眾號“沒藥花園”主理人
李一凡,藝術家、紀錄片導演,代表作《殺馬特我愛你》《淹沒》
劉悅來,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上海社區花園發起人
沈志軍,南京市紅山森林動物園園長,動物園創新設計實踐者
賈冬婷,三聯人文城市、三聯中讀執行總編輯
段志鵬,設計研究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訪問學者
名人/編輯推薦
“你好,陌生人”,不是說要我們一定要跟陌生人交朋友,而是去觀察、去注意、去想像。這個陌生人,他此刻在想什麼?學會看人之後,你周邊的面目會清晰起來。
書中的五位對話嘉賓,都是“認得陌生人”的專家——他們的工作是瞭解和表達陌生人的生活和心理狀態。
畫家劉小東以高度寫實的風格讓觀眾看到那些無所不在但又面目模糊的陌生人(比如民工、小鎮青年)究竟長什麼樣。人類學者何襪皮研究了中國社會裡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之一——保安,同時通過微信公眾號系統分析當下的犯罪案例。紀錄片導演李一凡,讓我們認識了“殺馬特”——以具有“炸街”效果的奇異髮型來表達自己的陌生感的低收入年輕人。城市設計專家劉悅來一直在組織陌生人參與城市社區花園建設。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的園長沈志軍,要把動物園變成以動物為中心的動物園,把作為陌生者的動物放在中心。
同時,作為藝術家、研究者、社會行動者,他們的工作不僅僅是把陌生的現象變得熟悉,他們更是要提出陌生的視角,把熟悉的現象重新變得陌生,引起新的反思。
書中的五位對話嘉賓,都是“認得陌生人”的專家——他們的工作是瞭解和表達陌生人的生活和心理狀態。
畫家劉小東以高度寫實的風格讓觀眾看到那些無所不在但又面目模糊的陌生人(比如民工、小鎮青年)究竟長什麼樣。人類學者何襪皮研究了中國社會裡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之一——保安,同時通過微信公眾號系統分析當下的犯罪案例。紀錄片導演李一凡,讓我們認識了“殺馬特”——以具有“炸街”效果的奇異髮型來表達自己的陌生感的低收入年輕人。城市設計專家劉悅來一直在組織陌生人參與城市社區花園建設。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的園長沈志軍,要把動物園變成以動物為中心的動物園,把作為陌生者的動物放在中心。
同時,作為藝術家、研究者、社會行動者,他們的工作不僅僅是把陌生的現象變得熟悉,他們更是要提出陌生的視角,把熟悉的現象重新變得陌生,引起新的反思。
目次
前言:我是陌生人
透明,不透氣
認可和認得:作為陌生人的小鎮做題家
反向共情
不能安生的陌生人,如何安生式地思考?
第一章
看人不是看相,看的是內在的生活感
項飆對談畫家劉小東
“生活”跟“活著”不一樣
誠懇就是不停地矯正自己;方便到最後可能導致野蠻
分類的目的,在於看見具體的人
看身體,看一個生活積澱出來的人
酷,就是敢於下判斷,而且下的判斷非常準確
生活樣式下面,還有沒有生活
線上是觀點和觀點的打架,線下是人與人的交流
今天的生活,同時面臨著意義過剩和意義缺失
重複地工作,就像重複地吃飯一樣
第二章
我們怕的是親密關係還是陌生人
項飆對談罪案研究者何襪皮
身邊的安全和擺脫的願望
對陌生人戒備和對親密關係的恐懼
陌生化和靠切割解決問題
寄居蟹人格,表面是“你需要我”,其實是“我需要你”
保安群體: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
危險是對“被污染”的恐懼
保安的自我價值感很低
恐懼成了一種會員制
盲盒式生活是恐懼的另一面
第三章
在流水線上沒有歷史,做殺馬特才有
項飆對談導演李一凡
自黑不是殺馬特
殺馬特是個家族
殺馬特和屌絲不一樣
暴富、抱負、報復
難以進入的宿舍
陌生和陌生化的區別
流水線上是沒有歷史的,做殺馬特才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急迫
肉身經驗為什麼很重要
殺馬特和父輩的隔閡能和解嗎
知識與所處環境的斷裂
到他們生活的現場去
年輕人如何對自己的生活形成一套解釋
為什麼我們對生活的理解沒有質感
第四章
為什麼陌生的花園會帶給我們喜悅
項飆對談社區營造實踐者劉悅來
重建附近,“把手”很重要
社區花園不是一種佔有,而是一種照顧
怎麼處理花園裡的麻煩
開始行動就好
花園再小,也要有個名字
植物的邏輯,不是折疊,是展開
“小”往往更有韌性,來克服脆弱性
中國的社區營造,需要重建附近
第五章
在動物園看動物,其實也是在看自己
項飆對談“百獸之王”沈志軍
紅山動物園有什麼不一樣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萬物皆通
喜歡或不喜歡的,身邊或遙遠的,不同的動物構成了生物多樣性
人類用範疇把世界打包,動物有自己的一套
通過對動物的談論,人和人的關係也可能會變化
社會修復,動物如何成為啟動點
和諧取食與優勝劣汰
動物園到底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第六章
“你好,陌生人”
是“附近的消失”議題的延續
跟陌生人交往,是一種場景閱讀,是對自己生命經驗的調動
找到具體的把手,感受生命過程的意義
代際關係中的陌生:跟逐漸老去的父母對話
病了,才看到了完整的自己
年輕人的所謂“玻璃心”,是一件好事情
生活就是各種各樣的“非必要”
別人的魅力和力量,其實是來自你自己
後記:“製造”對話場
透明,不透氣
認可和認得:作為陌生人的小鎮做題家
反向共情
不能安生的陌生人,如何安生式地思考?
第一章
看人不是看相,看的是內在的生活感
項飆對談畫家劉小東
“生活”跟“活著”不一樣
誠懇就是不停地矯正自己;方便到最後可能導致野蠻
分類的目的,在於看見具體的人
看身體,看一個生活積澱出來的人
酷,就是敢於下判斷,而且下的判斷非常準確
生活樣式下面,還有沒有生活
線上是觀點和觀點的打架,線下是人與人的交流
今天的生活,同時面臨著意義過剩和意義缺失
重複地工作,就像重複地吃飯一樣
第二章
我們怕的是親密關係還是陌生人
項飆對談罪案研究者何襪皮
身邊的安全和擺脫的願望
對陌生人戒備和對親密關係的恐懼
陌生化和靠切割解決問題
寄居蟹人格,表面是“你需要我”,其實是“我需要你”
保安群體: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
危險是對“被污染”的恐懼
保安的自我價值感很低
恐懼成了一種會員制
盲盒式生活是恐懼的另一面
第三章
在流水線上沒有歷史,做殺馬特才有
項飆對談導演李一凡
自黑不是殺馬特
殺馬特是個家族
殺馬特和屌絲不一樣
暴富、抱負、報復
難以進入的宿舍
陌生和陌生化的區別
流水線上是沒有歷史的,做殺馬特才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急迫
肉身經驗為什麼很重要
殺馬特和父輩的隔閡能和解嗎
知識與所處環境的斷裂
到他們生活的現場去
年輕人如何對自己的生活形成一套解釋
為什麼我們對生活的理解沒有質感
第四章
為什麼陌生的花園會帶給我們喜悅
項飆對談社區營造實踐者劉悅來
重建附近,“把手”很重要
社區花園不是一種佔有,而是一種照顧
怎麼處理花園裡的麻煩
開始行動就好
花園再小,也要有個名字
植物的邏輯,不是折疊,是展開
“小”往往更有韌性,來克服脆弱性
中國的社區營造,需要重建附近
第五章
在動物園看動物,其實也是在看自己
項飆對談“百獸之王”沈志軍
紅山動物園有什麼不一樣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萬物皆通
喜歡或不喜歡的,身邊或遙遠的,不同的動物構成了生物多樣性
人類用範疇把世界打包,動物有自己的一套
通過對動物的談論,人和人的關係也可能會變化
社會修復,動物如何成為啟動點
和諧取食與優勝劣汰
動物園到底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第六章
“你好,陌生人”
是“附近的消失”議題的延續
跟陌生人交往,是一種場景閱讀,是對自己生命經驗的調動
找到具體的把手,感受生命過程的意義
代際關係中的陌生:跟逐漸老去的父母對話
病了,才看到了完整的自己
年輕人的所謂“玻璃心”,是一件好事情
生活就是各種各樣的“非必要”
別人的魅力和力量,其實是來自你自己
後記:“製造”對話場
書摘/試閱
透明,不透氣
中國社會的陌生化趨勢,體現近幾十年陌生人的形象的變化。在20世紀末,中國人公共意識裡的陌生人是和道德焦慮聯繫在一起的。當時出現一系列見死不救,對陌生人冷漠無情的事件;也出現了陌生人對提供幫助的人倒打一耙、所謂“碰瓷”的現象。人們不敢幫助陌生人,也不敢輕易接受陌生人的幫助。1994年暑假我和北京大學的同學一起去東莞做民工調查,京廣線上火車一路廣播“千萬不要把貴重物品託付給陌生人照看,對陌生人的建議要額外的小心”。我和同行的同學對此頗不以為然,我們說公共宣傳應該提倡公共信任,不應該反復提醒去提防彼此。一通理論評論後我在座位上酣然入睡。醒來的時候,我放在頭邊的價值不菲的索尼牌小型錄音機不翼而飛。坐在周圍的乘客面無表情,一問三不知。我和同學面面相覷,不知道怎麼在理論上自圓其說,經濟上的損失更讓我心疼了一路。
當時的公共道德焦慮,是和1980末期以後城鄉人口流動的陡然增加、城市裡出現了大量的陌生人緊密相關的。在東莞我們親眼看到了市民和地方政府對經濟蓬勃發展中的社會秩序的顧慮。我們也看到了民工的陌生人狀態:他們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卻進入不了城市社會;他們在農村老家還有自己的根,但是也回不了老家。他們被城裡人當作陌生人、他們自己也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民工告訴我,他們最經常的衝突並不起源於車間裡面的勞動關係,而往往是宿舍裡面的生活瑣事,比如上廁所、洗頭、用電熱爐的問題。我原來想像宿舍是農民工變成朋友、形成團結互助的基礎,而事實則相反,在狹小的共同生活空間裡,他們形同陌路。
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火車的廣播不再提醒陌生人的危險,我也不用擔心錄音機會被偷。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人臉識別技術,使社會治安大大好轉,陌生人和陌生人不再彼此害怕。但是生活裡的“陌生化”似乎也進一步加強了。我們這組對話的嘉賓之一李一凡導演,在拍《我愛你,殺馬特》的紀錄片時,去了我們當年調查的同一個鎮。李一凡導演發現,同一宿舍的民工幾乎不認識彼此。車間的流水線是24小時不停的,工人沒有統一的上下班時間,而是被輪番安排進廠出廠,宿舍成為工人們輪番睡覺的地方,在任何一個時點都有人在睡覺。室友的陌生化在今天已經普及到大學生、青年白領、青年公寓和城中村的租客等等。 我的一位德國同事問我,他的朋友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同宿舍的中國學生從來不跟別人說話,而且別人問他願不願意聚餐、一起出來玩時,他的反應讓人覺得他似乎受到了冒犯。我的猜想是,這位同學首先可能覺得交往是一種負擔,同時他也可能害怕,當彼此不再陌生,有了互相瞭解後,關係會變得複雜,成為更大的負擔。
伴隨著陌生化趨勢的是有序化,即社會變得更安全更可預測。這種高度有序的陌生化,呈現出段志鵬所說的“透明不透氣”的特徵。設計研究者段志鵬是我在德國馬普所的同事,是這組對話的策劃人之一,和《三聯生活週刊》的賈冬妮一起主持了我們的對話。志鵬指出,像玻璃和塑料這樣的材料是透明不透氣的,它們讓人一覽無餘,但是物質無法穿透,密封的玻璃和塑料容器可以殺死幾乎一切生命。透氣不透明的,包括樹葉、泥土、海水、帶著露水和灰塵的空氣、特別是有機體的皮膚。靠著永不停息、但是往往是不可見的物質的滲透和交換,生命才得以維持。志鵬進一步闡述道 :
從建築學的角度想,我認為現代建築設計的主要的戰場就是對於透明性的爭奪。早期玻璃由於技術限制,它的透明性沒有這麼好。18世紀建築之前,玻璃的作用主要是透光,而不是透明。例如,中世紀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要讓光線穿過卻沒有讓視覺完全穿過;甚至,它需要視覺上不能穿過去來保持神秘。但在工業革命之後,一種新的建築形式——車間出現了,這種近似教堂的尺度的建築需要大量自然採光來讓工人在白天的室內工作。技術上也是因為18世紀平板玻璃的生產技術有很大的優化,包括批量生產,打磨技術還有增加透明度的玻璃配方。在車間的設計上,大片平板玻璃大量用於建築的外立面;這種車間式的建築成為了現代設計的母題。
玻璃和互動的線索的進階就是屏幕的出現,玻璃不僅僅用來作為展示的物質,它自己開始能互動了。智能手機的出現就是玻璃可觸摸的作品:按壓玻璃。我想到透氣也是我們的聊天裡想到了觸摸屏開始的。疫情期間我能從我的屏幕裡看到那麼多信息,這些信息讓我焦慮,但是我關上屏幕,它突然就變成一塊玻璃了。玻璃成了一種有限可交互的物質。20世紀有很多人穿過屏幕的科幻想象,但是現在這種想像不多了,仿佛默認了玻璃的交互只能是輸入和輸出信號的邏輯。觸摸屏幕和鍵盤輸入信號,屏幕上的視覺給你返回一些信息。那時讓我在想,這個材料真冷酷,讓你看到但是鎖死你的其他五感。看到世界、摸不到世界還挺殘忍的。項老師之前寫過一個移民和窗口的短文也可以從玻璃這種特性來理解。
21世紀早期的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透明,或者更精確地說,越來越按照透明化的原則來組織。要把一切都變得一目了然,可以預測,儘量減少驚訝、奧妙和等待。但是,人和人之間聽不到彼此的呼吸,難以打開自己,也不敢打開對方。一個個陌生人就是一個個清晰的陌生人,他們不會轉變成朋友、敵人、客人,不會帶來曖昧、驚喜、陰影、高光。這裡的透明,並不是說人真的可以看到一切,而是說你想看到的、覺得重要的東西都已經擺在眼前,而那些你不想看到的、覺得不重要的——比如那一個蹲在離我50米遠的地上的戴滑雪帽的中年人為什麼傷心——被處理成不可見。凡是可以被看到的都是合理的,那些沒有看到的是不想看也不用看到的。反過來,當我們看不到某件東西,我們也就認為那個東西不存在或者不應該存在。客觀上的看不見,內化為主觀的不去看見。我們可以看到想看到的無窮無盡的陌生人,可以和他們打招呼、通過社交平臺建立聯繫、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們永遠是陌生人。如果這些陌生人的回應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可以馬上拉黑他們或者他們屏蔽我們。整個世界似乎就在我們的指尖,在屏幕上一切盡收眼底,但是頃刻間這個世界會變回成一個黑屏。我們似乎掌握了從天上鳥瞰世界的神器,但是好像總是站在生活的外面。
生活變得透明而不透氣,是和公共的抽象化聯繫在一起的。透明顯然意味著公共——大家在這裡一覽無餘甚至無處遁身,但這個公共不是由無數個個體通過互動而搭建出來的,而是靠一個全面貫穿我們生活的第三方系統捏合而成的。這個第三方定義所有的個體,規定所有個體的行為,所有的個體都直接對著第三方負責。通過個體間橫向互動而形成的公共是不透明的,而是透氣的;通過一個統一的第三方建立的公共是抽象的也是透明的。這個第三方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和效果。它可以是神,比如在一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所有的個人對神效忠和負責。這個第三方可以是貨幣,如齊美爾分析的那樣,貨幣可以把一切定量化,讓所有人按統一的理性去計算和預測。 這個第三方也可以是商品,比如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生產和交易的邏輯消除了各種社會差異,把幾乎所有的社會關係都變成商品的隸屬。這個第三方也可以是政治權威。邊沁設計的圓形監獄是高度透明的,因為所有的囚犯把監獄中央瞭望塔上的士兵當作核心的參照,即唯一的一個近乎萬能的第三方,而囚犯和囚犯之間沒有溝通。 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興起作了這樣的描畫:所有的個體奔向一個權威,個體和個體之間沒有隱私、沒有實質性差異、也沒有實質性聯繫,從而完全透明。
在21世紀,這幾種力量——意識形態的、經濟的、政治的——以空前細密複雜的方式聯繫在一起。同樣重要的是,技術成為貫穿各個領域、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三方。線上支付、監視和人臉識別,使得社會生活高度透明,也使得彼此的實質性交流近乎消失,不再透氣。技術對日常公共話語的影響尤其明顯。日常公共話語原來是通過個人的書信、面對面的對話、閒言碎語、口碑、名氣等等要素交叉而成的。在社交媒體和平臺經濟時代,每個個體都可以直接參與到透明的公共中去,其間沒有間隔沒有纏繞,也不需要中介和等待,但是同時大家的表達非常小心,因為在系統面前,每個人都是“裸人”。出租車的變化是一個值得分析的例子。在1990年代的中國城市,出租車曾被戲稱為“人民廣播電臺第一頻道”。出租車司機有無數的社會新聞和小道消息,也有無盡的熱情去向乘客輸出觀點、和乘客辯論。但是今天的出租車裡變得非常安靜。變化的緣起之一,是2010年代末網約車的治安事件。在治安事件普遍減少的趨勢下,這些案件引起了社會的恐慌。平臺公司和政府的策略不是加強資格認證和勞動關係調整、而是引入了全面的監聽體系。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身安全,但是也使得司機和乘客彼此間不再交流。司機不願意多談,有的司機在座位前貼上“此車有錄音”的提示,監測系統甚至會自動提醒司機和乘客“請不要討論和行程無關的事項”。另一個例子,人們在街上、飯館等公共場合說話時也不得不多留一個心眼,因為不知道哪裡有人在錄屏、錄像、直播,隨口說的話可能被錄音甚至直播。在日益稀薄的生活裡,無數的人在稠密地錄製,製造一個透明的世界。
職場是第三方力量把公共抽象化的另一個場所。一位名叫“Opera”的網友反思為什麼同事之間如此陌生。他在工作中發現,同事之間往往是點頭之交,反而是離職了之後才有更深的互動。工作中的陌生化當然和人際之間的競爭和利益爭端有關,但是更可能是結構性的。技術的發展,使得每個人的工作過程對系統來說是幾乎完全透明的。因為每個個人直接和系統對應,個人之間不再需要發生聯繫。系統為了保證和個體的高效互動,也不鼓勵個人間的橫向聯繫。友情變得稀缺,正因為友情是自由個體之間情感上的共振、思想上的共享,可以完全脫離作為第三方的體系。因為抽象的公共性,陌生人本身不再可怕,而陌生人的聚集——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間也許會產生某種超出陌生的關係——成為需要不斷提防的危險。
當一切都是透明的,抽象的公共性往往也失去了內容。比如道德考慮可能變得虛無。人類之所以有道德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信息有限。在事情不透明的情況下人們需要做出判斷和選擇,這時候人們就需要道德,道德使得人和人可以在不透明中繼續有意義地交往。作為美德的助人為樂,是要求人們在很多方面做模糊處理的,比如求助者是不是需要幫助、求助者怎麼用了善款、是不是真的感恩。當人們要把求助和幫助變成一個完全透明的過程,對求助者高度警惕、要調查求助者的“真實背景”、審問施助者的“真實動機”,那就把道德問題變成了風險控制和效率管理的問題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從此不再有道德焦慮,就可以安心。相反,在道德問題變成概率問題之後,一切變得不可信,不真實、不可控。所有的善意都帶上了陰影和疑團,道德倫理考慮被彌散性的心理緊張和焦慮所取代。通過社交媒體精確尋友是另一個透明可能帶來焦慮的例子。當人和人的交流變成一個配對和選擇的過程,當然是空前高效的。但是這也意味著你永遠是在被判斷、被審視。人們要時刻警惕不能釋放負面信號,否則就可能被拋棄和否定。加繆筆下《局外人》中的陌生人默爾索(Meursault),到處看見燦爛的陽光,照亮一切的強光讓他目眩、失控。讓默爾索失控的陽光是不是我們的透明?
一方面人們覺得有太多未知,前途未蔔,另外一方面又覺得一切都可以一眼看穿;這二者在追求透明化的社會裡並不矛盾。一個囚犯不知道另一個囚犯的情況,囚犯也不知道今天和明天會發生什麼,這完全不影響他們生活的透明感。在透明的世界,人的命運已經被系統的力量決定了,未蔔的前途是個人的不幸,它們沒有意義;同時,如果一個人真正符合了透明世界的規則,這些未蔔事件都可以被克服,變成可蔔。人生的意義似乎就在於按照那些寫在牆上、掛在空中的標語來克服自己那些不透明的經歷,變成人人認可的人。歸根到底,透明是社會組織的方式,是人們理解個人和社會關係的一個意象,從而也成為人們客觀的存在狀態。
認可和認得:作為陌生人的小鎮做題家
如果說流動人口是20世紀後期中國社會中陌生人的代表,那麼“小鎮做題家”則是21世紀陌生人的一個典型形象。小鎮做題家是在2010年代,中國青年中出現的一個普遍而強烈的自我意識。小鎮做題家是一個具有強烈反思性的自我指稱。一方面,小鎮做題家意識到自己是成功者,他們學業優秀,上了大學、落戶城市、進入了中產,實現了社會地位的躍升。另一方面,小鎮做題家往往在工作和生活裡感到無所適從、孤獨和迷茫,明明自己通過努力獲得了這個位置上,卻覺得這個位置不是自己的。小鎮做題家和流動人口形成鮮明的對比。流動人口是體系(特別是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陌生人,他們無法從正式體系裡獲得生存資源,而必須在體系之外闖出一片天地。而小鎮做題家是體系的自己人,他們一直受體系的高度認可,從體系裡獲得保障,在城市裡他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人口。但是小鎮做題家卻覺得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小鎮做題家往往把自己的陌生感歸因於出身背景;來自小城鎮的他們沒有見過“世面”,教育資源的匱乏造成他們社會和文化資本的缺乏。但是這不能夠解釋為什麼小鎮做題家的意識沒有在以前出現。村鎮出生的人口在中國的革命和改革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並沒有這樣的陌生感。相反,小鎮背景往往被認為是一個優勢。比如我們的對話嘉賓之一畫家劉小東,他的小鎮背景是他的創作和思想的重要靈感來源。而且,在二十世紀末,城鄉的教育條件的差距是明顯縮小。2000年以後全國範圍的鄉村撤點並校,讓大量的農村孩子進入縣城小學,實行住校,他們的學習和娛樂方式和城市孩子沒有太大不同。最後,小鎮做題家的心態,在很多城市出生的年輕人身上也有體現。小鎮做題家的意識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正是因為它反映了很多人的心態,而不僅僅是某個群體的獨特之處。
小鎮做題家的自我陌生化,與其說是因為他們的特殊背景所致,不如說是他們長期背負的、要擺脫自己的背景的壓力使然。不是鄉村背景“不饒恕”他們,而是他們切斷鄉村背景的努力奪去了他們的從容,使他們不再能有力地運用自己的“生活世界” 提供的資源。1990年代的流動人口雖然是城裡的陌生人,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老鄉關係,他們與老家保持精神上的聯繫,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世界;而小鎮做題家往往是孤身作戰。和大城市裡的年輕人相比,小鎮做題家從小就被告知:離開你的家鄉是你要追求的目標,你應該把自己看作是你的環境裡的陌生人。他們熟悉城市環境和城市中產的生活方式,對自己的原生環境反而是知之甚少。深圳大學的一位本科生在我的一場對話中講到:
小鎮做題家的宿命就是總覺得自己要離開自己所出生的地方,而且要離開得越遠越好,因為在出生的地方都是痛。家看似熟悉,也是不熟悉。這一路下來沒有跟任何一個土地產生真正的聯繫。上學期間,就是在非常孤立的一個生活空間,封閉管理。總是猶豫的,覺得不安全,不熟悉。覺得逃離就是我們的使命,這個鬼地方再也不想回來了。覺得生活不受自己的掌控,有一種徹底的無力感。
除了要逃離家鄉,小鎮做題家也一直生活在簡化、甚至切斷生活關系的狀態中。深圳大學的另一位同學在同一次對話中說:
(小時候)課業很繁重,沒有什麼社會化,父母就把我們拋給學校。生活的經驗跟我自己的經歷完全是分隔開的。父母在外面做生意的情況我完全不知道。我那些不在這些好學校裡讀書的同齡人的情況我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就這樣孤立在實際當中……覺得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很遠。沒有辦法理解這些人。覺得自己是怪物,也覺得別人是怪物。
小鎮做題家的陌生化也可能和他們強烈的自我否定傾向有關。一位參加了《看見最初500米》的學員雖然本人並不是來自於小鎮,但是她對自己的勇敢剖析可能講出了很多年輕人的心聲:
父母、老師和自己構造出一個理想的人,這個理想的人非常強大,對自己非常厭惡,但是他是假的人,他壓抑了“我”的真的自己,把“我”變成一個空心的人,所以形成無力感。不知道為什麼會存在在這裡。所以“我”的鬥爭真的是一個生死的鬥爭,就是覺得要不要存在的鬥爭。因為這個強大的“我”看著自己,是不願意接納自己的。如果自己不能夠滿足世俗的那些成功標準,就覺得自己沒有存在的價值,不能被別人接納。是的,“我”的底層邏輯就是自己不能夠接受自己。現在的情況是不好的,“我”是厭惡自己的。我的厭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對象,或者對自己某一種性格,這種厭惡是很擴散性的,就是覺得本來的自己都不好,只有努力的樣子才是好的。這不僅僅是在工作上,學習上,在顏值上,身體上,體重上都是覺得自己不能接受,所以都是要去健身、要去學各種班,去學習社交禮儀,去講話。所以說人設,就是覺得本來的自己不好,需要重新設計一個人。
小鎮做題家的陌生感,反映了社會生活“透明不透氣”的特徵。他們生活的透明性體現在,他們的成長軌跡和成績,符合體系規定的標準和預期,被毫無懸念地認可。他們體會到的不透氣,體現在他們無法從容地呈現個人的掙扎、猶豫和苦惱。他們獲得了“認可”,欠缺的是“認得”。認可是系統根據既定的標準,評價一個人的成果,決定給與獎勵還是懲罰。認得,則是一個主體對另外一個主體的理解,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情緒、考慮、掙扎和歷史的看見,它不涉及考驗、判斷和獎懲。
認可是單向的,是系統對個體的判斷,追求認可的個體無法對系統產生影響。而認得是雙向的。認得必須通過雙向的交流而實現;認得給人們帶來的尊嚴感,不來自表揚和獎勵,而來自交流過程的真誠性。認得的雙向意味著,如果我們不認得別人,我們也不能夠感知到別人對我們的認得。這也意味著,我們對自身價值的確認,不只來自於別人對我們的認得,其實也來自我們對別人的認得。這是因為,在認得別人的時候,我們要把自己打開,要在喚起自己的經歷和情緒的過程中去認得別人。這裡認得的“得”,不僅是對別人的新的理解,也是自己對自己會有新的心得。我們對別人的認得、別人對我們的認得、我們對自己的認得,是渾然一體的。一個人如果只有光鮮透明的成績,而沒有可以述說的經歷,那他(她)不能被認得,也很難認得別人。而且,在長年的追求認可中,自己變成自己要動員和控制的對象,要壓抑自己的各種和學業無關的衝動,自己不再認得自己的自然感受,自己成為自己的陌生人。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認可取代了認得,更嚴重的是,認可成為了認得的基礎。“愛是有條件的”——你要證明你值得愛,愛才存在——是不少年輕人從小感到生活沉重的重要原因。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缺乏愛,但是家庭、學校和社會灌輸的愛的“條件感”讓滋養變成了負擔。而獲得愛和認得的條件,就是要先獲得認可。很多人之所以要犧牲這麼多時間和精力來追求認可,正是因為這是他們獲得認得的基礎——通過證明我是正常的、成功的,以獲得關注、理解和愛。網名為KK的朋友(26歲,大學畢業後在公務部門工作,最近辭職)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道,我們從小浸淫在一種緊繃的氛圍裡。在親情中,要償還父母的犧牲;在學業或事業中,要把別人擠下去;在婚姻中,要維持伴侶心中的理想形象。似乎每種社會關係都有一套要求,無法達到標準的人,就會失去被傾聽與被愛的資格。”在我們的線上交流中,他提到了吳謝宇的案子:“從農村到北大,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他。他沒有別的可以抓住的東西,他自己的上進心、自己努力學習、證明自己,是唯一可以生存的理由。他母親是證明的對象。他的生命被這樣的證明耗盡,殺死母親是他的終結(無止境的追求認可和認得)。”當認可成為認得的基礎,親情可以變得額外沉重。吳謝宇也許是默爾索的鏡中像。默爾索疏離了他的母親(“我母親在今天去世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是我們聽到默爾索的第一句話),拒絕社會對他的判斷,認為人的存在毫無意義。默爾索在疏離和抵制社會關係的過程中陌生化。吳謝宇依附于母親、依附于社會、不斷得到認可,他在追求認可和獲得認可的過程中陌生化。吳謝宇,是我們這個時代悲劇性的陌生人。
………
中國社會的陌生化趨勢,體現近幾十年陌生人的形象的變化。在20世紀末,中國人公共意識裡的陌生人是和道德焦慮聯繫在一起的。當時出現一系列見死不救,對陌生人冷漠無情的事件;也出現了陌生人對提供幫助的人倒打一耙、所謂“碰瓷”的現象。人們不敢幫助陌生人,也不敢輕易接受陌生人的幫助。1994年暑假我和北京大學的同學一起去東莞做民工調查,京廣線上火車一路廣播“千萬不要把貴重物品託付給陌生人照看,對陌生人的建議要額外的小心”。我和同行的同學對此頗不以為然,我們說公共宣傳應該提倡公共信任,不應該反復提醒去提防彼此。一通理論評論後我在座位上酣然入睡。醒來的時候,我放在頭邊的價值不菲的索尼牌小型錄音機不翼而飛。坐在周圍的乘客面無表情,一問三不知。我和同學面面相覷,不知道怎麼在理論上自圓其說,經濟上的損失更讓我心疼了一路。
當時的公共道德焦慮,是和1980末期以後城鄉人口流動的陡然增加、城市裡出現了大量的陌生人緊密相關的。在東莞我們親眼看到了市民和地方政府對經濟蓬勃發展中的社會秩序的顧慮。我們也看到了民工的陌生人狀態:他們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卻進入不了城市社會;他們在農村老家還有自己的根,但是也回不了老家。他們被城裡人當作陌生人、他們自己也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民工告訴我,他們最經常的衝突並不起源於車間裡面的勞動關係,而往往是宿舍裡面的生活瑣事,比如上廁所、洗頭、用電熱爐的問題。我原來想像宿舍是農民工變成朋友、形成團結互助的基礎,而事實則相反,在狹小的共同生活空間裡,他們形同陌路。
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火車的廣播不再提醒陌生人的危險,我也不用擔心錄音機會被偷。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人臉識別技術,使社會治安大大好轉,陌生人和陌生人不再彼此害怕。但是生活裡的“陌生化”似乎也進一步加強了。我們這組對話的嘉賓之一李一凡導演,在拍《我愛你,殺馬特》的紀錄片時,去了我們當年調查的同一個鎮。李一凡導演發現,同一宿舍的民工幾乎不認識彼此。車間的流水線是24小時不停的,工人沒有統一的上下班時間,而是被輪番安排進廠出廠,宿舍成為工人們輪番睡覺的地方,在任何一個時點都有人在睡覺。室友的陌生化在今天已經普及到大學生、青年白領、青年公寓和城中村的租客等等。 我的一位德國同事問我,他的朋友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同宿舍的中國學生從來不跟別人說話,而且別人問他願不願意聚餐、一起出來玩時,他的反應讓人覺得他似乎受到了冒犯。我的猜想是,這位同學首先可能覺得交往是一種負擔,同時他也可能害怕,當彼此不再陌生,有了互相瞭解後,關係會變得複雜,成為更大的負擔。
伴隨著陌生化趨勢的是有序化,即社會變得更安全更可預測。這種高度有序的陌生化,呈現出段志鵬所說的“透明不透氣”的特徵。設計研究者段志鵬是我在德國馬普所的同事,是這組對話的策劃人之一,和《三聯生活週刊》的賈冬妮一起主持了我們的對話。志鵬指出,像玻璃和塑料這樣的材料是透明不透氣的,它們讓人一覽無餘,但是物質無法穿透,密封的玻璃和塑料容器可以殺死幾乎一切生命。透氣不透明的,包括樹葉、泥土、海水、帶著露水和灰塵的空氣、特別是有機體的皮膚。靠著永不停息、但是往往是不可見的物質的滲透和交換,生命才得以維持。志鵬進一步闡述道 :
從建築學的角度想,我認為現代建築設計的主要的戰場就是對於透明性的爭奪。早期玻璃由於技術限制,它的透明性沒有這麼好。18世紀建築之前,玻璃的作用主要是透光,而不是透明。例如,中世紀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要讓光線穿過卻沒有讓視覺完全穿過;甚至,它需要視覺上不能穿過去來保持神秘。但在工業革命之後,一種新的建築形式——車間出現了,這種近似教堂的尺度的建築需要大量自然採光來讓工人在白天的室內工作。技術上也是因為18世紀平板玻璃的生產技術有很大的優化,包括批量生產,打磨技術還有增加透明度的玻璃配方。在車間的設計上,大片平板玻璃大量用於建築的外立面;這種車間式的建築成為了現代設計的母題。
玻璃和互動的線索的進階就是屏幕的出現,玻璃不僅僅用來作為展示的物質,它自己開始能互動了。智能手機的出現就是玻璃可觸摸的作品:按壓玻璃。我想到透氣也是我們的聊天裡想到了觸摸屏開始的。疫情期間我能從我的屏幕裡看到那麼多信息,這些信息讓我焦慮,但是我關上屏幕,它突然就變成一塊玻璃了。玻璃成了一種有限可交互的物質。20世紀有很多人穿過屏幕的科幻想象,但是現在這種想像不多了,仿佛默認了玻璃的交互只能是輸入和輸出信號的邏輯。觸摸屏幕和鍵盤輸入信號,屏幕上的視覺給你返回一些信息。那時讓我在想,這個材料真冷酷,讓你看到但是鎖死你的其他五感。看到世界、摸不到世界還挺殘忍的。項老師之前寫過一個移民和窗口的短文也可以從玻璃這種特性來理解。
21世紀早期的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透明,或者更精確地說,越來越按照透明化的原則來組織。要把一切都變得一目了然,可以預測,儘量減少驚訝、奧妙和等待。但是,人和人之間聽不到彼此的呼吸,難以打開自己,也不敢打開對方。一個個陌生人就是一個個清晰的陌生人,他們不會轉變成朋友、敵人、客人,不會帶來曖昧、驚喜、陰影、高光。這裡的透明,並不是說人真的可以看到一切,而是說你想看到的、覺得重要的東西都已經擺在眼前,而那些你不想看到的、覺得不重要的——比如那一個蹲在離我50米遠的地上的戴滑雪帽的中年人為什麼傷心——被處理成不可見。凡是可以被看到的都是合理的,那些沒有看到的是不想看也不用看到的。反過來,當我們看不到某件東西,我們也就認為那個東西不存在或者不應該存在。客觀上的看不見,內化為主觀的不去看見。我們可以看到想看到的無窮無盡的陌生人,可以和他們打招呼、通過社交平臺建立聯繫、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們永遠是陌生人。如果這些陌生人的回應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可以馬上拉黑他們或者他們屏蔽我們。整個世界似乎就在我們的指尖,在屏幕上一切盡收眼底,但是頃刻間這個世界會變回成一個黑屏。我們似乎掌握了從天上鳥瞰世界的神器,但是好像總是站在生活的外面。
生活變得透明而不透氣,是和公共的抽象化聯繫在一起的。透明顯然意味著公共——大家在這裡一覽無餘甚至無處遁身,但這個公共不是由無數個個體通過互動而搭建出來的,而是靠一個全面貫穿我們生活的第三方系統捏合而成的。這個第三方定義所有的個體,規定所有個體的行為,所有的個體都直接對著第三方負責。通過個體間橫向互動而形成的公共是不透明的,而是透氣的;通過一個統一的第三方建立的公共是抽象的也是透明的。這個第三方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和效果。它可以是神,比如在一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所有的個人對神效忠和負責。這個第三方可以是貨幣,如齊美爾分析的那樣,貨幣可以把一切定量化,讓所有人按統一的理性去計算和預測。 這個第三方也可以是商品,比如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生產和交易的邏輯消除了各種社會差異,把幾乎所有的社會關係都變成商品的隸屬。這個第三方也可以是政治權威。邊沁設計的圓形監獄是高度透明的,因為所有的囚犯把監獄中央瞭望塔上的士兵當作核心的參照,即唯一的一個近乎萬能的第三方,而囚犯和囚犯之間沒有溝通。 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興起作了這樣的描畫:所有的個體奔向一個權威,個體和個體之間沒有隱私、沒有實質性差異、也沒有實質性聯繫,從而完全透明。
在21世紀,這幾種力量——意識形態的、經濟的、政治的——以空前細密複雜的方式聯繫在一起。同樣重要的是,技術成為貫穿各個領域、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三方。線上支付、監視和人臉識別,使得社會生活高度透明,也使得彼此的實質性交流近乎消失,不再透氣。技術對日常公共話語的影響尤其明顯。日常公共話語原來是通過個人的書信、面對面的對話、閒言碎語、口碑、名氣等等要素交叉而成的。在社交媒體和平臺經濟時代,每個個體都可以直接參與到透明的公共中去,其間沒有間隔沒有纏繞,也不需要中介和等待,但是同時大家的表達非常小心,因為在系統面前,每個人都是“裸人”。出租車的變化是一個值得分析的例子。在1990年代的中國城市,出租車曾被戲稱為“人民廣播電臺第一頻道”。出租車司機有無數的社會新聞和小道消息,也有無盡的熱情去向乘客輸出觀點、和乘客辯論。但是今天的出租車裡變得非常安靜。變化的緣起之一,是2010年代末網約車的治安事件。在治安事件普遍減少的趨勢下,這些案件引起了社會的恐慌。平臺公司和政府的策略不是加強資格認證和勞動關係調整、而是引入了全面的監聽體系。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身安全,但是也使得司機和乘客彼此間不再交流。司機不願意多談,有的司機在座位前貼上“此車有錄音”的提示,監測系統甚至會自動提醒司機和乘客“請不要討論和行程無關的事項”。另一個例子,人們在街上、飯館等公共場合說話時也不得不多留一個心眼,因為不知道哪裡有人在錄屏、錄像、直播,隨口說的話可能被錄音甚至直播。在日益稀薄的生活裡,無數的人在稠密地錄製,製造一個透明的世界。
職場是第三方力量把公共抽象化的另一個場所。一位名叫“Opera”的網友反思為什麼同事之間如此陌生。他在工作中發現,同事之間往往是點頭之交,反而是離職了之後才有更深的互動。工作中的陌生化當然和人際之間的競爭和利益爭端有關,但是更可能是結構性的。技術的發展,使得每個人的工作過程對系統來說是幾乎完全透明的。因為每個個人直接和系統對應,個人之間不再需要發生聯繫。系統為了保證和個體的高效互動,也不鼓勵個人間的橫向聯繫。友情變得稀缺,正因為友情是自由個體之間情感上的共振、思想上的共享,可以完全脫離作為第三方的體系。因為抽象的公共性,陌生人本身不再可怕,而陌生人的聚集——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間也許會產生某種超出陌生的關係——成為需要不斷提防的危險。
當一切都是透明的,抽象的公共性往往也失去了內容。比如道德考慮可能變得虛無。人類之所以有道德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信息有限。在事情不透明的情況下人們需要做出判斷和選擇,這時候人們就需要道德,道德使得人和人可以在不透明中繼續有意義地交往。作為美德的助人為樂,是要求人們在很多方面做模糊處理的,比如求助者是不是需要幫助、求助者怎麼用了善款、是不是真的感恩。當人們要把求助和幫助變成一個完全透明的過程,對求助者高度警惕、要調查求助者的“真實背景”、審問施助者的“真實動機”,那就把道德問題變成了風險控制和效率管理的問題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從此不再有道德焦慮,就可以安心。相反,在道德問題變成概率問題之後,一切變得不可信,不真實、不可控。所有的善意都帶上了陰影和疑團,道德倫理考慮被彌散性的心理緊張和焦慮所取代。通過社交媒體精確尋友是另一個透明可能帶來焦慮的例子。當人和人的交流變成一個配對和選擇的過程,當然是空前高效的。但是這也意味著你永遠是在被判斷、被審視。人們要時刻警惕不能釋放負面信號,否則就可能被拋棄和否定。加繆筆下《局外人》中的陌生人默爾索(Meursault),到處看見燦爛的陽光,照亮一切的強光讓他目眩、失控。讓默爾索失控的陽光是不是我們的透明?
一方面人們覺得有太多未知,前途未蔔,另外一方面又覺得一切都可以一眼看穿;這二者在追求透明化的社會裡並不矛盾。一個囚犯不知道另一個囚犯的情況,囚犯也不知道今天和明天會發生什麼,這完全不影響他們生活的透明感。在透明的世界,人的命運已經被系統的力量決定了,未蔔的前途是個人的不幸,它們沒有意義;同時,如果一個人真正符合了透明世界的規則,這些未蔔事件都可以被克服,變成可蔔。人生的意義似乎就在於按照那些寫在牆上、掛在空中的標語來克服自己那些不透明的經歷,變成人人認可的人。歸根到底,透明是社會組織的方式,是人們理解個人和社會關係的一個意象,從而也成為人們客觀的存在狀態。
認可和認得:作為陌生人的小鎮做題家
如果說流動人口是20世紀後期中國社會中陌生人的代表,那麼“小鎮做題家”則是21世紀陌生人的一個典型形象。小鎮做題家是在2010年代,中國青年中出現的一個普遍而強烈的自我意識。小鎮做題家是一個具有強烈反思性的自我指稱。一方面,小鎮做題家意識到自己是成功者,他們學業優秀,上了大學、落戶城市、進入了中產,實現了社會地位的躍升。另一方面,小鎮做題家往往在工作和生活裡感到無所適從、孤獨和迷茫,明明自己通過努力獲得了這個位置上,卻覺得這個位置不是自己的。小鎮做題家和流動人口形成鮮明的對比。流動人口是體系(特別是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陌生人,他們無法從正式體系裡獲得生存資源,而必須在體系之外闖出一片天地。而小鎮做題家是體系的自己人,他們一直受體系的高度認可,從體系裡獲得保障,在城市裡他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人口。但是小鎮做題家卻覺得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小鎮做題家往往把自己的陌生感歸因於出身背景;來自小城鎮的他們沒有見過“世面”,教育資源的匱乏造成他們社會和文化資本的缺乏。但是這不能夠解釋為什麼小鎮做題家的意識沒有在以前出現。村鎮出生的人口在中國的革命和改革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並沒有這樣的陌生感。相反,小鎮背景往往被認為是一個優勢。比如我們的對話嘉賓之一畫家劉小東,他的小鎮背景是他的創作和思想的重要靈感來源。而且,在二十世紀末,城鄉的教育條件的差距是明顯縮小。2000年以後全國範圍的鄉村撤點並校,讓大量的農村孩子進入縣城小學,實行住校,他們的學習和娛樂方式和城市孩子沒有太大不同。最後,小鎮做題家的心態,在很多城市出生的年輕人身上也有體現。小鎮做題家的意識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正是因為它反映了很多人的心態,而不僅僅是某個群體的獨特之處。
小鎮做題家的自我陌生化,與其說是因為他們的特殊背景所致,不如說是他們長期背負的、要擺脫自己的背景的壓力使然。不是鄉村背景“不饒恕”他們,而是他們切斷鄉村背景的努力奪去了他們的從容,使他們不再能有力地運用自己的“生活世界” 提供的資源。1990年代的流動人口雖然是城裡的陌生人,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老鄉關係,他們與老家保持精神上的聯繫,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世界;而小鎮做題家往往是孤身作戰。和大城市裡的年輕人相比,小鎮做題家從小就被告知:離開你的家鄉是你要追求的目標,你應該把自己看作是你的環境裡的陌生人。他們熟悉城市環境和城市中產的生活方式,對自己的原生環境反而是知之甚少。深圳大學的一位本科生在我的一場對話中講到:
小鎮做題家的宿命就是總覺得自己要離開自己所出生的地方,而且要離開得越遠越好,因為在出生的地方都是痛。家看似熟悉,也是不熟悉。這一路下來沒有跟任何一個土地產生真正的聯繫。上學期間,就是在非常孤立的一個生活空間,封閉管理。總是猶豫的,覺得不安全,不熟悉。覺得逃離就是我們的使命,這個鬼地方再也不想回來了。覺得生活不受自己的掌控,有一種徹底的無力感。
除了要逃離家鄉,小鎮做題家也一直生活在簡化、甚至切斷生活關系的狀態中。深圳大學的另一位同學在同一次對話中說:
(小時候)課業很繁重,沒有什麼社會化,父母就把我們拋給學校。生活的經驗跟我自己的經歷完全是分隔開的。父母在外面做生意的情況我完全不知道。我那些不在這些好學校裡讀書的同齡人的情況我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就這樣孤立在實際當中……覺得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很遠。沒有辦法理解這些人。覺得自己是怪物,也覺得別人是怪物。
小鎮做題家的陌生化也可能和他們強烈的自我否定傾向有關。一位參加了《看見最初500米》的學員雖然本人並不是來自於小鎮,但是她對自己的勇敢剖析可能講出了很多年輕人的心聲:
父母、老師和自己構造出一個理想的人,這個理想的人非常強大,對自己非常厭惡,但是他是假的人,他壓抑了“我”的真的自己,把“我”變成一個空心的人,所以形成無力感。不知道為什麼會存在在這裡。所以“我”的鬥爭真的是一個生死的鬥爭,就是覺得要不要存在的鬥爭。因為這個強大的“我”看著自己,是不願意接納自己的。如果自己不能夠滿足世俗的那些成功標準,就覺得自己沒有存在的價值,不能被別人接納。是的,“我”的底層邏輯就是自己不能夠接受自己。現在的情況是不好的,“我”是厭惡自己的。我的厭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對象,或者對自己某一種性格,這種厭惡是很擴散性的,就是覺得本來的自己都不好,只有努力的樣子才是好的。這不僅僅是在工作上,學習上,在顏值上,身體上,體重上都是覺得自己不能接受,所以都是要去健身、要去學各種班,去學習社交禮儀,去講話。所以說人設,就是覺得本來的自己不好,需要重新設計一個人。
小鎮做題家的陌生感,反映了社會生活“透明不透氣”的特徵。他們生活的透明性體現在,他們的成長軌跡和成績,符合體系規定的標準和預期,被毫無懸念地認可。他們體會到的不透氣,體現在他們無法從容地呈現個人的掙扎、猶豫和苦惱。他們獲得了“認可”,欠缺的是“認得”。認可是系統根據既定的標準,評價一個人的成果,決定給與獎勵還是懲罰。認得,則是一個主體對另外一個主體的理解,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情緒、考慮、掙扎和歷史的看見,它不涉及考驗、判斷和獎懲。
認可是單向的,是系統對個體的判斷,追求認可的個體無法對系統產生影響。而認得是雙向的。認得必須通過雙向的交流而實現;認得給人們帶來的尊嚴感,不來自表揚和獎勵,而來自交流過程的真誠性。認得的雙向意味著,如果我們不認得別人,我們也不能夠感知到別人對我們的認得。這也意味著,我們對自身價值的確認,不只來自於別人對我們的認得,其實也來自我們對別人的認得。這是因為,在認得別人的時候,我們要把自己打開,要在喚起自己的經歷和情緒的過程中去認得別人。這裡認得的“得”,不僅是對別人的新的理解,也是自己對自己會有新的心得。我們對別人的認得、別人對我們的認得、我們對自己的認得,是渾然一體的。一個人如果只有光鮮透明的成績,而沒有可以述說的經歷,那他(她)不能被認得,也很難認得別人。而且,在長年的追求認可中,自己變成自己要動員和控制的對象,要壓抑自己的各種和學業無關的衝動,自己不再認得自己的自然感受,自己成為自己的陌生人。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認可取代了認得,更嚴重的是,認可成為了認得的基礎。“愛是有條件的”——你要證明你值得愛,愛才存在——是不少年輕人從小感到生活沉重的重要原因。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缺乏愛,但是家庭、學校和社會灌輸的愛的“條件感”讓滋養變成了負擔。而獲得愛和認得的條件,就是要先獲得認可。很多人之所以要犧牲這麼多時間和精力來追求認可,正是因為這是他們獲得認得的基礎——通過證明我是正常的、成功的,以獲得關注、理解和愛。網名為KK的朋友(26歲,大學畢業後在公務部門工作,最近辭職)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道,我們從小浸淫在一種緊繃的氛圍裡。在親情中,要償還父母的犧牲;在學業或事業中,要把別人擠下去;在婚姻中,要維持伴侶心中的理想形象。似乎每種社會關係都有一套要求,無法達到標準的人,就會失去被傾聽與被愛的資格。”在我們的線上交流中,他提到了吳謝宇的案子:“從農村到北大,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他。他沒有別的可以抓住的東西,他自己的上進心、自己努力學習、證明自己,是唯一可以生存的理由。他母親是證明的對象。他的生命被這樣的證明耗盡,殺死母親是他的終結(無止境的追求認可和認得)。”當認可成為認得的基礎,親情可以變得額外沉重。吳謝宇也許是默爾索的鏡中像。默爾索疏離了他的母親(“我母親在今天去世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是我們聽到默爾索的第一句話),拒絕社會對他的判斷,認為人的存在毫無意義。默爾索在疏離和抵制社會關係的過程中陌生化。吳謝宇依附于母親、依附于社會、不斷得到認可,他在追求認可和獲得認可的過程中陌生化。吳謝宇,是我們這個時代悲劇性的陌生人。
………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