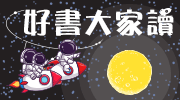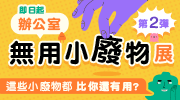商品簡介
張歷君橫跨二十年文學評論選集
王德威:「張歷君是當代中文及比較文學界最獨特的聲音之一。」
王德威、黃子平 專文作序
李歐梵、李維怡、郭詩詠、楊佳嫻、潘國靈、謝曉虹、鄺可怡 共同推薦
本書乃作者二十年(2002-2023)來的文學評論選集,涵蓋香港文學、二十世紀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等三個領域的評論文章。香港文學部份既包括關於香港文學的外邊思維和香港魯迅閱讀史等議題的討論,亦網羅有關香港不同輩代作家如西西、馬覺和李智良的作品分析;世界文學部份主要探討歐陸現代派作家波德萊爾、卡夫卡和巴塔耶作品的文學理論意涵;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的部份則嘗試將華文作家、思想家和戲劇家如路翎、張東蓀和梅蘭芳等,重新置放在跨文化和跨媒體的視野中進行再解讀,借此展示華文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緊密聯繫和同步性。
本書作者立足香港,致力溝通連結二十世紀華文文學與世界文學。他多年來一直透過各個不同層面的文學評論實踐,探究「香港作為方法」這一命題在理論和方法上的意義,亦即隱含於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學批評中的「外邊思維」和「視差視野」。這種「香港作為方法」的批評視野貫串全書,構成這本文學評論選集的主要特色。
作者簡介
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研究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客座助理教授,亦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現代中文學刊》通訊編委、《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學術編輯以及《字花》雜誌編委。他曾為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2009-2010)、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訪問學人(2019-2020)。代表作為專書《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獲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文學評論組)推薦?(2022)。
名人/編輯推薦
名家推薦:
張歷君是當代中文及比較文學界最獨特的聲音之一。2020年出版的《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研究瞿秋白多重跨文化因緣,廣受好評,新作《文學的外邊》更顯現他獨特的治學方法與開闊的思路。這本評論集選錄他歷年的文論書評,涵蓋的對象從魯迅、路翎到西西、李智良;從波德萊爾到普魯斯特、卡夫卡;從梅蘭芳與艾森斯坦和特列季亞科夫的莫斯科會面,到張東蓀與克里斯特瓦的跨時代想像對話。理論方面更是旁徵博引,現當代西方大家如班雅明、巴塔耶、什克洛夫斯基、阿甘本、德勒茲、傅科……,無不盡入眼下。
——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這是一本思想深厚的跨文化研究論文集,作者張歷君以香港為基地,放眼世界,廣徵博引當代文化理論,並特別突出香港的關鍵地位,藉此營造「香港作為方法」的多面向論述,讀後令我獲益良多。
我個人覺得最受啟發的是書中幾篇對波德萊爾、本雅明、卡夫卡、布萊希特和魯迅等世界名家作品的嶄新闡釋,往往有發人所未發的洞見。作者非但遊走於各家各派的理論,更能將之「重新連結」(re-connection),因而展示出發人所未發的洞見,值得在此向讀者極力推薦。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間」這個概念的引入,正足以為張歷君的書名《文學的外邊》作詮。和辻哲郎在《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人間の学としての倫理学》1934 年初版)中曾展開他有關「人間」和「世間」的思考。[……]張歷君指出,當王德威用海德格爾式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來討論文學史,其「動詞進行時」的「世界」(worlding),正可以參考和辻哲郎不斷「間」著的「人(世)間」來理解。
而張歷君傑出的工作,正在於藉由極多的個案,來展示「人(世)間」不斷流轉、流變、生成的思想和生命吧。
——黃子平(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
二十年後的回頭凝視,宛如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筆下奧菲斯攜七弦琴縱深走向地獄的歷程:她作為夜的中心、一種經驗的幽微,作品完成的一刻隨即消失殆盡,只有背向轉身才得以靠近。張歷君致力通過「外在」、「外邊」、「視差」的研讀方法,不僅尋找二十世紀香港、華文與歐洲文學對話摺疊的反思空間,當中也隱含著他敏銳而不安地感受到的時代顫動與危機。在張歷君的冷靜凝視裡,閃現葉靈鳳與柄谷行人、梅蘭芳與特列季亞科夫、張東蓀與克里斯蒂娃、路翎和羅曼.羅蘭等世代交錯的身影,跨地域跨文化的歷史偶然,一再令人瞠目結舌。本書念茲在茲的仍是我城,在全球語境下對香港「自身」的思考位置及轉化力量的再發現。
——鄺可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目次
推薦序:無法言明的共同體/王德威
推薦序:人(世)間流轉的知識與生命/黃子平
語言的外在與視差的反思: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學批評的外邊思維
魯迅「內面」之發現:華語世界與「世間」的中國文學
生活在他方--馬覺的詩歌生命及其時代
布萊希特抑或什克洛夫斯基?──論西西〈肥土鎮灰闌記〉中的雙重視角
非母語寫作與生成女人:論李智良的「陰性書寫」
路翎的「落後書寫」:讀宋玉雯的《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
歷史十字路口上的見證: 梅蘭芳、特列季亞科夫與愛森斯坦
文本互涉與相關律名學:論克里斯蒂娃對張東蓀知識論的接受
迷狂與開悟:論巴塔耶與鈴木大拙的關係
憂鬱的都會:閱讀本雅明的波德萊爾研究
無望的訴訟:論卡夫卡的法律書寫
換取的孩子:卡夫卡與猶太德語文學
附錄:波德萊爾與我們--與楊振教授筆談
後記:香港作為方法
書摘/試閱
布萊希特抑或什克洛夫斯基?
──論西西〈肥土鎮灰闌記〉中的雙重視角
1986年底,正值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逝世三十周年,而香港的布萊希特熱也達至高潮。該年12月9日,「第七屆國際布萊希特研討會」和「國際布萊希特戲劇節」,均在香港隆重揭幕。其中,由市政局、香港藝術中心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的「國際布萊希特戲劇節」,邀請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與陳顒導演,來港演出布萊希特的名作《高加索灰闌記》(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同年同月,西西寫成了她的〈肥土鎮灰闌記〉。雖然根據已出版的文字資料,我們無法證明這次演出與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有任何關係,但有趣的是,在〈肥土鎮灰闌記〉中,布萊希特的影子卻無處不在。
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大體是對李行道的元雜劇《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的改編。正如黃子平所言,「情節乃至台詞其實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戲還照著,『古時候』那樣,有板有眼地演著。」整篇小說並沒有納入布萊希特版本的《灰闌記》的任何情節內容。事實上,在西西這篇小說的字句中,我們所能找到的與布萊希特相關的痕跡,便只有篇末的這幾個無關痛癢的句子:「這麼多的人來看戲,到底想看甚麼?看穿關、看臉譜、看走場、看佈局的結與解,看古劇、看史詩、看敘事、看辯證;還是,看我……?」可以說,在〈肥土鎮灰闌記〉中,布萊希特基本上是缺席者。何以我們會說,在〈肥土鎮灰闌記〉中,布萊希特的影子無處不在呢?答案很簡單,因為在改編《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時,西西所借重的手法不是別的,恰恰是布萊希特的敘述體戲劇(episches Theater)模式。如果說,在內容的層面上,布萊希特是〈肥土鎮灰闌記〉故事裡的缺席者,那麼,在形式的層面上,他便是無處不在的幽靈了。
為要深入疏理〈肥土鎮灰闌記〉與布萊希特戲劇理論之間的關係,本文嘗試借助帕維(Patrice Pavis)在〈關於舞台的翻譯問題〉(Problems of Translation for the Stage)一文中闡述的劇場翻譯(theatre translation)理論,對〈肥土鎮灰闌記〉作細緻的釋讀。
第一重視角:布萊希特的敘述體戲劇模式
正如帕維所指出的,一個有待翻譯的文本的真實境況,實際上是一次本源(source)和譯體(target)的發言狀況(situation of enunciation)之間的交易(transaction),而翻譯則是以譯體的眼睛凝望本源的過程。如果說,西西在〈肥土鎮灰闌記〉中以其譯體的眼睛凝望了《包待制智勘灰闌記》這一本源,那麼,西西的這雙眼睛便是一對擁有雙重透視點的眼睛:一方面,西西以布萊希特敘述體戲劇的眼睛重組了《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另方面,在應用布萊希特的敘述體戲劇模式時,西西則以其形式主義(Formalism)的視角重寫了敘述體戲劇模式。而這也是本文題目中所提及的「雙重視角」,下面我們將首先處理第一個方面,即西西對敘述體戲劇模式的應用。
〈肥土鎮灰闌記〉開篇的句子是這樣的:「肥土鎮藝術中心劇院正在敷演《灰闌記》。你可聽見鼓板鑼砵的喧聲?」而整篇小說實際上也是一次虛構的、布萊希特式的《灰闌記》表演過程。因此,若要精細地辨識布萊希特表演體系在小說中每一個細節中的展現,我們便得借用帕維在討論劇場翻譯時所構想的分析工具和概念。
帕維在〈關於舞台的翻譯問題〉中,以T0到T4五個符號重組劇場翻譯的整個過程:
1. T0:作者寫作的戲劇故事;
2. T1:劇作家對劇本所作的宏觀文本的翻譯(macrotextual translation),亦即依據劇場行動的邏輯,重組劇本的情節和藝術的整體性;
3. T2:依據劇場空間的實際情況,導演對劇本所作的劇作分析;
4. T3:在舞台上對文本作實際測試;
5. T4:觀眾對劇作的接受和詮釋。
以帕維的觀點看來,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闌記》顯然是這個劇場翻譯過程中的T0階段,是有待翻譯的原作,至於西西在小說中對《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劇情、時空架構和角色關係的重組則處於T1和T2的階段。在討論T1的宏觀文本翻譯時,帕維羅列了一組在這一階段中被重新組織的文本元素,其中包括角色的系統、中介者(the agents)在其中開展作者的意識形態觀點的時間和空間、文本所呈現的時段、每個角色的個別特性、以及作者的超越於局部片斷之上的特性等元素。從這一層面入手分析,我們可以釋讀出西西如何在戲劇結構上採納敘述體戲劇的模式。
1935年,布萊希特在莫斯科觀看了梅蘭芳的演出。觀演後不久,他便於1936年寫成〈中國戲劇表演藝術中的陌生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s in Chinese Acting)一文,詳細闡述了他對戲曲表演方法的觀感。在這篇文章的第一段,他便開宗明義,清楚點明文章的主旨:「在這篇文章裡簡短地論述一下中國古典戲劇中的陌生化效果的運用。……這種嘗試就是要在表演的時候,防止觀眾與劇中的人物在感情上完全融合為一。」換言之,對於布萊希特來說,中國戲曲表演方法的特別之處,乃在於其所產生的陌生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s),還有其對於感情共鳴(empathy)效果的抵制。但他這種對中國戲曲表演的理論,卻引來論者的反駁。譬如,陸潤棠便曾在〈西方現代戲劇中之中國戲曲技巧〉一文中談及這一問題:
他(引者按:指布萊希特)指出中國戲曲中的演員能經常保持自己和角色和觀眾的距離、故有疏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s)云云。但這種疏離演出是否能經常在傳統的中國戲曲演出和觀眾觀賞習慣的關係中產生觀眾知性的疏離認受性,則來有深究,他只想當然這種觀眾疏離感會發生。事實則剛相反。無論中國傳統戲曲演出是如何的虛擬化,非幻覺真實化或甚至誇張化,中國傳統戲曲的觀眾仍會真情的和以戲如人生代入。疏離效果只是表面程度,實質上不能將這種演出說成絕對性的疏離。
陸氏並在文中就音樂、舞台調度和演員演出等不同方面,闡述了中國戲曲中的幻覺化效果。對於這一問題,西西亦持相類看法。在一次與何福仁的對談中,她談到了布萊希特式戲劇與亞洲傳統戲劇的分別:
何:「陌生化效果」是「中止懷疑」的另一面,他(引者按:指布萊希特)要破除觀眾的迷信,要觀眾「中止相信」。不過懷疑與相信,是辯證地互相依存的。陌生化並不一面倒排斥共鳴,相反,它建立在共鳴之上。
西:入而能出。觀眾不入戲的話,則始終只是陌生人,漠不關心。這也是新舊陌生化的區別,……亞洲的傳統戲劇,也運用諸如音樂、啞劇等陌生化手法,其結果卻是令觀眾無法入戲,是出而不入;太隔了,觀眾無法介入,只是旁觀遙遠的物事。何況,這種陌生化,仍然是建立在幻覺的基礎上。(引者按:著重號乃引者所加)
正是依據這一「入而能出」的原則,西西以布萊希特式的陌生化手法重寫了《包待制智勘灰闌記》。
余匡復在討論亞里士多德式(Aristotelian)的戲劇性戲劇和布萊希特式的敘述體戲劇的分別時指出:戲劇性戲劇有一個貫串於全劇的中心戲劇事件,戲劇必須圍繞這一中心戲劇事件分幕分場,結構上必須按序幕→情節上升→高潮→情節下降→結局,循序漸進,直線進行,一環扣一環,一場扣一場;至於敘述體戲劇則不分幕,只分場,採用場與場之間關係鬆散的結構(所謂Lockere Bilderfolge),目的是不用動人的戲劇性情節使觀眾迷醉於感情。如此一來,便沒有貫串全劇的「戲劇性情節曲線」,一場一場猶如拉洋片,一場敘述一件事,沒有全劇性的戲劇高潮。依據這一劃分標準,《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便是一齣戲劇性戲劇。整齣戲包括楔子和四折戲,共五幕。從張海棠嫁給馬均卿始,到灰闌斷案止,其間幕幕緊扣,均圍繞同一個中心戲劇事件層層遞進。至於〈肥土鎮灰闌記〉,我們則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暸解其布萊希特式的改編手法:
首先,就故事時段的開展而言,原本《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從張海棠嫁給馬均卿始,到灰闌斷案止,故事以直線前進的方式囊括了所有事件發生的時段,而〈肥土鎮灰闌記〉則把整個故事時段壓縮進包拯審案一幕中,故事的來龍去脈則透過證人和犯人的供詞以及灰闌中的小孩的內心獨白來交代。這樣,戲劇的情節被打散,戲劇的高潮亦無法營造出來。
其次,因著這一故事時段的改變,戲劇中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系統亦隨之改變。譬如,在《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中,證人如劉四嬸和張大嫂某些供詞是在鄭州衙門向趙令史說出的,但在〈肥土鎮灰闌記〉中卻改編成向包拯所作的供詞。再如,在《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中,劉婆婆和馬均卿在第一折便已安排死去,此後再沒出場,但在〈肥土鎮灰闌記〉中,他/她們卻被包拯以招魂的方式請到大殿上作供。又如,在《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中,鄭州太守蘇順並沒有在包拯面前接受審問,但在〈肥土鎮灰闌記〉中,他卻被安排向包拯作供。可見隨著故事時段的改變,戲劇中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亦相應出現了大幅度的調整。
此外,由於引入了敘述體戲劇的模式,《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原本單一敘述層和直線行進的時空模式,被雙層敘述和斷片式的時間結構所代替。正如黃子平所指出的,兩個敘述層面交錯著展開,一是原有的人物對白,在舞台上發聲呈現,用的仍是元雜劇的文體語言;另一個卻是五歲小孩馬壽郎的內心獨白,一如電影裡的畫外音,迭加於古久的對白之上,不免摻雜了好些(西西本人的)現代語言進去,諸如「婚姻,是唯一的出路」之類。也正是在這一雙層敘述的安排中,西西運用了她所說的布萊希特式的「入而能出」的手法:一方面,在情節的安排上,〈肥土鎮灰闌記〉雖然打破了《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直線行進式的劇情安排,但〈肥土鎮灰闌記〉所採用的案件審訊的情節鋪展框架卻以偵探小說式的佈局,產生了「懸念」的效果,首先讓讀者/觀眾投入於故事之中;但另方面,在證人每次作供之後,卻又安排插入馬壽郎的「畫外音」,既進一步提供故事細節的來龍去脈,但更重要的卻是打破讀者/觀眾與故事人物之間的感情共鳴,產生出疏離的效果,讓讀者/觀眾能夠理智地分析舞台上所發生的一切。
至於角色的特性方面的改變,則主要集中在馬壽郎一角上。在《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中,馬壽郎只有一句對白:「這個是我親娘,你是我奶子。」但在〈肥土鎮灰闌記〉中,馬壽郎成了旁觀的評論者,其內心獨白幾乎佔整篇小說的一半篇幅。此外,馬壽郎更從一個被描述成不懂思考的小孩,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極度理智的評論者。到了篇末,他甚至打算開腔,提出自己「選擇的權利」。說到這裡,談及馬壽郎這個角色的問題,我們的分析已經進入帕維所謂的T3的層面,亦即在舞台上對文本作實際測試。
在分析〈肥土鎮灰闌記〉時,我們應該緊記,這篇小說是對一次虛構演出的整體描述。如此一來,我們便不會驚訝於馬壽郎的理智以及他獨白中所摻雜的(西西本人的)現代語言。因為〈肥土鎮灰闌記〉中的馬壽郎不單是劇本中的角色,他更是一個在實際演出中的布萊希特式演員。在馬壽郎的內心獨白中,我們至少可以聽到兩重聲音的相互交織。有關馬壽郎的多重身份問題,黃子平便曾分析道:
他(引者按:指馬壽郎)至少,有三重身份:首先是故事裡的那個馬壽郎,一切都有他在場親歷親見;其次則是舞台邊上正在扮演「馬壽郎」的馬壽郎……,我們經由他的耳目聽到對白看到劇情;再次,便是由西西「質詢」武裝起來的五歲小孩,見多識廣,心明眼亮,莫說大娘、趙令史、蘇模棱、董超、薛霸等一班惡人瞞不過他,就連裝神弄鬼的包待制,他也有一肚子的「腹誹」。
黃子平的這一劃分,依據的是敘述學的分析框架。若以敘述體戲劇的模式重加劃分,我們可以把第二和第三個身份劃歸為,西西所塑造的布萊希特式演員的兩個不同面向;而第一個身份,則是劇本中的角色:馬壽郎。
事實上,演員「馬壽郎」對於他自身的演員身份也是有其自覺的,在他的內心獨白中,我們可以找到這幾句:「舞台上演出的是《灰闌記》,上演之前,演員們還在爭佔排名位置,彷彿這也是戲劇的一部份,結果以出場為序。奇怪的是,我出場最多,排名卻在最末尾,是因為,我並不是來演戲的麼?雖然和這麼多的演員站在一起,我是身在劇場的外角。」布萊希特在談及自己對敘述體戲劇的演員的要求時指出:演員在舞台上有雙重身份,既是勞頓(Laughton),又是伽利略(Galileo),表演著的勞頓並沒有在被表演著的伽利略中消失。換言之,演員一刻也不可徹底轉化為角色。「他不是在演李爾(Lear),他就是李爾」,這種評價對演員說來是致命的。因為演員僅只要去表現他的角色,而非全然投入認同他的角色。參照布萊希特這一解釋,我們可以說,〈肥土鎮灰闌記〉中的馬壽郎充份展現了一個布萊希特式演員的複雜性。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說,〈肥土鎮灰闌記〉的世界全然是一個布萊希特式的世界?西西是否完全採納了布萊希特的觀點?
(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