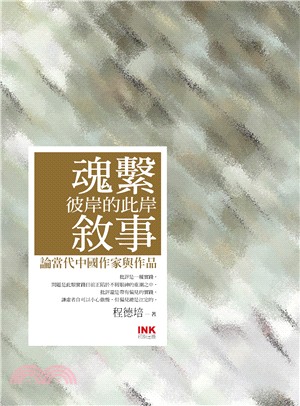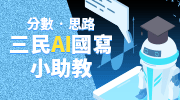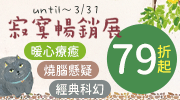定價
:NT$ 420 元優惠價
:
90 折 378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1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中國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程德培
如同小說是無法說出真情的一樣,批評何謂也是永遠說不清的。
真理比小說更奇怪,生活比小說更加超現實,而批評呢?
處於小說和理論的中間,生於創作和文學史的夾縫中。
批評是一種實踐,問題是此類實踐目前正陷於不屑眼神的重圍之中,批評還是帶有偏見的實踐,謙虛者自可以小心傲慢,但偏見總是注定的。這也是為什麼伽達默爾寫道:「一切釋義都是一邊倒的。」羅蘭‧巴特在辯論中說,沒有釋義是「單純的」。含義的語境是批評家的必需,也是其產生偏見的根源。在語境之中獲得,也在語境之中失去,這大概是批評家的宿命。
本書以作家論、作品論及對談錄三部分呈現,以作者程德培其獨特的觀點及筆觸細膩中肯地評析中國當代知名作家及其作品,其作家包括遲子建、劉恆、呂志清、方方、張旻、葛水平、須一瓜、孫甘露、魯敏、金仁順、戴來、楊少衡、鐵凝、劉震雲、王安憶、盛可以、吳玄、葉彌、陳善壎、麥家、韓少功等二十多位作家;引領讀者進入作者所創造的瑰麗、夢幻、暗黑的多重世界。程德培並以對談方式與張新穎、白亮、陳村及吳亮探討當代文學的問題、新時期文學評論,以及80年代文學作品的變遷、差異與批評。
本書探討的重點作家及作品蒐羅廣泛,是程德培三十餘年來對文學的關注、閱讀、思考的結晶,而於這幾年所寫下的文字。以程德培專業的視角評論當代中國作家及作品,深入剖析作者及其作品背後所欲表達的潛在思想及心理活動,引領讀者進入作者所創造的異想世界。
—節錄〈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論遲子建的小說〉
如果說在小說創作中存在著敘事體能的話,遲子建無疑將進入中國當代小說最為出色的行列。無論長、中、短各項,她都能從容應對,始終保持著敘事的活力。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平均每年兩部中篇、若干短篇,自一九九一年出版長篇小說《茫茫前程》以來,幾乎每三年有一部長篇問世。……
在雨中想起了〔老師〕講給我們的一個童話故事。他說有一個音樂家窮困潦倒,他創作的所有作品都不被時代所重視。當他的呼吸將要停止的時候,他的滿頭白髮忽然像琴弦一樣直直地豎起來,一縷陽光猶如一雙纖巧修長柔韌的女人的手指一樣,在那上面彈奏出他的最後作品。他的作品使窗外春色萌發,音樂家終於在他自己創作的音樂中沉醉離去。
這是遲子建作品中無數個傳說和童話中的一個。它既是童話故事又傳達出一個關於藝術的信念。藝術即生命的燃燒,猶如在「逝川」邊上生活了一輩子的吉喜,儘管牙齒可怕地脫落,頭髮稀疏而斑白,嗓音嘶啞喘著粗氣,用盡最後的力氣將一條條豐滿的淚魚放回逝川。這種類似放河燈的結尾在遲子建的作品中屢屢出現,表現了生命不息的傳承。遲子建相信「生命是有去處的」,這既是輪迴也是一種傳遞。
於是,在遲子建的世界中,生命是無處不在的,不管是記掛著夢想與童話的「北極村」,還是「感受最多的鋪天蓋地的雪,連綿不斷的秋雨以及春日時長久的泥濘,當然還有森林、莊稼、牲靈等」。感覺上遲子建那童年的世界離我們非常遠,恰如它具體的地理位置;記憶中的故鄉、傳說和故事又都是那麼美好,猶如夢中的田園詩一般。……
如同小說是無法說出真情的一樣,批評何謂也是永遠說不清的。
真理比小說更奇怪,生活比小說更加超現實,而批評呢?
處於小說和理論的中間,生於創作和文學史的夾縫中。
批評是一種實踐,問題是此類實踐目前正陷於不屑眼神的重圍之中,批評還是帶有偏見的實踐,謙虛者自可以小心傲慢,但偏見總是注定的。這也是為什麼伽達默爾寫道:「一切釋義都是一邊倒的。」羅蘭‧巴特在辯論中說,沒有釋義是「單純的」。含義的語境是批評家的必需,也是其產生偏見的根源。在語境之中獲得,也在語境之中失去,這大概是批評家的宿命。
本書以作家論、作品論及對談錄三部分呈現,以作者程德培其獨特的觀點及筆觸細膩中肯地評析中國當代知名作家及其作品,其作家包括遲子建、劉恆、呂志清、方方、張旻、葛水平、須一瓜、孫甘露、魯敏、金仁順、戴來、楊少衡、鐵凝、劉震雲、王安憶、盛可以、吳玄、葉彌、陳善壎、麥家、韓少功等二十多位作家;引領讀者進入作者所創造的瑰麗、夢幻、暗黑的多重世界。程德培並以對談方式與張新穎、白亮、陳村及吳亮探討當代文學的問題、新時期文學評論,以及80年代文學作品的變遷、差異與批評。
本書探討的重點作家及作品蒐羅廣泛,是程德培三十餘年來對文學的關注、閱讀、思考的結晶,而於這幾年所寫下的文字。以程德培專業的視角評論當代中國作家及作品,深入剖析作者及其作品背後所欲表達的潛在思想及心理活動,引領讀者進入作者所創造的異想世界。
—節錄〈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論遲子建的小說〉
如果說在小說創作中存在著敘事體能的話,遲子建無疑將進入中國當代小說最為出色的行列。無論長、中、短各項,她都能從容應對,始終保持著敘事的活力。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平均每年兩部中篇、若干短篇,自一九九一年出版長篇小說《茫茫前程》以來,幾乎每三年有一部長篇問世。……
在雨中想起了〔老師〕講給我們的一個童話故事。他說有一個音樂家窮困潦倒,他創作的所有作品都不被時代所重視。當他的呼吸將要停止的時候,他的滿頭白髮忽然像琴弦一樣直直地豎起來,一縷陽光猶如一雙纖巧修長柔韌的女人的手指一樣,在那上面彈奏出他的最後作品。他的作品使窗外春色萌發,音樂家終於在他自己創作的音樂中沉醉離去。
這是遲子建作品中無數個傳說和童話中的一個。它既是童話故事又傳達出一個關於藝術的信念。藝術即生命的燃燒,猶如在「逝川」邊上生活了一輩子的吉喜,儘管牙齒可怕地脫落,頭髮稀疏而斑白,嗓音嘶啞喘著粗氣,用盡最後的力氣將一條條豐滿的淚魚放回逝川。這種類似放河燈的結尾在遲子建的作品中屢屢出現,表現了生命不息的傳承。遲子建相信「生命是有去處的」,這既是輪迴也是一種傳遞。
於是,在遲子建的世界中,生命是無處不在的,不管是記掛著夢想與童話的「北極村」,還是「感受最多的鋪天蓋地的雪,連綿不斷的秋雨以及春日時長久的泥濘,當然還有森林、莊稼、牲靈等」。感覺上遲子建那童年的世界離我們非常遠,恰如它具體的地理位置;記憶中的故鄉、傳說和故事又都是那麼美好,猶如夢中的田園詩一般。……
作者簡介
程德培
1951年生於上海,廣東中山人。
自1978年始從事文學評論和研究工作,發表論文及批評文字200萬字。著有《小說家的世界》、《小說本體思考錄》、《三十三位小說家》、《當代小說藝術論》,編選並評述《探索小說集》、《新小說在1985》《新聞小說’86》等。
曾獲首屆、第二屆「上海文學評論獎」,第一屆「上海市文學作品獎」,首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表彰獎」,第三屆《作家》獎等。
1951年生於上海,廣東中山人。
自1978年始從事文學評論和研究工作,發表論文及批評文字200萬字。著有《小說家的世界》、《小說本體思考錄》、《三十三位小說家》、《當代小說藝術論》,編選並評述《探索小說集》、《新小說在1985》《新聞小說’86》等。
曾獲首屆、第二屆「上海文學評論獎」,第一屆「上海市文學作品獎」,首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表彰獎」,第三屆《作家》獎等。
目次
作家論
一、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論遲子建的小說
二、地獄與天堂背後的多副面孔——對劉恆二十年前舊文本的新閱讀
三、難以言說的言說——二○○九年的呂志清小說
四、方的就是方的——論方方小說的敘事鋒芒
五、冒犯的悖論——關於張旻小說的文本脈絡
六、當敘事遭遇詩——葛水平小說長短論
七、正視斜視審視凝視——須一瓜的敘事之鏡
八、對白天來說,黑夜很可能是它的一束光照——由孫甘露引發對先鋒小說的思考
九、距離與欲望的「關係學」——魯敏小說的敘事支柱
十、甜蜜的「懷疑論者」——金仁順的七個短篇
十一、「熟悉」與「陌生」的對峙——戴來的三個短篇及其他
十二、置身波瀾不驚的詭祕心跡——評楊少衡小說的講述策略
十三、「鏡子」裡外都是「鏡子」——鐵凝小說論
作品論
一、我們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評劉震雲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
二、消費主義的流放之地——評王安憶近作《月色撩人》及其他
三、一個「亂」字竟如此了得——評盛可以小說《道德頌》
四、陌生人的鏡子哲學——讀吳玄長篇小說《陌生人》
五、「水邊的兩塊石頭」——讀葉彌短篇小說《「崔記」火車》
六、夢幻與現實——讀陳善壎短篇小說《大老闆阿其》
七、記憶是一種忘記的形式——讀麥家短篇小說《漢泉耶穌》
八、風度的含義——讀鐵凝短篇小說《風度》
九、隱喻之旅——讀楊少衡短篇小說《輪盤賭》
十、「偏執」的藝術——讀韓少功短篇小說《生氣》
十一、《也許》的也許——讀盛可以短篇小說《也許》
十二、讀後ABCD——《上海文學》小說讀札一至六
談話錄
一、當代文學的問題在哪裡/程德培、張新穎
二、記憶‧閱讀‧方法/程德培‧白亮——程德培與新時期文學批評
三、八○年代:文學‧歲月‧人/程德培、吳亮、陳村
四、八○年代:歲月‧作品‧變遷/程德培、吳亮、陳村
五、八○年代:差異‧批評‧碎片/程德培、吳亮、陳村
後記
一、魂繫彼岸的此岸敘事——論遲子建的小說
二、地獄與天堂背後的多副面孔——對劉恆二十年前舊文本的新閱讀
三、難以言說的言說——二○○九年的呂志清小說
四、方的就是方的——論方方小說的敘事鋒芒
五、冒犯的悖論——關於張旻小說的文本脈絡
六、當敘事遭遇詩——葛水平小說長短論
七、正視斜視審視凝視——須一瓜的敘事之鏡
八、對白天來說,黑夜很可能是它的一束光照——由孫甘露引發對先鋒小說的思考
九、距離與欲望的「關係學」——魯敏小說的敘事支柱
十、甜蜜的「懷疑論者」——金仁順的七個短篇
十一、「熟悉」與「陌生」的對峙——戴來的三個短篇及其他
十二、置身波瀾不驚的詭祕心跡——評楊少衡小說的講述策略
十三、「鏡子」裡外都是「鏡子」——鐵凝小說論
作品論
一、我們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評劉震雲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
二、消費主義的流放之地——評王安憶近作《月色撩人》及其他
三、一個「亂」字竟如此了得——評盛可以小說《道德頌》
四、陌生人的鏡子哲學——讀吳玄長篇小說《陌生人》
五、「水邊的兩塊石頭」——讀葉彌短篇小說《「崔記」火車》
六、夢幻與現實——讀陳善壎短篇小說《大老闆阿其》
七、記憶是一種忘記的形式——讀麥家短篇小說《漢泉耶穌》
八、風度的含義——讀鐵凝短篇小說《風度》
九、隱喻之旅——讀楊少衡短篇小說《輪盤賭》
十、「偏執」的藝術——讀韓少功短篇小說《生氣》
十一、《也許》的也許——讀盛可以短篇小說《也許》
十二、讀後ABCD——《上海文學》小說讀札一至六
談話錄
一、當代文學的問題在哪裡/程德培、張新穎
二、記憶‧閱讀‧方法/程德培‧白亮——程德培與新時期文學批評
三、八○年代:文學‧歲月‧人/程德培、吳亮、陳村
四、八○年代:歲月‧作品‧變遷/程德培、吳亮、陳村
五、八○年代:差異‧批評‧碎片/程德培、吳亮、陳村
後記
書摘/試閱
難以言說的言說─二○○九年的呂志清小說
不清楚批評業的專家學者是如何評說呂志清的小說。
是無法認同還是不屑一顧,是無法言說還是無需言說?問了一些熟悉行情的朋友,依然是不甚了了。
二○○九年的《鍾山》雜誌試圖打破僵局,不僅一年之中兩次頭條發表呂志清的小說,而且執行主編賈夢瑋親自執行並請人操刀,連續在《小說評論》上發表推薦文章。
今年,呂志清總共發表三個中篇,除了《鍾山》上的以外,還有就是發表在《山花》上的《蛇蹤》。
粗略地統計一下,這些年發表呂志清小說最勤快的,非《山花》雜誌莫屬。
即便如此,在評價上依然是沉默。
文章寫完時,見到《山花》雜誌二○○九年十二期上發表的饒向陽的評論文章:《哲性的拷問與詩性的解答─呂志清創作瑣論》。
也不清楚有多少人閱讀或喜歡閱讀呂志清的小說,我的估計不會太多。
如同呂志清本人也不怎麼閱讀中國小說一樣,都是一種拒絕對方的不期而遇。
呂志清曾在一篇關於《老五》的創作談中說:「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基本不太看中國的當代作品。
」(見《中篇小說選刊》二○○七年第六期)
這樣一種作品與閱讀、小說與批評間不明不白的關係,很像今年呂志清小說的所有開頭:
禹斌覺得,他和章彥的關係似乎一直都有點古怪:同學不像同學,戀人不像戀人。
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他似乎一直也沒怎麼明白。
─《一九三七年的情節劇》
小馮和小奚屬於那種「閃婚」族,與小布希和蘿拉的情況一樣,相識三個月就結了婚。
─《蛇蹤》
何莉莉每週有三個晚上去臧醫生那裡。
週一、週三、週五。
何莉莉下了班就直接去臧醫生家。
現在,何莉莉仍然管臧醫生叫臧醫生,但他們之間已不再是心理醫生和救助者的關係了,而是一種新型的關係…… ─《黑暗中的帽子》
三部小說三個開頭:設問、肯定、陳述中的轉變,講的都是人與人的關係。
問題在於,人與人的關係是無處不在的東西,並不只是在我們探討它的時候才會存在。
當呂志清以其假定的敘事方式探討這樣或那樣的關係時,究竟是拒絕了無處不在的直觀世界,還是進入了一種與直觀世界相類似的無限的不確定性之中?批評作為探討的探討很容易地進入了無法言說,難以抉擇的困境之中。
認同是進入角色的方式,而關於認同的認同很可能也是退出角色的方式。
我們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混合性的角色,這些角色表面上能滿足我們的認知欲望,實則與我們的認知欲望相對立。
需要認清的是,生活很可能不再是身體力行的運動場所,更多形態的日常生活往往發生在翻閱報刊雜誌打開電視之際,在電腦前隨意瀏覽、和陌生人隨意聊天之中。
當我們竭力地去獲取這個世界的有關信息,而作為信息的世界已經順利誕生了。
只要你有思辨的頭腦,只要你有發問的能力,而想像呢,很可能是尾隨其後的東西。
激進的現代派曾試圖抹平藝術和生活的差別。
現在看來,生活為他們做到了這一點。
讀呂志清的小說,我們彷彿坐落於書齋之中,沉陷於思辨的困境,同時又沉迷於一套獨特而富有魅力的敘事圈套,難以自拔。
這些符號化的世界很明確是內心和隱喻性的,但也被表現為具有頑強的物質性─那空洞而又無處不在的「關係」。
我的身分處於別人的保管之中,儘管這個別人是由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欲望組成,儘管這種保管永遠不會安全。
我的自我監護人正是他人,正如梅洛龐蒂所說的「我從他人那裡借來了我自己」(〔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符號》,商務印書館二○○三年九月版)。
1
《黑暗中的帽子》圍繞著心理醫生與不同患者之間演繹其敘事。
所謂黑暗,與恐懼有關;所謂帽子,與控制有關。
何莉莉婚後與丈夫小魯無法交流,從言語無法交流發展到肢體衝突,暴力生活前,何莉莉心生恐懼,頗似受虐狂。
「什麼是恐懼症呢?害怕不該害怕的,或者,對不存在的恐懼感到恐懼。
」何莉莉的疑似恐懼症在臧醫生處得到這樣的解答。
我們需要顧及自己,部分原因就是恐懼。
而來自於別人信任的這種信任,則是我們能戰勝恐懼的希望。
對何莉莉而言,是真實的恐懼還是疑似的恐懼症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她與臧醫生的關係由信任到依賴的過程中獲得一絲慰藉,產生了忘卻或抵禦恐懼的「藥方」。
「藥方」產生心理醫生的「價值中立」:把自己當他人,把他人當自己,把自己當自己。
就像臧醫生診所裡掛著的那幅心理學經典圖,那兩個男人頭像,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個,其實只是一個。
一個明朗、一個陰森;一個和藹如春,一個卻猙獰可怖。
每一個裡面都藏著另一個,彼此包藏。
在呂志清的筆下,關係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是一種為了瞭解現實而做出的努力。
人們為什麼期待交心呢?因為「心」是人的內在奧祕,不瞭解它就不瞭解人。
人們為什麼害怕以心交心呢?因為互相交底就意味著互相控制,祕密也是一種權力。
問題還在於,我們都未必清楚內心的奧祕,未必知道也未必說得清楚心在何處。
對臧醫生而言,信奉「價值中立」其實只是精神分析的「醫術」而已。
所謂不偏不倚包藏的卻是不明不白。
湯瑪斯‧曼曾一針見血地說過,佛洛依德的偉大在於他有這樣的見解,即我們稱之為「病的東西實際上是人們做的某種事,而不是他們遇到的某種事。
在這些問題上佛洛依德採取騎牆的態度,他怎麼會屢戰屢勝呢?」的確,臧醫生是屢戰屢勝的。
那個學生家長沈潔的「社會恐懼症」與「赤面恐懼症」,經由臧醫生的「系統脫敏療法」,迅速地有了變化。
還有那個常常在網上與臧醫生打來打去、鬥來鬥去、殺來殺去的「十步芳草」,也神奇地走上了逃亡之路。
沈潔的突然轉身,由社交恐懼症轉為過度參與的社交狂熱病症,正是應驗了精神分析的格言:人所希望,人亦害怕;人所害怕,人亦希望。
變化中的沈潔,「既有點期盼又有點恐懼。
她對這期盼感到恐懼,對恐懼感到期盼。
在這種期盼的恐懼或恐懼的期盼中,她感到有點惶惶不安。
」惶恐並不是「患者」才有,臧醫生也不例外。
無休止地陷入別人的問題和麻煩中!陷入自己的職業角色裡!沒有誰會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他的問題和他的麻煩。
當我們沉浸於臧醫生的醫術之中沾沾自喜時,很容易忽略操弄這醫術的也是人,也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麻煩和問題。
在敘事者自鳴得意的敘述之中,恐怕最得意的莫過於這一洞見。
臧醫生想從所有患者中獲得駕馭的自主,以滿足自身的權力欲。
醫治了她的疾病就等於失去了控制的權力。
何莉莉的不滿和疑惑、沈潔的走向反面,還有那范彬彬無休止的逃跑,都是一種對「控制欲」的懲罰,控制與反控制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和甜瓜,它們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共謀的關係。
至少,在呂志清的小說中是如此。
其實,「中立價值」並非無價值,至少人類數千年追求正義公平的理想與實踐,都來之於中立性的標準。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聖經》中的「你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你就怎麼待別人」,這些普世性的正義準則都是源出「中立價值」。
問題是如今這個「中立價值」成了醫術,成了精神病醫生和患者的「關係學」。
在諮詢師與救助者之間,除了職業關係,誰能保證不再有任何其他關係。
在「中立價值」的指導下,臧醫生和何莉莉的關係轉而成為一種新型的同居關係,「這種關係介於朋友和情人之間,比朋友略多,比情人略少,結構也比較鬆散。
」於是,有了維護這種不偏不倚關係的「黑暗中的帽子」,「黑暗中的帽子」成了「中立價值」的符號,成了無形中的戒律,成了防範何莉莉進一步追求私人完美的「律法」,何莉莉只能陷入無以言說的困惑之中。
在解決精神問題時忘卻身體,在解決肉體問題時丟棄精神,臧醫生也隱隱約約地露出其兩個男人頭像的真面目。
一個人的真實面目是難以自我認知的,當你達到自知之明時,你就會遭遇一個殘片的自己。
當小說通過沈潔的講述,終於明白、終於認清臧醫生的真面目和騙術時,至多也只是表現了敘事者的精心安排和一廂情願。
我們生活在符號秩序中的客觀處與自己的想像性觀念之間,對他者來說我所是的一切與我對自己來說我所是的一切之間,存在著差距。
原來憑藉著這種差距才是我們擁有的一切。
控制是一種偏執的意願,反控制也是一種片面的行徑。
也許在控制和反控制之間,我們才能強烈地體味那無法言說的言說。
所謂外星人,無非也是一種權力控制無所不在的想像,是一種替代型的符號。
「控制的勢力無處不在,它操縱你的思想,甚至操縱你的肉體。
哪怕是隔著遙遠的距離,它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玩你於股掌之間。
你要是一不小心被它抓住了,就等於是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
」對薩特來說,自由的哲學就是人處在不斷逃亡之中,而對「網名十步芳草」的范彬彬來說,逃亡僅僅只是恐懼被控制的絕望,這既是一種精神病症,也是一種常態的抽象。
這裡同樣包藏著敘事者對於抽象含義的急功近利,為了突出一點而不及其餘的敘事偏頗。
實際上,我們有時很難區分本源意義上的二重性,抵制權力控制還是與權力合謀,施虐與受虐的彼此依存在實際經驗中並不是涇渭分明的。
權力之所以生生不滅的一個重要原因,那是因為權力與受害者身上的某種東西沆瀣一氣。
敘事者自以為看得清楚明白的東西,很可能實際存在的是相反的他途。
心理諮詢並不簡單地提供了醫師和病人之間的依附關係,他們的關係要複雜得多,中立、不表態都是幌子,與其說是維繫一種單一並不存在的關係,倒不如說試圖遮掩更為錯綜糾纏、模稜兩可的相互依賴,彼此都在借助對方而表現自我的機會。
借助對方的心理病症而更好地表現自己的病症,或者借助自己的病兆來掩飾他人的病兆。
在《馬克白》中,當馬克白問三女巫「你們是什麼?」時,她們在答覆中對他說了他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很像是臧醫生和何莉莉、沈潔、范彬彬的關係,也很像是臧醫生在患者面前的自我呈現。
健康的關係無疑存在,但通往健康的道路卻是病態。
我們必須聆聽一個個反諷的故事,內容是健康如何產生於反面,如何在各種各樣的關係中經歷不明不白、各類恐懼病症、控制與反控制、施虐和受虐、統一與分歧等無謂的嘗試、死胡同,所有這些涉及故事過程的東西以及病態中的真實人性。
只有不斷地檢討病態,才能最終認識健康,完全脫離病態的健康恐怕只剩虛無,只有審視各種似乎是病態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帽子」和「口罩」,一個明白易懂、連貫的文本才會呈現。
為了回歸自我而落入世俗的王國,為了尋求健康而不惜陷入病態的糾纏。
《黑暗中的帽子》是一部控制與反控制文本,小說製造的恐懼症一個接一個,擺脫舊的恐懼,新的恐懼接踵而來。
作為心理諮詢,表面是治療和幫助別人擺脫心理病症的糾纏和控制,實際上又是以一種新的控制來擺脫舊的控制,牢籠始終存在,牢籠無處不在。
說到底,心理諮詢又是一種黑暗中的誅心之術。
沈潔怕到公共場所,害怕上街,害怕進商場、超市和菜市,雖說她就是在這個城市裡長大的,但卻常找不到東南西北,走著走著就迷了路。
逃無可逃,這個世界不是為了她這一類人準備的。
她、她這一類人,只是一些蜷縮在某個角落的多餘人;在臧醫生看來,范彬彬「幾乎是某種權力─知識、權力─真理的犧牲品。
或者是這個社會製造的一個規範化的標準件。
她僵化的頭腦中裝了太多的現存觀念。
這些觀念無疑來自灌輸─幾乎她一出生就開始了的灌輸。
結果,她不僅對自己毫無自知之明,還以為真理在握」。
結果,不斷地逃亡,又無功而返。
加上那何莉莉,她們都感到被困在自己狹隘的地平線上,需要自己待定的彼岸,然而又害怕經歷這一彼岸,就像你把所有的蛋都放進了籃子,你又必須為了生活而攥緊籃子。
一個人想獲取整個世界,卻用單一的對象和單一的恐懼來容納。
說到底控制與被控制就是那黑暗的帽子,臧醫生的診所並不是那麼具體的,它既是一種延伸又是一種隱喻,權力、社會、公共關係弄得不好就是一個偌大的診所。
2
呂志清的小說總是從兩個人的關係入手,是敘事舞台上的「二人轉」。
身分問題、人的境遇、人的精神狀況,還有那人與生活的分離性都是其探詢的對象。
自以為理解的那種不理解,自以為溝通的那種無法溝通;在沒有矛盾的地方引進矛盾,在常識通常稱之為有矛盾的地方不引進矛盾,這些都是呂志清敘事的慣用手法。
既是呂志清的對象又是他的方法,既是他的形式又是他的內容。
呂志清的著眼點是關係種種:不確定的關係、變化中的關係、過早明確但又虛幻的關係。
敘事過程總是一種關係引入另一種關係,而兩個人的關係演變為三個、四個甚至更多人的關係。
對呂志清而言,關係不是地點,也算不上時間,而是一種可能性、一種存在、一種徵兆、一種猜測、一種似是而非的假設。
正因為人與人的關係經常是極為傷腦筋的、模糊的、意義不明確的,才會有對故事的探尋、詢問、疑問和追問。
對許多作家而言,局外人、多餘人的生活促進了思想的深度與視角的敏銳,呂志清不然,他更多是在深陷其中的苦惱與快樂之間左顧右盼;對大多數人來說,暫時中止活動、變形和擁有多重身分,將會是一種令人愉悅的放鬆,呂志清不然,他固執地讓其敘事者陷入單一的身分,讓其在說不清理還亂的困境中自生自滅。
一句話,呂志清自成一體的敘事特色,在於他很少理會人們業已習慣了的敘事情節和促進因素,他刻意地將其小說演繹成一種符號交換台,通過它,編碼被倒著解讀,信息又總是被攪亂成對立面。
因此,他的小說缺乏可比性,難以歸類,無法貼上「主義」、「流派」的標籤。
這讓熱中於類比、沉浸於「連續性」的批評作業經常陷入難以言說的困愕之中。
二○○九年發表的《蛇蹤》是個既新又舊的故事。
說其新,那是因為在關注當下現實社會問題如此急功但並不一定近利的敘事,在呂志清的小說中尚屬少見。
小說中凡鄉村選舉、競選縣人大代表、進城打工、房地產開發、強行拆遷、託朋友走門路、新舊現象、時尚寵物、環境污染、三農問題……都有所涉足。
說其舊,那是因為《蛇蹤》和作者以往的小說有點似曾相識。
故事圍繞著那到過房中的蛇,不見蹤影的蛇,留下痕跡的蛇,因蛇而引發的心病,因蛇蹤而引起的對蛇的依賴─不管它是真蛇還是假蛇,直至關於小奚的心病而引發的脫敏療法而循序漸進。
呂志清的小說都是圍繞著一個物體和事件而展開,諸如《老五》中那頭正在慢慢死去的老黃牛、《闖入者》中的牙齒、《愛智者的晚年》中那陽台上的牽牛花等等。
追蹤無疑是我在這個世界存在的連鎖反應,但是,對於一條蛇所留下痕跡的追蹤,便形成了我試圖從莫名的他物中回收到自我心中對恐懼的留戀。
有點神經質的小奚,不時地把幻想和現實混淆起來,經常會有一種神神道道或疑神疑鬼的神情。
詭祕、隱蔽、鬼鬼祟祟,這些詞都成了小奚的代言名詞。
這些自以為明白的確切性實際上正昭示著某種無法明白的焦慮。
佛洛依德晚年在很大程度上,把焦慮視為一個對普遍的孤弱、遺棄以及不可逃避之宿命的反應。
這裡,又一次出現了我們業已熟悉的脫敏療法。
「小奚的那個脫敏療法,不是在虛擬和想像中進行的那種,而是活生生的、實打實的方式。
是在活生生的景象中,實打實地接近那個引起恐懼的恐懼對象,目的當然是為了擺脫它。
這也就是說,不管是她還是他,那東西如今已成了他生活的一種必需品了。
」實際上,那留下蹤影的蛇是否曾經出現、是否能再次出現,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依賴它以對付它的存在與不存在。
如果小奚經歷的是虛幻走向現實的過程,那個遠在鄉村的董大奎則是反其道而行之。
不安分的農民董大奎,因揭發了村幹部向地產商出賣土地、出租土地的非法行徑而嶄露頭角,競選縣人大代表而一舉成名,選舉村主任成功而準備大施拳腳時,不如意的現實種種卻迫使其遠離他鄉。
我們終於明白,接近是一種擺脫,遠離又何嘗不是一種擺脫。
小奚是對不現實之物的過度接近,而董大奎則是對現實的過度參與。
不清楚批評業的專家學者是如何評說呂志清的小說。
是無法認同還是不屑一顧,是無法言說還是無需言說?問了一些熟悉行情的朋友,依然是不甚了了。
二○○九年的《鍾山》雜誌試圖打破僵局,不僅一年之中兩次頭條發表呂志清的小說,而且執行主編賈夢瑋親自執行並請人操刀,連續在《小說評論》上發表推薦文章。
今年,呂志清總共發表三個中篇,除了《鍾山》上的以外,還有就是發表在《山花》上的《蛇蹤》。
粗略地統計一下,這些年發表呂志清小說最勤快的,非《山花》雜誌莫屬。
即便如此,在評價上依然是沉默。
文章寫完時,見到《山花》雜誌二○○九年十二期上發表的饒向陽的評論文章:《哲性的拷問與詩性的解答─呂志清創作瑣論》。
也不清楚有多少人閱讀或喜歡閱讀呂志清的小說,我的估計不會太多。
如同呂志清本人也不怎麼閱讀中國小說一樣,都是一種拒絕對方的不期而遇。
呂志清曾在一篇關於《老五》的創作談中說:「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基本不太看中國的當代作品。
」(見《中篇小說選刊》二○○七年第六期)
這樣一種作品與閱讀、小說與批評間不明不白的關係,很像今年呂志清小說的所有開頭:
禹斌覺得,他和章彥的關係似乎一直都有點古怪:同學不像同學,戀人不像戀人。
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他似乎一直也沒怎麼明白。
─《一九三七年的情節劇》
小馮和小奚屬於那種「閃婚」族,與小布希和蘿拉的情況一樣,相識三個月就結了婚。
─《蛇蹤》
何莉莉每週有三個晚上去臧醫生那裡。
週一、週三、週五。
何莉莉下了班就直接去臧醫生家。
現在,何莉莉仍然管臧醫生叫臧醫生,但他們之間已不再是心理醫生和救助者的關係了,而是一種新型的關係…… ─《黑暗中的帽子》
三部小說三個開頭:設問、肯定、陳述中的轉變,講的都是人與人的關係。
問題在於,人與人的關係是無處不在的東西,並不只是在我們探討它的時候才會存在。
當呂志清以其假定的敘事方式探討這樣或那樣的關係時,究竟是拒絕了無處不在的直觀世界,還是進入了一種與直觀世界相類似的無限的不確定性之中?批評作為探討的探討很容易地進入了無法言說,難以抉擇的困境之中。
認同是進入角色的方式,而關於認同的認同很可能也是退出角色的方式。
我們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混合性的角色,這些角色表面上能滿足我們的認知欲望,實則與我們的認知欲望相對立。
需要認清的是,生活很可能不再是身體力行的運動場所,更多形態的日常生活往往發生在翻閱報刊雜誌打開電視之際,在電腦前隨意瀏覽、和陌生人隨意聊天之中。
當我們竭力地去獲取這個世界的有關信息,而作為信息的世界已經順利誕生了。
只要你有思辨的頭腦,只要你有發問的能力,而想像呢,很可能是尾隨其後的東西。
激進的現代派曾試圖抹平藝術和生活的差別。
現在看來,生活為他們做到了這一點。
讀呂志清的小說,我們彷彿坐落於書齋之中,沉陷於思辨的困境,同時又沉迷於一套獨特而富有魅力的敘事圈套,難以自拔。
這些符號化的世界很明確是內心和隱喻性的,但也被表現為具有頑強的物質性─那空洞而又無處不在的「關係」。
我的身分處於別人的保管之中,儘管這個別人是由他們自己的利益和欲望組成,儘管這種保管永遠不會安全。
我的自我監護人正是他人,正如梅洛龐蒂所說的「我從他人那裡借來了我自己」(〔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符號》,商務印書館二○○三年九月版)。
1
《黑暗中的帽子》圍繞著心理醫生與不同患者之間演繹其敘事。
所謂黑暗,與恐懼有關;所謂帽子,與控制有關。
何莉莉婚後與丈夫小魯無法交流,從言語無法交流發展到肢體衝突,暴力生活前,何莉莉心生恐懼,頗似受虐狂。
「什麼是恐懼症呢?害怕不該害怕的,或者,對不存在的恐懼感到恐懼。
」何莉莉的疑似恐懼症在臧醫生處得到這樣的解答。
我們需要顧及自己,部分原因就是恐懼。
而來自於別人信任的這種信任,則是我們能戰勝恐懼的希望。
對何莉莉而言,是真實的恐懼還是疑似的恐懼症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她與臧醫生的關係由信任到依賴的過程中獲得一絲慰藉,產生了忘卻或抵禦恐懼的「藥方」。
「藥方」產生心理醫生的「價值中立」:把自己當他人,把他人當自己,把自己當自己。
就像臧醫生診所裡掛著的那幅心理學經典圖,那兩個男人頭像,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個,其實只是一個。
一個明朗、一個陰森;一個和藹如春,一個卻猙獰可怖。
每一個裡面都藏著另一個,彼此包藏。
在呂志清的筆下,關係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是一種為了瞭解現實而做出的努力。
人們為什麼期待交心呢?因為「心」是人的內在奧祕,不瞭解它就不瞭解人。
人們為什麼害怕以心交心呢?因為互相交底就意味著互相控制,祕密也是一種權力。
問題還在於,我們都未必清楚內心的奧祕,未必知道也未必說得清楚心在何處。
對臧醫生而言,信奉「價值中立」其實只是精神分析的「醫術」而已。
所謂不偏不倚包藏的卻是不明不白。
湯瑪斯‧曼曾一針見血地說過,佛洛依德的偉大在於他有這樣的見解,即我們稱之為「病的東西實際上是人們做的某種事,而不是他們遇到的某種事。
在這些問題上佛洛依德採取騎牆的態度,他怎麼會屢戰屢勝呢?」的確,臧醫生是屢戰屢勝的。
那個學生家長沈潔的「社會恐懼症」與「赤面恐懼症」,經由臧醫生的「系統脫敏療法」,迅速地有了變化。
還有那個常常在網上與臧醫生打來打去、鬥來鬥去、殺來殺去的「十步芳草」,也神奇地走上了逃亡之路。
沈潔的突然轉身,由社交恐懼症轉為過度參與的社交狂熱病症,正是應驗了精神分析的格言:人所希望,人亦害怕;人所害怕,人亦希望。
變化中的沈潔,「既有點期盼又有點恐懼。
她對這期盼感到恐懼,對恐懼感到期盼。
在這種期盼的恐懼或恐懼的期盼中,她感到有點惶惶不安。
」惶恐並不是「患者」才有,臧醫生也不例外。
無休止地陷入別人的問題和麻煩中!陷入自己的職業角色裡!沒有誰會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他的問題和他的麻煩。
當我們沉浸於臧醫生的醫術之中沾沾自喜時,很容易忽略操弄這醫術的也是人,也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麻煩和問題。
在敘事者自鳴得意的敘述之中,恐怕最得意的莫過於這一洞見。
臧醫生想從所有患者中獲得駕馭的自主,以滿足自身的權力欲。
醫治了她的疾病就等於失去了控制的權力。
何莉莉的不滿和疑惑、沈潔的走向反面,還有那范彬彬無休止的逃跑,都是一種對「控制欲」的懲罰,控制與反控制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和甜瓜,它們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共謀的關係。
至少,在呂志清的小說中是如此。
其實,「中立價值」並非無價值,至少人類數千年追求正義公平的理想與實踐,都來之於中立性的標準。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聖經》中的「你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你就怎麼待別人」,這些普世性的正義準則都是源出「中立價值」。
問題是如今這個「中立價值」成了醫術,成了精神病醫生和患者的「關係學」。
在諮詢師與救助者之間,除了職業關係,誰能保證不再有任何其他關係。
在「中立價值」的指導下,臧醫生和何莉莉的關係轉而成為一種新型的同居關係,「這種關係介於朋友和情人之間,比朋友略多,比情人略少,結構也比較鬆散。
」於是,有了維護這種不偏不倚關係的「黑暗中的帽子」,「黑暗中的帽子」成了「中立價值」的符號,成了無形中的戒律,成了防範何莉莉進一步追求私人完美的「律法」,何莉莉只能陷入無以言說的困惑之中。
在解決精神問題時忘卻身體,在解決肉體問題時丟棄精神,臧醫生也隱隱約約地露出其兩個男人頭像的真面目。
一個人的真實面目是難以自我認知的,當你達到自知之明時,你就會遭遇一個殘片的自己。
當小說通過沈潔的講述,終於明白、終於認清臧醫生的真面目和騙術時,至多也只是表現了敘事者的精心安排和一廂情願。
我們生活在符號秩序中的客觀處與自己的想像性觀念之間,對他者來說我所是的一切與我對自己來說我所是的一切之間,存在著差距。
原來憑藉著這種差距才是我們擁有的一切。
控制是一種偏執的意願,反控制也是一種片面的行徑。
也許在控制和反控制之間,我們才能強烈地體味那無法言說的言說。
所謂外星人,無非也是一種權力控制無所不在的想像,是一種替代型的符號。
「控制的勢力無處不在,它操縱你的思想,甚至操縱你的肉體。
哪怕是隔著遙遠的距離,它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玩你於股掌之間。
你要是一不小心被它抓住了,就等於是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
」對薩特來說,自由的哲學就是人處在不斷逃亡之中,而對「網名十步芳草」的范彬彬來說,逃亡僅僅只是恐懼被控制的絕望,這既是一種精神病症,也是一種常態的抽象。
這裡同樣包藏著敘事者對於抽象含義的急功近利,為了突出一點而不及其餘的敘事偏頗。
實際上,我們有時很難區分本源意義上的二重性,抵制權力控制還是與權力合謀,施虐與受虐的彼此依存在實際經驗中並不是涇渭分明的。
權力之所以生生不滅的一個重要原因,那是因為權力與受害者身上的某種東西沆瀣一氣。
敘事者自以為看得清楚明白的東西,很可能實際存在的是相反的他途。
心理諮詢並不簡單地提供了醫師和病人之間的依附關係,他們的關係要複雜得多,中立、不表態都是幌子,與其說是維繫一種單一並不存在的關係,倒不如說試圖遮掩更為錯綜糾纏、模稜兩可的相互依賴,彼此都在借助對方而表現自我的機會。
借助對方的心理病症而更好地表現自己的病症,或者借助自己的病兆來掩飾他人的病兆。
在《馬克白》中,當馬克白問三女巫「你們是什麼?」時,她們在答覆中對他說了他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很像是臧醫生和何莉莉、沈潔、范彬彬的關係,也很像是臧醫生在患者面前的自我呈現。
健康的關係無疑存在,但通往健康的道路卻是病態。
我們必須聆聽一個個反諷的故事,內容是健康如何產生於反面,如何在各種各樣的關係中經歷不明不白、各類恐懼病症、控制與反控制、施虐和受虐、統一與分歧等無謂的嘗試、死胡同,所有這些涉及故事過程的東西以及病態中的真實人性。
只有不斷地檢討病態,才能最終認識健康,完全脫離病態的健康恐怕只剩虛無,只有審視各種似乎是病態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帽子」和「口罩」,一個明白易懂、連貫的文本才會呈現。
為了回歸自我而落入世俗的王國,為了尋求健康而不惜陷入病態的糾纏。
《黑暗中的帽子》是一部控制與反控制文本,小說製造的恐懼症一個接一個,擺脫舊的恐懼,新的恐懼接踵而來。
作為心理諮詢,表面是治療和幫助別人擺脫心理病症的糾纏和控制,實際上又是以一種新的控制來擺脫舊的控制,牢籠始終存在,牢籠無處不在。
說到底,心理諮詢又是一種黑暗中的誅心之術。
沈潔怕到公共場所,害怕上街,害怕進商場、超市和菜市,雖說她就是在這個城市裡長大的,但卻常找不到東南西北,走著走著就迷了路。
逃無可逃,這個世界不是為了她這一類人準備的。
她、她這一類人,只是一些蜷縮在某個角落的多餘人;在臧醫生看來,范彬彬「幾乎是某種權力─知識、權力─真理的犧牲品。
或者是這個社會製造的一個規範化的標準件。
她僵化的頭腦中裝了太多的現存觀念。
這些觀念無疑來自灌輸─幾乎她一出生就開始了的灌輸。
結果,她不僅對自己毫無自知之明,還以為真理在握」。
結果,不斷地逃亡,又無功而返。
加上那何莉莉,她們都感到被困在自己狹隘的地平線上,需要自己待定的彼岸,然而又害怕經歷這一彼岸,就像你把所有的蛋都放進了籃子,你又必須為了生活而攥緊籃子。
一個人想獲取整個世界,卻用單一的對象和單一的恐懼來容納。
說到底控制與被控制就是那黑暗的帽子,臧醫生的診所並不是那麼具體的,它既是一種延伸又是一種隱喻,權力、社會、公共關係弄得不好就是一個偌大的診所。
2
呂志清的小說總是從兩個人的關係入手,是敘事舞台上的「二人轉」。
身分問題、人的境遇、人的精神狀況,還有那人與生活的分離性都是其探詢的對象。
自以為理解的那種不理解,自以為溝通的那種無法溝通;在沒有矛盾的地方引進矛盾,在常識通常稱之為有矛盾的地方不引進矛盾,這些都是呂志清敘事的慣用手法。
既是呂志清的對象又是他的方法,既是他的形式又是他的內容。
呂志清的著眼點是關係種種:不確定的關係、變化中的關係、過早明確但又虛幻的關係。
敘事過程總是一種關係引入另一種關係,而兩個人的關係演變為三個、四個甚至更多人的關係。
對呂志清而言,關係不是地點,也算不上時間,而是一種可能性、一種存在、一種徵兆、一種猜測、一種似是而非的假設。
正因為人與人的關係經常是極為傷腦筋的、模糊的、意義不明確的,才會有對故事的探尋、詢問、疑問和追問。
對許多作家而言,局外人、多餘人的生活促進了思想的深度與視角的敏銳,呂志清不然,他更多是在深陷其中的苦惱與快樂之間左顧右盼;對大多數人來說,暫時中止活動、變形和擁有多重身分,將會是一種令人愉悅的放鬆,呂志清不然,他固執地讓其敘事者陷入單一的身分,讓其在說不清理還亂的困境中自生自滅。
一句話,呂志清自成一體的敘事特色,在於他很少理會人們業已習慣了的敘事情節和促進因素,他刻意地將其小說演繹成一種符號交換台,通過它,編碼被倒著解讀,信息又總是被攪亂成對立面。
因此,他的小說缺乏可比性,難以歸類,無法貼上「主義」、「流派」的標籤。
這讓熱中於類比、沉浸於「連續性」的批評作業經常陷入難以言說的困愕之中。
二○○九年發表的《蛇蹤》是個既新又舊的故事。
說其新,那是因為在關注當下現實社會問題如此急功但並不一定近利的敘事,在呂志清的小說中尚屬少見。
小說中凡鄉村選舉、競選縣人大代表、進城打工、房地產開發、強行拆遷、託朋友走門路、新舊現象、時尚寵物、環境污染、三農問題……都有所涉足。
說其舊,那是因為《蛇蹤》和作者以往的小說有點似曾相識。
故事圍繞著那到過房中的蛇,不見蹤影的蛇,留下痕跡的蛇,因蛇而引發的心病,因蛇蹤而引起的對蛇的依賴─不管它是真蛇還是假蛇,直至關於小奚的心病而引發的脫敏療法而循序漸進。
呂志清的小說都是圍繞著一個物體和事件而展開,諸如《老五》中那頭正在慢慢死去的老黃牛、《闖入者》中的牙齒、《愛智者的晚年》中那陽台上的牽牛花等等。
追蹤無疑是我在這個世界存在的連鎖反應,但是,對於一條蛇所留下痕跡的追蹤,便形成了我試圖從莫名的他物中回收到自我心中對恐懼的留戀。
有點神經質的小奚,不時地把幻想和現實混淆起來,經常會有一種神神道道或疑神疑鬼的神情。
詭祕、隱蔽、鬼鬼祟祟,這些詞都成了小奚的代言名詞。
這些自以為明白的確切性實際上正昭示著某種無法明白的焦慮。
佛洛依德晚年在很大程度上,把焦慮視為一個對普遍的孤弱、遺棄以及不可逃避之宿命的反應。
這裡,又一次出現了我們業已熟悉的脫敏療法。
「小奚的那個脫敏療法,不是在虛擬和想像中進行的那種,而是活生生的、實打實的方式。
是在活生生的景象中,實打實地接近那個引起恐懼的恐懼對象,目的當然是為了擺脫它。
這也就是說,不管是她還是他,那東西如今已成了他生活的一種必需品了。
」實際上,那留下蹤影的蛇是否曾經出現、是否能再次出現,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依賴它以對付它的存在與不存在。
如果小奚經歷的是虛幻走向現實的過程,那個遠在鄉村的董大奎則是反其道而行之。
不安分的農民董大奎,因揭發了村幹部向地產商出賣土地、出租土地的非法行徑而嶄露頭角,競選縣人大代表而一舉成名,選舉村主任成功而準備大施拳腳時,不如意的現實種種卻迫使其遠離他鄉。
我們終於明白,接近是一種擺脫,遠離又何嘗不是一種擺脫。
小奚是對不現實之物的過度接近,而董大奎則是對現實的過度參與。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