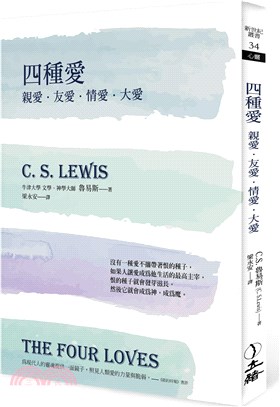商品簡介
《四種愛》是在魯易斯對愛產生更深刻的人生體驗後所留下的思想筆記。
它不但描述了不同種類的愛,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學習如何辨別真愛。
它是認識愛的一本重要讀物,在裡面魯易斯特別給了我們非常寶貴的洞見,能成為讀者生命的格言。
納尼亞傳奇.英國牛津學者C.S. Lewis
用靈魂寫成的一本書
英國知名學者、作家及神學家C.S.魯易斯(C.S. Lewis, 1898-1963)晚年的重要著作《四種愛:親愛.友愛.情愛.大愛》,是用他的靈魂寫成的書,也是他自身經歷與愛的見證。魯易斯與喬伊深摯的愛情故事,詳盡紀錄於《影子大地》一書(立緒文化出版)。1960年魯易斯出版《四種愛:親愛.友愛.情愛.大愛》,當時他正深情陪伴病重的靈魂伴侶喬伊,他對恆久騷動人類的課題:愛是什麼?做了全新的闡發。
愛(love),希臘字原本分為四種:storge親愛(affection),philiaq友愛(friendship),eros情愛(sexual or romantic love),和agape無私的大愛(selfness love)。
魯易斯以其一貫幽默感、洞察力,將各種人類的愛加以歸類,並深入分析它們的本質。
他把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人與鄰居、人與動物之間的感情稱為親愛之情,是各種愛中「最沒有歧視性的一種」。至於情愛,性與愛的複合體,雖然可以點燃人無私的犧牲奉獻精神,但同樣潛伏著讓人走向自毀的因子。友愛是各種人類愛中「最不動物性」、最超塵絕俗的一種,儘管如此,友愛仍不免挾帶不良的副作用,唆使一群朋友走向孤芳自賞、目空一切。
每種愛都能為人帶來歡愉,但稍一不慎,恨就會接踵而來。
在魯易斯看來,親愛、友愛、情愛這三種人類愛,若少了第四種愛――大愛的扶持,將無法結出甜美的果實。儘管人類愛潛伏著讓人走火入魔的危險,魯易斯仍然鼓勵我們去愛,因為「除天堂外,能讓人完全不用冒愛之風險的所在,唯有地獄」。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C. S.魯易斯 (C. S. Lewis)
英國著名學者及作家。1954年至1963年間,任劍橋大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講座」教授。無論教學或創作,皆以機智、博學、想像力及以精確的表達1898年生於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1918年入牛津大學專攻古典文學,1925年至1954年在牛津馬格達倫(Magdalen)學院任研究員。能力著稱。1963年卒於英格蘭的牛津。
魯氏著作等身,以《愛情的寓言》(1936)一書享譽學界。其他重要的學術作品包括《失樂園序篇》(1942)、《十六世紀英國文學》(1954),以及《摒棄的意象: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英國文學導讀》(1964)。除為數不少探討基督教義的著作外,還先後出版過一組科幻三部曲:《來自沈默的行星》(1938)、《佩利蘭德拉》(1943)以及《那駭人的威力》(1945)、三卷詩作、一部小說和多部文學批評論著。
他也是深受喜愛的兒童故事集經典之作《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的作者。其他還有一系列兒童讀物《馬兒與馬童》(The Horse and His Boy, 1945),《魔術師的外甥》(The Magicians Nephew, 1955),《最後一戰》(The Last Battle, 1956)等書。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譯著包括《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現代主義》(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名人/編輯推薦
為現代人的靈魂提供一面鏡子,照見人類愛的力量與脆弱。
――《紐約時報》書評
目次
〈導言〉
「無所求的愛」和「有所求的愛」
.愛從它膨脹為神的那一剎那開始,就會淪落為魔。
.「有所求的愛」可能是貪婪的,不饜足的,但最少它們不會自封為神。
1對人類以外事務的喜歡與愛
.「激賞之樂」本身就是一件有權利要求我們欣賞的東西。
.對大自然的熱愛者來說,「氣韻」或「精神」才是至觀眾要的事情。
2親愛:依戀、親愛之情
.讓平凡無華的臉留在家裡吧,而親愛之情所擁有的,正是一張平凡無華的臉。
.如果人一任愛成為他生活的最高主宰,恨的種子就會發芽滋長。它會成為神,成為魔。
3友愛:朋友之愛
.戀人是臉對臉的,朋友是肩並肩的。
.戀人以無遮的身體相向,朋友則以無遮的人格相向。
.本身沒有東西可與別人分享的人,不可能分享到別人什麼。那裡都不打算去的人,也不可能有人願意當他的旅伴。
4情愛:戀人.夫妻之愛
.以崇高之姿說話的愛情,有可能為善,也有可能為惡。
.愛情的真正標誌就是願意與愛人共享不幸。
.只要是愛情,就都會有招引人都烈士的傾向。
.在各種人類愛中,愛情的短命是惡名昭著的
5大愛:屬天之愛
.不要把好東西放在有裂痕的容器內。
.不願選擇擔驚受怕的人,剩下的唯一去處就是地獄。
.拿地上的快樂來強求天國是有害無益的。
書摘/試閱
〈導言〉「無所求的愛」和「有所求的愛」
GIFT-LOVE AND NEED-LOVE
愛從它膨脹為神的那一剎那開始,就會淪落為魔。
「有所求的愛」可能是貪婪的,不饜足的,但最少它們不會自封為神。
「上帝是愛。」
剛下筆寫此書的時候,我原以為藉著聖約翰上述箴言之助,就可迅速解開「愛是什麼」這個謎。我本認定,人類的愛,如果配稱為愛的話,就應該和上帝的愛肖似。我曾把人世間的愛區分為兩種,稱其中一種為「無所求的愛」(Gift-love),稱另一種為「有所求的愛」(Need-love)。「無所求的愛」典型地體現在父親對子女的愛:子女的未來明明是父親所無法參與的,但他們仍然心甘情願,為子女未來的幸福而辛勤工作、儲蓄和籌謀;「有所求的愛」的典型則是嬰兒對母親的愛:嬰兒會對母親伸出雙手,是在他們備感孤獨或受到驚嚇之時。
到底是「無所求的愛」還是「有所求的愛」更肖似上帝的愛,不言自喻。上帝一無所缺,所以也一無所求。另一方面,又有什麼比我們對上帝的愛,更可以道道地地被稱為一種「有所求的愛」的呢?「有所求的愛」是我們人類的專利,是一種――正如柏拉圖所言――「因匱乏而生的產物」(the son of poverty)。它是我們人類生存境遇在意識上的反映。我們生而無助。一旦我們開始產生意識,我們就會感到孤獨。我們無論在身體上、感情上和智性上都需要別人。沒有他們,我們無法認識任何事物,甚至無法認識自己。
我原初是把「無所求的愛」大大褒美一番,而把「有所求的愛」狠狠奚落一頓。但現在的我卻有了不同的想法。我仍然認為我上述大部分看法都是允當的。我仍然認為,如果一個人僅僅出於「需要」而愛,他就會顯得相當可悲可憐。只是,我現在不再(像我的恩師麥克唐納那樣)認為,那些把「有所求的愛」稱為愛的人,是指鹿為馬。我不再願意把「有所求的愛」擯斥為非愛,因為,每次我沿著這種思路思考問題,總會以困惑和自相矛盾告終。
首先,如果我們否定「有所求的愛」可稱為愛的話,那我們就違背了大部分語言(包括我們自己的英語)的規範。語言不見得就是不會有誤的嚮導,然而,不管它有多少缺點,它無疑仍包含著好些洞察與經驗。如果你從一開始就輕蔑它,那它到頭來準會給你吃一記回馬槍。所以,我們最好不要學昏弟敦弟(Humpty Dumpty)的樣子,愛怎麼用一個字,就怎樣用一個字。
第二,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輕率地把「有所求的愛」完全等同於「自私」。 沒有錯,「有所求的愛」也有可能像我們其他的生理衝動一樣,完全是出於不饜足的私慾。但試問,在日常生活中,誰又會把一個渴求母愛的小孩或一個尋求友情的成年人稱為是自私的呢?往往,那些對母愛或友情最不在意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反而才是最自私的人。沒有「有所求的愛」,正好就是冷酷和唯我的標記。由於我們生而需要別人(「人單獨生活不好」),所以,沒有「有所求的愛」,往往是一種不好的心理癥候,道理就好比我們生而需要食物,胃口欠佳反而是生病的徵兆。
第三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每個基督徒都一定會同意,人靈性層面的健康,絕對跟他對上帝的愛成正比。然而,人對上帝的愛,卻在很大程度上――往往甚至全然的――是一種「有所求的愛」。這一點,在我們身處困苦,祈求上帝伸出援手時,應有甚深體會。不過,我並不是說,人對上帝除了能獻上「有所求的愛」以外,別無所能。很多偉大的靈魂業已向我們證明,人所能達到的境界,不僅止於此。不過,恐怕也是這同一批人,向我們透露出,當一個人膽敢以為他可以撇開一切需要巍然獨立時,他業已在不自覺中陷入了魔鬼所設下的幻象。誠如《效法基督》一書所說的:「至高總是與至低形影相隨」(至高若無至低,則無以立足)。如果一個受造者膽敢走到他的創造者面前,說出像「我不是乞丐,我對你的愛一無所求」這樣的話來,他將是何等的愚昧和大言不慚!其實,上帝自己也鼓勵我們把需要擺在祂的面前。祂說過:「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又說過(在《舊約》裡):「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
綜上所述,可見,最少有一種「有所求的愛」(對上帝的愛),是可以讓人達到最健康的精神狀態的。不過,如果這是事實,一個奇怪的引申就會接踵而來:人,只有在與上帝最不肖似的時候,才會與上帝最接近。因為試問,還有什麼比豐盛與匱乏、至高與卑微、公義與腐敗、無限與無助,更天淵的分別呢?這個兩難式破壞了我原先的寫作構想,讓我舉步踟躕。
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區分兩種意義的「與上帝接近」(nearness to God)。第一種意義的「與上帝接近」是因肖似而接近(nearness-by-likeness)。我相信,上帝在創造萬物之初,確曾把自己的形象分授給萬物。時間與空間,是上帝博大的反映;所有的生命體,是上帝豐盛的反映;動物的生命,則是上帝能動性的反映。而人之所以比萬物更肖似上帝,是因為他擁有理性。至於天使,則因為擁有不死之身和非感官性的直觀能力,而更勝人一籌。因此,人(不管好人壞人)和天使(包括那些墮落了的天使)都要比動物來得與上帝更相像。他們在本質上可以說是與上帝「更相近」。不過,還有第二種意義的「與上帝接近」,這種接近,我名之為「因舉步而接近」(nearness-of-approach)。這是指人透過實踐上的努力,讓自己一步一步靠近主。「因肖似而接近」和「因舉步而接近」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它們有時會同時出現,有時則否。
讓我打個比方。假設我們的家位在山谷裡,而我們現正走在回家的山道上。中午時分,我們來到一處崖頂,我們的家就位於山崖底下。從空間上來說,我們這時離自己的家非常接近,擲一顆石子下去,甚至就可以打得著屋頂。但我們不是攀岩專家,無法就這樣垂直往下爬。要回家,只能繞路而行。在迂迴繞道的過程中,我們反而比站在崖頂上的時候離家更遠了。不過這只是物理學意義上的遠,因為從實際上來說,我每邁出一步,就離家近了一步。
站在崖頂上,我們確實是離家更近,但這種近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呆站在崖頂上愈久,就愈晚才回得了家。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也可作如是觀。我們與生俱來就帶有一部分上帝的形象,那是上帝在造物的時候把它們烙印在我們身上的,在這個意義上,人確實是與上帝接近的。不過,單靠與上帝形象上的相似,並沒法使我們多接近祂一些。只有透過行動上的接近、實踐上的努力,我們才有望更接近祂。與上帝的相似是上帝所賜與的(我們可以感激或不感激這種賜予,善用或濫用這種賜予),相反的,舉步而近卻是一件需要我們主動自發的事情。萬物各從不同的方面肖似上帝,但它們並不因此就一定能成為上帝的子女。要取得當上帝子女的資格,人就要努力在意志上與上帝結合。這種意志上的結合,讓人比肖像意義上的「像」更像上帝。一個作家說得好:我們想「像」上帝,就應該以上帝的道成肉身作為榜樣。換言之,我們應效法的是耶穌。但我們所要效法的,不只是殉道的耶穌,還是勞累、跋涉、被群眾揶揄、沒有內心平靜和沒有隱私可言的耶穌。這些事情,顯然沒有一樣是全能的上帝的屬性,不過,經受它們,我們卻反而與上帝更接近了。
現在我必須解釋,為什麼我會覺得這種觀念上的分疏,在我們處理愛這個課題的時候至關緊要。長久以來,聖約翰「上帝是愛」的提法雖然深得我心,但我始終沒有忘記一位現代作家德尼‧德‧魯日蒙特(M. Denis de Rougemont)的提醒:「愛,只有在它沒有膨脹為神的時候,才不會淪落為魔。」這句話顯然也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表達:「愛,從它膨脹為神的那一剎那開始,就會淪落為魔。」在我看來,魯日蒙特的話是聖約翰的箴言一個不可少的安全閥。少了它,「上帝是愛」這句話很容易就會被人顛倒過來,變成:「愛是上帝」。
我相信,任何深思的人都會明白魯日蒙特的話因何而發。任一種人類愛,當它的熱度高張到沸點的時候,都會傾向於認為自己具有神聖的權威性。它會把自己當成上帝意志的代言人。它會要求我們不計代價、毫無保留地獻身,它會把一切的不同意見都打為異端邪說,它會慫恿我們,不管什麼樣的行為,只要是「為愛而發」,就都是合法的,都是值得嘉許的。愛情或愛國心之易於「膨脹為神」,很多人早有所知。但一般人較不察覺的是,即使是親情或友情,都有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掉入同樣的陷阱。這一點,我現在不打算多談,因為在往後的章節裡,我還會反覆再提。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類愛之中,會自封為神的,倒不是那些我們稱之為「低層次」的愛,反而是那些我們稱之為「高層次」的愛。這在男女之愛的領域尤其明顯:說起話來聲音特別像神的情人,不是那些因對方美色而生愛戀的人,反而是那些對對方懷抱真正犧牲奉獻精神的人(我不是說前一類人就沒有毛病,而只是說他們不會犯自封為神的毛病)。一個因為慾念而愛戀異性的人,不會認為自己的愛戀有什麼可敬之處,道理就如一個抓癢的人不會認為抓癢是件有什麼可敬的事情一樣。相似的,一個過度溺愛、放任孩子的母親,比起一個自命「為子女犧牲奉獻」的母親,也較不容易自我膨脹為神。
人類愛不會在自己顯得有說服力以前自封為神,而要是它們不能肖似上帝的愛,也不會顯得有說服力。沒有錯,我們的「無所求之愛」確實是與上帝肖似,而詩人對它的種種頌讚都是公允的:它是歡娛的、有活力的、有耐心的、不吝於寬恕的。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點頭同意,表現出「無所求之愛」的人, 比一般人「更接近」上帝。問題是,這種與上帝的接近只是一種「因肖似而接近」,而非「因舉步而接近」。「肖似」是一種授與我們之物,而「舉步」則是一件靠我們自己來做,緩慢且費力的事情,兩者間並沒有必然關係。但是,由於人類的「無所求之愛」與上帝的愛確實太肖似了,以致很多人誤把它們等同不別。於是,我們很容易就會把本來只該歸屬給上帝之愛的無限制性歸屬給我們自己的「無所求之愛」,於是,它們就成了神――接著就成了魔。再下來,它們就會摧毀我們,然後自我摧毀。人類的愛,一旦被容許成為神,它就不再成其為愛。雖然它們仍被稱為愛,但實質上不過是恨一種較複雜的變形而已。
我們的「有所求的愛」可能是貪婪的、不饜足的,但最少它們不會自封為神。它們和上帝太不肖似了,以致它們根本不敢奢望當神。
由是觀之,我們既不應苟同於人類愛的盲目崇拜者,也不應苟同於人類愛的「拆穿家」。十九世紀文學家的最大謬誤就在於把愛情和親情謳歌得過了頭:在白朗寧(Browning)、金斯利(Kingsley)和帕特摩爾(Patmore)等人筆下,愛情往往被描繪得有如人生的救贖;而小說家們拿來跟「混濁塵世」相對照的,竟不是天國,而是家庭。我們自己時代的知識氣氛則恰恰與此相反。「拆穿家」把我們父輩對愛的大部分頌詞貶得一文不值。他們不遺餘力地把人類愛那隱藏在地底下的汙穢根部拔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過,在我看來,我們既不應附和那些「聰明得過頭的巨人」,也不應附和那些「愚蠢得過頭的巨人」。至高總是與至低形影相隨的。一棵植物,單有陽光而沒有髒兮兮的根部,一樣無法存活。況且,只要你不是把它拿到書房的書桌上,而是把它留在花園裡,那它的髒也是無傷大雅的。人類愛可以是上帝愛的輝煌映象。但也僅僅是映象而已,不多也不少。有時候,它們會是我們趨近主的助力,有時則是阻力。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