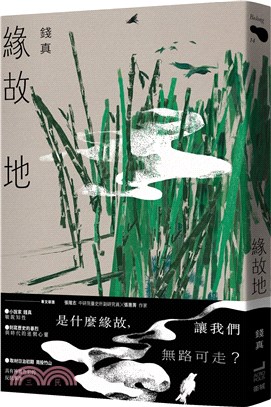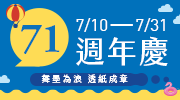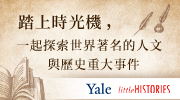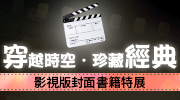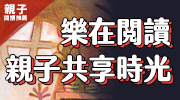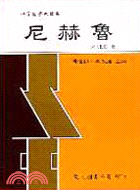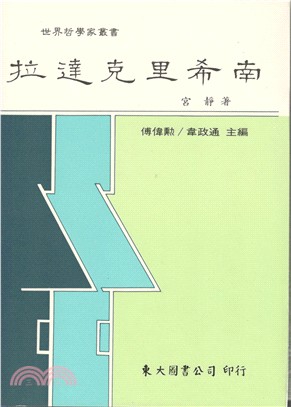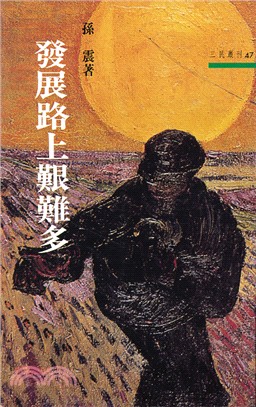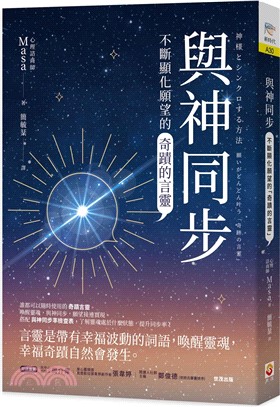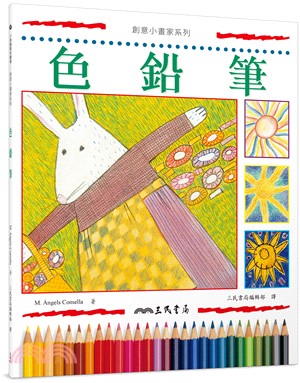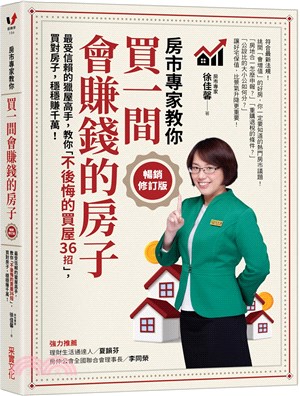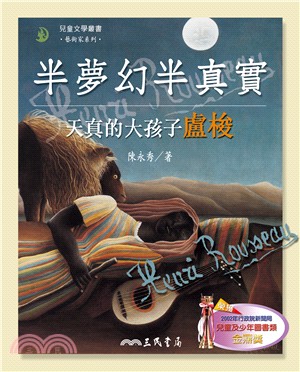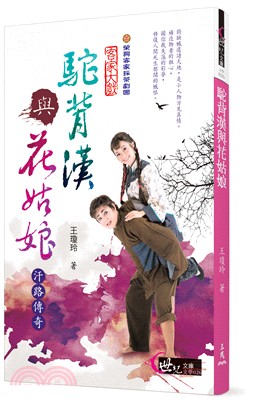商品簡介
一群徘徊在時代岔路口的人,以生命與歷史洪流拚搏……
小說家 錢真
取材日治初期 南投竹山具有神異色彩的反抗事件
刻寫歷史的暴烈與時代的迷惘心靈
本書獲得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當文明成為懾人心魂的法術,
山林的濃霧,能否保護生活在其中的人們?
最終,誰擁有權力居住在此地?
劉乾第一次與劉賜相遇時,他彷彿已預見兩人未來的命運。
明治四十二年,日本人統治臺灣的第十五年,文明的法術盤旋於林圮埔。
山中濃霧氤氳,人神交處,一不小心迷路就會被魔神仔牽去。劉乾與劉賜,一位是會施法念咒、為人消災解厄的術士,一位是隱居山林、躲避世事的質樸竹農。他們身體勞動、心靈遊蕩在山中,以竹林榮枯作為恆常的紀年。
然而,日本人帶著法律與技術到來。廣大的竹林因為沒留下明文契約,被劃歸為和當地人只存在「緣故關係」的國有地,兩人的生命也受到激烈震盪。什麼是法律?什麼是守時?什麼是秩序?當嶄新的觀念語言有如色彩奇異的咒語,遍布在日常生活每個角落,人們應如何重新安頓自身,辨認賴以生存的世道?
本書為曾獲得臺灣歷史小說獎的作家錢真,以家鄉竹山為場景,書寫一段日治時期帶有神異色彩的抗日故事。透過靜謐悠緩的筆觸,錢真寫下臺灣人經歷近代化洗禮的震顫、新舊秩序更迭的迷惘,以及人與土地的深厚關係。人們因何緣故相聚,又何以分歧、抵抗與消亡?錢真以最細膩之筆,寫下一段不為人知歷史的暴烈與溫柔。
作者簡介
本名錢映真,南投竹山人,現居臺南,寫作亦學習南管。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地球科學教師。曾獲臺灣歷史小說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獎、打狗鳳邑文學獎、南投縣玉山文學獎、桃城文學獎、臺中文學獎。
錢真擅於以寧靜知性筆法,挖掘歷史內面的幽微人心,她的小說兼具史識、詩意與哲思,著作《羅漢門》取材清代臺灣朱一貴抗爭事件,於二○一九年出版。
名人/編輯推薦
張隆志|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張惠菁|作家
共同推薦:
甘耀明|作家
朱和之|小說家
張俐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陳淑瑤|作家
陳耀昌|作家
序
開拓臺灣歷史小說的新天地
張隆志/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本文涉及部分小說情節,請斟酌閱讀。)
在閱讀歷史小說時,我們看到的是歷史、還是小說呢?
有鑑於歷史小說既不純然是講述歷史,更不是虛構的文學小說,學者在評論歷史小說時,常提到歷史性與小說性的強弱比重問題。而作者則需要兼顧歷史真實與小說創作,並成功地透過文學角度切入歷史,才能為讀者重現人事物的時空脈絡與歷史場景,帶領大眾穿越時光隧道體驗先人的音容笑貌,從而更深刻地認識與反思當代的情境與挑戰。
具體而言,臺灣歷史小說是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敘事作品,新興作家們運用歷史文獻,發掘田野史料,結合重要事件與人物傳記,重現各個時代與不同族群的歷史故事。作者們運用小說手法寫歷史,讓作品比一般學術論著更具有歷史溫度及人文關懷,並將臺灣歷史知識推廣給更多讀者。無論採取故事、改編、轉譯乃至非虛構寫作手法,或處理時代大歷史、區域地方史或個人生命史等課題,都提供讀者迥異於傳統教科書式的閱讀體驗和趣味,更有助於想像歷史行動者的心理感受與主觀意識。歷史小說家們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描述人物、事件與地點,透過人物對話呈現其個性思想及整體劇情的發展,並傳達人文社會的理想與願景。
相較於眾多種類的文學作品,臺灣歷史小說長期以來並非發達的創作文類。直到政治解嚴與民主化以來,才因著官方與民間各項獎助政策的提倡,以及各世代作家的人才輩出而蔚為新風潮。從二○○三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二○○七年國立臺灣文學館設立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二○一一年佛光山舉辦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的歷史小說獎、到新臺灣和平基金會自二○一四年開辦的臺灣歷史小說獎,這一波歷史小說熱潮除了鼓勵並培養出多位從事臺灣歷史小說的作者,同時更為臺灣影視戲劇與動漫文化提供了嶄新的創作靈感和豐富素材,讓讀者們更深刻地認識島嶼的歷史、土地與人群。
錢真是近年來歷史小說創作潮中頗受矚目的女性作者。她曾以魏晉歷史創作《嘉平夢》(二○一五年)榮獲第五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而首部臺灣歷史小說《羅漢門》(二○一九年)榮獲第四屆臺灣歷史小說獎。本書《緣故地》是由國藝會的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也是她以臺灣近代史為主題的最新力作。在完成以清初朱一貴事件和南臺灣移民社會為題材的《羅漢門》之後,錢真回到她的故鄉南投竹山,並選擇以日治前期發生於中臺灣的竹林事件為創作主題。
竹林事件的背景為臺灣總督府於一九○八年完成竹林調查後,將斗六、竹山乃至嘉義地區的竹林強制編入模範竹林,並交由三菱製紙株式會社實際支配所引發的地方抗爭。一九一二年三月,部分居民襲擊頂林警察派出所,造成三名員警死亡,史稱林圮埔事件。《緣故地》不僅重構了竹林事件的發展原委,更追溯至晚清開山撫番政策對於中部邊區市鎮與民眾生活的影響,並以臺灣文化協會的政治社會運動作為結語。
在《緣故地》一書中,錢真生動地呈現住在邊區竹林的漢人生活動態,尤其是他們由民間信仰與咒術構成的傳統世界觀。更進一步探討在乙未之變與政權轉移的時代巨變中,由日本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國家機器、資本主義體制與文明開化經驗,對於基層臺灣民眾的衝擊與影響。不同於多數作者著重書寫外在的大事件,錢真著重刻畫歷史人物的內面心理與思想變遷,尤其是基層民眾在面對時代巨變時的困惑與追尋、適應與衝突、以及啟蒙與行動。
錢真在本書中延續了她在《羅漢門》的寫作特色如歷史考據、文學想像、平民歷史、反抗精神,以及對於小人物、女性及鄉土議題的關懷。然而《緣故地》更進一步探索臺灣人面對殖民現代性的多重心理回應及集體行動邏輯,尤其是傳統世界觀與近代科學、法律、產業、教育等啟蒙思想的互動拮抗和變遷。她以更成熟的筆法與流暢的情節,透過人物深層心理的描繪,不同身份角色間的對白,與歷史空間場景的營造,帶領讀者體驗想像臺灣社會從舊慣到文明的時代巨變,並及反思現代與傳統的價值變遷。書中主人翁們的思緒、情愫、心理乃至夢境的情節,跨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邊界的日常生活互動、殖民暴力與資本掠奪的無情、反抗行動的荒謬與挫敗、以及新世代與新時代的到來與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緣故地》一書不再屈從於主流歷史的宏大敘事,亦刻意避免史料史實的生硬排比,而是如同年鑑史學名著《蒙大猶》般,以歷史民族誌式的深描詮釋(thick description),讓小人物們更有血肉與生命,更能引發讀者的共鳴共感與歷史想像。如同作者在一篇專訪中所提到的創作宗旨:「我希望角色是能給人力量,更促進對話可能的。這也是歷史小說的意義,透過認識自己歷史的過程,加深自己跟人、土地的連結。在歷史情境裡,人跟人的互動,可以更溫暖也更惆悵,這也是我偏好歷史或武俠小說的地方,我喜歡的美學,都能在裡面揮灑。」
總而言之,《緣故地》是本很好看很耐讀的臺灣歷史小說新作!期待讀者們閱讀時除了理解殖民歷史的複雜深邃,享受小說故事的曲折樂趣,更能想像同理先人們的情感思想與精神世界。從而發揮智慧與勇氣,共同面對當代臺灣另一次歷史變局的挑戰。
目次
推薦序一 開拓臺灣歷史小說的新天地 張隆志
推薦序二 多重宇宙中,迷霧行路者 張惠菁
第一章 術
第二章 新舊
第三章 劉乾
第四章 賣卜
第五章 測量
第六章 林氏蕊
第七章 六十甲子
第八章 造紙燒金
第九章 夢中印字
第十章 巡查的妻女,以及巡查
第十一章 外地人
第十二章 二月初四夜
第十三章 審判與抗爭
後記
參考資料
書摘/試閱
日本軍隊來的時候,已是秋天了。他們許多人都揹著長槍,穿戴洋氣的制服、軍帽、鞋靴,有的另佩掛軍刀。他們駐紮在舊日衙門跟廟宇祠堂,部分神像跟家族牌位只好轉往他處安座。劉乾看見昔日的廟宇改插上日本人白底紅圓的旗幟,不敢相信神明必須讓出居所。日軍每天列隊巡邏跟訓練,他們的休息時間,商店跟小吃店的生意非常好。他發現,那幾間日本人的店,就是為了這些軍人來開的。
也是這時候,民軍跟日軍的爭戰逐漸明顯。
一度民軍趕走林圮埔街上的日軍,但沒有留守,很快就離開。日軍又帶了更多日軍回來,再度控制林圮埔街。日軍在街上抓不到民軍就往內山找,他們庄頭也就開始有日軍出入了。有時守備隊來搜索過一次,憲兵隊又來,警察也上門來問,弄得眾人十分憂懼。傳言憲兵可以依自己判斷,當場處決匪徒,因此他們特別畏懼憲兵。憲兵圍在帽沿上的布料是紅色的,那是辨認憲兵的方法,他們就都叫日本憲兵「紅帽仔」。那時還流傳這樣一首四句聯:「憲兵出門戴紅帽,肩頭揹銃手舉刀,若有歹人即來報,銀票澤山免驚無。」澤山用日本話念,有「很多」的意思,說告密可以拿很多賞金。眾人所恐懼的就不只是「紅帽仔」,也怕身邊有人為了貪那錢財亂講話。
劉乾曾在慚愧祖師爺和觀音佛祖的神壇前長跪,求問神明,何時能了卻這場動亂?卻怎麼也卜不到結果。他換了幾種方式細問,問一個月內可會結束?還是一年內?民軍會贏嗎?日本軍會輸嗎?也是一樣沒有獲得解答。他想可能是神明不要他問這種問題,才會卜不到杯。用竹籌去算,同樣渾沌不明。神明廳外,老一輩的議論說這是「日本反」,跟當年「萬生反」一樣,都是造清朝皇帝的反。亂的這幾年想辦法躲過就是,日本人要經過就讓他們經過。也有到過外地的人說:「這次是整個臺灣都割給日本,日本人到底是要留下的。」
劉乾想到蘇先生,想聽他的意見,正好看見蘇先生在福德祠旁的兩個石碑前發呆。蘇先生見到他說:「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兩篇碑文有個奇怪的地方。可是我又覺得我不該有此想法,所以當初講解給你聽時,我並沒有說出來。坦白說,亦是我怕你又告訴別人,不知會惹出何等禍事。」
「到底是什麼地方呢?還請先生告訴我。我答應先生,一定不會說出去。」
「如今說與不說,倒是沒什麼關係了。你看,原先禁止百姓入山的就是朝廷,開除禁例之後,百姓卻又感念官吏的恩德。當然官吏也是奉朝廷的命令才能開除禁例。為什麼只是恢復成原來的樣子,就讓人感謝?我以前想因為土地都是皇上的,所以這樣講也沒錯,這確實是朝廷的恩惠。可是現在這裡的土地山林已經不再屬於皇上……回頭再來看這兩個石碑,我心中的疑問還是沒有得到解答。」
站在石碑前的蘇先生,像是被什麼困住了。他不明白蘇先生為什麼如此在意兩個久遠前的碑文,而不是眼前日本人的問題。
他問蘇先生關於日本人的事。
蘇先生說:「現在先不要說這個。」
他也沒能從蘇先生那裡得到解答。
山裡零星的戰鬥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有好幾次,劉乾聽見遠方的槍聲、砲聲,但不確定發生在哪裡?只知道某處有人在打仗,也不知道戰爭結束了沒有?傳聞有一個日本軍官為了探險,還有一個清朝將領為了撤退,各自帶人從臺東那一邊走過來。劉乾沒有遇見過這些人。沒隔幾年,又有一個日本學者從這邊走過去,再走回來,據說是為了考察。有碰上的人,言之鑿鑿,劉乾一樣沒能目睹。
在那些看似接近,卻跟他沒有任何交會的來往之間,劉乾一直在設法過日子。雖然他能靠賣卜或幫人念咒治病賺錢,但收入時多時少,沒有人來請的時候,還是得主動去找一些雜工做。
他阿爸跟他說,日本人駐紮在林圮埔街的守備隊在招苦力,去過的人都說是講信用,有錢可拿的,讓他跟著一起去做。那時庄裡好幾個年輕人也想去,就都一起去。他們在守備隊裡面,看到大砲、槍和彈藥,都是能拿來殺人的東西。他們的工作很雜,有時運送補給品,有時鋪橋造路,有時被派去戰線上挖坑洞。會有通譯解釋他們要做的事,讓他們盡量做得正確。劉乾因此學會了一點日本話,偶爾也能直接聽懂。不過他發現,日本人跟日本人之間有時講話的腔調亦差很多。當他學會一些,換另一個人來講,又都聽不懂了。
這份苦力工作,他一開始覺得還不錯。體力撐得住,又都能固定拿到錢,也見識到新奇的東西,還能學日本話。原本他對聲音的記性就好,以前背誦經咒也是這樣,總是用聲音去記。這次卻沒有學得那麼快。固定的幾個命令和器物名稱早就熟悉,當他想要聽懂更複雜的語句,關乎想法、判斷的,卻好似被什麼阻擋著,無法像以前那樣,即使不懂意思也能先單純記住聲音。
有一個常常出入守備隊的年輕日本商人會講臺灣話,而且喜歡找人練習臺灣話,聽說也是來臺灣才現學現賣的。苦力們對他印象都不錯。他的名字叫赤司初太郎,原來也是軍人,因為受傷改當伙頭兵,來到林圮埔的時候,離開軍隊到園田商店幫忙。後來園田商店的頭家過世,他就繼承這間商店,變成新頭家,繼續做軍方的生意。看見赤司跟苦力們聊天的笑容時,劉乾想,因為能聽懂彼此的語言而傳達想法是有可能的。
當他說起這個想法,一起當苦力的同伴勸他不要太過天真。
「一件事說給你聽。去年冬天,林圮埔的撫墾署長帶人到阿里山那一帶的番境巡視,不知他聽了什麼,讓手下聯合番人在清水溪上游沿途殺害了二十幾個居住在那裡的漢人,說那些人都是民軍的奸細。他們還活著的家裡人下山去告官,事情鬧很大,本來應該當殺人罪處理,但最後那個署長只有丟掉官職。跟他一起去的通事,則是被禁止再進入番境做通事的工作。」
「為什麼通事要被處罰呢?」
「說因為他翻譯錯誤,傳達了錯誤的消息,才導致那個署長做錯判斷。把責任全推到通事身上。你想,他要把番語翻譯成清國的官話,日本人這邊要再把清國的官話譯成日本話,他們真的知道彼此的意思嗎?」
「……」
「也不是叫你不要學日本話啦,就是要小心。我們講同種話的人都會有誤會了,何況是語言不通的。那件事,說不定就只是殺人的藉口。」
同伴口中,語言翻譯過程的落差,竟足以害命,曾讓劉乾一時對學習日本話感到退卻。在守備隊的工作結束後,劉乾繼續跟著父親轉到憲兵隊屯駐所當苦力。在憲兵隊屯駐所,他並不特別害怕這些憲兵,甚至感覺到彼此有同伴的關係,他又希望自己能聽懂日本話了。但他也深知,如果某天夜裡憲兵來敲他的家門,他一定會非常害怕。
那段時間,對於人的好壞、互相了解的可能,他時常感到錯亂。
有一次他和另一位苦力送物資到病院。這病院以前是觀音亭,因為被日軍徵調作為病院,原來祀的觀音佛祖鎮殿本尊、分身、韋馱爺、伽藍爺、十八羅漢都遷祀到同一條街的媽祖宮後殿,只剩下門板、外牆、屋簷還留有廟的形式。裡頭靠牆兩側是釘成大通鋪的木板病床,左、右龍柱中間擺滿了醫療工作用的桌椅、器具。
劉乾和同伴走進那裡時,刺鼻的陌生氣味取代了原有的焚香味,不知道是桌上那些玻璃瓶裡面裝的東西,還是角落桶子裡使用過的繃帶、棉球所散發出來的味道?一個滿臉病容看不出哪裡受傷的人,坐在中門的門檻上,拿著一支短筆,捧著一本簿冊,似乎在畫街道的模樣。劉乾沒看過那樣的筆,沒有筆毛,也不用沾墨汁。他握筆的姿勢跟畫出來的線條,還有畫街道這件事,對劉乾來說,都是陌生的。
劉乾在意他坐在門檻上。門檻只能跨過,不能踩踏,而且那是中門,原是給神明走的路。縱然現在神明遷居他處,他見了還是很不舒服,覺得這樣不好。有神靈在的感受,這裡曾經香煙繚繞、信徒熱絡進出的模樣,仍很深刻地留存在他的思緒裡,跟眼前的景象交疊,彷彿無數舊日的痕跡流動而過。但他又不敢去跟那個人說。一來,他懂的日本話很難完整傳達他的想法;二來,就算能傳達,對方會不會因此生氣,甚至一刀將他斬殺呢?
那個畫畫的人看見劉乾在看他,揮手讓劉乾靠近一些。把畫拿給劉乾看,問他像不像?劉乾點點頭,最後什麼也沒說。
溫柔與殘暴,理解與統治,相悖的情緒糾纏著劉乾。
劉乾夢見一只壁鐘,下緣的鐘擺不停晃動。
一下子他在守備隊,一下子在憲兵隊,不管從哪個角度都能看見這只壁鐘。
圓圓的盤面上,指針有快有慢自己在動,經過的刻度上寫著某種文字,但他讀不出那上面的時間。他老是在想,現在是什麼時辰?但沒有一個能讓他知道時辰的地方。他找不到線香,沒有看到線香在燒,他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工頭突然從屋舍轉角處跳出來罵他,口氣非常緊張,提醒他看那壁鐘,說幾點鐘之前要完成工作。但他不知道要做什麼,他一邊亂轉一邊想著完了,我無法完成工作。那個叫赤司的日本人滿臉笑容對著他,說一連串他聽不懂的話。赤司不是會說臺灣話嗎?怎麼現在又一直講日本話了?一個憲兵走出來,端起長槍,瞄準了他。他急著大喊:「救命!」但赤司只是一直在笑。
他不斷地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劉乾發現自己的感應出了問題。他很久沒有誦念經咒,他不再感覺到好的氣或壞的氣。那些原本每天都會感覺到的消失不見,他的眼睛像被矇住了一樣。他不知道這是因為他變遲鈍,還是有人破壞了原本可以顯現出來的東西?周遭看起來的模樣,就像病院那個人所畫的那種圖,是能擦掉的。被人抹去了幾筆,又添加了幾筆,這樣慢慢偷換過去,逐漸變成一張完全不一樣的畫了。
他跟著阿爸再轉到林內街的憲兵隊工作。那陣子因為戊戌年大水災造成的損害很嚴重,需要的苦力很多。他們幫忙修復道路、橋梁、屋舍,工作多到不用煩惱沒工可做。但劉乾越發緊張不安,感覺到自己擁有的術力逐漸消失,心裡一直想著不要再去做,不能那樣過活。可是每天早上,想起屯駐所的壁鐘就渾身不自在。總想,別人已經出發了,等等又會做什麼工;不去也不太好,很多人等著有人來幫忙;如果最近沒別的事,還是去多賺點錢好,說不定哪天日本人的工做完了,就沒這樣的機會……如此煎熬著。
此時正好笋仔林庄的人到新寮街找他,留了話請他幫忙念咒治病。他於是暫時離開林內憲兵隊,前往笋仔林庄幫劉萬池治病。在幫劉萬池治病那段時間,他更加確認自己的術力發生問題。雖然別人都說他厲害,但他知道自己以前更厲害。當他看到劉賜被一棵大樹吞入的景象,自己也嚇了一跳,因為他已經很久都沒有看到什麼了。
劉賜瘦削細緻的臉孔微微張開嘴的時候,細長的眼裡,深黑色的瞳眸看起來像有無止盡的迷茫。劉乾忽然就覺得,我能使他聽我的話。
但是為什麼?我為什麼要使他聽我的話?
那偶然升起的念頭,劉乾仔細再想,並沒有什麼道理,可又清楚強烈的猶若一種預兆,或是早已發生卻不復記憶的前世。
他確信,他和劉賜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轉世攜來的牽繫。
唯獨一件事令他介意,笋仔林庄的人接受東方有貴人的指示時,他人其實是在笋仔林庄西方的林內街。他真是那個神明指示的貴人?一件事可以是錯誤的開始,卻走向對的結果嗎?
在劉賜身旁,他覺得自己越來越好。彷彿劉賜分享了某種無形的、珍貴的東西給他,或是喚醒了他什麼。他感覺原先的自己又慢慢回來,決心養回自己的術力,不願再去幫日本人做苦力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