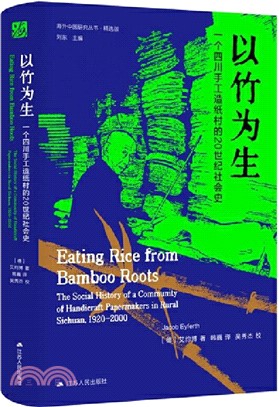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進入20世紀以後,夾江的手工造紙技術面臨著一系列重大衝擊,改朝換代、戰爭、革命、集體化、現代化的理念和建設實踐、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這些發生在“城鄉鴻溝”宏觀背景下的每一項重大社會變革都促使造紙人在技術層面和社會層面上重新定義身份認同。本書追蹤了知識分配在一個世紀內的變遷,這導致了對技能的控制權大量地從農村轉向城市,從初級生產者轉向管理精英,從女人轉向男人。在作者看來,造紙技能是一種資源,是分配和爭奪的對象。作者從這一獨特的角度出發,從一項傳統技藝個案入手來介入對大問題的思考:革命、建國以及市場化等現代化進程如何改變著20世紀的中國農村。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艾約博這本出色而重要的著作所包含的內容遠遠超出了其副標題所述。作者圍繞著四川著名造紙中心夾江縣的手工造紙業展開了廣泛的田野調查和檔案研究,對思考現代國家建設、精英技術官僚的崛起和鄉村手工業之間的關係提出了新的方法,改變了我們評估20世紀中國多重革命意義的方式。
——布朗大學歷史系教授包筠雅(Cynthia Brokaw)
這項研究詳細而豐富地描繪了一個手工藝社群如何經得起社會和經濟的風雲變幻。艾約博的寫作具有田野調查才有的權威性和親切感。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杜博思(Thomas DuBois)
序
導論
本書勾勒了一個四川農村手工技藝從業者社區20世紀的社會變遷史。村莊落地處成都與樂山之間的夾江縣。在將竹子和其他纖維物轉化為柔軟而具有韌性的紙張過程中,男人和女人們需要完成的那些耗時而艱辛的工作,在這部社會史中佔據著核心位置。造紙是一項要求有高度技能的工作,而「技能」這個主題會以兩種互相關聯的線索貫穿全書。我最為關注的是那些與生產相關的技能,這些技能也許是技術性的(如何打漿、如何刷紙),也許是社會性的(如何給產品找到買主、如何與鄰居相處)。除此之外,我也對那些可以被稱為日常生活技能的內容感興趣:儘管有戰爭、革命、極度迅疾的社會和經濟轉變,那些讓夾江的造紙人得以存活下來,甚至有時候還能做到繁榮程度更甚從前的慣常策略(quotidianstrategies)。這些不同類型的技能彼此連結在一起。去聚焦於一種技能勞動的具體細節,讓我們有可能透徹地了解鄉村民眾的生活世界。不然的話,他們所經驗的東西可能還會隱而不顯。
儘管我聚焦於某一特定地方的物質條件與日常生活,並將本書的研究置於中國鄉村研究這一豐富的學術傳統之內,但我還是力圖追求在一個更為宏大的層面上提出論點。在全書中一以貫之的論點是,中國的革命——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系列彼此關聯的政治、社會和技術上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技能、知識、技術掌控的再分配,正如其對土地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一樣;發生在20世紀的對技能進行爭奪的結果是,技術掌控權大規模地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一線生產者手中轉移到管理層精英手中,從女性身上轉移到男性身上。
這項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國的城鄉分野——這是研究當代中國的大學生們耳熟能詳的:制度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鴻溝將農村人(包括那些數以千計來到城市裡工作生活,但是因為戶籍制度還和他們的農村老家綁在一起的人)與城市人區分開來。這道鴻溝之巨大,不亞於中國城市居民與西方國家城市居民之間的距離。儘管造成這一城鄉分野的製度安排在近年來有所變化,但是這鴻溝還沒有任何趨於彌合的跡象。我在本書中所持的論點是:這種城鄉分野部分地是由於城鄉之間在知識分配上的變化所造成的,這些變化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在19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更得以強化。目前,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在這一點上有共識:中國經歷了一個長長的原工業化進程,與歷史記載中西歐和日本所經歷的情形並無二致。中國的清朝(1644—1911年)和民國(1911—1944年)時期與日本的德川幕府時期、歐洲19世紀以前的情形相似,大部分製造品來自農村,出自農民家庭或那些半專業化的農民手工業者。與歐洲和日本形成反差的是:在19世紀末的西歐和日本,大多數手工製品已經為工廠產品所取代,而中國的手工業則相對來說完好地保持到20世紀中期。毛派歷史闡釋學說堅持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後大量湧入中國的廉價外國商品壓垮了傳統的中國手工業,但是現有的材料表明,民國期間“在絕對數量上,手工業總體產出保持不變甚至有所增加」,儘管它在經濟中的相對份額有所減少,因為這段期間形成了一個現代工業部門。在中國遭受大蕭條和戰爭侵害之前最後一個「正常」年景的1933年,手工業仍佔工業產出的四分之三。甚至到了1952年,當中國的現代工業部門已經開始從戰爭和革命帶來的後果當中得以恢復之時,按照當時的價格(重工業被給予很大的權重性)計算,手工業仍佔工業總產值的42%;若以戰前的價格計算,則高達令人驚異的68%。
儘管手工業擁有強大的經濟持久力,或者恰巧因為這種持久力,很多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在1900年後主政中國的精英們反而認為中國鄉村工業存在著嚴重問題。 1895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帶來的羞辱以及西方與日本工業化先例的激勵,促使中國的精英們開始考慮將「經濟」當作國與國競爭的展示舞台———在那個時代,經濟尚且被視為一個與社會、文化、道德割裂的獨立範疇。他們從西歐和日本看到,國民經濟由若干界線分明然而又彼此互補的領域組成。工業是主導部門,因為單有工業就能推動國家走向更美好的未來。這是通常的城市圖景,其根基不在農民的家戶,而是在大型的、機械化的工廠。相比之下,鄉下是農民的所在地,他們為國家提供糧食,不能夠也不應該在工業品產出方面佔據要位。這種將經濟作為有所區分的城鄉二元分野的視角並不能正確地描繪出真實的中國,但這在改變中國方面是一個強有力的藥方。依照詹姆斯‧史考特(JamesScott)的說法,也許我們最好將其視為「國家式簡易化」(statesimplification)。斯科特認為,國家現代化的傾向是將複雜的社會事實轉換為簡單化的表徵——地圖、統計數字、人口登記,這些表徵使得社會變得「清晰」,因而也容易控制。在某種程度上,這類簡化性做法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國家將社會事實的抽象化表徵與基本面上的事實混淆在一起,或者甚至認為這是某種更為高級的秩序形式,以致讓那些可觀察的事實必須屈從於此,這樣就會引發很大問題。在中國,這導致了形成經濟部門的過程被延長。在這樣的進程中,中國的村落和城市被迫更為近切地屈從於那些想像中的理想類型。這個過程開始於國民黨政府的南京時代(1927—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滿腔熱忱地相信,有必要對中國經濟實行一種計劃之下的轉型。這項做法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達到巔峰:那時農村與城市分屬於不同的行政管理範圍;在治理上實行不同的規章制度;全部農村人口,無論其職業如何都被歸類為農民;幾乎所有尚存於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之間的關聯都被切斷。這些年來自四川的兩個軼事性質的觀察可以很好地表明城鄉之間的鴻溝之深:在20世紀80年代末,因為營養不良,18歲的農村小伙子其身高要比城市同齡人矮8厘米。這一事實把他們標記成兩種不同類型的人。農村人難得有一次進城的機會,然而馬上就會被認出來是農村人。在1990年代,夾江人在祭奠已故親人時焚燒仿製的城市戶口本,以此希望這會讓他們來世免於再投胎為農民。
經過20餘年的市場改革,某些分隔城鄉世界的壁壘確已日漸消失,但另外一些則原封未動。由農村湧向城市的移民潮的確在大規模地發生(截至2003年,估計有1.4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佔當時中國總人口的10%),與之並存的是,這些農民被系統地排除在生活地的權利體系之外。戶籍制度原本是要限制人口遷移,現在則用來讓移民者難以進入他們在新居住地的公民權體系,他們以自己的工作為當地的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體係做出經濟上的貢獻,然而他們卻被拒絕享有這些社會保障權利。從1990年代開始,中央政府就反覆宣稱要取消戶籍制度,但是大多數市政府搶在中央改革之先發布了明顯地區分和排斥外來人口的規定。直到2008年,專家們認為,那堵將中國農村與城市分離開的「看不見的牆」還留在那裡。此外,這種城鄉分隔主要不再立足於行政管理上的規則,取而代之的是在修辭建構上將農村人視為準族群上的異類: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必須得容忍這些人留在城市裡,但是不能將他們吸收進城市人口當中。在這看法中居於核心之處的是關於「素質」的討論:「素質」一詞以循環論證的方式被定義為一個人所具有的正面質性,而這正是中國農村大眾所缺乏的。就這樣,這些幫助建設和維護中國的城市,以自己的勞動支撐著城市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農村人,被永久地放置在價值等級序列的最底端。
技藝純熟的農民
城鄉差異得以產生並延續,原因在於整個社會對農村人形成的刻板印象:農村人是一群見識如井底之蛙的農民,他們的活動囿於當地生活範圍,與他們有所關聯的主要紐帶是以地域來定義的社區以及他們耕耘的土地,他們不加入地區性或全國性的交換網絡,因此他們也沒有能力參與公共生活。這種刻板印象的出現可以回溯到五四運動那一代人,這些反傳統、反底層文化的激進知識分子們認為,中國的農村人口是「在文化上不同的、異類的'他者',他們懈怠、無助、蒙昧,深陷於那些醜陋而且在根本上一無用處的風俗當中,極其需要接受教育和文化改造」。對於「五四」世代的改革者們以及他們的思想繼承者來說,農民的生活從本質上是抱殘守缺的,是對不同的(但是總是艱苦的)當地條件的被動適應。商業本身是一種敵對的力量,這些自給自足的農民在意識上不諳此道,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恐懼而無知,每次與精明的城裡商人打交道都處處碰壁。儘管這種認為農民囿於土地、根植於土地的成見從來都沒能正確地描繪中國農村的真實,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當千百萬農村人加入到中國的工業和後工業經濟當中之時,這種完全沒有依據的成見還是一直延續到今天。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民族誌著作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描寫:
農民十分依戀土地,土地就是家鄉,他們自己就像稻穀,土地是他們生長的基礎和死後的歸宿。年紀大的農民住不慣城市的樓房,他們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樓上不習慣,沾不到地氣。」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們不是在潛意識裡將自己當作植物,這種觀念無論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實上農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沒有時間和歷史的輪迴。
作者以植物來類比農村人,並無對他們的貶損之意。恰好相反,這種「根植性」恰好是更為自然的生存狀態的明證。這種解讀方式與19世紀歐洲人對西方農民的描寫遙相呼應:在這裡,農民也被用來代表一種比城市居民更少一些異化的、更為固定和靜態的生活方式,一個只做必需之事的國度,與那種遍布蹩腳的自由、問題成堆的選擇的城市王國形成對比。我堅持認為,這只是一種臆想而已。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並不比其他有技能的生產者與他們的生產資料的關係更為直接,更為“渾然天成”。人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必然受到技術和知識的調停,而技術和知識在根本上是屬於人的、社會的範疇。土地只有在能帶來收穫時才會有其價值,而這一產出過程需要有技能介入;這些產出品只有在轉化成可消費或者可交換的物品時才有價值,而這也要求有技能。我認為,鄉村(以及在任何其他地方)的社會生活以在經濟上有用之技能的生產和再生產為核心而展開,因為不管人們居住在哪裡,那裡的資源基礎如何,離開技能任何經濟活動都不可能。
社會組織與技能生產群體
法國技術人類學家弗朗索瓦·席格特(FrançoisSigaut)堅定地認為,一切社會組織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關乎技能生產的:
從技術角度來看,技能生產群組是所有社會中存在的基本社會單元,因為沒有技術的社會是難以想像的。這一基本單元可以有諸多不同的形式,與其他單元諸如家庭、居住群組、年齡群組等形成極其多樣的組合。所有這些組合都是所涉技藝種類的某種功能,是加之於技能上的社會價值、本土關於學習的理念、依據社會地位和性別來分派的活動,諸如此類。理想情況下,所有社會的結構都應該從頭開始構建,將這一必不可少的,然而迄今為止尚未被關注的單元考慮進去。顯然我們還差得很遠。
將技藝再生產視為社會群組的核心功能,這的確能改變我們對社會組織的理解。讓我們以親屬關係為例:中國的親屬制度通常被認為是由血親形成的來進行儀式與政治活動的組織,他們累積共有資源,其中以土地最為典型。如果我們截取一個即時斷面來分析就可以看到,對地方知識的保護、將這些知識傳承給年輕一代、依據性別和輩分來分派活計,是在許多中國親屬群組當中更為重要的活動。正如我在本書第三章中要詳細描述的那樣,夾江的大多數造紙人(“槽戶”)社區,都由彼此有血緣關係的男性和他們的家庭組成。親屬關係與技術能力高度重疊,當地人典型的說法是,用親屬稱謂來定義擁有技能的群體:「我們家族祖祖輩輩抄過紙。」然而,我們在造紙作坊裡看到的親屬關係,與那些在研究文獻中被描寫的親屬關係大為不同。實際生活中造紙人的親屬關係並不在意對土地和地位的訴求,而是著重於在一個工坊之內和在不同的工坊之間建立工作關係以及與資訊管理。造紙人更為強調的是在橫向上同輩男性之間的紐帶,以及晚輩與長輩男性間的相互履責,而不是去強調沿父系血緣的縱向關係。這種容括性親屬關係實踐帶來的結果是,不光知識技能在血親之間更為容易流通,同時也強化了親屬與非親屬之間的邊界線,從而使得知識保留在親屬群體手中。
儘管我在夾江觀察到的親屬實踐在造紙活動中顯示出具有講求實效的功能,但是這種情形是否為特殊技術需求所導致的,抑或造紙人的親屬實踐與鄰區從事農業活動者的親屬實踐有所不同,對此我還不能有所定論。也許,這種親屬實踐-鼓勵親屬間的合作與知識共享-普遍存在卻不為人注意,是因為它們不符合慣常的關於中國親屬制度的觀點:中國的親屬關係主要被認為對土地和權力有法理上的訴求,以不同繼嗣群體之間的競爭為特徵。在我們將農村人看作以土地為根基的農民時,一些社會組織的類型就被隱藏起來了,而透過技能這一視角卻可以幫助我們看到這些隱藏的社會組織類型。
「農民性」(peasantness)的模式
社會整合源自於行之有效的區分這一觀點,在社會學家塗爾幹(Emile Durkheim)那裡被闡釋得最為清晰,不過這一觀點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那裡:「國家並非簡單地由眾人組成,而是由不同類型的人組成,因為相同之人無法形成國家。 「固定僵化,一成不變」——這是馬克思對農民生活的描寫——使得人與人隔絕開來,使得他們對公共生活顯得束手無策。在晚期帝制的中國,專業化和交換已經十分常見,大部分工業品都出自鄉村專業化或者半專業化的工匠之手。明清以及民國初期的政府認識到這一事實,因而在總體上支持鄉村手工業。專門化被看作是混合型農村經濟的必要因素,手工業和副業被認為有助於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因為它們可以帶來收入,讓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仍然留在土地上。只有當專業化生產將過多勞動力從農業上吸引過來並幹擾到農業經濟,或者那些不受管束的男性僱工過度集中造成危險性隱患時,政府才不鼓勵專業化生產。甚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從中獲得足夠大的財政收益或者商業利益,政府也會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根據曾小萍(MadeleineZelin)的估計,當時自貢境內最大的鹽場(離夾江縣約100公里)招工人數在6.8萬到9.8萬之間,是19世紀世界上最大的產業工人聚集地之一。
專業化沒能產生「公民權」(citizenship)——這一概念直到19世紀90年代才在中國出現,甚至那些最為激進的共和派人物也只是在最為抽象的意義上來考慮將農村人視為「公民」。然而,專業化將農村人與一種物品和符號經濟聯結起來,而這種經濟已經從偏僻的村落延展到權力中心地帶。夾江的造紙人一直很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所生產的不光是一種有用途的物品,也是中國書寫文化和官僚文化的一種象徵物。 300多年來,他們這裡產出的「貢紙」是科舉考試中四川省鄉試的專用紙,即便在科舉考試於1905年被廢除以後,國家以及省級政府部門依然對夾江造紙業興趣盎然,因為他們也需要紙張。誠然,在建構文化紐帶方面,紙張比其他商品顯得更為合適;然而,所有物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注入了含義,因而可以被看作傳達社會訴求與文化訴求的介質。例如,紡織業這一最為重要的鄉村手工藝,與勞動的性別分工、道德秩序和社會穩定性連在一起,工藝生產者會援引這些準則來護衛自己的行當。正如我們在本書的第四章中可以看到的,夾江的造紙人利用文化上的訴求來吸引省級,甚至是國家級精英的關注,遊說他們為自己減免稅收。
將地方性的特別產出視為正常的、必要的、積極的這一看法,在20世紀的頭幾十年裡開始發生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些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堅定不移地認為中國需要迅速工業化,來保衛自己不受西方和日本的侵害。在20世紀初期,工業被認為是在達爾文式的生存鬥爭中拯救國家的一種手段(“實業救國”)。同時,城市菁英認為身為農民的鄉下人目光短淺、愚蠢無知,不足以將重要的國家資源交給他們。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她對山西的研究中發現,在清末以及民國時期,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們帶著如此強烈的意圖去發展「工業」(在機械化生產這一意義上),以至於他們無視當時實際存在而且生機盎然的產業,有時甚至有意去壓制它們以便讓現代風格的生產獲得青睞(這種做法經常成效甚微)。政府對小規模產業的敵意導致了製造業集中在城市裡,而先前的混合型鄉村經濟變成了單一的農業經濟。
近年來的許多研究都顯示,中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在1949年之前與之後有著根本連續性。共產黨也將「搶佔工業化製高點」作為其追求的戰略,將所有努力都集中於大規模的、現代的、以城市為主的工業上,尤其是在國防工業上,這與此前的國民黨政府並無二致。在國際環境充滿敵意、物資極度短缺的條件下,共產黨的計劃經濟締造者們制定了一個分化的經濟體系,即讓農村的經濟部門從屬於帶有保護層的、受到保護的城市經濟部門。其基本特徵廣為人知:這個體係自1953年起以國家規定的固定價格從農村廉價收購糧食、棉花和其他城市經濟所需的原材料,而農業所需的原材料以及消費品都維持著高價,以保證國營工廠有穩定的利潤。為了防止農村人遷移到城市裡並由此沖淡現代化的收益,國家將農村人口禁錮在他們出生或(女性)出嫁到的村莊裡。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移民和(經濟上的)多元化是發家致富的常規線路,如今這兩條途徑受到限制甚至最終被禁止了。城市居民享有由國家來保證的生計基礎,有時候還有經由工作單位而發放的不可小覷的福利;與此形成反差的是,農村人的生活來源只能依賴當地的資源供給以及反复無常的氣候條件。政府實行了許多措施來實現毛澤東提出來的「兩條腿走路」的政策,即同時發展農業和小規模工業。然而,這項政策的目標是加強而不是去減少農村的自給自足經濟。毛派政策中理想化的鄉村是:自力更生,實行相互獨立的集體生產形式,為城市提供餘糧和其他原材料,但不向城市有任何索取。 70年代的公社和大隊的企業,即後毛澤東時代鄉鎮工業繁榮的前身,其設計的目標是“服務於農業”,明文規定禁止它們與國有企業爭奪原材料、資本或者市場。
我在這裡想要指出來的,不光是農村居民的物質生活條件相對不如城市居民——儘管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比農村居民高出兩到三倍;我還想指出的是,他們被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到人事政策當中。絕大多數城市居民都隸屬於工作單位,這些單位高度專業化,牢牢地融入地域上和功能上的等級序列當中。由於國家計劃經濟體系將產業重複保持在最小的程度上,大多數工作單位在某一區域內都是獨此一家:在某個省或者某個州里只有唯一一家滾珠軸承廠或者建築公司。工作單位也沿著具有功能性作用的「條」(與地域性的「區塊」相對)整合在一起,其方式是:每一個工作單位都依賴於同一管理體系當中的上游和下游單位。在這個複雜而嚴格的結構中,一個地方的問題可以很容易波及到整個體系的各個角落。在供應鏈上的任何一處因為任何問題引起的停滯或者放緩,都是關於相互依賴性的實例課堂,這也給工人們帶來自己的不可或缺感。農村居民面對的情況與此正好形成反差: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壓制專業化,將村落變成自給自足的單元,將農村人從那些他們曾經是其中一部分的互相依賴和交換的網絡中剔除出去。農民作為一個階級仍然是被需要的,在某種抽象意義上是「革命的」,但是每一個單獨的農民個體都與整體有著非特定的關係。他們與村落共同體之外的人沒有關聯,每個人面前只有兩個方向:向下朝向土地,向上朝向國家。如果說農民還有所差異的話,那也只是因為他們適應了不同的地方性條件,正如長在沙土里和長在沃土裡的捲心菜之間的區別一樣。將農村居民視為自給自足的農民這一觀點,一直塑造著城市居民對農民的感知,這一觀點也為將農民排除於完全公民權之外提供了理由。
目次
表格、示意圖、圖片目錄
度量衡及貨幣
致謝
導論
技藝嫻熟的農民
社會組織與技能生產群體
「農民性」(peasantness)的模式
兩種類型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
技能的本質
田野調查及資料情況
本書的結構
第一章 定位技能
造紙技術
造紙的勞務量需求
勞動的性別分工和代際分工
家庭勞力的補充、培訓和管控
僱工的招募、訓練和管控
勞務交換與互助原則
公開和保密
性別與技術的宗親控制
夾江造紙業的技術定位
第二章 夾江山區的社區和宗族
居住區
保甲制
袍哥會
宗教組織
暴力與權力
造紙地區的親屬關係
夾江的正式親屬組織
輩分順序
親屬關係派上用場
技能的共同體
第三章 階級與貿易
「大戶」:石子青的工坊
階級與擁有土地
市場
信貸
造紙區的市場與社區
第四章 從匠人到農民
紙匠與清朝的國家
清代的工藝控制和自我管理
民國初年利益代表模式的變遷
1936—1937年和1941—1942年的糧食危機
帝國主義與“中國手工業的崩潰”
槽戶-改革的阻撓者
自上而下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改革
第五章 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造紙人,1949—1958年
工業改造與社會主義國家
造紙業重組:規劃與當務之急
造紙地區的土地改革
向集體造紙過渡:1952—1956年
踏入國營部門
合作社下的生活
對技能的提取
專家說了算
第六章 「大躍進」、困難時期與農村的「去工業化」
恢復…
…再次衰退
對手工紙的需求
挖竹根
在生產隊管理下的生活
夾江的產業化和去產業化
第七章 家庭生產的回歸
回歸到家庭工坊
家庭作坊的鞏固
一個小型技術變革
家庭、政府和技術變革
石堰的紙張生產:一個案例
改造過的家庭作坊
僱工
換工與互助
第八章 改革開放時期的紙張貿易與鄉村產業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遊擊」貿易
石榮軒
石勝新
石威方
彭春斌
從「行商」到「坐商」
商人與槽戶的關係
鄉鎮與農村工業化
盲目發展:石堰的鄉村企業
鄉鎮企業發展的得與失
行政和經濟上的分化
家庭工廠
專有技術
2000年以來的變化
第九章 加檔橋石碑
石碑
對親戚講輩分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親族關係、職業和身份認同
結語
國家的視角,市場的嗅覺
堅壁起來的公用資源
附錄一
附錄二
文獻資料目錄
譯校後記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