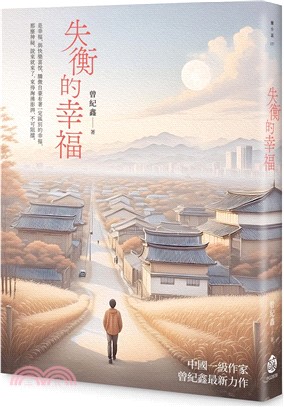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幸福是什麼?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是否即意味著擁有幸福人生?
而當生活遭遇現實壓力,幸福又能帶領我們去往何處?
中國一級作家曾紀鑫長篇小說作品,透過中國農村與城市的變遷,剖析「幸福」的真諦!
★ 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是否即意味著擁有幸福人生?而當生活遭遇現實壓力,幸福又能帶領我們去往何處?
孟慶來一出生就失去了父親,母親的艱難、同儕的欺侮,都令他覺得自己好似天生就缺少幸福。幸福於孟慶來而言,竟是如此神祕而飄忽,它總是來得少,去得快,還來不及咀嚼回味,就轉瞬即逝。
出身馬灣村的的孟慶來加入軍隊,進入國營鋼廠工作,娶了城市姑娘,於古冶市落地生根,甚至因緣際會成為了一名工人作家。而孟慶來也不忘在人生中追尋每一個能感受幸福的時刻,這輩子痛痛快快、瀟瀟灑灑地走一回──有過激情與迸發,也有過沸騰與燃燒……既如此,他便知足、幸福了!
中國一級作家曾紀鑫,以「幸福」為題,描寫二十世紀的中國農人,前往工業城市打拚的酸甜苦辣;並藉由一起攻擊案件的偵辦過程,探討「幸福」的本質與意義。
幸福是什麼?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是否即意味著擁有幸福人生?
而當生活遭遇現實壓力,幸福又能帶領我們去往何處?
中國一級作家曾紀鑫長篇小說作品,透過中國農村與城市的變遷,剖析「幸福」的真諦!
作者簡介
曾紀鑫
中國一級作家,福建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寫作文化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出版專著三十多部,多次獲中國國家、省市級獎勵,著作進入中國熱書排行榜。其作品被報刊、圖書廣為選載、連載並入選《大學語文》教材,中國媒體廣泛關注、評論,匯為《我們活在歷史中.曾紀鑫創作論》、《萬年寫入胸懷間.曾紀鑫作品研究》等六部論文集、評論集出版。代表作有文化歷史散文《千秋家國夢》、《歷史的刀鋒》、《千古大變局》,長篇小說《楚莊紀事》、《風流的駝哥》,長篇人物傳記《晚明風骨.袁宏道傳》、《抗倭名將俞大猷》,論著《遲熟之果.中國戲劇發展與反思》等。
中國一級作家,福建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寫作文化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出版專著三十多部,多次獲中國國家、省市級獎勵,著作進入中國熱書排行榜。其作品被報刊、圖書廣為選載、連載並入選《大學語文》教材,中國媒體廣泛關注、評論,匯為《我們活在歷史中.曾紀鑫創作論》、《萬年寫入胸懷間.曾紀鑫作品研究》等六部論文集、評論集出版。代表作有文化歷史散文《千秋家國夢》、《歷史的刀鋒》、《千古大變局》,長篇小說《楚莊紀事》、《風流的駝哥》,長篇人物傳記《晚明風骨.袁宏道傳》、《抗倭名將俞大猷》,論著《遲熟之果.中國戲劇發展與反思》等。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書摘/試閱
「抓歹徒,抓歹徒啊──」
叫過一陣,阮巧巧望一眼倒在草叢中的孟慶來,突然嚇得不知所措。面對做夢也沒想過的突發暴力事件,她的思維一時間陷入不可理喻的驚恐與一塌糊塗的混亂。
她竭力調整失控的情緒,使自己鎮靜下來,將剛剛發生的留在腦海裡的片斷綴合在一起,盡可能地理出一條完整的線索,尋出它們的真實意義。暴風雨般的激情……達至快樂峰巔的交媾……關閉外界視域後的內心自足與享受……無力的四肢使得全身猶如一癱稀泥……歹徒的突然襲擊……血!啊,血!當她的目光移向孟慶來後腦,聚焦於鮮血依然汩汩湧流不止的創洞時,不禁如夢初醒般回到現實──嚴酷得令她不忍目睹的現實。
除了盡快應對、收拾殘局外,阮巧巧別無選擇!
一旦明白了眼前發生的一切,阮巧巧不禁變得異常冷靜起來。她一把抓過自己脫在一旁的衣褲,並沒有馬上將它們套在身上,而是找出放於一旁的隨身攜帶的手提包,雙手顫抖著打開,掏出一個香氣撲鼻且繡有花朵的白色手帕,揉成一團,按住孟慶來被石塊砸出的如洞穴般的傷口。然後,才不緊不慢地穿上衣褲,還不忘將散亂的頭髮理了理。
手帕很快就被滲出的鮮血染成紅色,阮巧巧按了按,揭開,蹲下身子,仔細看了看傷口,血似乎不再往外流淌,至少是流得細小而緩慢了。於是,她不得不開始下一步的「工作」了,將孟慶來的衣褲「復原」。好在他穿得不多,上身一件背心,一件襯衫;下身一條短褲,一條西褲。然而,孟慶來有氣無力地呻吟著,全身癱軟得無法配合,她只有拼出全身力氣,使出渾身解數,費盡周折後才一件一件地重新給他穿上。這看似簡單的「工作」弄得阮巧巧一身臭汗,扶著一旁的松樹直喘粗氣。正喘著,突然發現了一個不該出現的失誤,下身的西褲還敞開著呢,深藍色的內褲隱約可見,她趕緊過去捏住拉鍊扣,一點一點地將外褲拉鍊合上。
在緊張地做著這一切的時候,一個應對現實的謊言,也在阮巧巧心中漸成雛型。
她又細心地將周圍的一切檢查了一番,盡可能地不給他人留下證據與把柄。她將他們剛才瘋狂做愛時弄得倒伏的青草盡可能地扶正、復原,正整理著,右腳踩在一塊硬硬的石頭上,她撥開草叢,發現了一塊碩大的尖角石塊,還發現了石塊上已呈暗紅色的斑斑血痕。這無疑就是兇手剛才使用的兇器了,她拿在手中感覺沉沉的,心頭也隨之一沉,這塊石頭,是兇手準備好了一直隨身帶著的,還是在山上臨時撿拾的呢?念頭像火星般一閃即逝,阮巧巧的思維,轉瞬般又移到了孟慶來身上。
異常冷靜的她,做完了自認為該做的一切後,最為關注的,自然就是孟慶來的生命了。
流了那麼多的血,直到現在還沒甦醒,就連呻吟也止息了,傷勢一定十分嚴重!他還活著嗎?還有救嗎?不能再耽擱了,一定要想方設法將他盡快送到醫院。
這樣地想著時,阮巧巧不禁湊在他耳邊「慶來,慶來」直叫喚。孟慶來雙眼閉合,似乎半點反應也沒有。她急了,撥了撥孟慶來的眼皮,又將右手食指放在他鼻下,嗯,還有那麼一點微弱的氣息,又摸了摸他的胸口,哦,還好,心臟仍跳動不已呢。阮巧巧這才吁一口氣放下心來,彷彿呼應著讓她放心似的,一直沉默的孟慶來又發出了一聲痛苦的呻吟。這呻吟再次激發了阮巧巧的生命本能與力量,她蹲在地上,讓孟慶來軟耷耷的身子伏在她的背上,慢慢積蓄力量……她想將他背下山坡,背出公園,然後打的送進醫院。憋了一股勁,感覺著應該沒有問題了,阮巧巧猛然發勁,卻怎麼也直不起腰來。
她怎麼也背不動孟慶來,她沒有將他送往醫院的能力,看來只有求助別人了。
時間緊迫,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一切,她必須與時間賽跑。
她剛才大聲呼救過,聲音早已傳送遠去,卻沒有任何回應。他們所處的位置太偏太遠,遊人稀少,公園管理人員也少,而時辰又近中午,午餐與午休使得青山湖公園,特別是人跡罕至的凝翠山變得更為空曠寂寥。
阮巧巧放下孟慶來,又扯開嗓子大聲呼救:「抓歹徒啊,救命啊──」她一邊呼叫,一邊向山下跑去。藤蔓、樹枝、野草、荊棘不時掛著她的衣服,絆著她的鞋子,她跌跌撞撞地往下跑,大聲呼喚著不顧一切地往下沖。
快到山腳,終於見到了兩個迎面跑來的男人。他們是公園值班的職工,正扒著午飯呢,聽到一聲緊似一聲的呼救,趕緊將飯碗、筷子一擱,每人操了一根木棒,就迎著喊聲跑來了。「在哪裡?歹徒在哪裡?」他們問。阮巧巧回道:「跑……跑了……」聽說歹徒跑了,兩名職工頓時松了一口氣。年輕的道:「咱們公園一直都挺安全的啊,青天白日的,還從沒出過這樣的事呢。」
「現在社會越來越複雜,看來得好好加強保衛措施了。」年長的說著,又安慰阮巧巧,「有咱們保護,妳別怕。」阮巧巧連連擺手道:「我……我……我……」內心想要表達的意思一時間無法明確道出,她急得直跺腳。年長的見狀道:「別擔心,妳已經安全了,咱們要送妳出公園。」年輕的接著道:「如果需要,我們可以保護妳回家。」
「不……不,我……我不能出去!」阮巧巧好不容易說出這一句,往下就顯得十分順暢了,「山上還有一名勇士,為了救我,他被歹徒打傷了,流了一地的血……」兩人聞言,對望一眼,相互鼓了鼓勁,異口同聲地說道:「他在哪兒?快,咱們快去把他救下來!」
阮巧巧又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回奔,兩個男人緊隨其後。
他們見著了躺在青草地上的傷勢十分嚴重的孟慶來。
兩人不敢怠慢,趕緊輪流背著,將他背下山去,以最快的速度送往離青山湖公園最近的古冶市第二人民醫院。
阮巧巧一路機械地跟著,而腦子則走馬燈似的轉個不停。那心中臨時編造的謊言,既然已經向人道出,就只有繼續編下去聽憑它自由發展了。問題的關鍵,是要自圓其說,將謊言抹得完整圓滿,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要是哪兒有一點漏洞可就麻煩了,也許會功虧一匱全部敗露。
她想像著可能出現的意外,先在心中一遍遍地述說著,盡可能地自我找出缺陷,想出應對更改之策。她敘說著,修改著,謊言漸趨成熟。然而,又一個新的問題出現在巧巧腦海,這謊言還只是她個人的一廂情願,她必須與孟慶來統一口徑才行。要是他甦醒過來,原樣說出,或說走岔,他們的隱私將完全暴露於眾,後果不堪設想。
怎麼辦?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堅守在孟慶來身邊,寸步不離,一旦醒來就尋機將她編造的謊言原封不動地塞給他,澈底隱瞞事實真相。
估摸編造得八九不離十了,巧巧就開始主動向兩位公園職工敘說。她說她獨自一人在公園寂靜無人的凝翠山上漫步,正享受著歸返大自然的山野之趣,突然就出現了一個居心不良、身材高大的男子。那男子望她一眼,就動了強姦邪念。他逼近她,要她自己脫光衣服,服服帖帖地躺在地上,並做出緊掐脖頸的手勢,威脅她說如果不從,就要撲上前去掐死她。她說她是一個性情剛烈的堅貞女人,寧可死在歹徒手下,也不能就此屈辱失身。於是,她假意屈從解扣,趁歹徒不注意,回頭撒腿就跑,一邊奔跑一邊呼救……
阮巧巧正陷於自己的想像中慢慢述說時,公園職工中的年輕者打斷她的話問道:「妳跑下山之前,是不是先呼叫過幾聲?」阮巧巧馬上回道:「是的,可沒有人回應。」
「哦,我當時隱約聽到了,還問過老李呢。」叫老李的回道:「我真的沒聽見,我的耳朵有點背。」
「老李說沒聽見,我也不相信歹徒真的這麼猖狂,當時就沒管沒問了,直到後來,呼救的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大,咱們才奔了出去。」
「咳,要是早點去,說不定就可當場捉住歹徒了。」
巧巧道:「就是啊,這位英雄也不會遭這麼大的罪了。」
這樣的一番議論過後,阮巧巧又接著先前敘述的話頭往下說。她說她畢竟是一個女子,怎麼也跑不過歹徒,不一會,就被歹徒趕上了,摀住她的嘴,將她壓在地上。但她死也不從,就拼了全身力氣掙扎,她用手抓、用腳踢,摀著的嘴發出一陣「嗚嗚嗚」的聲音。歹徒不肯放手,看來他也鐵了心,不達目的誓不甘休。他掀開了她的上衣,右手伸進她的腰間,一下解開了她的褲子,然後往下褪,褪著褪著就要去扯內褲……她差不多絕望了,連反抗的力氣也沒有了,也不知道該怎麼叫喊了。就在這緊急關頭,另一個男子──也就是咱們送往醫院的這位英雄突然出現了。阮巧巧感激涕零地往下說,他肯定是聽到她最先最早的呼救後趕來的。他不顧一切地撲上前來,一把將歹徒撲倒在地。沒想到歹徒一個鯉魚打挺就翻起身來,兩人便攪在一起,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巧巧當時簡直嚇傻了眼,就那麼躺在地上眼睜睜地瞧著他們倆你進我退地鬥來打去,也不知繼續叫喊,更不知該怎樣幫助這位恩人……後來,歹徒就占了上風,將恩人摔倒在地,又順手拾起一塊石頭砸在他的後腦勺上,然後,就撒開腿跑了,一眨眼就跑入樹叢,跑得無影無蹤……
敘說完畢,阮巧巧已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要不是這位無名英雄趕來,那我……我……我就無臉見人,活不下去了啊……」
「這樣的英雄,要好好宣傳表揚。」年長者說。
「對,英雄要表揚,歹徒要嚴懲,」年輕的附和道,「不然的話,誰還敢上凝翠山?公園遊客本來就少,這麼一弄,逛公園的人就更少了。」
孟慶來被送到第二醫院急救室後,兩個職工一合計,也沒有請示公園及上級主管部門領導,他們認為沒有這種必要,或者說從未想過請示領導之類的問題,他們是普通工人,沒有官場歷練,不懂得什麼潛規則之類的東西,只是憑著良心、憑著本能,就決定分頭開來,去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年長的前往轄區派出所報案,希望盡快破案、嚴懲歹徒;年輕的則先到電視臺再到報社,最後前往電臺找記者,他想通過新聞媒體廣泛宣傳英雄見義勇為的先進事蹟。
其實,在危險的緊急關頭,阮巧巧也想過撥打一一○報警。但她不想將一樁畢竟不那麼光彩的醜事張揚開來,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了了之。她的第一次呼救,完全出自本能,後來也曾決心獨自一人將慶來送往醫院,實在沒有辦法,才不得已再次呼救,不得已編造一個英雄救人的謊言。直到慶來進了急救室,她一顆懸著的心差不多才落了地。她想只要輸點血、輸點液,慶來就會醒過來,住個兩三天後就會痊癒,這事情也就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地過去了。當然,她不得不繼續編造謊言,直到有關人員相信,直到謊言幫助他們度過難關為止。
是的,如果公園的兩個職工不多事,要是他們沒有出於正義感、責任感去報什麼案,去找新聞媒體廣泛宣傳擴大影響,這事情也許真的就像阮巧巧預想的那樣過去了。一旦過去,也就水波不驚、悄無聲息地成為他們兩個的祕密,永遠不為外人所知道了。
然而,兩個職工一多事,公安機關、新聞媒體一介入,事情就逸出了常軌,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變得相當複雜起來,完全出乎阮巧巧的意料與想像之外,以一種不可逆轉的非常規態勢向前發展。
遭受石塊突襲後的孟慶來一直昏迷不醒,對此後發生的一切無以知曉,即便知曉,也無法控制。
搶救室內,醫生開始緊張救治。
孟慶來流血過多,身體處於嚴重失血、失重、失衡狀態,生命懸於一息。
殷紅的血液通過輸血管道緩緩流入他的身體。
後腦勺的傷口經過反覆消毒,清洗,然後縫合,包紮。
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搶救,孟慶來的病情終於得到控制,沒有繼續惡化。
又是兩小時過去了,血液得到補充的孟慶來臉上,死一般的慘白消失了。隨著血紅的色彩漸漸塗抹在他的臉上,心跳由微轉弱,由弱向正常狀態平穩恢復,鼻息也變得均勻起來。
孟慶來的病情穩定下來,一直在長長的走廊焦躁不安地踱來踱去的阮巧巧終於獲准可以進入搶救室了。
他的身子被白色的床單包裹著,只有經過紗布包紮的頭部露在外面。吊瓶高掛在病床旁的鐵支架上,透明的藥液順著細細的塑膠管道,既舒緩又迫促地往下滴落,注入慶來的靜脈管道,向全身迴圈滲透。
阮巧巧的眼珠一錯不錯地盯著他那正在恢復血色的臉龐,眼淚不由自主地湧上眼眶。她想忍住,可怎麼也控制不住內心的悲傷與失落,淚水突破眼瞼,無聲地滑過臉龐往下掉落。她抬起右腕擦了擦,眼前的一切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這時,她聽到靜靜躺著的孟慶來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嘆息。不錯,是嘆息,她聽得很清楚,是一聲發自胸腔深處的嘆息。
他醒過來了,真的醒過來了,並且明白發生了的一切。哦,謝天謝地,只要醒過來就好!剛才還在暴風雨般的快樂峰巔享受呢,一下子就跌入了痛苦的深淵,在死亡線上掙扎徘徊。她無法接受,怎麼也不能接受!幸而慶來生命無虞地醒過來了,只要活著就好。生命倘若就此煙消雲散,那該是一種怎樣的造孽啊!
她立時湊近慶來耳邊,輕而柔地喚道:「慶來,慶來──」
慶來的身子動了動,說明他已聽到巧巧的呼喚。
阮巧巧望望室內,醫生、護士不知什麼時候全都出去了,她趕緊起身走到門邊,緊緊地關上房門。然後,又回到病床邊,躬腰伏在孟慶來身邊繼續喚道:「慶來,你醒醒,你快醒醒呀,我有話對你說,很重要、很重要的話!」
孟慶來的喉管發出含糊的「嗯嗯」聲,但他的眼睛仍然沒有睜開。這「嗯嗯」聲無疑在向巧巧昭示,他已經醒過來了,但還無法睜開眼睛。
於是,巧巧又附在他耳邊道:「慶來,如果你醒了,聽得明白,就再嗯嗯兩聲。」
孟慶來就真的又發出兩聲嗯嗯,這聲音似出自喉嚨,又似來自胸腔。
巧巧道:「哦,你能聽懂了,那就好。現在沒人,我不得不抓緊時間說,說了你要記住,咱們一定要統一口徑,不能說岔,要不咱們倆的事情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無地自容了……」
巧巧快速說著,將慶來失去知覺後世界上關於他們倆發生的一切簡要地告訴了他,又將她自個兒編造的英雄捨身救人的謊言複述了一遍。這一遍她已敘說得相當流暢,她自己似乎也相信了這個謊言。「慶來,你記住了嗎?事情的真相就是這樣的,我構思了一遍又一遍,比你構思小說還不容易吶,總算沒有什麼漏洞了。慶來,你可一定要記住啊,事情的經過與真相就是我剛才敘說的那樣,你醒來後別人問你,你就這樣說好了,並且只能這樣說了,你不這樣說都不行了……」
此後,阮巧巧還要在人們的問詢與需要中多次重複這一謊言。謊言初成時那不可避免的漏洞與罅隙,在她多次敘說的縫補中不斷彌合,慢慢變得天衣無縫,一段時間,謊言達到的效果似乎比曾經發生過的一切還要真實。而成熟與真實的謊言也在同樣的訴說中露出孔洞,就像吹足了氣的氣球,哪怕孔洞再細再小,那呼呼洩漏的氣體很快就會使得孔洞變大,或破綻百出,氣球迅速變癟變小消失殆盡──直到謊言成為被人們洞悉的真正謊言為止。
已然甦醒的孟慶來在巧巧的敘述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也聽懂了她要求他以同樣方式敘說的謊言。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與巧巧的偷情會朝著這麼一個方向發展,會導致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咳,只怪他們倆太放肆了,只怪他太不謹慎太不收斂了……事情怎麼會一至如此、一至如此啊?!這樣地想著時,他的胸腔就又發出了一聲沉沉的鳴響。顯然,事情不會像巧巧想的那麼簡單,不會就此結局,那麼,它會朝怎樣的方向,怎樣的情形發展,又該如何收場呢?不清楚,誰也一下子弄不清楚,可在孟慶來內心深處,卻有一種不祥的徵兆與預感。
怎麼會有這樣的直覺呢?他不知道。
但他相信直覺之類神祕的東西,就像兒時所經歷的「過陰」一樣,不可能用科學的方式加以解釋說明,你可以說它是封建迷信,是荒誕虛幻,是巫術把戲……然而,它卻實實在在地發生過。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慶來也是不會相信的。
想到這裡,他不禁感到了幾分恐怖,一股似乎帶著陰風的恐怖。慶來一激靈,全身一緊縮,緊閉著的眼簾就睜開了。於是,他的眼裡出現了巧巧的面孔,上面似乎還留著道道淚痕。
阮巧巧也發現慶來睜開了眼睛,不由得驚喜地叫道:「慶來,你醒了,這回真的醒了!還在疼嗎?感覺怎樣?我說的你都聽見了記住了該不會弄岔吧?」
面對巧巧的一連串詢問,慶來睜開的眼睛很快就又閉上了。
雖只短短的一瞬,雖然慶來什麼也沒有回答,卻令巧巧感到了一種滿足、欣慰與踏實。
慶來閉合的眼睛定格了巧巧的臉龐,不知怎麼回事,這張娟秀的臉龐變幻出無數張錯雜開來,迭合著相互干擾越來越模糊,模糊中又漸漸整合清晰,浮出另外一張同樣娟秀卻更加年輕的臉。這是熊曉玉的臉龐,儘管過去了三十多年時光──三十多年於人類來說可以忽略不計,而對個體生命卻是近半輩子啊──可在慶來內心深處,是永遠不會,也是不可能忘卻的。
叫過一陣,阮巧巧望一眼倒在草叢中的孟慶來,突然嚇得不知所措。面對做夢也沒想過的突發暴力事件,她的思維一時間陷入不可理喻的驚恐與一塌糊塗的混亂。
她竭力調整失控的情緒,使自己鎮靜下來,將剛剛發生的留在腦海裡的片斷綴合在一起,盡可能地理出一條完整的線索,尋出它們的真實意義。暴風雨般的激情……達至快樂峰巔的交媾……關閉外界視域後的內心自足與享受……無力的四肢使得全身猶如一癱稀泥……歹徒的突然襲擊……血!啊,血!當她的目光移向孟慶來後腦,聚焦於鮮血依然汩汩湧流不止的創洞時,不禁如夢初醒般回到現實──嚴酷得令她不忍目睹的現實。
除了盡快應對、收拾殘局外,阮巧巧別無選擇!
一旦明白了眼前發生的一切,阮巧巧不禁變得異常冷靜起來。她一把抓過自己脫在一旁的衣褲,並沒有馬上將它們套在身上,而是找出放於一旁的隨身攜帶的手提包,雙手顫抖著打開,掏出一個香氣撲鼻且繡有花朵的白色手帕,揉成一團,按住孟慶來被石塊砸出的如洞穴般的傷口。然後,才不緊不慢地穿上衣褲,還不忘將散亂的頭髮理了理。
手帕很快就被滲出的鮮血染成紅色,阮巧巧按了按,揭開,蹲下身子,仔細看了看傷口,血似乎不再往外流淌,至少是流得細小而緩慢了。於是,她不得不開始下一步的「工作」了,將孟慶來的衣褲「復原」。好在他穿得不多,上身一件背心,一件襯衫;下身一條短褲,一條西褲。然而,孟慶來有氣無力地呻吟著,全身癱軟得無法配合,她只有拼出全身力氣,使出渾身解數,費盡周折後才一件一件地重新給他穿上。這看似簡單的「工作」弄得阮巧巧一身臭汗,扶著一旁的松樹直喘粗氣。正喘著,突然發現了一個不該出現的失誤,下身的西褲還敞開著呢,深藍色的內褲隱約可見,她趕緊過去捏住拉鍊扣,一點一點地將外褲拉鍊合上。
在緊張地做著這一切的時候,一個應對現實的謊言,也在阮巧巧心中漸成雛型。
她又細心地將周圍的一切檢查了一番,盡可能地不給他人留下證據與把柄。她將他們剛才瘋狂做愛時弄得倒伏的青草盡可能地扶正、復原,正整理著,右腳踩在一塊硬硬的石頭上,她撥開草叢,發現了一塊碩大的尖角石塊,還發現了石塊上已呈暗紅色的斑斑血痕。這無疑就是兇手剛才使用的兇器了,她拿在手中感覺沉沉的,心頭也隨之一沉,這塊石頭,是兇手準備好了一直隨身帶著的,還是在山上臨時撿拾的呢?念頭像火星般一閃即逝,阮巧巧的思維,轉瞬般又移到了孟慶來身上。
異常冷靜的她,做完了自認為該做的一切後,最為關注的,自然就是孟慶來的生命了。
流了那麼多的血,直到現在還沒甦醒,就連呻吟也止息了,傷勢一定十分嚴重!他還活著嗎?還有救嗎?不能再耽擱了,一定要想方設法將他盡快送到醫院。
這樣地想著時,阮巧巧不禁湊在他耳邊「慶來,慶來」直叫喚。孟慶來雙眼閉合,似乎半點反應也沒有。她急了,撥了撥孟慶來的眼皮,又將右手食指放在他鼻下,嗯,還有那麼一點微弱的氣息,又摸了摸他的胸口,哦,還好,心臟仍跳動不已呢。阮巧巧這才吁一口氣放下心來,彷彿呼應著讓她放心似的,一直沉默的孟慶來又發出了一聲痛苦的呻吟。這呻吟再次激發了阮巧巧的生命本能與力量,她蹲在地上,讓孟慶來軟耷耷的身子伏在她的背上,慢慢積蓄力量……她想將他背下山坡,背出公園,然後打的送進醫院。憋了一股勁,感覺著應該沒有問題了,阮巧巧猛然發勁,卻怎麼也直不起腰來。
她怎麼也背不動孟慶來,她沒有將他送往醫院的能力,看來只有求助別人了。
時間緊迫,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一切,她必須與時間賽跑。
她剛才大聲呼救過,聲音早已傳送遠去,卻沒有任何回應。他們所處的位置太偏太遠,遊人稀少,公園管理人員也少,而時辰又近中午,午餐與午休使得青山湖公園,特別是人跡罕至的凝翠山變得更為空曠寂寥。
阮巧巧放下孟慶來,又扯開嗓子大聲呼救:「抓歹徒啊,救命啊──」她一邊呼叫,一邊向山下跑去。藤蔓、樹枝、野草、荊棘不時掛著她的衣服,絆著她的鞋子,她跌跌撞撞地往下跑,大聲呼喚著不顧一切地往下沖。
快到山腳,終於見到了兩個迎面跑來的男人。他們是公園值班的職工,正扒著午飯呢,聽到一聲緊似一聲的呼救,趕緊將飯碗、筷子一擱,每人操了一根木棒,就迎著喊聲跑來了。「在哪裡?歹徒在哪裡?」他們問。阮巧巧回道:「跑……跑了……」聽說歹徒跑了,兩名職工頓時松了一口氣。年輕的道:「咱們公園一直都挺安全的啊,青天白日的,還從沒出過這樣的事呢。」
「現在社會越來越複雜,看來得好好加強保衛措施了。」年長的說著,又安慰阮巧巧,「有咱們保護,妳別怕。」阮巧巧連連擺手道:「我……我……我……」內心想要表達的意思一時間無法明確道出,她急得直跺腳。年長的見狀道:「別擔心,妳已經安全了,咱們要送妳出公園。」年輕的接著道:「如果需要,我們可以保護妳回家。」
「不……不,我……我不能出去!」阮巧巧好不容易說出這一句,往下就顯得十分順暢了,「山上還有一名勇士,為了救我,他被歹徒打傷了,流了一地的血……」兩人聞言,對望一眼,相互鼓了鼓勁,異口同聲地說道:「他在哪兒?快,咱們快去把他救下來!」
阮巧巧又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回奔,兩個男人緊隨其後。
他們見著了躺在青草地上的傷勢十分嚴重的孟慶來。
兩人不敢怠慢,趕緊輪流背著,將他背下山去,以最快的速度送往離青山湖公園最近的古冶市第二人民醫院。
阮巧巧一路機械地跟著,而腦子則走馬燈似的轉個不停。那心中臨時編造的謊言,既然已經向人道出,就只有繼續編下去聽憑它自由發展了。問題的關鍵,是要自圓其說,將謊言抹得完整圓滿,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要是哪兒有一點漏洞可就麻煩了,也許會功虧一匱全部敗露。
她想像著可能出現的意外,先在心中一遍遍地述說著,盡可能地自我找出缺陷,想出應對更改之策。她敘說著,修改著,謊言漸趨成熟。然而,又一個新的問題出現在巧巧腦海,這謊言還只是她個人的一廂情願,她必須與孟慶來統一口徑才行。要是他甦醒過來,原樣說出,或說走岔,他們的隱私將完全暴露於眾,後果不堪設想。
怎麼辦?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堅守在孟慶來身邊,寸步不離,一旦醒來就尋機將她編造的謊言原封不動地塞給他,澈底隱瞞事實真相。
估摸編造得八九不離十了,巧巧就開始主動向兩位公園職工敘說。她說她獨自一人在公園寂靜無人的凝翠山上漫步,正享受著歸返大自然的山野之趣,突然就出現了一個居心不良、身材高大的男子。那男子望她一眼,就動了強姦邪念。他逼近她,要她自己脫光衣服,服服帖帖地躺在地上,並做出緊掐脖頸的手勢,威脅她說如果不從,就要撲上前去掐死她。她說她是一個性情剛烈的堅貞女人,寧可死在歹徒手下,也不能就此屈辱失身。於是,她假意屈從解扣,趁歹徒不注意,回頭撒腿就跑,一邊奔跑一邊呼救……
阮巧巧正陷於自己的想像中慢慢述說時,公園職工中的年輕者打斷她的話問道:「妳跑下山之前,是不是先呼叫過幾聲?」阮巧巧馬上回道:「是的,可沒有人回應。」
「哦,我當時隱約聽到了,還問過老李呢。」叫老李的回道:「我真的沒聽見,我的耳朵有點背。」
「老李說沒聽見,我也不相信歹徒真的這麼猖狂,當時就沒管沒問了,直到後來,呼救的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大,咱們才奔了出去。」
「咳,要是早點去,說不定就可當場捉住歹徒了。」
巧巧道:「就是啊,這位英雄也不會遭這麼大的罪了。」
這樣的一番議論過後,阮巧巧又接著先前敘述的話頭往下說。她說她畢竟是一個女子,怎麼也跑不過歹徒,不一會,就被歹徒趕上了,摀住她的嘴,將她壓在地上。但她死也不從,就拼了全身力氣掙扎,她用手抓、用腳踢,摀著的嘴發出一陣「嗚嗚嗚」的聲音。歹徒不肯放手,看來他也鐵了心,不達目的誓不甘休。他掀開了她的上衣,右手伸進她的腰間,一下解開了她的褲子,然後往下褪,褪著褪著就要去扯內褲……她差不多絕望了,連反抗的力氣也沒有了,也不知道該怎麼叫喊了。就在這緊急關頭,另一個男子──也就是咱們送往醫院的這位英雄突然出現了。阮巧巧感激涕零地往下說,他肯定是聽到她最先最早的呼救後趕來的。他不顧一切地撲上前來,一把將歹徒撲倒在地。沒想到歹徒一個鯉魚打挺就翻起身來,兩人便攪在一起,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巧巧當時簡直嚇傻了眼,就那麼躺在地上眼睜睜地瞧著他們倆你進我退地鬥來打去,也不知繼續叫喊,更不知該怎樣幫助這位恩人……後來,歹徒就占了上風,將恩人摔倒在地,又順手拾起一塊石頭砸在他的後腦勺上,然後,就撒開腿跑了,一眨眼就跑入樹叢,跑得無影無蹤……
敘說完畢,阮巧巧已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要不是這位無名英雄趕來,那我……我……我就無臉見人,活不下去了啊……」
「這樣的英雄,要好好宣傳表揚。」年長者說。
「對,英雄要表揚,歹徒要嚴懲,」年輕的附和道,「不然的話,誰還敢上凝翠山?公園遊客本來就少,這麼一弄,逛公園的人就更少了。」
孟慶來被送到第二醫院急救室後,兩個職工一合計,也沒有請示公園及上級主管部門領導,他們認為沒有這種必要,或者說從未想過請示領導之類的問題,他們是普通工人,沒有官場歷練,不懂得什麼潛規則之類的東西,只是憑著良心、憑著本能,就決定分頭開來,去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年長的前往轄區派出所報案,希望盡快破案、嚴懲歹徒;年輕的則先到電視臺再到報社,最後前往電臺找記者,他想通過新聞媒體廣泛宣傳英雄見義勇為的先進事蹟。
其實,在危險的緊急關頭,阮巧巧也想過撥打一一○報警。但她不想將一樁畢竟不那麼光彩的醜事張揚開來,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了了之。她的第一次呼救,完全出自本能,後來也曾決心獨自一人將慶來送往醫院,實在沒有辦法,才不得已再次呼救,不得已編造一個英雄救人的謊言。直到慶來進了急救室,她一顆懸著的心差不多才落了地。她想只要輸點血、輸點液,慶來就會醒過來,住個兩三天後就會痊癒,這事情也就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地過去了。當然,她不得不繼續編造謊言,直到有關人員相信,直到謊言幫助他們度過難關為止。
是的,如果公園的兩個職工不多事,要是他們沒有出於正義感、責任感去報什麼案,去找新聞媒體廣泛宣傳擴大影響,這事情也許真的就像阮巧巧預想的那樣過去了。一旦過去,也就水波不驚、悄無聲息地成為他們兩個的祕密,永遠不為外人所知道了。
然而,兩個職工一多事,公安機關、新聞媒體一介入,事情就逸出了常軌,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變得相當複雜起來,完全出乎阮巧巧的意料與想像之外,以一種不可逆轉的非常規態勢向前發展。
遭受石塊突襲後的孟慶來一直昏迷不醒,對此後發生的一切無以知曉,即便知曉,也無法控制。
搶救室內,醫生開始緊張救治。
孟慶來流血過多,身體處於嚴重失血、失重、失衡狀態,生命懸於一息。
殷紅的血液通過輸血管道緩緩流入他的身體。
後腦勺的傷口經過反覆消毒,清洗,然後縫合,包紮。
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搶救,孟慶來的病情終於得到控制,沒有繼續惡化。
又是兩小時過去了,血液得到補充的孟慶來臉上,死一般的慘白消失了。隨著血紅的色彩漸漸塗抹在他的臉上,心跳由微轉弱,由弱向正常狀態平穩恢復,鼻息也變得均勻起來。
孟慶來的病情穩定下來,一直在長長的走廊焦躁不安地踱來踱去的阮巧巧終於獲准可以進入搶救室了。
他的身子被白色的床單包裹著,只有經過紗布包紮的頭部露在外面。吊瓶高掛在病床旁的鐵支架上,透明的藥液順著細細的塑膠管道,既舒緩又迫促地往下滴落,注入慶來的靜脈管道,向全身迴圈滲透。
阮巧巧的眼珠一錯不錯地盯著他那正在恢復血色的臉龐,眼淚不由自主地湧上眼眶。她想忍住,可怎麼也控制不住內心的悲傷與失落,淚水突破眼瞼,無聲地滑過臉龐往下掉落。她抬起右腕擦了擦,眼前的一切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這時,她聽到靜靜躺著的孟慶來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嘆息。不錯,是嘆息,她聽得很清楚,是一聲發自胸腔深處的嘆息。
他醒過來了,真的醒過來了,並且明白發生了的一切。哦,謝天謝地,只要醒過來就好!剛才還在暴風雨般的快樂峰巔享受呢,一下子就跌入了痛苦的深淵,在死亡線上掙扎徘徊。她無法接受,怎麼也不能接受!幸而慶來生命無虞地醒過來了,只要活著就好。生命倘若就此煙消雲散,那該是一種怎樣的造孽啊!
她立時湊近慶來耳邊,輕而柔地喚道:「慶來,慶來──」
慶來的身子動了動,說明他已聽到巧巧的呼喚。
阮巧巧望望室內,醫生、護士不知什麼時候全都出去了,她趕緊起身走到門邊,緊緊地關上房門。然後,又回到病床邊,躬腰伏在孟慶來身邊繼續喚道:「慶來,你醒醒,你快醒醒呀,我有話對你說,很重要、很重要的話!」
孟慶來的喉管發出含糊的「嗯嗯」聲,但他的眼睛仍然沒有睜開。這「嗯嗯」聲無疑在向巧巧昭示,他已經醒過來了,但還無法睜開眼睛。
於是,巧巧又附在他耳邊道:「慶來,如果你醒了,聽得明白,就再嗯嗯兩聲。」
孟慶來就真的又發出兩聲嗯嗯,這聲音似出自喉嚨,又似來自胸腔。
巧巧道:「哦,你能聽懂了,那就好。現在沒人,我不得不抓緊時間說,說了你要記住,咱們一定要統一口徑,不能說岔,要不咱們倆的事情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無地自容了……」
巧巧快速說著,將慶來失去知覺後世界上關於他們倆發生的一切簡要地告訴了他,又將她自個兒編造的英雄捨身救人的謊言複述了一遍。這一遍她已敘說得相當流暢,她自己似乎也相信了這個謊言。「慶來,你記住了嗎?事情的真相就是這樣的,我構思了一遍又一遍,比你構思小說還不容易吶,總算沒有什麼漏洞了。慶來,你可一定要記住啊,事情的經過與真相就是我剛才敘說的那樣,你醒來後別人問你,你就這樣說好了,並且只能這樣說了,你不這樣說都不行了……」
此後,阮巧巧還要在人們的問詢與需要中多次重複這一謊言。謊言初成時那不可避免的漏洞與罅隙,在她多次敘說的縫補中不斷彌合,慢慢變得天衣無縫,一段時間,謊言達到的效果似乎比曾經發生過的一切還要真實。而成熟與真實的謊言也在同樣的訴說中露出孔洞,就像吹足了氣的氣球,哪怕孔洞再細再小,那呼呼洩漏的氣體很快就會使得孔洞變大,或破綻百出,氣球迅速變癟變小消失殆盡──直到謊言成為被人們洞悉的真正謊言為止。
已然甦醒的孟慶來在巧巧的敘述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也聽懂了她要求他以同樣方式敘說的謊言。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與巧巧的偷情會朝著這麼一個方向發展,會導致這樣一種尷尬的境地。咳,只怪他們倆太放肆了,只怪他太不謹慎太不收斂了……事情怎麼會一至如此、一至如此啊?!這樣地想著時,他的胸腔就又發出了一聲沉沉的鳴響。顯然,事情不會像巧巧想的那麼簡單,不會就此結局,那麼,它會朝怎樣的方向,怎樣的情形發展,又該如何收場呢?不清楚,誰也一下子弄不清楚,可在孟慶來內心深處,卻有一種不祥的徵兆與預感。
怎麼會有這樣的直覺呢?他不知道。
但他相信直覺之類神祕的東西,就像兒時所經歷的「過陰」一樣,不可能用科學的方式加以解釋說明,你可以說它是封建迷信,是荒誕虛幻,是巫術把戲……然而,它卻實實在在地發生過。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慶來也是不會相信的。
想到這裡,他不禁感到了幾分恐怖,一股似乎帶著陰風的恐怖。慶來一激靈,全身一緊縮,緊閉著的眼簾就睜開了。於是,他的眼裡出現了巧巧的面孔,上面似乎還留著道道淚痕。
阮巧巧也發現慶來睜開了眼睛,不由得驚喜地叫道:「慶來,你醒了,這回真的醒了!還在疼嗎?感覺怎樣?我說的你都聽見了記住了該不會弄岔吧?」
面對巧巧的一連串詢問,慶來睜開的眼睛很快就又閉上了。
雖只短短的一瞬,雖然慶來什麼也沒有回答,卻令巧巧感到了一種滿足、欣慰與踏實。
慶來閉合的眼睛定格了巧巧的臉龐,不知怎麼回事,這張娟秀的臉龐變幻出無數張錯雜開來,迭合著相互干擾越來越模糊,模糊中又漸漸整合清晰,浮出另外一張同樣娟秀卻更加年輕的臉。這是熊曉玉的臉龐,儘管過去了三十多年時光──三十多年於人類來說可以忽略不計,而對個體生命卻是近半輩子啊──可在慶來內心深處,是永遠不會,也是不可能忘卻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