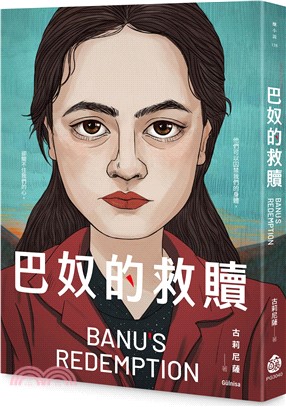商品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回去了。每次回國,從機場開始的盤問會持續到伊犁老家,不同的部門詢問同樣的問題,答案已經爛熟於心。據說今年回去的新疆維吾爾人都是從機場直接到再教育營。……」
----
2017年夏天,性格奔放的維吾爾女子巴奴遠從土耳其回新疆探望病重的母親,儘管巴奴是漢語流利的「民考漢」共產黨員,一到北京,仍迅速被中國安全部門控制,並莫名成為大數據系統判定的「資恐嫌疑人」!
審訊室裡,巴奴被迫自白過往的情殤之路:不倫的初戀、早夭的稚子和短暫的婚姻、與漢人導師的情色交易,以及那道藏在心底最深處的疤──那年,她與閨密賽南姆在烏魯木齊相知相遇,卻因自己的占有慾而背叛了賽南姆,隨後而來的七.五事件,讓她們從此音訊永隔。
為了懺悔,也為了承諾,巴奴想方設法營救賽南姆那正關押在「再教育營」的女兒娜迪耶。在鋪天蓋地的監控鏡頭和密不透風的公檢法組織網下,巴奴能順利帶著娜迪耶逃出高牆、得到救贖嗎?
----
2017年夏天,性格奔放的維吾爾女子巴奴遠從土耳其回新疆探望病重的母親,儘管巴奴是漢語流利的「民考漢」共產黨員,一到北京,仍迅速被中國安全部門控制,並莫名成為大數據系統判定的「資恐嫌疑人」!
審訊室裡,巴奴被迫自白過往的情殤之路:不倫的初戀、早夭的稚子和短暫的婚姻、與漢人導師的情色交易,以及那道藏在心底最深處的疤──那年,她與閨密賽南姆在烏魯木齊相知相遇,卻因自己的占有慾而背叛了賽南姆,隨後而來的七.五事件,讓她們從此音訊永隔。
為了懺悔,也為了承諾,巴奴想方設法營救賽南姆那正關押在「再教育營」的女兒娜迪耶。在鋪天蓋地的監控鏡頭和密不透風的公檢法組織網下,巴奴能順利帶著娜迪耶逃出高牆、得到救贖嗎?
目次
第一章 自投羅網
第二章 我的供述
第三章 壞人
第四章 如花盛開
第五章 我的黑眼睛
第六章 重生
第七章 如魚得水
第八章 意亂情迷
第九章 生離死別
第十章 應收盡收
第十一章 急中生智
第十二章 娜迪耶關在哪裡
第十三章 資恐嫌疑人
第十四章 真真假假
第十五章 喝茶
第十六章 逃離
新疆大事紀
第二章 我的供述
第三章 壞人
第四章 如花盛開
第五章 我的黑眼睛
第六章 重生
第七章 如魚得水
第八章 意亂情迷
第九章 生離死別
第十章 應收盡收
第十一章 急中生智
第十二章 娜迪耶關在哪裡
第十三章 資恐嫌疑人
第十四章 真真假假
第十五章 喝茶
第十六章 逃離
新疆大事紀
書摘/試閱
〈第一章 自投羅網〉
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回去了。每次回國,從機場開始的盤問會持續到伊犁老家,不同的部門詢問同樣的問題,答案已經爛熟於心。據說今年回去的新疆維吾爾人都是從機場直接到再教育營。我也知道二○一七年是不尋常的一年,家鄉傳來的消息是那麼地令人震驚,一個個熟悉的同事和朋友一夜之間失去蹤影,沒有公開的審判,人們在竊竊私語中傳遞著各種消息。我對自己在這邊看到的報導和傳言將信將疑。
給母親打電話是想打聽那邊的情況,可是母親對時局的探尋避而不答,告訴我她生病了,住在重症監護室已經三天了。起初我心裡一沉,但是聽到她絲絨般溫暖的嗓音,話語間令人安心的語氣,隨即猜到她又像過去一樣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生起「病」來了。可是,究竟為了什麼呢?母親不願意直接回答,她的閃爍其詞更增加了我的疑慮。作為女兒聽到母親說自己住進了ICU當然不能無動於衷。於是,我問母親,您希望我回去看您嗎?你不覺得應該回來看看我嗎?媽媽反問了一句。我和媽媽的關係並不親密,我們之間的牽掛比應該有的要少得多。我很清楚媽媽她想要的是兒女環繞病榻前的滿足感。嫂子是醫生,應該向她瞭解一下情況,但是我又覺得沒有必要,實際上自己潛意識裡就是想弄清楚家鄉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回去看望母親是作為女兒的一種姿態。打電話給馬修,告訴他我要回中國了。馬修並沒有特別阻攔,只是讓我再慎重考慮一下,說這不是一個好主意。不是我膽子大,我相信凡事都有一個因,我用「人在正道走,不怕皇帝抓」的維吾爾老話自我安慰,相信沒有越過政府的紅線,就沒有什麼必要擔心自己的安危。馬修知道我決定了的事情定是要做的,於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隨便你怎樣」便不再談論此事。我向大學人事處請了一個星期的假,買了伊斯坦堡─北京往返機票。
經過九個小時充滿憂思的飛行,飛機安全降落在北京國際機場停機坪。凌晨五點多走出飛機通道,打著哈欠尾隨著奔向海關的人們緩緩移步,並沒有特別的擔心,因為每次只有在烏魯木齊入境時才會被帶到小屋裡去單獨問話,我一直都覺得北京是一個可以講道理的地方。但是,我還是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接受所有的不測。
在通往邊防檢查站的路上我拐進衛生間,站在梳妝鏡前望著自己布滿血絲的雙眼自言自語:鎮定,最壞的結果無非是跟自己的族人遭受共同的命運。忽然間從鏡子裡看到一個女人站在我身後,心一驚,牙刷掉落在地,撿起來再一回頭女人已無蹤影。我深吸一口氣竭力鎮定下來,然後不緊不慢地刷牙洗臉,抹了點口紅。我望著鏡子,鏡中人神情張皇。咬緊打顫的牙齒,甩了甩頭髮,推著小巧的行李箱加入了湧向海關通道的人流。
前方不遠處邊防檢查站的武警身後站著幾位身穿便衣的人,似乎翹首望向這邊,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衝著我來的。邊防檢查窗口排起了長隊,我不敢抬頭看向前方,不時朝我瞟過來的目光讓人心慌。我遞上護照時,邊防武警迅速翻看了幾頁抬頭問了句:「什麼民族?」這個問題觸碰到了我最敏感的神經,我翻了翻白眼一字一頓地大聲回答說:「維吾爾!」他驚愕地抬頭眨巴了幾下眼睛,不敢相信有人竟敢如此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他面帶慍怒轉身將護照遞給了等在一旁的女警,咕噥了一句:「這個人有情緒,你帶她去那邊。」
我默默地跟在女警察身後,走進了一間辦公室。裡面已經有人在等著我了,他們開始翻看我的雙肩包、手提箱,拿走了手機。時間在流逝,想到來接我的侄女,我有點沉不住氣了,開始變得煩躁,對盤查我的女武警說:「告訴我,我可以出去跟家人說句話嗎?」
「不行!」一名男武警簡短地回答。
「那我打個電話吧,叫接機的人別等我了。」
「可以。說漢語!」說著把手機還給了我。
打完電話我問他們檢查完我可以走吧?
周圍的人仔細翻看我的筆記和隨身攜帶的書籍,沒有人理會我的問題。
我沉默了。這是每次出入境時都會遇到的例行檢查,任何抗議和爭辯都將會使自己的處境更加糟糕。我不想給自己惹麻煩。他們把護照還給了我,把我帶出海關交給兩名持槍武警。他們押著我來到一樓大廳。這通常是我出機場時的最後一道關口,右邊掛著白色門簾的門楣寫著衛生室,進去後是一個走廊,兩邊是各種名目的處置室,我被帶進一間寫著「出入境管理辦公室」的大房間,裡面只有幾把椅子和幾張靠牆擺放的辦公桌。我被告知要在這裡等待來自烏魯木齊相關部門的人,不能自己回烏魯木齊。我問他們出了什麼事,他們說沒出什麼事,凡是從國外回來的新疆人都要這樣。聽了這話我放鬆下來了,根據以往的經歷,我深信這種針對特定族群的陣勢不會對像自己這樣的人造成太大的損害。經歷了一場驚嚇,舌頭和上顎黏在一起,於是站起來想要倒杯水喝,可是警惕地望著我的那名武警戰士立刻喝令我坐下,並且陰著臉從抽屜裡取出一副手銬走過來,麻利地把我的雙手銬在了一起。這一切都發生在幾秒鐘裡,我一時難以接受,大喊:「你們這是幹嘛呀?怎麼能這麼對待我,我做了什麼?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武警戰士大聲呵斥道:「再說就給你上腳鐐!」
空氣像凝固了一般,我無奈地坐回到椅子裡。讓我冷靜下來的倒不是恐懼,而是隨遇而安的麻木心境。這種情感上的麻木,是我每次出入境時遭遇到超過我本身承受能力的緊張狀態後的慣常反應。終於,等到了烏魯木齊來的人。看到熟悉的女警官,我像遇到救星一樣站了起來並迎上去。這是我的責任民警張曉芳,搞「警民一家親」活動的時候,她還邀請我跟她一起去游過泳呢。她看上去四十歲左右,油黑的齊耳短髮和白皙的皮膚給她增添了幾分知性,要不是上眼皮有點耷拉,她的眼睛算是好看的杏仁眼。她擠出笑容說了聲:「啊,你回來了?」算是打了招呼,用下巴示意武警打開了手銬。
他們帶我上了飛往烏魯木齊的飛機,我被一個男便衣警察和張警官夾在中間。飛機起飛前,我們像其他乘客一樣簡單交流了幾句,張警官刻意與我保持距離,而扁平臉小個子便衣卻對我在國外從事的工作甚感興趣不停地問這問那,滿臉堆笑,完全不像一個執行嚴肅公務的人。他還提議互加微信,主動給了他的電話號碼。他說他叫烤肉串,我知道這只是一個網名,問他怎麼起了這麼一個名字,他說隨便起的。
烤肉串的親切使我的精神鬆懈下來,進入了昏昏欲睡的狀態。過去的兩天我幾乎沒有闔眼,不確定的狀態讓我十分焦慮不安,無數種可能的情況在我的腦子裡像小老鼠一樣竄來竄去,令我亢奮不已。四小時二十分鐘的航程不算太長,但是也足以在睡眠中解除困乏。既然已經像網飛蟲一樣被蜘蛛網黏住,轉機去伊犁探望媽媽也幾無可能,那就隨他們處置吧。這樣想著一陣睏意襲來,我漸漸進入了夢鄉。
天空布滿陰霾,颳著刺骨的寒風。我起晚了,因為害怕遲到後的罰站,發瘋似地往學校跑,可是學校不在了,那裡出現了一個又大又厚的黑鐵門。大門緊閉,我想進去可怎麼也推不開,繞著學校的圍牆走了一圈,發現已經不可能從禮堂後邊那個豁口鑽進去了。因為牆更高更結實了,上面還有鐵絲網。牆外的老榆樹還在,這使我安下心來。哼,你們休想害我挨剋。我爬上老榆樹,抓住伸展到校園裡的樹枝,像猴兒一樣盪進了校園。
音樂和口號聲。循聲走進禮堂,看到一群赤裸的青年男女一邊唱歌一邊手舞足蹈。啊,難道這就是那個傳說中人們永遠唱歌跳舞,不知憂愁的地方?對著我的是一個女人的大屁股。我躲在她的身後,裸體女人嘴裡不停地喊著什麼,弓背彎腰,使勁舞動雙臂打著節拍,兩腿之間的陰影就在我的鼻子下面,甚至聞到了她下體的氣味。面朝我的小夥兒和姑娘們似乎正傾盡全部心力,揚臉望著屋頂張開雙臂旋轉、旋轉再旋轉,彷彿他們可以由此升向天空!他們看上去像上了發條的玩偶,既無羞恥也無怨怒,歌唱舞蹈,不知疲倦。離我最近的是一個瘦高的小夥子,兩撇漆黑的眉毛,右眼烏青,下巴有一個胎記,似乎在笑,但那只是面部肌肉的震顫。我儘量讓自己盯著女人的身體,她們擺動著腰肢,有的纖細,有的臃腫,形態各異的乳房在胸前晃來晃去。突然,有胎記的大哥哥朝我大聲喊了起來:「巴奴──快逃,巴奴──快逃!」我扭頭看到一群僵屍一樣面目可憎的男人正站在我的身後。我衝出禮堂,卻怎麼也搆不著那個伸進校園的樹枝。僵屍變成了手提長槍的士兵,他們並不上來抓我,獰笑著看我徒勞地跳啊跳……
我在驚恐中醒來,有片刻功夫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看到身邊的兩個人才意識到自己正被押解回家,不禁心情黯然起來。到了烏魯木齊機場,烤肉串說把你交給轄區民警了,沒有什麼大事,不用擔心,有事可以找我。說完就朝停車場方向去了。便衣的態度可以說是溫和親切的,這使我感覺十分困惑,難道這是暴風雨前的異常徵兆?
我和轄區民警上了一輛在便道等候的警車,車上有一位少女坐在司機旁邊,正跟司機說說笑笑。這種輕鬆的氣氛讓我感覺自己的夢境是那麼地荒誕。我主動跟他們打了招呼,還問司機這個小美女是您女兒嗎?司機笑了笑對這個套近乎的問題算是作出了禮貌的回應。我還想跟張警官敘敘舊,可是她臉上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讓我退縮了,不過她還是讓我坐在身邊,也許覺得我沒有逃跑的機會,或者並沒有把我當成犯人。幾個人輕鬆地一路寒暄著開出了機場高速公路。北京時間兩點十五分正是烏魯木齊的午休時間。新疆警察對我的態度始終是禮貌和溫和的,這讓我感覺自己似乎受到了優待。
到了派出所,張警官刷卡開了電動門,穿過一樓值班室走到盡頭的樓梯口進入地下室,映入眼簾的是一排帶鐵柵欄的囚籠,裡面的人聽到動靜走到鐵柵欄邊向外張望,我看到一雙深邃憂傷的眼睛,卻不忍直視,忙別過臉看向別處。警官帶著我穿過囚籠走到一間像實驗室一樣的房間,吩咐她的同事先弄「五採」然後帶我去一號審訊室做筆錄。
一個留著平頭穿著白大褂的年輕民警滿面笑容地向我解釋說,例行公事啊,不要緊張,現在先採血。聽到他說維吾爾語時略帶哈薩克族口音,我馬上改用哈薩克語回應他:「當然,這是你的工作,採就採唄,正好可以提供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與其說我的配合態度,不如說是我地道的哈薩克語讓他釋放出了更多的善意。於是我們在笑談中很快完成了採血採指紋、拍攝多角度照片,取瞳孔紋樣、讀短文錄聲音。生物資訊採集進行得十分順利,白大褂不停地誇我素質高,配合得好。
白大褂領著我穿過一排拘留室,刷卡打開一扇電動門,指了指那個開著的門說了聲「進去吧」。身後的鐵門閉合相撞的聲音令我心驚膽戰。一號審訊室大概九平方公尺,方方正正,正對著門擺著一張辦公桌,上面是一台電腦,屋子對面的牆上有一個長方形的電子螢幕,顯示的:2017.06.17, 15:08。正中擺放著一把可以上鎖的椅子,我想這就是傳說中的老虎椅了。我打算坐進去,可是張警官示意我坐在離她最近的一把普通的椅子上,她自己坐在電腦前開始錄口供。
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回去了。每次回國,從機場開始的盤問會持續到伊犁老家,不同的部門詢問同樣的問題,答案已經爛熟於心。據說今年回去的新疆維吾爾人都是從機場直接到再教育營。我也知道二○一七年是不尋常的一年,家鄉傳來的消息是那麼地令人震驚,一個個熟悉的同事和朋友一夜之間失去蹤影,沒有公開的審判,人們在竊竊私語中傳遞著各種消息。我對自己在這邊看到的報導和傳言將信將疑。
給母親打電話是想打聽那邊的情況,可是母親對時局的探尋避而不答,告訴我她生病了,住在重症監護室已經三天了。起初我心裡一沉,但是聽到她絲絨般溫暖的嗓音,話語間令人安心的語氣,隨即猜到她又像過去一樣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生起「病」來了。可是,究竟為了什麼呢?母親不願意直接回答,她的閃爍其詞更增加了我的疑慮。作為女兒聽到母親說自己住進了ICU當然不能無動於衷。於是,我問母親,您希望我回去看您嗎?你不覺得應該回來看看我嗎?媽媽反問了一句。我和媽媽的關係並不親密,我們之間的牽掛比應該有的要少得多。我很清楚媽媽她想要的是兒女環繞病榻前的滿足感。嫂子是醫生,應該向她瞭解一下情況,但是我又覺得沒有必要,實際上自己潛意識裡就是想弄清楚家鄉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回去看望母親是作為女兒的一種姿態。打電話給馬修,告訴他我要回中國了。馬修並沒有特別阻攔,只是讓我再慎重考慮一下,說這不是一個好主意。不是我膽子大,我相信凡事都有一個因,我用「人在正道走,不怕皇帝抓」的維吾爾老話自我安慰,相信沒有越過政府的紅線,就沒有什麼必要擔心自己的安危。馬修知道我決定了的事情定是要做的,於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隨便你怎樣」便不再談論此事。我向大學人事處請了一個星期的假,買了伊斯坦堡─北京往返機票。
經過九個小時充滿憂思的飛行,飛機安全降落在北京國際機場停機坪。凌晨五點多走出飛機通道,打著哈欠尾隨著奔向海關的人們緩緩移步,並沒有特別的擔心,因為每次只有在烏魯木齊入境時才會被帶到小屋裡去單獨問話,我一直都覺得北京是一個可以講道理的地方。但是,我還是做了最壞的打算,準備接受所有的不測。
在通往邊防檢查站的路上我拐進衛生間,站在梳妝鏡前望著自己布滿血絲的雙眼自言自語:鎮定,最壞的結果無非是跟自己的族人遭受共同的命運。忽然間從鏡子裡看到一個女人站在我身後,心一驚,牙刷掉落在地,撿起來再一回頭女人已無蹤影。我深吸一口氣竭力鎮定下來,然後不緊不慢地刷牙洗臉,抹了點口紅。我望著鏡子,鏡中人神情張皇。咬緊打顫的牙齒,甩了甩頭髮,推著小巧的行李箱加入了湧向海關通道的人流。
前方不遠處邊防檢查站的武警身後站著幾位身穿便衣的人,似乎翹首望向這邊,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衝著我來的。邊防檢查窗口排起了長隊,我不敢抬頭看向前方,不時朝我瞟過來的目光讓人心慌。我遞上護照時,邊防武警迅速翻看了幾頁抬頭問了句:「什麼民族?」這個問題觸碰到了我最敏感的神經,我翻了翻白眼一字一頓地大聲回答說:「維吾爾!」他驚愕地抬頭眨巴了幾下眼睛,不敢相信有人竟敢如此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他面帶慍怒轉身將護照遞給了等在一旁的女警,咕噥了一句:「這個人有情緒,你帶她去那邊。」
我默默地跟在女警察身後,走進了一間辦公室。裡面已經有人在等著我了,他們開始翻看我的雙肩包、手提箱,拿走了手機。時間在流逝,想到來接我的侄女,我有點沉不住氣了,開始變得煩躁,對盤查我的女武警說:「告訴我,我可以出去跟家人說句話嗎?」
「不行!」一名男武警簡短地回答。
「那我打個電話吧,叫接機的人別等我了。」
「可以。說漢語!」說著把手機還給了我。
打完電話我問他們檢查完我可以走吧?
周圍的人仔細翻看我的筆記和隨身攜帶的書籍,沒有人理會我的問題。
我沉默了。這是每次出入境時都會遇到的例行檢查,任何抗議和爭辯都將會使自己的處境更加糟糕。我不想給自己惹麻煩。他們把護照還給了我,把我帶出海關交給兩名持槍武警。他們押著我來到一樓大廳。這通常是我出機場時的最後一道關口,右邊掛著白色門簾的門楣寫著衛生室,進去後是一個走廊,兩邊是各種名目的處置室,我被帶進一間寫著「出入境管理辦公室」的大房間,裡面只有幾把椅子和幾張靠牆擺放的辦公桌。我被告知要在這裡等待來自烏魯木齊相關部門的人,不能自己回烏魯木齊。我問他們出了什麼事,他們說沒出什麼事,凡是從國外回來的新疆人都要這樣。聽了這話我放鬆下來了,根據以往的經歷,我深信這種針對特定族群的陣勢不會對像自己這樣的人造成太大的損害。經歷了一場驚嚇,舌頭和上顎黏在一起,於是站起來想要倒杯水喝,可是警惕地望著我的那名武警戰士立刻喝令我坐下,並且陰著臉從抽屜裡取出一副手銬走過來,麻利地把我的雙手銬在了一起。這一切都發生在幾秒鐘裡,我一時難以接受,大喊:「你們這是幹嘛呀?怎麼能這麼對待我,我做了什麼?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武警戰士大聲呵斥道:「再說就給你上腳鐐!」
空氣像凝固了一般,我無奈地坐回到椅子裡。讓我冷靜下來的倒不是恐懼,而是隨遇而安的麻木心境。這種情感上的麻木,是我每次出入境時遭遇到超過我本身承受能力的緊張狀態後的慣常反應。終於,等到了烏魯木齊來的人。看到熟悉的女警官,我像遇到救星一樣站了起來並迎上去。這是我的責任民警張曉芳,搞「警民一家親」活動的時候,她還邀請我跟她一起去游過泳呢。她看上去四十歲左右,油黑的齊耳短髮和白皙的皮膚給她增添了幾分知性,要不是上眼皮有點耷拉,她的眼睛算是好看的杏仁眼。她擠出笑容說了聲:「啊,你回來了?」算是打了招呼,用下巴示意武警打開了手銬。
他們帶我上了飛往烏魯木齊的飛機,我被一個男便衣警察和張警官夾在中間。飛機起飛前,我們像其他乘客一樣簡單交流了幾句,張警官刻意與我保持距離,而扁平臉小個子便衣卻對我在國外從事的工作甚感興趣不停地問這問那,滿臉堆笑,完全不像一個執行嚴肅公務的人。他還提議互加微信,主動給了他的電話號碼。他說他叫烤肉串,我知道這只是一個網名,問他怎麼起了這麼一個名字,他說隨便起的。
烤肉串的親切使我的精神鬆懈下來,進入了昏昏欲睡的狀態。過去的兩天我幾乎沒有闔眼,不確定的狀態讓我十分焦慮不安,無數種可能的情況在我的腦子裡像小老鼠一樣竄來竄去,令我亢奮不已。四小時二十分鐘的航程不算太長,但是也足以在睡眠中解除困乏。既然已經像網飛蟲一樣被蜘蛛網黏住,轉機去伊犁探望媽媽也幾無可能,那就隨他們處置吧。這樣想著一陣睏意襲來,我漸漸進入了夢鄉。
天空布滿陰霾,颳著刺骨的寒風。我起晚了,因為害怕遲到後的罰站,發瘋似地往學校跑,可是學校不在了,那裡出現了一個又大又厚的黑鐵門。大門緊閉,我想進去可怎麼也推不開,繞著學校的圍牆走了一圈,發現已經不可能從禮堂後邊那個豁口鑽進去了。因為牆更高更結實了,上面還有鐵絲網。牆外的老榆樹還在,這使我安下心來。哼,你們休想害我挨剋。我爬上老榆樹,抓住伸展到校園裡的樹枝,像猴兒一樣盪進了校園。
音樂和口號聲。循聲走進禮堂,看到一群赤裸的青年男女一邊唱歌一邊手舞足蹈。啊,難道這就是那個傳說中人們永遠唱歌跳舞,不知憂愁的地方?對著我的是一個女人的大屁股。我躲在她的身後,裸體女人嘴裡不停地喊著什麼,弓背彎腰,使勁舞動雙臂打著節拍,兩腿之間的陰影就在我的鼻子下面,甚至聞到了她下體的氣味。面朝我的小夥兒和姑娘們似乎正傾盡全部心力,揚臉望著屋頂張開雙臂旋轉、旋轉再旋轉,彷彿他們可以由此升向天空!他們看上去像上了發條的玩偶,既無羞恥也無怨怒,歌唱舞蹈,不知疲倦。離我最近的是一個瘦高的小夥子,兩撇漆黑的眉毛,右眼烏青,下巴有一個胎記,似乎在笑,但那只是面部肌肉的震顫。我儘量讓自己盯著女人的身體,她們擺動著腰肢,有的纖細,有的臃腫,形態各異的乳房在胸前晃來晃去。突然,有胎記的大哥哥朝我大聲喊了起來:「巴奴──快逃,巴奴──快逃!」我扭頭看到一群僵屍一樣面目可憎的男人正站在我的身後。我衝出禮堂,卻怎麼也搆不著那個伸進校園的樹枝。僵屍變成了手提長槍的士兵,他們並不上來抓我,獰笑著看我徒勞地跳啊跳……
我在驚恐中醒來,有片刻功夫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看到身邊的兩個人才意識到自己正被押解回家,不禁心情黯然起來。到了烏魯木齊機場,烤肉串說把你交給轄區民警了,沒有什麼大事,不用擔心,有事可以找我。說完就朝停車場方向去了。便衣的態度可以說是溫和親切的,這使我感覺十分困惑,難道這是暴風雨前的異常徵兆?
我和轄區民警上了一輛在便道等候的警車,車上有一位少女坐在司機旁邊,正跟司機說說笑笑。這種輕鬆的氣氛讓我感覺自己的夢境是那麼地荒誕。我主動跟他們打了招呼,還問司機這個小美女是您女兒嗎?司機笑了笑對這個套近乎的問題算是作出了禮貌的回應。我還想跟張警官敘敘舊,可是她臉上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讓我退縮了,不過她還是讓我坐在身邊,也許覺得我沒有逃跑的機會,或者並沒有把我當成犯人。幾個人輕鬆地一路寒暄著開出了機場高速公路。北京時間兩點十五分正是烏魯木齊的午休時間。新疆警察對我的態度始終是禮貌和溫和的,這讓我感覺自己似乎受到了優待。
到了派出所,張警官刷卡開了電動門,穿過一樓值班室走到盡頭的樓梯口進入地下室,映入眼簾的是一排帶鐵柵欄的囚籠,裡面的人聽到動靜走到鐵柵欄邊向外張望,我看到一雙深邃憂傷的眼睛,卻不忍直視,忙別過臉看向別處。警官帶著我穿過囚籠走到一間像實驗室一樣的房間,吩咐她的同事先弄「五採」然後帶我去一號審訊室做筆錄。
一個留著平頭穿著白大褂的年輕民警滿面笑容地向我解釋說,例行公事啊,不要緊張,現在先採血。聽到他說維吾爾語時略帶哈薩克族口音,我馬上改用哈薩克語回應他:「當然,這是你的工作,採就採唄,正好可以提供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與其說我的配合態度,不如說是我地道的哈薩克語讓他釋放出了更多的善意。於是我們在笑談中很快完成了採血採指紋、拍攝多角度照片,取瞳孔紋樣、讀短文錄聲音。生物資訊採集進行得十分順利,白大褂不停地誇我素質高,配合得好。
白大褂領著我穿過一排拘留室,刷卡打開一扇電動門,指了指那個開著的門說了聲「進去吧」。身後的鐵門閉合相撞的聲音令我心驚膽戰。一號審訊室大概九平方公尺,方方正正,正對著門擺著一張辦公桌,上面是一台電腦,屋子對面的牆上有一個長方形的電子螢幕,顯示的:2017.06.17, 15:08。正中擺放著一把可以上鎖的椅子,我想這就是傳說中的老虎椅了。我打算坐進去,可是張警官示意我坐在離她最近的一把普通的椅子上,她自己坐在電腦前開始錄口供。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