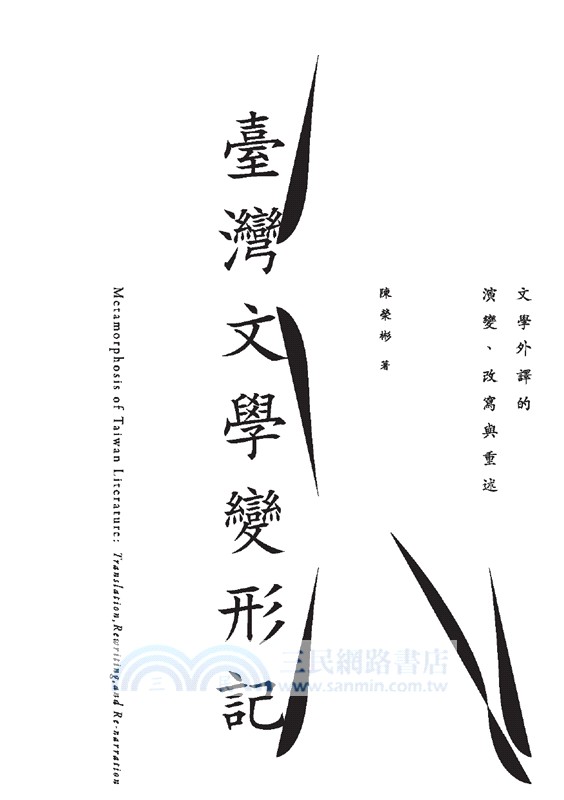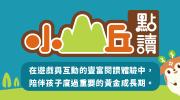臺灣文學變形記:文學外譯的演變、改寫與重述
商品資訊
系列名:臺灣研究系列
ISBN13:9786267612255
出版社: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作者:陳榮彬
出版日:2026/01/07
裝訂/頁數:平裝/320頁
規格:21cm*14.8cm*2cm (高/寬/厚)
重量:500克
版次:初版
商品簡介
國內第一本臺灣文學外譯研究專書
解析臺灣文學如何從「自由中國」走向世界
▍臺灣文學的翻譯,是一趟漫長且仍在持續的「變形記」 ▍
● 白先勇《臺北人》英譯時,書名改為《遊園驚夢》(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 《孽子》的英文版書名是《水晶男孩》(Crystal Boys),義大利文版又變為《夜晚的師傅》(Il maestro della notte)
● 鍾理和的〈假黎婆〉,既可以英譯〈我那來自山地的祖母〉(My Grandma from the Mountains),也可以回到〈假黎婆〉(The Gali Wife)
● 為了更加理解小說背景,陳耀昌《傀儡花》的英文書名添增了副標「關於1867年台灣的小說」(A Novel of 1867 Formosa)
十九世紀初期,當德國文豪歌德在倡議「世界文學」時,主張翻譯能促進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的理解,甚至樂觀地認為文學交往能帶動政治、經濟等其他活動;然而此一概念也引發更多討論:當文學作品翻譯時,面對的不僅是將一個語言過渡為另一個語言,同時亦包含──「文本」的意義真的有辦法被完整翻譯嗎?
學者陳榮彬鑽研臺灣文學翻譯研究十數年,於本書中,他梳理了聶華苓、白先勇、鍾理和、夏曼.藍波安、田雅各與陳耀昌等人的外譯作品。書中結合勒菲弗爾的「重寫」理論,揭示意識形態與美學如何影響臺灣文學英譯選集的發展,並藉由達姆洛許的「世界文學」相關論述,闡明文學建構主體性的必要;同時延伸夢娜.貝克四種策略,講述白先勇的《臺北人》、《孽子》、陳耀昌的《傀儡花》等,如何利用導讀、書名、譯者序等,讓異文化讀者更理解文本;以及皮姆的「行動者」理論,揭示產業鏈的各專業工作者,如何影響文本的生產過程。
從一個語言過度至另一個語言,陳榮彬認為文學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一種文化的翻譯。臺灣文學翻譯透過漫長且仍在持續的「變形」,不僅將島嶼的故事傳遞出去,更是在每一次的閱讀中重新定義自身,並在世界文學的宏大星圖裡,找到一個清晰、獨特、不容忽視的位置。
本書特色
▪ 臺大教授暨翻譯家陳榮彬睽違十年最新作品
▪ 國內第一本臺灣文學外譯研究專書
▪ 剖析臺灣文學如何脫離「新自由中國」的框架,逐步建立臺灣意識
▪ 解讀聶華苓、白先勇、鍾理和、夏曼.藍波安、田雅各、陳耀昌等作家的經典外譯作品
作者簡介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自二〇一一年即開設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學外譯的相關課程,除了介紹臺灣生態文學、都市文學、歷史小說的英譯作品,也與臺灣文學館合作開設「臺灣文學英譯工作坊」課程。譯者生涯迄今已作品超過六十種,並以海明威戰爭小說經典《戰地春夢》獲得二〇二三年第三十五屆梁實秋文學翻譯大師獎優選獎,也曾以Indigenous Voices: Short Stories by Taiwanese Writers一書譯介甘耀明、瓦歷斯.諾幹的短篇小說。長期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臺灣文學研究雧刊》、《編譯論叢》(以上皆收錄於THCI)與Kultura Kritika(收錄於AHCI)等學術期刊發表臺灣文學外譯主題的論文,亦有論文收錄於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Translation(2024年出版)。
序
臺灣文學外譯的多重視角
2013 年11 月,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舉辦了「臺灣文學外譯學術研討會」,我有幸獲選前往發表會議論文〈臺灣小說的英譯與實用—走入教室的臺灣小說翻譯作品〉,這篇論文可說是我在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累積兩年臺灣文學授課經驗的心得。當時的臺大因為是全英語教學,學生大半是不諳中文或中文程度不高的國際生與外國交換生,也促使我開始挑選英譯的臺灣文學作品當教材,最後不但開發出「戰後臺灣歷史小說導論」、「臺灣小說與戰後都市經驗」、「臺灣生態文學導論:書寫山林與海洋」、「臺灣戰爭小說導論:從反共小說到後現代」與「戰後臺灣歷史小說導論」等課程,也讓我一窺1950 年代末期以降臺灣小說英譯史的全貌。
不過,教學跟研究畢竟是兩回事,想要把會議論文裡的教學經驗轉化為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對於當時的我而言可說是不小的挑戰。我在攻讀比較文學博士期間,因為半工半讀、修課時間有限,始終錯過中研院特聘研究員李奭學老師(時任研究員)在輔仁大學比較文學所開設的翻譯課程,因此對於翻譯研究可說是個門外漢。當我要把〈臺灣小說的英譯與實用〉這篇會議論文改寫成期刊論文投稿時,一開始因為欠缺翻譯理論的視角,過程並不順利;所幸在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任教後,承蒙同事兼同門師兄馬耀民的指點,認識了操縱學派的翻譯理論大師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經典之作《翻譯、重寫與文學聲譽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自此才算是正式踏入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在勒菲弗爾的理論視角加持下,該篇會議論文也就順利改寫成〈英譯臺灣小說選集的編選史研究—從1960 年代到1990 年代〉(即本書第二章),並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在這篇論文發表後,我感覺到這是個值得耕耘的領域,持續在臺灣文學館的《臺灣文學研究學報》、臺大臺文所的《臺灣文學研究雧刊》等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經過十幾年積累,才有《臺灣文學變形記》的問世。
綜觀這本論文集的內容,其實正足以反映出我個人在翻譯研究方面的學術偏好。雖然最早是透過操縱理論(manipulation theory)進入這個學術領域,但基本上我自詡為「翻譯史」研究者—這當然跟我對於歷史的偏好有關,主要更是因為翻譯研究雖以文本為研究對象,但沒有譯者(以及與他們密切相關的專業人士,如學者、編輯等)何來譯本?因此本書的讀者不難發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另一位重要學者安東尼.皮姆(Anthony Pym)的身影。對於皮姆理論分析架構的應用,個人認為最完整地反映在本書第一章〈創作、編輯、翻譯:譯者聶華苓與冷戰下的臺灣文學翻譯〉。而除了翻譯史以外,近年來我因為執行科技部(目前已改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接觸各種類型的臺灣文學文本,在研究不同文本時、因應文本內容差異而陸續又採用了描述性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以及「論述」(narrative)概念等不同研究取徑,正因如此才會有這本論文集的問世。
從「折射」到「重寫」
本書的標題「變形記」,意在捕捉臺灣文學在跨越語言與文化疆界時所經歷的深刻質變。根據我的研究心得,翻譯研究的本質旨在追求「為何」與「如何」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因此臺灣文學在經過翻譯後為何會「變形」,而且又是如何「變形」,就變成臺灣文學外譯研究的核心。從翻譯研究的視角看來,我所指的翻譯並非傳統觀念中單純的語言轉換或講求「對等」(equivalence)的跨語言傳遞,而是一種更具能動性與操縱性的文化實踐。1980 年代以降,西方翻譯研究發生「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這當然與文化研究等學門的興起密切相關),學術典範從追求語言層面的忠實(fidelity),轉向探討翻譯在文化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脈絡下,比利時學者勒菲弗爾的理論成為理解此一變形過程的關鍵。
勒菲弗爾提出,翻譯的本質是一種「重寫」(rewriting)。此概念是他早期「折射」(refraction)理論的深化(詳見本書第五章):任何文本在進入一個新的文化系統時,必然會像光線穿過稜鏡一樣被折射,其形態與意義均會發生改變。從勒菲弗爾的理論視角看來,不只是翻譯,就連文學批評、選集編纂、文學史書寫等活動,一樣都是「重寫」的具體形式,共同塑造了讀者對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乃至一整個時代的文學之認知與想像。具有強大「重寫」功能的不只是選集,其餘如譯註、譯序、學者寫的前言、推薦文等等,從稍後我將予以闡述的「論述」視角看來,都是重塑文學作品,進行文學詮釋的重要依據。
勒菲弗爾認為,此一「重寫」過程並非任意為之,而是受到兩大宰制性力量的制約:意識形態(ideology)與詩學(poetology 或 poetics)。意識形態,指得是社會中關於「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主導觀念,其力量往往來自於勒菲弗爾所稱的「贊助者」(patronage)─包括政府機構、出版社、基金會等權力實體。1960 年代冷戰高峰期,由美國新聞處 (USIS)資助的一系列「新自由中國」(New China)英譯臺灣小說選集,便是一個鮮明的例證。這些選集的編選與出版,首要動機即是建構一個與共產中國相對立的文化形象,意識形態的考量遠遠凌駕於純粹的文學價值之上 。正因如此,當時入選的作家,除了青壯世代的林海音、張愛玲、聶華苓等人,還有幾位才二十出頭的《現代文學》雜誌創辦人: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與陳若曦等:他們不見得是多麼成熟的作家,但卻因為代表「新自由中國」的新生代文壇而入選。當然,他們之所以入選,也不能排除皮姆所強調的翻譯史「網絡」(network),因為他們普遍受到臺大外文系的老師夏濟安欣賞,而夏濟安則是該選集系列重要旗手吳魯芹(Lucian Wu)的文友:他們倆在文學理念方面聲氣相投,曾經共創學院派期刊《文學雜誌》。
與之相對的「詩學」,則指涉特定文化內部主流的文學慣例、美學標準與形式要求。在某些情境下,詩學的影響力會超越意識形態。例如,張誦聖與安.卡佛(Ann Carver)合編的《雨後春筍:當代臺灣女性作家的故事》(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或是馬嘉蘭 (Fran Martin)編選的《天使之翼:當代臺灣酷兒小說》(Angelwings: 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其選文標準主要根植於特定的文學史脈絡(女性文學、同志文學的發展)與美學風格的考量,而非直接服務於某種政治宣傳。
意識形態與詩學之間的關係並非靜態,而是一種權力上的動態辯證。勒菲弗爾雖認為意識形態通常占據主導地位,但本書收錄的論文透過對臺灣文學外譯史的考察,揭示了更為複雜的翻譯文學史發展軌跡。在強勢贊助者的主導下,如冷戰時期的美新處,意識形態確實是決定性的力量。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當贊助者的政治意圖較為隱晦、或編選者本身具備足夠的學術自主性時,詩學的考量便可能成為主導文本變形方向的關鍵。以學者杜國清為例,就是一位憑藉自身堅定詩學觀而重寫臺灣文學史(將日本文學、美國文學納入)的重要「重寫者」(詳見本書第三章)。因此,理解任何一部翻譯作品的「變形」樣貌,都必須先釐清其背後意識形態與詩學力量的消長與權力平衡。
(未完)
目次
前言 臺灣文學外譯的多重視角
Part One 當臺灣文學走入世界
第一章 創作、編輯、翻譯:譯者聶華苓與冷戰下的臺灣文學翻譯
第二章 從自由中國到斷代史:1960 到1990 年代英譯臺灣小說中的臺灣形象
第三章 臺灣文學如何「入世」:杜國清與《臺灣文學英譯叢刊》
第四章 星球性、反全球化、地方知識:世界文學的轉變與臺灣原住民文學英譯
Part Two 經典翻譯的兩難
第五章 白先勇西遊記──如何翻譯?怎樣重寫?
第六章 重讀鍾理和〈假黎婆〉:論翻譯與譯註
第七章 田雅各〈最後的獵人〉英譯:異化與歸化的抉擇
第八章 從《傀儡花》到《Puppet Flower》:翻譯的重寫與重述
結語 重寫臺灣,譯向世界──臺灣文學外譯的歷史軌跡與文化政治
本書論文出處
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書摘/試閱
第五章 白先勇西遊記—如何翻譯?怎樣重寫?
《臺北人》與《孽子》之譯名
1970 年代後半,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成立「英譯中國文學」叢書,由該校中國文學教授李歐梵、羅郁正、歐陽禎擔任編輯,而劉紹銘雖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任教,但因為是印大校友,也加入了叢書的編委會。後來,叢書於1982 年推出白先勇短篇小說集《臺北人》的英譯本,但事實上,白先勇的合譯者葉佩霞(Patia Yasin)曾表示他們是在1976 年就展開了翻譯工作,可見這本充滿中國文化要素和語言藝術的文學作品在翻譯時可謂困難重重。另一個有趣之處是英譯本在出版時並未直譯《臺北人》的這個書名,而是借用了白先勇的代表性短篇小說作品〈遊園驚夢〉之名,將書名轉譯為《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後來到了2000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英對照版《臺北人》,雖然英譯文字大致上是採用印大的英譯本,但書名卻又改為直譯的《Taipei People》。
為什麼會有上述兩個不同的英譯書名?英譯本的編輯喬志高(George Kao)在中英對照版〈編者序〉裡面有非常明確的說明:英譯版原是1982 年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當時考慮到要適合英美讀者的需求, 並表示此書寫的不是臺北本地人, 因此採用書中的名篇《遊園驚夢》為書名: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副題: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現在這部中英對照版,我們決定回到原書所訂的名稱—《臺北人》, 英文直譯為Taipei People 以便存真,同時保留一點原文的反諷意味。
從喬志高的說法看來,隱然可以感覺到印大英譯版訴求的讀者是英美人士,直譯《臺北人》書名恐生困擾—因為書中主角都來自中國大陸,並非道地的「臺北人」,英美讀者不知箇中原由,難免感到困惑;港中大中英對照版的讀者很大一部分都懂中文,所以就改採直譯,把原有的反諷意味(主角都來自中國大陸,卻偏偏取名《臺北人》)予以恢復。
但「以便求真」這四個字堪稱關鍵:為什麼印大英譯版不用求真,但十八年後的港中大中英對照版就需要?還有,當初印大英譯版為了「不求真」是否做了哪些與原書有所不同的安排?
此外,白先勇的另一部代表性作品《孽子》的英譯本由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翻譯後在1990 年出版,書名也非直譯,而是被改成了《Crystal Boys》,後來1993 年由法國漢學家雷威安(Andre Levy)操刀的法文譯本在1993 年出版,則是選擇直接把《Crystal Boys》這個書名再轉譯為法文《Garcons de cristal》,十三年後出版的荷蘭文譯本《Jongens van glas》也是直接採用同一個書名。值得細究的是,2005 年由義大利杜林埃諾蒂(Giulio Einaudi)出版社推出的《孽子》義大利文譯本並未採用英譯本的處理方式,而是重寫為《Il maestro della notte》—這書名的意思是「夜晚的師傅」。10 如此看來,《孽子》又是另一個「不求真」的例子,而且我們同樣也可以追問,英、法譯本的書名翻譯為什麼都「不求真」?義大利文版書名為什麼又與英、法譯本不同?
雖然白先勇的兩本代表作都有譯名顯然不同於原著的現象,但過去長久以來,關於《臺北人》英譯本的研究,主要都是聚焦在譯文內容,而且以「自譯現象」的研究居多,例如吳波於2004 年發表的〈從自譯看譯者的任務—以《臺北人》的翻譯為個案〉、史慧於2016 年發表的〈白先勇小說自譯區別性策略研究—以《臺北人》文末註釋為例〉。另外也有Qiongfang Zhang 撰寫的〈翻譯策略與文化立場:《臺北人》中英對照版的研究〉(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Stand: A Study of th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Taipei People, 2019)、李明哲的〈得魚忘筌,得意忘言?—淺論白先勇《臺北人》英、日譯本之得與失〉(The Gain and Loss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 Japanese Renditions of Pai Hsien-yung’s Taipei People, 2021),兩者都是從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問題去檢視《臺北人》英譯本。
相較之下,關於《孽子》的翻譯研究,則是往往把酷兒研究與翻譯文本的分析予以掛勾,但是在進行文本分析之餘,兩者的論述都能意識到書名改譯成《Crystal Boys》之後,對於原書名甚至整本書產生了哪些影響。首先是美國學者白安卓於2017 年發表了〈全球酷兒: 英譯的臺灣同性情慾〉(Globally Queer?: Taiwan Homosexualities in Translation)一文,指出譯者葛浩文選用的書名一來略去了「孽」一詞帶有的佛教「業報」(karmic retribution)概念,二來這書名雖然讓讀者比較能夠進入小說的同志情愛脈絡,但卻淡化了白先勇強調的「父子關係」(male filiation)。另一篇代表性論文〈同志文學翻譯之敘事建構 : 以白先勇作品《孽子》的英譯為例〉,由中國學者李波撰寫,發表於2020 年,他採用翻譯研究學者夢娜.貝克(Mona Baker)於《翻譯與衝突:從論述的觀點來說明》(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一書提出的理論架構,在對譯文進行細讀式的分析後,認為英譯本「無論是封面設計、導語、譯者前言、註釋等副文本手段」都促成了「譯者重新定位自己、譯文讀者以及該時空涉及到的其他參與者」,因此翻譯顯然不只是簡單的語言轉換。
由此看來,白安卓與李波的兩篇論文深具啟發性。首先,雖然他們談的都只是《孽子》一書的英譯本,但兩者的相關論述應該也可以延伸運用到法文及義大利文兩個譯本,尤其是追溯白先勇的小說從《孽子》變為《水晶男孩》,再從《水晶男孩》變為《夜晚的師傅》的過程。其次,《臺北人》的書名英譯從《遊園驚夢》經過十八年再變回《臺北人》,是不是也跟《孽子》的書名改變一樣,需要經過貝克所謂的「論述重塑」(narrative reframing)過程?如果需要的話,怎樣重塑?是不是像李波所觀察到的那樣,「導語、譯者前言、註釋等副文本」發揮了功效?這兩個問題是本文最為關切的兩個題旨。
(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