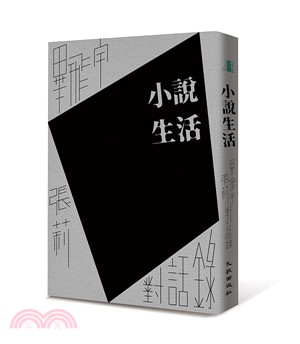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31元
商品簡介
評論家張莉、小說家畢飛宇,透過這場極具邏輯的對談,梳理出畢飛宇的創作歷程、寫作理念。他們從成長談起,關於父親的邏輯教育、詩詞啟蒙,到閱讀知青文學、先鋒文學、哲學名著、中外名著對他產生的影響;畢飛宇也真誠分享了許多有趣、精闢見解,諸如成功拆解海明威小說脈絡的激動、從城牆磚頭靈光閃過找到中國歷史怪現象、批判與懷疑是小說家的氣質、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人物書寫觀念先行同等重要、汪曾祺與杜斯妥也夫斯基不可學習模仿……這些經驗與理念,爆出了驚喜的火花,也讓人了解,他如何成為無法被定位、也拒絕被定位的成功小說家。
畢飛宇的成功,絕非憑空而來,他的養分來自大量閱讀、學院系統訓練,他長期關注社會與人,秉持著作家的社會責任,透過小說向社會表達他的批判與質疑。張莉的精心提問,畢飛宇幽默生動的答問,率真地展露他驕傲、刻苦、執著的一面,打破一般訪談式文章的生硬拘謹,不僅內容扎實飽滿,讀來格外酣暢痛快,且收穫豐盛。
作者簡介
一九六四年生於江蘇興化。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教師,後從事新聞工作。八○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文字敘述鮮明,節奏感掌握恰到好處。曾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百花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推拿》獲選為《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
著有《玉米》、《青衣》、《平原》、《造日子》、《推拿》等書。
張莉
河北保定人。學者,批評家。二○○○至二○○七年先後就讀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出版《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魅力所在:中國當代文學片論》、《姐妹鏡像》等專著。論著獲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中國婦女研究會第三屆婦女/性別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第十三屆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一四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等。曾任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現為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
序
張莉
在我的理解裡,寫作、閱讀、批評都是我們感應時代和社會、確認自我的途徑,也是我們在陌生人中尋找同道、使自己不再孤單的方式—透過那些優秀寫作者的語言和文字,我們享受在茫茫人世中的不期而遇,延展對生命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擴大自身認識世界的邊際。
和畢飛宇先生相識是二○○七年十月,那年我剛從北師大博士畢業,正在南開大學做博士後。我和我的好朋友,彼時正在北京大學做博士後的韓國學者任佑卿女士相約去太原,參加女性文學年會。畢飛宇則是那次會議的特邀嘉賓。會議間隙,我們三人坐在了一起聊天,都是純粹的文學話題,關於魯迅、張愛玲、小說閱讀及中外文學翻譯等等。第二年,當我從現代文學研究轉向當代文學批評時,我們的交流話題便也開始涉及當代文本。
近四五年來,畢飛宇先生和我有過三次對談:︿理解力比想像力更重要﹀、︿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作家和批評家可以互相照亮對方﹀,均為期刊報紙所邀,在業內也都有反響,尤其是︿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一篇,作為附錄收入︽推拿︾︵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一年版︶、被︽PATHLIGHT︾︵︽人民文學︾英文版︶夏季版轉載,在網絡上也流傳頗廣。此為進行這次長篇談話的前提和基礎。
二○一三年十月,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邀,我們用兩天時間在南京龍江﹁月光曲和﹂咖啡館裡完成了長篇對話的大部分內容,之後又各自進行補充修正,使之成為今天的對談錄。對談錄希望以一種家常、樸素、鮮活的方式回顧畢飛宇的成長環境、工作經歷、創作體會,分享我們對經典文學作品的理解和認識。當然,隨著對談的進行,我對畢飛宇的了解也越來越深入:眼前這位小說家絕非﹁憑空而來﹂,他有經年累月的閱讀和思考、他有不為人知的艱苦的自我訓練,他有他的儲備、他的沉積、他的學養。某種意義上,這部對談錄裡潛藏有鄉下少年畢飛宇何以成為當代優秀小說家的諸多祕密。
與畢飛宇有過對談的朋友都有體會,他是具有人格魅力的談話對象—他的講述總是那麼生動、形象、深刻、風趣,舉重若輕,令聽者如沐春風,過耳難忘。坦率地說,這些年來,與畢飛宇的交流經驗對我彌足寶貴,那既是知性意義上的長見識、受啟發,也是純粹意義上的愉悅享受。誠摯感謝畢飛宇先生一路以來給予的信任和支持;作為同行,我要向他時時處處閃現的語言天才和卓越的敘述本領表示敬意。
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趙萍女士,沒有她的策劃、督促、組織,就沒有這本書的問世。感謝李殷小姐,本書中鮮活的現場圖片都由她拍攝。
二○一四年一月十二日於天津
目次
成長
1屁股決定腦袋
2真實的邊界
3用哲學思索這個世界
4思維要有品質
經歷
1孤獨是有價值的
2自行車上的堅持
3《雨花》中綻放
4城牆下的夜遊者
5《孤島》的心很大
6作家與批評家的有效對話
7魯迅文學獎
8告別先鋒的〈敘事〉
9為人的姿態
10電影《推拿》
11《青衣》、《玉米》的譯介
12南大教授
質地
1物理學之後
2歷史的腳手架
3地球上的王家莊
4「里下河小說流派」
5寫作的難度
6用語言確認世界
7寵愛「人物」
8及物的日常生活
9尊嚴是平等
閱讀(一)
1唐詩
2《紅樓夢》與《水滸傳》
3《聊齋志異》
4魯迅
5張愛玲
6周作人
閱讀(二)
1、歐美文學
2、俄羅斯文學
3、現代主義文學
寫作歷史
1〈敘事〉
2〈哺乳期的女人〉
3〈是誰在深夜說話〉
4〈懷念妹妹小青〉
5〈地球上的王家莊〉
6〈大雨如注〉
7短篇和唐詩
8 《玉米》
9《上海往事》和《那個夏季,那個秋天》
10《平原》
11《推拿》
12《蘇北少年唐吉訶德》
後記 張莉
書摘/試閱
歷史的腳手架
張 莉─王彬彬在那個跋裡說,你對歷史特別感興趣。你早期寫作時對歷史的那種興趣到了執迷的程度。後來許多人覺得沒了,我感覺其實也是有的,你小說裡有一種強烈歷史感,到現在也是有的。
畢飛宇─我小說裡面歷史感剝離比較厲害的是《推拿》,《推拿》的歷史感沒有那麼強。這個是我的一個嘗試。對,一個嘗試,這個我要對你慢慢說。《推拿》的寫作是有精神背景的。你知道嗎,我跟陳曉明有一段很重要的對話,他在會議上重點強調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他為什麼要說這個呢?曉明教授有一個看法,他覺得中國的小說家其實是有先天缺陷的,離開了歷史這個腳手架以後,中國的小說家幾乎不會寫作。就在這次會議上,我和曉明爭論起來了。我的理由也很簡單,一九八九年,隨著「蘇東波」的解體,冷戰結束了,「歷史」似乎「終結」了,但是,對中國作家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而言,歷史終結了沒有?沒有。「冷凍的歷史」還在那裡。爭論規爭論,其實曉明的一句話還是說到了我的心坎裡了,那就是中國作家在離開「歷史這個腳手架」之後到底還能不能寫作。我是第一次對外界披露這個事情,為什麼我以前對媒體沒說呢,因為這個話題過於專業了。客觀上,曉明刺激了我的思考。
張 莉─那是在寫小說之前就有的念頭嗎?
畢飛宇─有這個念頭。所以你注意到,在《推拿》這個作品當中,我也尋求一個極端,即便是有可能跟歷史有關的,我把他剝離了,我既然要嘗試一下,我就嘗試到底。《玉米》是標準的歷史寫作,面對的是文革,〈敘事〉面對的是家族史,《雨天的棉花糖》面對的越戰,《平原》複雜一些,面對的是反右和文革。《推拿》是一個沒有腳手架的作品。它是否成功,不在我的考量範圍裡面,我只是嘗試一下這麼做。
張 莉─你和他討論是在什麼會議上,哪一年?
畢飛宇─二○○五年,在遼寧的錦州,一個長篇小說研討會上,他一上來就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我,我那時候《平原》剛剛寫出來。
張 莉─他是不是覺得,你《玉米》已經寫完了,怎麼又寫了一個和文革有關的東西。
畢飛宇─是。他是善意的,他認為我應該嘗試一下非歷史敘事了,我知道的,他對我有期待。應當說那次會議並不愉快,當然,主要不是集中在我和曉明之間,但是,對我有啟發。今年的三月,我們在威尼斯巧遇,喝酒的時候我們再一次提起了這個話題,歷史是不是「終結」了,我至今保留我的看法,但是,一個小說家嘗試的願望和勇氣不該泯滅。
也許我還想說一點別的,我很不喜歡中國文壇現在的風氣,那就是規避爭論。大家都怕一件事,那就是「得罪人」,無論遇上什麼事,都是微笑,然後呢?「挺好」,「滿好的」,大家都在比試誰更有親和力,這很糟糕。當所有的人都在爭著「做好人」的時候,這個時代就注定了是平庸的,為什麼?我們主動放棄了自由,自由熄滅了,生命就枯萎了。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只有江湖之爭,很少有真正的思想之爭。爭論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哪,有趣,充滿了知識和智力的美,我和那麼多人爭論過,從來都沒有影響友誼。
張 莉─關於歷史,這個我要多說幾句。一個好的文本應該有可以使作品脫離具體語境的能力,比如《平原》和《玉米》,離開了文革語境,小說還在那裡的,那些人那些事也是在的,這小說和文革並不全是點對點的關係。
但是,我堅持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有他的歷史感,應該有他的歷史情懷。沒有歷史感的作家,很容易滑進歷史虛無主義。一個大作家,一定要有他的獨特的歷史感,對他所處的時代、所經歷的歷史要有獨立思考和認知能力,不能剝離,不能對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視而不見,一定要有介入社會現實和歷史的勇氣。前幾天讀《歷史與反覆》,柄谷行人對村上春樹小說中的歷史虛無主義進行了批評,很對。村上春樹有一種「去歷史化」的傾向,而一位嚴肅的小說家要對此保持足夠清醒。另外,關於小說是否依賴歷史,也要看我們怎麼理解歷史。比如《推拿》,你說這裡面沒有歷史嗎?小說中關於世紀之交人們內心焦灼的書寫是不是一種歷史的書寫呢?〈相愛的日子〉、〈大雨如注〉中沒有寫特定歷史場景,但它內在裡有一種深切的現實關懷,我認為這種情懷很重要。我要重複一遍,我對那種純粹脫離歷史的寫作很警惕,也反對。
畢飛宇─對作家來說,歷史真的就是一條蛇,有人怕,有人愛。害怕的人見到有人把蛇當作寵物來飼養,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會說以後的創作一定會離開歷史,不會說這樣的話,但是《推拿》這樣的作品,離開這個腳手架,我依然把這個建築給支撐起來了,我也挺高興。我覺得一個作家做這樣的嘗試是有必要的。說起這個來,我特別想補充一下。大概是九九年還是二○○○年左右,有一天,我在一個什麼場合碰到了敬澤,他叼著煙,拿著一本刊物,看到我的時候,很不高興,他在那兒自言自語,他媽的,離開了「我」,怎麼都不會寫小說了。我把刊物拿過來一翻,整個刊物全是第一人稱小說。他是做刊物的,他敏感,我一想,天哪,那幾年我的小說基本上也是第一人稱的。第一人稱當然沒有任何不對,但是,我立即就想到了一個問題,我是一個寫作的人,如果用第三人稱都不會寫,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告訴我自己,該把第三人稱小說的這一門課給補上了。小說是自由的,這個還要說麼,可是,馮唐有一句話我特別同意,小說之所以是小說,它是有它的「金線」,它有它最基本的一些要求,每一個「行當」都是這樣。一個作家只會第一人稱敘事,沒問題,但他一定有缺陷,這個同樣沒有問題。同樣,到了二○○五年,陳曉明的那番話對我也有啟發。我很敏感,和朋友相處的時候尤其是這樣,我的心始終處在一個開放的姿態裡,這個開放其實就是學習和吸收。越是喜歡自作主張的人越是要吸收,否則,你會越來越枯瘦,最後只剩下光禿禿的「我」。
張 莉─第一人稱泛濫很久了。喜歡使用「我」,其實就是依賴個人經驗,這也不是中國作家的問題,幾乎現代主義以來的很多作家都喜歡使用這樣的方式進行創作。作家們渴望創造一個有現代性特徵的自我。讀柄谷行人時,他說日本現代文學產生了一種自白制度,通過這個制度,它創造出了現代意義上的「我」和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很對。可是,這種定位方式也引發了我們讀者的新困惑,用「我」講故事,小說其實進入了一個心理和個人身分認同的領域。但如果這種敘述泛濫,也便沒有了創造性和獨特性,當所有文本中全都是「我」的時候,其實就是沒有了「我」,「我」的生活方式變成了公共經驗和公共知識。某種程度上,這種主觀性特別強的創作方式反而會成為複製記憶和經驗的藉口,使小說進入死胡同。這也會使作家忽略,小說本身應該是一個自足的空間,故事應該有自己的動機背景,一個小說人物為什麼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它有一個自足的在文本空間可以成立的邏輯。那種依賴個人經驗的自傳體小說方式會使作家完全忽略這一點。──說起來,當時李敬澤的說法也是「聽者有意」吧,有些人可能當耳旁風一樣聽了也就聽了,你看當時關於「我」的小說都成災了,現在也挺多的。回過頭說第三人稱的引入吧,這對你寫小說很關鍵,《青衣》之後,一下子不一樣了。
寵愛「人物」
張 莉─你說先鋒文學的問題是沒有人物,你是怎麼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畢飛宇─中國的先鋒小說是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繼承者,我發現小說人物退場不是在先鋒小說那裡,是從博爾赫斯那兒,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讀到了一本奇書,那就是霍金的《時間簡史》,《時間簡史》的表述很有意思,我始終不覺得這是一本關於科學的書,相反,我覺得它是小說裡的一個宏觀場景描繪,帶有天才的玄思性。我承認我讀不懂,可是,有時候,讀不懂是一種奇妙的吸引,它會激發你一點一點的讀下去。它讓我想起了另一本書,那就是康定斯基《論藝術的精神》,它也有這種特徵。後來,我又想起了一個人,那就是博爾赫斯。我讀博爾赫斯是大學階段的事情,迷戀得不得了。可是,等我一九九四年的夏天再一次閱讀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博爾赫斯的表述方式和《時間簡史》差不多,就是玄妙的場景,人物其實不重要,都是為場景服務的。
張 莉─這個觸動了你。
畢飛宇─我在一九九四年的時候讀小說的能力已經比大學時代提高了,我很慌。我在骨子裡是個農民,相信多子多福。我希望我有一大堆的孩子,玩丁克我是不喜歡的。
張 莉─所以,你渴望你的小說有自己的人物,希望有一個文學的家庭,兒孫滿堂。
畢飛宇─是這個意思。沒人物我總是不踏實。
張 莉─在小說中,與其說人物,不如說人最重要。如果有一天,小說中的人淪為寫作/語言實驗的工具和道具,小說的枯燥和無趣便開始了。回過頭來看,先鋒小說中的人太平面了。它完成的只是詞語和形式的革命。你開始對小說人物有想法後的小說是《青衣》、〈玉米〉、〈玉秀〉、〈玉秧〉,這些小說名字也說明,人物是你最關心的。──我想到個問題,都說你是你寫女性最好的作家,這是不是從白燁那個評論開始的?
畢飛宇─應該是。這句話開始還只是小範圍的一個說法,後來,媒體知道了,媒體知道了之後,這就成了標籤了。
張 莉─人總是會被貼上各種標籤,關鍵是我們怎麼看這些標籤。
畢飛宇─關於標籤我想說幾句,從不接受,到處之泰然,這裡頭也有一個過程。我怎麼就處之泰然的呢?因為作品會覆蓋作品的,所以,問題的關鍵就變得簡單,你後面的作品有沒有能力覆蓋前面的作品。我不相信我的文學價值就是「寫女性」。
張 莉─只要一個人強大,前面的標籤很快就會被覆蓋,過眼雲煙了。
畢飛宇─我也沒多大的野心,就是想再多塑造幾個人物。
張 莉─這個理想也不小。人物是閱讀行為中最切實的憑藉物,借助於他們,讀者和作者的情感產生交匯。我教當代文學史,講到先鋒派作品,現在的年輕人理解起來是困難的,是隔的,脫離語境以後,他和這些文本完全找不到對接,情感上的對接沒有、人物沒有,很難理解。反而今天看起來有些文學成就打了折扣的小說,比如《平凡的世界》,或者《人生》,年輕人愛看,能懂。所以,你不得不承認,人物對小說世界而言,太重要了。人物可以使一位死去的小說家不斷地重生,不朽。當我們討論賈寶玉林黛玉就像講鄰居男女時,我們就能體會一位小說家何等偉大了,曹雪芹的意義在於,他使他的人物滲透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婦孺皆知。
畢飛宇─寫人物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你不孤獨,你每天都要和「那個人」或「那一撥人」在一起,這讓創作的心態變得很鬆弛。當年,我信了汪曾祺,小說就是寫語言,所以,那時候寫起來特別地枯,每天都是孤家寡人。「小說就是寫語言」,這句話用於短篇也許不錯,到了中篇就勉強了,寫長篇絕對不能相信,要不然會把人弄死的。語言是一個目標,但不是唯一的目標。
張 莉─你說這個,我想起莫言的一個演說,他說,最初他是追著小說走,等他意識到建造高密東北鄉後,小說開始追著他走,他發現原來有那麼多的東西可以寫,發現自己的文學地盤活了。對你來說,可能就是發現人物之後,小說天地一下子活起來了,有很多可寫的東西了。
畢飛宇─是這樣的。
尊嚴是平等
張 莉─你對人的尊嚴的關注,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只不過在盲人身上體現的更為明顯,即使是《玉米》,或者是〈哺乳期的女人〉裡面也有這樣的理念,比如說一個孩子的成長中,乳汁也是人的尊嚴的一部分,還有比如紅豆,一個戰俘,他的尊嚴在哪裡?但是到《推拿》的時候,這種對人的尊嚴的認識讀者理解起來更容易。我的意思是,你對人的尊嚴的關注,似乎比較早了。
畢飛宇─是的,尊嚴是我一直關注的一個話題,不過,很少有人和我談論。《推拿》之後,這個問題浮出水面了,和我探討尊嚴的朋友慢慢多了起來。
張 莉─《推拿》剛發表之後,尊嚴成了評論你的關鍵詞。
畢飛宇─尊嚴問題看似複雜,似乎是一個理論問題,其實一點也不複雜。在我的腦海裡頭,尊嚴問題其實就是一個平等的問題。平等的問題則更加簡單,簡單到不需要討論的地步,那就是「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你注意到了嗎,在西方重要的文獻裡,這個問題不討論,不搞邏輯論證。你不覺得奇怪嗎?西方人那麼在意邏輯,那麼在意論證,但是,在平等這個問題上,他們很「粗暴」,就是不論證,就是不講邏輯,直接就是「天賦」人權,人是「生而」平等。當然,這個與他們的基督文化背景有關。
張 莉─尊嚴應該是人與生俱來的。
畢飛宇─在這個問題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很大的,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很困難,與這種的文化差異有很大的關係。在中國,尊嚴不是一個「天賦」的問題,而是一個權力的問題。人們很容易把尊嚴問題和權力的力量對比聯繫起來,那麼好吧,我們來看一看。在專制制度底下,太監沒有尊嚴,這個是一定的,皇帝的權力最大,他就有尊嚴了?也沒有。皇帝依附於他的皇權,這是最高權力,在這個權力之下,作為皇帝的個人,也沒有一個有效的法律來保護他。一旦皇權喪失,你可以在皇帝的腦袋上拉屎,一刀捅死了算是便宜的,鞭屍都是常事。所以,尊嚴的前提是「拿人當人」,得有「拿人當人」的制度和「拿人當人」的法律做保證,太監連人的玩意兒都沒了,他低於人,皇帝高於人,他們不能算作主體意義上的人。不是人就沒有人的尊嚴。
張 莉─評論《推拿》時,我起了個名字叫《日常的尊嚴》。因為我認為尊嚴就應該是日常性的,時時處處人都應該有尊嚴。當然,尊嚴不是人想得到就能得到的,得靠爭取,也得有文化環境以及社會制度做保障。
畢飛宇─所以,尊嚴的問題一定牽扯到制度的問題,說到這裡話題就得大處走,那就是,一個作家如果你關心尊嚴問題,你就得有制度關懷。簡.愛對羅持斯特說:「在上帝的面前,我們是平等的」。這句話簡.愛說得一點都不錯,她和羅切斯特的腦袋上方的確有一個上帝,上帝是神,不是人。我們的腦袋上方是誰呢?是人,是權力更大的人。這一來問題就複雜得多。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文化是更容易產生權力的文化,也是更加依附於權力的文化。對我們來說,文化與權力是二位一體的,麻煩就在這裡。
張 莉─你分析過《紅樓夢》裡的劉姥姥帶著板兒去「打抽豐」的那段。進入大觀園之前,她不停的關照板兒,不停地扯板兒上衣的下襬。當然,從程度上說,劉姥姥的尊嚴似乎還達不到我們剛才所討論的那個高度,她只是自尊,愛體面,但是,她的自主意識問題又是那樣的醒目。
畢飛宇─我對劉姥姥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完全是因為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鄉村教師,特別地愛體面。因為特殊的家境,在走親戚的時候,我的母親一定會替我整理衣服,讓我呈現出「有家教」的樣子。某種程度上說,我的母親就是劉姥姥,我就是那個板兒。我讀《紅樓夢》的時候,劉姥姥的那幾下一直扯在我的背脊上,我甚至可以知道劉姥姥關照板兒的話是什麼。我為什麼那麼喜愛曹雪芹?是這樣,我有一個判斷,你一個做作家的,你也不認識我,可你都寫到我們家裡來了,都寫到我的身上來了,那我就一定會喜歡你。魯迅也是這樣,他也能把他的筆一直寫到我的家裡來。什麼是偉大的作家,可以把他的筆寫到千家萬戶的作家就是大作家。說到底,我的母親為什麼要對我那樣,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賤民,在我母親的那一頭,她就必須保證賤民的兒子不能再像賤民,你得「有個人樣」,對吧?
張 莉─這真是小說家的表達,把「筆一直送到千家萬戶去」,也就是送到千家萬戶的心裡去。
畢飛宇─曹雪芹描寫劉姥姥進大觀園的那些文字一點也不抒情,甚至相反,有遊戲的成分,很鬧,還「搞笑」,但是,每次讀到那裡我的心裡都非常難受,想哭也哭不出來。曹雪芹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只有洞穿了人生的人才有那樣的筆力,對著你的心臟,在很深的地方扎進去。
張 莉─回過頭來說尊嚴,有人把《推拿》定義為「關於尊嚴的書」,我想你大概不會反對。
畢飛宇─我不會反對。二○○六年,我打算寫《推拿》的時候,中國社會最流行的一個詞是什麼你知道麼?是厚黑。也許這個詞並不是在那一年流行起來的,可是,那一年我開始關注它了。厚黑。我在盲人的世界裡看到的完全不是這一路的東西。厚黑已經文化化了,成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一個時代的特徵。我一直在說,《推拿》也許不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我珍惜它,它的小體量裡有我關注的大問題。我想這樣說,在當下的中國,尊嚴不再是一個人的感受問題,它實在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