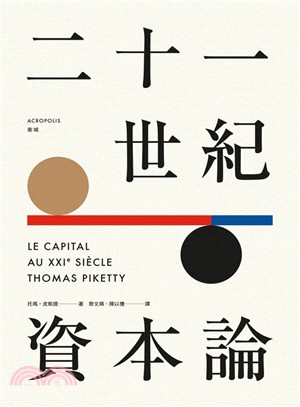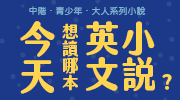商品簡介
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之作
貧富不均漸趨惡化已是當前極受熱議的問題。它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儘管眾說紛紜,但各種議論的資料根據似乎略嫌不足。
皮凱提從稅收與遺產紀錄著手,蒐集整理橫跨二十幾個國家、長達二百多年的數據資料,藉此分析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財富分配動態,從中提出一個系統而全面的解釋。
這個源自龐大實證資料的見解,其核心概念相當簡單:從歷史證據來看,資本報酬率通常大於整體的經濟成長率,也就是說,有錢人財富增生累積的速度快過一般人工作收入增加的速度,因此富者將愈來愈富,占掉社會大部分的所得與財富份額。
過去的主流意見認為,貧富差距拉大只是經濟發展的初期現象,到了成熟階段,分配不均的情況會逐漸減低。然而皮凱提指出,上述說法只是剛好看到二十世紀初期到中期的發展所導致的誤會。資本主義經濟在那一段時間出現貧富差距縮小的情況,主因在於兩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摧毀了許多原本的財富積累,以及當時的高累進稅政策。
皮凱提認為,各國政府應積極改革稅制,減低財富過度集中的趨勢,否則將危害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我們也很可能回到十九世紀那種貧富極度不均的景況。
本書出版後造成十分罕見的討論熱潮,在經濟學界引起強烈迴響,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亦撰文解析讚許,推崇「此書將改變我們思索社會與研究經濟學的方式」。
作者簡介
托瑪.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巴黎經濟學院(PSE)、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教授。二十二歲便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一九九五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經常替《解放報》撰寫專欄,偶爾替《世界報》撰寫社論。對經濟發展以及所得與財富分配之間的相互關係有重要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成果,針對高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份額的長期演變,他也是文獻累積的主要推手,如今都收在「全球高所得資料庫」(WTID)。二○○二年獲得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二○一三年獲得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四十五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詹文碩
法國電訊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巴黎經濟戰爭學院畢業。現任文饗文創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淡江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央廣法文部節目主持人。
陳以禮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法國里昂二大經濟史碩士班畢業,曾任電子時報研究中心、中經院國際經濟所研究員,現為德拉邦文化工作室成員,譯有《聽彼得杜拉克的課》《我們為什麼老犯錯》《數學之書》《華爾街的物理學》等。
名人/編輯推薦
今年甚或往後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克魯曼 Paul Krugma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一部切合時局的重要作品。
──史迪格里茲 Joseph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對一個舊主題提出新穎而有力的貢獻。
──索洛Robert M. Solow,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之作……將會影響往後的經濟分析(或許也包括政策制定)。
──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前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
光是確立這項事實的貢獻就值得一座諾貝爾獎。
──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前美國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
對資本主義內在動力的權威性論著。
──羅德里克Dani Rodrik,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序
引論(節錄)
財富分配是當今最能引起廣泛討論和熱烈爭辯的議題之一。然而,關於財富分配的長期演變,我們究竟知道多少?是否真如十九世紀馬克思所深信,私有資本累積的慣性必然導致財富與權力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還是如同二十世紀顧志耐(Simon Kuznets)所認為的,經濟成長、自由競爭與科技進步等平衡力量,將會在經濟發展的後期階段減低財富分配不均,使社會較為平和穩定?十八世紀以來財富與所得分配究竟如何演變?身處二十一世紀,我們又能從中獲取什麼教訓?
以上是我在本書嘗試回答的問題。謹此聲明:書中提出的看法並非完善。然而,相較於先前的相關研究,這些看法依據的是更為廣泛的歷史和比較數據,數據範圍涵蓋三個世紀、遍及二十幾個國家,同時亦立足於翻新的理論架構,對於各種趨勢及現象背後的運作機制能有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紀的經濟成長以及知識的廣為傳播,的確使得人類免於遭受馬克思所預言的末世景象,然則,資本及分配不均的深層結構卻未曾改變,即便有也未曾達到二次大戰之後幾十年內人們所樂觀想像的程度。一旦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產出及所得的成長率,如同十九世紀那樣,資本主義便會自動產生許多令人無法接受的人為分配不均,從而徹底瓦解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這正是二十一世紀極有可能重現的情況。所幸還有一些方法可以讓民主與公眾利益重拾對資本主義及個體利益的控管,同時又能避免重蹈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覆轍。本書嘗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就這個方面提出建議,本書的主要架構即是勾勒這些歷史經驗。
缺乏資料根據的辯論?
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論辯與政治論辯,往往充斥各種成見而缺乏事實根據。
誠然,每個人基於經驗而形成的關於所得與財富的直覺知識,儘管缺乏任何理論架構和可靠的統計數據,其重要性仍不可低估。比如在電影和文學,特別是十九世紀的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各個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和富裕程度的詳細資訊,尤其是當時種種不平等的深層結構、這樣的情況如何被視為理所當然,以及其對個人生命有什麼樣的影響。珍.奧斯汀(Jane Austen)與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的小說,對於一七九○至一八三○年間英、法兩國的財富分配狀態有非常精采的描述。兩位小說家對於所處時代的財富高低位階有切身的瞭解。他們精準掌握其中的無形界限,更明白此種限制對這些男男女女的人生、他們的聯姻策略、他們的希望與苦痛產生的必然後果。這些小說家栩栩如生、牽動人心的文字,勾勒出財富不均的深遠影響,可謂勝過任何統計數字與學術分析。
事實上,財富分配的議題太過重要,不應成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的專利。每個人都對這個議題深感興趣,這是一件好事。財富不均的具體事實明顯可見,人人皆有切身感受,自然也由此產生明確但互相衝突的政治判斷。不論是農民還是權貴、勞工或者實業家、服務生抑或銀行家,每個人都從自己所在的觀察位置,看到關於自己與他人生活條件的重要事實,見到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與支配關係,從而形塑出自己心中公平與不公平的概念。也因此,財富分配這個議題將永遠具有此一主觀而心理的層面,難以避免帶有政治性與互相衝突的特質,無法藉由任何科學分析平緩。幸運的是,民主政治永遠不會被專家政治所取代。
儘管如此,財富分配的課題仍然值得,也應該有系統、有方法地研究。因為少了資料、方法和界定清楚的概念,大概任何說法都可以講得通。某些人認為分配不均一直在擴大,世界也愈來愈不公平;另一群人則認為分配不均會自然縮小,或者會自動達到和諧,尤其不應該採取任何作為以免破壞這種美好的平衡。每個陣營都憑藉對方智識上的怠惰來為自己的智識怠惰辯護,在這種完全各說各話的狀況下,有系統、有方法的(儘管不完全是科學的)研究取徑便有其存在價值。學術分析永遠無法終結各種不平等所引發的政治衝突,社會科學的研究始終是、以後也還會是試探性的、不盡完善的。社會科學研究並不強求將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化為精確科學。然而,藉由耐心釐清事實與規律性,冷靜分析背後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機制,社會科學研究可以為民主論辯提供更多資訊與知識,並聚焦在有意義的問題上。這樣的研究可以協助重新定義民主論辯中的詞彙用語,破除成見與謊言,不斷質疑與檢視各種立場。這也是我心目中知識分子有能力也應扮演的角色,包括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內,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是公民,但又有幸享有較多時間可以做研究(甚至還可以領薪水,可以說得天獨厚)。
無可否認的是,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研究,往往是根據相對少量的可信事實和大量的純粹理論性臆測。在往下深入介紹本書當中集結使用的資料來源之前,我想先就前人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一個快速的歷史概觀。
馬爾薩斯、楊格與法國大革命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法兩國誕生之時,財富分配的議題便已經是各種研究分析的核心。大家都意識到許多重大變革正在發生,尤其是前所未見的人口持續成長、剛剛啟動的工業革命以及農村人口外移。究竟這些改變將會為財富分配、社會結構以至於歐洲政治生態,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對於一七九八年出版《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書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來說,人口過剩毫無疑問是最大的威脅。他的資料來源不多,卻能善加利用。馬爾薩斯尤其受到英國農學家楊格(Arthur Young)於一七八七及八八年,法國大革命前夕至法國旅行時所寫下的遊記所影響。楊格縱橫穿梭法國南北各地,從加萊(Calais)到庇里牛斯(Pyrénées),從不列塔尼(Bretagne)到法蘭琪康提(Franche-Comté),在遊記中記錄了法國農村的貧困景象。
這份精采的敘述並非完全不可信,反而還相當確實。當時法國人口遠較歐洲各國為多,是絕佳的觀察對象。一七○○年左右,法國人口已經超過二千萬,而英國才剛達到八百萬(單算英格蘭只有五百萬)。整個十八世紀,從路易十四末期到路易十六末期,法國人口穩定成長,一七八○年代已經接近三千萬人。各種跡象顯示,此一前所未見的人口劇變,確實導致一七八九革命爆發前的幾十年間,農民收入停滯不前而地租卻節節升高。儘管這絕非大革命爆發的唯一因素,但很顯然這樣的演變,只會使得當權者和貴族階級更加不受歡迎。
不過,這本一七九二年付梓的遊記也充斥著民族主義偏見和各種粗糙的比較。這位農學家對於路上投宿的旅館和餐廳女侍者的服裝很不滿意,筆下充滿不屑。他試圖從充滿瑣碎軼事的觀察當中,推導出普遍的結論。他特別擔心群眾的貧窮將引發政治動盪。楊格尤其確信唯有像英國那樣,將國會分成由貴族組成的上議院與平民組成的下議院,並讓上議院貴族享有否決權的政治制度,國家才能在一群負責任之人的領導下和諧發展。他確信法國於一七八九至九○年間決定將貴族和平民擺在同一個議院是沉淪的開始。可以說整本書因為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懼怕而染上一層陰影。只要談到財富分配,政治議題從來不會離太遠,而要跳脫所屬時代的階級利益與偏見更是難上加難。
馬爾薩斯牧師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名著《人口論》中,提出比楊格更極端的看法。他和同胞楊格一樣對於法國的政治情勢感到非常憂心,認為要避免同樣情形在英國發生,必須立即停止針對窮人的任何救濟措施,並且嚴格控管貧民的出生率,否則全世界終將走向人口過剩、混亂與貧窮。事實上,若不正視一七九○年代歐洲精英普遍恐懼法國大革命的現象,簡直無法理解馬爾薩斯各種推測的過度悲觀色彩。
李嘉圖:稀少性原則
要當事後諸葛,取笑以上幾位末日預言家當然容易。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發生的經濟與社會巨變,確實令人感到不安,甚至精神受創。事實上,當時多數觀察家都和馬爾薩斯與楊格一樣,對於財富分配和社會結構的長期演變,抱持相對悲觀甚至絕望的態度。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馬克思尤其如此,他們兩位堪稱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兩者皆認為一個人數不多的社會群體──對李嘉圖而言是地主,對馬克思來說是工業資本家──將無可避免地掌握愈來愈大份額的產出與所得。
李嘉圖在一八一七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他所關注的主要是土地價格與土地租金的長期演變。如同馬爾薩斯一般,李嘉圖手上幾乎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儘管如此,他對當時的資本主義仍然擁有切身的知識。生於猶太金融家庭、祖上來自葡萄牙的他,感覺上比馬爾薩斯、楊格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更能跳脫政治成見。他受到馬爾薩斯模型的影響,但又將其論點推得更遠。他對以下邏輯悖論尤其感興趣:一旦人口及產出持續成長,那麼相較於其他商品,土地就會變得愈來愈稀少。依據供需法則,此時土地價格和付給地主的租金應會持續攀升。長此以往,地主的收入在國民所得當中占據的份額將會愈來愈高,而其餘人口的收入所占的份額則愈來愈低,從而破壞社會平衡。李嘉圖認為邏輯上與政治上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針對土地租金收入課徵逐步加重的稅金。
我們將發現這項悲觀的預測並未成真:雖然土地租金的確在高檔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相較於其他形式的財富,農地的價格終究隨著農業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持續下降而逐步下滑。在一八一○年代著書立說的李嘉圖,或許沒能預見當時剛剛開展的新世紀當中,將會有多大幅度的科技進步與工業發展。他也和馬爾薩斯及楊格一樣,無法想像人類能夠完全擺脫食物與農業的羈絆。
雖然如此,李嘉圖關於土地價格的直覺看法,仍舊相當有價值:他的論點所依據的「稀少性原則」,可以導致某些商品的價格連續數十年維持在極高檔。這樣的現象已足以動搖整個社會。價格體系扮演一項無可取代的角色,協調著數百萬人的行動,在嶄新的全球化經濟當中,甚至是數十億人的行動。問題在於,價格體系沒有任何限度,也不具備任何道德觀念。
要分析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財富分配,若是忽略「稀少性原則」的重要性不諦是一大謬誤。欲說明此點,只需將李嘉圖模型當中的農地價格,替換成世界各國的首都不動產價格,或者是石油的價格。不論用何者替換,若將一九七○至二○一○年間觀察到的趨勢,延伸到二○一○至二○五○或二○一○至二一○○年之間,結果便會是國與國之間或者同一個國家之內,產生大規模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失衡,令人不免聯想到李嘉圖所描繪的社會崩解浩劫。
當然,照理說有項簡單的經濟機制可以平衡上述狀況,亦即供需原理。當某項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價格過高,該項商品的需求便會降低,使得供需間邁向平衡。舉例來說,若房地產和石油價格雙雙飆漲,民眾可以選擇住到鄉下,或者改騎腳踏車(也可以兩者併行)。但實際上,做出這樣的決定不僅複雜而不便,而且供需間的調整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十年,以至於一開始便擁有不動產和石油的富人,在供需調整過渡期間所累積的財富,已足以讓他們購買並長期持有所有可購買的標的物,其中當然包括鄉村不動產和腳踏車。3一如過往,最糟的狀況不一定會發生。讀者也還不到需要擔憂二○五○年是否要繳交房租給卡達國王的地步:這個問題稍後會再探討,屆時我的答案會比較細緻,但令人心安的程度也相當有限。在此必須要瞭解的是,單靠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互動,仍有可能因為某些相對價格的極端化發展,而產生財富分配長期嚴重不均的狀況。這就是李嘉圖「稀少性原則」所傳達的最主要訊息。但我們仍能有所作為,不一定要聽天由命。
馬克思:資本無限累積原則
馬克思於一八六七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距離李嘉圖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時間正好半個世紀,兩人所面對的經濟與社會現實也已經有了深刻變化。馬克思關注的議題不再是農業能否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或者土地價格是否會一飛沖天,而是如何理解正蓬勃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動態。
當時,最顯著的現象便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窮困。儘管經濟不斷成長,或者說正因為經濟不斷成長,以及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原因是人口持續增加與農業生產率提高),使得愈來愈多工人擠在都會貧民窟之中,過著工作時間冗長,薪資卻低廉的生活。一種新的都會貧窮開始出現,相較於舊制度時代(Ancien Régime)的農村貧窮,它更為明顯、更令人震撼,某種程度上也更加嚴厲。《萌芽》(Germinal)、《孤雛淚》(Oliver Twist)和《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等小說並非純粹出自作家的想像。同樣的,法國於一八四一年立法禁止工廠聘雇八歲以下童工,英國一八四二年禁止十歲以下兒童成為礦工等法令,在在反映出當時的情況。不論是維樂美醫師(Dr Villermé)於一八四○年出版的《工廠工人身心狀態紀實》(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導致一八四一年的法案通過),或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所描繪的都是同樣令人反胃的現實。
事實上,所有能夠運用的歷史資料皆指出,薪資購買力的有效提升要到十九世紀後半,甚至是最後三分之一才出現。從一八○○年代到一八五○年代,工人的薪水不但非常低而且幾無成長,停留在十八世紀或是更早期的水準,有的甚至更低。十九世紀前葉英、法兩國薪資停滯不前的現象,恰與同時期經濟成長的逐步加速形成強烈對比。從目前能使用的不完善資料來估算,這段期間兩個國家的資本所得──包含工業利潤、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等收入──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也大幅攀升。直到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工資往上追回了部分先前延遲的成長,資本所得的占比才稍微下降。然而我們蒐集到的資料顯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財富不均的狀況,並未有任何結構性的縮減。在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間,頂多可以說是穩定維持在財富極度不均的狀況,就某些層面來說,我們甚至看到永無止盡的分配不均螺旋已經形成,使得財富愈來愈集中。若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帶來空前規模的經濟與政治衝擊,很難說當時原本的趨勢會發展到什麼境地。透過歷史分析和現在的後見之明看來,上述衝擊甚至可以說是工業革命以來,唯一曾有效縮小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
即便當時沒有任何可靠的國家統計數據,但每個人都能清楚感受到,一八四○年代大幅成長的工業利潤與資本,與一成不變的勞動所得之間落差是多麼大。最初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他們質疑的核心問題相當簡單:假如經過了半世紀的工業成長,大眾的生活條件仍然如此不堪,而我們能做的只有禁止八歲以下兒童至工廠上班,那麼工業發展的用處何在?所有這些技術創新、勞力投入、人口遷徙又是為了什麼?現存政治經濟體系的失敗看來十分明顯。接下來的問題同樣重要:這樣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的長期發展將會如何?
這正是馬克思想解答的。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爆發「人民之春」的一系列武裝革命前夕,馬克思出版了簡短有力的《共產黨宣言》,它著名的開頭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 同樣著名的第一章結尾則預言了革命:「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接下來的二十幾年,馬克思致力於書寫一部龐大著作,要為這個結論提供證明,並針對資本主義及其崩潰提出科學的分析。這項巨大工程並未完成: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確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然而他於一八八
三年過世的時候卻仍未完成後面兩卷。馬克思死後,他的好友恩格斯才將他時而晦澀不明的手稿片段整理出版。
如同李嘉圖所為,馬克思試圖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內部的邏輯矛盾。他一方面將自己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切開(他們認為市場是能自我調節的系統,可以自己找到平衡點而不會產生嚴重的分歧失衡,正如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還有賽伊(Jean-Baptiste Say)的「市場定律」),一方面也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與普魯東主義者區隔,因為他認為這兩派人只以批評勞工貧窮的現實為滿足,而不思以真正科學的方法剖析造成貧窮的經濟機制。簡而言之,馬克思以李嘉圖的模型為基礎,根據他的「資本價格」和「稀少性原則」針對資本的動態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其中,資本主要是工業資本(機具、設備等),而非土地資本,故而有無限累積的可能。事實上,馬克思的主要結論可稱為「資本無限累積原則」,亦即資本注定無限制累積和集中的趨勢。由此,馬克思推測資本主義最後將會崩解:不是資本報酬率愈來愈低(造成累積的動能消失,資本家開始互相廝殺),就是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不斷上升(迫使勞工階級或快或慢團結起來反抗)。無論是哪一種情形,似乎資本主義都無法取得社會經濟或者政治上的平衡。
此一黯淡命運和李嘉圖的悲觀預言一樣沒有實現。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工資終於有了成長:雖然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分配不均的情形實際上仍相當嚴重,甚至在某些層面有惡化的趨勢,但購買力的普遍上升,卻使得情勢產生劇變。共產革命確實發生了,卻是在歐洲最落後的國家,工業革命剛起步的俄羅斯。歐洲工業最發達的一些國家則嘗試了其他的道路,社會民主的路,對其國民來說相當幸運。就跟前面提到的幾位一樣,馬克思也完全忽略了技術持續創新以及生產力不斷提升的可能性,而這兩者正是某種程度上可以平衡私人資本無止盡累積和集中的因素。或許當時的統計數據不足以讓馬克思的分析更細膩。他也可能受制於一八四八年就定下的結論,即便他當時還沒有進行足以支撐這些結論的研究。顯然,馬克思是在強烈政治熱忱的驅使之下寫作,使得他難免做出一些草率的推論,這也是為什麼理論論述絕對必須要和歷史資料相連接,而馬克思在這方面並未窮盡他的努力。此外,馬克思也從未探討在資本私有權被完全廢除的社會之中,應當有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那些廢除私有制的國家所進行的悲慘極權試驗,適可證明這是多麼複雜的議題。
儘管有其不足,馬克思的研究分析仍在若干要點上有其參考價值。首先,馬克思從真正重要的問題出發(工業革命期間不可思議的財富集中程度),然後試著運用手中資源解答它:這樣的取徑,值得當代的經濟學家做為借鏡。更重要的是,馬克思闡述的「資本無限累積原則」具有一項非常關鍵的洞見,對於瞭解分析十九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同樣重要,在某方面也較李嘉圖的「稀少性原則」更令人擔憂。一旦人口及生產力的成長率相對低落,過去累積的財富的重要性便相對提高,甚至可能過高,達到動搖社會基礎的地步。換句話說,微弱的經濟成長,只能稍微平衡資本的無限累積趨勢。由此所達到的平衡點,雖不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極端,卻也令人相當不安:資本累積有其限度,到達頂點便會停止,然而這個資本存量的頂點可能極高,而達到動搖社會基礎的地步。我們稍後將看到自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以來,所有先進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的私有資本巨幅成長(以國民所得的倍數來衡量),此一現象正符合了資本有限卻高度累積的邏輯。
從馬克思到顧志耐:從末世啟示錄到童話故事
從十九世紀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分析,到二十世紀顧志耐的結論,可以說經濟學從過度偏愛災難性末世預言,到同樣過度傾向喜愛童話故事,或至少是皆大歡喜的結局。根據顧志耐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不論這些國家採取何種政策,又有哪些特殊國情,所得不均的現象都會自己逐步縮小,最後達到一個穩定而可接受的財富分配平衡。這項理論於一九五五年問世,非常契合二次大戰之後歐陸經濟「光輝三十年」的美好時光,亦即「只要有點耐心,經濟成長終將使所有人受惠」的年代。英文有句諺語適足以代表當年的時代精神:「經濟成長如漲潮,水漲船高無例外(Growth is a grow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當時亦有索洛(Robert Solow)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他的研究,指出一個經濟體要符合哪些必要條件才能走上「平衡成長路徑」,意思是說在這條成長路徑上,所有的變項,像是產出、所得、利潤、工資、資本、股市跟不動產等等,都會以同樣速率成長,因此每一種社會群體都會從成長當中得到相同比例的利益,不會嚴重拉開距離。以上諸點,正好和李嘉圖與馬克思的財富不均螺旋,以及十九世紀的各種悲觀論述完全相反。
欲瞭解顧志耐的理論何以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直到一九八○和九○年代,並在某種程度上仍對今日有所影響,就必須要知道這是該領域第一個奠基在大規模統計資料的理論。事實上,關於所得分配的時間序列數據要等到一九五三年顧志耐出版其鉅作《高所得群體占所得與儲蓄的份額》(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才首次出現。儘管顧志耐整理出來的時間序列數據只有美國的數據,時間上也僅涵蓋三十五年(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然而該統計工作仍為一項重大貢獻,其中動用了兩種十九世紀學者完全不可能獲得的資料來源:美國聯邦政府一九一三年開始課徵所得稅之後的所得申報書,以及顧志耐自己先前估算出的美國國民所得。該項研究是史上首次出現如此大規模衡量社會財富分配情形的嘗試。
在此必須強調,少了上述兩種必要且互補的數據資料來源,根本無法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及其演變。在顧志耐之前當然也有人曾嘗試估算國民所得,例如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的英國和法國,類似的嘗試在十九世紀更是頻繁。然而,先前的研究都是估算特定單一時期的國民所得。以年度為單位的國民所得時間序列資料要等到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才由美國的顧志耐和坎卓克(John W. Kendrick)、英國的包利(Arthur Bowley)和克拉克(Colin Clark),以及法國的貝儂維爾(Dugé de Bernonville)等人整理出來。這些資料使我們得以衡量各國的總體所得。而要估算高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中的份額,我們還需要所得申報紀錄,這種資料要從各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左右開始課徵累進稅率所得稅才存在(一九一三年美國、一九一四年法國、一九○九年英國、一九二二年印度和一九三二年阿根廷)。
在尚未課徵所得稅的時期,當然也有許多用於稅基計算的統計(例如法國在十九世紀就曾統計各省〔département〕的門窗數量,頗為有趣),不過關於所得的資料卻付之闕如。在不需要申報所得稅的年代,往往連個人對自己的收入到底多少都缺乏認識。營所稅和財富稅的情形也是如此。賦稅不僅僅是讓大家為公共支出和共同計畫提供資金,並且以眾人最能接受的方式分配稅收的手段;賦稅同時也是一種可以產生分類、知識和民主透明度的方式。
無論如何,正是有了這些數據資料,顧志耐才有辦法計算美國十等分位的各所得階層以及前幾個百分位的最高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份額的演變。那麼他的發現為何?他發現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相當程度地縮小了。具體來說,一九一○至二○年間,所得最高的一成美國人,其所得約占國民所得的45%至50%。及至一九四○年代末期,同一階層的所得占比則減至國民所得的30%至35%。超過十個百分點的降幅相當可觀,因為這約略等於美國後半段所得五成人民的一半所得。貧富差距的減少不但明顯而且無可置疑。這樣的訊息非常重要,在戰後不論是學術界或國際組織的經濟論辯中,都造成巨大的影響。
許多年來,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和其他眾多有志者,都在談論財富不均的問題,卻沒有人提出任何數據跟方法來準確比較各時代間的差異,並依此檢驗各種假說。顧志耐的貢獻正在於首次提出一個客觀的研究基礎。這項研究當然有其明顯不足之處,然而其存在本身便是一大進步。除此之外,這部作品提供了極為詳盡的紀錄:顧志耐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這篇厚重論文,以最公開透明的方式詳列他的所有資料來源跟計算方法,所有成果都可以重新驗算。尤有甚者,顧志耐帶來的是好消息:財富不均正在縮減。
顧志耐曲線:冷戰當中的一線曙光
事實上,顧志耐本人也十分清楚,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高所得被壓縮的現象是相當偶然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連番衝擊,而非自然而然發生。顧志耐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這篇研究,除了詳細分析時間序列,也警告讀者勿輕率概括、以偏概全。不過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顧志耐以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身分在底特律的年會當中發表演說時,卻選擇以樂觀許多的角度詮釋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研究。正是這篇在一九五五年以「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不均」(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為題出版的演說,促成「顧志耐曲線」理論的誕生。
根據這項理論,分配不均的現象乃是依循一條「鐘形曲線」演變,也就是說,它會隨著工業化與經濟發展而先擴大後縮減。根據顧志耐的說法,在工業化初期的分配不均自然擴大階段(在美國約略是十九世紀)之後,會進入分配不均迅速縮減的階段(在美國是從二十世紀前半開始)。
閱讀這篇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講稿可以帶來很大的啟發。再次提醒眾人必須謹慎,並且說明外在衝擊對於縮減美國分配不均現象的明顯影響之後,顧志耐以近乎不著痕跡的方式提出,經濟發展自身的邏輯應該也可以導致同樣的結果,無關乎任何政策干預或外在衝擊。他的想法是,在工業化剛開始的階段分配不均會擴大(因為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到工業化帶來的財富),然而隨著經濟持續發展達到高度階段,分配不均會自動縮小(因為愈來愈多人進入有前景的產業,分潤到經濟成長的果實)。
顧志耐認為,這種「高度發展階段」在各工業化國家大約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因此,美國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年間所發生的分配不均縮減情形,不過是普遍現象當中的一個例子。所有國家,包括當時仍備受貧窮所苦、正和殖民主義搏鬥的眾多未開發國家,理論上遲早也都會走上這條道路。顧志耐在一九五三年的著作裡提出的這些事實資料,變成了極具威力的政治武器。顧志耐非常清楚這個理論有相當高的臆測成分。然而,在「主席演說」的場合發表這樣樂觀的理論,面對的是一群樂於相信和散播優秀同儕帶來的福音的美國經濟學家,顧志耐知道自己將會發揮極大的影響力:「顧志耐曲線」理論於焉產生。為了確保每個人都體認到這個理論的意義,顧志耐進一步向聽眾強調,其樂觀預測的重要性,在於讓所有未開發國家繼續「待在自由世界的陣營」之中。可以說,「顧志耐曲線」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冷戰的產物。
在此必須強調,顧志耐的研究工作建立了第一套美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以及第一份關於所得分配不均的時間序列數據,貢獻卓著,而從他的書中(相較於他的文章)更可明顯看出他嚴格遵守研究倫理。此外,二次大戰後,所有已開發國家的強勁成長確實是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所有社會群體都從中得到益處。在這樣的狀況下,「光輝三十年」期間樂觀論調盛行,而十九世紀那種對於財富分配發展的悲觀預測不受青睞,也是相當合情合理的事。
儘管如此,我們必須說「顧志耐曲線」這個神奇理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不單純的理由,其實證基礎也非常薄弱。就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間各個富有國家的所得分配不均出現大幅縮減,主要因素實為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其所帶來的重大經濟與政治衝擊(特別是對那些擁有大量財富的人),跟顧志耐所描繪的產業部門勞動力和緩轉移沒有關聯。
讓財富分配議題回到經濟學研究的核心
財富分配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只是為了探討過去的歷史而已。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富裕國家的貧富差距再度擴大,在美國尤其嚴重,該國在二○○○至二○一○年間的所得集中化程度,已經回到一九一○年代的紀錄高峰,甚至略微超越。由此可見,瞭解當初貧富差距為何以及如何縮小極為重要。不可諱言,貧窮國家及新興國家的迅速成長,正如當年富裕國家在戰後「光輝三十年」的成長一樣,可能是減緩全球層次財富不均的一股強勁力道。然而,這個過程也在新興國家內部引起許多憂慮,在富裕國家內部更是如此。此外,近數十年在金融、石油和不動產等市場所見到幅度可觀的失衡現象,也令人質疑顧志耐和索洛描繪的「平衡成長路徑」是否真的存在:根據他們的說法,所有重要經濟變項都應該以同樣速率成長。二○五○或二一○○年的世界,是否會成為金融交易員、超級經理人、超級巨富或石油輸出國家的囊中物?或者會由中國銀行持有?還是會掌握在寄身避稅天堂的上述各種人士手中?如果不提出誰將占有財富的問題,只是固守成見認為經濟成長長期而言會自然「維持平衡」,不啻十分荒謬。
就某方面來說,二十一世紀初的我們,處境其實和十九世紀的前人差不多:我們正目睹各種重大變遷,很難說這些轉變會走到什麼程度,也很難知道全球財富分配的情況(不論是國與國之間或者是各個國家內部)幾十年後將會如何。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有一項重要優點:他們都將財富分配視為核心議題,並且試著探究長期趨勢。儘管他們得到的答案未必令人滿意,問的問題卻切中要點。實際上,沒有任何理由足以讓我們堅信經濟成長可以自動維持平衡。我們早就該讓財富不均的問題回到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再次提出十九世紀就開啟的問題。長期以來,財富分配問題受到經濟學家忽略,一方面是因為顧志耐的樂觀結論所致,另一方面則因為經濟學界太過偏愛使用所謂「代表性個人」(agent représentatif; representative agent)的過度簡化數學模型。要讓財富分配問題重回研究核心,首先必須盡可能蒐集歷史數據,以便瞭解過去的演變和當前的趨勢。唯有耐心整理出事實與規律性,並且比較不同國家的經驗,才有可能瞭解其中運作的機制並讓我們看清未來的模樣。
目次
引論
第一部:所得與資本
1 所得與產出
2 經濟成長:現實與假象
第二部:資本∕所得比的演變動態
3 資本的形態轉變
4 從舊歐洲到新世界
5 資本∕所得比的長期發展
6 二十一世紀勞務所得與資本所得的相對占比
第三部:分配不均的結構
7 分配不均與集中化:初步概念
8 兩個世界
9 勞務所得的分配不均
10 資本所有權的分配不均
11 個人才能與財產繼承的長期趨勢
12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財富不均
第四部: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規範
13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國家
14 反思累進所得稅
15 全球資本稅
16 公共債務問題
結論
誌謝
注釋
章節細目
圖表目次
基本詞彙對照
得獎作品
《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華爾街日報》暢銷榜第一名
《華盛頓郵報》暢銷榜第一名
《波士頓環球報》暢銷榜第一名
《洛杉磯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舊金山紀事報》暢銷榜第一名
亞馬遜書店暢銷榜第一名
美國國家廣播網暢銷榜第一名
榮獲英國國家學術院2014年獎章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