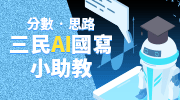雙聲.雙身:當代電影中的分裂主體研究
商品資訊
定價
:NT$ 300 元優惠價
:
90 折 270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8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電影敘事美學特殊性徹底揭露
☆分裂主體電影完整評析──《黑天鵝》、《隔離島》、《鬥陣俱樂部》
「分裂主體」是電影理論界所普遍關注的一個話題──就電影本身具備傳統文學作品的敘事特質,同時具備鏡頭(包括蒙太奇)敘事的特殊性。
本書從電影敘事美學的特殊性入手,以「分裂主體」為主論,闡述了不同電影對於人類社會大時代的反映。針對1999年以來在世界影壇飽受爭議的三部電影——戴倫‧艾洛諾夫斯基《黑天鵝》、馬丁‧史柯西斯《隔離島》與大衛‧芬奇《鬥陣俱樂部》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探討。
☆分裂主體電影完整評析──《黑天鵝》、《隔離島》、《鬥陣俱樂部》
「分裂主體」是電影理論界所普遍關注的一個話題──就電影本身具備傳統文學作品的敘事特質,同時具備鏡頭(包括蒙太奇)敘事的特殊性。
本書從電影敘事美學的特殊性入手,以「分裂主體」為主論,闡述了不同電影對於人類社會大時代的反映。針對1999年以來在世界影壇飽受爭議的三部電影——戴倫‧艾洛諾夫斯基《黑天鵝》、馬丁‧史柯西斯《隔離島》與大衛‧芬奇《鬥陣俱樂部》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探討。
作者簡介
黃資婷
一九八六年生,世新大學新聞系雙主修中文系畢業,成功大學中文所與藝術所雙碩士。現為成大中文所與建築所之博士生。
一九八六年生,世新大學新聞系雙主修中文系畢業,成功大學中文所與藝術所雙碩士。現為成大中文所與建築所之博士生。
序
序
Ma Bohème
Je m’en allais, les poings dans mes poches crevées;
Mon paletot soudain devenait idéal;
J’allais sous le ciel, Muse, et j’étais ton féal;
Oh! là là! que d’amours splendides j’ai rêvées!
Mon unique culotte avait un large trou.
Petit-Poucet rêveur, j’égrenais dans ma course
Des rimes. Mon auberge était à la Grande-Ourse.
Mes étoiles au ciel avaient un doux frou-frou
Et je les écoutais, assis au bord des routes,
Ces bons soirs de septembre où je sentais des gouttes
De rosée à mon front, comme un vin de vigueur;
Où, rimant au milieu des ombres fantastiques,
Comme des lyres, je tirais les élastiques
De mes souliers blessés, un pied près de mon coeur!
Arthur Rimbaud
謹將本文獻給我的父親與母親,以及這段虛擲年華的歲時。
2016年‧處暑‧於南都
Ma Bohème
Je m’en allais, les poings dans mes poches crevées;
Mon paletot soudain devenait idéal;
J’allais sous le ciel, Muse, et j’étais ton féal;
Oh! là là! que d’amours splendides j’ai rêvées!
Mon unique culotte avait un large trou.
Petit-Poucet rêveur, j’égrenais dans ma course
Des rimes. Mon auberge était à la Grande-Ourse.
Mes étoiles au ciel avaient un doux frou-frou
Et je les écoutais, assis au bord des routes,
Ces bons soirs de septembre où je sentais des gouttes
De rosée à mon front, comme un vin de vigueur;
Où, rimant au milieu des ombres fantastiques,
Comme des lyres, je tirais les élastiques
De mes souliers blessés, un pied près de mon coeur!
Arthur Rimbaud
謹將本文獻給我的父親與母親,以及這段虛擲年華的歲時。
2016年‧處暑‧於南都
目次
△序「秀威文哲叢書」
△推薦序──哲思與書寫/賴俊雄
△推薦序──一種優雅,萬種風情/韓晗
△序
△緒論
一、創傷世代裡的雙數主體
二、文本選擇與回顧
三、本書架構
△壹、 我為美殉身:《黑天鵝》
一、以父之名:童話故事變形的三層意涵
二、沒有名字的母親:前伊底帕斯情結滯留
三、鏡像階段與死亡驅力的鞭轉
四、 Make Real:幻見公式($〈〉a)的操演與主體分裂
小結
△貳、 我為創傷而活:《隔離島》
一、全控機構下的主體問題
二、以瘋狂抗拮死亡的哀悼儀式
三、家庭的崩毀:喪子與弒妻
四、馬勒之於創傷主體的隱喻
小結
△參、 我為存在而痛:《鬥陣俱樂部》
一、主體之難:被圍困的個人
二、穿梭於時差罅隙:泰勒德頓
三、身體意識與主體辯證
四、倖存的只有愛:瑪拉辛格
小結
△尾聲、我們是自己的魔鬼
△參考文獻
△推薦序──哲思與書寫/賴俊雄
△推薦序──一種優雅,萬種風情/韓晗
△序
△緒論
一、創傷世代裡的雙數主體
二、文本選擇與回顧
三、本書架構
△壹、 我為美殉身:《黑天鵝》
一、以父之名:童話故事變形的三層意涵
二、沒有名字的母親:前伊底帕斯情結滯留
三、鏡像階段與死亡驅力的鞭轉
四、 Make Real:幻見公式($〈〉a)的操演與主體分裂
小結
△貳、 我為創傷而活:《隔離島》
一、全控機構下的主體問題
二、以瘋狂抗拮死亡的哀悼儀式
三、家庭的崩毀:喪子與弒妻
四、馬勒之於創傷主體的隱喻
小結
△參、 我為存在而痛:《鬥陣俱樂部》
一、主體之難:被圍困的個人
二、穿梭於時差罅隙:泰勒德頓
三、身體意識與主體辯證
四、倖存的只有愛:瑪拉辛格
小結
△尾聲、我們是自己的魔鬼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我們是自己的魔鬼
有股確切的力將語言曳向不幸,曳向自我摧殘:我的表達狀態猶如旋轉的飛輪:語言轉動著,一切現實的權宜之計都拋諸在腦後。我設法對自己作惡,將自己逐出自己的天堂,竭盡全力曳造出種種能傷害自己的意象(妒嫉、被遺棄、受辱等等);不僅如此,我還使創痕保持開放,用別的意象來維持它、滋養它,直至出現另一個傷口來轉移我的注意力。
羅蘭巴特極為詩意的文字,拆解愛情,在〈我們是自己的魔鬼〉篇章,寫下與自己對話的心緒。恍如鐘擺般的自我矛盾與妥協,也許可以為分裂主體留下註解,來到本書尾聲。《黑天鵝》、《隔離島》、《鬥陣俱樂部》此三個文本之主角,若說有共同的人格特質,便是不肯輕易放過自己,以自身的反面與內在傷口拉扯、撕裂,本書能刻畫的,也僅是此議題下的碎片。這三部文本分別呈現出:當意識的碎裂已浮出象徵秩序表層諸種分崩離析,「正常」的生活型態是否從未存在過?三位導演選擇戲劇化的張力,將主體一分為「二」,分裂出另外一個人格:妮娜╱莉莉、泰迪╱雷德斯、傑克╱泰勒德頓等。這並非康麥倫‧魏斯特(Cameron West)《第一人稱複數》(First Person Plural)裡,「我」與眾聲譁噪的「他們」共處及妥協;而是「我」與另一個「我」正反辯證的「第一人稱雙數」。
討論解離人格的電影,主要都圍繞在「我是誰」的主體問題,最早一九六○年希區考克的《驚魂記》(Psycho)中諾曼‧ 貝茲(Anthony Perkins飾演)分裂出「母親」(另一個人格),二○○四年《機械師》(The machinist)的特拉沃(Christian Bale 飾演)因重度失眠,不停質問身旁揮之不去的人影:「你是誰」,同年略顯粗糙的《秘窗》(Secret window)改變史蒂芬金劇本,主角除法承受妻子外遇而分裂出另一人格;二○○五年的《捉迷藏》(Hide and seek),心理醫生覺得自己女兒性情古怪,最後才發現是他自己人格分裂等等作品,因為能造成結局瞬間翻轉,達到驚悚效果,頗受觀眾喜愛。精神分裂症與解離人格之差異如表格所示──
兩個病徵的最大差異在於:精神分裂者會幻想與多人交談,但不會出現兩種以上的分裂人格(split personality);解離是心因性的精神疾病,多半伴隨著失憶與幻覺具象化的視覺特性,不難想見導演們對這兩種題材的喜愛之因。精神科醫師瑪琳‧史坦伯格將解離視為當代普遍流行的精神癥候,如不認得鏡中的自己、無法確認記憶的真實與虛構、時間感的喪失等等。《黑天鵝》、《隔離島》、《鬥陣俱樂部》屬於後者,電影側重在主體精神性的刻畫,皆具有心理驚悚類型片的色彩,卻不受此類型之侷限,關鍵在於三位導演對於電影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使得作品除了在商業考量上討好觀眾外, 強烈的自我風格兼具娛樂性與反身性(reflexive),在藝術與商業擺盪之光譜間,找尋巧妙的平衡點。三部電影都是從主角心理創傷與重建自我認同出發,展開分裂主體的過程,最終還是無法逃離以肉身死亡作結,換得主體的能動性之命運。於風格呈現上, 戴倫‧艾洛諾夫斯基、馬丁‧史柯西斯、大衛‧芬奇三位導演的藝術成就,帶給閱聽眾相當不同的觀影經驗,除了遵循好萊塢體系內在某種公式敘事的「回饋」循環、關於「分裂主體」之討論之外,導演們對影片後設思考的高度自覺也達到有效的創新。
何為劃穿主體的鏡像斜線?
《黑天鵝》怪誕家庭裡母親對女兒的傷害,女兒置身黑色洞穴,舞蹈的力量,一切凝結在隱喻死亡驅力永劫回歸的鞭轉裡, 在溫柔且開放式的傷口餵養下,偽裝出另一個人格,由主體分裂出來的他者(other),野性、暴力且飢渴,是一陣踮起腳尖旋轉的風,與妮娜形成聖女與蕩婦之對比。妮娜透過高速旋轉,將壓抑、純真的聖女形象之自我甩出,上肢旋轉成黑色羽翼,激發她的動物性,她終於與童話中的女子一樣,半人半天鵝,當她完成了整齣芭蕾舞劇,投身「完美」的擁抱,看見在臺下的母親雙眼泛著淚光,才能弭平母親給予的創傷,黑天鵝終於褪去羽翼,躺在偌大死亡之牀安然睡去。
回應阿多諾(Theodor Adorno)名言「奧許維茲之後,不再可能有詩。」(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遍經猶太大屠殺後的歷史創傷,《隔離島》電影捨棄同名小說中對於原生家庭的鋪陳,讓主體自原生家庭出走,與妻子共築愛巢後又親手摧毀,來到精神病院這座被全控機構綑綁之籠,這次的創傷內核是愛情與殺戮。人倫悲劇之發生,主體產生解離性失憶症(Dissociative Amnesia),遺忘了那年夏天在渡假小屋裡發生的事,只肯承認達豪集中營所見的屠戮―納粹追捕猶太人,美國以正義之名屠殺納粹―這一連串血流成川的戰爭食物鏈, 啟動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主體愎諫所有他者給的告誡,驅離了主人格,被掩藏的,其實是主體深信自己是他者, 於癲狂世界裡虛擬出殺妻仇人的外表特徵,絕非鏡子裡的我。那些午夜夢迴響起的馬勒A小調鋼琴弦樂四重奏(Quartet in A minor for piano and strings)是最最深沉的生命低謳,宛如身為猶太人的馬勒正在為他同胞之死,奏上一曲哀樂,死亡是主體應許對妻子最後的承諾,唯有透過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消解記憶,纔能如螻蟻苟活。
從死亡之島的權力結構邁向現代性,進入消費社會的桂宮柏寢,存在之痛屆臨。創傷從來不是具體、有所指涉的對象物,而是根基於存在之本質。主體恐懼褕衣甘食的生活態度,自來往世界各地調節時差罅隙裡,捏造另一個理想人格。他憤世嫉俗、不受倫理道德規範,勇於自我挑戰,他讓主體見識到消費社會下的自虐之詩―抽脂脂肪萃取後製成肥皂回到消費者的手中,對身體賤斥,將自己不潔的部分排除後,透過那些殘餘物洗滌自己,以化學藥劑燃燒自己,有如佛教灼臂恭佛之祭儀。理想人格的目的,是在主體受到社會傷害時,提前一步讓傷口生成存在,主動對消費社會提出反擊,以恐怖行動瓦解經濟。然而破壞行動造成組織人員死亡並非預期,提醒主體這不是他腦內幻想的小遊戲,某種英雄情懷被激起,主體決定以自身死亡來兌換他人的平安。
回到電影本身,從敘事技藝中可發覺《黑天鵝》與《鬥陣俱樂部》皆是從主人格的視角出發,《隔離島》則顛覆了電影中呈現解離人格的慣用敘事策略,顛倒觀眾認知;而《黑天鵝》中妮娜幻想出來的人格,是在電影塑造的現實世界裡,有其相對應之人物;《隔離島》與《鬥陣俱樂部》則是完全虛擬;戴倫艾洛諾夫斯基、馬丁史柯西斯、大衛芬奇這三位導演在票房與藝術價值中取得平衡,透過這些戲劇性強烈的人格分裂的電影,傳達現世分裂主體之困境。
本文最初與最終,都在進行嘗試,或許這三部文本無法涵括如此龐大之議題,卻也達到為二十世紀末以降的主體困境做一個小結。三位主角皆面臨自我間的拉扯,將分裂主體衍伸到極致,啟動內心的防禦機制,直接創造出另外一個人格,來預防主體受到傷害的策略,試圖將自己包含在傷口之外。從《黑天鵝》自我對於美的追求,到《隔離島》由他人對主體造成之創傷波痕,再擴及《鬥陣俱樂部》集體社會之問題。三個故事呈現雙重生存困境,視覺上也賦予虛擬人格雙重肉身,讓精神狂想的世界視覺化、聽覺化,使閱聽眾透過影像理解他人的疼痛,並非以同情或者同理心的姿態,而是如波洛克所云,以一種「美學邂逅的特定方式」,讓主體與藝術產生母體式的連結。
無論是「創傷世代」、「焦慮世代」、「解離世代」、或者是斷梗飄萍的分裂世代,都將問題指向精神傷口,證明存在之痛確實存在。無論是百無聊賴的消費社會恐慌、全控機構對主體的壓抑,乃至家庭倫理關係,在走向死亡,踏入下一輪的太平盛世之前,終需與自己主體和解。
有股確切的力將語言曳向不幸,曳向自我摧殘:我的表達狀態猶如旋轉的飛輪:語言轉動著,一切現實的權宜之計都拋諸在腦後。我設法對自己作惡,將自己逐出自己的天堂,竭盡全力曳造出種種能傷害自己的意象(妒嫉、被遺棄、受辱等等);不僅如此,我還使創痕保持開放,用別的意象來維持它、滋養它,直至出現另一個傷口來轉移我的注意力。
羅蘭巴特極為詩意的文字,拆解愛情,在〈我們是自己的魔鬼〉篇章,寫下與自己對話的心緒。恍如鐘擺般的自我矛盾與妥協,也許可以為分裂主體留下註解,來到本書尾聲。《黑天鵝》、《隔離島》、《鬥陣俱樂部》此三個文本之主角,若說有共同的人格特質,便是不肯輕易放過自己,以自身的反面與內在傷口拉扯、撕裂,本書能刻畫的,也僅是此議題下的碎片。這三部文本分別呈現出:當意識的碎裂已浮出象徵秩序表層諸種分崩離析,「正常」的生活型態是否從未存在過?三位導演選擇戲劇化的張力,將主體一分為「二」,分裂出另外一個人格:妮娜╱莉莉、泰迪╱雷德斯、傑克╱泰勒德頓等。這並非康麥倫‧魏斯特(Cameron West)《第一人稱複數》(First Person Plural)裡,「我」與眾聲譁噪的「他們」共處及妥協;而是「我」與另一個「我」正反辯證的「第一人稱雙數」。
討論解離人格的電影,主要都圍繞在「我是誰」的主體問題,最早一九六○年希區考克的《驚魂記》(Psycho)中諾曼‧ 貝茲(Anthony Perkins飾演)分裂出「母親」(另一個人格),二○○四年《機械師》(The machinist)的特拉沃(Christian Bale 飾演)因重度失眠,不停質問身旁揮之不去的人影:「你是誰」,同年略顯粗糙的《秘窗》(Secret window)改變史蒂芬金劇本,主角除法承受妻子外遇而分裂出另一人格;二○○五年的《捉迷藏》(Hide and seek),心理醫生覺得自己女兒性情古怪,最後才發現是他自己人格分裂等等作品,因為能造成結局瞬間翻轉,達到驚悚效果,頗受觀眾喜愛。精神分裂症與解離人格之差異如表格所示──
兩個病徵的最大差異在於:精神分裂者會幻想與多人交談,但不會出現兩種以上的分裂人格(split personality);解離是心因性的精神疾病,多半伴隨著失憶與幻覺具象化的視覺特性,不難想見導演們對這兩種題材的喜愛之因。精神科醫師瑪琳‧史坦伯格將解離視為當代普遍流行的精神癥候,如不認得鏡中的自己、無法確認記憶的真實與虛構、時間感的喪失等等。《黑天鵝》、《隔離島》、《鬥陣俱樂部》屬於後者,電影側重在主體精神性的刻畫,皆具有心理驚悚類型片的色彩,卻不受此類型之侷限,關鍵在於三位導演對於電影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使得作品除了在商業考量上討好觀眾外, 強烈的自我風格兼具娛樂性與反身性(reflexive),在藝術與商業擺盪之光譜間,找尋巧妙的平衡點。三部電影都是從主角心理創傷與重建自我認同出發,展開分裂主體的過程,最終還是無法逃離以肉身死亡作結,換得主體的能動性之命運。於風格呈現上, 戴倫‧艾洛諾夫斯基、馬丁‧史柯西斯、大衛‧芬奇三位導演的藝術成就,帶給閱聽眾相當不同的觀影經驗,除了遵循好萊塢體系內在某種公式敘事的「回饋」循環、關於「分裂主體」之討論之外,導演們對影片後設思考的高度自覺也達到有效的創新。
何為劃穿主體的鏡像斜線?
《黑天鵝》怪誕家庭裡母親對女兒的傷害,女兒置身黑色洞穴,舞蹈的力量,一切凝結在隱喻死亡驅力永劫回歸的鞭轉裡, 在溫柔且開放式的傷口餵養下,偽裝出另一個人格,由主體分裂出來的他者(other),野性、暴力且飢渴,是一陣踮起腳尖旋轉的風,與妮娜形成聖女與蕩婦之對比。妮娜透過高速旋轉,將壓抑、純真的聖女形象之自我甩出,上肢旋轉成黑色羽翼,激發她的動物性,她終於與童話中的女子一樣,半人半天鵝,當她完成了整齣芭蕾舞劇,投身「完美」的擁抱,看見在臺下的母親雙眼泛著淚光,才能弭平母親給予的創傷,黑天鵝終於褪去羽翼,躺在偌大死亡之牀安然睡去。
回應阿多諾(Theodor Adorno)名言「奧許維茲之後,不再可能有詩。」(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遍經猶太大屠殺後的歷史創傷,《隔離島》電影捨棄同名小說中對於原生家庭的鋪陳,讓主體自原生家庭出走,與妻子共築愛巢後又親手摧毀,來到精神病院這座被全控機構綑綁之籠,這次的創傷內核是愛情與殺戮。人倫悲劇之發生,主體產生解離性失憶症(Dissociative Amnesia),遺忘了那年夏天在渡假小屋裡發生的事,只肯承認達豪集中營所見的屠戮―納粹追捕猶太人,美國以正義之名屠殺納粹―這一連串血流成川的戰爭食物鏈, 啟動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主體愎諫所有他者給的告誡,驅離了主人格,被掩藏的,其實是主體深信自己是他者, 於癲狂世界裡虛擬出殺妻仇人的外表特徵,絕非鏡子裡的我。那些午夜夢迴響起的馬勒A小調鋼琴弦樂四重奏(Quartet in A minor for piano and strings)是最最深沉的生命低謳,宛如身為猶太人的馬勒正在為他同胞之死,奏上一曲哀樂,死亡是主體應許對妻子最後的承諾,唯有透過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消解記憶,纔能如螻蟻苟活。
從死亡之島的權力結構邁向現代性,進入消費社會的桂宮柏寢,存在之痛屆臨。創傷從來不是具體、有所指涉的對象物,而是根基於存在之本質。主體恐懼褕衣甘食的生活態度,自來往世界各地調節時差罅隙裡,捏造另一個理想人格。他憤世嫉俗、不受倫理道德規範,勇於自我挑戰,他讓主體見識到消費社會下的自虐之詩―抽脂脂肪萃取後製成肥皂回到消費者的手中,對身體賤斥,將自己不潔的部分排除後,透過那些殘餘物洗滌自己,以化學藥劑燃燒自己,有如佛教灼臂恭佛之祭儀。理想人格的目的,是在主體受到社會傷害時,提前一步讓傷口生成存在,主動對消費社會提出反擊,以恐怖行動瓦解經濟。然而破壞行動造成組織人員死亡並非預期,提醒主體這不是他腦內幻想的小遊戲,某種英雄情懷被激起,主體決定以自身死亡來兌換他人的平安。
回到電影本身,從敘事技藝中可發覺《黑天鵝》與《鬥陣俱樂部》皆是從主人格的視角出發,《隔離島》則顛覆了電影中呈現解離人格的慣用敘事策略,顛倒觀眾認知;而《黑天鵝》中妮娜幻想出來的人格,是在電影塑造的現實世界裡,有其相對應之人物;《隔離島》與《鬥陣俱樂部》則是完全虛擬;戴倫艾洛諾夫斯基、馬丁史柯西斯、大衛芬奇這三位導演在票房與藝術價值中取得平衡,透過這些戲劇性強烈的人格分裂的電影,傳達現世分裂主體之困境。
本文最初與最終,都在進行嘗試,或許這三部文本無法涵括如此龐大之議題,卻也達到為二十世紀末以降的主體困境做一個小結。三位主角皆面臨自我間的拉扯,將分裂主體衍伸到極致,啟動內心的防禦機制,直接創造出另外一個人格,來預防主體受到傷害的策略,試圖將自己包含在傷口之外。從《黑天鵝》自我對於美的追求,到《隔離島》由他人對主體造成之創傷波痕,再擴及《鬥陣俱樂部》集體社會之問題。三個故事呈現雙重生存困境,視覺上也賦予虛擬人格雙重肉身,讓精神狂想的世界視覺化、聽覺化,使閱聽眾透過影像理解他人的疼痛,並非以同情或者同理心的姿態,而是如波洛克所云,以一種「美學邂逅的特定方式」,讓主體與藝術產生母體式的連結。
無論是「創傷世代」、「焦慮世代」、「解離世代」、或者是斷梗飄萍的分裂世代,都將問題指向精神傷口,證明存在之痛確實存在。無論是百無聊賴的消費社會恐慌、全控機構對主體的壓抑,乃至家庭倫理關係,在走向死亡,踏入下一輪的太平盛世之前,終需與自己主體和解。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