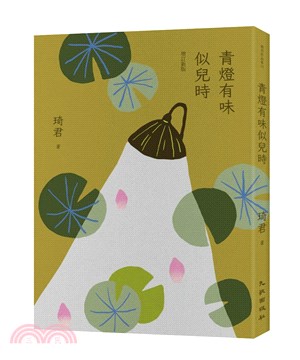定價
:NT$ 300 元優惠價
:79 折 237 元
領券後再享88折起
領
團購優惠券A
8本以上且滿1500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26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26元
領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可得紅利積點:7 點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琦君憶童年,溫馨而趣味盎然,人人愛讀。
本書分二卷「懷舊篇」與「生活篇」,篇篇有真意,雋永而引人深思。她以童心真情體察萬物,在最微細處領悟生命的愉悅與痛苦;以生花妙筆寫半世紀前可喜可憎之人、事、物,栩栩如生,情感真摯,哀而不傷,為悲苦的人間塑造出一片祥和。
懷舊篇中她以一只〈玳瑁髮夾〉追憶那個嚴格限制頭髮長度的學生時代;〈南海慈航〉懷念母親如觀世音菩薩般的慈悲;〈青燈有味似兒時〉則書寫二位兒時難忘的人物:天主堂的白姑娘和不言不語的岩親爺。〈吃大菜〉則是以小女孩的眼光看待成人世界,文字無怨,卻有淡淡的哀傷。也寫梁實秋與老師夏承燾的長文,更展現她豐厚的國學根柢,在今古間從容遨遊。生活篇中趣談戒菸經驗,連抽筋都寫得妙趣橫生。撫今追昔,盡濾塵囂,使人面對未來更有信心。
作者簡介
琦君(1917-2006)
浙江永嘉人,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於中央大學、文化大學等校中文系。
榮獲文協散文獎章、中山文藝獎、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資深作家敬慰獎」、總統府二等卿雲勳章。《鞋子告狀》榮獲新聞局優良圖書金鼎獎,《此處有仙桃》榮獲國家文藝獎。
著有《母親的金手錶》、《水是故鄉甜》、《萬水千山師友情》等散文及小說、兒童文學等書四十多種,曾被譯為美、韓、日文,極受海內外讀者喜愛,旅居美國多年,返台定居,2006年6月7日病逝,享壽九十。
浙江永嘉人,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於中央大學、文化大學等校中文系。
榮獲文協散文獎章、中山文藝獎、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資深作家敬慰獎」、總統府二等卿雲勳章。《鞋子告狀》榮獲新聞局優良圖書金鼎獎,《此處有仙桃》榮獲國家文藝獎。
著有《母親的金手錶》、《水是故鄉甜》、《萬水千山師友情》等散文及小說、兒童文學等書四十多種,曾被譯為美、韓、日文,極受海內外讀者喜愛,旅居美國多年,返台定居,2006年6月7日病逝,享壽九十。
目次
出版前言:童心不老,愛心不覺
小序 琦君
第一輯 懷舊篇
玳瑁髮夾
南海慈航
菜籃挑水
吃大菜
青燈有味似兒時
鷓鴣天
難忘的歌
胡蝶迷
兩位裁縫
講英語
永恆的思念
紙的懷念
三十年點滴念師恩
第二輯 生活篇
藉煙消愁愁更愁
但願虔修來世閒
撿來歲月
讀禪話偶感
「鬼抽筋」
公路凶手
「有我」與「無我」
生與死
恩與愛
「閨秀派」與醜惡面描寫
風車老人
自己的書房
遙遠的祝福
讀書瑣憶
有甚閒愁可皺眉
千古浮名餘一笑
一回相見一回老
附錄
了解琦君‧認識琦君(琦君小傳)
琦君與我 林太乙
千里懷人月在峰 周芬伶
──與琦君越洋筆談
《青燈有味似兒時》相關評論索引
琦君作品目錄一覽表
書摘/試閱
青燈有味似兒時
相信人人都愛念陸放翁的兩句詩:「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尤其我現在客居海外,想起大陸的兩個故鄉,和安居了將近四十年的第三個故鄉臺北,都離得我那麼遙遠。一燈夜讀之時,格外的緬懷舊事。尤不禁引發我「青燈有味」的情意,而想起兒童時代兩位難忘的人物: 白姑娘 我家鄉的小鎮上,有一座小小的耶穌堂,一座小小的天主堂。由鄉人自由地去做禮拜或望彌撒,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當然兩處都不去。但對於天主堂的白姑娘,卻有一分好感。因為她會講一口道地的家鄉土話,每回來都和母親有說有笑,一邊幫母親剝豆子,理青菜,一邊用家鄉土音教母親說英語:「口」就是「牛」,「糖糕」就是「狗」,「拾得糖」就是「坐下」,母親說:「番人話也不難講嘛。」 我一見她來,就說:「媽媽,番女來了。」母親總說:「不要叫她番女,喊她白姑娘嘛。」原來白姑娘還是一聲尊稱呢。因她皮膚白,夏天披戴雪白一身道袍,真像仙女下凡呢。 母親問她是那一國人,她說是英國人。問她為什麼要出家當修女,又飄洋過海到這樣的小地方來,她摸著念珠說:「我在聖母面前許下心願,要把一生奉獻給祂,為祂傳播廣大無邊的愛,世上沒有一件事比這更重要了。」我聽不大懂,母親顯得很敬佩的神情,因此逢年過節,母親總是盡量地捐獻食物或金錢,供天主堂購買衣被等救濟貧寒的異鄉人。母親說:「不管是什麼教,做慈善好事總是對的。」 阿榮伯就只信佛,他把基督教與天主教統統叫做「豬肚教」,說中國人不信洋教。儘管白姑娘對他和和氣氣,他總不大理她,說她是代教會騙錢的,總是叫她番女番女的,不肯喊她一聲白姑娘。 但有一回,阿榮伯病了,無緣無故的發燒不退,郎中的草藥服了一點沒有用,茶飯都不想很多天,人愈來愈瘦。母親沒了主意,告訴白姑娘,白姑娘先給他服了幾包藥粉,然後去城裡請來一位天主教醫院的醫生,給他打針吃藥,病很快就好了。頑固的阿榮伯,這才說:「番人真有一手,我這場病好了,就像脫掉一件破棉襖一般,好舒服。」以後他對白姑娘就客氣多了。 白姑娘在我們鎮上好幾年,幾乎家家對她都很熟。她並不勉強拉人去教堂,只耐心又和藹地挨家拜訪,還時常分給大家一點外國貨的煉乳、糖果、餅乾等等,所以孩子們個個喜歡她。她常教我們許多遊戲,有幾樣魔術,我至今還記得。那就是用手帕摺的小老鼠會蹦跳;折斷的火柴一晃眼又變成完整的;左手心握緊銅錢,會跑到右手心來。如今每回做這些魔術哄小孩子時,就會想起白姑娘的美麗笑容,和母親全神貫注對她欣賞的快樂神情。 儘管我們一家都不信天主教,但白姑娘的友善親切,卻給了我們母女不少快樂。但是有一天,她流著眼淚告訴我們,她要回國了,以後會有另一位白姑娘再來,但不會講跟她一樣好的家鄉土話,我們心裡好難過。 母親送了她一條親手繡的桌巾,我送她一個自己縫的土娃娃。她說她會永遠懷念我們的。臨行的前幾天,母親請她來家裡吃一頓豐富的晚餐,她摸出一條珠練,掛在我頸上,說:「你媽媽拜佛時用念珠念佛。我們也用念珠念經。這條念珠送你,願天主保佑你平安。」我的眼淚流下來了。她說:「不要哭,在我們心裡,並沒有分離。這裡就是我的家鄉了。有一天,我會再回來的。」 我哭得說不出話來。她悄悄地說:「我好喜歡你。記住,要做一個好孩子,孝順父母親。」我忽然捏住她手問她:「白姑娘,你的父母親呢?」她笑了一下說:「我從小是孤兒,沒有父母親。但我承受了更多的愛,仰望聖母,我要回報這分愛,我有著滿心的感激。」 這是她第一次對我講這麼深奧嚴肅的話,卻使我非常感動,也牢牢記得。因此使我長大以後,對天主教的修女,總有一分好感。 連阿榮伯這個反對「豬肚教」的人,白姑娘的離開,也使他淚眼汪汪的,他對她說:「白姑娘,你這一走,我們今生恐怕不會再見面了,不過我相信,你的天國,同我們菩薩的天堂是一樣的。我們會再碰面的。」 固執的阿榮伯會說這樣的話,白姑娘聽了好高興。她用很親暱的聲音喊了他一聲:「阿榮伯,天主保佑你,菩薩也保佑你。」 我們陪白姑娘到船埠頭,目送她跨上船,一身道袍,飄飄然地去遠了。 以後,我沒有再見到這位白姑娘,但直到現在,只要跟小朋友們表演那幾套魔術時,總要說一聲:「是白姑娘教我的。」 白姑娘教我的,不只是有趣的遊戲,而是她臨別時的幾句話:「要做個好孩子,好好孝順父母……我要回報這分愛,我有著滿心的感激。」 岩親爺 我家鄉土話稱乾爹為「親爺」,乾兒子為「親兒」。那意思是「跟親生父子一樣的親,不是乾的。」這番深厚的情意,至今使我念念不忘故鄉那位慈眉善目,卻不言不語的岩親爺。 岩親爺當然不姓岩,因為沒有這麼一個姓。但也不是正楷字「嚴」字的象形或諧音姓嚴。有趣的是岩親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位神仙。 這位神仙不姓嚴,卻姓呂,就是八仙裡的呂洞賓。 呂洞賓怎麼會跑到我家鄉的小鎮住下來,做孩子們的親爺?那就沒哪個知道了。我問母親,母親說:「神仙嘛,有好多個化身,飄到那裡,就住到那裡呀。」問阿榮伯,阿榮伯說:「我們瞿溪風水好呀,給神仙看中了。」問到外公,外公說:「瞿溪不只風景好,瞿溪的男孩子聰明肯讀書,呂洞賓伯伯讀書人,就收肯讀書的男孩子做親兒。親兒越收越多,就索性住下來了,因此地方上給他蓋了個廟。」 這座廟是奇奇怪怪的,沒有門,也沒有圍牆。卻是依山傍水,建築在一塊臨空伸出的岩石上,就著岩石,刻了一尊道袍方巾,像戲臺上諸葛亮打扮的神像,那就是呂洞賓。神龕的後壁,全是山岩,神龕前面是一塊平坦的岩石,算是正殿。岩石伸向半空,離地面約有三丈多高。下面有一個潭,潭水只十餘尺深,卻是清澈見底。因為岩上的涓涓細流,都滴入潭中,所以潭水在秋冬時也不會枯涸。村子裡講究點的大戶人家,都到這裡來挑一擔潭水,供煮飯泡茶之用。神仙賜的水是補的,孩子喝了會長生,會聰明。 廟是居高臨下的,前面就是那條主流瞿溪。溪水清而淺。乾旱的日子,都露出潭底的沙石來,溪上有十幾塊大石頭稀稀疏疏搭成的「橋」,鄉下人稱之為「丁步」,走過丁步,就到熱鬧的市中心瞿溪街,岩親爺鬧中取靜,坐在正殿裡,就可一目了然地觀賞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與在丁步上跳來跳去的小孩。這裡實在是個風景很奇怪的地方,若是現在,可算得是個名勝觀光區呢。 廟其實非常的小,至多不過三、四十坪。裡面沒有和尚,也沒有掌管求籤問卜的廟祝,因此廟裡香火並不旺盛,平時很少人來,倒成了我們小孩子玩樂的好地方。我常常對母親說:「媽,我要去岩親爺玩兒啦。」「岩親爺」變成了一個地方的名稱了。母親總是吩咐,「小姑娘不許爬得太高,只在殿裡玩玩就好了。」但玩久不回來,母親又擔心我會掉到殿下面的潭裡去,就叫阿榮伯來找我。我和小朋友們一見阿榮伯來了,就都往殿後兩邊的石階門上爬,越爬越高,一點也不聽母親的話,竟然爬到岩親爺頭頂那塊岩石上去了。阿榮伯好生氣,把我們統統趕下來,說呂洞賓伯伯會生氣,會把我們都變成笨丫頭。 我們心裡想想才生氣呢!因為呂洞賓伯伯只收男生當親兒,不收女生當親女,這是不公平的。其實這種不公平,明明是村子裡人自己搞出來的。凡是那家生的第一個寶貝男孩子都要拜神仙做親爺。備了香燭,去廟裡禮拜許願。用紅紙條寫上新生孩子的乳名,上面加個岩字,貼在正殿邊的岩壁上。神仙就收了他做親兒,保佑他長命富貴。大人們叫自己的孩子,都加個岩字,岩長生、岩文源、岩振雄……聽起來,有的文雅、有的威武,好不令人羨慕。 有一回,我們幾個女孩子也偷偷把自己的名字上面加個岩字,寫了紅紙條貼在岩石上,第二天都掉了。阿榮伯笑我們女孩子沒有資格,呂洞賓伯伯不收。其實是我們用的漿糊不牢,是用飯粒代替的,一乾自然就掉了。 我認為自己也是「讀書人」,背了不少課古文,怎麼沒資格拜親爺,氣不過,就在神像前誠心誠意地拜了三拜,暗暗許下心願說:「有一天我一定要跟男孩子一般地爭氣,做一番事業,回到家鄉,給你老人家修個大廟。你可得收全村的女孩子做親女兒喲!」 慈眉善目的神仙伯伯,只是笑咪咪不說一句話。但我相信他一定聽見我的祝告,一定會成全我的願望的。 我把求神仙的事告訴外公,外公摸摸我的頭說:「要想做什麼事,成什麼事業,都在你自己這個腦袋裡。你也不用怨男女不平等。你心裡敬愛岩親爺,他就是你的親爺了。」因此我也覺得自己是岩親爺的女兒了。 離開故鄉,到杭州念中學以後,就把這位「親爺」給忘了。大一時,因避日寇再回故鄉,才想起去岩親爺廟巡禮一番。仰望岩親爺石像,雖然灰土土的,卻一樣是滿臉的慈祥,俯看潭水清澈依舊,而原來熱鬧街角那一分冷冷清清,頓然使我感到無限的孤單寂寞。 那時,慈愛的外公早已逝世,母親憂鬱多病,阿榮伯也已老邁龍鍾。舊時遊伴,有的已出嫁,有的見了我都顯得很生疏的樣子。我踽踽涼涼地一個人在廟的周圍繞了一圈,想起童年時在神前的祝告,我不由得又在心裡祈禱起來:「願世界不再有戰亂殘殺,願人人安居樂業,願人間風調雨順。」 阿榮伯坐在殿口岩上等我,我扶著他一同踩著溪灘上的丁步回家,兒時在此跳躍的情景都在眼前。阿榮伯說:「你如今讀了洋學堂,哪裡還會相信岩親爺保佑我們。」我連忙說:「我相信啊,外公說過的,只要心裡敬愛仙師,他就永遠是你的親爺,我以後永不會忘記的。」阿榮伯嘆口氣說:「你不會忘記岩親爺,不會忘記家鄉,能常常回來就好。人會老,神仙是不會老的,他會保佑你的。」 我聽著聽著,眼中滿是淚水。 再一次離家以後,我就時常的想起岩親爺,想起那座小小的、冷冷清清的廟宇,尤其是在顛沛流離的歲月裡。我不是祈求岩親爺對我的祐護,而是岩親爺廟裡,曾有我歡樂童年的蹤影。「岩親爺」這個親暱的稱呼,是我小時候常常喊的,也是外公、母親和阿榮伯經常掛在嘴上念的。 我到老也不會忘記那位慈眉善目,不言不語,卻是縱容我爬到他頭頂岩石上去的岩親爺。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副刊
相信人人都愛念陸放翁的兩句詩:「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尤其我現在客居海外,想起大陸的兩個故鄉,和安居了將近四十年的第三個故鄉臺北,都離得我那麼遙遠。一燈夜讀之時,格外的緬懷舊事。尤不禁引發我「青燈有味」的情意,而想起兒童時代兩位難忘的人物: 白姑娘 我家鄉的小鎮上,有一座小小的耶穌堂,一座小小的天主堂。由鄉人自由地去做禮拜或望彌撒,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當然兩處都不去。但對於天主堂的白姑娘,卻有一分好感。因為她會講一口道地的家鄉土話,每回來都和母親有說有笑,一邊幫母親剝豆子,理青菜,一邊用家鄉土音教母親說英語:「口」就是「牛」,「糖糕」就是「狗」,「拾得糖」就是「坐下」,母親說:「番人話也不難講嘛。」 我一見她來,就說:「媽媽,番女來了。」母親總說:「不要叫她番女,喊她白姑娘嘛。」原來白姑娘還是一聲尊稱呢。因她皮膚白,夏天披戴雪白一身道袍,真像仙女下凡呢。 母親問她是那一國人,她說是英國人。問她為什麼要出家當修女,又飄洋過海到這樣的小地方來,她摸著念珠說:「我在聖母面前許下心願,要把一生奉獻給祂,為祂傳播廣大無邊的愛,世上沒有一件事比這更重要了。」我聽不大懂,母親顯得很敬佩的神情,因此逢年過節,母親總是盡量地捐獻食物或金錢,供天主堂購買衣被等救濟貧寒的異鄉人。母親說:「不管是什麼教,做慈善好事總是對的。」 阿榮伯就只信佛,他把基督教與天主教統統叫做「豬肚教」,說中國人不信洋教。儘管白姑娘對他和和氣氣,他總不大理她,說她是代教會騙錢的,總是叫她番女番女的,不肯喊她一聲白姑娘。 但有一回,阿榮伯病了,無緣無故的發燒不退,郎中的草藥服了一點沒有用,茶飯都不想很多天,人愈來愈瘦。母親沒了主意,告訴白姑娘,白姑娘先給他服了幾包藥粉,然後去城裡請來一位天主教醫院的醫生,給他打針吃藥,病很快就好了。頑固的阿榮伯,這才說:「番人真有一手,我這場病好了,就像脫掉一件破棉襖一般,好舒服。」以後他對白姑娘就客氣多了。 白姑娘在我們鎮上好幾年,幾乎家家對她都很熟。她並不勉強拉人去教堂,只耐心又和藹地挨家拜訪,還時常分給大家一點外國貨的煉乳、糖果、餅乾等等,所以孩子們個個喜歡她。她常教我們許多遊戲,有幾樣魔術,我至今還記得。那就是用手帕摺的小老鼠會蹦跳;折斷的火柴一晃眼又變成完整的;左手心握緊銅錢,會跑到右手心來。如今每回做這些魔術哄小孩子時,就會想起白姑娘的美麗笑容,和母親全神貫注對她欣賞的快樂神情。 儘管我們一家都不信天主教,但白姑娘的友善親切,卻給了我們母女不少快樂。但是有一天,她流著眼淚告訴我們,她要回國了,以後會有另一位白姑娘再來,但不會講跟她一樣好的家鄉土話,我們心裡好難過。 母親送了她一條親手繡的桌巾,我送她一個自己縫的土娃娃。她說她會永遠懷念我們的。臨行的前幾天,母親請她來家裡吃一頓豐富的晚餐,她摸出一條珠練,掛在我頸上,說:「你媽媽拜佛時用念珠念佛。我們也用念珠念經。這條念珠送你,願天主保佑你平安。」我的眼淚流下來了。她說:「不要哭,在我們心裡,並沒有分離。這裡就是我的家鄉了。有一天,我會再回來的。」 我哭得說不出話來。她悄悄地說:「我好喜歡你。記住,要做一個好孩子,孝順父母親。」我忽然捏住她手問她:「白姑娘,你的父母親呢?」她笑了一下說:「我從小是孤兒,沒有父母親。但我承受了更多的愛,仰望聖母,我要回報這分愛,我有著滿心的感激。」 這是她第一次對我講這麼深奧嚴肅的話,卻使我非常感動,也牢牢記得。因此使我長大以後,對天主教的修女,總有一分好感。 連阿榮伯這個反對「豬肚教」的人,白姑娘的離開,也使他淚眼汪汪的,他對她說:「白姑娘,你這一走,我們今生恐怕不會再見面了,不過我相信,你的天國,同我們菩薩的天堂是一樣的。我們會再碰面的。」 固執的阿榮伯會說這樣的話,白姑娘聽了好高興。她用很親暱的聲音喊了他一聲:「阿榮伯,天主保佑你,菩薩也保佑你。」 我們陪白姑娘到船埠頭,目送她跨上船,一身道袍,飄飄然地去遠了。 以後,我沒有再見到這位白姑娘,但直到現在,只要跟小朋友們表演那幾套魔術時,總要說一聲:「是白姑娘教我的。」 白姑娘教我的,不只是有趣的遊戲,而是她臨別時的幾句話:「要做個好孩子,好好孝順父母……我要回報這分愛,我有著滿心的感激。」 岩親爺 我家鄉土話稱乾爹為「親爺」,乾兒子為「親兒」。那意思是「跟親生父子一樣的親,不是乾的。」這番深厚的情意,至今使我念念不忘故鄉那位慈眉善目,卻不言不語的岩親爺。 岩親爺當然不姓岩,因為沒有這麼一個姓。但也不是正楷字「嚴」字的象形或諧音姓嚴。有趣的是岩親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位神仙。 這位神仙不姓嚴,卻姓呂,就是八仙裡的呂洞賓。 呂洞賓怎麼會跑到我家鄉的小鎮住下來,做孩子們的親爺?那就沒哪個知道了。我問母親,母親說:「神仙嘛,有好多個化身,飄到那裡,就住到那裡呀。」問阿榮伯,阿榮伯說:「我們瞿溪風水好呀,給神仙看中了。」問到外公,外公說:「瞿溪不只風景好,瞿溪的男孩子聰明肯讀書,呂洞賓伯伯讀書人,就收肯讀書的男孩子做親兒。親兒越收越多,就索性住下來了,因此地方上給他蓋了個廟。」 這座廟是奇奇怪怪的,沒有門,也沒有圍牆。卻是依山傍水,建築在一塊臨空伸出的岩石上,就著岩石,刻了一尊道袍方巾,像戲臺上諸葛亮打扮的神像,那就是呂洞賓。神龕的後壁,全是山岩,神龕前面是一塊平坦的岩石,算是正殿。岩石伸向半空,離地面約有三丈多高。下面有一個潭,潭水只十餘尺深,卻是清澈見底。因為岩上的涓涓細流,都滴入潭中,所以潭水在秋冬時也不會枯涸。村子裡講究點的大戶人家,都到這裡來挑一擔潭水,供煮飯泡茶之用。神仙賜的水是補的,孩子喝了會長生,會聰明。 廟是居高臨下的,前面就是那條主流瞿溪。溪水清而淺。乾旱的日子,都露出潭底的沙石來,溪上有十幾塊大石頭稀稀疏疏搭成的「橋」,鄉下人稱之為「丁步」,走過丁步,就到熱鬧的市中心瞿溪街,岩親爺鬧中取靜,坐在正殿裡,就可一目了然地觀賞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與在丁步上跳來跳去的小孩。這裡實在是個風景很奇怪的地方,若是現在,可算得是個名勝觀光區呢。 廟其實非常的小,至多不過三、四十坪。裡面沒有和尚,也沒有掌管求籤問卜的廟祝,因此廟裡香火並不旺盛,平時很少人來,倒成了我們小孩子玩樂的好地方。我常常對母親說:「媽,我要去岩親爺玩兒啦。」「岩親爺」變成了一個地方的名稱了。母親總是吩咐,「小姑娘不許爬得太高,只在殿裡玩玩就好了。」但玩久不回來,母親又擔心我會掉到殿下面的潭裡去,就叫阿榮伯來找我。我和小朋友們一見阿榮伯來了,就都往殿後兩邊的石階門上爬,越爬越高,一點也不聽母親的話,竟然爬到岩親爺頭頂那塊岩石上去了。阿榮伯好生氣,把我們統統趕下來,說呂洞賓伯伯會生氣,會把我們都變成笨丫頭。 我們心裡想想才生氣呢!因為呂洞賓伯伯只收男生當親兒,不收女生當親女,這是不公平的。其實這種不公平,明明是村子裡人自己搞出來的。凡是那家生的第一個寶貝男孩子都要拜神仙做親爺。備了香燭,去廟裡禮拜許願。用紅紙條寫上新生孩子的乳名,上面加個岩字,貼在正殿邊的岩壁上。神仙就收了他做親兒,保佑他長命富貴。大人們叫自己的孩子,都加個岩字,岩長生、岩文源、岩振雄……聽起來,有的文雅、有的威武,好不令人羨慕。 有一回,我們幾個女孩子也偷偷把自己的名字上面加個岩字,寫了紅紙條貼在岩石上,第二天都掉了。阿榮伯笑我們女孩子沒有資格,呂洞賓伯伯不收。其實是我們用的漿糊不牢,是用飯粒代替的,一乾自然就掉了。 我認為自己也是「讀書人」,背了不少課古文,怎麼沒資格拜親爺,氣不過,就在神像前誠心誠意地拜了三拜,暗暗許下心願說:「有一天我一定要跟男孩子一般地爭氣,做一番事業,回到家鄉,給你老人家修個大廟。你可得收全村的女孩子做親女兒喲!」 慈眉善目的神仙伯伯,只是笑咪咪不說一句話。但我相信他一定聽見我的祝告,一定會成全我的願望的。 我把求神仙的事告訴外公,外公摸摸我的頭說:「要想做什麼事,成什麼事業,都在你自己這個腦袋裡。你也不用怨男女不平等。你心裡敬愛岩親爺,他就是你的親爺了。」因此我也覺得自己是岩親爺的女兒了。 離開故鄉,到杭州念中學以後,就把這位「親爺」給忘了。大一時,因避日寇再回故鄉,才想起去岩親爺廟巡禮一番。仰望岩親爺石像,雖然灰土土的,卻一樣是滿臉的慈祥,俯看潭水清澈依舊,而原來熱鬧街角那一分冷冷清清,頓然使我感到無限的孤單寂寞。 那時,慈愛的外公早已逝世,母親憂鬱多病,阿榮伯也已老邁龍鍾。舊時遊伴,有的已出嫁,有的見了我都顯得很生疏的樣子。我踽踽涼涼地一個人在廟的周圍繞了一圈,想起童年時在神前的祝告,我不由得又在心裡祈禱起來:「願世界不再有戰亂殘殺,願人人安居樂業,願人間風調雨順。」 阿榮伯坐在殿口岩上等我,我扶著他一同踩著溪灘上的丁步回家,兒時在此跳躍的情景都在眼前。阿榮伯說:「你如今讀了洋學堂,哪裡還會相信岩親爺保佑我們。」我連忙說:「我相信啊,外公說過的,只要心裡敬愛仙師,他就永遠是你的親爺,我以後永不會忘記的。」阿榮伯嘆口氣說:「你不會忘記岩親爺,不會忘記家鄉,能常常回來就好。人會老,神仙是不會老的,他會保佑你的。」 我聽著聽著,眼中滿是淚水。 再一次離家以後,我就時常的想起岩親爺,想起那座小小的、冷冷清清的廟宇,尤其是在顛沛流離的歲月裡。我不是祈求岩親爺對我的祐護,而是岩親爺廟裡,曾有我歡樂童年的蹤影。「岩親爺」這個親暱的稱呼,是我小時候常常喊的,也是外公、母親和阿榮伯經常掛在嘴上念的。 我到老也不會忘記那位慈眉善目,不言不語,卻是縱容我爬到他頭頂岩石上去的岩親爺。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副刊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