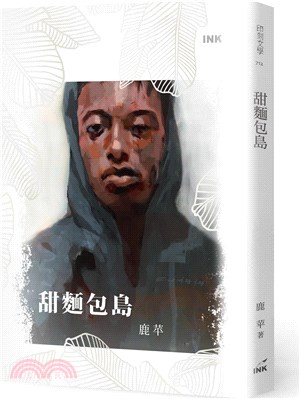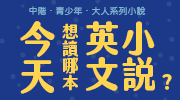甜麵包島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獻給海洋中每一座曾被殖民的島
我偏執的認為,微小的足以成就巨大的,卑微到透徹所剩下的就是堅強,不完美本就是生命的相貌,是上帝用來開啟智慧的鎖。──鹿苹
離開與重返,死亡與守候,桎梏與瘋狂,加勒比海的風浪,緩緩沁染人心的至深處,迴盪善與罪的永恆叩問。
那時候孩子們認為的遠方,差不多就是海灘對面的甜麵包島。
它像一艘隨著海浪上下起伏的大船,在海中搖動。
〈旱季〉
玫瑰十七歲時離開小島,她謹記母親的叮嚀,勤奮的在陰鬱的倫敦展開截了然不同的人生,求學、工作、與同鄉結婚生子,半生在的辛勞最終換得了故鄉的一方土地,和先生返回小島後,建設出了屬於自己的夢想家園,曾以為心中寄存的理想黃昏,已經到來……
〈半月瓣〉
羅蘭醒來,發現太陽已經下山了,但自己竟陷在一個雜草叢生的土坑中,她輕盈的爬出坑外,依隨著月光的照引找尋回家的法法,謎般的路程中,羅蘭想起了安大略湖畔的父親,想起當初帶著期盼與丈夫孩子移居到小海島……,直到在家門口,看到沉默不語卻渾身顫抖的丈夫。
〈腰果灣〉
塔塔踮起腳,從鏽色欄杆望出去,就能見到那日日不同的海面,他依稀記得監牢外的市集、教堂的鐘聲、烤餅、鹽尖山以及那條黑腹蛇。沉靜孤獨,他極少開口,唯一關心的只是:「看到蛇了嗎?」
遠方的孤島,三個無可傾訴的靈魂,如何穿透海面而來?
林懷民 阮慶岳 陳玉慧 馮品佳 駱以軍_至情推薦
加勒比海小島熱氣氤氳。巨大的蜈蚣在床上扭曲爬行。亡魂看著她的家人在教堂進行安息禮拜。你以為在讀《百年孤寂》,卻發現講的是現代人流離的故事。鹿苹敏感描述溫度、氣味、叢林的植物,夢想與絕望,語氣極端詩意,天羅地網的帶著讀者走過角色的心路歷程,讓人掩卷後又想重翻細讀那幽幽放光的文字。──林懷民
這是一本有著內斂自持態度,卻又力道深遠的小說,作者時而有如神佛般冷靜客觀地審視著受苦無助的蒼生們,時而細膩入裡地描繪著日常現實的各種細節,讓我們得以貼靠進入角色們的內裡哀傷情境,並在這樣的一出一入間,展現了作者的遼闊小說視野與真摯生命關懷。──阮慶岳
以詩意的筆觸勾勒異國奇妙風情,故事開始於地平線的盡頭,情節獨特。文字洋溢神祕而迷人的氛圍,內涵了現代感和實驗性,少見的寫作風格也愈臻成熟完善。她的小說彷彿自成一座熠熠生輝的島嶼。──陳玉慧
這幾篇小說,很奇妙的像在夢中的一台放映機,那種應是玻璃彩、膠彩的透明畫面,卻用卷軸畫的形式,不斷不斷捲動打開。你抱著讀小說的期待,跟著那捲開時的靜謐的傷害記憶,世界如此劇變但夢的流浪者,如此童話詩,輕盈溫柔的播放,小說其實是那麼痛苦,甚至恐怖的事件,耐性的鋪敘完痛苦之延異,這就是小小的人類我們,安靜的,溫和的,良善的,不瘋狂不激情的,能夠活下去的方式。讀完只覺醉眼朦朧,被那個美麗心靈,告知故事的同時,又被修復了。──駱以軍
封面繪圖:JV. Huang
作者簡介
鹿苹
因著寫日記而集結出版了詩集《流浪築牆》,為了探訪敘利亞詩人的家鄉而遠走大馬士革,爾後爆發的敘國內戰推促了小說《左手之地》的完成。
《甜麵包島》為鹿苹的第三本書,背景為大西洋及加勒比海間的西印度洋群島。這本書是她為海洋中每一座曾被殖民的島所獻上的故事。
名人/編輯推薦
重磅評論──
詩意,微縮影像,寫出生活過才懂得的美好日子與人際關係最可能的樣子。──蘇偉貞(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本為了「海洋中每一座曾被殖民的島」寫出的《甜麵包島》,圍繞著加勒比海,悠悠帶出來自遠方的沉默、旁觀與落空。──黃資婷(成功大學規劃設計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不是童話故事,也不是後殖民預言,而是記憶的書寫、感知的解放、感官的盛宴。──張淑麗(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
無間回轉,孤寂流離,人與自然共生為救贖之徑。──劉雪珍(輔仁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她的跨族群想像、抗殖民書寫和深刻的島嶼意識令人驚豔,她對歷史細節的掌握、人物心理的分析、還有加勒比海山林環境熱帶氣候的描寫都令人印象深刻。──梁一萍(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目次
半月瓣
腰果灣
(後記)某處與彼處
書摘/試閱
腰果灣
是下午五點了。塔塔用十指攀著過高的窗沿穩定住身體,踮起腳,透過鏽色的欄杆從陰暗的牢裡向海面上望去。
海岸邊的傍晚從來都是獨一的,遠遠的橘色浮標在海中忽隱忽現,每一次隱去後,似乎又從另一片的海面冒上來。鋪展開來的海面對塔塔來說,像是一個起點,通往一條漫無盡頭的航道,而站在起點上的他,卻從來沒有出發過。
海面上浮著星星點點的小艇,水線上鑲著一條條長長的浪花,除了海鳥的嘔嘔聲,也聽得到一些城市的喧囂,遠方的海天交融處聚集著團團陰影,天色黯然,再往深處看去,雲更彷彿凝成一片愁雲慘霧,死寂的壓制著海面,幾分鐘之內成團的烏雲相繼簇擁著來到,還來不及落下的夕陽在低伏的烏雲邊上鑲出了一道金線,金光沿著海平面沉了下去,突然之間金變成滯紅,光熱消散,白日便突然的熄滅了。
一長聲汽笛響起,一艘巨大的豪華郵輪正緩慢的離港。離岸漸遠的汽笛聲伴著空中海鳥與飛蟲的嗡嗡聲,閉上眼,塔塔似乎就真實的站在港岸邊,但牢房的牆壓圍在四周。房內僅有一扇透氣窗,那窗僅僅能容納一個角度的視野,永遠是面朝著大海。
房內是那樣的悶熱,就算是夜裡吹過風也格外的輕,若有若無,難以降溫。塔塔就像這座牢房的一部分,他可以是一面牆,也可以是那張兩英寸厚的破床墊,他也代表了房內那難聞的氣味,在這個沒有回音的地方,破碎的、完整的都被世上的一切隔絕。
塔塔依稀記得那片窗框外的城市。
小巷與街道蜿蜒曲折,面海的山坡上有兩座高聳的天主堂,一座已經廢棄,紅色屋頂被鬱鬱蔥蔥的樹枝藤蔓所覆蓋著,另一座教堂仍然敞亮的站立著,按時敲鐘。港邊的公共市場邊上小販很多,什麼都有,羅提烤餅、冰鎮過的整顆椰子、白棉紗內衣、殺螞蟻藥……,有幾年塔塔和他的父親也曾在那兒賣過種植園裡批來的水果。
天暗下來後,每日的風景大致相同,岸邊會亮起星星燈火,堤防的前端有座燈塔,船隻亮出零星的燈光,在海面上隨著夜的倒影搖曳,上上下下地晃。
有時,在睡眠被吞噬的夜裡,塔塔蜷縮在牆根下,側著身子抵著牆面,沒有一絲聲音,一切都緘默不語,城市與獄卒都安靜著,某些事情的標記在他腦中盤旋不去,常常就在那時候,山坡上教堂的鐘聲會隨著夜裡的風,一前一後帶著些微的時間差,叮叮噹噹的灌入狹窄幽暗的牢房中。
在牢裡,每一日的結尾都無聲無息地走向未來,掀不起任何的浪花,像塔塔的日漸敗落。那壯碩的又難以躲避人們關注的身形,曾是勤奮的,派得上用場的,但在矛盾環境的變遷下,卻又成了羞辱的標誌,隨著時光,連他有時候也無從分辨,再過些日子後有什麼能讓他記得,又有什麼會隨著時間散落。
再往海上看去時,郵輪已走遠,船身上一格一格的窗在片刻即沉的暮色中,反射著闊氣的光。
「離港的是皇家加勒比號嗎?」坎迪多用手指搔抓著下巴。
塔塔搖搖頭,海港停靠的每一艘郵輪,都有一個耀若珠寶的名稱,即使在這個陰暗的斗室中都熠熠生輝,但他無從分辨郵輪的名稱,何況答與不答,坎迪多的反應都是一樣的。坎迪多個子矮,站上椅子才搆得到窗框,他十分關心離港的郵輪,因為那些郵輪的名字提供了他一次想起外面的機會,多半時間他都只是隨口問問,沒有答案也行,像是一個定時的鬧鐘,時間到了就響起一樣的聲音。
坎迪多認得各式各樣來自不同公司的郵輪,那些載客量上千的加勒比海豪華郵輪,有九層樓的、十二層樓的,有的還有兩座劇院、滑水道。郵輪的內部是塔塔無法想像的事情,他看不到裡面,而且坎迪多貧乏的描述也沒有任何幫助,再說對於這兩名關在牢房中的人來說,這一種認知,只從方方面面顯出身處環境下的不幸。這就是塔塔和坎迪多的人生,他們永遠不會明白,對方是怎麼變成這個樣的,就算鉅細靡遺地講了,多半也與事實無關,至多只是一段扭曲的記憶,即便,他們自己以為那就是事實。
於是他倆的牢房中,除了坎迪多的郵輪往事,日復一日的傍晚,塔塔只是默默地等著晚餐單調的到來。中午有機會到飯廳與其他犯人共餐,但大部分的獄警都在五點鐘下班,晚餐時間管理人手不足,晚餐他們總是在牢房內吃。塔塔有什麼就吃什麼,安靜地接受一切,沒人探究,畢竟塔塔這種人並不稀奇,世界上每一座監獄裡,都找得出一個總是陷在沉默裡,徹底疏離的人。但坎迪多對這裡老用薑黃粉混著燉煮的,芋頭、木薯、甘藷這些根莖食物帶著極大的厭惡,放飯時常用帶著西班牙腔的英文咒罵、用手掌拍打著門板嚷嚷:「怎麼啦?怎麼啦?島上只有這種牛拉出來的稀屎嗎?」
在監獄裡已經待了七年的坎迪多,每當談起他為何背離正常生活,都會從他進監前所吃到的「食物」談起,雖然每一次的敘事不盡相同,但那些食物都傳達出了一種悲傷,一些因慾望而引起的不適,但這些不能和坎迪多產生任何關係的食物,很快的就會提醒他,躺在這張不屬於自己的鐵架床上的緣由。坎迪多曾是某艘豪華郵輪的服務生,那些郵輪熱門的路線都從邁阿密出港,圍繞著西印度洋的小島航行。工作時他穿著體面,制服都是熨燙過的白襯衫,每個月還能寄上幾百美金回家,但他老從遊客身上撈油水,從小費到可變賣錢財的貴重物品他都不放過。膽大妄為的坎迪多被捕的那一次,偷了客人的手機,待船靠了岸,便上岸去銷贓,一上岸他就被捕了。因為郵輪已出了公海靠了岸,就只能依照著島上的法律判了十年,他成了牢裡少數的幾個「白東西」。
塔塔入獄時,坎迪多像一件被遺棄的舶來品,孤獨的面對著最後一次旅程中沒有趕上船的奇遇。坎迪多第一眼見到塔塔進入牢房時,也像所有人一樣,不由自主地張大了嘴。
塔塔灰色的雙眼就像褪色的彈珠嵌在岩石裡,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寬大的手掌上端著剛發的枕頭和床單,身上那件不合身的制服,讓塔塔的手肘和腳踝都露在外面。是了,也許那一刻塔塔的模樣的確有點嚇人,坎迪多不由自主地對這個身形巨大的人產生了不安,但又不願示弱,在這種不知道如何反應的情緒中,坎迪多努力想展現平靜,又想恰如其分的保持尊嚴。他一面盡量不著痕跡地退往牆角,一面觀察著塔塔,坎迪多掛著副虛假的笑容,每次他試圖強壓住恐懼時,便會擠出這樣的面容來。
但還沒過幾周,坎迪多對塔塔,一如對這島上的食物,再也提不起興趣。這失去的興致,正好可以幫助他們不再互相干擾,在這個沒有驚喜可能的地方,多餘的好奇心一直都是輸家。除了養豬、種番薯等勞務工作能離開牢房,其他時間兩人都困在這一方斗室之中,一個躺在這邊,一個躺在那邊。對漫長的牢獄生活塔塔似乎做好了準備,大半的時間,他都緊閉著雙唇蜷曲在床上,看上去像是嵌在化石中的一條蟲子。每天晚上,九點五十分時會做熄燈前的廣播,十點一到,只剩一團漆黑,閉上眼睛或是張開眼睛,環境能給的差別都不大,在這期間無法入睡的人,只能去思考任何能讓人挨到隔日黎明的事情,只能在心中尋找一種帶著過去節奏的想望。塔塔平常不說話,但只要開口,無非是關於夢境與蛇。
但其實只是關於蛇。
不停的有人告訴他,那是他做的夢,但「看到了蛇嗎?」是他唯一在乎的。無數次發問,塔塔從來沒有得到真正的回應,但關乎蛇的事情仍然會成為他張開口的原因。無法有正常對話和坐姿不常變更的塔塔,讓他的獄友非常的不悅,幾次要求換房去和別人同住。沒人想像得到,沉默與平和也能引起人厭煩的情緒,坎迪多說塔塔是個瘋子,精神錯亂,再同住下去他也要瘋狂,就算他能夠提早出獄,也只怕塔塔會讓他在那之前就絕望地死去。
但在這樣的一個牢獄中,什麼都沒有特別的意義,那種消磨時間的艱難,讓凡事都沒有什麼好追究的,沒人在乎誰被愛過,誰被恨過,他們目前的境遇,就是他們人生的反饋,又會有誰來搭理這兩個被囚之人。
夜裡的牢房是最安靜的地方,時不時,塔塔會在夜裡醒來,一具具裹著毯子蜷成一團的身軀,都平穩的呼吸著。每逢這樣的夜裡,他不能再入睡,也不嘗試入睡,只是努力回憶那些細微滲出的,但越急切,那一切就掉頭跑得更快,很多時候,塔塔只能抬起手摩挲額角,只要摸著那道凹凸不平的疤痕,他就能不依不撓的相信,他曾有過盼望,曾享有過某種庇護。只不過,他仍繼續的被侵蝕,和被棄之於荒野的孩童一樣,找不到出口的塔塔,靜靜地匍匐在四壁之牢內,專注於其間,用屬於自己的想像,等待那無可附加的末了。
據說塔塔是雙生子,他的生母是個晨昏不分的酗酒婦人,因為她總是用吸管飲酒,人都叫她「麥稈子」。麥稈子在年輕的時候是腰果灣少年們爭競邀約的對象,她長得很高,有一雙筆直的長腿,而且比起其他的島民,她的膚色像是深棕色的蜂蜜,帶著淡淡的金黃。麥稈子的美貌應該是繼承了她的母親,一位來自法屬瓜德羅普島的黑白混血兒。出身這樣的特別,麥稈子家中就像某些發達的人,有些誰也沒見過的遠房的親戚,那種親戚通常很早就有辦法移民到國外去生活,在這小島上,任誰都對國外的親戚,懷有三分盼望和五分天馬行空的妄想。麥稈子家也一樣,他們緊緊地拉著風箏這一頭那條細細的線,深怕有什麼閃失就和英國的親戚斷了往來。
在緩慢的計畫之中,麥稈子的父親東存西湊的準備了好些年,總算弄到了一筆錢,買下了唯一一張前往倫敦的機票,不多久便出征般的在眾人羨慕的眼光中到英國去開拓新生活了。
打那時候起,麥稈子便在眾多追求者前宣告,她不會,也不能嫁給島上的當地人,再過不久她便要到英國與父親會合,在英國繼續學業,到那時一切都要能配合新環境才好,這樣的決定是免她多掛心島上的人與事物。在島上生活的樣貌,還不能讓麥稈子明白新世界到底是什麼的時候,她就盡了最大的努力,捕捉著未知的日子。過於虔誠地,她熱衷於一切可盼望的,在沒有徵兆的情況下便面對起未來生活的新義,她告訴自己,她絕不會,像腰果灣海灘邊的沙子落入大海,在空洞而反覆的海浪裡打轉。
麥稈子的父親一到了倫敦,發現了新世界後,不多久,便消失在大家想像的倫敦霧中。他一年半載杳無音信,後來有人傳消息,說他已搬到了威爾斯,再娶了一個其醜無比,但卻有房產的白種女人。不論那些無可求證的傳聞是不是真的,那些所寄望的未來,被一名其貌不揚的英國女人掠去,終究是讓那美麗的麥稈子母女,像得了胃病般的消沉。
兩年半之後,麥稈子的混血兒母親也拋下了她,母親經人介紹,二嫁回了瓜德羅普島。母親把一幢殘破不堪、搖搖欲墜的木板屋留給了麥稈子,曾經不可一世的她,孤伶伶地待在那如雞舍的房內,或睡或醒,或回首往日,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了,沒有人理睬她,回憶中單留下一些光彩亮麗的人物影像。儘管她仍然擁有那種被眾人渴求的美貌,但原本那些被她的高傲姿態嘲諷過的男子們,卻一去不復返。
那時,白天她會步行到下一個村莊的蒸餾酒廠去工作,在那兒看顧著正在烹煮的甘蔗汁,日子雖然差強人意,但麥稈子對自己的浪漫意識仍剩下盼望,她感覺隨著時間,自己就能過渡到另一番景象之中。
也許麥稈子的生活一直以來就是如此的,也許隨機又詭譎多變的島上人生,就是這樣,沒有誰,能將自己從困境之中解救出來。
在那種自然狀態中,一次颶風過境,麥稈子獨自一人在嘎茲作響的木板屋內瑟瑟發抖。風首先喚起了她心中的孤獨感,隨之而來的恐懼,讓麥稈子一整個下午都專心致志地盯著頭上的天花板,不幸的是,傍晚屋頂被還是被一陣巨風拔起,鐵皮頂像一張揚起的帆,隨風而去。本來就只是用幾根木材撐著的牆,在巨大壓力下搖搖晃晃,不多久水終於漫淹進了屋,一些塑膠水桶、盒子像逃命般跟著大量的雨水漂離開了她的家。幾個禮拜過去,風雨後的一些自然現象仍在發生,屋內的角落開始有雜草的細苗在汙泥上冒出頭來,剩下的半幢木板屋快速地,轉化成了一個骯髒的有機體。
自那風雨不停地下午起,一種介於窘迫與貧窮之間的嘲諷,讓沒有嫁妝又無處可去的麥稈子,杵在潮濕的汙泥中開始思考一些事情。沒過多久她就傲氣地,放開了那半幢破屋子,嫁給了塔塔的父親。
麥稈子就這樣嫁給了一個滿臉鬍渣的漁夫,一個如果她去了英國,根本再也不會記起的那種平庸的,腰果灣的男子。她嫁給塔塔的父親時,父親已經四十二歲了。儘管不太情願,但隨後麥稈子就馬上有了安身之處,也許她也有一些另外的想法,當然麥稈子不會承認,就算是對自己的靈魂,她也不會承認。
全村的人甚是隔壁村的都知道,漁夫有點產業,不但有自己的船,還是兩艘帶著馬達的,許多打漁人還得要跟著上他的船去幫忙捕撈,才能在日落時分到一些魚貨。
婚後的麥稈子曾經以為,自己可以過著安於家庭,愛惜丈夫的那種日子,但所有對未來燃起的期待,都埋藏於漁夫有一天能送她去英國尋親或度假的寄望之下。當然,這只是種新婚時期,常人都會產生的圓夢式盼望。
要不多久,麥稈子便了解到,一切都差不有定論了,就幸福生活而言,命運也就只能做到這個份上,在這個與世隔絕又貧瘠的小漁村裡所發生的一切,都並不是幸福生活的前提,在這裡,會橫空出世的,至多不過是一場暴風雨。自此她接受了,在那片腰果灣喧鬧的海灘前,她只能從這些妄想之中退身出來,將自己和排山倒海的憤怒,封閉在另一個時空裡。
麥稈子皺著眉,眼中盡是刻薄地,看著漁夫賴以為生的物件,她看不上那些綠色的漁網以及塑膠桶裡面那些灰撲撲的魚類,臉上老是帶著孩童般不掩飾的微怒表情,因為她一直夢想的那個救星,那個匿名人,那個天使或是上帝,現在她能肯定,是不存在的了。她仍然是年輕美麗的,卻在如此湛藍的海天之間,將內心所有激昂的東西都投向了海的深處。
漁夫三不五時會給她些零花錢,這讓她成天都在附近的林子裡面晃蕩,麥稈子既孤單又難以接近,在那樣的情緒中,對明日的盼望是稀少而模糊的,她常常以酒精來消耗一整天,或是來滿足一些不可名狀的人生空格。無所事事的麥稈子總拿著一瓶蘭姆酒,邊走邊用吸管慢慢地啜飲。海邊白辣的烈日常曬得她發怔,耳內的海浪聲也常帶著某種悲傷的節奏,有時候她會突然恢復了神智,想起那早已結束的盼望而啜泣。不管清不清醒,她的腳步永遠跟不上她修長的雙腿,走著走著,總是磕磕絆絆,反正,她已經不想對自己的命運挑戰,腰果灣就是一個懲罰,麥稈子像名犯人般的從容,去哪個方向都可以,高尚或拙劣的酒都是一樣的,有酒精就能順服於現實,不再厭惡自己破碎的心、無用處的美貌、腥鹹的海風、父母的遺棄,還有她被禁錮在腰果灣的靈魂。甚至那個改變一切的起頭,那名將她父親擄去,在威爾斯有房產的陌生女子,所有的那些,都可以透過酒後所經歷的死亡,爾後復生。
麥稈子在酒精中的迷茫,彷彿無法治癒的痼疾,附近的人從來不想管,任誰也不想捲進她的憂傷之中。塔塔的父親常在天之將暗時,在附近海灘上拉起麥稈子的胳膊,一個人揹上那個沒有多少重量的妻子回家。
塔塔出生的那年雨季,一月份海裡面旗魚和黃鰭金槍魚捕獲量大增,麥稈子的丈夫與幾名漁人日日出海,日落前帶回來的除了魚,也沒有什麼令麥稈子振奮的消息。憂鬱的麥稈子在孕期後段,肚子大得驚人,分娩的前一日下午,有人看見她膝蓋彎曲,用一種禱告的姿勢長跪在潮濕的沙灘上,望著天空許久,像是在尋找未來道路的指引,後來沙灘上的人發現,她只是醉了。
隔日是個星期四,下午三點鐘,塔塔的孿生兄弟先出生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