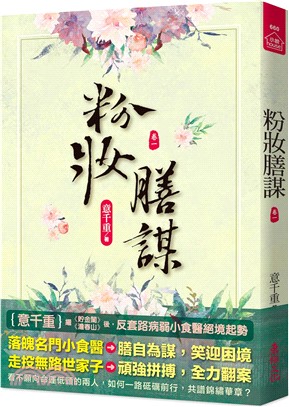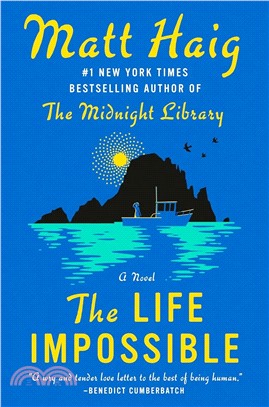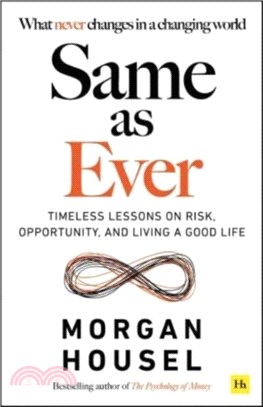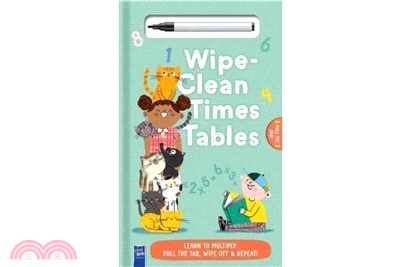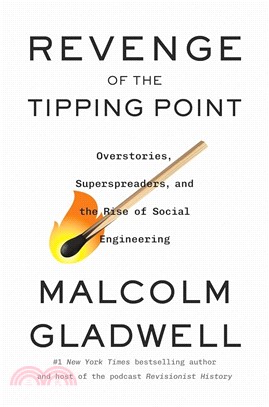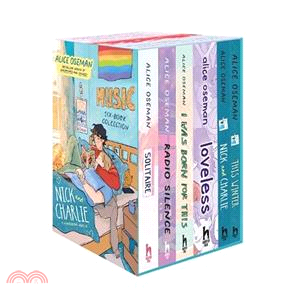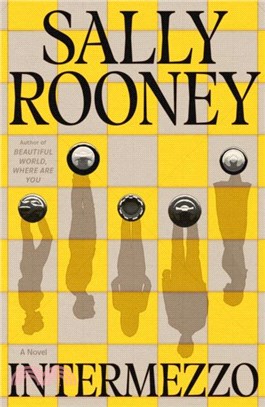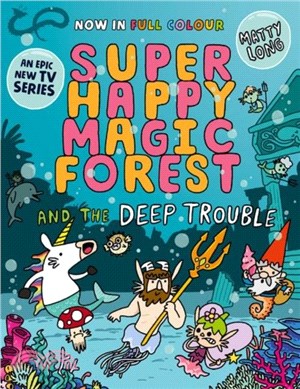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意千重繼《貯金閨》《澹春山》後,反套路病弱小食醫絕境起勢
落魄名門小食醫 >>> 膳自為謀,笑迎困境
走投無路世家子 >>> 頑強拼搏,全力翻案
看不願向命運低頭的兩人,如何一路砥礪前行,共譜錦繡華章?
★★編輯強推,必讀理由★★
這是一個看似柔弱,實則智武雙全的女子,以藥膳為謀生手段,一步步成為大唐女官兼談情說愛的故事。作者希望藉著這個作品,讓大家能夠看到成功女性的另一種活法,無論任何時候,都獨立自主,珍惜自己。女主本身設定討喜,會醫且善廚藝,外表清冷如仙女,其實狠辣兼有點痞痞的,不僅毒舌,還會揍人,總是不按牌理出牌。男主的人設也有所創新,更接地氣,幽默有趣,同時有勇有謀。兩人在人生低谷相遇,一路上以打怪升級的方式相互扶持,在匡扶正義的鬥爭中惺惺相惜,共同成長。一場極度可愛的戀情也就此展開,溢滿強大清新甜寵力。
大唐盛世,武周末年,科舉興起,新貴迭出,風起雲湧中,
曾經輝煌百年的名門士族走到了命運的轉折關頭。
本是散打搏擊冠軍,獅子座的鋼鐵直女,
穿越成為了大唐京兆杜氏旁支的孤女杜清檀,
不僅天生病弱,家財還被亡父耗盡,奴僕四散,
只剩寡居的伯母楊氏及幼小的堂弟團團相依為命,勉強度日。
這般落魄潦倒,也難怪簪纓世胄的蘭陵蕭氏要嫌棄悔婚了。
但蕭家真是好算計,竟逼迫她接受兒媳變義女!
明明是背信棄義,還怕名聲不好聽,非得拉著孤兒寡婦當遮羞布?
別以為嬌弱病美人好欺負,面對蕭家那些見不得人的腌臢手段,
她不光要咬牙爭上一爭,讓始作俑者裴氏付出相對代價!
還要走出一條與普通世家女子截然不同的路,
食醫之術,能養活並庇護自己和家人,還能造福很多人啊!
她要讓自己活得有尊嚴,身邊的人活得有體面,
像真正的人,而不是豬狗、草芥一樣的存在。
落魄名門小食醫 >>> 膳自為謀,笑迎困境
走投無路世家子 >>> 頑強拼搏,全力翻案
看不願向命運低頭的兩人,如何一路砥礪前行,共譜錦繡華章?
★★編輯強推,必讀理由★★
這是一個看似柔弱,實則智武雙全的女子,以藥膳為謀生手段,一步步成為大唐女官兼談情說愛的故事。作者希望藉著這個作品,讓大家能夠看到成功女性的另一種活法,無論任何時候,都獨立自主,珍惜自己。女主本身設定討喜,會醫且善廚藝,外表清冷如仙女,其實狠辣兼有點痞痞的,不僅毒舌,還會揍人,總是不按牌理出牌。男主的人設也有所創新,更接地氣,幽默有趣,同時有勇有謀。兩人在人生低谷相遇,一路上以打怪升級的方式相互扶持,在匡扶正義的鬥爭中惺惺相惜,共同成長。一場極度可愛的戀情也就此展開,溢滿強大清新甜寵力。
大唐盛世,武周末年,科舉興起,新貴迭出,風起雲湧中,
曾經輝煌百年的名門士族走到了命運的轉折關頭。
本是散打搏擊冠軍,獅子座的鋼鐵直女,
穿越成為了大唐京兆杜氏旁支的孤女杜清檀,
不僅天生病弱,家財還被亡父耗盡,奴僕四散,
只剩寡居的伯母楊氏及幼小的堂弟團團相依為命,勉強度日。
這般落魄潦倒,也難怪簪纓世胄的蘭陵蕭氏要嫌棄悔婚了。
但蕭家真是好算計,竟逼迫她接受兒媳變義女!
明明是背信棄義,還怕名聲不好聽,非得拉著孤兒寡婦當遮羞布?
別以為嬌弱病美人好欺負,面對蕭家那些見不得人的腌臢手段,
她不光要咬牙爭上一爭,讓始作俑者裴氏付出相對代價!
還要走出一條與普通世家女子截然不同的路,
食醫之術,能養活並庇護自己和家人,還能造福很多人啊!
她要讓自己活得有尊嚴,身邊的人活得有體面,
像真正的人,而不是豬狗、草芥一樣的存在。
作者簡介
意千重
資深網路原創小說人氣作家,閱文集團大神作者,言情小說口碑作家。最擅長用濃淡皆宜的筆觸描述出女子內心最柔軟溫暖的故事,人物塑造飽滿鮮活,情節富有張力。
出版作品:《澹春山》、《貯金閨》、《粉妝膳謀》。
目次
第一章 要這美貌何用?
第二章 窮與弱不是理由
第三章 僅剩一路可走了
第四章 以拳抵債如何?
第五章 專治窮病的藥膳
第六章 給梁王做妾算了
第七章 以項上人頭作保
第八章 出乎意料的效果
第九章 躺平就沒有希望
第十章 夢與仙,最合適
第十一章 沒有證據就出族
第十二章 從雲端直落地底
第十三章 我的命,我作主
第十四章 拼命的時刻到了
第十五章 女子未必不如男
書摘/試閱
第一章 要這美貌何用?
上元節剛過,長安城的暖風便迫不及待地吹綠了灞橋的柳枝,再吹薄了小娘子們的衣衫,卻怎麼也吹不暖杜清檀那顆冰冷絕望的心。
她面無表情地注視著銅鏡裡的自己,冷白皮,細長眉,鳳目媚,唇瓣粉,天鵝頸,身形纖長。
柔弱無辜,我見猶憐,確實是她從未有過的美貌。
杜清檀裝模作樣地捏了個蘭花指,卻被自己這舉動嚇得一個激靈,暴躁地將銅鏡摁翻,長長嘆了口氣。
真是有夠倒楣,穿成窮逼病弱孤女一個,走一步喘三氣,風都能吹倒,要這美貌何用?和她一點不匹配,散打搏擊冠軍,獅子座鋼鐵直女,在這裡根本毫無用武之地!
「五娘,蕭家來人了,帶來好多禮品,大娘子讓您趕緊梳洗了去見客,您就要苦盡甘來了!」婢女采藍推門而入,歡喜中帶了幾分抱怨,「主君過世後他家再沒露過臉,這都兩年多了,總算想起來還有這麼一門親事。前幾天大娘子還念叨著,幸好來了。唉,無論如何,總是好事。」
杜清檀懶洋洋地趴在几案上,沒有半點興趣,「就算來了也未必是好事。」
這是她那位枉死的便宜老爹早年給定的親──蘭陵蕭氏,歷經幾朝的百年門閥,祖上出過皇帝和皇后,與當時尚且興旺的杜家算是門當戶對。但自從她爹捲入朝政紛爭枉死後,家財散盡,奴僕四散,只剩下她和寡居的伯母楊氏及幼小的堂弟團團相依為命,勉強度日。
蕭家不聞不問,四時八節也未按著規矩走禮,顯然是後悔了的。
聽聞她那位傳說中的未婚夫蕭七郎才貌雙全,科舉順遂,前途無量。
這樣的人,怎麼肯屈就這樁賠本的婚事!
「那倒是。」采藍神色瞬間黯淡下來,默默翻出一件五成新的月白色短襦,再配一條半舊的天水碧羅裙,在杜清檀身上比劃又比劃,無奈一嘆,「這都舊了,短了,而且連件像樣的首飾都沒有,按說您該好好裝扮一番才是,都兩年多沒露面了呢!」
堂堂京兆杜氏貴女,窮困如斯,竟然連件體面的衣裳都穿不起了,實在讓人心酸。
「倒也不必在意這些虛的。」
杜清檀自來不看重衣服首飾這些外在之物,能穿就行了,何況對方又不是什麼要緊人物。
「怎會是虛的呢?體面總是要的。」采藍挑剔地看著她的前胸,「您實在太瘦,這都沒胸了!必須打扮好看些,他家見著您這麼美,一定捨不得。不成,得弄一弄才行!」
片刻後,采藍手裡抓了兩團發黃的舊絲綿,妄想塞進杜清檀的前胸衣襟,「把這個塞進去就好了!」
「又皮癢了?」杜清檀耐心殆盡,威脅地抓起雞毛撢子,但她天生弱不勝衣,擺出這麼一副凶悍模樣也不過像是小奶貓哈氣伸爪子罷了。
「哎呀,生什麼氣嘛!婢子都是為了您著想,脾氣真是越來越壞了。」采藍一點不怕她,「就算不塞這個,也該搭塊披帛擋一擋……」
「滾!」杜清檀舉起雞毛撢子,沒胸礙著誰啦?
她又不奶孩子,況且這能怪她嗎?
沒變成嬌弱美人之前,她的胸堅挺漂亮,恰到好處,不知被多少人羡慕!
唉!想起自由滋潤強壯的從前,杜清檀暴躁到生無可戀。
采藍敷衍地道:「是婢子錯了,咱們快走吧!」
破落戶的宅子小得很,後院到前院就幾步路。
杜清檀走進正堂,就見地上放了一堆禮盒,一群衣著光鮮的僕婦、婢女圍著兩個裝扮華貴的婦人,再一旁的主位上坐著她的伯母楊氏。
「五娘,快來拜見蕭夫人。」楊氏神色凝重,語氣低沉。
她本以為蕭家是來談婚期的,畢竟杜清檀守孝期滿,年齡也不小了。
誰知她反復提了幾次都被對方擋了回去,思及這幾年蕭家的表現,只怕婚事已經生了變故。
「見過夫人。」杜清檀屈了屈膝。
蕭家長媳裴氏出身河東名門,生得圓臉富態,高髻金梳碧玉釵,寶藍燙金花羅衫配著大紅八幅裙,腳下一雙精緻的絲質高履,盡顯富貴。
「聽說妳一直病著,看這樣子是還沒好,氣色太差了!」
裴氏嫌棄地打量著杜清檀,衣裙半舊,袖口和裙腳都短了,頗不合身,頭上也只有一支寒酸的木簪子。
個頭倒是高,臉也生得極美麗,舉止穩重。就是胸部太平,屁股太小,整個人瘦弱蒼白,不折不扣的紙糊美人,別說操持家業主持中饋,怕是傳宗接代都做不了。
再看看杜家這窮愁沒落的樣子,確實是配不上她的兒子七郎了。
任誰也不喜歡見面就被人說是氣色差,何況是這樣倨傲的姿態和語氣。
杜清檀面無表情,語氣也不好,「勞您費心,我還好。」
「人吃百樣米,樣貌各不同,我們杜家女兒都是天生的婀娜。」楊氏趕緊做了補充。
無論如何都不能落下「重病纏身」之說,否則對孩子的前途大為不利。
裴氏早就下定了退婚的決心,懶得糾纏這些細枝末節,自顧自地道:「我今日來,是有件喜事與妳們商量。前些日子,我家老夫人得了個奇怪的夢。夢裡佛祖說,有個小娘子與她有前世定下的祖孫緣分,需得趕緊了結,不然業障纏身,不得安寧。追問人在哪裡,佛祖說是姓杜的,名字裡有個檀字,與佛有緣。醒來時言猶在耳,室內猶有異香未散,我家老夫人實在不敢不信,叫了家裡人一合計,想起來五娘不就是姓杜,名字裡又有個檀字!為慎重起見,老夫人特意去了大慈恩寺請教玄空大師。大師確認就是五娘,讓趕緊收了做孫女兒消災解厄。所以啊,七郎和五娘的親事怕是不能成了。」
杜清檀聽笑了,不就是想悔婚嘛!
這個理由足夠清奇,真是費心了,想必一家子人琢磨了很久吧?
因見楊氏憤怒欲言,便握住她的手,表示聽完再說。
裴氏接著道:「我們再一琢磨,想起五娘從小三災八難的,她娘生她難產死了,伯父沒了,她爹又莫名其妙犯了事。你們家這日子越過越差,她自己也是重病纏身的,確實是很不好啊!」
只差沒直說杜清檀剋父剋母剋全家,還剋自己了。
「欺人太甚!」楊氏再也忍不住,怒聲道:「悔婚就悔婚,直說自家嫌貧愛富,要另攀高枝得了,拿神佛說什麼事!自己背信棄義,還要踐踏我們五娘,天下哪有這般道理!」
裴氏惱羞成怒,高聲道:「妳這人怎麼這樣!我說的哪句有假?我這不是為了孩子著想嘛!我還要收她做義女呢,怎麼踐踏她了?」
「我呸!真為孩子著想,為何這些年從未上門看過問過?」
楊氏可不是個好欺負糊弄的,當即吵了起來。
「做什麼義女!兒媳變義女,府上真是好算計!背信棄義要悔婚,還怕名聲不好聽,非得拉著我們孤兒寡婦給你們當遮羞布?真敢想!蕭家列祖列宗的臉面都給你們丟乾淨了,臭不要臉!」
「妳個粗魯沒見識的村婦,好心當成驢肝肺!」
裴氏在家主持中饋,說一不二,並不是容得人的性子。
二人互不相讓,更不肯聽勸,吵得只差沒把房頂給掀了。
杜清檀只覺耳邊恍若有上千隻鴨子在叫,鬧得人控制不住的暴躁,索性一把推翻了矮几。
砰地一聲巨響,裴氏和楊氏嚇了一跳,同時住口回頭查看是怎麼回事?
只見杜清檀坐在那裡撫著胸口,細眉微擰,臉色蒼白,氣息不穩,搖搖欲墜,倒像是嚇得比她們還要厲害些。
裴氏也沒想到她是故意而為,因覺剛才罵不過癮,還要回過頭去繼續吵,就聽杜清檀細聲細氣道:「有事說事,別瞎扯,不然滾出去!」
「是妳推的桌子?」裴氏大吃一驚,認真看向杜清檀。
真沒想到,這麼個安靜嬌弱的紙美人,脾氣竟然這般大!
杜清檀懶得多說,懨懨地道:「送客。」
在她看來,有事就解決,吵架完全是浪費口舌和時間。
真要洩憤的話,直接上手就好,皮疼肉痛了才能觸及靈魂,才能讓對方記住教訓。
若不是她體虛無力揍不了人,哪能忍到現在,早出手了。
楊氏一個眼色,采藍立刻拿著笤帚進來,對著裴氏等人腳下一陣亂掃,惹得蕭家人一陣雞飛狗跳。
裴氏從沒這麼丟臉過,氣得發抖,板著臉厲聲道:「走!」
與她同來的那位年輕婦人連忙摁住采藍的笤帚,涎著臉笑,「都消消氣,且聽我一言。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婚事是一定不成的了。為了孩子們著想,還得漂漂亮亮收個尾才是。不然這麼下去,小姑娘拖成老姑娘,可就不好了!」
煩死了,廢話一堆!杜清檀撩起薄薄的眼皮,「妳誰啊?」
她真心實意懟人,可惜聲音細軟無力,再配著這副柔弱的可憐樣,半點氣勢全無。
年輕婦人自是不會與這麼一個柔弱可憐人計較,笑咪咪道:「我是七郎的四嬸,娘家姓崔,咱們以前見過的,那會兒妳才齊我的胸高呢!這樣吵下去不會有結果的,聽我勸一勸,如何?」
杜清檀挑釁不成,只好強行壓下暴躁,持續面無表情。
楊氏母雞似地將她護在身後,警告崔氏,「快說!」
崔氏語重心長地道:「七郎和五娘都是好孩子,被這樁沒緣分的婚事耽擱了多不值啊!我們真心想收五娘做義女,見面禮都帶來了,趁著天色還早,索性把禮行了,改日請了左鄰右舍和族裡吃吃喝喝說說,就掰扯清楚了。事出有因,傳出去也不怕別人亂嚼舌頭,不影響五娘另行婚配,如何?」
繞來繞去,就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非得逼著孤兒寡婦忍氣吞聲替他家遮羞,以保全他家的好名聲。
「不如何!退婚就退婚,現在就算你們求著我們也看不上了!約好日子,兩邊都去請了族裡,當面鑼,對面鼓地掰扯清楚!」楊氏噁心得不行,「別再給老娘扯什麼神啊佛啊義女的,當今天下姓武不姓蕭!聖上夢見神佛示喻那是應當的,你們算什麼東西!還以為是前朝那時候呢?」
這話夠誅心的,且近來朝中謀反株連案件頻發,別說崔氏,便是傲慢驕橫如裴氏,也是當即變了臉色。
「走!與這種粗鄙無禮的村婦扯不清楚。且等著,有你們求我的時候!」
裴氏討不了好,只得用力一甩袖子,仇恨地瞪了楊氏和杜清檀一眼,走了。
「唉,這可真是……好說好散不行嗎?非得鬧得這樣難看,到底吃虧的是你們。」
崔氏假惺惺地嘆了口氣,見杜家人並沒有後悔的意思,只好示意奴僕拿起地上的禮品跟著離開。
裴氏登上馬車,陰惻惻地看著杜家低矮簡陋的門頭,冷笑連連,「不識抬舉的破落戶,福薄短命的小賤人!」
崔氏在她身旁坐下來,擔憂地道:「大嫂,這窮酸油鹽不進的怎麼好?若是鬧到兩邊族裡,掰扯起來就很難看,對七郎的名聲更是影響不小,萬一傳回我娘家那邊就不好了。」
蕭家悔婚,自是因為有了更好的婚配對象。
當世最講門第出身,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五姓七望,是為頭等的高門大戶,世人皆以娶五姓女為榮。
此種高貴榮耀,便是尚公主也比不上。
而清河崔氏近來接連出了好幾任宰相,可謂風光無比、權柄在握,倘若蕭七郎能夠與之結親,前途必然順遂無比。
這樣的婚姻有多難得自不用說,所以這欺負孤兒寡婦、背信棄義悔婚的名聲定然不能傳出去。
裴氏陰沉著臉慢慢轉了會兒腕間的金鑲玉鐲,眼裡露出凶光,「敬酒不吃吃罰酒,這樣的不知趣,為了我兒的前程,少不得要動些非常手段了。我記得楊氏的兒子在宣陽坊讀書……叫屠二過來。」
送走惡客,屋子裡瞬間清淨下來。
杜清檀長長地舒了口氣,閉上眼睛躺下,示意采藍給她揉揉太陽穴。
躺了會兒,突然覺得氣氛不大對,睜眼一看,只見楊氏怔怔地看著她,眼淚流得滿臉都是。
「別哭了,不值得。」杜清檀向來不怎麼會安慰人,只覺得自己詞彙貧乏,索性掏出手絹遞過去,「我又不在意。」
誰想楊氏接過她的帕子一看,哭得更厲害了,「這手絹都快破洞了妳還在用,都怪我沒本事,守不住家業,害得妳吃苦受罪,被人欺辱……」
杜清檀很無語,眼看楊氏哭得越發厲害,索性伸出手臂摟住她的肩頭,「算起來也是我一直生病吃藥,把家裡吃垮了。還有,大伯母是不是也如同裴氏所言那般,認為我剋父剋母呢?」
「胡說八道!妳娘又不是因為妳死的,我不也生過病吃過藥?」楊氏立刻收了眼淚,憤怒地道:「那就不是個東西!按照她的說法,我還剋夫呢!」
杜清檀喜歡楊氏的爽利性子,更感激她這樣照顧自己,便輕輕一笑,「既然知道她不是個東西,還哭什麼?」
「我就是太生氣了啊!」
生氣、屈辱,卻無力無處發洩,不是就只有哭鼻子了嘛!
杜清檀哄孩子似地拍拍她的肩頭,「哭好了就來商量該怎麼辦才好?」
活了幾十歲,還不如孩子冷靜懂事。
楊氏不好意思地接過采藍遞來的帕子擦了臉,「這事還得族裡出面解決,我這就去杜陵。稍後團團也要下學了,妳在家等著他。」
京兆杜氏自西漢起便名臣輩出,鼎鼎有名的凌煙閣開國二十四功臣之一杜如晦正是本家代表人物,只可惜後續無人,如今族中多是寂寂無名之輩。
而杜清檀家又是旁支,上兩輩便搬出了杜家世居的杜陵,只有逢年過節或是婚喪嫁娶等大事才會回去,日常與族裡聯繫並不緊密。
也正是這個原因,裴氏才敢如此囂張霸道地欺上門來。
但無論如何,只要族裡肯出面,總能讓蕭家不好過。
杜清檀卻覺得族裡不會管太多,畢竟自己這支的成年男丁已經死絕,餘下一個團團尚且年幼不知前途如何,誰會願意為了他們去得罪蕭家呢?
楊氏這一去少不得也要低三下四求人,不如另想他法。
楊氏嘆道:「不是我不通人情世故,只是這事無論如何都要告知族裡,不說就不對,況且這也是最便捷簡單的法子。行了,妳先去歇會兒,別回頭又生了病。」
事不宜遲,趁著天色還早,楊氏帶上粗使婆子于婆,雇了輛驢車火速往曲江池南邊的杜陵去了。
杜清檀回房躺了會兒,瞅著時辰差不多就起了身,走到前頭叮囑男僕老于頭,「時辰差不多了,你去接團團,路上小心些,別耽擱,別與人鬧紛爭。」
團團已經七歲,兩年前由楊氏給他開了蒙,家裡請不起先生,便在宣陽坊一個杜氏宗親家裡附了學。
宣陽坊和他們住的永寧坊隔了一個坊區,雖說不算遠,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況且之前她看裴氏眼神陰沉狠戾,總覺得這種人跋扈慣了,也不講什麼道義,做事必然不擇手段,自家怎麼小心都不為過。
「五娘放心,老僕無論如何都會護得小郎周全。」
老于頭與于婆是一家,老倆口無兒無女,待杜清檀和團團就和自家小輩一樣疼愛。
杜清檀自是放心的,等老于頭出了門,便去廚房看采藍做飯。
其實不過是些粗糧蔬菜罷了,並沒有肉食之類的。
當然,想吃也沒得吃,不止是窮,還因為女皇篤信佛教,下令禁屠宰。
有權勢的人家可以冒著風險偷偷弄了肉食解饞,他們這樣的小可憐就算了,又不是嫌命長。
所以杜清檀看著那黃燦燦的小米,以及滿眼的青綠素菜,心裡淒風陣陣,覺得人生又慘澹了幾分。
她想吃大白米飯,想吃油汪汪的紅燒肉,想吃香噴噴的烤雞啊!
就算沒有,好歹也給她一個白麵餅子加顆蛋之類的,這才是病號需要的啊!
采藍被她絕望悲涼的目光看得受不了,索性趕她走,「快去歇著,小郎回來就叫您。」
杜清檀出了廚房,便去大門口站著往外張望。
團團這孩子年紀雖小,卻長得玉雪可愛,聰慧乖巧,她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小堂弟了,半天沒見,怪想的。
日影一點點的斜下去,始終不見老于頭和團團回來,杜清檀慌了起來,難道蕭家真對這孩子出手了?
不成,得去瞅瞅。
采藍也擦著手走了出來,「飯好了,怎麼還沒回來?」
「我們去接他們。」杜清檀見采藍想拒絕,便將眼睛一瞪,「不許多話!」
「知道了。」采藍無奈地取了帷帽給她戴上,攙著她往前走。
杜清檀走得很慢,走一段路就要停下來歇一歇。
采藍也沒有嫌煩的意思,反而誇她,「您這身子骨真是比從前好多了,之前哪裡敢上街啊!」
杜清檀沒吱聲,只管睜大眼睛在過往行人裡尋找老于頭和團團,然而一直走到宣陽坊,還是沒見著人。
采藍奇怪道:「難道錯過了?要不就是還沒放學?」
杜清檀緊抿著唇,儘量加快速度趕到杜氏宗親家中。
門房見到她們很驚奇,「今日先生有事,提前放了學,小郎早在半個多時辰前就走了。府上的老于頭也才來過,還沒回家去嗎?」
杜清檀皺起眉頭,「沒見著,不知他是否與同學同行?」
門房笑道:「因放學早,其他學生約了去東市閒逛,小郎說要回家背書,是自己走的。」
團團懂事,知道家裡沒錢,所以遇到這種要花錢的事都會避開。
杜清檀發愁地看向街道,這麼大個長安城,團團和老于頭究竟去哪裡了呢?
雖然難,卻也不能什麼都不做。
主僕二人沿著團團往日上下學的線路依次尋找過去,逢人就問,卻也沒能問出個名堂來。
「五娘,那是小郎的書包!」采藍激動地指向前方。
那是一個穿灰色粗布圓領缺胯袍的年輕男人,抱著一把橫刀,漫不經心地斜靠在坊牆上,看起來像個遊俠。
他身後跟著一匹老得斑禿了的灰驢,正在專心地啃食牆縫裡的野草。
灰驢的脖子上,掛著團團的書包。
杜清檀這會兒已經累得不行,歪著帷帽,撫著胸口,說一句喘一下,「這位俠士……請問您這個書包……是從哪裡來的?」
男人身量極高,半垂眸子,居高臨下斜瞅著她,濃密捲翹的睫毛裡透出的目光又清又冷,「五十文!」
杜清檀和采藍愣了片刻才明白,他是要她們給錢才肯說。
采藍先不滿了,潑辣地道:「五十文都夠買三斗米了,你怎麼不去搶?」
年輕男人完全無視她,只看著杜清檀淡淡地道:「妳應當曉得,重要的消息是用錢換不來的。」
杜清檀立刻明白了,「那是自然,給你五十文!」
年輕男人嘴角輕輕一勾,露出一個淺淺的笑容,潔白修長的手掌往她面前一伸,「給錢。」
杜清檀身上是沒錢的,當即給了采藍一個眼神。
采藍心不甘情不願,肉疼得直哆嗦地解下腰間的錢袋子,噘著厚厚的嘴唇小聲嘀咕,「長得人模人樣的,怎麼這樣!只有四十文,多的沒了,這還是我們家幾天的口糧錢呢!」
年輕男人也不計較,把錢往懷裡一塞,解了書包丟過去,指著前方道:「人在那間屋子裡,哄著那孩子去車裡看猴戲,然後就鬧騰起來,說是偷了東西。孩子鬧騰得厲害,書包也扔在街上,接著一個瘸腿老者找過來,和他們吵鬧一回,兩個人都被拉進那道門去了,說是要報官。」
「胡說!我們家小郎乖巧懂事,才不會偷東西呢!」采藍又氣又急,「五娘,這可怎麼辦?」
才和蕭家鬧過,就出了這樣的事,多半是裴氏設了圈套,要借此逼迫自己和楊氏就範。
杜清檀微一思忖便有了數,當即和采藍說道:「不急,一時半會兒不會有性命之憂。我在這裡守著,你去請武侯過來。」
長安城共計一百一十坊,各坊均設置武侯鋪管理治安,武侯便是緝盜安良的公差,這種事正該歸他們管。
「只要不是殺人放火之類的大事,要請武侯就得給錢,婢子沒錢了。」
采藍目光炯炯地盯著一旁的年輕男人,希望這人能夠良心發現,把錢還回來。
然而年輕男人坦然大方地由著她看,絲毫沒有羞愧之意,更沒有願意還錢的意思,只提醒她們,「一共兩個彪形大漢,手臂有我兩隻那麼粗,能輕輕就能把妳們脖子捏斷的那種。妳們是得罪什麼人了吧?請武侯過來未必有用,只怕還會適得其反。」
采藍立時嚇哭了,「五娘,怎麼辦啊?一定是蕭家幹的!」
杜清檀嚴肅地打量面前的男人,雖然穿著粗布衣裳破靴子,然而膚白貌美,眼眸深邃,睫毛捲長,身形勻稱健美,氣質儀態俱佳,手上也沒什麼繭子,顯然不是貧苦出身。
這樣的人總不會平白無故守在這裡管閒事,雖不知對方的目的是什麼,但此刻光憑她和采藍是沒辦法處理好這件事的,不如找個幫手。
「這位俠士。」杜清檀掂量著開了口,「您見義勇為給我們傳信,真是幫了我們的大忙。能不能請您好人做到底,再幫我們把孩子救出來?」
「見義勇為,好人做到底?」年輕男人一笑,很是文雅地道:「妳看錯了,我不是什麼俠士,也不是好人。我之所以留在這裡,是因為沒錢吃飯,所以想弄點錢住店。」
杜清檀一時不知道該怎麼接話,「所以?」
「所以小娘子若要請我幫忙,得給錢。」
男人頗有耐心,畢竟杜清檀這副氣喘吁吁,蹙眉撫胸的嬌弱模樣實在讓人心軟,彷彿是一顆晶瑩剔透的露珠,隨時會被陽光曬化了似的。
「再給你五十文。」杜清檀記得家裡似乎還有點錢,只是不多。
「五十文!?」男人喊出聲來,因為太過震驚,瞳孔縮了又放。
「我暫時只有這麼多,可以打欠條,您要多少?」杜清檀有些抱歉,說到底是打打殺殺的買賣,五十文確實太少了,萬一受傷什麼的,還不夠醫藥費。
「欠條?」男人盯著她看了片刻,勾起嘴角笑了起來,頗不像個正經人,「小娘子覺得我值多少錢呢?」
采藍警惕地把杜清檀護在身後,這人看起來太不正經了,就像是想要利用美貌勾引自家五娘似的。
看他那五官似是有胡人血統,這種樣貌最勾人了,自家五娘日常不怎麼出門,對男人沒啥見識,很可能會被蒙蔽。
然而杜清檀並不能體會采藍的苦心,反而嫌她擋了視線,「閃邊,別擋著。」
采藍很鬱悶地往旁一站,看杜清檀和男人討價還價。
「一千文,不能再多了。」
「兩千文,不能再少了。」
「一千五百文,我家太窮了,不然也不會穿舊衣,打補丁。」杜清檀拉起采藍的裙腳,給他看上面的補丁賣慘,「我們平時只能勉強吃飽,生病了都看不起大夫吃不起藥,不然我也不會這麼虛弱。」
男人皺著眉頭嘆了口氣,「行吧,確實挺可憐的。」
杜清檀猛點頭,以為對方已經同意了她給的價,不想男人跟著就道:「一千八百文,再講價就算了。」
采藍很不高興,覺得一個大男人鑽到錢眼裡去,和女人這麼斤斤計較的,簡直不像話。
杜清檀倒是沒啥想法,「前頭鋪子裡尋了筆墨給您寫欠條?敢問尊姓大名?」
「獨孤不求。」男人邁開長腿朝著鋪子走去,脊背挺得直直的,然而每走一步,破了的靴子總會發出一聲「啪嘰」的怪響。
見主人走了,老禿驢也不吃草了,慢悠悠地跟上去,一瘸一瘸的,走不得幾步,幾根毛隨著風飄落下來,身上又禿了一塊。
反正就很落魄的樣子。
「死要錢會不會是洛陽獨孤氏啊?」采藍和杜清檀咬耳朵,八卦獨孤不求的出身來歷,「獨孤家祖上是胡人來著,我看很像!」
洛陽獨孤氏也是百年門閥,族中尚武,出了不少名將。前朝時還出過好幾位皇后,到了本朝,家主曾被封為郡王,族中子弟又尚公主,是有名的貴戚。只是近年來也和杜家一樣,沒啥出色的人才,沒落了。
杜清檀聽采藍這麼一分析,也覺得像,她便很直白地問了,「獨孤公子,您家是洛陽獨孤氏嗎?」
獨孤不求正在吹乾欠條上的墨跡,聞言懶洋洋地瞥了她一眼,「是啊,妳找獨孤家有事?」
這話挺不客氣的,包著火氣。
杜清檀猜想他或許是和族裡有怨,被趕出來什麼的,不然不會混得這麼慘,好脾氣地笑笑,「這不是互通家門嗎?我們是京兆杜氏旁支。」
獨孤不求沒什麼反應,將欠條往懷裡一塞,大步流星往前走,整個人都透著不高興。
杜清檀跟著小跑了一段路,累得肺都要炸了,就連頭上的帷帽都像是負擔,索性扯掉帷帽,揪著采藍的胳膊喘個不停。
采藍便道:「獨孤公子,還請您慢些,我家五娘身子虛弱跟不上。」
獨孤不求不耐煩地回頭看杜清檀一眼,「嘖」了一聲,拉過老禿驢,「坐上去!」
杜清檀看看那頭可憐的老禿驢,很不忍心,「還是算了,就幾步路工夫,很快就到了。」
獨孤不求抬眼看看天色,「很快就要敲暮鼓了。」
長安城規矩多,晨鐘起,暮鼓歇,暮鼓響完,坊門關閉,各人歇市歸家,是不許在外頭逗留閒逛的,否則犯了夜禁,被打死也有可能。
被嫌棄了,弱者是沒有人權的,杜清檀默默地在采藍的幫助下上了驢背,跟在獨孤不求身後。
獨孤不求埋著頭走了一會兒,心情似有好轉,「等會兒妳的婢子去敲門,妳跟著上前問清楚他們的目的,反正各種找事就對了。我在一旁看著,瞅住機會先去救人。這老驢我留在門外,完事妳就騎著牠回去。」
這和杜清檀的想法差不多,只不知道這人的本領如何,拎刀的樣子倒像是很在行。
於是她很委婉地道:「對方人多勢眾,公子千萬要小心些,咱們是取巧,不是拼命。」
當然了,若是獨孤不求不行,她也還有預備方案。
獨孤不求瞥她一眼,輕哼道:「該小心的人是妳,風都能吹倒,也不知道多吃些飯。」
說起這個,杜清檀也很惆悵啊,幽幽地道:「這不是吃多吃少的問題,命運如斯,能奈其何!」
這真的是個命理問題,沒有辦法的那種。
獨孤不求又瞥了她一眼,突然勾著唇角笑了起來。
采藍不爽,「你幹嘛總是看我家五娘?你笑什麼?」
獨孤不求笑得更燦爛了,「人生來不就是給別人看的嗎?妳家五娘又不是醜八怪怕人看,我看看怎麼了?我天生愛笑關妳何事?」
采藍完全不能回嘴,氣得噘起厚厚的嘴唇,恨恨地瞪過去。
獨孤不求並不理她,看著前方說道:「那人就是領頭的。」
一個粗壯的灰衣漢子從馬上下來,陰沉著臉敲響了門。
裡頭有人大聲問道:「誰啊?」
灰衣漢子不耐煩地道:「我,屠二。」
門應聲而開,一個塌鼻子男人探出頭來四處張望,「找著人了嗎?」
屠二不高興地道:「杜家沒人在,不知死哪裡去了?」
卻聽塌鼻子男人喊了一聲,「那不是嗎?」
屠二回過頭來,正好和杜清檀等人碰了個面對面。
雙方一時都有些措手不及和呆住,就那麼傻傻地看著對方不說話,場面頗為詭異。
杜清檀先回過神來便要下驢,奈何采藍手忙腳亂扶不穩,險些把她摔個大馬趴。
還是獨孤不求實在看不下去,伸手搭了一把。
「我家團團和老僕是被你們綁了?」
杜清檀話音未落,便被一陣冷風吹得忍不住咳了起來。
雪白的臉上浮起幾縷病態的紅暈,如同一朵在風雨中搖擺的玉白染紅的芍藥花,柔弱嬌妍得讓人忍不住心疼。
屠二眼裡淫光大盛,叉著腰帶,頂著肥肚走過來,色咪咪地盯著她,「是杜家的五娘吧?妳那堂弟盜竊我家的寶貝,按律該送官處置,妳說要怎麼辦吧?」
杜清檀好不容易停止咳嗽,細聲細氣地道:「孩子還小,不懂事,裡頭怕是有誤會,不如把他帶出來,我們當面問問?」
她想得很美,進了人家屋子就好比入了牢籠,給人甕中捉鱉,把人帶出來就好了,要跑要逃都能方便許多。
然而人家卻也不是傻子,屠二笑道:「那孩子精得跟猴兒似的,萬一帶出來跑了怎麼辦?還是妳們進來談吧!」
說話間,又淫邪地往杜清檀臉上身上看了一遍。
采藍氣到不行,衝到前面護住杜清檀大聲道:「你們這些壞人,誰曉得是不是要把我們哄進去做什麼壞事?」
「壞事?我們能對妳們做什麼壞事呢?快說說!」
屠二激動的使勁拍著大腿和同伴笑個不停,就想佔點言語上的便宜。
畢竟出身這麼好,又長得這麼美,還可以任由他們調戲的小娘子可不多。
采藍彪悍地破口大罵,「豬狗不如的腌臢東西,你們長腦袋只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高點嗎?你們就像一堆狗屎,又臭又爛,令人作嘔。你們連最基本的人性都沒有,別再出來丟人現眼了!」
杜清檀目瞪口呆,她從來不知道罵人竟然可以有這麼多花樣,更不知道采藍這麼個小姑娘居然可以罵人不重樣!
不過,要的就是這麼個效果。
上元節剛過,長安城的暖風便迫不及待地吹綠了灞橋的柳枝,再吹薄了小娘子們的衣衫,卻怎麼也吹不暖杜清檀那顆冰冷絕望的心。
她面無表情地注視著銅鏡裡的自己,冷白皮,細長眉,鳳目媚,唇瓣粉,天鵝頸,身形纖長。
柔弱無辜,我見猶憐,確實是她從未有過的美貌。
杜清檀裝模作樣地捏了個蘭花指,卻被自己這舉動嚇得一個激靈,暴躁地將銅鏡摁翻,長長嘆了口氣。
真是有夠倒楣,穿成窮逼病弱孤女一個,走一步喘三氣,風都能吹倒,要這美貌何用?和她一點不匹配,散打搏擊冠軍,獅子座鋼鐵直女,在這裡根本毫無用武之地!
「五娘,蕭家來人了,帶來好多禮品,大娘子讓您趕緊梳洗了去見客,您就要苦盡甘來了!」婢女采藍推門而入,歡喜中帶了幾分抱怨,「主君過世後他家再沒露過臉,這都兩年多了,總算想起來還有這麼一門親事。前幾天大娘子還念叨著,幸好來了。唉,無論如何,總是好事。」
杜清檀懶洋洋地趴在几案上,沒有半點興趣,「就算來了也未必是好事。」
這是她那位枉死的便宜老爹早年給定的親──蘭陵蕭氏,歷經幾朝的百年門閥,祖上出過皇帝和皇后,與當時尚且興旺的杜家算是門當戶對。但自從她爹捲入朝政紛爭枉死後,家財散盡,奴僕四散,只剩下她和寡居的伯母楊氏及幼小的堂弟團團相依為命,勉強度日。
蕭家不聞不問,四時八節也未按著規矩走禮,顯然是後悔了的。
聽聞她那位傳說中的未婚夫蕭七郎才貌雙全,科舉順遂,前途無量。
這樣的人,怎麼肯屈就這樁賠本的婚事!
「那倒是。」采藍神色瞬間黯淡下來,默默翻出一件五成新的月白色短襦,再配一條半舊的天水碧羅裙,在杜清檀身上比劃又比劃,無奈一嘆,「這都舊了,短了,而且連件像樣的首飾都沒有,按說您該好好裝扮一番才是,都兩年多沒露面了呢!」
堂堂京兆杜氏貴女,窮困如斯,竟然連件體面的衣裳都穿不起了,實在讓人心酸。
「倒也不必在意這些虛的。」
杜清檀自來不看重衣服首飾這些外在之物,能穿就行了,何況對方又不是什麼要緊人物。
「怎會是虛的呢?體面總是要的。」采藍挑剔地看著她的前胸,「您實在太瘦,這都沒胸了!必須打扮好看些,他家見著您這麼美,一定捨不得。不成,得弄一弄才行!」
片刻後,采藍手裡抓了兩團發黃的舊絲綿,妄想塞進杜清檀的前胸衣襟,「把這個塞進去就好了!」
「又皮癢了?」杜清檀耐心殆盡,威脅地抓起雞毛撢子,但她天生弱不勝衣,擺出這麼一副凶悍模樣也不過像是小奶貓哈氣伸爪子罷了。
「哎呀,生什麼氣嘛!婢子都是為了您著想,脾氣真是越來越壞了。」采藍一點不怕她,「就算不塞這個,也該搭塊披帛擋一擋……」
「滾!」杜清檀舉起雞毛撢子,沒胸礙著誰啦?
她又不奶孩子,況且這能怪她嗎?
沒變成嬌弱美人之前,她的胸堅挺漂亮,恰到好處,不知被多少人羡慕!
唉!想起自由滋潤強壯的從前,杜清檀暴躁到生無可戀。
采藍敷衍地道:「是婢子錯了,咱們快走吧!」
破落戶的宅子小得很,後院到前院就幾步路。
杜清檀走進正堂,就見地上放了一堆禮盒,一群衣著光鮮的僕婦、婢女圍著兩個裝扮華貴的婦人,再一旁的主位上坐著她的伯母楊氏。
「五娘,快來拜見蕭夫人。」楊氏神色凝重,語氣低沉。
她本以為蕭家是來談婚期的,畢竟杜清檀守孝期滿,年齡也不小了。
誰知她反復提了幾次都被對方擋了回去,思及這幾年蕭家的表現,只怕婚事已經生了變故。
「見過夫人。」杜清檀屈了屈膝。
蕭家長媳裴氏出身河東名門,生得圓臉富態,高髻金梳碧玉釵,寶藍燙金花羅衫配著大紅八幅裙,腳下一雙精緻的絲質高履,盡顯富貴。
「聽說妳一直病著,看這樣子是還沒好,氣色太差了!」
裴氏嫌棄地打量著杜清檀,衣裙半舊,袖口和裙腳都短了,頗不合身,頭上也只有一支寒酸的木簪子。
個頭倒是高,臉也生得極美麗,舉止穩重。就是胸部太平,屁股太小,整個人瘦弱蒼白,不折不扣的紙糊美人,別說操持家業主持中饋,怕是傳宗接代都做不了。
再看看杜家這窮愁沒落的樣子,確實是配不上她的兒子七郎了。
任誰也不喜歡見面就被人說是氣色差,何況是這樣倨傲的姿態和語氣。
杜清檀面無表情,語氣也不好,「勞您費心,我還好。」
「人吃百樣米,樣貌各不同,我們杜家女兒都是天生的婀娜。」楊氏趕緊做了補充。
無論如何都不能落下「重病纏身」之說,否則對孩子的前途大為不利。
裴氏早就下定了退婚的決心,懶得糾纏這些細枝末節,自顧自地道:「我今日來,是有件喜事與妳們商量。前些日子,我家老夫人得了個奇怪的夢。夢裡佛祖說,有個小娘子與她有前世定下的祖孫緣分,需得趕緊了結,不然業障纏身,不得安寧。追問人在哪裡,佛祖說是姓杜的,名字裡有個檀字,與佛有緣。醒來時言猶在耳,室內猶有異香未散,我家老夫人實在不敢不信,叫了家裡人一合計,想起來五娘不就是姓杜,名字裡又有個檀字!為慎重起見,老夫人特意去了大慈恩寺請教玄空大師。大師確認就是五娘,讓趕緊收了做孫女兒消災解厄。所以啊,七郎和五娘的親事怕是不能成了。」
杜清檀聽笑了,不就是想悔婚嘛!
這個理由足夠清奇,真是費心了,想必一家子人琢磨了很久吧?
因見楊氏憤怒欲言,便握住她的手,表示聽完再說。
裴氏接著道:「我們再一琢磨,想起五娘從小三災八難的,她娘生她難產死了,伯父沒了,她爹又莫名其妙犯了事。你們家這日子越過越差,她自己也是重病纏身的,確實是很不好啊!」
只差沒直說杜清檀剋父剋母剋全家,還剋自己了。
「欺人太甚!」楊氏再也忍不住,怒聲道:「悔婚就悔婚,直說自家嫌貧愛富,要另攀高枝得了,拿神佛說什麼事!自己背信棄義,還要踐踏我們五娘,天下哪有這般道理!」
裴氏惱羞成怒,高聲道:「妳這人怎麼這樣!我說的哪句有假?我這不是為了孩子著想嘛!我還要收她做義女呢,怎麼踐踏她了?」
「我呸!真為孩子著想,為何這些年從未上門看過問過?」
楊氏可不是個好欺負糊弄的,當即吵了起來。
「做什麼義女!兒媳變義女,府上真是好算計!背信棄義要悔婚,還怕名聲不好聽,非得拉著我們孤兒寡婦給你們當遮羞布?真敢想!蕭家列祖列宗的臉面都給你們丟乾淨了,臭不要臉!」
「妳個粗魯沒見識的村婦,好心當成驢肝肺!」
裴氏在家主持中饋,說一不二,並不是容得人的性子。
二人互不相讓,更不肯聽勸,吵得只差沒把房頂給掀了。
杜清檀只覺耳邊恍若有上千隻鴨子在叫,鬧得人控制不住的暴躁,索性一把推翻了矮几。
砰地一聲巨響,裴氏和楊氏嚇了一跳,同時住口回頭查看是怎麼回事?
只見杜清檀坐在那裡撫著胸口,細眉微擰,臉色蒼白,氣息不穩,搖搖欲墜,倒像是嚇得比她們還要厲害些。
裴氏也沒想到她是故意而為,因覺剛才罵不過癮,還要回過頭去繼續吵,就聽杜清檀細聲細氣道:「有事說事,別瞎扯,不然滾出去!」
「是妳推的桌子?」裴氏大吃一驚,認真看向杜清檀。
真沒想到,這麼個安靜嬌弱的紙美人,脾氣竟然這般大!
杜清檀懶得多說,懨懨地道:「送客。」
在她看來,有事就解決,吵架完全是浪費口舌和時間。
真要洩憤的話,直接上手就好,皮疼肉痛了才能觸及靈魂,才能讓對方記住教訓。
若不是她體虛無力揍不了人,哪能忍到現在,早出手了。
楊氏一個眼色,采藍立刻拿著笤帚進來,對著裴氏等人腳下一陣亂掃,惹得蕭家人一陣雞飛狗跳。
裴氏從沒這麼丟臉過,氣得發抖,板著臉厲聲道:「走!」
與她同來的那位年輕婦人連忙摁住采藍的笤帚,涎著臉笑,「都消消氣,且聽我一言。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婚事是一定不成的了。為了孩子們著想,還得漂漂亮亮收個尾才是。不然這麼下去,小姑娘拖成老姑娘,可就不好了!」
煩死了,廢話一堆!杜清檀撩起薄薄的眼皮,「妳誰啊?」
她真心實意懟人,可惜聲音細軟無力,再配著這副柔弱的可憐樣,半點氣勢全無。
年輕婦人自是不會與這麼一個柔弱可憐人計較,笑咪咪道:「我是七郎的四嬸,娘家姓崔,咱們以前見過的,那會兒妳才齊我的胸高呢!這樣吵下去不會有結果的,聽我勸一勸,如何?」
杜清檀挑釁不成,只好強行壓下暴躁,持續面無表情。
楊氏母雞似地將她護在身後,警告崔氏,「快說!」
崔氏語重心長地道:「七郎和五娘都是好孩子,被這樁沒緣分的婚事耽擱了多不值啊!我們真心想收五娘做義女,見面禮都帶來了,趁著天色還早,索性把禮行了,改日請了左鄰右舍和族裡吃吃喝喝說說,就掰扯清楚了。事出有因,傳出去也不怕別人亂嚼舌頭,不影響五娘另行婚配,如何?」
繞來繞去,就是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非得逼著孤兒寡婦忍氣吞聲替他家遮羞,以保全他家的好名聲。
「不如何!退婚就退婚,現在就算你們求著我們也看不上了!約好日子,兩邊都去請了族裡,當面鑼,對面鼓地掰扯清楚!」楊氏噁心得不行,「別再給老娘扯什麼神啊佛啊義女的,當今天下姓武不姓蕭!聖上夢見神佛示喻那是應當的,你們算什麼東西!還以為是前朝那時候呢?」
這話夠誅心的,且近來朝中謀反株連案件頻發,別說崔氏,便是傲慢驕橫如裴氏,也是當即變了臉色。
「走!與這種粗鄙無禮的村婦扯不清楚。且等著,有你們求我的時候!」
裴氏討不了好,只得用力一甩袖子,仇恨地瞪了楊氏和杜清檀一眼,走了。
「唉,這可真是……好說好散不行嗎?非得鬧得這樣難看,到底吃虧的是你們。」
崔氏假惺惺地嘆了口氣,見杜家人並沒有後悔的意思,只好示意奴僕拿起地上的禮品跟著離開。
裴氏登上馬車,陰惻惻地看著杜家低矮簡陋的門頭,冷笑連連,「不識抬舉的破落戶,福薄短命的小賤人!」
崔氏在她身旁坐下來,擔憂地道:「大嫂,這窮酸油鹽不進的怎麼好?若是鬧到兩邊族裡,掰扯起來就很難看,對七郎的名聲更是影響不小,萬一傳回我娘家那邊就不好了。」
蕭家悔婚,自是因為有了更好的婚配對象。
當世最講門第出身,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五姓七望,是為頭等的高門大戶,世人皆以娶五姓女為榮。
此種高貴榮耀,便是尚公主也比不上。
而清河崔氏近來接連出了好幾任宰相,可謂風光無比、權柄在握,倘若蕭七郎能夠與之結親,前途必然順遂無比。
這樣的婚姻有多難得自不用說,所以這欺負孤兒寡婦、背信棄義悔婚的名聲定然不能傳出去。
裴氏陰沉著臉慢慢轉了會兒腕間的金鑲玉鐲,眼裡露出凶光,「敬酒不吃吃罰酒,這樣的不知趣,為了我兒的前程,少不得要動些非常手段了。我記得楊氏的兒子在宣陽坊讀書……叫屠二過來。」
送走惡客,屋子裡瞬間清淨下來。
杜清檀長長地舒了口氣,閉上眼睛躺下,示意采藍給她揉揉太陽穴。
躺了會兒,突然覺得氣氛不大對,睜眼一看,只見楊氏怔怔地看著她,眼淚流得滿臉都是。
「別哭了,不值得。」杜清檀向來不怎麼會安慰人,只覺得自己詞彙貧乏,索性掏出手絹遞過去,「我又不在意。」
誰想楊氏接過她的帕子一看,哭得更厲害了,「這手絹都快破洞了妳還在用,都怪我沒本事,守不住家業,害得妳吃苦受罪,被人欺辱……」
杜清檀很無語,眼看楊氏哭得越發厲害,索性伸出手臂摟住她的肩頭,「算起來也是我一直生病吃藥,把家裡吃垮了。還有,大伯母是不是也如同裴氏所言那般,認為我剋父剋母呢?」
「胡說八道!妳娘又不是因為妳死的,我不也生過病吃過藥?」楊氏立刻收了眼淚,憤怒地道:「那就不是個東西!按照她的說法,我還剋夫呢!」
杜清檀喜歡楊氏的爽利性子,更感激她這樣照顧自己,便輕輕一笑,「既然知道她不是個東西,還哭什麼?」
「我就是太生氣了啊!」
生氣、屈辱,卻無力無處發洩,不是就只有哭鼻子了嘛!
杜清檀哄孩子似地拍拍她的肩頭,「哭好了就來商量該怎麼辦才好?」
活了幾十歲,還不如孩子冷靜懂事。
楊氏不好意思地接過采藍遞來的帕子擦了臉,「這事還得族裡出面解決,我這就去杜陵。稍後團團也要下學了,妳在家等著他。」
京兆杜氏自西漢起便名臣輩出,鼎鼎有名的凌煙閣開國二十四功臣之一杜如晦正是本家代表人物,只可惜後續無人,如今族中多是寂寂無名之輩。
而杜清檀家又是旁支,上兩輩便搬出了杜家世居的杜陵,只有逢年過節或是婚喪嫁娶等大事才會回去,日常與族裡聯繫並不緊密。
也正是這個原因,裴氏才敢如此囂張霸道地欺上門來。
但無論如何,只要族裡肯出面,總能讓蕭家不好過。
杜清檀卻覺得族裡不會管太多,畢竟自己這支的成年男丁已經死絕,餘下一個團團尚且年幼不知前途如何,誰會願意為了他們去得罪蕭家呢?
楊氏這一去少不得也要低三下四求人,不如另想他法。
楊氏嘆道:「不是我不通人情世故,只是這事無論如何都要告知族裡,不說就不對,況且這也是最便捷簡單的法子。行了,妳先去歇會兒,別回頭又生了病。」
事不宜遲,趁著天色還早,楊氏帶上粗使婆子于婆,雇了輛驢車火速往曲江池南邊的杜陵去了。
杜清檀回房躺了會兒,瞅著時辰差不多就起了身,走到前頭叮囑男僕老于頭,「時辰差不多了,你去接團團,路上小心些,別耽擱,別與人鬧紛爭。」
團團已經七歲,兩年前由楊氏給他開了蒙,家裡請不起先生,便在宣陽坊一個杜氏宗親家裡附了學。
宣陽坊和他們住的永寧坊隔了一個坊區,雖說不算遠,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況且之前她看裴氏眼神陰沉狠戾,總覺得這種人跋扈慣了,也不講什麼道義,做事必然不擇手段,自家怎麼小心都不為過。
「五娘放心,老僕無論如何都會護得小郎周全。」
老于頭與于婆是一家,老倆口無兒無女,待杜清檀和團團就和自家小輩一樣疼愛。
杜清檀自是放心的,等老于頭出了門,便去廚房看采藍做飯。
其實不過是些粗糧蔬菜罷了,並沒有肉食之類的。
當然,想吃也沒得吃,不止是窮,還因為女皇篤信佛教,下令禁屠宰。
有權勢的人家可以冒著風險偷偷弄了肉食解饞,他們這樣的小可憐就算了,又不是嫌命長。
所以杜清檀看著那黃燦燦的小米,以及滿眼的青綠素菜,心裡淒風陣陣,覺得人生又慘澹了幾分。
她想吃大白米飯,想吃油汪汪的紅燒肉,想吃香噴噴的烤雞啊!
就算沒有,好歹也給她一個白麵餅子加顆蛋之類的,這才是病號需要的啊!
采藍被她絕望悲涼的目光看得受不了,索性趕她走,「快去歇著,小郎回來就叫您。」
杜清檀出了廚房,便去大門口站著往外張望。
團團這孩子年紀雖小,卻長得玉雪可愛,聰慧乖巧,她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小堂弟了,半天沒見,怪想的。
日影一點點的斜下去,始終不見老于頭和團團回來,杜清檀慌了起來,難道蕭家真對這孩子出手了?
不成,得去瞅瞅。
采藍也擦著手走了出來,「飯好了,怎麼還沒回來?」
「我們去接他們。」杜清檀見采藍想拒絕,便將眼睛一瞪,「不許多話!」
「知道了。」采藍無奈地取了帷帽給她戴上,攙著她往前走。
杜清檀走得很慢,走一段路就要停下來歇一歇。
采藍也沒有嫌煩的意思,反而誇她,「您這身子骨真是比從前好多了,之前哪裡敢上街啊!」
杜清檀沒吱聲,只管睜大眼睛在過往行人裡尋找老于頭和團團,然而一直走到宣陽坊,還是沒見著人。
采藍奇怪道:「難道錯過了?要不就是還沒放學?」
杜清檀緊抿著唇,儘量加快速度趕到杜氏宗親家中。
門房見到她們很驚奇,「今日先生有事,提前放了學,小郎早在半個多時辰前就走了。府上的老于頭也才來過,還沒回家去嗎?」
杜清檀皺起眉頭,「沒見著,不知他是否與同學同行?」
門房笑道:「因放學早,其他學生約了去東市閒逛,小郎說要回家背書,是自己走的。」
團團懂事,知道家裡沒錢,所以遇到這種要花錢的事都會避開。
杜清檀發愁地看向街道,這麼大個長安城,團團和老于頭究竟去哪裡了呢?
雖然難,卻也不能什麼都不做。
主僕二人沿著團團往日上下學的線路依次尋找過去,逢人就問,卻也沒能問出個名堂來。
「五娘,那是小郎的書包!」采藍激動地指向前方。
那是一個穿灰色粗布圓領缺胯袍的年輕男人,抱著一把橫刀,漫不經心地斜靠在坊牆上,看起來像個遊俠。
他身後跟著一匹老得斑禿了的灰驢,正在專心地啃食牆縫裡的野草。
灰驢的脖子上,掛著團團的書包。
杜清檀這會兒已經累得不行,歪著帷帽,撫著胸口,說一句喘一下,「這位俠士……請問您這個書包……是從哪裡來的?」
男人身量極高,半垂眸子,居高臨下斜瞅著她,濃密捲翹的睫毛裡透出的目光又清又冷,「五十文!」
杜清檀和采藍愣了片刻才明白,他是要她們給錢才肯說。
采藍先不滿了,潑辣地道:「五十文都夠買三斗米了,你怎麼不去搶?」
年輕男人完全無視她,只看著杜清檀淡淡地道:「妳應當曉得,重要的消息是用錢換不來的。」
杜清檀立刻明白了,「那是自然,給你五十文!」
年輕男人嘴角輕輕一勾,露出一個淺淺的笑容,潔白修長的手掌往她面前一伸,「給錢。」
杜清檀身上是沒錢的,當即給了采藍一個眼神。
采藍心不甘情不願,肉疼得直哆嗦地解下腰間的錢袋子,噘著厚厚的嘴唇小聲嘀咕,「長得人模人樣的,怎麼這樣!只有四十文,多的沒了,這還是我們家幾天的口糧錢呢!」
年輕男人也不計較,把錢往懷裡一塞,解了書包丟過去,指著前方道:「人在那間屋子裡,哄著那孩子去車裡看猴戲,然後就鬧騰起來,說是偷了東西。孩子鬧騰得厲害,書包也扔在街上,接著一個瘸腿老者找過來,和他們吵鬧一回,兩個人都被拉進那道門去了,說是要報官。」
「胡說!我們家小郎乖巧懂事,才不會偷東西呢!」采藍又氣又急,「五娘,這可怎麼辦?」
才和蕭家鬧過,就出了這樣的事,多半是裴氏設了圈套,要借此逼迫自己和楊氏就範。
杜清檀微一思忖便有了數,當即和采藍說道:「不急,一時半會兒不會有性命之憂。我在這裡守著,你去請武侯過來。」
長安城共計一百一十坊,各坊均設置武侯鋪管理治安,武侯便是緝盜安良的公差,這種事正該歸他們管。
「只要不是殺人放火之類的大事,要請武侯就得給錢,婢子沒錢了。」
采藍目光炯炯地盯著一旁的年輕男人,希望這人能夠良心發現,把錢還回來。
然而年輕男人坦然大方地由著她看,絲毫沒有羞愧之意,更沒有願意還錢的意思,只提醒她們,「一共兩個彪形大漢,手臂有我兩隻那麼粗,能輕輕就能把妳們脖子捏斷的那種。妳們是得罪什麼人了吧?請武侯過來未必有用,只怕還會適得其反。」
采藍立時嚇哭了,「五娘,怎麼辦啊?一定是蕭家幹的!」
杜清檀嚴肅地打量面前的男人,雖然穿著粗布衣裳破靴子,然而膚白貌美,眼眸深邃,睫毛捲長,身形勻稱健美,氣質儀態俱佳,手上也沒什麼繭子,顯然不是貧苦出身。
這樣的人總不會平白無故守在這裡管閒事,雖不知對方的目的是什麼,但此刻光憑她和采藍是沒辦法處理好這件事的,不如找個幫手。
「這位俠士。」杜清檀掂量著開了口,「您見義勇為給我們傳信,真是幫了我們的大忙。能不能請您好人做到底,再幫我們把孩子救出來?」
「見義勇為,好人做到底?」年輕男人一笑,很是文雅地道:「妳看錯了,我不是什麼俠士,也不是好人。我之所以留在這裡,是因為沒錢吃飯,所以想弄點錢住店。」
杜清檀一時不知道該怎麼接話,「所以?」
「所以小娘子若要請我幫忙,得給錢。」
男人頗有耐心,畢竟杜清檀這副氣喘吁吁,蹙眉撫胸的嬌弱模樣實在讓人心軟,彷彿是一顆晶瑩剔透的露珠,隨時會被陽光曬化了似的。
「再給你五十文。」杜清檀記得家裡似乎還有點錢,只是不多。
「五十文!?」男人喊出聲來,因為太過震驚,瞳孔縮了又放。
「我暫時只有這麼多,可以打欠條,您要多少?」杜清檀有些抱歉,說到底是打打殺殺的買賣,五十文確實太少了,萬一受傷什麼的,還不夠醫藥費。
「欠條?」男人盯著她看了片刻,勾起嘴角笑了起來,頗不像個正經人,「小娘子覺得我值多少錢呢?」
采藍警惕地把杜清檀護在身後,這人看起來太不正經了,就像是想要利用美貌勾引自家五娘似的。
看他那五官似是有胡人血統,這種樣貌最勾人了,自家五娘日常不怎麼出門,對男人沒啥見識,很可能會被蒙蔽。
然而杜清檀並不能體會采藍的苦心,反而嫌她擋了視線,「閃邊,別擋著。」
采藍很鬱悶地往旁一站,看杜清檀和男人討價還價。
「一千文,不能再多了。」
「兩千文,不能再少了。」
「一千五百文,我家太窮了,不然也不會穿舊衣,打補丁。」杜清檀拉起采藍的裙腳,給他看上面的補丁賣慘,「我們平時只能勉強吃飽,生病了都看不起大夫吃不起藥,不然我也不會這麼虛弱。」
男人皺著眉頭嘆了口氣,「行吧,確實挺可憐的。」
杜清檀猛點頭,以為對方已經同意了她給的價,不想男人跟著就道:「一千八百文,再講價就算了。」
采藍很不高興,覺得一個大男人鑽到錢眼裡去,和女人這麼斤斤計較的,簡直不像話。
杜清檀倒是沒啥想法,「前頭鋪子裡尋了筆墨給您寫欠條?敢問尊姓大名?」
「獨孤不求。」男人邁開長腿朝著鋪子走去,脊背挺得直直的,然而每走一步,破了的靴子總會發出一聲「啪嘰」的怪響。
見主人走了,老禿驢也不吃草了,慢悠悠地跟上去,一瘸一瘸的,走不得幾步,幾根毛隨著風飄落下來,身上又禿了一塊。
反正就很落魄的樣子。
「死要錢會不會是洛陽獨孤氏啊?」采藍和杜清檀咬耳朵,八卦獨孤不求的出身來歷,「獨孤家祖上是胡人來著,我看很像!」
洛陽獨孤氏也是百年門閥,族中尚武,出了不少名將。前朝時還出過好幾位皇后,到了本朝,家主曾被封為郡王,族中子弟又尚公主,是有名的貴戚。只是近年來也和杜家一樣,沒啥出色的人才,沒落了。
杜清檀聽采藍這麼一分析,也覺得像,她便很直白地問了,「獨孤公子,您家是洛陽獨孤氏嗎?」
獨孤不求正在吹乾欠條上的墨跡,聞言懶洋洋地瞥了她一眼,「是啊,妳找獨孤家有事?」
這話挺不客氣的,包著火氣。
杜清檀猜想他或許是和族裡有怨,被趕出來什麼的,不然不會混得這麼慘,好脾氣地笑笑,「這不是互通家門嗎?我們是京兆杜氏旁支。」
獨孤不求沒什麼反應,將欠條往懷裡一塞,大步流星往前走,整個人都透著不高興。
杜清檀跟著小跑了一段路,累得肺都要炸了,就連頭上的帷帽都像是負擔,索性扯掉帷帽,揪著采藍的胳膊喘個不停。
采藍便道:「獨孤公子,還請您慢些,我家五娘身子虛弱跟不上。」
獨孤不求不耐煩地回頭看杜清檀一眼,「嘖」了一聲,拉過老禿驢,「坐上去!」
杜清檀看看那頭可憐的老禿驢,很不忍心,「還是算了,就幾步路工夫,很快就到了。」
獨孤不求抬眼看看天色,「很快就要敲暮鼓了。」
長安城規矩多,晨鐘起,暮鼓歇,暮鼓響完,坊門關閉,各人歇市歸家,是不許在外頭逗留閒逛的,否則犯了夜禁,被打死也有可能。
被嫌棄了,弱者是沒有人權的,杜清檀默默地在采藍的幫助下上了驢背,跟在獨孤不求身後。
獨孤不求埋著頭走了一會兒,心情似有好轉,「等會兒妳的婢子去敲門,妳跟著上前問清楚他們的目的,反正各種找事就對了。我在一旁看著,瞅住機會先去救人。這老驢我留在門外,完事妳就騎著牠回去。」
這和杜清檀的想法差不多,只不知道這人的本領如何,拎刀的樣子倒像是很在行。
於是她很委婉地道:「對方人多勢眾,公子千萬要小心些,咱們是取巧,不是拼命。」
當然了,若是獨孤不求不行,她也還有預備方案。
獨孤不求瞥她一眼,輕哼道:「該小心的人是妳,風都能吹倒,也不知道多吃些飯。」
說起這個,杜清檀也很惆悵啊,幽幽地道:「這不是吃多吃少的問題,命運如斯,能奈其何!」
這真的是個命理問題,沒有辦法的那種。
獨孤不求又瞥了她一眼,突然勾著唇角笑了起來。
采藍不爽,「你幹嘛總是看我家五娘?你笑什麼?」
獨孤不求笑得更燦爛了,「人生來不就是給別人看的嗎?妳家五娘又不是醜八怪怕人看,我看看怎麼了?我天生愛笑關妳何事?」
采藍完全不能回嘴,氣得噘起厚厚的嘴唇,恨恨地瞪過去。
獨孤不求並不理她,看著前方說道:「那人就是領頭的。」
一個粗壯的灰衣漢子從馬上下來,陰沉著臉敲響了門。
裡頭有人大聲問道:「誰啊?」
灰衣漢子不耐煩地道:「我,屠二。」
門應聲而開,一個塌鼻子男人探出頭來四處張望,「找著人了嗎?」
屠二不高興地道:「杜家沒人在,不知死哪裡去了?」
卻聽塌鼻子男人喊了一聲,「那不是嗎?」
屠二回過頭來,正好和杜清檀等人碰了個面對面。
雙方一時都有些措手不及和呆住,就那麼傻傻地看著對方不說話,場面頗為詭異。
杜清檀先回過神來便要下驢,奈何采藍手忙腳亂扶不穩,險些把她摔個大馬趴。
還是獨孤不求實在看不下去,伸手搭了一把。
「我家團團和老僕是被你們綁了?」
杜清檀話音未落,便被一陣冷風吹得忍不住咳了起來。
雪白的臉上浮起幾縷病態的紅暈,如同一朵在風雨中搖擺的玉白染紅的芍藥花,柔弱嬌妍得讓人忍不住心疼。
屠二眼裡淫光大盛,叉著腰帶,頂著肥肚走過來,色咪咪地盯著她,「是杜家的五娘吧?妳那堂弟盜竊我家的寶貝,按律該送官處置,妳說要怎麼辦吧?」
杜清檀好不容易停止咳嗽,細聲細氣地道:「孩子還小,不懂事,裡頭怕是有誤會,不如把他帶出來,我們當面問問?」
她想得很美,進了人家屋子就好比入了牢籠,給人甕中捉鱉,把人帶出來就好了,要跑要逃都能方便許多。
然而人家卻也不是傻子,屠二笑道:「那孩子精得跟猴兒似的,萬一帶出來跑了怎麼辦?還是妳們進來談吧!」
說話間,又淫邪地往杜清檀臉上身上看了一遍。
采藍氣到不行,衝到前面護住杜清檀大聲道:「你們這些壞人,誰曉得是不是要把我們哄進去做什麼壞事?」
「壞事?我們能對妳們做什麼壞事呢?快說說!」
屠二激動的使勁拍著大腿和同伴笑個不停,就想佔點言語上的便宜。
畢竟出身這麼好,又長得這麼美,還可以任由他們調戲的小娘子可不多。
采藍彪悍地破口大罵,「豬狗不如的腌臢東西,你們長腦袋只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高點嗎?你們就像一堆狗屎,又臭又爛,令人作嘔。你們連最基本的人性都沒有,別再出來丟人現眼了!」
杜清檀目瞪口呆,她從來不知道罵人竟然可以有這麼多花樣,更不知道采藍這麼個小姑娘居然可以罵人不重樣!
不過,要的就是這麼個效果。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