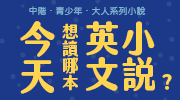今後每一個盛夏
商品資訊
系列名:潮流文學
ISBN13:9786264036467
替代書名:Every Summer After
出版社:尖端出版
作者:卡莉・弗瓊
譯者:劉銘廷
出版日:2025/05/06
裝訂/頁數:平裝/432頁
規格:21cm*14.5cm*2cm (高/寬/厚)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好讀網超過60萬名讀者盛情推薦!
★《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蟬聯前15名十三週!
★《環球郵報》年度最佳圖書!
.「這是繼《愛在字裡行間》你下一本必讀的書,讀起來簡直是一種享受!」──艾希莉‧歐娟(AshleyAudrain,《紐約時報》暢銷書《在所有母親之間》作者)
.「這是一部充滿情感衝擊力、光芒四射的處女作。」——艾米莉·亨利(Emily Henry,《紐約時報》暢銷書排名第一《圖書愛好者》、《愛在字裡行間》的作者)
夏天剩下的日子裡,我陷在自責的迷霧中,試圖搞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
身為一名深受上司讚賞的資深編輯,
波瑟芬.費雪在多倫多這個大城市中過著光鮮亮麗的時尚生活,
一切看似成功順遂,直到一通電話戳破了虛假的幸福泡泡。
彷彿從長年的昏迷中清醒,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繼續逃避下去,
一場喪禮給了她回去的藉口,回到她心中深愛之處──
少女時期的她,每年總是期待盼著遠離城市學校的麻煩社交,
前往擁有山光水色的湖畔木屋度過夏日假期。
在那裡,她遇見了欣賞她恐怖電影收藏的唯一知心,
但也是在那裡,一個錯誤的衝動,讓她失去了擁有摯愛的資格……
這些年來,她一直在為自己犯下的錯誤付出代價,
無法擁有長期的戀愛關係,也沒有勇氣回到心愛的湖畔。
如今,她得到了一個說出真相的機會,
她能否鼓起勇氣修補這個錯誤,祈求他的原諒,重新贏回他的心?
★《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蟬聯前15名十三週!
★《環球郵報》年度最佳圖書!
.「這是繼《愛在字裡行間》你下一本必讀的書,讀起來簡直是一種享受!」──艾希莉‧歐娟(AshleyAudrain,《紐約時報》暢銷書《在所有母親之間》作者)
.「這是一部充滿情感衝擊力、光芒四射的處女作。」——艾米莉·亨利(Emily Henry,《紐約時報》暢銷書排名第一《圖書愛好者》、《愛在字裡行間》的作者)
夏天剩下的日子裡,我陷在自責的迷霧中,試圖搞清楚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
身為一名深受上司讚賞的資深編輯,
波瑟芬.費雪在多倫多這個大城市中過著光鮮亮麗的時尚生活,
一切看似成功順遂,直到一通電話戳破了虛假的幸福泡泡。
彷彿從長年的昏迷中清醒,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繼續逃避下去,
一場喪禮給了她回去的藉口,回到她心中深愛之處──
少女時期的她,每年總是期待盼著遠離城市學校的麻煩社交,
前往擁有山光水色的湖畔木屋度過夏日假期。
在那裡,她遇見了欣賞她恐怖電影收藏的唯一知心,
但也是在那裡,一個錯誤的衝動,讓她失去了擁有摯愛的資格……
這些年來,她一直在為自己犯下的錯誤付出代價,
無法擁有長期的戀愛關係,也沒有勇氣回到心愛的湖畔。
如今,她得到了一個說出真相的機會,
她能否鼓起勇氣修補這個錯誤,祈求他的原諒,重新贏回他的心?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卡莉・弗瓊Carley Fortune卡莉.弗瓊(Carley Fortune)是《Refinery29 Canada》的執行編輯。她是一位屢獲殊榮的記者,曾在加拿大頂級媒體工作,包括《環球郵報》、《多倫多生活》和《Chatelaine》。她職業生涯的最後六年一直在女性媒體工作,並對與女性觀眾建立聯繫有著濃厚的熱情。她與丈夫和兩個兒子住在多倫多。《今後每一個盛夏》是她的第一本小說。
譯者簡介
劉銘廷
嘉義人,曾任出版社資深主編,現為英、法文翻譯。
卡莉・弗瓊Carley Fortune卡莉.弗瓊(Carley Fortune)是《Refinery29 Canada》的執行編輯。她是一位屢獲殊榮的記者,曾在加拿大頂級媒體工作,包括《環球郵報》、《多倫多生活》和《Chatelaine》。她職業生涯的最後六年一直在女性媒體工作,並對與女性觀眾建立聯繫有著濃厚的熱情。她與丈夫和兩個兒子住在多倫多。《今後每一個盛夏》是她的第一本小說。
譯者簡介
劉銘廷
嘉義人,曾任出版社資深主編,現為英、法文翻譯。
書摘/試閱
第一章
現在
第四杯雞尾酒在當時看起來是個好主意。現在回想起來,剪瀏海似乎也是如此。但如今我站在公寓房門口掙扎著將鑰匙插入鎖孔,不禁開始懷疑,自己在明天早上醒來時,八成會後悔將最後那杯氣泡調酒喝下肚。也許瀏海也是個錯誤。今天我坐在珍的椅子上剪頭髮時,她還特別提醒我,分手瀏海十之八九會是個糟糕透頂的決定。可是珍今晚不需要以剛剛恢復單身的狀態去參加她朋友的訂婚派對。這瀏海是剪定了。
我會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我還愛著前男友;我沒有。我從來沒有愛過他。賽巴斯丁是個虛榮的勢利鬼。作為一個前途無可限量的企業律師,若是也讓他來參加襄妲的派對,用不上一小時,他就會開始嘲笑她精心挑選的招牌調酒,並引述《紐約時報》上刊登的某篇自以為是的文章,大聲嚷嚷著「阿佩羅雞尾酒過時了」。反之,他八成會假裝認真研究酒單,詢問調酒師一些關於風土條件和酸度的煩人問題,然後不管對方給的答案是什麼,他都會點那杯最貴的紅酒。他並非品味出眾或對葡萄酒有什麼深入的研究,他只是利用昂貴奢侈的花費來營造自己擁有獨到眼光的假象。
賽巴斯丁和我在一起七個月,創下了我這輩子迄今為止最長戀情的記錄。最後,他說他「並不是真的認識我」。他說得有道理。
在賽巴斯丁之前,我挑選的對象都只是為了及時行樂,他們對於保持輕鬆的交往關係也都沒什麼意見。當我遇見他的時候,我便想,作為一位成熟的大人,就代表自己應該找一位可以穩定發展的對象了。而賽巴斯丁符合我的標準。他非常有吸引力、博學多聞、功成名就,雖然有點傲慢自大,但他幾乎能和任何人聊任何話題。但我仍然很難和他分享過於真實的自己。我很早以前就學會將各種零碎的想法給壓抑下來,並三思而後言。我以為自己已經很努力在給這段感情一個真正的機會,但最後賽巴斯丁察覺到我的漠不關心,他是對的。我不在乎他。我不曾在乎過他們任何人。
只有一個。
一個早已離我遠去的人。
於是我流連於男人之間,我也同時耽溺於性愛為我降下的心靈逃生梯。我喜歡逗男人歡心,我喜歡有人陪伴,我喜歡可以暫時不用按摩棒來滿足自己,但是我不會因此就一時意亂情迷,也不會持續與對方深交。
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用鑰匙打開公寓的門──別鬧了,這鎖孔到底有什麼毛病──而就在此時,我皮包裡的手機響了。太詭異了。沒有人會在這麼晚的時間打給我。事實上,根本不會有人會想打電話給我,除了襄妲和我的爸媽之外。但是襄妲應該還在結婚派對上,而爸和媽跑去布拉格旅遊了,這時間他們根本還沒醒。就在我終於打開門,並跌跌撞撞地進入了我的小單人房裡時,手機也停止了震動。我看向門口的鏡子,發現自己的口紅雖然糊了,但瀏海卻美得不可開交。滾一邊去吧,珍!
我開始脫掉腳上的金色羅馬鞋,一縷深色髮絲垂落我臉旁;此時,我的手機又響了。我從包裡挖出手機,只脫掉了其中一支鞋,邊往沙發的方向移動,邊皺著眉看著螢幕上顯示「未知號碼」。對方大概是打錯了。
「喂?」我邊說,邊彎腰脫掉另一支鞋。
「是波西嗎?」
我整個身子彈起的速度太快,以致於不得不扶著沙發扶手來穩住腳步。波西。已經沒有人會用這個名字稱呼我了。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叫我波瑟芬。有時後,他們會直接叫我「波」。但絕對不會是波西。我已經不叫波西很多年了。
「喂……波西?」那聲音深沉而柔和,是我已經十幾年未曾聽見的聲音。但它是如此熟悉,使我在一瞬間回到了全身塗滿防曬係數45的防曬乳,並躺在碼頭邊讀著平裝書的十三歲。然後是十六歲,從酒館下班後就脫光衣服跳進湖裡,全身赤裸且黏答答的我。十七歲,穿著溼漉漉的泳衣躺在山姆床上的我,看著在我腳邊的他,用修長的指尖滑過他正在苦讀的解剖學教科書。一股熱浪迎頭撞上我的臉頰,我的心跳聲厚重且堅定地充斥在我的耳膜內,隆隆作響。我顫抖著吸了口氣,坐了下來,胃袋緊縮。
「我是。」我勉強回答。對方吐了一口悠長且放鬆的氣。
「是我,查理。」
查理。
不是山姆。
查理。兩兄弟裡不對的那一個。
「查爾斯・佛洛萊克。」查理聲明,並開始解釋他是如何取得我的電話號碼──什麼某個朋友的朋友,以及那個誰認識我目前工作的雜誌社之類的──但我根本聽得心不在焉。
「查理?」我打斷他,聲音尖銳且緊繃,有一部分是因為雞尾酒,但更多的是來自震驚。又或者,完全是出自於失望。因為這個聲音不是山姆的。
它當然不會是山姆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老天,我甚至不知道有多久。」他說,聽起來像是在道歉。
但我很清楚。我完全知道過了多久。我一直沒有停止計算。
我上次見到查理,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十二年前,在那個災難般的感恩節周末,在我與山姆之間的一切都崩潰之後。在我毀了一切之後。
我曾經期待家人前往別墅度假的日子,這樣我便可以再次見到山姆。現在他變成了一個痛苦的記憶,被我深深地埋藏在肋骨之下。
我也知道,我離開山姆的時間比和他在一起的時間更長。在距離我和他最後一次交談滿七年的感恩節當天,我第一次恐慌症發作,然後灌下了一瓶半的粉紅酒。我和他一起在湖畔的時光,已經正式被我離開他的時間所超越,感覺就像是跨越了一個里程碑。我哭得花容失色,上氣不接下氣,倒在浴室的地板上昏了過去。第二天,襄妲外帶了一些油膩的食物登門,替我在嘔吐的時候抓住頭髮,我滿面淚水,將一切都告訴她。
「彷彿已經過了一輩子。」我告訴查理。
「我知道,也很抱歉在這麼晚打給妳。」他說。他的聲音聽起來太像山姆了,這使我非常難受,彷彿骨鯁在喉。我記得我們十四歲時,要在電話中辨別出他和查理的聲音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我也記得那個夏天,我注意到一些其他與山姆有關的事。
「聽著,小波,我會打來是因為有件事情,」他用他以前暱稱我的方式叫我,然而語氣卻比我認識的查理嚴肅許多。我聽見他吸了吸鼻子。「我媽媽在幾天前去世了,我想……我想妳應該會想知道。」
他的話像海嘯一般朝我襲來,在一時半刻之間我還沒辦法立刻全然理解。蘇還很年輕啊。
我只能發出一聲破碎的「什麼?」。
查理在回答時聽起來很疲憊。「是癌症。她已經和它纏鬥了好幾年。我們當然傷心欲絕,但她已經厭倦了病懨懨的自己,妳懂嗎?」
這已經不是我頭一次感覺有人偷走了我人生故事的劇本,然後把它改寫得面目全非。蘇會生病這件事簡直難以置信。總是掛著大大的笑容、穿著牛仔短褲,將她的白金秀髮紮成馬尾的蘇。全世界最會做波蘭餃的蘇。把我當成女兒對待的蘇。我曾經夢想有一天會成為我婆婆的蘇。疾病纏身多年卻將我蒙在鼓裡的蘇。我應該要知道的。我應該要在她身邊的。
「我實在非常,非常抱歉,」我開口。「我……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你媽媽……她……」我聽起來很慌張,我自己都感覺得到。
振作點,我對自己說。妳早就失去了擁有蘇的權利。妳現在沒有資格崩潰。
我想起蘇獨自撫養兩個男孩,同時經營著酒館,以及我第一次見到她時的情景。當時她來到別墅,向年紀大她很多的我父母保證山姆是個好孩子,她也會好好看著我們。我記得她教會我如何一次端三個盤子,還有告訴我對於任何男孩的欺負都不要忍氣吞聲,包括她自己的兩個兒子。
「她是⋯⋯她是一切。」我說。「她是一個多麼稱職的母親。」
「她的確是。我也知道在我們都還只是孩子的時候,她對妳的意義有多重大。這也是我打電話給妳的原因,」查理猶豫了片刻。「她的告別式會在這週日舉行。我知道已經過了很久,不過我想妳應該來一趟。妳願意出席嗎?」
過了很久?已經過了十二年。距離我上次驅車北上,去到那個比任何地方都更像家的歸屬之地,已經過了十二年。距離上一次我頭朝下跳入湖水裡,已經過了十二年。已經十二年了,我的生活從此翻天覆地。已經十二年了,我沒再見過山姆一眼。
但是答案只有一種。
「我當然願意。」
第二章
夏天,十七年前
我覺得爸媽在買下別墅的時候,並不知道隔壁住著兩個青少年男孩。爸媽希望能讓我遠離城市的喧囂,遠離同齡的孩子,而佛洛萊克家的兩個男孩──經常整個下午到傍晚都沒人管──的出現讓我出乎意料,他們或許也有同感。
我班上的一些同學家裡也有度假別墅,但都在離市區北上不遠的馬斯科卡區,沿著那裡的岩岸放眼望去,就是一整排的濱海豪宅,把它們稱做「別墅」似乎有些名不副實。老爸直接拒絕將別墅買在馬斯科卡區。他說,如果我們在那裡買一下一棟別墅,還不如乾脆整個夏天都待在多倫多──那裡離市區太近,而且所到之處幾乎全是多倫多人。所以他和老媽把搜尋範圍擴大到東北方更偏遠的郊區,但是老爸又嫌那裡被過度開發或價格過高。於是他們繼續往更北邊尋找,最後選定了貝瑞灣。這個安靜的工人階級村莊,一到夏天就會變成熙熙攘攘的旅遊小鎮,人行道上會擠滿前來度假的旅客,以及打算前往阿岡昆省立公園露營或登山健行的歐洲觀光客。「妳會喜歡那裡的,小鬼,」老爸承諾。「那裡是真正的度假勝地。」
雖然最終我還是會期待從多倫多市中心的都鐸式建築開四小時的車來到湖邊,但第一次的旅程卻彷彿感覺過了一個世紀般漫長。等到我們開車行經「歡迎來到貝瑞灣」的招牌時,我感覺人類文明已經興衰過了好幾輪。老爸和我坐在搬家用的卡車上,老媽則開著家裡那輛Lexus跟在後頭。和老媽的那臺車不同,卡車上既沒有像樣的音響,也沒有空調。我只能聽著加拿大廣播公司單調的悶哼聲,任憑大腿後側黏在人造皮革椅上,瀏海緊貼著我溼透的前額。
幾乎所有在我國一班上的女孩,都因為黛莉拉・梅森剪了瀏海後就一窩蜂地跟隨潮流,儘管那些瀏海並不適合我們所有人。黛莉拉是全年級最受歡迎的女孩,而我認為自己能成為她最親近的朋友之一實屬幸運。或者至少以前是,在睡衣派對事件發生之前。她的瀏海像紅色帷幔整齊地垂掛在額頭上,而我的瀏海則像是同時違背了地心引力和造型產品般,以奇怪的角度鼓脹分岔,讓我看起來像個愚鈍的十三歲女孩,而非我一直想成為的神祕黑眼棕髮少女。我的頭髮既不直也不鬈,並且它似乎會根據一系列不可預測的因素改變個性,從今天星期幾到天氣狀況,甚至是前一天晚上睡覺的方式也包含在內。即便我會盡一切所能討他人歡心,但我的頭髮卻不願意配合。
***
「裸岩巷」蜿蜒在卡曼尼斯克湖西岸蜿蜒的灌木叢中,是一條名副其實的狹窄泥土路。老爸拐進的這條道路被過長的樹葉枝條給霸占,不斷刮著小卡車的兩側。
「小鬼,妳聞到了嗎?」老爸問,並在卡車顛簸前進的同時搖下車窗。我們一起深呼吸,落地許久的松針帶著泥土的氣息,混合著藥草清香,充滿了我的鼻腔。
我們抵達一棟不起眼的A字形小木屋的後門,周圍環繞著白與紅的松樹,使得小屋顯得格外矮小。老爸將引擎熄火,轉過身,在他銀灰色的鬍子下透露出一抹微笑,他的雙眼在黑框眼鏡底下跟著瞇起,對著我說:「歡迎來到湖畔,波瑟芬。」
這棟小木屋別墅裡有一股不可思議的熏木香味。即使老媽多年以來在屋內點著昂貴的Diptyque蠟燭(註一) ,也都不會使這種味道消散。每次回來,我都會站在門口,像第一天來到這裡那樣深呼吸。一樓是一個開放的小空間,從地板到天花板都用淺色的結木板覆蓋。屋內一面巨大的窗戶則將湖泊壯麗到幾乎讓人有點不快的景色充分展現。
「哇。」我喃喃道,並看見一條從露天平臺通往陡峭山坡的階梯。
「還不賴吧?」爸爸拍拍我的肩膀。
「我要去湖邊看看。」我說,已經從側門衝向外頭,門在我身後砰一聲地關上。我飛奔而下幾十道臺階,直到我抵達碼頭邊。這是一個潮溼的下午,厚重的灰色雲層鋪滿整片天空,映照在下方紋風不動的銀色湖面。我幾乎看不見散落在遠處岸邊上的小屋。我好奇自己能不能游得過去。我坐在碼頭邊緣,在水裡擺盪著雙腿,驚訝於這裡的寧靜,直到老媽朝我大聲疾呼,要我幫忙搬行李。
我們在搬箱子的過程中還得不停與蚊子奮戰,結束後所有人都相當疲憊且煩躁。我留下爸媽獨自整理廚房,自己一個人上了樓。樓上有兩間臥室,爸媽把擁有湖景的房間讓給了我,他們的理由是我比起他們更喜歡待在房間裡,可以好好欣賞風景。我整理了行李箱的衣服,鋪了床,並折好一條哈德遜灣百貨(註二) 的毛毯放在床尾。老爸覺得夏天不需要這麼厚重的羊毛毯,但媽堅持每張床上都要有一條。
「這樣才夠加拿大啊。」她解釋,語氣彷彿像在說這種事情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才對。
我在床頭櫃的一側疊滿搖搖欲墜的平裝書,並釘了一張《黑湖妖潭》(註三) 的海報在床頭。我相當著迷於恐怖片。我看過很多恐怖電影,爸媽老早就放棄替我審查內容,我還一口氣讀完了R・L・史坦恩和克里斯多夫・派克(註四) 的經典作品,以及新出的那些關於性感的青少年在滿月時變成狼人,或性感的青少年在啦啦隊訓練結束後化身猛鬼獵人的小說。以前我還有朋友的時候,我會把這些書帶到學校,為她們大聲朗讀精采的部分(例如任何血腥橋段或稍微有點性感的部分)。一開始,我只是喜歡得到女孩們的反應,享受成為目光焦點,但同時又可以利用他人的文字作為娛樂手段,以策人際關係上的安全距離。但讀過的恐怖小說越多,就越喜歡故事背後的創作過程──作者如何將不可能發生的情況變得有可信度。我喜歡每本書的情節既可預測卻又獨樹一格,閱讀起來既舒適又出乎意料。故事既保險又永遠不會無聊。
「晚餐吃披薩好嗎?」老媽站在門口,盯著床頭的海報卻沒有多說什麼。
「這地方有賣披薩?」貝瑞灣的大小看起來不像是可以叫外送的樣子。果然,這裡沒有這種服務,所以我們開車到了一間叫「披薩披薩」的外賣店,它就座落鎮上唯二兩間超市的其中一間的角落。
「這裡住了多少人?」我問媽。當時是晚上七點,但主要街道上大多數的商家看起來都已經關門了。
「大約一千兩百人,不過我想一但到了夏天,來這裡度假的人應該會讓人數翻個三倍左右。」她說。除了一個擠滿了人的餐廳露臺外,小鎮上幾乎空無一人。
「酒館八成是週六夜晚最熱鬧的好去處。」當我們經過時,她邊放慢車速邊評論道。
「八成是唯一的去處。」我回答。
我們回到小木屋的時候,老爸已經把小電視安裝好。沒有第四臺可以看,但我們將整個家的DVD收藏全都打包來了。
「我想看《荒野大進擊》,」爸說。「非常切合時宜,對吧,小鬼?」
「嗯⋯⋯」我蹲下來查看櫃子裡的選擇。「《厄夜叢林》也很適合。」
「我才不要看那個。」老媽一邊在茶几上的披薩盒旁擺上盤子和餐巾紙,一邊說。
「那就是《荒野大進擊》了。」爸一邊把它放進播放器裡,一邊說。「約翰・坎迪的經典之作,還有什麼能比這個更好呢?」
外頭開始起風,松樹枝隨之擺動,湖面也漸漸掀起漣漪。微風從窗戶吹入,聞起來像是下雨的味道。
「是啊,」我咬了一口披薩。「的確還不賴。」
***
一道閃電劃過天空,照亮了松樹、湖泊和遠岸的山丘,像是有人用一臺巨大相機的閃光燈拍了照片般。我在臥室窗邊怔怔地望著暴風雨。這裡的景色,比起我在多倫多房間裡被窗框給楔住的天空還要遼闊許多;雷聲如此巨大,感覺像落在小木屋的正上方,彷彿是為了我們在這裡的第一晚所特別預定的排程。震耳欲聾的擊打聲最終逐漸轉為遙遠的轟隆聲,我回到床上,聽著雨水敲打窗戶。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看到窗外投射進來的明亮陽光,以及在天花板上移動的
光影,使我在一時之間感到困惑,而此時爸媽已經在樓下。他們坐在那裡,端著咖啡,手裡拿著他們的讀物──爸坐在扶手椅上,手上是《經濟學人》的週報,心不在焉地摸著鬍子;媽坐在廚房櫃檯前的凳子上,翻閱一本厚重的設計雜誌,她那副過大的紅框眼鏡在她鼻尖上試圖找到平衡。
「昨晚有聽到雷聲嗎,小鬼?」爸問。
「要錯過也是不容易。」我說著,從幾乎空無一物的櫥櫃裡抓了一盒麥片。「我覺得我沒睡好。」
早餐後,我把帆布托特包裝滿──一本小說、幾本雜誌、護脣膏,和一支防曬係數45的防曬乳──然後走到湖邊。雖然前一天晚上才剛下過大雨,但在早晨的陽光下,碼頭已經乾了。
我把毛巾鋪在地上,把防曬乳塗滿整張臉,然後趴下,用雙手撐著頭。在大約一百五十公尺的距離內沒有其他的碼頭在這一側,倒是對面的碼頭還相對較接近一些。碼頭上綁著一艘划艇,在更遠處還有一艘木筏漂浮在水面上。我拿出我的平裝小說,從前一天晚上讀到的地方接下去讀。
我一定是睡著了,因為我突然被巨大的落水聲和男孩們的歡笑聲給驚醒。
「我一定會抓到你!」其中一個男孩喊著。
「你做夢比較快!」一個更深沉的聲音嘲笑他。
撲通!
兩顆頭探出水面,在鄰居的木筏旁載浮載沉。我仍然趴著,看著他們爬上木筏再輪流跳入湖中,做著各種騰空翻滾和跳水的動作。才七月初,他們倆都已經曬成古銅色了。我猜他們是兄弟,那個瘦瘦的小男孩可能和我差不多大。大一點的男孩比他高出一顆頭,隱約能透過陰影看出他上半身與手臂上瘦瘦的肌肉。當他把那個小男孩扛在肩膀上扔進水裡時,我坐起身來大笑。直到那時,他們才注意到我,而現在大男孩笑著朝我這邊看了過來。小男孩爬到他旁邊的木筏上。
「嘿!」大男孩揮著手喊道。
「嗨!」我喊了回去。
「新鄰居?」他問。
「對啊。」我大聲回應。
小男孩看著我,直到大男孩撞了撞他的肩膀。
「天啊,山姆。打招呼啊。」
山姆舉起手,盯著我,然後又被大男孩推回湖裡。
***
佛洛萊克兄弟花了八個小時才找到我。在洗完晚餐的碗盤後,我坐回書桌前繼續讀著書,直到我聽見有人敲門。我拉長脖子,但還是看不見老媽在跟誰說話,於是我將書籤塞進書中,然後從折疊椅上跳起。
「稍早前,我們在您的碼頭邊看見一個女孩,我們想過來和她打聲招呼。」聲音來自一名青少年男孩,聽起來有些低沉但仍非常年輕。「在附近一帶,都沒有與我弟弟年齡相仿的人可以和他一起玩。」
「一起玩?我又不是小孩子。」另一個男孩開口回應,他的聲音因爲惱怒而有點分岔。
媽媽轉過頭瞇起眼睛,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波瑟芬,有人找妳。」她說,語氣表明了她對這件事並不是太高興。
我走出門外,關上紗門,抬頭看著我白天見過的那兩個棕黃頭髮、在湖中游泳的男孩。他們很明顯是兄弟──兩人都身材瘦長,且膚色黝黑──但他們的相異之處也同樣顯著。大男孩滿面笑容,整個人乾淨俐落,顯然知道如何使用造型髮膠,而小男孩則是盯著自己的腳,波浪般的頭髮隨意地垂落在眼睛上。他穿著寬鬆的工裝短褲和一件褪色的威瑟樂團T恤,那件衣服至少比他還要大一號;大男孩則穿著牛仔褲、合身的白色圓領T恤和一雙黑色的Converse布鞋,橡膠製的鞋頭潔白無瑕。
「嗨,波瑟芬,我是查理。」年紀較大的男孩說道,深邃的酒窩和翠綠色的雙眼在我的面前跳躍。真可愛。像男子團體的那種可愛。「這是我弟弟,山姆。」他把手放在弟弟的肩膀上。山姆用被頭髮遮住的臉龐害羞地給了我半個微笑,然後又再度低下頭。我想以他的年紀而言,他算是高個子,但由於太過於瘦弱,導致手臂和雙腿看起來就像樹枝一般纖細,手肘和膝蓋則像鋸齒狀的岩石一樣鋒利。他的雙腳看起來隨時有跌倒的風險。
「呃⋯⋯嗨,」我開口,在他們倆之間來回望著。「我想我今天在湖邊有看到你們。」
「答對了,就是我們。」查理說,山姆則踢著地上的松針。「我們就住在隔壁。」
「你是說,一直都住在這裡?」我提出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
「全年不間斷。」他證實。
「我們來自多倫多,所以這裡的一切,」我手比畫著周圍的灌木叢。「對我來說很新奇。你們能住在這裡真幸運。」
山姆哼了一聲,但查理無視他,繼續說道。
「既然如此,我和山姆很樂意帶妳四處逛逛。對吧,山姆?」他問弟弟,沒有等待對方回答。「妳也隨時可以使用我們的木筏,我們不介意。」他仍然面帶微笑地說。他說起話來像個自信的成年人。
「酷,我一定會用的,謝謝。」我害羞地回了他一個微笑。
「聽著,我想請妳幫個忙。」查理神祕兮兮地說。山姆在他沙黃色頭髮的掩蓋下呻吟了一聲。「今晚有幾個我的朋友會過來,我想讓山姆和妳待在一起,直到他們離開。他沒什麼社交生活,而且你們看起來年齡差不多。」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我十三歲。」我回答,瞥了一眼山姆,看他對這個提議是否有任何看法,但他仍然在觀察地面。或者也可能是在看他那雙堪比潛水艇大小的腳掌。
太完美了。」查理邊彈舌邊說。「山姆也十三歲。我十五歲。」他自豪地補充。
「還真是恭喜。」山姆咕噥了一句。
查理繼續說道。「總之,波瑟芬⋯⋯」
「波西。」我打斷他。查理給了我一個好笑的表情。我緊張地笑了一下,轉動著手腕上戴的友誼手環,向他們解釋:「叫我波西就好。波瑟芬⋯⋯這個名字太長了。而且聽起來有點做作。」山姆在這個時候挺起身,皺起眉頭和鼻子看了我一眼。他的長相平凡,沒有任何特別吸引人的特徵,除了他那雙驚人的天空藍眼睛。
「那就叫妳波西吧。」查理同意了,但我的注意力仍然在山姆身上,他歪著頭看著我。查理清了清嗓子。「所以,正如我所說,如果晚上妳可以娛樂一下我的弟弟,那真的會幫我一個大忙。」
山姆低聲喊著「老天」時,我也同時脫口問出:「娛樂一下?」我們互相眨了眨眼。我將身體重量轉換到另外一隻腳上,不知道該說什麼。在我因為徹底冒犯了黛莉拉・梅森導致再也沒有朋友之後,已經過了幾個月,距離我上一次和同齡人相處也同樣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了。但現在我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就是讓山姆被迫和我待在一塊。就在我開口之前,他搶先一步。
「如果妳不想的話,也不用勉強。」他聽起來很抱歉。「他只是想趁我媽不在家的時候把我打發走。」查理在他胸口上揍了一拳。
老實說,我非常想要有一個朋友,更勝於讓我的瀏海乖乖聽話。如果山姆願意的話,我不介意有個同伴。
「我並不介意。」我告訴他,並虛張聲勢地補充道:「我的意思是,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負擔。所以你可以選一個你在木筏上做的那些空翻跳躍的動作來教我,當作是回報。」他給了我一個歪斜的微笑。它是一個安靜的微笑,但也是一個很棒的微笑,他的藍色眼睛像海玻璃一樣,在他陽光的皮膚上閃閃發光。
我做到了。我心想,一股興奮的感覺貫穿了我。我想再做一次。
第三章
現在
年輕時候的我大概會不可置信,但我名下沒有半輛車。在當時,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四輪轎車,如此一來我才得以盡可能在每個週末往北邊跑。如今,我的生活侷限於多倫多西區一塊綠樹成蔭的區域,也就是我的住處,以及市中心,那裡則是我的工作地點。我可以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達辦公室、健身房,或是我父母住的公寓。
我有一些朋友甚至連駕照都懶得去考;他們總是吹噓自己從沒有去過布魯亞街以北之外的地方。他們的整個世界都被限制在一個時尚的小型城市泡泡裡,並且以此為傲。我的世界也是這樣,但有時候我會感到窒息。
事實上,自從我在十三歲時愛上了湖泊、小木屋和灌木叢之後,城市就從未真正有家的感覺。然而,大多數時候,我都不允許自己去想它。我沒有時間可以想。我為自己建造的世界充斥著忙碌的城市陷阱──工作到深夜、飛輪單車課程,以及數不清的早午餐。這就是我希望的樣子。一份過度庸碌的行事曆能夠使我感到快樂。但偶爾我會發現自己幻想著能夠離開城市──在水畔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寫作,在餐廳找份打工以支付生活開銷──而我會突然變得全身緊繃,感覺自己找不到容身之處。
這大概會讓幾乎所有認識我的人感到驚訝。我是一名三十歲的女子,通常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方面總是得心應手。我的住處是一間位於朗士華街區的高樓頂層公寓,在附近的波蘭社區裡還吃得到相當不錯的波蘭餃。公寓空間的特色顯著,裸露的橫梁和傾斜的天花板,雖然確實很小,但在這座城市的這一帶,要擁有一間完整的單人公寓可不便宜,而我在《避風港》雜誌的薪水只能稱得上是⋯⋯微薄。好吧,是低得不像話。但這是媒體業的普遍通病,雖然我的薪水可能少,但我的工作卻很重要。
我在《避風港》工作了四年,從編輯助理穩紮穩打地一路晉升到資深編輯的位置。這使我擁有話語權,可以負責分配報導,並實際監督這個國家最大的居家雜誌的拍攝現場。我們能在社交媒體上累積一票忠實的粉絲以及龐大的線上受眾,也多半歸功於我的努力。這是我熱愛且擅長的工作,而在《避風港》四十週年慶典上,雜誌社的總編輯布蘭達對我讚譽有加,表揚我讓這份出版品成功闖進數位時代。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大亮點。
編輯是一個會被大眾定義為光鮮亮麗的職業。它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與快速的潮流並駕齊驅,但若要說實話,大部分的工作內容其實都是坐在辦公室隔間裡,整天用Google搜尋「極簡主義者」的同義代名詞。不過,編輯有時候也能出席產品發表會,還有獲得與新興設計師共進午餐的機會。這個工作同時也是那種會讓炙手可熱的企業律師或試圖躋身上流社會的銀行家在約會軟體上往右滑的對象,這一點在我想要尋找能夠攜伴參加一連串雞尾酒會的對象時,確實滿有用的。這個工作的福利也不少,例如可以參與新聞發佈會和開香檳,以及獲取數量驚人的免費贈品。當然還有源源不斷的業界八卦供我和襄妲咀嚼,這是我們在禮拜四晚上最喜歡的消遣。(還有,我媽對於一直在雜誌刊頭上看見波瑟芬・費雪這個名字樂此不疲。)
查理的來電就像一把斧頭,將我的泡泡摧毀殆盡,而我對於要重新北上一事焦慮不已,以致於在我通話結束後,立刻租訂了一輛車以及明晚的一間旅館房間,即使告別式還有幾日之遙。我彷彿從一場十二年的昏迷當中清醒,而我的頭則因為期待與恐懼同時出現而陣痛。
我會見到山姆。
***
我坐下來寫了封電子郵件給爸媽,告訴他們關於蘇的事情。他們在這趟歐洲度假旅遊期間並沒有定期查看他們的信箱,所以我不確定他們什麼時候會收到。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還和蘇有聯絡。在我和山姆「分手」後,我媽和蘇都還一直保持聯繫少說好幾年,但只要她一提到佛洛萊克家的任何一個人,淚水都會溢出我的眼框。最後,她不再向我提到他們的消息。
我儘量長話短說,並在寫完信後把一些衣服扔進那個我雖然負擔不起但還是買了下來的日默瓦行李箱裡。現在已經是深夜了,我早上還有一場面試,接著還要長途駕駛,於是我換上睡衣,躺下來,閉上眼睛。但是,我輾轉難眠。
當我沉浸在懷舊的情緒裡時,我總是會回想起這樣的一些時刻,而我只想要和山姆一起蜷縮在過去的回憶裡。我可以把它們當成以前的家庭錄影帶一樣在腦海中播放。在大學期間,我把這個行為當作是睡前的例行公事,就像那條我從小木屋帶來,且已經起了毛球的哈德遜灣百貨毛毯一樣令人熟悉。但這些記憶和它們所承載的遺憾,全都和毯子的羊毛一起摩擦著我,我會在夜裡失眠,想著山姆,想知道在此時此刻,他有沒有可能也在想我。有時候,我相信他確實在想我──彷彿有一條隱形且不會斷裂的線,跨越十萬八千里,將我們彼此相連。其他時候,我在昏沉中入睡,在凌晨時分醒來,感覺我的肺快要崩塌般,不得不靠調整紊亂的呼吸來緩解恐慌症發作。
最後,在學期即將結束之際,我成功關閉這些深夜的混亂頻率,用即將到來的考試、報告截止日,以及實習申請將我的大腦填滿,我的恐慌症也開始漸緩。
今晚,我沒有這些限制來綁住自己。我在腦海中喚醒了我們的那些第一次──第一次見面,第一次親吻,山姆第一次告訴我他愛我──而就在我意識到自己即將與他見面這件事逐漸變得真實,我的思緒便開始變成一場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漩渦。他對我的出現會有什麼反應?他改變了多少?他還是單身嗎?或者,哦幹,他結婚了嗎?
我的心理諮商師珍妮佛──千萬不要叫她小珍,我曾犯過一次這樣的錯誤而被她嚴厲指正──是個會在她的牆上掛滿標語和心靈雞湯的女子(「人生在喝過咖啡之後才開始」、「我並不奇怪,而是限量版」),所以我也不是很確定
現在
第四杯雞尾酒在當時看起來是個好主意。現在回想起來,剪瀏海似乎也是如此。但如今我站在公寓房門口掙扎著將鑰匙插入鎖孔,不禁開始懷疑,自己在明天早上醒來時,八成會後悔將最後那杯氣泡調酒喝下肚。也許瀏海也是個錯誤。今天我坐在珍的椅子上剪頭髮時,她還特別提醒我,分手瀏海十之八九會是個糟糕透頂的決定。可是珍今晚不需要以剛剛恢復單身的狀態去參加她朋友的訂婚派對。這瀏海是剪定了。
我會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我還愛著前男友;我沒有。我從來沒有愛過他。賽巴斯丁是個虛榮的勢利鬼。作為一個前途無可限量的企業律師,若是也讓他來參加襄妲的派對,用不上一小時,他就會開始嘲笑她精心挑選的招牌調酒,並引述《紐約時報》上刊登的某篇自以為是的文章,大聲嚷嚷著「阿佩羅雞尾酒過時了」。反之,他八成會假裝認真研究酒單,詢問調酒師一些關於風土條件和酸度的煩人問題,然後不管對方給的答案是什麼,他都會點那杯最貴的紅酒。他並非品味出眾或對葡萄酒有什麼深入的研究,他只是利用昂貴奢侈的花費來營造自己擁有獨到眼光的假象。
賽巴斯丁和我在一起七個月,創下了我這輩子迄今為止最長戀情的記錄。最後,他說他「並不是真的認識我」。他說得有道理。
在賽巴斯丁之前,我挑選的對象都只是為了及時行樂,他們對於保持輕鬆的交往關係也都沒什麼意見。當我遇見他的時候,我便想,作為一位成熟的大人,就代表自己應該找一位可以穩定發展的對象了。而賽巴斯丁符合我的標準。他非常有吸引力、博學多聞、功成名就,雖然有點傲慢自大,但他幾乎能和任何人聊任何話題。但我仍然很難和他分享過於真實的自己。我很早以前就學會將各種零碎的想法給壓抑下來,並三思而後言。我以為自己已經很努力在給這段感情一個真正的機會,但最後賽巴斯丁察覺到我的漠不關心,他是對的。我不在乎他。我不曾在乎過他們任何人。
只有一個。
一個早已離我遠去的人。
於是我流連於男人之間,我也同時耽溺於性愛為我降下的心靈逃生梯。我喜歡逗男人歡心,我喜歡有人陪伴,我喜歡可以暫時不用按摩棒來滿足自己,但是我不會因此就一時意亂情迷,也不會持續與對方深交。
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用鑰匙打開公寓的門──別鬧了,這鎖孔到底有什麼毛病──而就在此時,我皮包裡的手機響了。太詭異了。沒有人會在這麼晚的時間打給我。事實上,根本不會有人會想打電話給我,除了襄妲和我的爸媽之外。但是襄妲應該還在結婚派對上,而爸和媽跑去布拉格旅遊了,這時間他們根本還沒醒。就在我終於打開門,並跌跌撞撞地進入了我的小單人房裡時,手機也停止了震動。我看向門口的鏡子,發現自己的口紅雖然糊了,但瀏海卻美得不可開交。滾一邊去吧,珍!
我開始脫掉腳上的金色羅馬鞋,一縷深色髮絲垂落我臉旁;此時,我的手機又響了。我從包裡挖出手機,只脫掉了其中一支鞋,邊往沙發的方向移動,邊皺著眉看著螢幕上顯示「未知號碼」。對方大概是打錯了。
「喂?」我邊說,邊彎腰脫掉另一支鞋。
「是波西嗎?」
我整個身子彈起的速度太快,以致於不得不扶著沙發扶手來穩住腳步。波西。已經沒有人會用這個名字稱呼我了。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叫我波瑟芬。有時後,他們會直接叫我「波」。但絕對不會是波西。我已經不叫波西很多年了。
「喂……波西?」那聲音深沉而柔和,是我已經十幾年未曾聽見的聲音。但它是如此熟悉,使我在一瞬間回到了全身塗滿防曬係數45的防曬乳,並躺在碼頭邊讀著平裝書的十三歲。然後是十六歲,從酒館下班後就脫光衣服跳進湖裡,全身赤裸且黏答答的我。十七歲,穿著溼漉漉的泳衣躺在山姆床上的我,看著在我腳邊的他,用修長的指尖滑過他正在苦讀的解剖學教科書。一股熱浪迎頭撞上我的臉頰,我的心跳聲厚重且堅定地充斥在我的耳膜內,隆隆作響。我顫抖著吸了口氣,坐了下來,胃袋緊縮。
「我是。」我勉強回答。對方吐了一口悠長且放鬆的氣。
「是我,查理。」
查理。
不是山姆。
查理。兩兄弟裡不對的那一個。
「查爾斯・佛洛萊克。」查理聲明,並開始解釋他是如何取得我的電話號碼──什麼某個朋友的朋友,以及那個誰認識我目前工作的雜誌社之類的──但我根本聽得心不在焉。
「查理?」我打斷他,聲音尖銳且緊繃,有一部分是因為雞尾酒,但更多的是來自震驚。又或者,完全是出自於失望。因為這個聲音不是山姆的。
它當然不會是山姆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老天,我甚至不知道有多久。」他說,聽起來像是在道歉。
但我很清楚。我完全知道過了多久。我一直沒有停止計算。
我上次見到查理,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十二年前,在那個災難般的感恩節周末,在我與山姆之間的一切都崩潰之後。在我毀了一切之後。
我曾經期待家人前往別墅度假的日子,這樣我便可以再次見到山姆。現在他變成了一個痛苦的記憶,被我深深地埋藏在肋骨之下。
我也知道,我離開山姆的時間比和他在一起的時間更長。在距離我和他最後一次交談滿七年的感恩節當天,我第一次恐慌症發作,然後灌下了一瓶半的粉紅酒。我和他一起在湖畔的時光,已經正式被我離開他的時間所超越,感覺就像是跨越了一個里程碑。我哭得花容失色,上氣不接下氣,倒在浴室的地板上昏了過去。第二天,襄妲外帶了一些油膩的食物登門,替我在嘔吐的時候抓住頭髮,我滿面淚水,將一切都告訴她。
「彷彿已經過了一輩子。」我告訴查理。
「我知道,也很抱歉在這麼晚打給妳。」他說。他的聲音聽起來太像山姆了,這使我非常難受,彷彿骨鯁在喉。我記得我們十四歲時,要在電話中辨別出他和查理的聲音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我也記得那個夏天,我注意到一些其他與山姆有關的事。
「聽著,小波,我會打來是因為有件事情,」他用他以前暱稱我的方式叫我,然而語氣卻比我認識的查理嚴肅許多。我聽見他吸了吸鼻子。「我媽媽在幾天前去世了,我想……我想妳應該會想知道。」
他的話像海嘯一般朝我襲來,在一時半刻之間我還沒辦法立刻全然理解。蘇還很年輕啊。
我只能發出一聲破碎的「什麼?」。
查理在回答時聽起來很疲憊。「是癌症。她已經和它纏鬥了好幾年。我們當然傷心欲絕,但她已經厭倦了病懨懨的自己,妳懂嗎?」
這已經不是我頭一次感覺有人偷走了我人生故事的劇本,然後把它改寫得面目全非。蘇會生病這件事簡直難以置信。總是掛著大大的笑容、穿著牛仔短褲,將她的白金秀髮紮成馬尾的蘇。全世界最會做波蘭餃的蘇。把我當成女兒對待的蘇。我曾經夢想有一天會成為我婆婆的蘇。疾病纏身多年卻將我蒙在鼓裡的蘇。我應該要知道的。我應該要在她身邊的。
「我實在非常,非常抱歉,」我開口。「我……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你媽媽……她……」我聽起來很慌張,我自己都感覺得到。
振作點,我對自己說。妳早就失去了擁有蘇的權利。妳現在沒有資格崩潰。
我想起蘇獨自撫養兩個男孩,同時經營著酒館,以及我第一次見到她時的情景。當時她來到別墅,向年紀大她很多的我父母保證山姆是個好孩子,她也會好好看著我們。我記得她教會我如何一次端三個盤子,還有告訴我對於任何男孩的欺負都不要忍氣吞聲,包括她自己的兩個兒子。
「她是⋯⋯她是一切。」我說。「她是一個多麼稱職的母親。」
「她的確是。我也知道在我們都還只是孩子的時候,她對妳的意義有多重大。這也是我打電話給妳的原因,」查理猶豫了片刻。「她的告別式會在這週日舉行。我知道已經過了很久,不過我想妳應該來一趟。妳願意出席嗎?」
過了很久?已經過了十二年。距離我上次驅車北上,去到那個比任何地方都更像家的歸屬之地,已經過了十二年。距離上一次我頭朝下跳入湖水裡,已經過了十二年。已經十二年了,我的生活從此翻天覆地。已經十二年了,我沒再見過山姆一眼。
但是答案只有一種。
「我當然願意。」
第二章
夏天,十七年前
我覺得爸媽在買下別墅的時候,並不知道隔壁住著兩個青少年男孩。爸媽希望能讓我遠離城市的喧囂,遠離同齡的孩子,而佛洛萊克家的兩個男孩──經常整個下午到傍晚都沒人管──的出現讓我出乎意料,他們或許也有同感。
我班上的一些同學家裡也有度假別墅,但都在離市區北上不遠的馬斯科卡區,沿著那裡的岩岸放眼望去,就是一整排的濱海豪宅,把它們稱做「別墅」似乎有些名不副實。老爸直接拒絕將別墅買在馬斯科卡區。他說,如果我們在那裡買一下一棟別墅,還不如乾脆整個夏天都待在多倫多──那裡離市區太近,而且所到之處幾乎全是多倫多人。所以他和老媽把搜尋範圍擴大到東北方更偏遠的郊區,但是老爸又嫌那裡被過度開發或價格過高。於是他們繼續往更北邊尋找,最後選定了貝瑞灣。這個安靜的工人階級村莊,一到夏天就會變成熙熙攘攘的旅遊小鎮,人行道上會擠滿前來度假的旅客,以及打算前往阿岡昆省立公園露營或登山健行的歐洲觀光客。「妳會喜歡那裡的,小鬼,」老爸承諾。「那裡是真正的度假勝地。」
雖然最終我還是會期待從多倫多市中心的都鐸式建築開四小時的車來到湖邊,但第一次的旅程卻彷彿感覺過了一個世紀般漫長。等到我們開車行經「歡迎來到貝瑞灣」的招牌時,我感覺人類文明已經興衰過了好幾輪。老爸和我坐在搬家用的卡車上,老媽則開著家裡那輛Lexus跟在後頭。和老媽的那臺車不同,卡車上既沒有像樣的音響,也沒有空調。我只能聽著加拿大廣播公司單調的悶哼聲,任憑大腿後側黏在人造皮革椅上,瀏海緊貼著我溼透的前額。
幾乎所有在我國一班上的女孩,都因為黛莉拉・梅森剪了瀏海後就一窩蜂地跟隨潮流,儘管那些瀏海並不適合我們所有人。黛莉拉是全年級最受歡迎的女孩,而我認為自己能成為她最親近的朋友之一實屬幸運。或者至少以前是,在睡衣派對事件發生之前。她的瀏海像紅色帷幔整齊地垂掛在額頭上,而我的瀏海則像是同時違背了地心引力和造型產品般,以奇怪的角度鼓脹分岔,讓我看起來像個愚鈍的十三歲女孩,而非我一直想成為的神祕黑眼棕髮少女。我的頭髮既不直也不鬈,並且它似乎會根據一系列不可預測的因素改變個性,從今天星期幾到天氣狀況,甚至是前一天晚上睡覺的方式也包含在內。即便我會盡一切所能討他人歡心,但我的頭髮卻不願意配合。
***
「裸岩巷」蜿蜒在卡曼尼斯克湖西岸蜿蜒的灌木叢中,是一條名副其實的狹窄泥土路。老爸拐進的這條道路被過長的樹葉枝條給霸占,不斷刮著小卡車的兩側。
「小鬼,妳聞到了嗎?」老爸問,並在卡車顛簸前進的同時搖下車窗。我們一起深呼吸,落地許久的松針帶著泥土的氣息,混合著藥草清香,充滿了我的鼻腔。
我們抵達一棟不起眼的A字形小木屋的後門,周圍環繞著白與紅的松樹,使得小屋顯得格外矮小。老爸將引擎熄火,轉過身,在他銀灰色的鬍子下透露出一抹微笑,他的雙眼在黑框眼鏡底下跟著瞇起,對著我說:「歡迎來到湖畔,波瑟芬。」
這棟小木屋別墅裡有一股不可思議的熏木香味。即使老媽多年以來在屋內點著昂貴的Diptyque蠟燭(註一) ,也都不會使這種味道消散。每次回來,我都會站在門口,像第一天來到這裡那樣深呼吸。一樓是一個開放的小空間,從地板到天花板都用淺色的結木板覆蓋。屋內一面巨大的窗戶則將湖泊壯麗到幾乎讓人有點不快的景色充分展現。
「哇。」我喃喃道,並看見一條從露天平臺通往陡峭山坡的階梯。
「還不賴吧?」爸爸拍拍我的肩膀。
「我要去湖邊看看。」我說,已經從側門衝向外頭,門在我身後砰一聲地關上。我飛奔而下幾十道臺階,直到我抵達碼頭邊。這是一個潮溼的下午,厚重的灰色雲層鋪滿整片天空,映照在下方紋風不動的銀色湖面。我幾乎看不見散落在遠處岸邊上的小屋。我好奇自己能不能游得過去。我坐在碼頭邊緣,在水裡擺盪著雙腿,驚訝於這裡的寧靜,直到老媽朝我大聲疾呼,要我幫忙搬行李。
我們在搬箱子的過程中還得不停與蚊子奮戰,結束後所有人都相當疲憊且煩躁。我留下爸媽獨自整理廚房,自己一個人上了樓。樓上有兩間臥室,爸媽把擁有湖景的房間讓給了我,他們的理由是我比起他們更喜歡待在房間裡,可以好好欣賞風景。我整理了行李箱的衣服,鋪了床,並折好一條哈德遜灣百貨(註二) 的毛毯放在床尾。老爸覺得夏天不需要這麼厚重的羊毛毯,但媽堅持每張床上都要有一條。
「這樣才夠加拿大啊。」她解釋,語氣彷彿像在說這種事情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才對。
我在床頭櫃的一側疊滿搖搖欲墜的平裝書,並釘了一張《黑湖妖潭》(註三) 的海報在床頭。我相當著迷於恐怖片。我看過很多恐怖電影,爸媽老早就放棄替我審查內容,我還一口氣讀完了R・L・史坦恩和克里斯多夫・派克(註四) 的經典作品,以及新出的那些關於性感的青少年在滿月時變成狼人,或性感的青少年在啦啦隊訓練結束後化身猛鬼獵人的小說。以前我還有朋友的時候,我會把這些書帶到學校,為她們大聲朗讀精采的部分(例如任何血腥橋段或稍微有點性感的部分)。一開始,我只是喜歡得到女孩們的反應,享受成為目光焦點,但同時又可以利用他人的文字作為娛樂手段,以策人際關係上的安全距離。但讀過的恐怖小說越多,就越喜歡故事背後的創作過程──作者如何將不可能發生的情況變得有可信度。我喜歡每本書的情節既可預測卻又獨樹一格,閱讀起來既舒適又出乎意料。故事既保險又永遠不會無聊。
「晚餐吃披薩好嗎?」老媽站在門口,盯著床頭的海報卻沒有多說什麼。
「這地方有賣披薩?」貝瑞灣的大小看起來不像是可以叫外送的樣子。果然,這裡沒有這種服務,所以我們開車到了一間叫「披薩披薩」的外賣店,它就座落鎮上唯二兩間超市的其中一間的角落。
「這裡住了多少人?」我問媽。當時是晚上七點,但主要街道上大多數的商家看起來都已經關門了。
「大約一千兩百人,不過我想一但到了夏天,來這裡度假的人應該會讓人數翻個三倍左右。」她說。除了一個擠滿了人的餐廳露臺外,小鎮上幾乎空無一人。
「酒館八成是週六夜晚最熱鬧的好去處。」當我們經過時,她邊放慢車速邊評論道。
「八成是唯一的去處。」我回答。
我們回到小木屋的時候,老爸已經把小電視安裝好。沒有第四臺可以看,但我們將整個家的DVD收藏全都打包來了。
「我想看《荒野大進擊》,」爸說。「非常切合時宜,對吧,小鬼?」
「嗯⋯⋯」我蹲下來查看櫃子裡的選擇。「《厄夜叢林》也很適合。」
「我才不要看那個。」老媽一邊在茶几上的披薩盒旁擺上盤子和餐巾紙,一邊說。
「那就是《荒野大進擊》了。」爸一邊把它放進播放器裡,一邊說。「約翰・坎迪的經典之作,還有什麼能比這個更好呢?」
外頭開始起風,松樹枝隨之擺動,湖面也漸漸掀起漣漪。微風從窗戶吹入,聞起來像是下雨的味道。
「是啊,」我咬了一口披薩。「的確還不賴。」
***
一道閃電劃過天空,照亮了松樹、湖泊和遠岸的山丘,像是有人用一臺巨大相機的閃光燈拍了照片般。我在臥室窗邊怔怔地望著暴風雨。這裡的景色,比起我在多倫多房間裡被窗框給楔住的天空還要遼闊許多;雷聲如此巨大,感覺像落在小木屋的正上方,彷彿是為了我們在這裡的第一晚所特別預定的排程。震耳欲聾的擊打聲最終逐漸轉為遙遠的轟隆聲,我回到床上,聽著雨水敲打窗戶。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看到窗外投射進來的明亮陽光,以及在天花板上移動的
光影,使我在一時之間感到困惑,而此時爸媽已經在樓下。他們坐在那裡,端著咖啡,手裡拿著他們的讀物──爸坐在扶手椅上,手上是《經濟學人》的週報,心不在焉地摸著鬍子;媽坐在廚房櫃檯前的凳子上,翻閱一本厚重的設計雜誌,她那副過大的紅框眼鏡在她鼻尖上試圖找到平衡。
「昨晚有聽到雷聲嗎,小鬼?」爸問。
「要錯過也是不容易。」我說著,從幾乎空無一物的櫥櫃裡抓了一盒麥片。「我覺得我沒睡好。」
早餐後,我把帆布托特包裝滿──一本小說、幾本雜誌、護脣膏,和一支防曬係數45的防曬乳──然後走到湖邊。雖然前一天晚上才剛下過大雨,但在早晨的陽光下,碼頭已經乾了。
我把毛巾鋪在地上,把防曬乳塗滿整張臉,然後趴下,用雙手撐著頭。在大約一百五十公尺的距離內沒有其他的碼頭在這一側,倒是對面的碼頭還相對較接近一些。碼頭上綁著一艘划艇,在更遠處還有一艘木筏漂浮在水面上。我拿出我的平裝小說,從前一天晚上讀到的地方接下去讀。
我一定是睡著了,因為我突然被巨大的落水聲和男孩們的歡笑聲給驚醒。
「我一定會抓到你!」其中一個男孩喊著。
「你做夢比較快!」一個更深沉的聲音嘲笑他。
撲通!
兩顆頭探出水面,在鄰居的木筏旁載浮載沉。我仍然趴著,看著他們爬上木筏再輪流跳入湖中,做著各種騰空翻滾和跳水的動作。才七月初,他們倆都已經曬成古銅色了。我猜他們是兄弟,那個瘦瘦的小男孩可能和我差不多大。大一點的男孩比他高出一顆頭,隱約能透過陰影看出他上半身與手臂上瘦瘦的肌肉。當他把那個小男孩扛在肩膀上扔進水裡時,我坐起身來大笑。直到那時,他們才注意到我,而現在大男孩笑著朝我這邊看了過來。小男孩爬到他旁邊的木筏上。
「嘿!」大男孩揮著手喊道。
「嗨!」我喊了回去。
「新鄰居?」他問。
「對啊。」我大聲回應。
小男孩看著我,直到大男孩撞了撞他的肩膀。
「天啊,山姆。打招呼啊。」
山姆舉起手,盯著我,然後又被大男孩推回湖裡。
***
佛洛萊克兄弟花了八個小時才找到我。在洗完晚餐的碗盤後,我坐回書桌前繼續讀著書,直到我聽見有人敲門。我拉長脖子,但還是看不見老媽在跟誰說話,於是我將書籤塞進書中,然後從折疊椅上跳起。
「稍早前,我們在您的碼頭邊看見一個女孩,我們想過來和她打聲招呼。」聲音來自一名青少年男孩,聽起來有些低沉但仍非常年輕。「在附近一帶,都沒有與我弟弟年齡相仿的人可以和他一起玩。」
「一起玩?我又不是小孩子。」另一個男孩開口回應,他的聲音因爲惱怒而有點分岔。
媽媽轉過頭瞇起眼睛,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波瑟芬,有人找妳。」她說,語氣表明了她對這件事並不是太高興。
我走出門外,關上紗門,抬頭看著我白天見過的那兩個棕黃頭髮、在湖中游泳的男孩。他們很明顯是兄弟──兩人都身材瘦長,且膚色黝黑──但他們的相異之處也同樣顯著。大男孩滿面笑容,整個人乾淨俐落,顯然知道如何使用造型髮膠,而小男孩則是盯著自己的腳,波浪般的頭髮隨意地垂落在眼睛上。他穿著寬鬆的工裝短褲和一件褪色的威瑟樂團T恤,那件衣服至少比他還要大一號;大男孩則穿著牛仔褲、合身的白色圓領T恤和一雙黑色的Converse布鞋,橡膠製的鞋頭潔白無瑕。
「嗨,波瑟芬,我是查理。」年紀較大的男孩說道,深邃的酒窩和翠綠色的雙眼在我的面前跳躍。真可愛。像男子團體的那種可愛。「這是我弟弟,山姆。」他把手放在弟弟的肩膀上。山姆用被頭髮遮住的臉龐害羞地給了我半個微笑,然後又再度低下頭。我想以他的年紀而言,他算是高個子,但由於太過於瘦弱,導致手臂和雙腿看起來就像樹枝一般纖細,手肘和膝蓋則像鋸齒狀的岩石一樣鋒利。他的雙腳看起來隨時有跌倒的風險。
「呃⋯⋯嗨,」我開口,在他們倆之間來回望著。「我想我今天在湖邊有看到你們。」
「答對了,就是我們。」查理說,山姆則踢著地上的松針。「我們就住在隔壁。」
「你是說,一直都住在這裡?」我提出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
「全年不間斷。」他證實。
「我們來自多倫多,所以這裡的一切,」我手比畫著周圍的灌木叢。「對我來說很新奇。你們能住在這裡真幸運。」
山姆哼了一聲,但查理無視他,繼續說道。
「既然如此,我和山姆很樂意帶妳四處逛逛。對吧,山姆?」他問弟弟,沒有等待對方回答。「妳也隨時可以使用我們的木筏,我們不介意。」他仍然面帶微笑地說。他說起話來像個自信的成年人。
「酷,我一定會用的,謝謝。」我害羞地回了他一個微笑。
「聽著,我想請妳幫個忙。」查理神祕兮兮地說。山姆在他沙黃色頭髮的掩蓋下呻吟了一聲。「今晚有幾個我的朋友會過來,我想讓山姆和妳待在一起,直到他們離開。他沒什麼社交生活,而且你們看起來年齡差不多。」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我十三歲。」我回答,瞥了一眼山姆,看他對這個提議是否有任何看法,但他仍然在觀察地面。或者也可能是在看他那雙堪比潛水艇大小的腳掌。
太完美了。」查理邊彈舌邊說。「山姆也十三歲。我十五歲。」他自豪地補充。
「還真是恭喜。」山姆咕噥了一句。
查理繼續說道。「總之,波瑟芬⋯⋯」
「波西。」我打斷他。查理給了我一個好笑的表情。我緊張地笑了一下,轉動著手腕上戴的友誼手環,向他們解釋:「叫我波西就好。波瑟芬⋯⋯這個名字太長了。而且聽起來有點做作。」山姆在這個時候挺起身,皺起眉頭和鼻子看了我一眼。他的長相平凡,沒有任何特別吸引人的特徵,除了他那雙驚人的天空藍眼睛。
「那就叫妳波西吧。」查理同意了,但我的注意力仍然在山姆身上,他歪著頭看著我。查理清了清嗓子。「所以,正如我所說,如果晚上妳可以娛樂一下我的弟弟,那真的會幫我一個大忙。」
山姆低聲喊著「老天」時,我也同時脫口問出:「娛樂一下?」我們互相眨了眨眼。我將身體重量轉換到另外一隻腳上,不知道該說什麼。在我因為徹底冒犯了黛莉拉・梅森導致再也沒有朋友之後,已經過了幾個月,距離我上一次和同齡人相處也同樣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了。但現在我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就是讓山姆被迫和我待在一塊。就在我開口之前,他搶先一步。
「如果妳不想的話,也不用勉強。」他聽起來很抱歉。「他只是想趁我媽不在家的時候把我打發走。」查理在他胸口上揍了一拳。
老實說,我非常想要有一個朋友,更勝於讓我的瀏海乖乖聽話。如果山姆願意的話,我不介意有個同伴。
「我並不介意。」我告訴他,並虛張聲勢地補充道:「我的意思是,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負擔。所以你可以選一個你在木筏上做的那些空翻跳躍的動作來教我,當作是回報。」他給了我一個歪斜的微笑。它是一個安靜的微笑,但也是一個很棒的微笑,他的藍色眼睛像海玻璃一樣,在他陽光的皮膚上閃閃發光。
我做到了。我心想,一股興奮的感覺貫穿了我。我想再做一次。
第三章
現在
年輕時候的我大概會不可置信,但我名下沒有半輛車。在當時,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擁有一輛屬於自己的四輪轎車,如此一來我才得以盡可能在每個週末往北邊跑。如今,我的生活侷限於多倫多西區一塊綠樹成蔭的區域,也就是我的住處,以及市中心,那裡則是我的工作地點。我可以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達辦公室、健身房,或是我父母住的公寓。
我有一些朋友甚至連駕照都懶得去考;他們總是吹噓自己從沒有去過布魯亞街以北之外的地方。他們的整個世界都被限制在一個時尚的小型城市泡泡裡,並且以此為傲。我的世界也是這樣,但有時候我會感到窒息。
事實上,自從我在十三歲時愛上了湖泊、小木屋和灌木叢之後,城市就從未真正有家的感覺。然而,大多數時候,我都不允許自己去想它。我沒有時間可以想。我為自己建造的世界充斥著忙碌的城市陷阱──工作到深夜、飛輪單車課程,以及數不清的早午餐。這就是我希望的樣子。一份過度庸碌的行事曆能夠使我感到快樂。但偶爾我會發現自己幻想著能夠離開城市──在水畔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寫作,在餐廳找份打工以支付生活開銷──而我會突然變得全身緊繃,感覺自己找不到容身之處。
這大概會讓幾乎所有認識我的人感到驚訝。我是一名三十歲的女子,通常在處理生活大小事方面總是得心應手。我的住處是一間位於朗士華街區的高樓頂層公寓,在附近的波蘭社區裡還吃得到相當不錯的波蘭餃。公寓空間的特色顯著,裸露的橫梁和傾斜的天花板,雖然確實很小,但在這座城市的這一帶,要擁有一間完整的單人公寓可不便宜,而我在《避風港》雜誌的薪水只能稱得上是⋯⋯微薄。好吧,是低得不像話。但這是媒體業的普遍通病,雖然我的薪水可能少,但我的工作卻很重要。
我在《避風港》工作了四年,從編輯助理穩紮穩打地一路晉升到資深編輯的位置。這使我擁有話語權,可以負責分配報導,並實際監督這個國家最大的居家雜誌的拍攝現場。我們能在社交媒體上累積一票忠實的粉絲以及龐大的線上受眾,也多半歸功於我的努力。這是我熱愛且擅長的工作,而在《避風港》四十週年慶典上,雜誌社的總編輯布蘭達對我讚譽有加,表揚我讓這份出版品成功闖進數位時代。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大亮點。
編輯是一個會被大眾定義為光鮮亮麗的職業。它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與快速的潮流並駕齊驅,但若要說實話,大部分的工作內容其實都是坐在辦公室隔間裡,整天用Google搜尋「極簡主義者」的同義代名詞。不過,編輯有時候也能出席產品發表會,還有獲得與新興設計師共進午餐的機會。這個工作同時也是那種會讓炙手可熱的企業律師或試圖躋身上流社會的銀行家在約會軟體上往右滑的對象,這一點在我想要尋找能夠攜伴參加一連串雞尾酒會的對象時,確實滿有用的。這個工作的福利也不少,例如可以參與新聞發佈會和開香檳,以及獲取數量驚人的免費贈品。當然還有源源不斷的業界八卦供我和襄妲咀嚼,這是我們在禮拜四晚上最喜歡的消遣。(還有,我媽對於一直在雜誌刊頭上看見波瑟芬・費雪這個名字樂此不疲。)
查理的來電就像一把斧頭,將我的泡泡摧毀殆盡,而我對於要重新北上一事焦慮不已,以致於在我通話結束後,立刻租訂了一輛車以及明晚的一間旅館房間,即使告別式還有幾日之遙。我彷彿從一場十二年的昏迷當中清醒,而我的頭則因為期待與恐懼同時出現而陣痛。
我會見到山姆。
***
我坐下來寫了封電子郵件給爸媽,告訴他們關於蘇的事情。他們在這趟歐洲度假旅遊期間並沒有定期查看他們的信箱,所以我不確定他們什麼時候會收到。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還和蘇有聯絡。在我和山姆「分手」後,我媽和蘇都還一直保持聯繫少說好幾年,但只要她一提到佛洛萊克家的任何一個人,淚水都會溢出我的眼框。最後,她不再向我提到他們的消息。
我儘量長話短說,並在寫完信後把一些衣服扔進那個我雖然負擔不起但還是買了下來的日默瓦行李箱裡。現在已經是深夜了,我早上還有一場面試,接著還要長途駕駛,於是我換上睡衣,躺下來,閉上眼睛。但是,我輾轉難眠。
當我沉浸在懷舊的情緒裡時,我總是會回想起這樣的一些時刻,而我只想要和山姆一起蜷縮在過去的回憶裡。我可以把它們當成以前的家庭錄影帶一樣在腦海中播放。在大學期間,我把這個行為當作是睡前的例行公事,就像那條我從小木屋帶來,且已經起了毛球的哈德遜灣百貨毛毯一樣令人熟悉。但這些記憶和它們所承載的遺憾,全都和毯子的羊毛一起摩擦著我,我會在夜裡失眠,想著山姆,想知道在此時此刻,他有沒有可能也在想我。有時候,我相信他確實在想我──彷彿有一條隱形且不會斷裂的線,跨越十萬八千里,將我們彼此相連。其他時候,我在昏沉中入睡,在凌晨時分醒來,感覺我的肺快要崩塌般,不得不靠調整紊亂的呼吸來緩解恐慌症發作。
最後,在學期即將結束之際,我成功關閉這些深夜的混亂頻率,用即將到來的考試、報告截止日,以及實習申請將我的大腦填滿,我的恐慌症也開始漸緩。
今晚,我沒有這些限制來綁住自己。我在腦海中喚醒了我們的那些第一次──第一次見面,第一次親吻,山姆第一次告訴我他愛我──而就在我意識到自己即將與他見面這件事逐漸變得真實,我的思緒便開始變成一場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漩渦。他對我的出現會有什麼反應?他改變了多少?他還是單身嗎?或者,哦幹,他結婚了嗎?
我的心理諮商師珍妮佛──千萬不要叫她小珍,我曾犯過一次這樣的錯誤而被她嚴厲指正──是個會在她的牆上掛滿標語和心靈雞湯的女子(「人生在喝過咖啡之後才開始」、「我並不奇怪,而是限量版」),所以我也不是很確定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