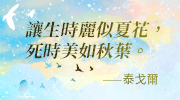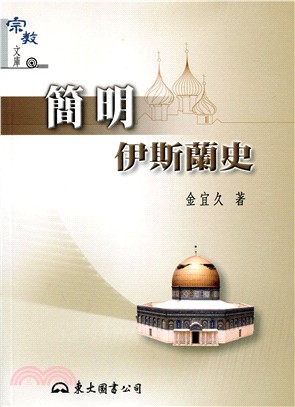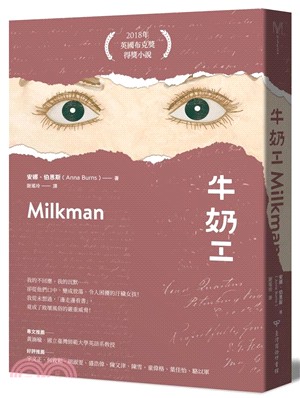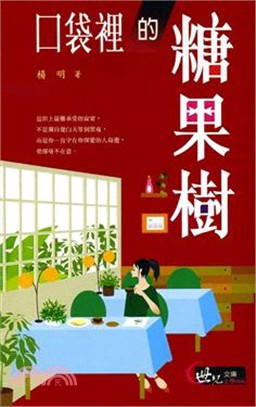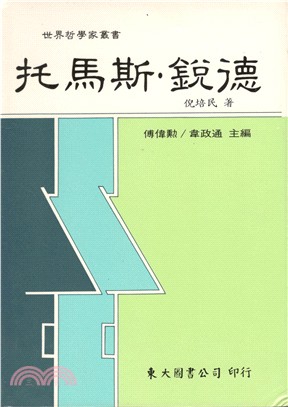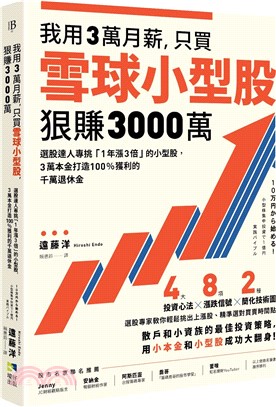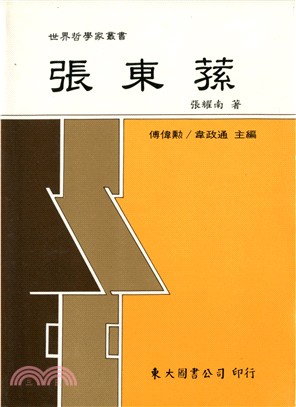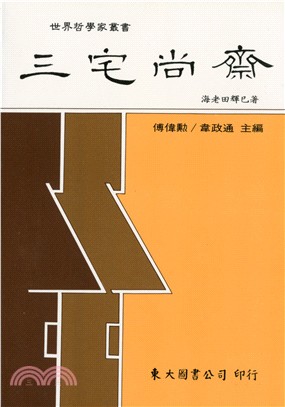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漢斯·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20世紀德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與哈貝馬斯齊名,從古典學入手通過解讀神話、《圣經》、文學文本以重構西方思想史,重視文學感悟與生命籌劃的關系,關注思想歷史的隱喻、象征、修辭等語言維度,試圖為現代奠定正當性基礎。他的著作思想精深,氣魄宏大,主要包括《現代正當性》(1966)、《哥白尼世界的起源》(1975)、《神話研究》(1979)、《馬太受難曲》(1990)等。
名人/編輯推薦
20世紀德國思想巨匠、現代正當性之奠基者——布魯門伯格神話解釋學經典,首度中譯
目次
第一部 源始權力分封 第一章 實在專制主義探源 第二章 命名闖入無名的混沌 第三章 神話孕育意義 第四章 制序化統治權力 第二部 故事向歷史生成 第一章 扭曲的時間境域 第二章 基本神話與藝術神話 第三章 神話與教義 第四章 把神話帶向終結 譯名對照表
書摘/試閱
第四章 把神話帶向終結 故事多多,因此我要揮霍x的故事,揮霍y的故事。 ——司湯達(Stendhal):《亨利?勃呂拉傳》(Henry Brulard) 豐塔納伊在討論神話時表達了啟蒙時代的一個迷惑,那就是古希臘神話仍然沒有煙消云散。確切地說,宗教與理性讓人同神話揖別,但詩歌與繪畫卻給神話以綿延生存的手段。神話便明白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知道如何讓這些藝術須臾不可離開自己。這一說法企圖表達人類的錯誤對于歷史的貢獻。笛卡兒學派的部分計劃也的確在于將神話這個范疇連同整個偏見系統從人類心靈中清除出去。要想理解神話生生不息的活力,似乎是難上加難,因為對于這些頑固偏見的解釋總是不得要領。按照這些頑固的偏見,神話通過人的本質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來取悅于人,阻止人們去獲得更可靠的認識,從而維持自己生生不息的活力。豐塔納伊不僅沒有看到新興自然科學與古代神話之間勢不兩立的排斥關系,而且他還投靠于這么一種假設——由于被賦予了一種合度的表達方式,科學就能夠填補需要系統中因為對于神話的批判而出現的空白。毫無疑問,他沿著“多元世界對話”(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e des mondes)的邏輯考慮過補償這一傳統中一切美的失落。在摧毀這一傳統時,他又在《神諭歷史》(Historie des Oracles, 1686)一書中如此成功地預見了這一失落,而這發生在“多元世界對話”發軔之初。“再度占有”(Umbesetzung),這一基本觀念激勵著豐塔納伊為啟蒙時代發明一種傳道授業的文學體裁,可是這并沒有一以貫之地關注這種體裁所必須服務的外在目標。 基督降生的時刻,古代神諭歸于沉默。在這么一種神話傳說當中,豐塔納伊只看到了一種由祭司們所實施的系統欺騙的計謀。而他的論辯對手則認為,歷史真理之真諦不在于無差別境界。因而,對他而言,創造真理是再也重要不過的事情了;不僅如此,創造真理還讓他欣賞到簡潔之美;同時,還讓他明白,發現歷史意蘊這一基本需要如何在純粹同時性形式的呈現當中得以滿足。但是,豐塔納伊還是左顧右盼,勉為其難地將他的批判邏輯貫徹到底——這一邏輯簡直就是為間接批判基督教而設計出來的。當他的讀者耶穌會士巴爾圖斯(Baltus)作出回應,他并沒有徹底地覺察到其中的隱含的誹謗中傷,以便避免一個辯護者的引誘。他致書萊克勒克(Leclerc)表示,他不想繼續爭論下去,而寧愿說明神諭中的先知畢竟是魔鬼;所以,假如耶穌會士喜歡的話,他們會說,耶穌降生之時,先知魔鬼被迫歸于沉默。 豐塔納伊接受了論辯對手的前提。因為,沒有這樣的前提,神話事件簡直就不值得爭論。他把諸種異教神話與神諭提升為比肩而立而又互相沖突的真理、歷史命題以及“信仰”的等量內容,然后進一步打擊這種自負主張,并間接地抨擊其他一些作類似比較的同伙。而這也就注定了他無法理解,神話在當時的詩歌和藝術中仍然保有地位。他認為,這幾乎就是神話的內容在其自我斷言的努力中所實施的一種慧黠,因為神話內容自我標榜為必要之物的行為顯然就是一種不可言喻的神秘。他仍然不能理解這么一個事實:當我們以為能夠查明神話的“虛幻”之時,首先就沒有與神話拉開距離。距離就呈現在神話當中,作為對其意蘊的接受。通過這么一種呈現,它們使其自身方便審美接受,以至于最后成為一種特殊的審美接受范疇。歌德可能會說:“希臘神話,而非一團亂麻,只能被看做隱含于對象中的潛在藝術主題的展開。” 被美其名曰神話的“偏見”與新興科學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一種彼此競爭的關系。而這么一種識見必將假設,對于個別神話的解釋是因果相推。這就說明,身為巴黎科學院的秘書,豐塔納伊何以能看到,那個時代的啟蒙思想在關于“閃電”本質的解釋上占了上風。在他之前,早有一種全局性信念支配著對這些自然現象的看法,他將這些信念形成了一副同意識的其他構成要素平行并列的門面,以至于一損俱損,敗則全敗。只要我們一味排他,專從它與理性解釋需要的關系出發來審視《圣經》神話,只要那種與古代人對風暴與洪水的恐懼相對的《圣經》神話的“驅邪”(apotrop?ischen)功能之制序性仍然沒有得到重視,那么,一種對于彩虹本質的解釋就可能被看做對《圣經》神話功能的反駁。 《圣經》文本揭示,制造可怕大洪水的上帝需要確立一種絕對距離的符號,即表示世界信托的可能性,于是就從心里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詛咒地(人從小時心里懷著惡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創世記》,8:20—21)他給了那些剛剛從大洪水中死里逃生的人一系列最原始的協議和契約的范本,顯示了他和自己的人民作交易的特征:“我與你們并你們這里的各樣活物所立得永約是有記號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這就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創世記》,9:13—14)我們不會認為,這是一種必須盡快地用更高的認識、用一種物理學理論來取代的對于彩虹的“解釋”。一切理論所能達到的境界是:只要用這種方法將它看透了,對人而言這一現象就完全喪失了它的“意蘊”。 關鍵不在于哀嘆這種失落,卻在于抑制這種黑暗歷史神話。而僅當它作為科學而被制度化時,理性才從中脫穎而出,照耀自己前行的道路。我們盡情欣賞那些浪漫主義風景畫家的壯舉,他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再次從啟蒙時代所指派的無意義深淵中召喚出彩虹形象。把這種自然現象維持在可以敘述、可以描畫的層面上,卻不至于像可能在歷史編年史中最清楚地顯示的那樣,理論清晰的程度讓它變成可有可無的贅物。根據一種“創造形式的”事件,將整體性納入可以理解的范圍,而不讓它被分散在事實與偶然的迷霧中;而當對立的一面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足夠的呈現,這一切都將永遠作為歷史學家的使命而自我肯定。 盡管歷史可能顯得像是某種可以創造的東西,顯得像是某種可以在其偉大的事件中通過主題定格和加封加冕而被創造的東西,但接受過程所接納的神話卻不是某種可以創造的東西:神話不可能被創造,因而它沒有一個開端。神話確實是被創作的,盡管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以及在什么時刻創造了它們——不論這一點是如何毋庸置疑,但知識的缺乏仍然顯示了這么一種事實:神話一定屬于原始之物的庫藏,我們所熟悉的一切都是那些已經進入了接受過程的神話。我們必定都已經擁有了一個神話背后的神話作品,然后才能專心致志地進行神話創作,感到它激發了一種直接指向物質素材的努力,而其素材的堅硬性和抵抗力必定有深不可測的根源。神話作品的限制概念可能就是我所謂的“實在專制主義”。而神話創作的限制概念則可能將神話帶向終結,可能大膽進行最極端的變形,于是僅僅只是或者幾乎就是不讓人們認出神話的本源形象。在接受理論看來,這可能就虛構了一個終極神話,即虛構了一個充分地利用和窮盡了形式的神話。 為了不讓這種情形變成一個純粹的啞謎,我還要補充說:這么一個終極神話本來可能是德國唯心主義的基本神話。如果我利用席勒向歌德描述神話的詞語來介紹基本神話,也許可以讓人更明確地看清這一點。席勒從耶拿寫信給魏瑪的歌德,用了一個非常簡潔明了的句子;這個句子是對費希特(Fichte)榮登耶拿教席之后第一次講演的反諷式縮略戲仿,甚至還可以補充說,僅僅在他會見康德后三年,費希特就發表了這次講演。這個句子是:“對他(費希特)而言,世界僅僅是一個由自我拋出卻被‘反思’接住的球!”在現代凱歌高奏、科學摧毀神話的計劃空前成功的過程中,一種終極神話——至少一種臆想中必須是終極的神話——如何可能出現呢? 終極(letzte)神話乃是終極懷疑的結果。笛卡兒引入了“邪惡的精靈”(genius malignus)的思想實驗,完全不是無緣無故,也非缺乏歷史壓力,而是依然相信他自己能夠仰賴“最完美的存在”(ens perfectissmum)這一觀念來制服“邪惡的精靈”,來保證可以證明的存在權威。萊布尼茨早就反駁說,一種可謂激進徹底的懷疑是無法通過論證來消除的。康德亦證明,上帝存在的一切證明都是不可能的,因而讓懷疑的赤裸鋒芒直接去延續其顛覆的存在。這里有一種惟一的手段可以將這最后的怪物從這個世界上清除出去,即讓認識主體自我塑造為權威,對它所認識的對象負責。因此,唯心主義的“終極神話”是一條同恐懼對象拉開距離的途徑——這種恐懼現在僅僅是心靈的恐懼,現在還深深地扎進了理論主體之內。因為完全徹底地被欺騙了,只要主體可以確信他絕對不能從迄今為止一直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濃密實在中覺醒過來,變成一種未知的主體,那么,就不需要去擾亂生活世界的主體。 從唯心主義基本神話的視野來看,笛卡兒懷疑論的惡魔就是一個恐怖的先驗世界的怪物,而今它肯定是被我們制服了。在一種與之相關的、把過去狀況設立成絕對過去的歷史哲學當中,神話的先驗世界有其期望未來的必然性;未來可能是這樣,而且還可以肯定它必將變成現在。由笛卡兒引來、在哲學圣殿登堂入室的認識論惡魔,勢必有能耐在“蠱惑欺騙”的名分下做那些在悲劇中只能由希臘諸神來完成的事情。但是,在那里,面紗不僅總是不完整的,而且在“權力分裂”的復雜網絡中還可能以另外一個神靈的名義被撕破。在神話中根本就不會產生整體性和確定性,它們悉數是教義學抽象的產物。這就說明,唯心主義基本神話為什么會包容一種歷史哲學。這種歷史哲學集中表現了上帝不可能同時創造一切,甚至也不會自為創造。歷史哲學再一次把歷史變成了故事,這個故事講述了本源游戲的主體、冒險闖蕩的主體,或者塑造形體和組織社會的主體。但他再也不可能成為笛卡兒的“最完美的存在”,供他探索從理論上可以認識世界的保證。因為,這么一個主體的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按照其永恒性的古典定義,他同時也是一切。但是,如果絕對性只有靠時間的迂回來探索通往自身的路,那么,歷史就不會“降臨”到它身上,對于歷史它既不會感到恐慌,也不會覺得陌生;相反,作為它所創造的東西,它現實地進入體驗的地平線。嚴格地說,這種體驗本質上就是一種審美體驗。 1811年到1812年冬天,身在柏林的叔本華讀到了費希特的講演,并在他的筆記本上作了這么一條邊注:“我試圖解釋,這么一則神話是如何出現在費希特的腦海中的?”他果真解釋說,毫無疑問是因為不完整,費希特才誤解了康德的學說。與費希特的原始“給予”即那個默觀冥證的存在相對立,叔本華提出了這么一個反駁:當自我確確實實在沉思的時刻,它本身就絕對不可能成為沉思的對象。費希特的“知識學”的基本模型是:我們認識存在(das Seyn)之可能惟一的途徑是通過它的交流行為,通過它自為地得到理解。叔本華評論說:“如果我們斷言,那些根本就不可知的東西的故事必須靠同樣不可知的事實來證實,那不是十分寡廉鮮恥嗎?同樣,那些無賴出賣了本該屬于美洲的土地,卻在此之先就出示了這塊本來就已經標畫出來的土地的地圖。” 而今,將絕對反思性描述為默觀冥證僅僅是為了激起一場運動;如果沒有這場運動,什么都不可能出現在一種哲學中;但無論如何,這種哲學都必須準確無誤地出現在這場運動中。主體對自身的不滿,這就是它刻意要占有一個世界的先決條件。僅僅在三年之后,叔本華發現,主體無需接受這么一種體驗的恐嚇,仿佛世界就是無限時空中的絕對失落,而唯心主義從這么一個事實中獲得了一種無以估價的優勢。叔本華認為,在作為認識主體而自我反思的同時,“我”意識到“世界就是我的表象,也就是說,我這個永恒主題,就是宇宙的承載者,萬物皆備于我”。在這么一種認識中,全部崇高感情積聚起來,消融了恐怖與敬畏之情,而對于我們的世界體驗,這種崇高感情的出現預示著千年盛世的降臨,預示著“崇高的天國存在著無以數計的世界”……“恐怖怎么樣?敬畏怎么樣?我在,萬物不復存;我支撐著,世界安然入睡,世界就在由我放射而出的這份安靜中。它如何讓我恐懼?它的偉美又如何能讓我迷惘?一切偉美無非是我自己的尺度之偉美,而偉美永遠超克了萬物!”于是乎,一個故事講述了世界以及認識對象的主體,這就徹底地排除了實在專制主義。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故事,一個沒有見證的故事,但它蘊含著只有哲學家才能賦予的最崇高的品質——不可反駁,不可證偽。如果這一切都如此讓人將信將疑,那么,至關重要的將是見證它的浩蕩恩澤。但就此而論之,作為哲學家創造活動的產物,世界給予“蕓蕓眾生”的恩澤的確定性已經失落了可信度,因為他的全部經驗表明,作為世界的創造者他卻不能明白無誤地確保大千世界完全歸他所有。 如果說,在唯心主義基本神話中,惟有一則神話的形式將獲得抽象的名和具備自覺的不可僭越性,并由此而產生實效,那么,這則神話會以再現自我創生、再現主體的自我創造為自己的根本宗旨。通過這種手法,一切現實可能性的初始條件都將被置于主體的控制之下,就好像主體根本就不會對實在性感到驚訝,甚至不會對“存有而非虛無”這么一個事實感到驚訝。歷史必然發端于實在性的絕對統治,即發端于現實原則的絕對統治。而在這一歷史的對立極,我們不妨把這一目標描述為意愿的絕對統治,即快樂原則的絕對統治。因此,這是一項首先讓人心煩意亂,隨即可能轉化為肯定的原則,它的要義在于創造性想像和神經質的想像彼此依存,密不可分。這兩種想像都將從現實原則的統治中抽身而退。 主體反思自己的根源,可能同自己產生最深邃的沖突。這種自我沖突確認了他在這個世界上純屬偶然,而根本就沒有什么必然。也許,精神分析學所發現的,并在神話中再度被發現的父母沖突只不過是一些卓然昭著的表象,只不過是更深邃沖突的特殊形式。更深邃的沖突在于或者說源自這么一種事實:一個主體乃是自然過程的結果,因此他不能體驗到自我構型;相反,從他所占有的思維—存在(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之惟一絕對的確定性中,他才像接近某種外在于他的差異之物一樣地接近這種自我構型。根據奧托?蘭克(Otto Rank)的分析,我們認識到這一困境最精確的表述為何是這樣的:“你總想創造你自己,你不想由父精母血所生……你努力過自己的日子,就像生命是一則神話。你夢想與幻想中的一切,你都想變成現實。你是一個神話創造者。”神經病人沉湎于幻想,試圖把一切令他不快的存在之星和附屬之象轉化為意愿,轉化為那些能創造幻覺的意愿,事后諸葛一般地以為他仍然能夠改變真正的現實性。當然,這也包括自我創造的意愿。我們自我表演,仿佛一切都已完成。 對絕對本真性的渴望也系統地表現于存在主義的核心原理中。被拋性(Geworfenheit)、事實性(Faktiztaet),這些抽象概念都表達了那種單純環境因素,而這完全對立于主體自預存在的意愿及其存在條件。人類發現,作為某種最為真實的自然過程的產物,這些條件都已經存在;因而人類必須在其自我籌劃過程中,比照這些自然的前提條件來自我定位。最能表現這層涵義的是海德格爾顛倒經院哲學“本質先于存在”的公理,以為存在首先是從此在(Dasein,這是海氏描述人類存在的概念)當中獲得本質的。回溯既往,這么一種立場顯得像是對一個壓倒一切的前提的絕命抵抗——這個前提認為異化的社會的動力因創造了我們的存在——換句話說,顯得像是一種抵抗或取消這一前提的絕望努力,事后諸葛,百無一用。一點也不奇怪,自我創造在本質上一再以一種自我呈現的審美交易為歸宿。只有在審美的意義上,我們才能滿足這種不循人之常道的愿望(nicht so zu sein, wie man ist)。即使是對普羅提諾的上帝而言,自我創造亦已變成一個隱喻,而它的含義是將他的存在變成其本質的一個純粹結果,在最高原則上將他的本質呈現為其意志的縮影,從而終結形式與質料、本質與存在之間的分裂(Chorismos)。但這也成了審美對象的一個定義。對立一切“被給予的”(全部事實性),審美對象是境界與表象的同一,換言之,是作為存在的意志之絕對可靠性(die Unverfehlbarkeit)。 因為必須挑選一則神話來作為其“形式”的最終不可逾越的純粹再現,這就為研究神話性提供了最強烈的刺激,但這則神話尚不能被指定為“終極神話”。開端與終結互相對稱,因為它們都不可以清楚地觸摸。無論運用了什么樣的暴力來掙脫它的束縛,確立其最后形式,神話總是已經流傳在接受過程中,而且依然流布在接受過程中。如果神話只是以接受的形式向我們呈現,那么,就沒有某些版本作為更原始或者作為更終極的神話的特權。列維—施特勞斯提議,我們應該根據版本的總體性來規定個別的神話。因而,弗洛伊德和索福克勒斯應該一視同仁地被看做俄狄浦斯素材的“源本”。神話素材的一切變體都可以宣稱自己具有神話學上同樣的嚴肅性。這一中心論題所導致的最重要結果在于,它在我們的神學中嚴格地廢黜了“效果歷史或者影響的歷史”(Wirkungsgeschichte)。人們放棄了在時空上接觸“因果”關聯的要求。而這就假設了一種更近乎連續的創造性,而非一種跨越間距的被動容受性,因為它從根本上假定從人性的永恒基礎看,一切有意味的個別神話在一切時代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使一個接受過程可能如實地被記錄在案,我們也還是可以斷定,這么一種接受的傾向同成為真正創造者的傾向無法區分開來。 遼闊遙遠的文化中存在的種族志材料,特別有利于上述假設。如果我希望墨守成規,而不是與時俱進,就必須避免那種無法逃避的柏拉圖主義。柏拉圖主義必然會被一切文化傳統認為理所當然,因為它廢棄了神話的機械論傳播過程。因此,傳統概念可能削弱歷史概念,久而久之我們就只能指點“黑箱”內容來解釋這么一些現象:它們自我呈現一如飛散在時間中,但極少受到其在時間中地位的影響,一如柏拉圖的理念不被外觀表象所改變。可是,僅僅是早與晚的時間規定性讓如下情形意味深長:本來就是一個“毀滅者”的阿波羅** 阿波羅這個名字可以追溯到希臘語動詞apollumi,意為“毀滅”。變成了一位喜氣洋洋熱情友好的神民;赫淮斯托斯從一個恐怖的火神變成了藝術技巧的守護神;老邁的風暴之神宙斯成為世界的統治者;而且其他的神民形態上也發生了各不相同的變化。 即使我們堅持接受概念及其接受過程,甚至我們給予這個概念在神話學中以獨一無二的地位,列維—施特勞斯的核心論題的價值也仍然不能被忽略不計。情況依舊如此:與神話在空間中理想的同時性分布相對立,它們在時間中所占地位的偏差狀態卻再次被賦予了一種價值,被認為具有時間性秩序形式的優越性。因為,這么一種秩序形式在利用一種神話潛勢的同時,為各種神話變體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全部指標;如果沒有區分歷史中不斷變異與不斷充實的斷言要求,這么一種神話潛勢就仍然是遮蔽不明的。對民族學家而言,創造與修飾個別神話的前提下由文化差異所完成的業績,也同樣是由我們習慣上稱之為“歷史性”的東西完成于一種綿延不息的傳統中,比如說歐洲文化傳統中。這一點不妨更簡約地表述為,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永遠以同一方式去言說一種被給定的內容,或者像人們常常理解的那樣去構思神話。反之,卻是教義的思想方式公開表示要否定這種不可能性。 列維—施特勞斯提議,將一個神話的全部精選版本投射于一種分層化的結構,以此來確定神話的核心內容;這就顯示了他如何分離辨識時間要素:一切神話變體都被安置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平面。再也沒有永恒真理,但仍然有讓時間流程及其在時間地位呈現為無差異境界的真理。就哲學神話言之,經過歷史篩選之后,所留下的特別堅實的神話素材之所以特別具有啟示力量,其特殊的原因在于:神話素材抵制變形的毀滅的權力之引導與脅迫,而我們卻可能從這種抵制中獲得有關為那些力量所侵犯的歷史地平線的信息。這就是為什么不是一種唯歐洲歷史是善的價值偏好,即便神話在傳統中的流轉幾乎完全可能是呈現在這種歷史中。從這么一種可能性的視野來看,由于缺乏時間參數,種族學家理想的同時性成為一個純粹的困境。他的時間概念打上了重疊結構的印記,正是由于這一點,一則神話之所有變體的歸屬關系結果都不是一項要求,而是成為一種理性化的方式,來處理一種純粹偶然的匱乏狀態。在一種并非常識的專業化再度評價中,聚焦根本就不可能獲得一種時間深度,這種不可能性反而成為認識圓滿的標記。于是,它就避免了文化圈理論中一種恒常傳統——而不是一種恒常的傾向——輪回的論題,這一論題起源于一種已經在文化上高度發達的、供人類空間和時間傳播的中心。 當今,如下事實讓這一議題非常棘手:遷徙流離與自然分化必須在時間上被推后到更早的階段,而這一理論所要求的文化發展的顯著共時性在史前的時間表上越來越難以找到位置。不僅如此,必要的附加假定也顯然無法證實——這一附加假定斷言,原始共同性要素必定存在于這么一些場合:遷居流徙直至死路一條,眾多民族幾近滅絕,因而必須防范后來的影響,以及保護古代世界的存在物。遺傳學理論無論如何都承載著這么一種夸大其詞的,同人類社會傳承傳統的能力相聯系的常量假設,以至于在其“非歷史性”的要求上它完全等同于結構主義。不僅如此,假如一切都已經以終極完美的形式存在,同時什么也沒有留給流傳過程來解釋,那么,一切就都有待于原始血脈的發生來說明。絕非偶然,文化圈理論同一種原始啟示學說特別合拍,后者一旦應用于神話學,就已經明顯地表達在浪漫主義思想中,但它依然以斷簡殘篇的方式流傳,尚未被人們理解。一種遺傳理論同異質觀念之間的完滿協調,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由于將許多難題移置于人類歷史開端而造成的缺損。這樣,伊甸園神話再次成為必不可少的神話。 這種宏大的理論選擇是有趣的,只是因為也通過“把神話帶向終結”而為神話的接受設置了界限。如果神話在人類學上被自然化,在前歷史的意義上又被確定化,統統都歸屬于文化人類與人類文化的根本,一種就其整體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歷史或者根本就不允許存在歷史的根本,那么,這一觀念就仍然是不可理解的。 假如神話學的核心問題的確是要理解,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神話的構成要素如何會彼此類似,那么,就可以說,從人類歷史的一極到另一極神話在時間維度上都會以令人驚訝的方式保持穩定,這么一個事實不可能是無關緊要的。文化慣性沒有法則;繼續維持文化內容則必然要求解釋。也許,跨越個別神話的同時態空間流布而顯示的形態學上的可比性,也同神話的歷時轉換過程中的持久耐力相聯系。 如果穩定的敘述中心建基于神話之易于接受性,而這種易于接受與其說必然同尚未成形的先天模式相關,不如說必然同那些反映在神話構型中,并且使它們至少顯得在形式上類似的人類環境、需要和處境的有限多元性相關——果真如此,那么就有可能出現上述情形。假定時空上的普遍存在是等價的,我們就不得不認為神話接受的條件完全不會相異于神話起源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從神話接受的視野看來,關于先天性的前提至少必須不是被排除,就是被質疑。 在世界范圍和時間范圍的對應性這兩種情況下,神話都顯示了人類在激起并(在精神上)消化那些不能泰然任之的東西,那些保護在焦慮不安狀態中的東西。不妨把這還原為一個簡單樸素的說法:世界不僅不能為人類所透徹理解,而且也不能為它自己透徹理解。但這并不等于說,對現象的解釋總是已經獲得了優先性,神話類似于早期人們在缺乏理論時應付困難局面的方法。如果神話表達了科學的缺乏,或者表達了科學之前的解釋,那么,最遲也在科學憑著其日益增長的執行權力而登堂入室的時候,神話就可能自動地被操控了,反之亦然。最讓啟蒙運動的發起者們萬分驚訝,面對他們自以為是的最后努力之敗績而萬分茫然的,恰恰是那些荒唐下賤的古老神話還活著——神話的創作還在延續。 神話創作便假設了:不僅要了解那些主動地進行創作的人身上所發生的事件,而且要了解那些必須被動地接受神話的人身上所出現的變化。這就常常假設了一群能夠對接受機制作出反應的公眾。這樣一群公眾必須有能力辨識被保護的東西、被變形的東西、被變得差不多無法辨認的東西,以及最終被交付給暴力修正的東西。不言而喻,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公眾假設,無論如何,他們都被假定受過上流社會的古典的文學教育。不難理解,如果我們從這種環境下推測,特別是在美國和歐洲,在教育體系中有目的地摧毀古典文學份額的十余年間,文學藝術對于神話素材的利用與改造達到了過去做夢也無法達到的程度,那么這可能也是不正確的。作為這種現象的結果,許多人都受到激勵以專注于古代世界作為自己的業余愛好,而推動這種古典運動的系列出版物也漸漸地獲得了成功。 注意公眾在神話接受過程中的作用,卻不是什么新鮮事。在魏瑪宮廷劇院,當上演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創作的戲劇《伊安》(Ion)時,歌德向人們建議說,在看戲之前最好在家里利用神話手冊自學一點關于該劇的語境知識,而不要隨著劇情的發展,隨意地提供解釋:“我們可以向觀眾表白,對他們的最大尊敬就是不把他們當做下里巴人。”盡管假想的古典主義前提以及產生古典主義的可能性前提都可能發生了變化,但歌德的這句話依然顛覆不破。必須被嚴肅對待的審美公眾之部分訴求,在于要求我們保護這么一種普遍的期待:公眾可能會“記錄和注意某些東西”(etwas merken und bemerken),這些東西是不應該用赤裸的好為人師的姿態強行灌輸到公眾心里的。做點事情為公眾效勞(也就是說以公眾為目的),完全不同于直接為公眾效勞。 即使只是說出那些取自神話的名字,歌德也會再次提醒戲劇演員注意,“這些專有名詞不僅都非常重要,而且還呈現了全部意義”。歌德認為,即使只能拿想像力來自我再現“某些類似于其實際指稱對象的東西”,這種意義也仍然可以得到理解。這是一個值得同神話命名功能聯系起來予以認真考慮的命題。即使沒有可靠的知識作為它的基礎,想像力也還是有成功的機會。因為對于獨立處理的名字而言,故事都一定會提出同樣有效的充分要求:名字必須占有一種本身就有能力產生印象的意蘊,而且正是因為這一意蘊之故,它們必須能夠被占有,而與有限的知識儲備沒有關系。對想像力的影響是有些含糊的;但它將完成的使命,可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明——那就是——占有。 神話形象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便清楚地顯示在接受過程中,但并不是簡單地將某些本來可能已經被重新擺放、預先成型于其中的東西具象化。這實在是一種派生的創造過程。但是,我們又不能認為,這個過程獨立于其連續的始點。對于一種依賴于“源泉”的傳統而言,連續的始點可能只是一部已經匯入了書面形式的未知史前歷史之最后階段。甚至通過接受過程以及素材的積累而達到的豐富性,也表明了多種聯系的中轉站,表明了它能夠利用繼承所得的可用素材進行指稱。《神曲》塑造奧德賽這個形象的前提是——在但丁看來,荷馬未必是不可冒犯的,埃涅阿斯無家可歸的漫游,在創建羅馬帝國時抵達高潮,而這比始于以色佳,終于以色佳的任何一種循環涵義都有無與倫比的說服力。 如果說,因為僅僅將一個神話運用于一個神話就可以充分地證明“終結過程”的要求與意義,從而將這個神話帶向了終結,那么,一切都取決于接受過程所展開和產生的潛在意蘊。作為對時代的批判審視,恰如現時代的浮士德博士神話所表現出的精神較量,產生了無以復加的審美激蕩力量。 在布托爾(Michel Butor)和普索爾(Henri Pousseur)的浮士德歌劇變體的“預備版本”中,歌德《劇院序曲》就已經獨立成篇,結構完整。歌劇中的副歌是劇場導演對作曲家所下達的一個晦澀難懂的指令——“它必須講述一個關于浮士德的故事!”(Es muss ein Faust sein!)而且,事實上這出戲只能如此,而沒有其他可能。這倒不是因為從一開始這個形象就蘊含著不可窮盡的意蘊,而是因為它最為接近時代意識,其結果只能如此。僅僅是通過和它展開精神較量,自我欺騙的新形式才能自我呈現,假如已經存在或者必將存在這么一種自我欺騙形式的話。歌德的序曲自成一體,無止境地逃避變成現實的可能,盡管它也求助于木偶戲和年廟會,盡管它也求助于浮士德博士“罪惡深重的生活及其令人戰栗的結局”。但是,在這么一些神話氛圍下——比如,坦塔盧斯(Tantalus)的無限苦惱,普羅米修斯受盡了天鷹的折磨,西緒弗斯無奈巨大的圓石,猶滴(Judith)拯救祖國,敖羅裴乃(Holofernes)兵敗西方,婦人大利拉(Dalilah)出賣力士參孫(Samson),大衛王(David)飛石絕殺歌利亞(Goliath),雖然這種氛圍深深地浸潤在原始的媒介中,歌德的《序曲》還只不過是一部序曲而已。它展示了人們根本就不可能苛求那些被認為具有選擇能力的觀眾接受這么一個浮士德形象。 我們必須再次認識、考察神話歌曲的原始情境,因為對于作者的獨特貢獻、對于戲劇變體的進程與結局起決定作用的要素則完全在接受者方面。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審視一下,就一定會明白,這么一種審美的民主其實百無一用,什么也確定不了。一種年代迷亂的口傳程式被隱約暗示,而它的強烈影響被拙劣仿效。或者,我們應該說,公眾已經被塑造成了共謀者,他們一起逃避浮士德所必須擔負的一項使命。但這妨礙了目標的實現嗎?沒有一個同時代的公眾能欣賞《你的浮士德》(Votre Faust),因為這類公眾已經讓現代神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我們必須指出這一點么?公眾選擇的自由純粹是一個審美的虛構,因為公眾一點也不珍愛選擇的自由,或者不言不語而有所節制地忽略了選擇的權利,同時還把這種權利轉讓給另一方。正像歌劇作者所希望的那樣,亨利?普索爾將自己為布魯塞爾劇院(Brussel)創作一部浮士德歌劇的代理權轉讓給了米歇爾?布托爾。我們可以想像,在那里所得到的明確回答,事實上應該歸于文本中的作曲家的朋友:“寫一部浮士德?我的天哪!可是,為什么不呢?”當作曲家再次追問劇場經理這出戲是否一定要以浮士德為主角時,他得到的回答一定是這樣的:“我們首先必須考慮公眾的趣味和愿望。” 如果浮士德主題尚未深深扎根于時代意識中,這一切都將是不可思議的。不僅對于這一素材的全部暗示都會喚起驚訝與贊嘆并得到認可;而且還因為,我們可能常常指望,正像在實驗中那樣,這個素材的每一次重塑都更加清楚地顯示當前情境中突然出現的行為力量。它打算用來同這一素材一比高下的東西,早已被古老的浮士德傳奇以及馬洛的《浮士德博士》以來過分豐富的接受過程預先地規定了。如果以這個素材為基礎的創作尚未展開,尚未創造,尚未補充這則神話,那么,對于這個形象的意蘊,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在此,一項使命不可完成而又無法拒絕,這個事實顯示了接受過程的權重與義務。在一種方式的結尾中,恰恰就是甘淚卿/馬吉(Gretchen?Maggy)答應滿足惟一的條件,計劃寫出一部“它絕對不可能以浮士德為主角”(Es darf kein Faust sein)的歌劇。當浮士德/亨利(Faust?Henry)抵制這項計劃而與她交惡之時,她坦誠地表示再也不愛他。在不以觀眾的意志為轉移的終局,劇場經理徑直追問朋友理查德:“你愿意為我創作一部歌劇嗎?”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不!”至此,帷幕降落,劇到終場。 再也沒有其他的素材能像浮士德那樣,可以被不斷的重寫,這就圓滿地執行了斯達爾夫人的指令。但她卻只能效忠于法國人。但是,自歌德以降,到布托爾以決然的否定宣告不可能完成這一使命之前,最重要的浮士德形象還是已經在法國誕生了。 1940年的某一天,發生了空前絕后的一幕:詩人保羅?瓦雷里告訴我們,他覺得自己同時在用兩個聲音說話,一個是浮士德,一個是梅菲斯特,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記錄自己的言辭。在《致謹慎而非勉強的讀者》這篇序言中,我們能讀到:這里并不是某種相對于近乎終局的終局,而是追求一種必須同開端相配稱的結局,而這個開端遠在后面,是絕對不可逾越的。一方面是“我的浮士德”(Mon Faust),添加代詞所有格,就是以最大限度主體性的名分而將終結的訴求相對化,同時又表達了對作品的斷簡殘章的接納;另一方面是誘惑者與被誘惑者角色的互換,梅菲斯特成為被誘惑者,而浮士德成為誘惑者,此乃對于戲劇構型的最徹底的,顯然是無法超越的干預。 我們從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August Wilhelm Schlegel)的一次經驗記錄中了解到關于上述相對化的信息。這則記錄說的是,1755年齊默爾曼(Zimmermann)醫生和歌德在一起,前者向詩人問起那部已經聲名鵲起的名劇《浮士德》;歌德立即把書桌上一只裝滿了碎紙片的麻袋倒空在醫生面前,并用手指著這些碎片回答說:“這里面有我的浮士德!”(Voila mon Faust!)人們并不在意這袋碎紙片以及歌德的回答可能有什么意義。可以肯定,這并不意味著詩人將他的“最初版本的浮士德”(Urfaust)手稿寫在這些碎紙片上,然后把它裝進麻袋里保存起來。詩人更可能是用一部被撕成碎片的手稿作為遺跡來迷惑齊默爾曼先生。在《詩與真》中,歌德描述說,他同齊默爾曼之間的關系就建立在這么一種“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基礎上。 物主代詞、不定冠詞,以及浮士德名字上使用復數,都是用來表示相對化和主觀化的語言學標志。早在1755年,摩西斯?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s)在一封寫給萊辛的信中,就曾經提到過,萊辛有寫一部浮士德的計劃,可是這一計劃最后還是零落為斷簡殘章。在漢堡時期,他還說過“我的第二部浮士德”呢!至于這部佚失的浮士德,卡普泰因?馮?布蘭肯貝格(Hauptmanns von Blankenberg)的描述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知識來源。布蘭肯貝格用復數形式描述了這一計劃,并認為萊辛修改第一部浮士德的時間是這么一個特殊的時刻:“在當時的德國,浮士德這個名字幾乎滿天飛舞。”布蘭肯貝格肯定“確知”萊辛“只是在等待其他的多部浮士德面世”,再出版自己的那部浮士德。可是,從德萊斯頓到沃爾芬比特爾的轉運過程中,那部浮士德手稿被遺失了。 為其他版本的浮士德而“等待”,這一說法可能多少有些夸大其辭,因為1755年,同歌德的浮士德計劃的沖突已經公然記錄在案。舒巴爾特(Schubart)的《德國1755年大事記》(Deutsche Chronik auf das Jahr 1755)記載,萊辛“把他的優秀悲劇作品《浮士德博士》賣給了維也納劇場經理”,同時在腳注中引用了一條萊夏德(Reichard)的《1755年劇場日歷》(Theater-Kalender auf das Jahr 1755):“歌德也在寫一部浮士德博士。”于是,萊辛眼睛盯著歌德,猶豫不決。柏林啟蒙人士約翰?雅可布?恩格爾(Johann Jacob Engel)在寫給杜柏林(D?bberlin)的信中所作的一條評論確認了上述事實:在歌德拿出了他的浮士德之后不久,萊辛確實也出版了他的浮士德。據說萊辛還補充宣告:“我的浮士德——是魔鬼招來的,但我還要從他那里招來G(歌德)的浮士德!”裝有手稿的箱子不知歸落何處,但恩格爾認為遺失的手稿一定是“萊辛的一部杰作”。而手稿的遺失妨礙了后人決斷是誰最后贏得了這場競爭。 萊辛的復數形式所表達的,幾乎是對那種涵義的厭膩感:浮士德太多了。但是,浪漫作家阿齊姆?馮?阿爾寧(Achim von Arnim)在馬洛《浮士德博士》1818年德文版序言中斷言,“迄今為止,還沒有寫出足夠多的浮士德”,這不僅代表了浪漫派對復數形式浮士德的再度肯定,而且還是對這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主題的暗示。根據歌德1818年6月11日的日記所提供的證據,他不僅讀過這個譯本,而且還讀過阿爾寧的挑戰性論說。僅此即可給他的《浮士德》打上絕對完美的印記嗎?只是在1825年,他才重操舊業,繼續這部作品的寫作。在1826年2月16日的日記中,他把這項工作描述為“延續重要事業”,直至1831年才讓他如釋重負。 當歌德最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浮士德創作的時候,也并非絕無僅有。事實已經表明,1824年,另一位德國作家拜望歌德時,也在浮士德這個名字上加上了物主代詞。當年10月2日的記載非常非常地簡單:“海涅,自哥廷根來。”來訪者自報家門,要求懇切:“如果您允許我在您面前站幾分鐘,那就是賜予了我無限的幸福。”當他還在布洛肯(Brocken)的時候,他已經表達了一種急切的渴望:“到魏瑪去朝圣,以表達對歌德的崇敬。”因此,他以步代車,前往魏瑪。布洛肯決定,魏瑪朝圣,這段軼事的解神話版本說來略有不同:“秋天我徒步旅行,至哈茲山(Harz),我朝四面八方高喊,然后參觀布洛肯,回程順道魏瑪,拜訪歌德。”形體衰老、滿嘴無牙、“只有眼睛依然明亮閃爍”的奧林坪神讓他“深感恐懼”,“直逼靈魂”。他感到對立于他們的天性,他感到對那些不僅不太珍視生命,而且還不愿意公然為一種理念犧牲生命的人充滿了蔑視之情。自那以后,海涅就感到,他自己“真正處在同歌德及其作品的沖突中”。 至于他為什么要向《浮士德》的作者宣戰,海涅本人也語焉不詳。海涅的回憶錄首次發表在1866年的一份非常不可靠的通俗雜志《涼亭》(Gartenlaube)上。盡管如此,馬克西米利安?海涅(Maximilian Heine)是否真的如此充滿想像力,膽大妄為地捏造出他的兄弟與歌德通訊的只言片語嗎?他說,在邏輯混亂和卑躬屈膝的客套之后,歌德突然向海涅發問:“近來你在忙些什么?”青年詩人立即作答:“忙著寫一部浮士德。”歌德聽后大吃一驚,然后用一種嘲諷的口氣問:“你在魏瑪還有何貴干嗎?”如果這段軼事是捏造的,那么捏造者便一定是海因利希?海涅本人。 與后人所知所聞相比,海涅對歌德所說的話還隱含著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將奧林坪詩人之王歌德所禁錮的神話題材大眾化。同布托爾和普索爾將一系列情節留給大眾來抉擇的做法相比,海涅含而不露的詆毀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年,海涅在同埃杜阿德?威德金德(Eduard Wedekind)談話的內容再度強化了他向歌德提出的主張的真實性。同威德金德的談話當然也是就歌德的《浮士德》而展開:“我也想寫一部《浮士德》,但絕對不是為了和歌德一比高下;不是這樣的,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寫一部《浮士德》。”海涅已經考慮過要嚴格地顛倒作品的布局,因為他認為自己的《浮士德》“必須明確地成為歌德《浮士德》的絕對反面”。他說,自己的浮士德永遠是行動至上,積極地對梅菲斯特發號施令。他還希望讓梅菲斯特成為主動原則,“將浮士德引入一切神魔的故事中”。這樣一來,魔鬼就當然再也不可能是一種消極原則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