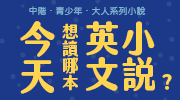商品簡介
身處新舊文化的激烈轉換,
身處「中華」概念的裹挾,
身處兩岸黨國體系的誘惑和扼殺
自負又渺小、無根如浮萍的文人,該如何自處?
有人放棄掙扎、有人隨波逐流、有人投機獲利、有人走向虛無。
透過銳利如手術刀般的史筆,
劉仲敬為在這場荒謬卻又無奈的歷史大戲中演出的諸位角色,
一一安排了他們所該有的歷史定位。
◎魯迅――紹興師爺的家族血統和祖父科舉舞弊案造成的陰影,讓他養成了一種「將所有的錯轉嫁給外界」的偏狹個性。他的創作力在晚年其實早已枯竭,但在勢力的吹捧下,居然變成一代文宗;靠著蘇聯的慷慨與遠見,他在身前身後都不乏大名,也不乏金錢收入。
◎陳寅恪――博通古今、精通各種難解語言的他,卻是「一種文化為另一種文化所化之際」,深感痛苦的文化遺民。他透過「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看穿了中國向蘇聯「一面倒」的本質,但他的心卻早已在民初王國維投湖之際便已死去,只能眼睜睜看著洪水淹沒一切。
◎余英時――他是擅為歷史診脈的神醫,卻不是擅長物理切片的良醫。失根的他,無法成為陳寅恪般的文化遺民,只能立基於虛幻的文化泛民族主義上,發表一些名重於實的言論,但在現實政治當中卻殊少貢獻。
◎李敖――他承襲了父親的五四運動傳統,也承襲了游士世家的德性。游士沒有定性、也沒有精進不止的熱忱與責任感。他們坐在樹枝上,卻想用西方的解構方式把自己的樹枝砍斷。他們所想的只是以名滾名,以利生利。粗製濫造的文字,展現了李敖自戀的本質,但隨著言論市場的開放,他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小,最後只能被淹沒在萬馬齊鳴的巨浪中,靠著一些拼貼文章發揮餘熱。
◎張愛玲──直隸舊家與閩粵海洋的血統結合,讓張愛玲一開始就具備了兩種相互衝突卻又互為因果的文化脈絡。但她的祖國不是北洋中國,也不是湖湘閩粵,而是歷經百年條約守護,卻飽受「新中國」破壞的上海自由市。在這裡,她以無心插柳的方式信手寫作,卻讓橫溢的才氣震驚四座。共產黨的文藝團隊看上她的才華,卻只把她當成三流鴛鴦蝴蝶作家,結果遭到她以《赤地之戀》和《秧歌》痛擊,得不償失。
繼「晚清北洋卷」和「國共卷」以來,劉仲敬再次將自身犀利的點評,展現在人物的月旦之上。在這本「文人卷」中,劉仲敬主要延續了他在前兩卷中的歷史生態學分析,民國文人在「地方主義/泛中華主義」角力的脈絡下,來探討知識分子和文人的發展狀態。
以李敖為例,一般我們談論李敖的時候,總會從他在《文星》時代的思路開始談起,但劉仲敬不同,他從李敖的父親李鼎彝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受的影響開始,再到李敖的恩主蕭孟能等人的背景,一步步抽絲剝繭,將李家的游士風格用手術刀做了徹底的剖析。
又如魯迅,劉仲敬敏銳地看到周家的科場弊案對魯迅造成的陰影,以及他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聯,指出「魯迅之所以暴得大名,其實跟他的投資(或者說投機)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劉仲敬看來,這些民國知識分子都是泛中華主義本身的產物,而泛中華主義衍生出的弱點,並非個人所能改變。正如建築藍圖的承重牆如果有問題,包工頭再廉潔也救不了房客的性命。所以即使如余英時般再有才能,也無法改變虛無的宿命;才能不佳者如余光中,更是只能仰賴政治勢力搏取其地位。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便深陷在所謂「中華」的迷思當中,而輕視「諸夏」的地方主義與小共同體精神。正是這種迷思,斬斷了鄉土根源的知識分子,只能落入虛無與失敗的窠臼之中。
透過銳利如手術刀般的史筆,劉仲敬為在這場荒謬卻又無奈的歷史大戲中演出的諸位腳色,一一安排了他們所該有的歷史定位。
作者簡介
目次
二、隔靴搔癢的圈外人――周作人
三、見證洪水的預言家――陳寅恪
四、失根的文化主義者――余英時
五、泛濫的郭沫若
六、慣於逃避的瞿秋白
七、在民族的矛盾之間――顧頡剛
八、「中華夢」――錢穆
九、迷失在「數字」中的黃仁宇
十、靈巧的水蜘蛛――錢鍾書
十一、傳統與西洋的花開――張愛玲
十二、以名滾名的游士典型――李敖
十三、「投機小粉紅」――金庸
十四、五四文學的窘境――余光中
書摘/試閱
書摘
蔣介石政權通過二二八事件、土地改革、接收敵產和經濟國有化,基本剷除了臺灣社會自發形成的土豪或凝結核,為自己帶來的流亡者空出了生態位,否則他們在哪兒都安置不了。滿洲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雖然也會零星使用鐵血的鎮壓手段,但部分出於君主國的保守本性,主要因為缺乏列寧主義的社會工程學機器,在系統性方面達不到同樣的水準,正如國民黨出於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軟弱性,在徹底性方面達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同樣水準。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社會工程,一九九○年代以後的臺灣民族主義大概就會在一九六○年代出現了。一九二○年代以後繁盛的日語文學和台語白話文學,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出現了斷層。蔣介石政權帶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殘餘文人,在視窗期佔據了這個真空。國民黨政府如果想要抹去日語和台語的影響,就必須借重他們推廣新文化運動發明的白話文,然而新文化運動的無根性和除根性天然導向共產主義,又不能不引起流亡者的深刻恐懼。事實上,這種兩難處境正是國民黨本身的特徵。如果沒有蘇聯,國民黨就不可能取得政權,然而只要有了蘇聯,國民黨就不可能保住政權。這種兩難處境產生了一九六○年代的《文星》雜誌,《文星》造就了作為公共人物的李敖。
《文星》在國民黨最失意的派系保護下,為萬馬齊喑的臺灣文壇開了一扇小小的天窗,從列寧主義生態學角度講,無異於《自由中國》從政治領域退到了文藝領域。得志的派系搶佔政治、軍事、情報部門,邊緣的派系得到了經濟、社會部門。文化部門留給了那些在黨國歷史上曾經顯赫一時,但目前已經只有混吃等死的位置可以安放的派系。李敖在青年時代的小夥伴居浩然、蕭孟能都是這種派系的子弟,永遠無法忘記他們的父、祖作為國民黨元老叱吒風雲的時代,蔣介石還是一位無人保護、無人賞識的孤寒子弟,更不能原諒蔣介石父子在臺灣提拔任用的新生代實權人物。他們的滿腔怨恨和嫉妒以文學和思想形式表現出來,在不懂列寧主義操作模式和演化歷史,喜歡用最為廉價和膚淺的符號性辭令判斷和分類的局外人眼中,就成了「自由主義」、「開明人士」、甚至「民主反對力量」,但他們的開明姿態和反對姿態本身就是中國殖民者特權的一部分,因為臺灣被殖民者社會即使作出同樣事情的極小一部分,都會遭到嚴厲和及時的取締,結果根本不會讓局外人有機會看到。只要被殖民者社會強大到足以產生真實的「民主反對力量」,階級生態的基本格局就會迫使這些符號經營者逃回自己的真實位置。李敖的家族在殖民者社會當中的地位和他的保護人在殖民者統治集團當中的地位,猶如照鏡人和鏡中像。蕭孟能對李敖的提攜,本質上是派系招募孤寒子弟為家臣的政治行動。蔣經國對宋楚瑜的提攜,屬於類似的機制,只是政治家需要的素質,跟文學家有所不同而已。
李敖的出身和環境,都比大多數中國殖民者家庭的子弟更適合進入上述角色。他的父親李鼎彝和他的老師嚴僑,都是陳獨秀思想和言論的三、四道販子。思想先驅者和粉絲傳播者在信息量方面的差別,通常低於百分之一,但結果通常是前者贏家通吃,後者一無所得。如果你把思想市場看作一個演化系統,那麼獎勵實際上屬於風險收益的一種,winner的資格通常不是取決於產品,而是取決於勇氣和機遇。李敖青年時代的作品,除了個人風格和青春朝氣以外,沒有給多重拷貝的原始版本增加任何信息量,因此引用價值不大。他的價值,也是其原版價值的一個子集。他們都是拙劣的西方負典傳播者,失敗的東亞文化泛民族主義發明家。他們羡慕西方文明的果實,但對西方文明的基石,非但缺乏瞭解,而且充滿敵意,力圖用西方解構者的技術,鋸斷自己坐在上面的樹枝,循其思想內在的邏輯,走向共產主義,只是由於境遇的差異和壽命的長短,定格在這條道路的不同階段而已。李鼎彝、嚴僑和李敖的政治覺悟和政治生命在其特殊的環境中,恰好發展到其對應人物劉和珍、林昭和江青的同等段位。李敖在《文星》時代的作品,達到了他畢生文學成就的巔峰。只有這段時間,他才具備不計功利的精益求精和比較純粹的好奇心,如果自戀的虛榮,不屬於功利範疇的話。此後由於牢獄之災和名人之累,他的作品範圍縮小到現實政治和私人恩怨的一孔之見。文學品質日漸粗疏,最終變得跟尋常的時評家和雜文家毫無區別了。名氣和金錢一樣,最初的一百塊比後來的一百萬更加難得,越過初始閾值以後,只要經常活動以保持存在感,以名生名、以錢生錢都是不必經過大腦的,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夠精進不止,就需要近乎宗教熱忱的信念和責任感。游士很少具備兩者當中的任何一種,李敖明顯是兩者都不具備。
李敖第一次入獄,是因為他恃才傲物,言論逾越了政治保護人能夠容忍的邊界,以後的入獄就純屬私人恩怨,但並不妨礙他將所有的不幸都發明為國民黨的迫害,然後變現為個人的政治資本。他出獄以後,加入了(國民)黨外的政治活動,在少數民選職位的競選宣傳,以英明導師自居,然後挑出不肯乖乖做粉絲的一部分,予以嬉笑怒駡。無論如何,這一階段(戒嚴時代的最後十年)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此後縱然名義職位更高,實際重要性和影響力卻是每況愈下的。順便說一句,這是文人在轉型期的普遍模式。當時的外部形勢註定了所有人都是敗多勝少,自戀狂魔的失敗就像布朗神父的樹葉,隱藏在森林當中毫不引人注目。他的言論得不到現實的檢驗,在轉型期不難招募大批尋找方向的粉絲。名人對粉絲的影響力也是一種隱形的權力,頗能考驗當事人的品格。李敖不是經得住考驗的人,在最庸俗的金錢和女色方面都敗筆累累。解嚴以後,成功的真實可能性出現了。言論的泡沫在「大狗小狗一起叫」的嘈雜中失去了意義,事實很快就會證明自戀狂魔屬於最不適合從政的類別。民選政治家必須擅長為各種真實或想像的失敗提供出氣筒服務,自戀狂魔必然反過來痛斥人民的愚蠢和庸俗。臺灣的選民對待李敖,已經算是超級厚道了。其中部分原因在於民族構建的需要,把厚道作為民族性格的品牌,跟兩個列寧主義殖民政權的刻薄寡恩形成黑白對照,正如波蘭民族發明家必然強調波蘭貴族的騎士精神和莫斯科人的亞細亞式奴性。
李敖失敗的特殊原因,在於「臺灣的民主化」只是一句模糊的外交辭令。「民主」一詞一次經過二戰、冷戰以來的話語權鬥爭,已經不再限於古希臘的本義,變成一鍋各取所需的觀念大雜燴,包含了平等化、自由化、統治權轉移和國民共同體構建多重涵義。「臺灣的民主化」本質上屬於臺灣民族的構建,自然體現為針對中國(列寧主義東亞殖民政權)的去殖民化。東亞奧斯曼主義者作為列寧主義殖民體系的白手套,必然先於其身體感受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痛苦。李敖對國民黨的仇恨,主要源於私人恩怨;反對國民黨的勇氣,主要源於殖民政權對「自家浮浪子弟」下不了狠手的舔犢之情。殖民者的社會由共產國際培訓的半列寧主義者殘餘和美國培訓的技術官僚組成,日益強大的後者將日益衰弱的前者捆住了手腳,兩者都缺乏土豪性和有機性,猶如無根無果的插花,縱然嬌豔一時,終歸後繼無人。被殖民者的社會雖然被征服者剪去了最鮮豔的花朵和最成熟的果實,但原封不動的根莖和土壤自然會養出下一代的土豪,徹底剷除土壤的沙漠化工程又非真正的無產階級和列寧主義嫡系不能勝任,超出了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和半列寧主義者的能力和勇氣範圍。土豪喬治‧華盛頓登上歷史舞臺以後,社會就不再有興趣傾聽游士湯瑪斯‧潘恩的聒噪了。新穩態只要初具規模,擾亂舊制度的游士就會回到符合自身德性的原位。他們過去是邊緣人,現在仍然是邊緣人,只不過在新舊交替的短暫視窗期,一度產生了自己相當重要的幻覺。民主社會不再用監獄收容邊緣人,而是讓他們在越來越寂寞的小圈子裡淘汰自己。
自知之明不是李敖的特長,自戀狂魔尤其易為廉價的粉絲和廉價的恭維所誤。言論市場的開放,使得任何人只要稍微勤快一點,都不愁得不到一定數量的讀者,結果是縱容他日益走向粗製濫造的方向。他把任何反對意見都解釋成政敵的迫害和人民的愚蠢,最後連起碼的文學判斷力都喪失了。《北京法源寺》對他個人而言,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失敗,證明他缺乏塑造立體人物的基本功,只能將所有人物和情節簡化為思想和政治符號。這是他為大批量生產時評和雜文,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上述兩類文字占了他產出的九成以上,甚至稱之為「作品」都有些勉強,主要效果就是維持他自戀的泡沫,而且愈往後期愈是如此。拉‧封丹寓言詩描繪飛蟲在馬車上方嗡嗡旋轉,一面指教馬兒和馬車夫應該怎樣工作,一面宣稱馬車的前進都是它的功勞,就是他們這種人的寫照。馬車最後駛向李大師飛行方向相反的地方,使他的言論看上去像個笑話。他在九十年代斷言台獨註定是票房毒藥,民進黨永遠不會逾越三成(支持率)政黨的境界。此後,他的時評就變成了《柏林之圍》的漫畫連載版。他以「黨外導師」起家從政,卻眼睜睜看著當年同儕的徒子徒孫紛紛拜相開府,自己一年比一年形單影隻,只得依附當年仇敵國民黨極端派的殘餘郁慕明、宋楚瑜、章孝慈。
(節錄自十二、以名滾名的游士典型——李敖)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