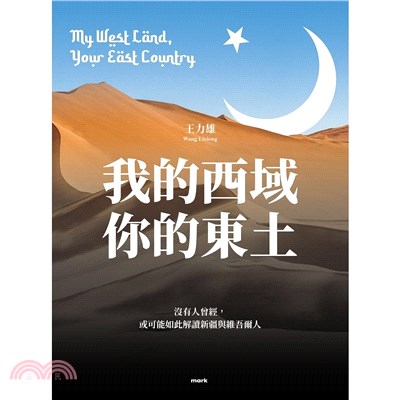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中國最敢言作家王力雄從維吾爾人出發的新疆議題爬梳。
●在新疆議題為舉世關注之前就已經從內部探索,深入議題的核心源頭。於「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前便提出警醒,因此本書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
●經典作品全新版本,新增〈十六年後續篇〉,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站到維吾爾人中間來思索
直接進入新疆議題的核心
中國最敢言的作家──《黃禍》、《天葬》、《權民一體論》作者王力雄
探索新疆議題經典著作新版,新增〈十六年後續篇〉
何謂「新疆」?顧名思義,「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而言,那片土地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近年來,「新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超過「西藏問題」,成為北京當局最頭疼的民族問題。所謂「新疆問題」,核心所在就是「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運動。九一一之後,中共當局以反恐名義全力鎮壓該獨立運動,導致整個維吾爾自治區更為緊張的對立局勢。後來的「七五事件」與「再教育營」,使得新疆議題全面躍上國際視線。
一九九九年,王力雄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他最初的想法。不過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文件」的指控,讓他鋃鐺入獄,而這個牢獄之災卻也成了他理解新疆的轉捩點。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他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同是政治犯的為維吾爾人穆合塔爾。正是因為有了他,這本書才有了新的角度。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他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
第一部分是王力雄被捕經歷的追憶,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作者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四次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核心――王力雄對穆合塔爾的訪談。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的談論,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議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王力雄對新疆問題的思考,以寫給穆合塔爾的信呈現。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的初版,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發生在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此次的新版添加了〈十六年後續篇〉,王力雄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王力雄
●在新疆議題為舉世關注之前就已經從內部探索,深入議題的核心源頭。於「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前便提出警醒,因此本書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
●經典作品全新版本,新增〈十六年後續篇〉,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站到維吾爾人中間來思索
直接進入新疆議題的核心
中國最敢言的作家──《黃禍》、《天葬》、《權民一體論》作者王力雄
探索新疆議題經典著作新版,新增〈十六年後續篇〉
何謂「新疆」?顧名思義,「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而言,那片土地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近年來,「新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超過「西藏問題」,成為北京當局最頭疼的民族問題。所謂「新疆問題」,核心所在就是「東土耳其斯坦」的獨立運動。九一一之後,中共當局以反恐名義全力鎮壓該獨立運動,導致整個維吾爾自治區更為緊張的對立局勢。後來的「七五事件」與「再教育營」,使得新疆議題全面躍上國際視線。
一九九九年,王力雄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他最初的想法。不過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文件」的指控,讓他鋃鐺入獄,而這個牢獄之災卻也成了他理解新疆的轉捩點。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他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同是政治犯的為維吾爾人穆合塔爾。正是因為有了他,這本書才有了新的角度。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他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
第一部分是王力雄被捕經歷的追憶,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作者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四次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核心――王力雄對穆合塔爾的訪談。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的談論,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議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王力雄對新疆問題的思考,以寫給穆合塔爾的信呈現。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的初版,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發生在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此次的新版添加了〈十六年後續篇〉,王力雄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王力雄
作者簡介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驚悚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影響力深遠。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大典》(以今日中國現實狀況為背景的政治驚悚小說)、《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權民一體論》(解決溝通結構被權力綁架的困境,避免社會動盪的遞進自組織社會制度思考)。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驚悚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影響力深遠。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大典》(以今日中國現實狀況為背景的政治驚悚小說)、《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權民一體論》(解決溝通結構被權力綁架的困境,避免社會動盪的遞進自組織社會制度思考)。
序
【自序】
再版前言
我於二○○七年在大塊文化出版《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二○○九年七月五日前後,發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然而這本在七五之前寫的書,幾乎都是當時新疆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用不著預測,明眼人當時就能看出類似七五的事件遲早爆發,所謂的轉折不是七五造成的結果,而是早已發生,其實是導致七五的原因。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經十六年,因為內容皆是我親身經歷與訪談,對了解新疆問題仍是第一手資料;其中的思考仍有尚待顯現的預見性。對跨越的十六年,我在本書最後的〈十六年後續篇〉中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二○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
前言
……新疆……寫下這兩個字讓我頗費躊躇,它是中國現實領土六分之一面積的稱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兩千多萬人民時刻掛在嘴上的名稱。但是當我在頭腦裡面對這本書的可能讀者時,會浮現我在波士頓經歷的場面。那是一個關於「族群」問題的研討會,到會的有藏人、蒙古人、臺灣人,還有大陸漢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維吾爾人代表,該到場的肯定不能算完整。當會議已經開始,才有一位維吾爾人從德國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向與會者宣佈,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絕參加會議。
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的歷史。什麼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麼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裡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麼又會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麼可能叫「新疆」呢?何況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經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過,只要談那片廣闊土地上的事,總得用一個名稱。最終我還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種現實的不得已(即使是東土人士談具體話題也難避免用「新疆」),其實也能讓雙方都從中各取所需――維吾爾人能以此證明他們的土地是被中國所占,中國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歸屬。
用這麼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僅為說明選擇地名的困難,而是想說明新疆問題的複雜。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糾葛與對立,揭示新疆問題全貌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本書寫作的起點,應該是一九九九年。那時我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沒有在新疆入獄,那寫作應該會按部就班地進行,書也會在幾年前就已問世。不過那樣寫出的書一定和這本不一樣。它會像《天葬》有個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臨下地概述,力圖包容新疆問題的全貌。但是當我被關進新疆的監獄,被勒令從此不可再觸碰任何官方資料,使我不得不放棄框架式的寫作。新疆問題的真實資訊幾乎都被封閉在官方資料內。沒有官方資料,框架是建不起來的。
不過這卻可以算作一種成全。入獄使我更深地進入了新疆的情景。當我準備繼續寫這本書時,已經變得躊躇漸多,不再覺得有資格搭建框架和居高臨下地概述,更不敢輕易給出結論。入獄是這變化的轉捩點。當監獄之門在我身後鋃鐺上鎖,進入新疆的另一道門卻悄然打開。那道門內的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我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
於是,我不再為缺少官方資訊而遺憾,也不再認為那是缺陷。資訊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沒人能比統治者得到更多資訊,卻不能說統治者瞭解了事物真相。歷史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過了一輩子的殖民者,又何嘗懂得那裡的人民?我寫新疆,重要的不在羅列資訊。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祕密,價值也不如去展現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去瞭解他們的生活、情感和願望。
這無疑非常困難。不錯,在新疆境內,每天都可以見到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作為一個漢人,你可以跟他們打交道、做買賣、討價還價,也許還可以開個玩笑。但所有這些都不意味你能進入他們內心。在漢人面前,他們把內心嚴密地包藏起來。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那雖然花費很多時間,耗費不少資財,但卻比看見一個維吾爾人的內心要容易。可以說,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即使在維吾爾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漢人圈子。不是我沒有接觸他們的願望,是他們不接納。每天在眼前掠過的維吾爾人,僅僅是街道或巴扎(維吾爾語: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對此,海外維吾爾人的發言並非可以全部彌補。他們可以講新疆境內沒人敢講的話,但是並不完整。角色的對立使他們的話語與中國官方涇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現的往往是政治姿態和組織立場。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內的維吾爾人內心想什麼。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第一部分是我離開監獄後的追憶,記錄了我被捕經歷,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我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是根據當時的旅行日記編寫。四次我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新疆對我的吸引,穆合塔爾已經是主要因素。那四次遊歷幾乎覆蓋了整個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沒有機會自己遊歷新疆的讀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儘管走馬觀花,卻至少是瞭解新疆的基礎。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重點――我對穆合塔爾的訪談。那是按現場錄音整理出來的,除了理順口語,基本保持原貌。你會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那席話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問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對新疆問題的思考。寫在我給穆合塔爾的信中。雖然被放在書的最後,卻不是結論。本來計畫等待穆合塔爾回應,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書。但是關係到維吾爾民族命運的話題,光靠寫幾封信是不夠的,需要由穆合塔爾寫出自己的書。
我為此書致謝的人可以開出長長名單,然而還是像以往在中國境外出書一樣――出於安全考慮無法公開。我只能心懷感激,默念名單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當然是穆合塔爾。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顯而易見,那不能讓需要防範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只能讓對他無害的讀者不知道他是誰。從這個角度,公開他的名字不會更有害,也許還能對他多一點保護。
不過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這樣做不會是一個錯誤。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夢見,我和穆合塔爾又坐在同一間牢房。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恐懼,沒有憂傷,好像那就是該有的命運,只是安靜相對,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再版前言
我於二○○七年在大塊文化出版《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比新疆民族問題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早了兩年。七五事件是二○○九年七月五日前後,發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維漢民族仇殺,數千人傷亡,被視為維吾爾人與漢人從此整體敵對,當局治疆從發展經濟為主轉向政治高壓的轉折點。《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因此被認為具有預見性,走在歷史之前。然而這本在七五之前寫的書,幾乎都是當時新疆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用不著預測,明眼人當時就能看出類似七五的事件遲早爆發,所謂的轉折不是七五造成的結果,而是早已發生,其實是導致七五的原因。
這本書出版至今已經十六年,因為內容皆是我親身經歷與訪談,對了解新疆問題仍是第一手資料;其中的思考仍有尚待顯現的預見性。對跨越的十六年,我在本書最後的〈十六年後續篇〉中新寫了兩位維吾爾朋友和一位西藏仁波切的命運,可以視為本書的續寫,供讀者一窺新疆問題和中國民族問題在這十六年的發展和現狀。
二○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北京
前言
……新疆……寫下這兩個字讓我頗費躊躇,它是中國現實領土六分之一面積的稱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兩千多萬人民時刻掛在嘴上的名稱。但是當我在頭腦裡面對這本書的可能讀者時,會浮現我在波士頓經歷的場面。那是一個關於「族群」問題的研討會,到會的有藏人、蒙古人、臺灣人,還有大陸漢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維吾爾人代表,該到場的肯定不能算完整。當會議已經開始,才有一位維吾爾人從德國姍姍來遲。他的第一句話是向與會者宣佈,如果有人使用「新疆」二字,他便拒絕參加會議。
新疆……一旦進入某種場合,就從一個地名變成包含很多難題和對抗的歷史。什麼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釋是「新的疆土」。但是對維吾爾人,那片土地怎麼會是他們「新的疆土」,明明是他們的家園,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對佔領者才是「新的疆土」。維吾爾人不願意聽到這個地名,那是帝國擴張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時是當地民族屈辱與不幸的見證。
新疆――即使對中國也是個尷尬地名。既然各種場合都宣稱那裡自古屬於中國,為什麼又會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學者絞盡腦汁,把「新疆」解釋成左宗棠所說「故土新歸」,卻實在牽強,那明明應該叫「故疆」才對,怎麼可能叫「新疆」呢?何況早在左宗棠前一百年,那片土地就已經被清王朝叫做「新疆」了。
不過,只要談那片廣闊土地上的事,總得用一個名稱。最終我還是用了「新疆」,除了是一種現實的不得已(即使是東土人士談具體話題也難避免用「新疆」),其實也能讓雙方都從中各取所需――維吾爾人能以此證明他們的土地是被中國所占,中國也能以此宣示疆土的歸屬。
用這麼多篇幅,我的目的不是僅為說明選擇地名的困難,而是想說明新疆問題的複雜。僅地名就已存在如此糾葛與對立,揭示新疆問題全貌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本書寫作的起點,應該是一九九九年。那時我剛出版《天葬――西藏的命運》。再寫一本新疆問題的《天葬》是我最初的想法。如果沒有在新疆入獄,那寫作應該會按部就班地進行,書也會在幾年前就已問世。不過那樣寫出的書一定和這本不一樣。它會像《天葬》有個面面俱到的框架,居高臨下地概述,力圖包容新疆問題的全貌。但是當我被關進新疆的監獄,被勒令從此不可再觸碰任何官方資料,使我不得不放棄框架式的寫作。新疆問題的真實資訊幾乎都被封閉在官方資料內。沒有官方資料,框架是建不起來的。
不過這卻可以算作一種成全。入獄使我更深地進入了新疆的情景。當我準備繼續寫這本書時,已經變得躊躇漸多,不再覺得有資格搭建框架和居高臨下地概述,更不敢輕易給出結論。入獄是這變化的轉捩點。當監獄之門在我身後鋃鐺上鎖,進入新疆的另一道門卻悄然打開。那道門內的新疆不再是文件、書本和資訊中的符號,而是真實的血肉、情感乃至體溫。我與新疆的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從此有了脈絡相通、呼吸與共的感覺。
於是,我不再為缺少官方資訊而遺憾,也不再認為那是缺陷。資訊不是真理,甚至不一定是真相。沒人能比統治者得到更多資訊,卻不能說統治者瞭解了事物真相。歷史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在殖民地過了一輩子的殖民者,又何嘗懂得那裡的人民?我寫新疆,重要的不在羅列資訊。哪怕是掌握最核心的官方祕密,價值也不如去展現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去瞭解他們的生活、情感和願望。
這無疑非常困難。不錯,在新疆境內,每天都可以見到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作為一個漢人,你可以跟他們打交道、做買賣、討價還價,也許還可以開個玩笑。但所有這些都不意味你能進入他們內心。在漢人面前,他們把內心嚴密地包藏起來。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 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那雖然花費很多時間,耗費不少資財,但卻比看見一個維吾爾人的內心要容易。可以說,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即使在維吾爾人最集中的地方,我也只能出入漢人圈子。不是我沒有接觸他們的願望,是他們不接納。每天在眼前掠過的維吾爾人,僅僅是街道或巴扎(維吾爾語:集市)上的影像。
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中國官方近年對新疆研究投入很大。眾多官方研究者有權看文件,瞭解機密,見的人廣,到的地方多,卻唯一做不到打開維吾爾人的心扉。對此,海外維吾爾人的發言並非可以全部彌補。他們可以講新疆境內沒人敢講的話,但是並不完整。角色的對立使他們的話語與中國官方涇渭分明、黑白相反,展現的往往是政治姿態和組織立場。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生活在新疆境內的維吾爾人內心想什麼。在我看來,能聽到一個維吾爾人的心裡話,絕對勝過讀一百本外人寫新疆的書。
如果沒有新疆入獄,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穆合塔爾是我的同牢獄友。在今日中國,能讓維吾爾人接納漢人的地方,大概只有關押政治犯的監獄。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
這本書的內容是在不同時間所寫,但都和穆合塔爾有關。第一部分是我離開監獄後的追憶,記錄了我被捕經歷,包括與穆合塔爾的相識。
第二部分是我出獄後四次重返新疆的經歷,是根據當時的旅行日記編寫。四次我都和穆合塔爾見了面。新疆對我的吸引,穆合塔爾已經是主要因素。那四次遊歷幾乎覆蓋了整個新疆(只有北疆一角未到)。沒有機會自己遊歷新疆的讀者,不妨利用我的眼睛,儘管走馬觀花,卻至少是瞭解新疆的基礎。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重點――我對穆合塔爾的訪談。那是按現場錄音整理出來的,除了理順口語,基本保持原貌。你會如同坐在我的位置,傾聽一位維吾爾人敞開心扉。那席話將會帶你直接進入新疆問題的核心。
第四部分是我對新疆問題的思考。寫在我給穆合塔爾的信中。雖然被放在書的最後,卻不是結論。本來計畫等待穆合塔爾回應,和我的信放在一起再出書。但是關係到維吾爾民族命運的話題,光靠寫幾封信是不夠的,需要由穆合塔爾寫出自己的書。
我為此書致謝的人可以開出長長名單,然而還是像以往在中國境外出書一樣――出於安全考慮無法公開。我只能心懷感激,默念名單中的所有名字。排在最前面的當然是穆合塔爾。原本我用××××代替他,但是顯而易見,那不能讓需要防範的人不知道他是誰,只能讓對他無害的讀者不知道他是誰。從這個角度,公開他的名字不會更有害,也許還能對他多一點保護。
不過我仍然心存忐忑,祈求這樣做不會是一個錯誤。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夢見,我和穆合塔爾又坐在同一間牢房。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恐懼,沒有憂傷,好像那就是該有的命運,只是安靜相對,等待把牢底坐穿的一刻。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 北京
目次
再版前言
前言
相逢塔合穆爾――追記一九九九新疆遇難
密訪塔合穆爾――四次重返新疆的筆記
塔和穆爾如是說――訪談實錄
致塔和穆爾的信――新疆問題的思考
十六年後續篇
前言
相逢塔合穆爾――追記一九九九新疆遇難
密訪塔合穆爾――四次重返新疆的筆記
塔和穆爾如是說――訪談實錄
致塔和穆爾的信――新疆問題的思考
十六年後續篇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相逢穆合塔爾――追記一九九九年新疆遇難
以作家身份竊取祕密文件
在中國做研究,沒有官方身份無法得到官方資訊,甚至進不了官方機構的門,在新疆更是如此。我離開「體制」二十年,Q的研究機構屬於民間,照樣給不了我身份。但是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想來想去,唯一能利用的是中國作家協會。我在八十年代成為作家協會會員,那時的目的也是讓自己有個身份,不過從來沒用過,我和「作協」也一直沒有過聯繫。
按照章程,作家協會有義務協助會員進行創作採訪,別的提供不了,至少能開個介紹信。於是我拿著會員證去「作協」,辦出來一張紙,上面的紅色公章和正是我需要的。到新疆後,我與官方機構打交道、採訪和索要資料,全憑這張紙。這是我加入作協十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處。
不過,作家不是官,僅有作協會員的身份,照樣無法接觸「祕密文件」。所謂「祕密文件」在中國往往專指黨政機關內部文件。當我開始有意識地收集跟兵團有關的法規時,有一天喜出望外地在兵團機關某個辦公室發現了一本「文件彙編」。那厚厚一本裝幀簡陋的內部印刷物,彙集了從中央到新疆自治區針對兵團的多數文件。如果能拿到那個「文件彙編」,對我可以省太多事!然而在我試圖索要時,卻被辦公室的人嚴肅告知――「內部文件,不可外傳!」。
「文件彙編」封面上的確印有「祕密」二字,但我並沒有放在心上。中國當局一向把什麼都搞成「祕密」,也就往往不是祕密。那個「文件彙編」成了我的一個心事,很想拿到,不是看一遍,而是自己有一本。從法律角度研究兵團,不是靠籠統模糊的想法。籠統在法律面前是無效的,必須依據精確無誤的文本琢磨每個字。於是問題就變成了,兵團研究能不能搞下去,前提是得到那本「文件彙編」。
我去見「兵團老戰士」J時,事先就在打這個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肯定會有「文件彙編」。果然,我在他家剛一坐下,就在他身後的書架上發現了那個不起眼的書脊。
我和J接上頭,是他過去一個老部下寫信,再加上作家協會的介紹信。J沒有下層官僚的習氣,似乎把我當作一個可能的仲介,希望把他的話傳到北京決策層。我這個「作協」來人興趣太明顯地與文學無關,因此難免顯得有點神祕,容易讓人聯想起「特派」之類的角色。J話中有話地向我感歎,從北京看新疆,會比從新疆看高得多,遠得多,深得多,中央領導應該學古代那些賢明君主,不用多,派幾個人下來搞點「微服私訪」,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飾太平,瞭解到真實情況。
當我提出借閱那本「文件彙編」時,J爽快答應。我輕描淡寫說隨便翻翻,沒有透露要複印。為複印又費了一番心思。雖然滿街都有複印店,但是不久前一位臺灣記者就是被複印店舉報稿件中有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因此被新疆警方拘押。我若複印一整本文件,更逃不過烏魯木齊人民的火眼金睛。好不容易輾轉一番,最後是托熟人在辦公室私下做了複印。
我把「文件彙編」還給了J。因為擔心郵寄丟失,沒把複印本隨資料寄回北京,而是帶在身邊。這樣,我的新疆之行圓滿結束,踏上回程,對正在身前身後張開的羅網,絲毫沒有覺察。
祕密警察的跟蹤
事後想起感到奇怪,似乎被捕前的那段時間,我關於自身安全的感覺都關閉了。照理說我剛出版《天葬》,同時公開了《黃禍》作者的身份,而官方正在加強政治鎮壓,我為何會在這時失去警惕呢?
進監獄後,想起來新疆前與兩個外國人談話,不免感到慚愧。我在談話時這樣解釋中國政治――今日中共比過去聰明,雖然打擊底層造反者依然強硬,卻可以容忍持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立場的知識精英。因為共產黨已經懂得,與他們不那麼一致的頭腦產生的思想資源也可以為他們所用。我說那話時,顯然把自己定位於能為當權者所用的知識精英,似乎只要與底層造反者劃清界限,就可以被恩賜持有異見的特權。我的安全敏感之所以失靈,可能就是這種膚淺認識的結果。
當J暗示我可能有「欽差」身份時,我並沒有明確否認,我自認研究可以對當局產生影響,也願意有那樣的效果。可想而知,帶著那樣一種自我感覺,難道還能注意身後有沒有盯梢,旁邊有沒有密探,電話有沒有竊聽嗎?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詳細記錄,每天整理採訪談話,記錄的文字、錄音磁帶、聯絡位址都攤在旅館房間裡,絲毫沒想過每次離開時監視者可以進去盡情查看。
一直到我離開烏魯木齊,什麼事都沒有。後來我瞭解到,那是祕密警察的工作習慣。只要目標在他們掌控之下,就不會著急抓捕,而是要拖到最後一刻,讓目標儘量多活動,以發現更多線索。
新疆如同一個口袋,向東進入中國內地的路雖有兩條,實際等於是一條,因為從若羌翻阿爾金山去青海的路遠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涼,絕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車都走烏魯木齊到蘭州的公路。那條路的新疆甘肅交界處叫星星峽,新疆警方長年設有堵截抓捕的關卡。那裡將是我不能逾越的界線。
懵然不知的我開車穿越天山,車內暖氣融融,隔絕著外面的冰雪。聽著日本作曲家喜多郎的西域音樂,阿克在旁邊座位沉睡。在孤獨中欣賞窗外風景,是我喜歡的狀態。一輛日本造的越野吉普車超過我,逐漸又被我超過,絲毫沒引起我注意。後來我才知道,那車裡就是即將抓捕我的祕密警察。他們像貓捉老鼠之前那樣,正在玩味我這個沒有知覺的獵物。
快到吐魯番時,日本吉普車又一次超過我,徑直先進城裡。前夜我打電話跟烏魯木齊友人告別,說了今天會在吐魯番過夜。十幾年前我在吐魯番住過一段,希望故地重遊。我向友人詢問了吐魯番旅館的情況,因此監聽電話的警察不僅得知我將住吐魯番,還知道要住哪家旅館。他們先進城,應該是提前去旅館安排監控。然而我進吐魯番後,看到滿眼都是平庸陋俗的「現代化」,便一路往下希望找到當年的感覺,以不枉多年的懷念,結果穿過整座城市都是一個模樣。我便失去了再進城的興趣,乾脆一踩油門開往下一座城市――哈密。後來聽說,祕密警察在旅館等不到我,著實忙亂了一陣,以為我布了個金蟬脫殼的迷陣呢。
傍晚到哈密,在城邊找了家旅館住下。飯後阿克留在房間看電視,我去黑夜哈密迷宮般的小巷轉了兩三個小時。回到旅館,阿克仍然躺在床上看電視,卻說剛來了一幫警察,把我們車開到交通大隊扣下,理由沒說,讓明天去處理。我出去看了看,車的確不在,知道不是阿克捉弄我。我和阿克討論可能是什麼事。車是在我到銀川後阿克才買的,上牌照至少要十天,我們不想等那麼久,就用新車的「移動證」上路了。所謂「移動證」是新車從購車地開到用車地的證明。買車時阿克把用車地寫成烏魯木齊,不用牌照就可以往新疆走,現在反著往回走就成了問題。交通警察如果追究這一點,只好認倒楣,但也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煩,沒什麼了不起。
後來在監獄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就警覺,有沒有機會逃走?可以雇輛計程車到星星峽,也就二百公里,用不了三小時。在關卡前下車,趁夜色從戈壁灘上繞行,步行三十公里到甘肅的馬蓮井,從那裡搭車去內蒙或青海,捉迷藏的餘地就大多了。不過那純粹是一種精神遊戲,既然我當時絲毫警覺未產生,也就沒有後悔的理由。何況阿克的車被扣,我也不能甩下他。
我們出了人命?
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先去哈密交通隊。像中國各地的交通隊一樣,那裡擠滿人,人手一隻煙,個個都在諂媚警察,托關係走後門。警察們大權在握的模樣,傲慢冷漠,說不上話。我們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等。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沒人說明。
正當我樓上樓下亂走不知找誰的時候,一間辦公室內突然有人打招呼,一個穿毛衣的中年人向我招手,讓我受寵若驚,總算有人理了,反倒沒深想他為什麼要理我,不理別人?那人不像其他警察,態度和藹可親,對我一連串提問,他娓娓道來解釋:昨天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輛載有兩個人的摩托車被一輛超過的轎車別了一下,造成摩托車翻下公路,駕駛員當場死亡,另一人受傷。據現場目擊者說,超車轎車是一輛黑色桑塔納2000,無牌照,跟你們的車一樣。我說不可能,我們的車沒有別過任何摩托車,你們也可以看到我們車上沒有任何痕跡。他說出這種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觸,對你們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車後回輪太快,一個小小的操作不當,但是被超的車做了一個幅度過大的躲閃動作,就可能沖下公路,造成事故。因為出事時候你們已經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們可能都不會覺察發生了事故。
他這番話說得很圓,我無法反駁。他又說也沒有認定事故就是你們造成的,但是因為死了人,也報了警,總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煩你們在這裡呆一段時間,配合查清問題。他為耽誤我們的行程表示歉意,對我接著就事故時間、地點等提出的問題,也耐心地一一回答。我問他姓什麼,他說姓薛,還跟我扯了一會家常。
隨後我在交通隊門口張貼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這位親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標明姓薛,職務是交通隊的指導員,照片上的臉卻明顯對不上號,不是他。剛才他的確是從掛著「指導員辦公室」牌子的房間裡叫我,一個到交通隊辦事的當地人從門外路過打招呼,卻稱他「處長」。交通隊怎麼會有處長呢?我當時已經顧不得對此深想,思維完全纏繞在我是不是害死了一個人上。那是人命關天的事,使我深受震動。我無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個什麼人。而且我越是回憶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看到我開車超過了一輛摩托車,連那騎手的棉帽是什麼形狀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嗎?
當我和阿克在交通隊旁一個清真小館吃面時,我向他說了剛剛瞭解的情況。阿克沉吟半晌,說他不認為是這麼回事,裡面肯定有文章。阿克平時表面大大咧咧,一般總是對我言聽計從,實際上內心精明,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但我當時卻沒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個「死者」纏繞不休。
下午,總算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隊的指導員。他說辦案警察正在調查事故現場,得等他們回來才能進入處理。於是我讓阿克在交通隊繼續等,自己回到旅館,想睡一覺,看能不能躲開那個「死者」的冤魂。
哈密被捕
後來我把各種線索聯繫起來,編織出當時情景:跟蹤的警察在吐魯番失去我的蹤跡,雖然忙亂,但是並不慌張,因為我們只有星星峽一條路,一個電話就能布好堵截,我們插翅也飛不過去,同時沿途城鎮的警察都會查找。哈密警察就是在對各旅館進行檢查時發現了我們。只是那時天已晚,執行抓捕的祕密警察只能第二天再從吐魯番趕到哈密。於是哈密警察就編造了一個交通事故,先把車扣下,讓我們無法跑掉。第二天在交通隊也是繼續拖時間,等待執行抓捕的警察從吐魯番趕到。至於那位自稱「薛」姓的處長(後來再沒有露過面),真實身份應該是哈密地區安全處的處長,來交通隊坐鎮指揮。那天我周圍肯定一直有便衣監視,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直到傍晚才動手。從吐魯番趕來的警察應該在下午二點就到了,那時我在交通隊的走廊裡看書,一個人看我的眼神奇怪,我以為是在交通隊那種不讀書的地方有人讀書顯得異類才被那麼看。等到抓我的人沖進旅館房間時,我發現那人也在其中,已經換上警服。後來我知道他姓楊,是新疆安全廳九處的一個科長,主辦我的案子。
被抓時我正躺在床上看書。「死人」纏繞使我無法入睡。聽見有人敲門,我想也沒想就去開門。黑壓壓一堆人隨著門開轟然湧入。最前面是一個兩米身高的大個(後來我知他是前排球運動員),把警官證亮在我眼前,隨後宣佈我攜帶危害國家安全的物品,依法對我進行搜查。另一些人圍住我照相錄影,閃光燈不停,使我產生了如同召開記者招待會的感覺。我當時沒有特別驚慌,腦子轉了一圈,知道只有複印的「文件彙編」可能是他們的目標。我把那複印件從包裡拿出,問他們是不是找這個。
好,證據確鑿(他們當然早知道),就可以名正言順拘捕了。隨後一切按程序展開,檢查物品,一一登記。他們扣留的,除了要我確認,還要在場的旅館保安見證和簽字。搜查中間阿克回來,照相機和攝像機又一齊對準他。他憤怒抗議。當時我還勸他冷靜,照個相有什麼了不得。同時我跟警察說,我做的所有事阿克都不知道,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如果說那時我對自己將會怎樣完全不清楚,至少一點可以感到安慰――不會連累阿克,因為我什麼都沒有跟他說過。我來新疆要做什麼,背景是什麼,見過什麼人,搞過什麼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我對他保密,沒有什麼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對那些不感興趣。出發前他要我帶些新寫的東西給他看,我特地列印了一份未完成的書稿,但他只看了一頁就昏昏入睡,從此再沒翻過。我被抓後,那書稿的「反動內容」倒成了我的罪證之一。
我和阿克被分開帶走,被捕期間再沒見過面。後來聽說幾天後就讓他開車回寧夏了,因為他一問三不知,的確什麼都不知道,那效果是裝不出的。審問者只能認為他是個傻帽,糊里糊塗被我利用了。
「反間諜支隊」的羅網
被捕的第一晚我被關在哈密一處不起眼的建築中。安全部門有偽裝成不同面目的據點。起初我沒認為事情有多嚴重。即使複印的文件有「祕密」字樣,但類似的「祕密」到處可見,無人在意,也少有人因此擔上罪名。不過我沒說複印文件是為做研究,也沒有扯出Q的機構。雖然Q有言在先不需要隱瞞,但是我打著作協會員的身份,拿著中國作協的介紹信,扯出個民間研究機構容易複雜化,於是我只說是為寫書來新疆收集材料。
關於複印件原稿從哪來,我知道警方一定已經掌握,要做的只是別讓J擔責任,便告訴審問者我如何拿作協介紹信去兵團宣傳部聯繫,再由兵團宣傳部介紹給J,因此J借給我「文件彙編」不屬違紀,我進行複印他也不知情,一切責任在我。
我馬上發現,寫書的說法和承攬複印文件的責任正是審問者需要的。既然對違法行為「供認不諱」,就有了進一步拘押和審判的法律根據;而複印文件的目的是為寫書,就有了盜竊情報換取金錢的關係,以寫書換稿費可以被視為間接出賣情報。不過這種邏輯不是一下子就讓我能清楚看到。他們的審訊手法講究迂回,不會讓你猜到引向何方,以免你躲避陷阱。我開始擔心,他們花了那麼大力氣,不會是僅為辦一個複印文件的案子吧?
第二天才讓我在拘傳文件上簽字,我意識到事情可能比我想像得嚴重。發出拘傳文件的單位欄裡填寫著「哈密地區國家安全處反間諜支隊」,這使我陷入深思。我當然不是間諜,然而事實到底是什麼並不重要,共產黨製造過無數冤案,從來不看事實,而是需要。一九九九年被當局視為「大事之年」。在這一年裡,接踵而來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關口,當局對這一年會不會出事心懷緊張,層層佈置嚴加防範。除了打壓民主黨組黨,重判了民主黨骨幹,還有數位知識份子被捕,以及民間知識份子組織被禁等鎮壓措施。
被抓以前,我沒有把這些事串起來看,現在才開始認真面對,我會不會也是當局安渡「大事之年」棋盤上要動的一顆棋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識界與我類似的人不要亂說亂動,不僅是對「現行」活動的警告,還可以傳達秋後算帳的威脅――就算《黃禍》已過多年,仍然逃不了應有懲罰! 而對不久前出版的《天葬》,就更有直截了當的恫嚇效果。
第二天,我被押上那輛一路跟蹤的日本越野車返回烏魯木齊。一棟外表看上去像老式居民樓那樣普通的建築,鐵門緊閉,進出複雜。那是新疆安全廳的一個祕密據點。我被帶進其中一個單元。楊科長煞有介事地展開一張紙向我朗讀,宣佈對我實施「監視居住」。我的「居住地」就是那單元房內一個小間,鐵欄封窗,窗上結著厚厚冰花,不透視線。
專業屠夫的宰割
接連幾天的審訊都是在關我那間小屋進行。一天審數次。每次由牆角一台攝像機錄下全過程。初期審訊者是一位哈密安全處的警員,完全用對待罪犯的方式。我和他的對抗逐步升級。隨後他便消失了,再未出現,換上楊科長登場。楊對我解釋因為那警員態度不好被撤換,著實讓我心裡溫暖了一下。但是不久我就明白,先出場的人態度蠻橫是一種有意安排,他們總是有人演紅臉,也有人演黑臉,是規範化的工作程序。
不過在我還不能看懂這種手法的時候,換上溫文有禮的楊科長,讓我感覺遇到了知心人――這就是黑臉先出場的作用。楊科長不是一本正經坐在審訊桌後,而是跟我面對面地促膝聊天(雖然我們的膝離得挺遠,卻給了我那感覺);負責記錄的任警員面目慈祥,笑容可掬;還有開車的祁師傅對我問寒問暖,關照我的生活;女警員小李動輒叫我「王老師」。可是沒過多久,我就知道這種方式比哈密那警員的簡單粗暴更難對付。對黑臉你可以乾脆不理他,你能被激發出鬥志。可現在人家笑盈盈地圍著你聊天,說都是為了你早獲自由,要把問題瞭解清楚,你總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開口說話,他們就會引導你不斷往下說。比如你接觸過甲,他們會問和甲怎麼認識的?如果是通過乙,就會問乙是什麼樣的人,人在哪裡,做什麼工作,然後再問和乙又是怎麼認識的?是通過丙?好,那再開始問丙……這樣的「談話」很快對我形成極大壓力。雖然我可以不說對別人不利的話,我這次接觸的人都屬泛泛,沒有實質內容,所以不會造成任何連累。但即使只說出別人名字,也讓我免不了有出賣的感覺。
除非是什麼話都不說,就像張春橋當年對付審訊那樣 。然而張春橋有那種意志,是因為知道無論怎樣都不可能改變他的下場。我卻是千方百計想把自己解釋清楚。我推翻了原來說的為寫書收集資料,告訴他們真實目的是做新疆問題研究,複印文件不是為了寫書,更不會危害國家安全,相反是要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對方一句話就讓我啞口無言:法律不考慮動機,一個好人殺了壞人照樣是犯法。不管你的動機是什麼,你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規定已經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們也可以幫你解脫――結果怎麼樣,完全取決你的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你產生了對方能幫你解脫的幻想,就不會有勇氣不回答審訊,頂多是不說對他人不利的話。
如果把審訊視為一場鬥智,被審者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審訊者是一個組織體系,有專業知識,有分工合作,掌控一切資訊和資源。而被審者的一切渠道都被封鎖,孤獨無助,任人宰割。對我來講,壓力最大的不是審訊過程中,雖然那時腦筋轉動激烈,事後會感到筋疲力盡,但比起審訊之間的間歇,至少不那麼緊張。審訊間歇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退到另外房間(那房間裡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沒搞清,只聽得到人來人往)。我清楚地知道一群專業屠夫就在離我咫尺的地方,合夥算計如何對我宰割,他們分析前面的審訊情況,尋找其中的破綻,商量對付的策略,擬定下一輪審訊內容,而我卻無法知道他們到底要怎麼做,要達到什麼目的。那時會拼命猜測,卻是絞盡腦汁也沒有可憑藉的資訊。那種大腦陷入盲目空轉的滋味非常難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時將從何處下手的刀割一樣。我逐漸開始產生頂不住的感覺,我怎麼能對付得了他們?!他們的職業就是整人,而且他們是一個機關!機關――何等形象和準確的一個詞!
我逐漸發現,他們的審訊手法分不同步驟與層次,經常故意製造一些迷惑,讓你搞不清他們的目的。也許每次問的是些不那麼重要的問題,你覺得回答起來不會對自己和別人有害,然而分開來看無足輕重的問題,合起來卻可能成為一個圈套,讓你不知不覺鑽進套中,而在最終明白的時候,已經無法解脫,因為你在每份審訊記錄上都簽下了「屬實」字樣,在每一頁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們最後把不同的審問記錄組裝在一起,你才會大吃一驚地發現,你承認的東西已經可以解釋為罪行。
儘管我已經告訴了他們我來新疆的目的,但他們並不相信:如果真是做有利於國家的研究,為什麼一開始不說,而是說寫書?何況你研究的結果是什麼?不是也要寫成書嗎?我能感覺他們是在往這樣一條路上引導:我多年一直盜竊國家祕密,炮製著作,換取金錢。我來新疆也是做同樣的事。甚至進一步,何必非以寫書換錢,直接竊取祕密出售豈不是更簡單?
出版《黃禍》和《天葬》兩本書的明鏡出版社,在中國情治部門眼中一直是重點懷疑對象。我和明鏡來往密切,明鏡在海外出版的大量涉及中國黨政軍內幕的出版物,會不會有我提供的情報?這似乎是非常合理的邏輯,甚至可以懷疑,我就是明鏡出版社在國內搜集情報的代理人和傳遞情報的樞紐!
審訊一度集中在我與明鏡出版社的金錢往來上,明顯是想從中發現我靠「出賣情報」得到的收入。這使我擔心陷入一個卡夫卡式的城堡,越來越說不清。我在香港有一個帳號,由明鏡出版社一個朋友與我共同署名並幫我管理,為的是收明鏡付給我的版稅。按規矩銀行每月會寄一份帳單給我。在來新疆的前兩個月,那位朋友的一筆錢被錯打進這個帳號,隨後馬上又被調走。那以後,銀行就不再把每月帳單寄給我,而是寄給明鏡的朋友,因此從我抽屜裡存放的帳單上,能看到有一筆錢在我來新疆前打進,卻看不到又被原封不動調走。安全機構對此能有什麼解釋呢――只能是來新疆刺探情報的經費。而我怎麼說清楚呢?可以作證的因素都在海外,無法得到,他們也不會相信。
審訊又轉向我的花銷。我的回答更是混亂,因為我基本不理財,說起來前後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特別像有鬼。在審訊者看來,我的生活方式需要不小的花費才能支持,如經常旅行,自己開車去西藏等。包括這次來新疆,竟買了一輛新車(好在能查證車屬於阿克)。如果對此解釋不清,至少有「財產來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經是罪名,何況對我,意義不止於經濟,還可以證明我是通過出賣情報換取收入的間諜!
他們真會相信我是間諜嗎?我覺得不應該。我哪有一點間諜模樣呢?就憑我對他們的監控毫無防範,從未有過任何「反偵查」,也足以說明我不可能是搞「祕密活動」。世上有這樣的間諜嗎?我努力和他們溝通,希望打消他們的懷疑,別往那種方向引導案情。
但我逐漸發現,問題其實不在於他們個人認為我是什麼,而在於他們的部門(或上司)需要我是什麼。中國年輕一代的情治人員基本已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對社會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聽你談論民主也會點頭附和。但你如果認為他們因此就會放你一馬,就大錯特錯了。相比之下,他們在這一點可能還不如上一輩。老輩情治人員有意識形態,面對「階級敵人」仇恨滿腔,可一旦瞭解到對方不是壞人,有時還真可能提供一些幫助。年輕一代則完全是技術化的,原則不再是意識形態,是他們的個人利益,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在於是非對錯,而在於他們個人能否完成任務、立功受獎。表面接觸,他們比老一代溫和,容易溝通,總是把自己擺在「吃這碗飯」的位置,說些有人情味的話,說他們是職業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配合」他們完成工作,別砸他們飯碗。然而你一旦被這種話打動,去「配合」他們的「飯碗」,結果一定遭殃。因為他們的「飯碗」是沒有底的,怎麼裝都不會滿。那些提升、加薪、獎金等有關他們個人的利益,取決的不是能否為你解脫冤情,而是能否板上釘釘地把你定為罪犯――不管事實上你是不是。
(摘錄)
相逢穆合塔爾――追記一九九九年新疆遇難
以作家身份竊取祕密文件
在中國做研究,沒有官方身份無法得到官方資訊,甚至進不了官方機構的門,在新疆更是如此。我離開「體制」二十年,Q的研究機構屬於民間,照樣給不了我身份。但是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想來想去,唯一能利用的是中國作家協會。我在八十年代成為作家協會會員,那時的目的也是讓自己有個身份,不過從來沒用過,我和「作協」也一直沒有過聯繫。
按照章程,作家協會有義務協助會員進行創作採訪,別的提供不了,至少能開個介紹信。於是我拿著會員證去「作協」,辦出來一張紙,上面的紅色公章和正是我需要的。到新疆後,我與官方機構打交道、採訪和索要資料,全憑這張紙。這是我加入作協十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處。
不過,作家不是官,僅有作協會員的身份,照樣無法接觸「祕密文件」。所謂「祕密文件」在中國往往專指黨政機關內部文件。當我開始有意識地收集跟兵團有關的法規時,有一天喜出望外地在兵團機關某個辦公室發現了一本「文件彙編」。那厚厚一本裝幀簡陋的內部印刷物,彙集了從中央到新疆自治區針對兵團的多數文件。如果能拿到那個「文件彙編」,對我可以省太多事!然而在我試圖索要時,卻被辦公室的人嚴肅告知――「內部文件,不可外傳!」。
「文件彙編」封面上的確印有「祕密」二字,但我並沒有放在心上。中國當局一向把什麼都搞成「祕密」,也就往往不是祕密。那個「文件彙編」成了我的一個心事,很想拿到,不是看一遍,而是自己有一本。從法律角度研究兵團,不是靠籠統模糊的想法。籠統在法律面前是無效的,必須依據精確無誤的文本琢磨每個字。於是問題就變成了,兵團研究能不能搞下去,前提是得到那本「文件彙編」。
我去見「兵團老戰士」J時,事先就在打這個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肯定會有「文件彙編」。果然,我在他家剛一坐下,就在他身後的書架上發現了那個不起眼的書脊。
我和J接上頭,是他過去一個老部下寫信,再加上作家協會的介紹信。J沒有下層官僚的習氣,似乎把我當作一個可能的仲介,希望把他的話傳到北京決策層。我這個「作協」來人興趣太明顯地與文學無關,因此難免顯得有點神祕,容易讓人聯想起「特派」之類的角色。J話中有話地向我感歎,從北京看新疆,會比從新疆看高得多,遠得多,深得多,中央領導應該學古代那些賢明君主,不用多,派幾個人下來搞點「微服私訪」,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飾太平,瞭解到真實情況。
當我提出借閱那本「文件彙編」時,J爽快答應。我輕描淡寫說隨便翻翻,沒有透露要複印。為複印又費了一番心思。雖然滿街都有複印店,但是不久前一位臺灣記者就是被複印店舉報稿件中有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因此被新疆警方拘押。我若複印一整本文件,更逃不過烏魯木齊人民的火眼金睛。好不容易輾轉一番,最後是托熟人在辦公室私下做了複印。
我把「文件彙編」還給了J。因為擔心郵寄丟失,沒把複印本隨資料寄回北京,而是帶在身邊。這樣,我的新疆之行圓滿結束,踏上回程,對正在身前身後張開的羅網,絲毫沒有覺察。
祕密警察的跟蹤
事後想起感到奇怪,似乎被捕前的那段時間,我關於自身安全的感覺都關閉了。照理說我剛出版《天葬》,同時公開了《黃禍》作者的身份,而官方正在加強政治鎮壓,我為何會在這時失去警惕呢?
進監獄後,想起來新疆前與兩個外國人談話,不免感到慚愧。我在談話時這樣解釋中國政治――今日中共比過去聰明,雖然打擊底層造反者依然強硬,卻可以容忍持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立場的知識精英。因為共產黨已經懂得,與他們不那麼一致的頭腦產生的思想資源也可以為他們所用。我說那話時,顯然把自己定位於能為當權者所用的知識精英,似乎只要與底層造反者劃清界限,就可以被恩賜持有異見的特權。我的安全敏感之所以失靈,可能就是這種膚淺認識的結果。
當J暗示我可能有「欽差」身份時,我並沒有明確否認,我自認研究可以對當局產生影響,也願意有那樣的效果。可想而知,帶著那樣一種自我感覺,難道還能注意身後有沒有盯梢,旁邊有沒有密探,電話有沒有竊聽嗎?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詳細記錄,每天整理採訪談話,記錄的文字、錄音磁帶、聯絡位址都攤在旅館房間裡,絲毫沒想過每次離開時監視者可以進去盡情查看。
一直到我離開烏魯木齊,什麼事都沒有。後來我瞭解到,那是祕密警察的工作習慣。只要目標在他們掌控之下,就不會著急抓捕,而是要拖到最後一刻,讓目標儘量多活動,以發現更多線索。
新疆如同一個口袋,向東進入中國內地的路雖有兩條,實際等於是一條,因為從若羌翻阿爾金山去青海的路遠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涼,絕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車都走烏魯木齊到蘭州的公路。那條路的新疆甘肅交界處叫星星峽,新疆警方長年設有堵截抓捕的關卡。那裡將是我不能逾越的界線。
懵然不知的我開車穿越天山,車內暖氣融融,隔絕著外面的冰雪。聽著日本作曲家喜多郎的西域音樂,阿克在旁邊座位沉睡。在孤獨中欣賞窗外風景,是我喜歡的狀態。一輛日本造的越野吉普車超過我,逐漸又被我超過,絲毫沒引起我注意。後來我才知道,那車裡就是即將抓捕我的祕密警察。他們像貓捉老鼠之前那樣,正在玩味我這個沒有知覺的獵物。
快到吐魯番時,日本吉普車又一次超過我,徑直先進城裡。前夜我打電話跟烏魯木齊友人告別,說了今天會在吐魯番過夜。十幾年前我在吐魯番住過一段,希望故地重遊。我向友人詢問了吐魯番旅館的情況,因此監聽電話的警察不僅得知我將住吐魯番,還知道要住哪家旅館。他們先進城,應該是提前去旅館安排監控。然而我進吐魯番後,看到滿眼都是平庸陋俗的「現代化」,便一路往下希望找到當年的感覺,以不枉多年的懷念,結果穿過整座城市都是一個模樣。我便失去了再進城的興趣,乾脆一踩油門開往下一座城市――哈密。後來聽說,祕密警察在旅館等不到我,著實忙亂了一陣,以為我布了個金蟬脫殼的迷陣呢。
傍晚到哈密,在城邊找了家旅館住下。飯後阿克留在房間看電視,我去黑夜哈密迷宮般的小巷轉了兩三個小時。回到旅館,阿克仍然躺在床上看電視,卻說剛來了一幫警察,把我們車開到交通大隊扣下,理由沒說,讓明天去處理。我出去看了看,車的確不在,知道不是阿克捉弄我。我和阿克討論可能是什麼事。車是在我到銀川後阿克才買的,上牌照至少要十天,我們不想等那麼久,就用新車的「移動證」上路了。所謂「移動證」是新車從購車地開到用車地的證明。買車時阿克把用車地寫成烏魯木齊,不用牌照就可以往新疆走,現在反著往回走就成了問題。交通警察如果追究這一點,只好認倒楣,但也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煩,沒什麼了不起。
後來在監獄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就警覺,有沒有機會逃走?可以雇輛計程車到星星峽,也就二百公里,用不了三小時。在關卡前下車,趁夜色從戈壁灘上繞行,步行三十公里到甘肅的馬蓮井,從那裡搭車去內蒙或青海,捉迷藏的餘地就大多了。不過那純粹是一種精神遊戲,既然我當時絲毫警覺未產生,也就沒有後悔的理由。何況阿克的車被扣,我也不能甩下他。
我們出了人命?
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先去哈密交通隊。像中國各地的交通隊一樣,那裡擠滿人,人手一隻煙,個個都在諂媚警察,托關係走後門。警察們大權在握的模樣,傲慢冷漠,說不上話。我們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等。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沒人說明。
正當我樓上樓下亂走不知找誰的時候,一間辦公室內突然有人打招呼,一個穿毛衣的中年人向我招手,讓我受寵若驚,總算有人理了,反倒沒深想他為什麼要理我,不理別人?那人不像其他警察,態度和藹可親,對我一連串提問,他娓娓道來解釋:昨天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輛載有兩個人的摩托車被一輛超過的轎車別了一下,造成摩托車翻下公路,駕駛員當場死亡,另一人受傷。據現場目擊者說,超車轎車是一輛黑色桑塔納2000,無牌照,跟你們的車一樣。我說不可能,我們的車沒有別過任何摩托車,你們也可以看到我們車上沒有任何痕跡。他說出這種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觸,對你們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車後回輪太快,一個小小的操作不當,但是被超的車做了一個幅度過大的躲閃動作,就可能沖下公路,造成事故。因為出事時候你們已經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們可能都不會覺察發生了事故。
他這番話說得很圓,我無法反駁。他又說也沒有認定事故就是你們造成的,但是因為死了人,也報了警,總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煩你們在這裡呆一段時間,配合查清問題。他為耽誤我們的行程表示歉意,對我接著就事故時間、地點等提出的問題,也耐心地一一回答。我問他姓什麼,他說姓薛,還跟我扯了一會家常。
隨後我在交通隊門口張貼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這位親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標明姓薛,職務是交通隊的指導員,照片上的臉卻明顯對不上號,不是他。剛才他的確是從掛著「指導員辦公室」牌子的房間裡叫我,一個到交通隊辦事的當地人從門外路過打招呼,卻稱他「處長」。交通隊怎麼會有處長呢?我當時已經顧不得對此深想,思維完全纏繞在我是不是害死了一個人上。那是人命關天的事,使我深受震動。我無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個什麼人。而且我越是回憶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看到我開車超過了一輛摩托車,連那騎手的棉帽是什麼形狀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嗎?
當我和阿克在交通隊旁一個清真小館吃面時,我向他說了剛剛瞭解的情況。阿克沉吟半晌,說他不認為是這麼回事,裡面肯定有文章。阿克平時表面大大咧咧,一般總是對我言聽計從,實際上內心精明,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但我當時卻沒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個「死者」纏繞不休。
下午,總算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隊的指導員。他說辦案警察正在調查事故現場,得等他們回來才能進入處理。於是我讓阿克在交通隊繼續等,自己回到旅館,想睡一覺,看能不能躲開那個「死者」的冤魂。
哈密被捕
後來我把各種線索聯繫起來,編織出當時情景:跟蹤的警察在吐魯番失去我的蹤跡,雖然忙亂,但是並不慌張,因為我們只有星星峽一條路,一個電話就能布好堵截,我們插翅也飛不過去,同時沿途城鎮的警察都會查找。哈密警察就是在對各旅館進行檢查時發現了我們。只是那時天已晚,執行抓捕的祕密警察只能第二天再從吐魯番趕到哈密。於是哈密警察就編造了一個交通事故,先把車扣下,讓我們無法跑掉。第二天在交通隊也是繼續拖時間,等待執行抓捕的警察從吐魯番趕到。至於那位自稱「薛」姓的處長(後來再沒有露過面),真實身份應該是哈密地區安全處的處長,來交通隊坐鎮指揮。那天我周圍肯定一直有便衣監視,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直到傍晚才動手。從吐魯番趕來的警察應該在下午二點就到了,那時我在交通隊的走廊裡看書,一個人看我的眼神奇怪,我以為是在交通隊那種不讀書的地方有人讀書顯得異類才被那麼看。等到抓我的人沖進旅館房間時,我發現那人也在其中,已經換上警服。後來我知道他姓楊,是新疆安全廳九處的一個科長,主辦我的案子。
被抓時我正躺在床上看書。「死人」纏繞使我無法入睡。聽見有人敲門,我想也沒想就去開門。黑壓壓一堆人隨著門開轟然湧入。最前面是一個兩米身高的大個(後來我知他是前排球運動員),把警官證亮在我眼前,隨後宣佈我攜帶危害國家安全的物品,依法對我進行搜查。另一些人圍住我照相錄影,閃光燈不停,使我產生了如同召開記者招待會的感覺。我當時沒有特別驚慌,腦子轉了一圈,知道只有複印的「文件彙編」可能是他們的目標。我把那複印件從包裡拿出,問他們是不是找這個。
好,證據確鑿(他們當然早知道),就可以名正言順拘捕了。隨後一切按程序展開,檢查物品,一一登記。他們扣留的,除了要我確認,還要在場的旅館保安見證和簽字。搜查中間阿克回來,照相機和攝像機又一齊對準他。他憤怒抗議。當時我還勸他冷靜,照個相有什麼了不得。同時我跟警察說,我做的所有事阿克都不知道,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如果說那時我對自己將會怎樣完全不清楚,至少一點可以感到安慰――不會連累阿克,因為我什麼都沒有跟他說過。我來新疆要做什麼,背景是什麼,見過什麼人,搞過什麼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我對他保密,沒有什麼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對那些不感興趣。出發前他要我帶些新寫的東西給他看,我特地列印了一份未完成的書稿,但他只看了一頁就昏昏入睡,從此再沒翻過。我被抓後,那書稿的「反動內容」倒成了我的罪證之一。
我和阿克被分開帶走,被捕期間再沒見過面。後來聽說幾天後就讓他開車回寧夏了,因為他一問三不知,的確什麼都不知道,那效果是裝不出的。審問者只能認為他是個傻帽,糊里糊塗被我利用了。
「反間諜支隊」的羅網
被捕的第一晚我被關在哈密一處不起眼的建築中。安全部門有偽裝成不同面目的據點。起初我沒認為事情有多嚴重。即使複印的文件有「祕密」字樣,但類似的「祕密」到處可見,無人在意,也少有人因此擔上罪名。不過我沒說複印文件是為做研究,也沒有扯出Q的機構。雖然Q有言在先不需要隱瞞,但是我打著作協會員的身份,拿著中國作協的介紹信,扯出個民間研究機構容易複雜化,於是我只說是為寫書來新疆收集材料。
關於複印件原稿從哪來,我知道警方一定已經掌握,要做的只是別讓J擔責任,便告訴審問者我如何拿作協介紹信去兵團宣傳部聯繫,再由兵團宣傳部介紹給J,因此J借給我「文件彙編」不屬違紀,我進行複印他也不知情,一切責任在我。
我馬上發現,寫書的說法和承攬複印文件的責任正是審問者需要的。既然對違法行為「供認不諱」,就有了進一步拘押和審判的法律根據;而複印文件的目的是為寫書,就有了盜竊情報換取金錢的關係,以寫書換稿費可以被視為間接出賣情報。不過這種邏輯不是一下子就讓我能清楚看到。他們的審訊手法講究迂回,不會讓你猜到引向何方,以免你躲避陷阱。我開始擔心,他們花了那麼大力氣,不會是僅為辦一個複印文件的案子吧?
第二天才讓我在拘傳文件上簽字,我意識到事情可能比我想像得嚴重。發出拘傳文件的單位欄裡填寫著「哈密地區國家安全處反間諜支隊」,這使我陷入深思。我當然不是間諜,然而事實到底是什麼並不重要,共產黨製造過無數冤案,從來不看事實,而是需要。一九九九年被當局視為「大事之年」。在這一年裡,接踵而來的有「六四」十周年、「五四」八十周年、西藏事件四十周年、千禧年等一系列關口,當局對這一年會不會出事心懷緊張,層層佈置嚴加防範。除了打壓民主黨組黨,重判了民主黨骨幹,還有數位知識份子被捕,以及民間知識份子組織被禁等鎮壓措施。
被抓以前,我沒有把這些事串起來看,現在才開始認真面對,我會不會也是當局安渡「大事之年」棋盤上要動的一顆棋呢?抓我可以警告知識界與我類似的人不要亂說亂動,不僅是對「現行」活動的警告,還可以傳達秋後算帳的威脅――就算《黃禍》已過多年,仍然逃不了應有懲罰! 而對不久前出版的《天葬》,就更有直截了當的恫嚇效果。
第二天,我被押上那輛一路跟蹤的日本越野車返回烏魯木齊。一棟外表看上去像老式居民樓那樣普通的建築,鐵門緊閉,進出複雜。那是新疆安全廳的一個祕密據點。我被帶進其中一個單元。楊科長煞有介事地展開一張紙向我朗讀,宣佈對我實施「監視居住」。我的「居住地」就是那單元房內一個小間,鐵欄封窗,窗上結著厚厚冰花,不透視線。
專業屠夫的宰割
接連幾天的審訊都是在關我那間小屋進行。一天審數次。每次由牆角一台攝像機錄下全過程。初期審訊者是一位哈密安全處的警員,完全用對待罪犯的方式。我和他的對抗逐步升級。隨後他便消失了,再未出現,換上楊科長登場。楊對我解釋因為那警員態度不好被撤換,著實讓我心裡溫暖了一下。但是不久我就明白,先出場的人態度蠻橫是一種有意安排,他們總是有人演紅臉,也有人演黑臉,是規範化的工作程序。
不過在我還不能看懂這種手法的時候,換上溫文有禮的楊科長,讓我感覺遇到了知心人――這就是黑臉先出場的作用。楊科長不是一本正經坐在審訊桌後,而是跟我面對面地促膝聊天(雖然我們的膝離得挺遠,卻給了我那感覺);負責記錄的任警員面目慈祥,笑容可掬;還有開車的祁師傅對我問寒問暖,關照我的生活;女警員小李動輒叫我「王老師」。可是沒過多久,我就知道這種方式比哈密那警員的簡單粗暴更難對付。對黑臉你可以乾脆不理他,你能被激發出鬥志。可現在人家笑盈盈地圍著你聊天,說都是為了你早獲自由,要把問題瞭解清楚,你總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開口說話,他們就會引導你不斷往下說。比如你接觸過甲,他們會問和甲怎麼認識的?如果是通過乙,就會問乙是什麼樣的人,人在哪裡,做什麼工作,然後再問和乙又是怎麼認識的?是通過丙?好,那再開始問丙……這樣的「談話」很快對我形成極大壓力。雖然我可以不說對別人不利的話,我這次接觸的人都屬泛泛,沒有實質內容,所以不會造成任何連累。但即使只說出別人名字,也讓我免不了有出賣的感覺。
除非是什麼話都不說,就像張春橋當年對付審訊那樣 。然而張春橋有那種意志,是因為知道無論怎樣都不可能改變他的下場。我卻是千方百計想把自己解釋清楚。我推翻了原來說的為寫書收集資料,告訴他們真實目的是做新疆問題研究,複印文件不是為了寫書,更不會危害國家安全,相反是要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對方一句話就讓我啞口無言:法律不考慮動機,一個好人殺了壞人照樣是犯法。不管你的動機是什麼,你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規定已經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們也可以幫你解脫――結果怎麼樣,完全取決你的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你產生了對方能幫你解脫的幻想,就不會有勇氣不回答審訊,頂多是不說對他人不利的話。
如果把審訊視為一場鬥智,被審者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審訊者是一個組織體系,有專業知識,有分工合作,掌控一切資訊和資源。而被審者的一切渠道都被封鎖,孤獨無助,任人宰割。對我來講,壓力最大的不是審訊過程中,雖然那時腦筋轉動激烈,事後會感到筋疲力盡,但比起審訊之間的間歇,至少不那麼緊張。審訊間歇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退到另外房間(那房間裡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沒搞清,只聽得到人來人往)。我清楚地知道一群專業屠夫就在離我咫尺的地方,合夥算計如何對我宰割,他們分析前面的審訊情況,尋找其中的破綻,商量對付的策略,擬定下一輪審訊內容,而我卻無法知道他們到底要怎麼做,要達到什麼目的。那時會拼命猜測,卻是絞盡腦汁也沒有可憑藉的資訊。那種大腦陷入盲目空轉的滋味非常難受,就像被蒙著眼睛等待不知何時將從何處下手的刀割一樣。我逐漸開始產生頂不住的感覺,我怎麼能對付得了他們?!他們的職業就是整人,而且他們是一個機關!機關――何等形象和準確的一個詞!
我逐漸發現,他們的審訊手法分不同步驟與層次,經常故意製造一些迷惑,讓你搞不清他們的目的。也許每次問的是些不那麼重要的問題,你覺得回答起來不會對自己和別人有害,然而分開來看無足輕重的問題,合起來卻可能成為一個圈套,讓你不知不覺鑽進套中,而在最終明白的時候,已經無法解脫,因為你在每份審訊記錄上都簽下了「屬實」字樣,在每一頁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們最後把不同的審問記錄組裝在一起,你才會大吃一驚地發現,你承認的東西已經可以解釋為罪行。
儘管我已經告訴了他們我來新疆的目的,但他們並不相信:如果真是做有利於國家的研究,為什麼一開始不說,而是說寫書?何況你研究的結果是什麼?不是也要寫成書嗎?我能感覺他們是在往這樣一條路上引導:我多年一直盜竊國家祕密,炮製著作,換取金錢。我來新疆也是做同樣的事。甚至進一步,何必非以寫書換錢,直接竊取祕密出售豈不是更簡單?
出版《黃禍》和《天葬》兩本書的明鏡出版社,在中國情治部門眼中一直是重點懷疑對象。我和明鏡來往密切,明鏡在海外出版的大量涉及中國黨政軍內幕的出版物,會不會有我提供的情報?這似乎是非常合理的邏輯,甚至可以懷疑,我就是明鏡出版社在國內搜集情報的代理人和傳遞情報的樞紐!
審訊一度集中在我與明鏡出版社的金錢往來上,明顯是想從中發現我靠「出賣情報」得到的收入。這使我擔心陷入一個卡夫卡式的城堡,越來越說不清。我在香港有一個帳號,由明鏡出版社一個朋友與我共同署名並幫我管理,為的是收明鏡付給我的版稅。按規矩銀行每月會寄一份帳單給我。在來新疆的前兩個月,那位朋友的一筆錢被錯打進這個帳號,隨後馬上又被調走。那以後,銀行就不再把每月帳單寄給我,而是寄給明鏡的朋友,因此從我抽屜裡存放的帳單上,能看到有一筆錢在我來新疆前打進,卻看不到又被原封不動調走。安全機構對此能有什麼解釋呢――只能是來新疆刺探情報的經費。而我怎麼說清楚呢?可以作證的因素都在海外,無法得到,他們也不會相信。
審訊又轉向我的花銷。我的回答更是混亂,因為我基本不理財,說起來前後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特別像有鬼。在審訊者看來,我的生活方式需要不小的花費才能支持,如經常旅行,自己開車去西藏等。包括這次來新疆,竟買了一輛新車(好在能查證車屬於阿克)。如果對此解釋不清,至少有「財產來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經是罪名,何況對我,意義不止於經濟,還可以證明我是通過出賣情報換取收入的間諜!
他們真會相信我是間諜嗎?我覺得不應該。我哪有一點間諜模樣呢?就憑我對他們的監控毫無防範,從未有過任何「反偵查」,也足以說明我不可能是搞「祕密活動」。世上有這樣的間諜嗎?我努力和他們溝通,希望打消他們的懷疑,別往那種方向引導案情。
但我逐漸發現,問題其實不在於他們個人認為我是什麼,而在於他們的部門(或上司)需要我是什麼。中國年輕一代的情治人員基本已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對社會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聽你談論民主也會點頭附和。但你如果認為他們因此就會放你一馬,就大錯特錯了。相比之下,他們在這一點可能還不如上一輩。老輩情治人員有意識形態,面對「階級敵人」仇恨滿腔,可一旦瞭解到對方不是壞人,有時還真可能提供一些幫助。年輕一代則完全是技術化的,原則不再是意識形態,是他們的個人利益,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在於是非對錯,而在於他們個人能否完成任務、立功受獎。表面接觸,他們比老一代溫和,容易溝通,總是把自己擺在「吃這碗飯」的位置,說些有人情味的話,說他們是職業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配合」他們完成工作,別砸他們飯碗。然而你一旦被這種話打動,去「配合」他們的「飯碗」,結果一定遭殃。因為他們的「飯碗」是沒有底的,怎麼裝都不會滿。那些提升、加薪、獎金等有關他們個人的利益,取決的不是能否為你解脫冤情,而是能否板上釘釘地把你定為罪犯――不管事實上你是不是。
(摘錄)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