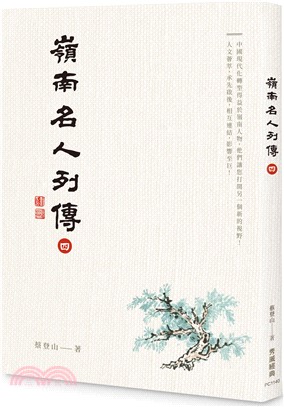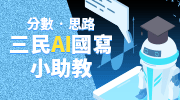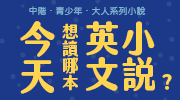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大灣區」其實是嶺南中的精華,是廣東人物的薈萃之所,若再細分,如香山一地,幾乎從晚清以來的洋務人才、革命志士都出現於此,如容閎、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孫中山、唐紹儀等等,而台山人更是非常早期就到美國參加修築鐵路的華工,他們在異國辛苦發展,他們的後代成就非凡,如在美國有漢學丁龍(DeanLung)講座,丁龍最近被證明是台山人馬進隆,DeanLung是「進隆」台山話的英文音譯。甚至連張愛玲的閨蜜鄺文美的父親鄺富灼都曾是美國鐵路的築路工人,後來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回國任上海商務印書館英文部主任,終身推廣英語教育而努力;而好萊塢第一位華裔美國演員黃柳霜、美國電影史上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黃宗霑,都是來自廣東台山人的後代。還有伍連德、溫應星,都來自廣東台山!台山人應該是最早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身為「賣豬仔」的勞工,他們刻苦耐勞,孤身奮鬥於異鄉,終於發光發熱,享譽國際,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華人奮鬥史!
作者簡介
蔡登山
一九五四年生,台灣台南人,淡江中文系畢業。曾任高職教師、電視台編劇,年代及春暉電影公司企劃經理、行銷部總經理。沈迷於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之間,達二十餘年。一九九三年起籌拍【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任製片人及編劇,將史料與影像融於一爐。四年間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該系列紀錄片,並榮獲一九九九年教育文化金鐘獎。一九九八年製作《蔣經國與蔣方良》三小時紀錄長片。二○○二年起製作【大師身影】系列紀錄片,讓晚清以降之思想家----嚴復、梁啟超、魯迅、陳寅恪、胡適、林語堂、錢穆諸大師長留身影。著有:《電影問題.問題電影》、《往事已蒼老》、《人間四月天》、《許我一個未來》、《人間花草太匆匆》、《人間但有真情在》、《傳奇未完----張愛玲》、《百年記憶》、《魯迅愛過的人》。編著有:《柔情裹著我的心----徐志摩的情詩與情話》、《徐志摩情書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
一九五四年生,台灣台南人,淡江中文系畢業。曾任高職教師、電視台編劇,年代及春暉電影公司企劃經理、行銷部總經理。沈迷於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之間,達二十餘年。一九九三年起籌拍【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任製片人及編劇,將史料與影像融於一爐。四年間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該系列紀錄片,並榮獲一九九九年教育文化金鐘獎。一九九八年製作《蔣經國與蔣方良》三小時紀錄長片。二○○二年起製作【大師身影】系列紀錄片,讓晚清以降之思想家----嚴復、梁啟超、魯迅、陳寅恪、胡適、林語堂、錢穆諸大師長留身影。著有:《電影問題.問題電影》、《往事已蒼老》、《人間四月天》、《許我一個未來》、《人間花草太匆匆》、《人間但有真情在》、《傳奇未完----張愛玲》、《百年記憶》、《魯迅愛過的人》。編著有:《柔情裹著我的心----徐志摩的情詩與情話》、《徐志摩情書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
序
月中推出了,我首先寫了幾期,中間有位香港的學者也寫了兩期,之後,就全部落在我一人的身上。我為了克服時間的壓力,就從我最熟悉的人物寫起,由於熟悉因此一週甚至可以寫上兩篇,慢慢就有一些存稿,免得因事忙或生病而脫稿,尤其那段期間還是疫情盛行的時期。記得我那段時間真的顧好身體,不敢出入公共場所,都戴者口罩進到圖書館去查閱資料,查好資料馬上回家寫作。一年後,因為累積存稿不少,於是二○二三年四、五月間,《晶報》「文化灣區」的專欄,一週刊出兩篇,每週二、五刊出,直至二○二三年年底,我總共寫了一○八位文化名人。這是已發表的篇章,之後我又陸續寫了近百篇,尚未發表的,因此本書共有二百零六位名人。
目次
121、陳受頤:被遺忘的中西文化開拓者
122、陳非儂:粤劇名旦‧培育新秀
123、陳垣:「竭澤而漁」的治學精神
124、陳寅恪:「無端來作嶺南人」
125、陳煙橋:中國第一代版畫家
126、陳煥鏞:一生與植物「苦戀」不渝
127、陳瑞鈿:「中國戰鷹」的華裔空戰英雄
128、陳榮捷:東學西漸的開創者
129、陳樂素:宋史專家‧作育英才
130、陳蝶衣:香港寫歌詞的大佬
131、陳樹人:詩情畫意稱雙絕
132、陳融:嶺南舊詩集成者
133、陸丹林:極重史料的名編輯
134、傅秉常:簽署《四國宣言》‧蜚聲國際
135、曾克耑:詩人兼書法家
136、程天固:廣州現代化的開拓者
137、程璧光:海軍大將‧護法身殉
138、馮乃超:默默的播火者
139、馮文鳳:民國第一女子書法家
140、馮平山:「興學育才」
141、馮自由:熟識蕭何擅史才
142、馮耿光:為梅蘭芳仗義紓財
143、馮康侯:篆刻、書法享譽國際
144、黃友棣:「大樂必易」‧百歲音樂家
145、黃文山:首創「文化學」體系
146、黃佐臨:夫唱婦隨‧話劇先鋒
147、黃君璧:春風化雨於藝術教育七十載
148、黃宗霑:享譽國際的華裔電影攝影大師
149、黃柳霜:首位勇闖好萊塢的華裔女星
150、黃苗子:以畫入書‧風格獨特
151、黃般若:師法自然成大器的畫家
152、黃紹芬:電影攝影的一代宗師
153、黃勝:近代香港中文報業先驅
154、黃節:一代詩宗,寂寞身後
155、黃寬:中國留洋學醫第一人
156、新馬師曾:慈善伶王‧德藝雙馨
157、楊秀瓊:南國「美人魚」‧一代泳將
158、楊耐梅:叛逆天使‧民國影后
159、楊善深:從嶺南畫派另闢蹊徑的畫家
160、楚岫雲:集青衣刀馬一身的名旦
122、陳非儂:粤劇名旦‧培育新秀
123、陳垣:「竭澤而漁」的治學精神
124、陳寅恪:「無端來作嶺南人」
125、陳煙橋:中國第一代版畫家
126、陳煥鏞:一生與植物「苦戀」不渝
127、陳瑞鈿:「中國戰鷹」的華裔空戰英雄
128、陳榮捷:東學西漸的開創者
129、陳樂素:宋史專家‧作育英才
130、陳蝶衣:香港寫歌詞的大佬
131、陳樹人:詩情畫意稱雙絕
132、陳融:嶺南舊詩集成者
133、陸丹林:極重史料的名編輯
134、傅秉常:簽署《四國宣言》‧蜚聲國際
135、曾克耑:詩人兼書法家
136、程天固:廣州現代化的開拓者
137、程璧光:海軍大將‧護法身殉
138、馮乃超:默默的播火者
139、馮文鳳:民國第一女子書法家
140、馮平山:「興學育才」
141、馮自由:熟識蕭何擅史才
142、馮耿光:為梅蘭芳仗義紓財
143、馮康侯:篆刻、書法享譽國際
144、黃友棣:「大樂必易」‧百歲音樂家
145、黃文山:首創「文化學」體系
146、黃佐臨:夫唱婦隨‧話劇先鋒
147、黃君璧:春風化雨於藝術教育七十載
148、黃宗霑:享譽國際的華裔電影攝影大師
149、黃柳霜:首位勇闖好萊塢的華裔女星
150、黃苗子:以畫入書‧風格獨特
151、黃般若:師法自然成大器的畫家
152、黃紹芬:電影攝影的一代宗師
153、黃勝:近代香港中文報業先驅
154、黃節:一代詩宗,寂寞身後
155、黃寬:中國留洋學醫第一人
156、新馬師曾:慈善伶王‧德藝雙馨
157、楊秀瓊:南國「美人魚」‧一代泳將
158、楊耐梅:叛逆天使‧民國影后
159、楊善深:從嶺南畫派另闢蹊徑的畫家
160、楚岫雲:集青衣刀馬一身的名旦
書摘/試閱
124、陳寅恪:「無端來作嶺南人」
在中國近現代發展過程中,陳寅恪可說是卓越而有極大貢獻的學者。他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學、和史學方法等領域的傑出成就,可說是為世人所矚目,因此論者以為,「民國以來,堪稱大儒,有『教授之教授』之稱的,陳寅恪是當之無愧的。」而到了九○年代以後,「義寧陳氏」更是為世人所稱頌,他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
陳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義寧,出生於湖南長沙。他是晚清湖南巡撫、維新派政治家陳寶箴之孫,大詩人陳三立(散原)之子。在江西修水桃里鄉的上竹塅,橫亘著一棟雕檐翹角的高大祠堂,就是「陳家大屋」。在「陳家大屋」前有兩件重要的文物:一是陳寶箴在咸豐元年(1851)中了舉人的旗竿石;一是陳三立在光緒十五年(1889)中進士的「旗竿墩」。上面還刻有「光緒己丑年主政陳三立」的字樣。許多傳記作家說陳三立在光緒十二年中進士,是不正確的,當是三年後的光緒十五年,以刻石為鐵證。陳寶箴在位期間,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整飭吏治、興辦實業,並開辦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武備學堂。陳三立亦協助其父親,父子通立合作,使得昔日閉塞落後的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可惜的是僅僅三年,政壇風雲突變,「戊戌變法」失敗,陳寶箴去官,三立亦受到革職處分,遠大的政治抱負盡付東流,父子兩人只能「往往深夜孤燈,相對唏噓,不能自已。」寶箴回到江西南昌「崝廬」,雖自放山水間,仍難掩心中之痛。光緒二十六年(1900)去世,享年七十歲。有關寶箴之死,說法不一:有的說是病死,有的說是慈禧派人賜死的。父親之死,使得陳三立從此不在過問政治,他自號「神州袖手人」。從此中國政壇少了一位智士,但文壇上卻多了一位詩家。他將滿腹幽憂鬱憤盡洩於詩文中,他被稱為「中國詩壇近五百年來之第一人」。他的詩歌代表了「同光體」詩派的最高成就。他成為近代江西詩派的領袖。
陳寅恪因家學淵源,他早年就打下國學基礎,後來留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具備了閱讀英語、法語、德語、日語、蒙古語、藏語、滿語、梵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和希臘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其學習科目,主要為古今各國語文,及中國邊疆民族語文,次及哲學宗教,似亦稍涉社會科學。最使人意想不到的是,陳寅恪負笈四海,學貫東西,卻連一張畢業證書都沒有。一九二五年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薦陳寅恪。曹雲祥問:「陳寅恪是哪國博士?」梁啟超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雲祥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啟超答:「也沒有。」曹雲祥拒絕:「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曹雲祥一聽,十分震驚,這才同意聘請陳寅恪。於是陳寅恪和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被聘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當時好友吳宓住工字廳後院「藤影荷聲之館」,而寅恪亦住工字廳宿舍與吳宓為鄰。陳寅恪首開的課是《佛經翻譯文學》,後又擔任《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文法》等課程。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同為清華「四大導師」的王國維在頤和園排雲殿魚藻軒自沉於昆明湖。他留下遺囑,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之句。對於王國維之死,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認為殉清者。陳寅恪與王國維相處雖短,但情誼卻深。對於王國維之死,他的看法是:「王氏志潔行芳,而所託身之文化傳統既墜,根本失而枝葉亦無所附著,故不得不死。」。他寫下了一篇被人們稱作「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為之辯護。一九二九年六月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決定集資,由梁思成設計,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樹立紀念碑於清華校園工字廳東側,碑文由陳寅恪撰文,陳寅恪在碑文中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體現了他對學術研究的終極關懷。學者夏中義在接受我的訪談就說:「中華民族的人文學術事業真的要後繼有人香火不斷,沒有陳寅恪的這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以自己的生命去踐履這麼一種血色碑銘的人,中華民族的學術事業,是沒有希望的,我們不能渴望或渴求,我們的政治家,我們的民眾,像我們那樣,珍視學術,把學術看的跟我們生命一樣重,這是很難做到的,但是我希望我們大家從陳寅恪的身上得到一種啟示。」
國學研究院僅四年就結束了,陳寅恪轉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並為兩系的研究所開專題課。這時他的研究方向已從佛教史研究,擴大到中古史的研究。陳寅恪常說他「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所謂「不古不今」就是只中古史那一段。從任教清華到「七七事變」,大約十年間,是陳寅恪讀書最勤,研究最力、收穫最多的時期。他發表的五十餘篇的學術論文與序跋。他旁徵博引、環環相扣,紮實的知識,不僅贏得了學子的心,也為其他教授請益的對象。他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當時像吳宓、朱自清、馮友蘭等一流學者,都去聽過他的課。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不久,日軍佔領北平,陳寅恪在料理父喪後,始攜一家倉皇逃離北平。幾經輾轉,艱困,得至長沙。而由於時局變化,清華大學臨時校址又決定遷往雲南。於是陳寅恪帶者全家再往南行。終於在一九三八年春節前抵達香港,夫人唐篔因沿途勞頓,心臟病發不能再走,陳寅恪遂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的西南聯大授課。秋天後,西南聯大又遷昆明,陳寅恪在聯大講授「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佛經翻譯文學」等課。一九三九年陳寅恪在艱苦的環境中,完成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此書從不同角度系統地考察了隋唐制度的淵源和演變,是陳寅恪貫通中古史,以橫向和縱向相結合,研究歷史的極具創見性的豐碩成果。
一九三九年春天英國牛津大學向陳寅恪發出聘書,聘他為該校漢學教授,並授予他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在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年夏天兩次到香港準備赴英,但終未成行。赴英未果,陳寅恪只得暫在香港大學任課,他在港大上學期講「唐史」,下學期講「唐代文學」。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陳寅恪離開港大閒居。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由香港取道廣州灣返回內地,後任教於廣西大學。這時期他寫完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此書集中探討唐代政治制度、統治集團、黨派分野、內政外交等問題。其研究之精細、議論之緊湊而富說服力,實為罕見。戰火南逼,陳寅恪再度挈家逃難,輾轉到成都,任教於燕京大學。這期間他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元白詩箋證稿》。此書以詩文證史,考其古典、求其今典,可謂獨具慧眼,亦為他日治文、史之學者,開闢無數新途徑。陳寅恪家學淵源,堪稱一代詩人,雖然他從不以「詩人」自居,但他的詩卻別具胸懷。一九四五年春,陳寅恪左眼視網膜剝離加重,導致失明,雖住進成都醫院手術。但並未成功,當年秋天又遠赴英倫治療,但因成都手術失敗導致視網膜皺在一起,已經無法弄平了。返國後,他重回到闊別九年的清華園,回想當年的種種,而今目盲身殘,可說是百感交集。但儘管如此,他從不考慮他的身體,他分別在中文系和歷史系開了課。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寅恪和胡適夫婦等二十餘人搭機至南京,又搭火車到上海住俞大綱家。傅斯年一再地發來電報,催促他隨國民黨政府一道到台灣,但陳寅卻婉拒了,他決定留在內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他從上海搭船到廣州,從此他再沒有離開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等人在碼頭上恭候,陳寅恪來到嶺南大學仍任中文系、歷史系合聘的教授,講授的科目有《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課程。而在五○年代陳寅恪也動過重返京城的念頭。從他的詩中,那種客居嶺南的情緒中可明顯看出。一九五三年北京國務院有意請陳寅恪出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並於翌年派曾任陳寅恪在清華的助教汪籤來廣東,但陳寅恪提出『允許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及『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向北京方面關上了大門。學者夏中義說陳寅恪有著一個純粹的、一個剛正的學人的風骨。這個風骨是不會為權力而折斷的,而這種精神,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所最欠缺的。在對〈科學院的答覆〉,陳寅恪把郭沫若比作段文昌,還顯示出兩人的積怨頗深。而後來陳寅恪和郭沫若還在廣州見過面。那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郭沫若在廣州休養,他拜訪中山大學很多有名的教授,如容庚、商承祚,他也去拜訪陳寅恪。陳寅恪以他博大的學者胸懷,接待了郭沫若,後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在談到李白的籍貫的時候,至少是參考陳寅恪的研究成果。
一九五三年九月起,陳寅恪開始撰寫《論再生緣》,陳寅恪認為該書是彈詞中空前之作,作者陳端生更是當時無數女性中思想最卓越之人。在完成《論再生緣》之後,陳寅恪在目盲足臏下,靠著助手黃萱的協助下,查閱一千多種文獻,經十年的歲月,完成了八十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該書可說是陳寅恪一生的嘔心瀝血之作。陳寅恪在早年就已經喜好錢牧齋的詩文,到抗戰時,在昆明得到常熟錢宅紅豆一顆,使他重燃舊思,重讀《錢牧齋集》,尤其對錢牧齋與柳如是的一段情緣,特感興趣,他發憤重新箋注錢柳詩,而在箋注過程,陳寅恪發現柳如是,不僅是後人所視之的名妓,更是一代才女,其才華與性格更不是當時的士大夫所能及的,即令錢牧齋也相較遜色,於是他將原來的書名──《錢柳姻緣詩釋証》改名為《柳如是別傳》,柳如是成為書中的主角。在書中陳寅恪除通解錢、柳詩詞外,並將「孤懷遺恨」的歷史感遇寫出,他對柳如是同情而仰慕,不僅讚美其才藝,更佩服其民族氣節。這也是陳寅恪自己所說的「著書唯剩頌紅妝」。陳寅恪將柳如是視為異代知己,他更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金明館」、「寒柳堂」都可為明證。陳寅恪的考證,素以細密而聞名,他為人所稱道的是「以詩證史」,在《柳如是別傳》中,他更是發揮所長,陳寅恪「以傳修史」,《柳如是別傳》可說是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明清交替之際的經濟、政治、軍事、黨社、宗教、藝術、文字各層面,可說是陳寅恪在明清史的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陳寅恪很欣賞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他希望能寫出像司馬光一樣不朽史書,但戰亂、眼睛失明,使他計劃落空。史學家汪榮祖就說過陳寅恪:「他佩服《資治通鑑》,它是一個大敘述,把這個歷史的事實敘述出來。因為他有這麼好的一些發現,假如再經過一些敘述,那是一個很偉大的作品,可以媲美英國大歷史學家《羅馬衰亡史》大部頭的著作。這個當然有受限於時代這個戰亂等等。後來因為他晚年身體的原因,他眼睛瞎了,在抗戰末期,後來在五○年代又把腳跌斷了,這種身體上的痛苦當然也限制了他的撰述。」
一九六四年陳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到廣州探視他,陳寅恪將他編定的書稿,託付給蔣天樞,陳寅恪還特定為這次相見寫下了〈贈蔣秉南序〉一文,論者認為那是陳寅恪的最後遺言,尤其是「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更是陳寅恪一生的寫照。陳寅恪晚年開始撰寫自傳性的《寒柳堂記夢》,到一九六六年完成七章,那是一段血淚凝成的文字,他力圖為世人留下真實的歷史。但文革風暴旋起,文稿至今下落不明。文革初起,紅衛兵衝入大學內,趕走陳寅恪的得力助手黃萱與護士,目喪足臏的陳寅恪,只得在夫人唐篔的扶持下苟活,後來革命小將不斷來抄家,陳宅已蕩然無存。一九六九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一號已住了十六年的家。同年十月七月陳寅恪在心力衰竭及腸梗塞中,走完他七十九歲的人生旅程。四十五天後,他的夫人唐篔亦追隨他於九泉。人們再也看不到康樂園那棟紅磚小樓前,陳寅恪夫婦沿著白色水泥路,蹣跚地走來的身影。陳寅恪的故去,也給歷史文化的長廊,留下巨大的空寂。直到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才總算聽到他的空谷足音。
陳寅恪作為一個學問家,他的視野是國際性的。學者葛兆光就說:「從學問家的角度而言,陳寅恪他的意義在於,真正地使中國學術有國際視野。他從剛回國的那一段時間,他實際上是和國際學術界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視野開闊,方法多樣,觀念很新。他有一個最大的長處就是他非常紮實,文獻資料非常清楚,而且他絕不以那個罕見的少見的東西來炫耀。」陳寅恪是在西學東漸,活躍於後五四時代的學者。他既有乾嘉樸學的深厚功力,又具有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化對話的深湛素養。綜觀陳寅恪的一生,有令人羨慕的才華與家學,也有令人扼腕的失明與臏足。但他的學問與人品,始終為人所敬仰也並將成為後世的典型。
一九四九年一月陳寅恪寫下〈己丑元旦作時居廣州康樂九家村〉七律一首:
無端來作嶺南人,朱橘黄蕉鬥歲新。
食蛤那知今日事,買花彌惜去年春。
避秦心苦誰同喻,走越裝輕任更貧。
獨臥荒村驚節物,可憐空負渡江身。
詩間可見「做嶺南人」的欣喜,但也有難以排解的悵惘,如陰影無法拂去。此年陳寅恪已經六十歲。在嶺南他度過最後的二十年,在他去世的幾年前,陳寅恪已為終身伴侶唐篔擬定了一幅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一字一句撕心裂肺,詠嘆出真正的絕唱。
在中國近現代發展過程中,陳寅恪可說是卓越而有極大貢獻的學者。他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學、和史學方法等領域的傑出成就,可說是為世人所矚目,因此論者以為,「民國以來,堪稱大儒,有『教授之教授』之稱的,陳寅恪是當之無愧的。」而到了九○年代以後,「義寧陳氏」更是為世人所稱頌,他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
陳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義寧,出生於湖南長沙。他是晚清湖南巡撫、維新派政治家陳寶箴之孫,大詩人陳三立(散原)之子。在江西修水桃里鄉的上竹塅,橫亘著一棟雕檐翹角的高大祠堂,就是「陳家大屋」。在「陳家大屋」前有兩件重要的文物:一是陳寶箴在咸豐元年(1851)中了舉人的旗竿石;一是陳三立在光緒十五年(1889)中進士的「旗竿墩」。上面還刻有「光緒己丑年主政陳三立」的字樣。許多傳記作家說陳三立在光緒十二年中進士,是不正確的,當是三年後的光緒十五年,以刻石為鐵證。陳寶箴在位期間,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整飭吏治、興辦實業,並開辦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武備學堂。陳三立亦協助其父親,父子通立合作,使得昔日閉塞落後的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可惜的是僅僅三年,政壇風雲突變,「戊戌變法」失敗,陳寶箴去官,三立亦受到革職處分,遠大的政治抱負盡付東流,父子兩人只能「往往深夜孤燈,相對唏噓,不能自已。」寶箴回到江西南昌「崝廬」,雖自放山水間,仍難掩心中之痛。光緒二十六年(1900)去世,享年七十歲。有關寶箴之死,說法不一:有的說是病死,有的說是慈禧派人賜死的。父親之死,使得陳三立從此不在過問政治,他自號「神州袖手人」。從此中國政壇少了一位智士,但文壇上卻多了一位詩家。他將滿腹幽憂鬱憤盡洩於詩文中,他被稱為「中國詩壇近五百年來之第一人」。他的詩歌代表了「同光體」詩派的最高成就。他成為近代江西詩派的領袖。
陳寅恪因家學淵源,他早年就打下國學基礎,後來留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具備了閱讀英語、法語、德語、日語、蒙古語、藏語、滿語、梵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和希臘語等十多種語言的能力,其學習科目,主要為古今各國語文,及中國邊疆民族語文,次及哲學宗教,似亦稍涉社會科學。最使人意想不到的是,陳寅恪負笈四海,學貫東西,卻連一張畢業證書都沒有。一九二五年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薦陳寅恪。曹雲祥問:「陳寅恪是哪國博士?」梁啟超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雲祥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啟超答:「也沒有。」曹雲祥拒絕:「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曹雲祥一聽,十分震驚,這才同意聘請陳寅恪。於是陳寅恪和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被聘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當時好友吳宓住工字廳後院「藤影荷聲之館」,而寅恪亦住工字廳宿舍與吳宓為鄰。陳寅恪首開的課是《佛經翻譯文學》,後又擔任《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文法》等課程。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同為清華「四大導師」的王國維在頤和園排雲殿魚藻軒自沉於昆明湖。他留下遺囑,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之句。對於王國維之死,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認為殉清者。陳寅恪與王國維相處雖短,但情誼卻深。對於王國維之死,他的看法是:「王氏志潔行芳,而所託身之文化傳統既墜,根本失而枝葉亦無所附著,故不得不死。」。他寫下了一篇被人們稱作「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為之辯護。一九二九年六月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決定集資,由梁思成設計,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樹立紀念碑於清華校園工字廳東側,碑文由陳寅恪撰文,陳寅恪在碑文中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體現了他對學術研究的終極關懷。學者夏中義在接受我的訪談就說:「中華民族的人文學術事業真的要後繼有人香火不斷,沒有陳寅恪的這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以自己的生命去踐履這麼一種血色碑銘的人,中華民族的學術事業,是沒有希望的,我們不能渴望或渴求,我們的政治家,我們的民眾,像我們那樣,珍視學術,把學術看的跟我們生命一樣重,這是很難做到的,但是我希望我們大家從陳寅恪的身上得到一種啟示。」
國學研究院僅四年就結束了,陳寅恪轉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並為兩系的研究所開專題課。這時他的研究方向已從佛教史研究,擴大到中古史的研究。陳寅恪常說他「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所謂「不古不今」就是只中古史那一段。從任教清華到「七七事變」,大約十年間,是陳寅恪讀書最勤,研究最力、收穫最多的時期。他發表的五十餘篇的學術論文與序跋。他旁徵博引、環環相扣,紮實的知識,不僅贏得了學子的心,也為其他教授請益的對象。他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當時像吳宓、朱自清、馮友蘭等一流學者,都去聽過他的課。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不久,日軍佔領北平,陳寅恪在料理父喪後,始攜一家倉皇逃離北平。幾經輾轉,艱困,得至長沙。而由於時局變化,清華大學臨時校址又決定遷往雲南。於是陳寅恪帶者全家再往南行。終於在一九三八年春節前抵達香港,夫人唐篔因沿途勞頓,心臟病發不能再走,陳寅恪遂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的西南聯大授課。秋天後,西南聯大又遷昆明,陳寅恪在聯大講授「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佛經翻譯文學」等課。一九三九年陳寅恪在艱苦的環境中,完成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此書從不同角度系統地考察了隋唐制度的淵源和演變,是陳寅恪貫通中古史,以橫向和縱向相結合,研究歷史的極具創見性的豐碩成果。
一九三九年春天英國牛津大學向陳寅恪發出聘書,聘他為該校漢學教授,並授予他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在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年夏天兩次到香港準備赴英,但終未成行。赴英未果,陳寅恪只得暫在香港大學任課,他在港大上學期講「唐史」,下學期講「唐代文學」。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陳寅恪離開港大閒居。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由香港取道廣州灣返回內地,後任教於廣西大學。這時期他寫完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此書集中探討唐代政治制度、統治集團、黨派分野、內政外交等問題。其研究之精細、議論之緊湊而富說服力,實為罕見。戰火南逼,陳寅恪再度挈家逃難,輾轉到成都,任教於燕京大學。這期間他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元白詩箋證稿》。此書以詩文證史,考其古典、求其今典,可謂獨具慧眼,亦為他日治文、史之學者,開闢無數新途徑。陳寅恪家學淵源,堪稱一代詩人,雖然他從不以「詩人」自居,但他的詩卻別具胸懷。一九四五年春,陳寅恪左眼視網膜剝離加重,導致失明,雖住進成都醫院手術。但並未成功,當年秋天又遠赴英倫治療,但因成都手術失敗導致視網膜皺在一起,已經無法弄平了。返國後,他重回到闊別九年的清華園,回想當年的種種,而今目盲身殘,可說是百感交集。但儘管如此,他從不考慮他的身體,他分別在中文系和歷史系開了課。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寅恪和胡適夫婦等二十餘人搭機至南京,又搭火車到上海住俞大綱家。傅斯年一再地發來電報,催促他隨國民黨政府一道到台灣,但陳寅卻婉拒了,他決定留在內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他從上海搭船到廣州,從此他再沒有離開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等人在碼頭上恭候,陳寅恪來到嶺南大學仍任中文系、歷史系合聘的教授,講授的科目有《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課程。而在五○年代陳寅恪也動過重返京城的念頭。從他的詩中,那種客居嶺南的情緒中可明顯看出。一九五三年北京國務院有意請陳寅恪出任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並於翌年派曾任陳寅恪在清華的助教汪籤來廣東,但陳寅恪提出『允許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及『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向北京方面關上了大門。學者夏中義說陳寅恪有著一個純粹的、一個剛正的學人的風骨。這個風骨是不會為權力而折斷的,而這種精神,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所最欠缺的。在對〈科學院的答覆〉,陳寅恪把郭沫若比作段文昌,還顯示出兩人的積怨頗深。而後來陳寅恪和郭沫若還在廣州見過面。那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郭沫若在廣州休養,他拜訪中山大學很多有名的教授,如容庚、商承祚,他也去拜訪陳寅恪。陳寅恪以他博大的學者胸懷,接待了郭沫若,後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在談到李白的籍貫的時候,至少是參考陳寅恪的研究成果。
一九五三年九月起,陳寅恪開始撰寫《論再生緣》,陳寅恪認為該書是彈詞中空前之作,作者陳端生更是當時無數女性中思想最卓越之人。在完成《論再生緣》之後,陳寅恪在目盲足臏下,靠著助手黃萱的協助下,查閱一千多種文獻,經十年的歲月,完成了八十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該書可說是陳寅恪一生的嘔心瀝血之作。陳寅恪在早年就已經喜好錢牧齋的詩文,到抗戰時,在昆明得到常熟錢宅紅豆一顆,使他重燃舊思,重讀《錢牧齋集》,尤其對錢牧齋與柳如是的一段情緣,特感興趣,他發憤重新箋注錢柳詩,而在箋注過程,陳寅恪發現柳如是,不僅是後人所視之的名妓,更是一代才女,其才華與性格更不是當時的士大夫所能及的,即令錢牧齋也相較遜色,於是他將原來的書名──《錢柳姻緣詩釋証》改名為《柳如是別傳》,柳如是成為書中的主角。在書中陳寅恪除通解錢、柳詩詞外,並將「孤懷遺恨」的歷史感遇寫出,他對柳如是同情而仰慕,不僅讚美其才藝,更佩服其民族氣節。這也是陳寅恪自己所說的「著書唯剩頌紅妝」。陳寅恪將柳如是視為異代知己,他更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金明館」、「寒柳堂」都可為明證。陳寅恪的考證,素以細密而聞名,他為人所稱道的是「以詩證史」,在《柳如是別傳》中,他更是發揮所長,陳寅恪「以傳修史」,《柳如是別傳》可說是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明清交替之際的經濟、政治、軍事、黨社、宗教、藝術、文字各層面,可說是陳寅恪在明清史的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陳寅恪很欣賞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他希望能寫出像司馬光一樣不朽史書,但戰亂、眼睛失明,使他計劃落空。史學家汪榮祖就說過陳寅恪:「他佩服《資治通鑑》,它是一個大敘述,把這個歷史的事實敘述出來。因為他有這麼好的一些發現,假如再經過一些敘述,那是一個很偉大的作品,可以媲美英國大歷史學家《羅馬衰亡史》大部頭的著作。這個當然有受限於時代這個戰亂等等。後來因為他晚年身體的原因,他眼睛瞎了,在抗戰末期,後來在五○年代又把腳跌斷了,這種身體上的痛苦當然也限制了他的撰述。」
一九六四年陳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到廣州探視他,陳寅恪將他編定的書稿,託付給蔣天樞,陳寅恪還特定為這次相見寫下了〈贈蔣秉南序〉一文,論者認為那是陳寅恪的最後遺言,尤其是「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更是陳寅恪一生的寫照。陳寅恪晚年開始撰寫自傳性的《寒柳堂記夢》,到一九六六年完成七章,那是一段血淚凝成的文字,他力圖為世人留下真實的歷史。但文革風暴旋起,文稿至今下落不明。文革初起,紅衛兵衝入大學內,趕走陳寅恪的得力助手黃萱與護士,目喪足臏的陳寅恪,只得在夫人唐篔的扶持下苟活,後來革命小將不斷來抄家,陳宅已蕩然無存。一九六九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一號已住了十六年的家。同年十月七月陳寅恪在心力衰竭及腸梗塞中,走完他七十九歲的人生旅程。四十五天後,他的夫人唐篔亦追隨他於九泉。人們再也看不到康樂園那棟紅磚小樓前,陳寅恪夫婦沿著白色水泥路,蹣跚地走來的身影。陳寅恪的故去,也給歷史文化的長廊,留下巨大的空寂。直到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才總算聽到他的空谷足音。
陳寅恪作為一個學問家,他的視野是國際性的。學者葛兆光就說:「從學問家的角度而言,陳寅恪他的意義在於,真正地使中國學術有國際視野。他從剛回國的那一段時間,他實際上是和國際學術界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視野開闊,方法多樣,觀念很新。他有一個最大的長處就是他非常紮實,文獻資料非常清楚,而且他絕不以那個罕見的少見的東西來炫耀。」陳寅恪是在西學東漸,活躍於後五四時代的學者。他既有乾嘉樸學的深厚功力,又具有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化對話的深湛素養。綜觀陳寅恪的一生,有令人羨慕的才華與家學,也有令人扼腕的失明與臏足。但他的學問與人品,始終為人所敬仰也並將成為後世的典型。
一九四九年一月陳寅恪寫下〈己丑元旦作時居廣州康樂九家村〉七律一首:
無端來作嶺南人,朱橘黄蕉鬥歲新。
食蛤那知今日事,買花彌惜去年春。
避秦心苦誰同喻,走越裝輕任更貧。
獨臥荒村驚節物,可憐空負渡江身。
詩間可見「做嶺南人」的欣喜,但也有難以排解的悵惘,如陰影無法拂去。此年陳寅恪已經六十歲。在嶺南他度過最後的二十年,在他去世的幾年前,陳寅恪已為終身伴侶唐篔擬定了一幅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一字一句撕心裂肺,詠嘆出真正的絕唱。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